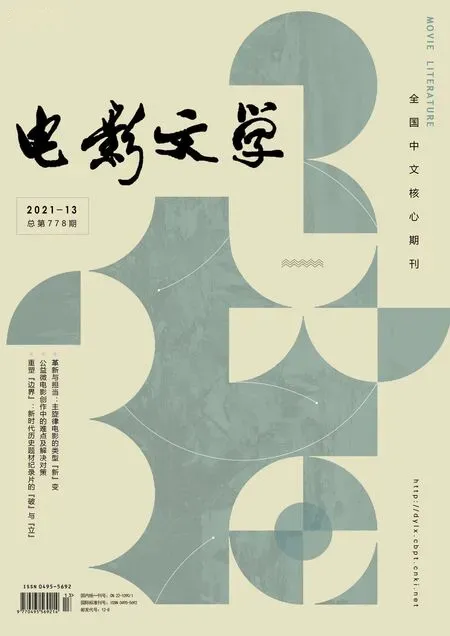《再會吧,上海》與在滬朝鮮影人鄭基鐸
武彥清(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北京 100082)
日占朝鮮時期流亡上海的影人身處中韓兩國電影歷史的邊緣,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關注。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鄭基鐸、鄭一松、全昌根等人從日占的故土前往上海從事電影活動。其中鄭基鐸從1928—1934年先后進入大中華百合公司和聯華公司第二制片廠與陸潔、朱瘦菊、周詩穆、湯天繡、阮玲玉、鄭君里等上海電影人合作,導演九部并參演三部影片。關于流亡影人鄭基鐸在上海的電影活動已有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從其僅存的影片《再會吧,上海》來看,影片呈現的異質之處與鄭基鐸創作母題、與其個人經歷、與1933—1934年聯華公司現實狀況的相關性等問題還未得到進一步的關注。本文以《再會吧,上海》為切口探索以上問題,以期作為已有研究的補充。
《再會吧,上海》由聯華影片公司出品,鄭基鐸導演,阮玲玉主演,于1934年11月2日在金城大戲院開映。主要講述鄉村女教員白露(阮玲玉飾演)因戰亂逃難上海,途中經歷船難與船上大副(張翼飾演)相識相知,并相約再次駛來時相見。白露到上海后寄居姑母王家,此后前往王家貴客吳醫學博士(何非光飾演)的醫院治病時被醫生趁機玷污。白露心懷被玷污之恥與無法相見愛人之悲,遂離開王家獨立生活。獨居后產下一子,經人介紹成為舞女維持生計。然而白露始終在被辱陰影和思念遠方愛人之間飽受折磨,最終無奈離開上海。現存82分鐘的殘片缺失開頭部分,殘片開始于白露已寄居在王太太家的一場舞會,上流人士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白露在房間獨自陷入航船上的美好回憶。影片在大副看到報紙上白露離開的消息,坐在建筑工地若有所思的中近景中結束。
此外還須說明的是,現存殘片為當年上映后經電檢會再度檢查刪減后的版本。因影片塑造了一個道德敗壞的醫生形象,上映不久上海醫師公會刊登公文訴訟其誹謗醫師,公文寫道:“該片內容竟侮辱醫師人格道德,卑鄙極矣。實令人發指,嗟夫我磊落光明之新醫界,無故遭此誹謗摧殘。”經由聯華公司、電影檢查會、醫師公會三方共同商討,刪減部分內容后再行公映。從醫師公會的公文來看,片中醫生吳光暉得知白露到來之前已心懷不軌,在電話里編造謊言欺騙情人,隨后為白露治療時使用注射器致其昏迷并實施迫害。根據現存影片來看,影片被刪減的正是吳光暉欺騙情人和注射實施迫害的場景,僅留白露進入病房和黑暗中蘇醒的鏡頭。片中這一鏡頭頗具表現性,極強的亮暗對比把病房暗化,僅留一束正面的光打在白露眼睛上,配合大特寫對準她恍惚的眼神,創作者利用場景氛圍的營造彌補了被刪部分的敘事內容。

《再會吧,上海》被刪減鏡頭之一
一、時代的“逃避者”
《再會吧,上海》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電影中具有其異質之處,全片以白露“進城—寄居—受害—出走—獨居—成為舞女和母親—離滬”為敘事線推進,人物受欺后喪失主動性,逃避是其唯一的選擇。創作者未像同時期大多影片滲入鮮明觀念或指明前進道路,使這部影片整體上彌漫著愁緒和模糊感。此外,影片以城市的浮華和黑暗為現實背景,但更側重表現女性人物的多重身份和心理狀態,突出塑造人物的多重身份和由此帶來的矛盾心理,表現人物心事重重、黯然神傷、躊躇不決的心理狀態,讓影片由表現現實升級為表現心理,這在中國早期電影中并不多見。
首先來看這部影片如何塑造集多重身份于一體的女性形象。影片中白露有五重身份,其一是城市寄居者,白露逃難至上海寄居于王家,影片多次表現其與城市上層生活格格不入。王家舉辦舞會時影片將屋內白露的愁容和大副的面部疊印,與屋外男女跳舞畫面交叉對比,同時交代出她的第二個身份即向往純真愛情的少女。其三是被男性壓迫的女性,白露被吳光暉欺辱一場使用明暗對比強烈的光影把醫生巨大的影子投射于墻面,以暗示白露的遭遇,她成為那個年代的女性弱者之一。這一身份之于白露是夢魘般的存在,醫生的可怖形象此后在白露內心多次復現,也是觸發她做出最終選擇的導火索,對呈現人物心理狀態發揮重要作用。其四是舞女,白露獨居后因無法交租被迫成為舞女,片中用幾個舞場交際鏡頭說明其作為舞女的社會身份和地位。其五是母親,白露出走后誕下吳光暉的孩子,因為是恥辱之果,所以她的母親身份總是不夠純粹,天然的母愛夾雜著悔恨和痛苦。
人物的五個身份隨情節推進和磨難疊加逐漸建立并存,影片后半部分設置五個身份共存并互換的一場戲,將多重身份造成的內心矛盾外化,進而使影片僅利用畫面表現力和演員表演就深入人物內心世界,此段也是片中阮玲玉表演最精彩的部分。這一段主要使用固定機位的搖鏡頭用少量鏡頭以簡馭繁,將睹物思人的表達思路結合疊印畫面充分實現心理現實的表達。具體處理為:做完舞女的白露深夜回到租房,她憐惜地抱起床上的孩子又狠心放下,轉頭看向桌上的花盤(大副的禮物),大副的面孔與花盤疊印,她的表情有所緩和,再次充滿愛意地看向孩子。同一鏡頭內白露再次回頭看向花盤,畫面疊印吳光暉兇暴的面孔,白露隨即愁容滿面。同時她意識到作為母親的責任,再次抱起床上的孩子。通過兩次看向花盤完成幸福和痛苦兩種狀態的轉變,短短一部電影白露既是城市的寄居者、舞女、純情少女、被欺的弱者又是一個擁有母性的母親,五個身份經阮玲玉富有層次和多變的表演恰如其分地共存并轉換。

分別為白露的五個身份:寄居者、憧憬愛情的少女、被欺女性、舞女、母親
這五種身份在當時的社會和電影中并不少見,每個身份都具有時代意義。特殊之處在于,導演并非僅僅意在把這樣的典型人物搬入電影抨擊現實,他把人物復雜的心理狀態逐漸推至頂點,由揭露城市底層生活苦難進入“人”的內心,關注現實環境帶給人情緒和情感上的困境。
影片的另一特殊之處在于人物的行動過于被動,片中兒子生病前來醫治的醫生恰巧是吳光暉,白露再度憶起慘痛經歷。夢魘進入現實的情緒高潮之時,人物沒有任何激烈的外部舉動,僅僅是微露苦痛表情無可奈何地看著吳光暉揚長而去。人物的內心矛盾疊加至頂點之時,白露下定決心離開(出逃)上海,這是人物面對幾次磨難主動采取的唯一行動。
《再會吧,上海》上映同期,被稱為中國第一部航空戰事巨片的《鐵鳥》和打破國片連映紀錄的《漁光曲》在金城大戲院公映。聯華公司正在攝制朱石麟的《青春》、孫瑜的《大路》、姜起鳳的《骨肉之恩》。聯華之外,明星公司主要影片有《到西北去》(程步高)、《再生花》(鄭正秋)、《婦道》(陳鏗然)、《青春線》(姚蘇鳳);藝華公司主要攝制《女人》(史東山)、《黃金時代》(卜萬蒼)、《飛花村》(鄭應時)、《人間仙子》(但杜宇);天一公司攝制《歌臺艷史》(薛覺先)、《春宵曲》(文逸民)等。可見,當時的電影以新舊觀念、城鄉對比、社會苦難、進步反抗等敘事主題為主,反思傳統、追求進步以及迎合官方觀念成為電影創作和批評的重要準則,《再會吧,上海》的異態和脫節之處在其中就更為明顯。
結合上文所述的異態,具體至與個別影片的對比也能發現其不同之處。與《再會吧,上海》部分敘事元素相似的影片有兩類,一類是20世紀30年代以女性為主角表現現實苦難的影片,此類影片或多或少都會加入反抗和前進的行動。比如《新女性》中“不倒翁”的象征和片尾人物面向鏡頭無聲吶喊“我要活”;又如《神女》結尾處人物在監獄寄托對孩子未來的希望;《母性之光》里飽受丈夫欺壓的昔日女歌星重返上海從事兒童教育工作等。
另一類是人物從農村逃難上海,通過都市和鄉村的諸多對比來昭示都市之險惡。比如《天明》中黎莉莉飾演的鄉村女性進入都市成為妓女,突出都市文化和革命意識交織下的人物變化;《姊妹花》更直接地讓胡蝶一人分飾兩角,對比鄉村和都市兩姐妹的性格和生活習慣。此外,也有一些影片利用都市和鄉村階級身份差異批駁封建思想,比如《野玫瑰》中黎莉莉飾演的鄉村女孩進入都市假扮富人引發“失態”行為,與她從前的樂天派性格形成沖突,創作者借此傳達鄉村的淳樸和活力并巧妙地結合進步性完成時代表達。再如《桃花泣血記》中鄉村女孩琳姑不被城里男友的母親接受,返鄉后郁郁而終,以此指摘封建婚戀觀和門第觀。
《再會吧,上海》與這兩類影片有相似的情節元素,但內在有很大不同。它雖以都市的險惡環境為背景,但全片僅使用舞場交際的幾個鏡頭來象征城市生活,側重表露人物內心的不安與不適。當時的觀眾也因此批評影片:“連別的影片所常用的對照的手法,《再會吧,上海》里都沒有運用,白露離開了姑母家以后的生活描寫只占了很短一段膠片,使觀眾感得悲哀的成分非常不夠,這樣又哪里談得到使觀眾感動、同情,或者得到一個對于現社會的深刻的啟示呢?”“編劇對于所謂上流社會的淫逸生活的暴露太淺薄了……如能用其他都市許多的黑暗素材以取代。不是尤可使觀眾得到一些真實感嗎?”也有評論從進步性的角度批評它是“感傷主義的說教”,“它們的價值,因了意識的畸形而完全喪失,嚴格說來,這類影片就是亡國的預兆”。可以看出當時的觀眾和要求進步的評論者對《再會吧,上海》這種刻畫人物幽怨彷徨心理的影片有所不滿,其哀訴的方式也不符合彼時要求電影承載進步性的觀念。
《再會吧,上海》是導演鄭基鐸(又名鄭云波)在上海拍攝的最后一部作品。由于鄭基鐸的特殊經歷和流亡影人身份,銀幕之外的他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時代“逃避者”。

鄭基鐸
1903年鄭基鐸生于朝鮮平壤,1910年8月22日,朝鮮第三代統監寺內正毅和李完用簽署《關于韓國合并》條約,8月29日大韓帝國正式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鄭基鐸進入光成高等學校,同年因參加三一獨立運動被退學。1920年進入漢城培才學校,1922年畢業前往日本進入東京音樂研究院。1924年前后他在中國居住一年,隨后返國出演李慶孫導演的《拓荒者》(1925),以演員身份出道。次年加入李慶孫主導成立的“雞林電影協會”,主演《長恨夢》(1926)。同年,鄭基鐸在平壤成立鄭基鐸制片公司攝制《鳳凰冠》(1926),因受日本高壓控制一直慘淡經營。
1926年7月5日,日本政府制定“活動寫真和電影檢閱”規約,將電影審查系統化。日占朝鮮時期對電影的嚴格管控和束縛,促使鄭基鐸逃往另一個“自由天地”,成為流亡影人。
二、短暫落腳的鄉愁:鄭基鐸創作的核心母題
身處異鄉之時,回不去的故鄉才更成為魂牽夢縈之地。鄭基鐸無力反抗的憤懣、無法自由創作的苦悶以及對故鄉復雜的情感在異國化為難言的愁緒,經過層層喬裝短暫安放在他的電影里。
綜觀鄭基鐸在上海的電影創作,無論是迎合電影商業潮流的武俠片〔《火窟鋼刀》(1929)、《女海盜》(1929)、《黑衣騎士》(1929)〕,通俗愛情和復古倫理片〔《三雄奪美》(1928)、《情欲寶鑒》(1929)、《銀幕之花》(1929)〕,還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影片〔《光明之路》(1934)、《再會吧,上海》(1934)〕都有著相似的創作元素和核心母題,即侵占、破壞、侮辱、復仇情節與東方共通的情感交織,暗示被侵略和壓迫的日占朝鮮。
比如他在上海的首部作品《愛國魂》,稍加比對即可看出此片由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事件改編而成。片中的魏國政客鄭吉文暗指懷有政治野心的伊藤博文,見鄰國黎國政治疲軟便與奸臣黎勇通奸,黎勇即指與伊藤博文合謀的韓國大臣李完用。影片以黎國愛國志士仲權刺殺鄭吉文為主線,講述愛國者幾經波折最終英勇就義的故事。片中的刺殺暗指日占朝鮮時期志士的反抗行動,人物臨絞前的“容色不變,慷慨就義”更是對安重根本人英勇行為的再現。1926年鄭基鐸剛到上海,“因見大中華百合公司規模宏大,設備完全,乃與王元龍君接洽,擬在該公司與王合攝一片,以留此次來滬之紀念”。《愛國魂》是鄭基鐸與上海影人首次合作的重要之作,他選擇把朝鮮英雄事件嫁接于中國古代背景來借古喻今,通過電影創作在他鄉悲故國。
還如《火窟鋼刀》和《女海盜》皆設置恬靜村莊被外來者入侵破壞的情節。前者惡霸闖入殘害當地民眾,孝子奮起報殺父之仇,后者女海盜及同黨入侵破壞世外桃源香島,孝子冒險駕舟獨闖巢穴以報血仇,可以看出其“外敵入侵—破壞—復仇”式的核心敘事。即使是《三雄奪美》三男爭奪一女的通俗愛情片也指涉日占朝鮮時期的社會事件。片中男大學生鄭大鎬就讀“三一大學”是三一足球隊的主將,富家男王喜萬攜暴徒強搶金瑪麗,鄭大鎬與其對抗被王喜萬嫁禍等情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919年鄭基鐸親自參與的三一獨立運動。
可以看出鄭基鐸作為朝鮮亡國的見證者,他的經歷和體驗成為他不斷反復的創作母題。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電影環境中,把自己的民族情感和愁緒附著在東方情感互通的家庭倫理、通俗愛情、愛國志氣等框架之中,借此隱射他作為流亡者和逃避者的復雜心境。
在此基礎上,《再會吧,上海》也更像是折射鄭基鐸個人心境的作品,片中人物多重身份暗含鄭基鐸作為流亡者的難言之隱。白露因鄉村兵災匪禍逃難上海委身寄居于王太太家,內心牽念的大副始終處于遙不可及、無法相遇的“遠方”。影片之外逃亡上海的鄭基鐸同樣是寄居者,他作為流亡者的“難處不只是在于被迫離開家鄉,而是在生活里許多東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社會環境和語言等諸多不同讓他時刻牽掛可望而不可即的故鄉,他的鄉愁就寄托在白露對大副反復牽念的疊印畫面里。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白露飽受思念和欺辱之苦卻從不采取反抗行動,聯系鄭基鐸本人多次反抗被鎮壓的經歷,反抗之于他早已是無力的空想,這與中國電影人通過電影提供力量振奮國人的觀念自有不同。
此外,《再會吧,上海》仍是他創作母題的再次重復,影片反復出現吳醫生的可怖面孔表明其“入侵強占”對白露造成的傷害,身體“入侵”等同于日本對殖民地政治經濟文化的入侵,暗指日治朝鮮時期民族共同的“夢魘”。吳醫生的妻子這一女性形象掌握金錢卻無實權,有如無實權的民族無法逃脫殖民者的壓榨。白露多重身份共存的一場戲,憶起所愛之人(故鄉)隨后又浮現所恨之人(殖民者),兩者揮之不去地交織正像流亡者遠走他鄉的復雜心境。鄭基鐸和片中白露巧妙地實現心理對位,他們作為寄居的人“永遠背井離鄉,一直與環境沖突,對于過去難以釋懷,對于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而他們無論流落何處,無法解決的仍是離鄉的失落、無盡的回憶、難融的新環境和無法歸去的苦悶。
三、若即若離:再會吧,上海
流亡者的心境不僅滲透于銀幕之內,也延伸至銀幕之外鄭基鐸與上海電影界的若即若離。
鄭基鐸東游日本后于1933年7月再次抵滬,入聯華二廠開始籌備拍攝《出路》。他再次投身上海電影界進入聯華二廠的原因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1931年鄭基鐸離開中國前曾在大中華百合公司任導演,1931年大中華百合改組為聯華二廠陸潔仍任廠長,再次抵滬順理成章投靠舊友;二是與彼時聯華的發展情況息息相關;三是鄭基鐸電影的主題與現實意義與聯華公司的核心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契合。
鄭基鐸進入聯華公司的1933年,聯華并非如電影史所載的鼎立于上海電影界那般外表光鮮。實際上1933年是聯華生產電影最少的一年,并且聯華公司的確存在較大的經濟問題。從外部來看,戰爭環境和社會經濟低迷是整個社會面臨的共同危機,也直接導致聯華多個廠被毀,如北平的聯華五廠因九一八停辦,上海的聯華四廠毀于淞滬之戰,四川的聯華七廠因川亂停辦。此外,1933年前后外片在中國電影市場仍占絕對優勢地位,“派拉蒙、米高梅、環球公司都有駐滬經理處,和大戲院訂了初映的優先權”。1933年輸入的外片中美片占大部分,多達七百八十部,外片輸入數量是國片出品總數的三倍之多。國片受外片擠壓生存空間很小,在電影公司和社會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更大的原因來自聯華內部,首先是聯華的分廠制度不完善,羅明佑組織聯華公司后相繼成立了七個制片廠,效仿好萊塢的獨立制片但并未像好萊塢規定每個廠的拍片數目、拍片時間和預算等。造成“制片人和導演們皆取‘在精不在多’的政策。所謂‘在精’,就是多花本錢,拖長時間,因為資本是公司出,名譽是自己得。故此,每一導演,每年最多出一兩部,有位導演甚至兩年始完成一部。”聯華公司的影片清新了電影界,但其生產以“出片太緩開支過巨,入不敷出”而聞名。其次,老板羅明佑未針對聯華已有的具體問題對癥下藥,或許是因其始終把目光集中在對中國電影事業更遠大的志向上。從相關史料可以看出,建造電影城是羅明佑最想完成的電影事業之一,在聯華公司建立之初他已提出此想法,要將制作、發行和放映一體化。1934年再次著文希望在香港九龍建立“東方荷里活”,指出香港的自然地理優勢既利于拍攝又便于經營國際市場與世界接軌,促進電影事業繁榮。可以看出,在內部經濟出現問題之時羅明佑未針對公司內部現存的制度問題進行改革,而將目光轉向香港尋求新發展。此時明星公司已從海外購買有聲設備試制有聲片,聯華公司資金緊缺無力購入,羅明佑使用招股、推銷、購機三個方式試圖解決經濟問題,故于1933年派關文清前往美國完成這三個任務。此行雖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對聯華上海各廠的經濟情況并無太大改善。“1933年曾經再次向社會招股,但不成功,不僅陷入危機,而且由于下面各廠‘自行籌款維持制片工作’處于一種半獨立的狀態,公司內部的矛盾也日見明顯,尤其是二廠與公司的矛盾更甚。”
在這樣的主、客觀情況下,羅致人才提高產量是當務之急。鄭基鐸1929年在大中華百合公司一年內就拍攝六部影片以出片快著稱。1933年前后,聯華多次提出為提高影片數量“除增加設備外,尚努力物色各項人才”。故聘任鄭基鐸入聯華二廠,連同孫瑜、蔡楚生、史東山共四位導演。
此外,鄭基鐸的電影一貫折射出的民族情感與羅明佑最初組織聯華公司的觀念具有契合之處。聯華公司成立之初提倡“復興國片”旨在讓中國電影表達自己的傳統故事、人生軼事和精神氣概。據聯華公司成立初期發表的諸多文章來看,羅明佑等人結合電影發展和時代環境明確了聯華的營業觀念。
首先是為了解決有聲電影時代到來,中國默片影院將面臨無片可放的危機。基于此現狀,進一步引發羅明佑對復興國片的提倡,他希望同業者重視中國深刻的人生軼事,特別提出“東方忠孝任俠,可歌可泣之往事,尚未能表而出之”。羅明佑復興國片的主要策略是回歸傳統,利用積淀已久的民族思想根基和素材來標示中國電影。事實上,筆者認為羅明佑的電影觀念緣于他內在的民族氣節,他多次顯示出利用電影來拯救民族危亡的決心。在《編制〈故都春夢〉宣言》中羅明佑從社會教育、對抗外片、提高藝術、尊重演員人格四方面希望利用電影的思想性、社會功用性和藝術性來對抗外片。包括其在《聯華之宗旨及工作》中提出“成中國之電影城”也是為把中國電影事業發展至規模化的成熟水平以對抗外片,從文化上抵抗侵略。其電影觀念的核心是為中國電影事業長足發展、為重塑民族氣節尋找出口。
鄭基鐸的影片中欺壓、侵占、復仇等主題的現實意義與中國電影相似,其借用中國的時代背景抒發個人民族氣節的本質與聯華公司的核心觀念具有一定的相通之處。
與此同時,流亡影人與異國電影界也存在不相適之處。聯華公司發展過程的堅守和變化也反映出鄭基鐸身處的創作環境以及他所做出的回應。
聯華公司成立和發展過程在創作上呈現出不同面貌,筆者認為以其成立初衷和一系列舉措為脈絡來看,這些不同的觀念可以概括為聯華公司整體的營業觀,即在電影制作、發行、放映各階段都極為注重電影與社會動向的聯系。
此聯系包含多個維度:一是社會歷史和現實方面的聯系,提倡國片要取材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有聲技術、攝制新聞片等,以此啟發民智進而發行海內外弘揚國光,為被壓迫的中國發聲;二是與社會經濟的聯系,建立專映國片的影院,注重制片和放映形成線性往來的商業互動關系,實現電影的商業效益;三是社會效應方面,興辦印刷業借助廣告宣傳國片,如黃漪磋所言“影業之發達,端賴其出品之宣傳有力……招貼與廣告設計之美觀,尤非羅致編譯及美術專才,自辦精良之印刷,以專其事不為功”,以此形成良好的社會效應;四是社會動態環境方面,聯華公司的營業注重應時而變,應社會變化而變。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后新思想沖擊傳統封建觀念,人們思想更新和行為滯后的矛盾突顯。1931年聯華公司以男女愛情為主題反思新舊觀念,尤其是門第觀、包辦觀等傳統婚戀觀念以及自由戀愛等新思想。拍攝了《戀愛與義務》(卜萬蒼)、《愛欲之爭》(王次龍)、《桃花泣血記》(卜萬蒼)、《銀漢雙星》(朱石麟)等;1932年前后拍攝發揚傳統道德和美德的影片以肅正社會風氣,如《海上閻王》(王次龍)、《人道》(卜萬蒼)、《海外鵑魂》(金擎宇)等;同時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后,拍攝暗含反抗和國難的影片如《野玫瑰》(孫瑜)、《共赴國難》(蔡楚生、史東山)、《火山情血》(孫瑜)、《奮斗》(史東山)等。1933年進步抗敵的高潮,聯華一廠和二廠的導演都貢獻多部優秀作品如《三個摩登女性》(卜萬蒼)、《天明》(孫瑜)、《城市之夜》(費穆)、《都會的早晨》(蔡楚生)、《母性之光》(卜萬蒼)、《小玩意》(孫瑜)等。隨著國民黨電檢制度的加強對進步影片的查禁力度,1934年前后,聯華公司攝制的影片由張揚的進步趨向關注社會現實和人的命運,如《光明之路》(鄭基鐸)、《人生》(費穆)、《歸來》(朱石麟)、《漁光曲》(蔡楚生)、《鐵鳥》(袁叢美)、《再會吧,上海》(鄭基鐸)、《青春》(朱石麟)、《香雪海》(費穆)等。1935年前后聯華公司拍攝響應執政黨官方號召的復古路線和重建新生活、新秩序的教育性影片,如提倡“新生活運動”的《國風》、提倡體育運動的《體育皇后》(孫瑜)、《破浪》(關文清)、宣傳兒童教育的《小天使》(吳永剛)。
基于這種與社會動向緊密聯系又適時變化的電影創作和營業觀,聯華公司發展過程的內部變動和官方意識形態訴求成為鄭基鐸難以適應的可能性所在。
《再會吧,上海》拍攝的同時,聯華公司仍面臨內部制度和經濟等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一年聯華開始減薪裁員“演職員一律減四分之一。導演費穆本來每月薪水二百元,現已減為一百五十元。第二廠和第三廠都裁員簡政”。與此同時,1934年聯華公司備受關注和重視的事件是老板羅明佑受國民黨黨部委派前往歐美考察電影事業,國民黨官方聯合電影界集合各行各界的名人特為此行舉辦歡送會。
羅明佑此行歐美的目的:一是奉官方委派考察歐美電影事業和電影工業;二是因外國多放映侮辱華人的影片,借此機會與歐美電影界交涉勸止并傳播中國優良的民風民俗;三是隨著有聲時代的到來,羅明佑希望可以購置西方先進的有聲設備;此外最重要的是聯華公司遇到經營困難,羅明佑希望借此公派機會謀求經驗和辦法,并且拓展海外市場。此行歷時五個月,羅明佑于1934年9月返滬。根據他回國后對聯華公司的一系列改革,可以看出此行其個人的主要目的還是吸取好萊塢制片廠的經驗為聯華所用。
羅明佑看到美國電影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同業之間相互合作合并大制片廠;各廠緊縮資源,只使用部分攝影場其余關閉或出租。受此經驗影響,同年10月他對聯華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有二,一是將聯華由分廠制改為集廠制,“在聯華高級人員十余日的磋商討論之下,決定整頓方法如下:
一、最有光榮之二廠維持現狀。
二、第一廠遷入第三廠廠址辦公。
三、第三廠并入一廠,其理由為‘輿論不佳,出品無成績’,該廠之外股一律發還,廠長朱石麟則改為第一廠副廠長。”
二是決定于1935年1月起集中廠址并擴建,將一、三廠合并于徐家匯三角街三號合稱為第一制片廠,由原有地十一畝、設一攝影棚一座,經三次擴展至三十畝。
除內部變動之外,聯華二廠的實際管理者陸潔和吳性栽與羅明佑之間一直存在復雜矛盾,“羅明佑所提出的許多經營方略,常遭到二廠的抵制,有些正確的方針如加快拍片速度、提高影片生產數量等,也同樣遭到抵制。甚至可以說,他們對羅明佑等有很深的成見”。陸潔在回復催詢《新女性》劇本的信中稱,因孫師毅要臨時加入一段戲故仍須等待,信中寫道:“三禮拜前我對你說,三天內可以寄給你,但在三禮拜后的今日,我卻不敢說三天了……我相信新女性劇本總有印出的一天。”可以看出陸潔尊重創作者們的精致創作且不在意拍片速度。聯華二廠的導演孫瑜在其回憶錄中談及聶耳曾私下模仿羅明佑“諷刺聯華總經理羅明佑好大喜功,同時搞了五六個分廠,以致經濟時常周轉不靈,問題一大堆”。從片段式的生活打趣細節也可看出當時聯華二廠的電影人對羅明佑的營業觀念存在看法。
聯華公司內部的改動革新以及一、三廠合并后與二廠內部矛盾的發酵升級,加之中國電影界不同意識形態介入干預等問題,這樣的異國環境對鄭基鐸來說實則是另一種束縛。同時鄭基鐸在實際拍攝環節也確實存在困難,也許這些因素都使他無法真正融入異國電影界。
從《光明之路》(《出路》)到《再會吧,上海》可以看出暗含著流亡影人的心境變化。“流亡意味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而身為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必須是自創的,因為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鄭基鐸身處中國的社會體制和環境內,須按照中國的情形和規定創作電影。《光明之路》中底層人物失業喪妻毫無出路,為報昔日援助之恩頂替盜者入獄。影片結尾受執政官方號召的開發西北計劃影響,要求傳輸建設國家、開墾荒地的觀念,故經幾番審查改為人物受當局發征找到一條西北墾荒的“光明之路”。
到了《再會吧,上海》,鄭基鐸回歸自己的創作母題,脫離中國電影的常規表達,不再顧慮進步、反抗與指明道路的要求,設置逃避型人物并重點塑造人物的多重身份,刻畫其復雜心理。這部在上海電影界最后之作的處理可以看出身處故鄉和他鄉縫隙的雙重邊緣者,流亡身份和心態反而使他能夠利用邊緣狀態拋開任何一方的束縛,這種“邊緣狀態也許看起來不負責或輕率,卻能使人解放出來。不再總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攪亂計劃,擔心使統一集團的成員不悅”。他不再主動適應難以真正融入的他國社會和電影環境,把自己的故鄉愁緒再次放入電影,留下不再積極尋找出路的人和漂泊在海上迷茫的人。這與鄭基鐸流亡他鄉的心境頗為相似,遂留下“再會吧,上海”的無奈之慨。
結 語
《再會吧,上海》于1934年11月2日在金城大戲院開映,此后鄭基鐸結束在上海的電影活動,期刊報紙上無法尋覓其此后的行蹤,只可據《申報》1935年10月16日八仙橋會刊登的行李欠租留存通告可知鄭基鐸離開上海已久。其離開時的真正心情和原因亦難知曉,綜合上述實際存在的歷史事實來看,或許《再會吧,上海》正是一個身處兩國電影歷史縫隙、流亡上海的朝鮮影人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