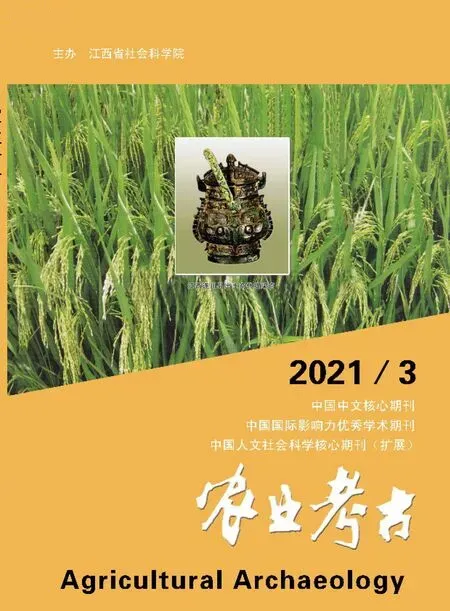嶺南“長生會”的實踐及變遷研究*
顧春軍
起源于晚清,盛行于民國,長生會是嶺南地區重要的民間社團組織。所謂“長生”,是指“長生福壽”之意,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福壽康寧”的現世追求。長生會以助喪為宗旨,兼具慈善與保險雙重性質[1]。
一、長生會研究綜述
1918年,惲代英在《東方雜志》第15卷發表了《人壽保險事業之新發展與長生會》一文,該文依據美國人Harding所撰寫之文章,介紹了美國人舉辦的公共衛生組織長生會的運作情況,與中國本土長生會無關。
1924年,《經濟學家》雜志發表了署名許葆誠的文章《長生會》。該文對長生會做了簡單描述,與國外人壽保險比較后得出結論:“(一)此種集會之創始,洪楊之亂前聞已有之,殆已無可考矣。(二)該會外觀似與保險公司同一類,而實際則炯不相符。緣保險公司為謀利起見,而本會則純粹互助與儲蓄二義也。”[2]許氏對長生會的認識頗有見地,但對長生會的運作也有一些誤解。如認為“會員資格,不論年齡之大小,身體之強弱,凡有志者,俱可入會。但年齡在三十以下者,又絕無僅有也。”事實上:(一)嶺南長生會對入會年紀有所規定:一般入會年紀為十六歲,且規定必須或同族、或同村、或同行才可入會,長生會是以血緣、地緣、行業為紐帶的組織;(二)從會費繳納方式來看,許氏認為長生會類似傳統合會。事實上,合會只不過是長生會初期的運作模式,經過不斷發展并改造,嶺南地區長生會已經發展為具有儲蓄與保險功能的互助組織。
1949年之前關于長生會的研究資料,存世史料可分為兩類:一為長生會簿冊及條據;二為碑刻文獻、地方方志對長生會的記載;三為晚清民國報章對長生會的一些新聞報道。就學術研究成果來看,基本沒有被當時學者界所關注,比如至今影響很大的王宗培學位論文 《中國之合會》一書,也沒有談及長生會。
新中國成立之后,長生會被取締。查閱文獻,亦沒有任何關于長生會的研究論文。改革開放之后,嶺南各地市政協文史委所編輯的地方文史資料,開始對長生會有一些回憶性記錄,但往往也只是片言只語的短文。1998年,中國保險學會主編的《中國保險史》,從人壽保險角度,對民國后期嶺南長生會的衰敗原因做了簡單介紹。該書所引史料及觀點,之后也被各種保險類圖書摘引甚至“剽竊”,但后來的研究成果均沒有超越《中國保險史》一書。
2014年,楊錦鑾博士發表了《傳統與現代之間:民國時期閩粵人壽小保險述論》一文。該文主要研究民國時期的壽險,但亦涉及到嶺南長生會組織。作者沒有見到流布于民間的長生會簿冊,為了能夠找到適當論據,就將福建與嶺南地區的長生會合起來討論①。事實上,兩個地區的情況大不一樣:福建長生會還是民間合會形式,而嶺南長生會則是具有現代意義的類似壽險的組織。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研究生毛迪發表學位論文《慈善?迷信?1929—1936年廣東中山縣民間慈善團體的研究》,該文第三章第三節為“翠微鄉的喪葬慈善活動與迷信”,作者以《香山翠微韋氏族譜》為一手材料,詳細探討了香山翠微韋氏家族所舉辦長生會的運作情況。該章節數據詳實,論述有力,有助于讀者全面了解家族長生會的具體運作情況。遺憾的是,這篇論文不見于知網,亦未公開出版,所以并沒有引起研究者過多的關注。
2020年10月,筆者發表了《傳統慈善組織中的現代保險意識》一文。本文依照晚清民國以來的長生會簿冊及條據,對長生會的機構組成及運行情況,做了一個概括性研究。筆者認為:“民間社團組織長生會盛行于晚清民國,流布于嶺南地區,其宗旨是助喪,資金源自會費、捐贈、祖產、投資收益。它以血緣、地緣、行業為紐帶而形成三種類型,在組織架構、管理運營等方面呈現封閉性特征,又具有慈善與保險性質,是中國本土慈善事業的一個總結,開現代保險業務先聲。”[1]在上述研究基礎之上,本文擬對嶺南長生會的具體實踐活動進行全面探討。本文與上一篇論文是姊妹篇,是對上述話題研究的演繹與推進。
二、長生會的助喪模式
有研究者認為,長生會的主要服務內容為三項:“(一)供奉某一廟觀或拜掃某一無主孤墳;(二)管理產業與收入;(三)發放帛金等。”[3](P525)不同的長生會在會務管理上會有所差別,但管理產業、及時發放帛金是所有長生會的主要任務。也就是說,長生會的主旨就是助喪。就助喪模式而言大致有以下三種。
1.經濟支持
就經濟支持方式來說,一般模式就是直接發放資金:“遇會友家內有喪事,由本會給喪費十二元,到總理報領,即立刻支給,不得延緩。凡做一份者領一次,待全部領勻,方準從頭再領。自后永遠照此類推。”[4](P879)當然,每個長生會的經營模式不同,在帛金的發放上,也有以稻谷代替帛金的,如“江尾頭聯益長生社,向靠九六秤捐應支,近因收入無多,帛金數目太小,耆老有見及此,乃于十一月開會討論,改善辦法多項,對于帛金數目,規定每人仙游領谷三石,以求實用。”[5]香山縣盧氏藝東祖長生會規定:“在外洋身故前未領帛金者,運柩回籍,帛金照領銀拾元”[6],但當其會員華葵因病去世之后,實際領取的帛金是稻谷:“茲因盧萬馀妹華葵于民國廿三年在北平身故,今由舊兩社賻金谷捌佰斤,此系實情。”②可以推測,每個長生會都會依據實際情況隨時調整帛金發放方式。
除此之外,個別長生會還給予一些喪葬用品支持:“凡會友有喪事,由會內致送足斤蠟燭一對、串炮一千、色香一排、天江寶一對、布帛九尺。各會友親到拜祭,以表哀情,以盡哀悼。”[4](P879)
2.會員助喪
傳統社會的喪葬習俗是一件大事,所謂的“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所以,但凡有長者去世,親朋好友助喪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一些長生會也將會員助喪列入其中:“將會內各友分為天、地、人三班,每班二十余人,按次第輪值事。如遇會友喪事,該班系輪值者,要立刻到場支理。倘若深夜寒冷,及遇風雨霜雪,俱要在場守候。倘或有要事,亦要請人代替到場守夜。凡輪班值事系為喪場守夜,事有專責起見。至于出殯事繁,會友一概俱要到齊,踴躍相助,不得以非系輪值班次推諉。”[4](P879)上架行是澳門最早木匠行業互助組織,其內部建有長生會,對于去世會員不但給予物質資助,而且需集體為會員送葬,《上架行永壽堂長生益會簿》云:“在澳埠內仙游者,領帛金銀壹拾兩正,領三旬寶燭金銀,本堂代辦山碑石銀,上山利是餅食銀,是日即晚齊集辦事,送柩到山,安葬妥當為率,以全始終之義。不得以有事推諉。”[7]
3.殯儀服務
長生會還積極為會員籌辦殯葬事務,從而減輕會員家屬的經濟負擔:“本聯保熱心公益人士,因鑒于仵作工人對喪家索取殯殮工值太昂,往往辦一宗喪事,索取港幣七八拾元至二三百元不等,窮苦民眾,因此受到仵工莫大的威脅,各界有見及此,為解除民眾痛苦起見,乃發起組織積善長生會。現已派員出發征求會員及勸捐開辦費等,查每占會一份,一次過收谷伍拾斤,作為該會之基金。至于開辦費則任各界樂助,聞征求隊所到,備受各界樂助,三日之間,已得谷一千一百余石,而自動繼續報名參加者,仍絡繹不絕。并建仵工館舍一所,為仵作安置用具及住宿之用。該館所現已興工建筑,于短時期內便可落成。查該會所得之基金,絕不動用,只收息為雇養仵工之常年經費,將來如有人去世,則因其路途遠近,規定其收取微少抬工價,不得多索,如是便可解除棺材平抬工貴之弊。”[8](P7)為了減輕會員家庭經濟負擔,長生會雇傭仵作,組建自己的殯葬隊伍。
非長生會會員去世,家人就要承擔更多的喪葬費用。據當時新聞報道:“張家邊老歸僑何蔭祥,年近七十,去年返里后,感到環境不佳,郁郁不樂,大有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之慨,因此臥病有日,于九月十日因病去世。家人知未加入長生會,雇傭仵工不無問題,急著人與主辦長生會會份之馬斗垣君,商量即時入會,以便享受方便所之權利。馬君以例經規定,未許遷就,著其自與仵工商妥工值,結果以港幣伍拾元講妥,始允工作,如事前做會,每工不過一斗,用五工計只須谷五斗便可了事,今竟用至五石以上,實為自誤。”[9](P4)此報道就是勸導市民加入長生會的活 廣告 :入會要早啊。
三、長生會的公益活動
長生會主要任務是解決會員的喪葬費用問題。一些運作良好的長生會,往往有著雄厚的資金儲備,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1.出資助學
一些長生會把不動產撥付學校,以作辦學經費來源,如“庫充新村保國民學校,經費不敷,該保長生會值理有見于此,乃開會通過在會嘗內割出旱田九畝,撥作學校校產,已于三月一日由該會主持人將送契正式交與學校。”[10](P16)一些學校也會向長生會借用資金:“三溪保國民學校,校長陳基、校基金管理委員歐培、董主席梁銳南、該校辦理校務人員業志本報。對于校務整理,咸感學風大振,現將校內改善裝修設置,異常美觀。惟惜該校校產,其每年收益為數無多。對于本屆學期,該校就讀學子,其數百有余人,意將下學期,每學子加收學谷若干,又感誠影響一般貧困的子弟,無力堅持繼讀。乃于本月廿日,召集全體校委會,由校董主席提出下屆學期支出經費,須成問題,亟應如何籌措,互相討論,結果通過公愿,向本保長生社,預借谷數若干,以應對支用”。[11](P7)
一般來說,長生會和學校均為家族或者鄉村舉辦,二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學校是純公益的社會團體,所以當學校遇到經濟困難,長生會給予經濟支持,也是情理之中了。
2.公共服務
一些長生會組織,主動承擔起鄉村的公共服務工作,比如“有些長生會還附設救火設施,如為鄉間購置手按式救火機(稱火燭車)、建立水車館(置放保管救火器械處)、開設閱報室、衛生醫療站等。”[3](P525)這些公共服務,包括為村民提供衛生保健:“大鰲溪保豐和長生社值理陳社培,永福黨長生社值理鄭結祥,著保內男女老幼來鄉校內種痘,并挪備火柴盒一個,以為痘冚,聘中西醫鄭可之負責施種云。”[12](P3)主動為無名死亡者修建墳場:“現已將所捐得之谷,撥一小部分,在庵前坑外建筑一方便所,為收斂無家可歸者之用。”[8](P7)
中國共產黨在1926年發布的《中共廣東區委關于廣東農民運動報告》評價說:“長生會,借貸會大概對農民協會都沒有什么沖突,并且還相當贊助農民協會。”[13]與其他社會團體比較,長生會沒有任何政治訴求,是地道的慈善團體。
四、長生會與宗族勢力
長生會的源頭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社會。以地緣為紐帶的鄉村長生會、以行業為紐帶的行業長生會,均與家族有著千絲萬縷聯系。長生會客觀上增強了宗族勢力,起到了敬祖聯宗的作用。
1.宗族背景下的長生會
長生會是宗族社會的產物,是以宗族為基礎的互助組織。很多長生會的名稱就以祖先堂號命名,如“本會命名為阮東澗祖繁衍堂長生會”[14],其辦事地點往往設在家族祠堂:“辦事處設在新厚街即阮氏大宗祠左側。”祖嘗往往占據長生會大半資產:“本會寫出本祖自置土名觀音沙,大有圍田二十畝零,又黃魚沙圍田壹十三畝零,又草塘圍田八畝零,又牛路涌圍田六畝零,又上下段圍田四畝零,作為保證,以昭信重。”
長生會在章程中明確舉辦目的,就是對家族中的貧困者、甚至全部成員給予喪葬費用支持:“我盧姓住居南溪鄉數百余年,一向貧民居多,咸豐年間設立帛金會二份,一名田谷祖,一名積谷祖,田谷祖中途解散,只留積谷祖帛金會一份。此乃會眾集資合成,并非合族有份。今于民國四年舊歷二月廿五日,會眾集祠磋商,將積谷祖帛金會本銀六百元及潮田五畝,一俱撥出,合族有份,另成,合族子孫踴躍捐款,資助藝東長生社會,以成善舉。”[6]“況我世輔祖,族大人稠,貧富不一,或有百年歸去,殯葬無資,即使四處搜羅,支持不易,爰邀老少,共議規條,聯我世輔之子孫,不及外房之兄弟。各捐四員之本,集腋未敢多求;終獲廿員之資,措籌不無少補。以祖嘗為依倚之策,暫且從權;以人事為培助之方,各宜奮力。將見棺槨、衣衾之美,百歲咸宜;宗功祖德之流,萬年不朽矣。”[6]
“辛亥革命后,縣城及墟鎮地方,族姓成立‘長生社’日多,但皆由祠堂值理或寺廟理事辦事。”[15](P274)一些家族長生會甚至規定,會份只能由嫡長子長孫繼承:“會員夫婦逝世,會籍由長子嫡孫繼承,世代相傳。”[3](P525)這更體現了宗法制社會傳統觀念。
2.以祭祀活動維持宗族凝聚力
通過祭祀共同的祖先,強調共同的血脈,增強族人的凝聚力,而祭祀祖先的費用則往往由長生會承擔:“同人等本通財之主義,振互助之精神,代儲壽金為群眾謀喪葬之費,得些余潤,籌我祖作烝嘗之資”[16]。
由祭祀祖先擴展到祭拜本土的其他神仙,比如天后誕辰:“本社專為喪費急需及恭祝天后圣誕而設,各社友均照簡章辦理。”[17]民國時期,端州端硯行長生會規定:“惠日兩坊每年每坊支回酬神銀五大元。”(《惠日端硯行長生義會簿》)[18]一些祭拜孤魂野鬼的活動,則似乎又可以歸為社會公益活動:“又聞每于立夏或重陽之日,備辦金豬牲醴等物,公祭無人拜掃之孤魂,而金豬則按份分與各會友,于可能范圍內,并擬多籌常費,為分派帛金之用,如能實現,全聯保民眾,獲益更不少云。”[18](P7)
通過祭祀祖先,祭祀鄉土神仙,確認會員之間有著相同血脈,確認會員有著共同的信仰,從而達到敬祖聯宗的目的。
3.宗族舉辦的長生會案例
長生會舉辦成功與否,與資金來源、管理制度緊密關聯。就家族長生會之舉辦實踐來看,宗族勢力強大的家族所舉辦的長生會,就更能獲得成功。有研究者依據《香山翠微韋氏族譜》,對香山翠微韋氏長生會的帛金發放情況做了統計,具體數字如下表[19](P56):

表 韋氏長生會歷年帛金發放一覽表
表中顯示,從1886年到1931年,韋氏長生會的帛金發放額度逐年提升,從1886年的10元/人增加到1931年的80元/人,增加了八倍。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對于去世的族人家屬來說,資助額度還是呈現遞增趨勢。韋氏長生會的成功進行,大約離不開幾個要素:
其一、嚴密的管理制度。《韋氏族譜》記載:“分房輸管,以一年為期,周而復始,輪至該房值年,由該房紳耆保舉一人為總管,以殷實公慎者當之,如未得其人,再行變通妥議。另擇族中二人為幫管,二人為書差,以明敏習事者當之。總管周年給辛金二十兩正,幫管給辛金五兩正,書差給辛金五員正。”[20](P76)上述制度制定于1909年,為了適應社會的不斷變遷,先后又于1932年、1936年兩次修訂管理制度。總體來看,制度越來越趨向嚴密化。
其二、充沛的資金來源。韋氏為珠海翠微第一大家族,在海外及港澳經商的族人眾多,他們不斷為長生會提供無償捐助:“康壽社的建立得到翠微旅外者的支持。經部分查證,47位康壽社倡捐人中,有13位旅居上海、福建、漢口等地。47位康壽社倡捐人共捐銀7973兩,其中捐款1000兩以上的4位倡建者共捐銀4300兩,占捐款總額的54%”[22](P15)。
其三、豐厚的宗族嘗產。韋氏家族本來有豐厚的祖產,隨著家族長生會資金的增多,還不斷買入田地以生息:“買置潮田土名蜘洲裕興圍共該稅一頃七十畝,計每歲租入隨時低昂,約得銀四百八十兩有奇,即將遞年出息為支給帛金之用”[23](P39)。
考察各個長生會,會發現其投資項目基本為田地、商鋪、房屋等不動產。在農耕社會,這樣的投資顯然更為穩妥,盡可能確保投資安全。
五、長生會的經濟困境
誕生于鄉土社會的長生會,與農耕生活相適應,但農業生產會受到天災人禍的影響,而以之為基礎的長生會也不可避免受到影響。嶺南地區多風災雨澇,晚清民國則又是一個政局動蕩的社會,所以長生會經常遇到各種風險。
1.自然災害影響
南方天氣炎熱,又多臺風暴雨,所以農業生產往往不穩定:“建成鄉大鰲溪保合鄉長生社,有嘗產廿余畝,向批與人耕種,所收租谷,以作社友身故支給壽金。年來上造禾稻,因受風雨打擊,收獲不及半數,各佃人親赴值理胡信安處要求減租,胡值理以該田系公有物業,不敢應允,減租事情必要懸紅召集社友磋商,方允答復。”[21]一方面是佃人要求減少租金,另一面則往往遇到債務危機:
大鰲溪永豐和長生社,值理胡毅,副值理陳社培,于十九日下午七時,召開社員大會,為本社嘗田租谷,佃人力求減租事有所討論,主席陳社培,記錄鄭鏡輝,宣布開會理由,首由陳社培提議,本社早年需款應用,在外揭入港紙,銀主屢屢向本社追討清還,應如何籌措案,議決:將嘗產土名大嶺旱田七畝,或將洋角沙九畝變賣,得款填還欠谷,二、各佃人上造慘被風旱為災,收獲不滿三石,請求減租,議決:減去租谷三石。議至十時,始行散會。[22]
像香山韋氏這樣的大家族,因為有海外經商的族人給予支持,所以在帛金的發放上,不會出大問題,但大多數依靠農業收入支持的家族長生會,就不免會受到天災影響。
2.內部管理失序
此外,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長生會舉辦者力求選擇品行端正之人負責管理,但也會有遇人不淑的情況發生,如“大鰲溪永豐和長生社,前任值理胡彬垣,于淪陷期間,被選為該社值理時,藉敵偽勢力,串通社員黃兆光、胡吉祥及偽鄉長胡潤忠等,膽敢將社嘗產土名第四區員山沙(即上蓢)旱田九畝零六厘三絲一忽二微,掃數變賣,此款藉飽私囊,社員等復受敵機轟炸,任他欲所欲為。”[23]據當時報紙報道,上述管理者變賣長生會土地一事,最后竟然變為一場馬拉松式的官司。可見管理制度的疏漏,遇到動蕩的時局,往往給長生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3.政府的混亂管理
晚清民國以來,政府對長生會都進行有效管理。民國時期,舉辦長生會就需政府批準,并辦理備案手續:“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呈一件:遵將申請書內列事項逐一補填,請賜核明給證由。呈悉:據稱遵將前請清理中山縣屬第五區土名申堂洲橋咀沙田一起申請書內列事項,逐一補填,請賜核明給證前來:查所填事項,尚無不合,應準給證。茲填印就廳字第四千三百六十八號登記確定證粘圖一張,發交第二科暫存。仰即備帶領結圖章,及繳費收據,來廳具領,可也。此批。”[24](P38)對于經營困難的長生會,政府往往予以取締:“現據第二區公所轉:據谿角鄉長呈請取締長生會社,經即訂定取締辦法,通令各區凡設立此項會社,須由鄉公所查明該會值理人是否殷實,有無嘗產,并將管業契據驗明登記,方準成立。并布告人民知照。”[25](P320)但天災人禍,尤其在政局動蕩的民國,政府的混亂作為,加上瘟疫對長生會的影響,那些面向民眾開放的長生會,往往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1937年在廣州尚存的4家人壽會,已負債累累,瀕臨破產邊緣。其主要原因:其一是1929年廣州市發生流行性霍亂和腦膜炎,會員死亡很多,人壽會因大量給付保險金而元氣大傷;其次是會員死亡多,而新入會的又甚少,因而日漸衰落。人壽會因大量給付保險金而元氣大傷,據羊城公記、萬年、升平、廣生4家人壽會1932年—1936年的統計資料,期間共死亡19858人,而同期入會的僅有2797人,死亡人數大大超過新入會的人數。其三是收取保險費與給付保險金比例失衡,保費明顯偏低;其四是國民政府財政部借用人壽會的基金長期不還。在1923年—1924年間,廣州市財政廳(府)代財政部先后兩次向市內各人壽會暫借54500元,充作軍餉,直到1935年尚未歸還,使人壽會運用基金生息以彌補虧損的渠道也被堵死。[26](P84-85)
六、傳統合會與長生會
長生會是由傳統合會演變而來,直到民國時期,在嶺南地區依然有合會性質的長生會。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十四日設立的永壽堂長生會,就采用傳統的合會方式運作:“照茲會式,領會者眾與錢陸千文,內扣欠會底錢陸百陸拾文,又扣合壹百陸拾會錢壹千伍百玖拾文,實收得錢叁千柒百陸拾文。領第二會者,眾與錢陸千文,內扣欠會底錢陸百文,又扣欠合壹百伍拾玖會錢壹千伍百玖拾文,實將得錢叁千捌百壹拾文,若二會未合,會底錢仍照首會得錢叁千柒百陸拾文,另補會底錢二百四拾文。”[27]
就現有材料來看,合會性質的長生會,舉辦者多以村落為單位,這種長生會一般缺少祖產支撐,只能依賴會員會份運作:
張家邊積善長生會,業已籌備完竣,鄉人所認知會份將近八百份,每份科谷五十斤,約有四萬谷左右,前經開會議決,會谷暫由吳孔嘉代收,決定一五息算隨便放出,如仍有余存,則由吳孔嘉照息以契據為按承揭,以示大公,連日認會鄉人紛紛將谷交到,隨即發給會簿,不日可以完全收集。[28]
合會性質的長生會,其舉辦目的與家族式長生會舉辦目的一樣,都是為了助喪。因為受到鄉人歡迎,有其存在必要性:“永年村組織之長生會,其宗旨系為一般貧苦之家免至百年終壽后,張羅葬費起見,故貧困之人,蒙該會增益不少。如本年該會某會員逝世,葬費無著,得藉會款以助,不致臨時無措之苦,村人咸頌該會增益地方,故入會人數更形踴躍云。”[29]
合會一般依靠借貸生息,偶爾也會以土地、房屋等不動產做長線投資,但凡遇到投資風險問題,一般開全體大會決策,這和家族投資大多依靠值理決策也有很大區別:
張家邊田糧主任馬紀文,因欠繳賦谷,被縣府違償一案,已志各報。日前馬具呈當局,愿將自置田產六十畝,獻出變賣以為抵繳欠谷之數,業經準予所請,查該田變價,尚未足欠繳賦谷之數,系由張家邊主持長生會人士,代馬籌足繳交,故該田亦由長生會承受,現該會擬于日間開全體公民大會解決一切,尤其注重置產或生息方面,聞善長之中有馬贊勤、林尚靄、馬業升等,對此事之發展,多主張考慮慎重處理云。[30]
這種以鄉村為紐帶的長生會,因為與宗族脫嵌,極容易引發社會問題:
封建社會沿至解放前,肇慶城區有以街道或社為單位,舉辦“義會”和“長生會”,由當地殷富或紳士者出名招會。搞小資交流,參會者會期可出利息標投會金,以后分期歸還,名為濟困,實為盤剝手續費。云樵此時束修所得不足為計,標投義會,年終無錢供會。被會社主事(當時稱總理)登門追討,結隊逼債,如當時不償清會款,就要拆房搬家什,在年近歲晚,一籌莫展。[31](P183)
對這條史料,筆者曾經論及:“此條關于長生會的資料,源于后人追憶,極有可能被追述說者夸大,因為按照長生會的規定:一旦不能準時繳納會費,后期補交一定利息即可;如果超時仍不能繳納,會底被沒收,算作本人放棄。長生會組織以自愿為原則,而沒必要被脅迫。”[1]隨著研究深入,筆者發現嶺南地區依然存在合會性質的長生會。合會性質的長生會容易引發社會問題:一旦某會員斷供,就會引起整個合會的“塌方”,所以會員必須繳納會費,否則會受到追討,這與溫情脈脈的家族長生會存在一定的差別。
長生會與傳統合會不同,不但體現在會費繳納及帛金的收取方式上,也體現在懲處制度上:“凡加入長生社者,交入社費2銀圓,領取長生簿1本。每月按社章交長生費半毫或一毫、雙毫銀不等。社員可提前交費。然逾期3個月的,酌情罰息,逾期半載,上門催繳;滿年欠交者,撤銷會籍。長生社將基金置業收租,存入錢莊收息或入股企業分紅。”[17](P274)家族式的長生會,雖然也會被催繳會費,但不會予以暴力行為,一方面會員就是家族成員,由于血緣關系,可以避免暴力行為;另一方面,對于會員來說,如果取消會底,帶來的損失不是長生會組織,而是會員本身。權衡利弊,就不會有暴力事件發生,這也是宗族社會溫情的一面。
縱觀長生會(包括合會性質的長生會)的運營模式,有保險性質在其中,但又絕非是現代意義上的人壽保險:人壽保險的主辦者是為了盈利;而長生會的主辦者則是為了成員福利,于主辦者來說,基本都是義務服務大眾。兩者的目標是大不一樣的。
但在具體運營模式上,合會形式的長生會,往往采用類似人壽保險的模式:“本保念峰祖房,自籌組長生墓祭會就緒,各項章則訂定后,隨即辦理入會登記,并收集基本金,查每份收基本金港幣一十元,另收會部印刷費一元,現且定期于五月初一宣告成立矣。聞是日為分發會部及首次供會之期,供會規定分例會與特會二種,例會每月供充一次,特會即于遇有會友仙逝時,臨時加供,每次會款均為二元,以供一百期為止。現聞入會者僅為百余份,人數不多,但在會期未滿前,隨時可以加入。自是而后,房內有份者,則于帛金及墓祭兩事,均可不虞缺乏矣”[32]。
以助喪為目的的長生會,隨嶺南商人外出經商,被復制到開埠不久的上海。聞名于世的廣肇幫在上海甚至成立了有十萬人之眾的長生會:“深以旅滬同鄉有三十余萬之多,集零成整,用是擬設立同鄉儲蓄銀行以資生產,得余利以作公益,此設長生會之由來也。假定長生會會員十萬人,以最少收入計,每人納同鄉會會費二元,長生會基金壹元,當年會費壹元五角,共應納四元五角,首年收入托共四十五萬元,作同鄉儲蓄銀行基金。”[33]由一家而擴展到一村,由一村而發展到一個城市,這種影響力真是無遠弗屆。
七、長生會與現代壽險
中國近代保險業務不發達,壽險業尤甚。一般研究者認為,由于中國人忌諱死亡話題,受此種生命觀影響,故人壽保險不彰:
中國民眾“凡提到死字,便會引起一種可怕的憧憬,由于這種不測事情的忌諱或否定,以致人壽保險未能獲得一般人的接納”。民國肇始,迷信舊俗雖然受到了一定的沖擊,但科學知識尚未普及,迷信觀念依然熾盛,加上保險宣教的滯后,以致二三十年代不少國民依舊“以投保壽險為不吉祥”。[34]
然而,與之類似的長生會卻在嶺南開花結果,從晚清直至民國長盛大約百年,這就產生一個悖論:緣何二者同道不同途?
首先,人壽保險是自然人與法人單位之間的契約,為了能保證履約,避免雙方糾紛,必須把權利與責任說得一清二楚,因為這個契約的標的就是人身健康,所以就不能避開死亡話題——什么情況下死亡,要說得明明白白。這種死亡話題,不免與傳統文化忌諱死亡相沖突,所以會受到冷遇。人壽保險是工商社會的產物,故需要依靠契約來維護雙方權益;而長生會則是農耕社會產物,權益雙方是同族、同村、同行業的熟人,所以往往依靠組織者的權威來執行。基于上述不同情況,故二者使用的語言會大不相同。把二者做一比較,就可以得知雙方語言上的區別。民國二十四年(1935)八月十日行政院頒布的《簡易人壽保險章程》規定:
第三十條 遇被保險人死亡時,要保人或受益人應立即向保險局報告,由局派員查驗,要保人或受益人對于被保險人之死亡,不立即報告,致保險局無從查驗者,于請求付給保險金額時,須覓具保證,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
第三十一條 給付保險金額時,遇有左列欠款未曾清償者,應于給付金額內扣除之。(一)延未繳納之保險費及逾期費。(二)借款之本利。
第三十二條 受益人請求給付保險金額時,應依式填具申請書,連同保險單及保險費收據單,一并交付保險局。因被保險人死亡而請求給付保險金額者,應附具醫師診斷書及其他證明文件。
第三十三條 保險局收到前條之請求,認為合法時,應即按照保險金額填發付款憑單,交付受益人。受益人收到付款憑單,即依式署名蓋章,連同保險單之收據,向憑單指定之局所領取保險金。[35](P237)
上述壽險章程語言淺顯明白流暢,關于責權利的界定也很清晰;長生會則傾向用文學語言描述辦會宗旨。如《象角鄉阮東澗祖繁衍堂長生會會簿》云:“嘗思人生貧富不常,命運修短有數。是以彭祖壽高,難免怛化;石崇富厚,具見榮枯。況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尚然,則窮通壽夭,安敢懸斷?倘猝遭大故,富者時虞不繼,貧者更感臨事而張惶。斯時曼卿重見,奚能再遇堯夫?人子徒有追遠之心,是難籌慎終之念。由此觀之,寧不憾乎?”[14]《任益壽堂長生祿會》云:“嘗思衣食之用,養生固所必需;棺槨之資,送死尤為切要。若不預為設備,勢必急難措施,大故適臨,惟求無憾。死,葬以禮,自古皆然。與其忙迫臨時,曷若決計遠慮,慎終葬費,誠莫善于長生會也。法以寸累而銖積,集腋以成裘,踵而行之,斯周急原非繼富庶,生順而死亦安。”[36]《石岐大廟合益長生社部》云:“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至哉!言乎溯自贏秦,廢井田之制遂失均輸之義,民無所資,又復獎奇尚巧,豪強壟斷,智富愚貧,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身無完襦矣。吾民終歲勤劬,尚難謀一頓之飽,奚有禮義之足言夫?養生送死,禮至重也。因貧而失乎禮,賢者恫焉。于是設儲蓄之法,以濟其窮顏,曰長生社,即維持禮儀之苦心,法至良意至善也。”[17]
傳統文化諱言死亡,儒家主張“未知生,焉知死”,對于死亡話題往往存而不論。所以說:“凡提到死字,便會引起一種可怕的憧憬,由于這種不測事情的忌諱或否定,以致人壽保險未能獲得一般人的接納。”[35]這種情況是存在的。
對于個體來說,向死而生,生命的終結也是必然。中國人喜歡用“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的態度來緩和這種人生困惑。這就形成了一種矛盾的生命觀:諱言死,但也不畏死。長生會的語言描述更傾向于用文學手法,如典故:“彭祖壽高,難免怛化;石崇富厚,具見榮枯”;或先賢成說:“死,葬以禮,自古皆然”;或套用禮制:“養生送死,禮至重也。因貧而失乎禮,賢者恫焉。”使用文學手法,模糊死亡概念,徐徐引入生死話題,這就使當事人感到親切而不唐突,從而樂意參與其中。長生會章程的撰寫者,一般喜歡用“仙游”替代“死亡”,也是從心理層面竭力避諱死亡恐懼。反觀現代壽險條例,為了避免糾紛,力求用精準語言描述死亡情況。這種缺乏鋪墊的語言描述,具有簡明扼要的特點,能讓人準確把握要點。但從接受美學角度看,卻會讓人聯想到死亡的陰森可怖,在當事人看來,更像是“詛咒”或“預卜”,這確實會讓忌諱死亡話題的中國人感到不快。
長生會是“土保險”,主辦者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土著,他們懂得用合適的辦法打動參加者,用妥帖的語言技巧說服他們;人壽保險系外來文化,其產生土壤是基督教視野下的死亡文化,其對死亡的直白描述,必然會與中國文化的含蓄蘊藉產生沖突。同為資助身后事的社會組織,與壽險相比較,長生會更容易被鄉民接受。
再者,嶺南宗族勢力較強,鄉人喜歡聚族而居。在一個熟人社會中,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組織,遠比陌生人所主辦的壽險公司更容易讓人信賴了。
八、結語: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長生會”
作為一個兼具慈善與保險性質自治組織機構,嶺南長生會通過鄰里互助、鄉村守望,起到了穩定社會的作用,所以受到鄉人歡迎:“會既成,老幼相愛,貧富相助,疾病相扶持,彼此相周恤,鄉之人歡呼鼓舞,相慶于廷。”[4](P879)長生會屬于經濟基礎,必然受到上層建筑的作用。受政局影響,長生會在民國晚期就開始衰落。
廣東省公安局是當時人壽會的主管機關。為使人壽會擺脫困境,曾采取過一些挽救措施,如對死亡會員按會章規定的8折給付保險金,規定各人壽會經費開支限額和員工按8折減薪等措施。但終因結欠應付保險金太多,亦未能奏效。1935年5月,該局再次批準,羊城公記人壽會將每月收入的會費,除新報死亡者每人給付5元外,余款用于平均償還已故會員的舊欠保險金。一些按規定年限尚未繳足保險費的會員,明知人壽會已無力給付保險金,想停繳保險費又怕喪失會員資格,迫于無奈,只得勉強續繳保費。面對人壽會所處的困境,政府便采取消極限制,禁止新設,而已經設立尚存者,則飭令結束。從此廣東省內的人壽會便消亡了[26](P85)。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經濟制度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長生會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不承認長生社。故土地改革運動中,長生社的田地與祠堂的‘太公田’同樣被沒收,分給無地農民。這可能因為長生社理事會的歷屆值理,多涉足管公嘗,有貪污舞弊行為,成了土改清算對象。于是,邑境各地長生社在1952年全面解體。”[15](P276)“50年代土改后,田產與房產皆充公,這些團體亦消失。”[3](P525)
長生會是私有制的產物,也是宗族社會的依托;當私有制被消滅,當宗族社會被打散,長生會也必然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珠海博物館文物征集專家吳流芳老師給予了資料幫助,并協助作者一同進行田野調查,在此鳴謝。)
注釋:
①作者在研究綜述中云:“這些研究在相關史料的發掘上均比較缺乏,在地域上的關注也僅局限于福建,對于同樣繁盛的廣東幾乎沒有涉及。本文將福建、廣東一并納入研究視野,盡量發掘和占有包括檔案、報刊在內的相關原始材料,力圖梳理人壽小保險業在民國閩粵興衰起落的脈絡。”事實上,該作者對晚清民國報刊的資料發掘遠遠不夠,更忽略了民間流布、個別檔案館保存的長生會簿冊和條據,所以對所探討的問題就難以深入。
②本單據由吳流芳先生征集,現由珠海博物館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