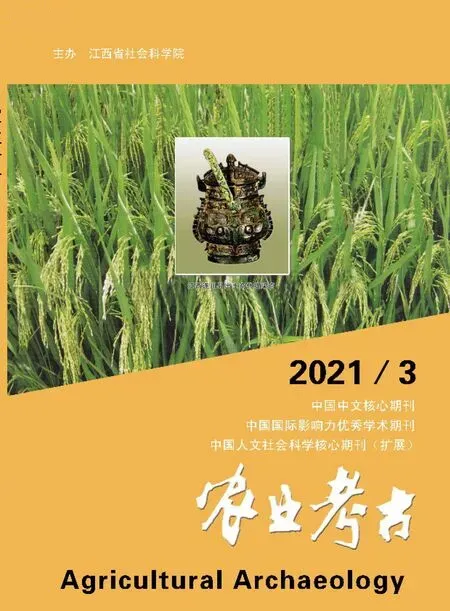漢晉時期湘西地區農業初探*
——以官田遺址為例
吳瑞靜 莫林恒 范憲軍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和大發展時期,大一統政局為經濟發展和民生進步提供了較好的條件[1](P5-17)。有學者認為東漢是南方成為我國經濟重心的孕育時期,這一時期南方地區得到了廣泛的開發[2](P16)。《史記·貨殖列傳》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無積聚而多貧”,表明西漢初,我國南方地區人口稀少,農業開發相對落后,而三國時期,荊州已被認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3](P1269)。從西漢的“無積聚而多貧”到三國時的“士民殷富”,說明這一時期南方地區社會經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過去有學者根據史料和考古出土生產工具對漢晉時期南方地區農業及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原因作了詳細論述[4],但關于湖南的專門研究并不多。符少輝、劉純陽等梳理了史前至民國時期湖南的農業發展過程,認為漢晉時期是湖南農業發展的第一個高峰,農產品生產結構多元化[5](P42-116)。周世榮先生根據馬王堆漢墓出土簡牘及實物,推測西漢長沙等地可能是以種植旱地作物為主,或者旱 地作物與稻各半[6](P81-89)。熊傳新 先生認為戰國兩漢時期湖南農業經濟有了新的飛躍,農副產品產量增加,農作物品種豐富多樣[7](P227-238)。李文濤先生根據走馬樓吳簡對麥的記載,認為三國時期麥作已在長沙地區得以推廣,推廣的原因是軍事上喂養戰馬的需要[8](P48-52)。另外鄧輝先生系統總結了土家族區域的經濟發展歷史,認為漢晉時期該地區經濟較前代有了更大發展,山區得到進一步開發,各小塊區域的發展特色有所不同[9](P136-188)。
上述關于湖南農業的研究均是基于墓葬中零星的植物發現、生產工具、文獻記載和民族學材料得出的結論。然而作為隨葬品的植物遺存不具備量化分析意義,生產工具又往往存在一器多用現象,并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當時的農業狀況。歷史文獻中關于湖南漢晉時期農業的記載也非常簡略,而地方史志的編修從明中期后才開始,依靠文獻來還原當時的農業,證據尚顯不足。深入分析這一時期湖南的農業經濟,迫切需要在遺址中開展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官田遺址的發掘恰好為我們提供了契機。與墓葬相比,聚落遺址的浮選結果更具代表性,更能真實地反映農業生產情況。基于此,本研究根據此次浮選結果,并結合已公布的植物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嘗試分析官田遺址及其所在湘西地區漢晉時期的農業生產特點和人地關系等問題。
一、材料和方法
官田遺址位于湖南省張家界市桑植縣澧源鎮朱家坪村東,地處武陵山區北麓,澧水支流郁水河西岸的臺地上。遺址面積約7.5萬平方米,主體堆積年代為東漢中晚期至三國時期,是一處與冶 鐵 有 關 的 遺 址[10](P69-92)。為 了 解 遺 址 農 業 發 展狀況,我們在發掘過程中采集了7份浮選土樣,其中3份來自灰坑,2份來自灰溝,其余2份來自地層,每份樣品土量約3升。
樣品的浮選采用小水桶浮選法完成,使用80目的分樣篩收取輕浮物。樣品陰干后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實驗室使用蔡司Stemi2000-C體式顯微鏡進行挑選和鑒定,鑒定主要依據各類植物種子圖譜[11]和已發表的相關文獻[12]。測量和拍照使用基恩士VHX-5000超景深三維顯微鏡完成。
二、結果和分析
(一)浮選結果
遺址出土炭化植物遺存包括炭屑、炭化植物種子和果實兩大類。大于1毫米炭屑共計3.9克,炭屑平均密度為1.86克/10升,具體種屬有待進一步鑒定。植物種子和果實大都保存較差,包括農作物和非農作物兩類,共計467粒(表1;次頁圖1)。其中稻、豆和麥既有整粒也有碎塊,但因數量少,對結果影響不大,統計時均按整粒計入。

表1 官田遺址出土植物種子和果實登記表
1.農作物
遺址出土農作物共計400粒,占所有植物遺存的85.7%,包括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ium)、稻(Oryza sativa)、大豆(Glycine max)、綠豆(Vigna radiata)、大麥(Hordeum vulgare)和小麥(Triticum aestivum)七種作物。盡管遺址中未發現水稻基盤、大小麥穗軸等作物加工的副產品,但從出土農田伴生雜草和鐵鍤等農業生產工具看,這些農作物應是本地種植的。
從農作物兩項量化數值看(圖2),粟的數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最高,均達到70%以上,是遺址最主要的農作物。種子近扁球形,少數帶殼,腹近平。黍的數量較少,僅在1個單位發現3粒黍,形狀呈長橢圓形,皆不帶殼。稻的數量比例只有2.5%,但出土概率相對較高,達到42.9%,表明在聚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過測量其中完整的4粒,得出平均粒長5.19毫米,寬2.44毫米,長寬比為2.13。大豆共30粒,集中出土于H1,豆粒呈橢圓形,外表爆裂明顯,多數種臍脫落,僅1粒保存較好,呈窄長圓形位于腹部偏上處。綠豆共34粒,其中5粒整豆,29粒碎塊,占農作物的8.5%,出土概率為28.6%,整體呈橢圓形,兩端較圓,表面光滑。大、小麥數量都很少,推測這一時期麥作可能還尚未在湘西地區得到大規模種植。
2.非農作物
官田遺址出土非農作物67粒,包括雜草類和果實類。雜草類植物以禾本科(Gramineae)為主,包括狗尾草屬(Setariasp.) 和黍亞科(Panicoideae),這兩類植物為典型的秋熟旱作物粟、黍的常見伴生雜草[13](P50-53),它們與農作物同出,很可能是隨著農作物的收割進入遺址。農田雜草以旱作物伴生雜草為主,也印證了遺址以旱作為主的農業生產模式。果實類僅發現7粒懸鉤子屬(Rubussp.),其味酸甜,可直接食用,可能是人們食用后的殘余。非農作物中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資源種類和數量都很少,暗示采集經濟在生業中所占的份額較小,僅作為農業的補充。
(二)植物遺存出土背景分析
植物遺存的埋藏環境承載著一定的人類行為信息,通過對植物遺存的出土背景和空間分布進行考察,可以為了解植物遺存的來源、遺跡性質和功能等問題提供借鑒。從各遺跡出土植物遺存的密度(圖3;圖4)看,各單位存在較大差異,同一單位炭屑和種子的分布具有正相關性,出土炭屑多的單位種子也多,兩種植物遺存可能存在相似的來源。
炭屑和種子密度最高的樣品來自G19和H1,出土植物以粟、豆類農作物和黍亞科雜草為主,與植物遺存同出的還有爐渣、礦石、積鐵塊等冶煉遺物殘塊和鐵刀、鐵錐等生產工具及陶、瓷器殘片。根據出土遺物,我們推測G19和H1應是先民傾倒生產和生活垃圾的主要場所。比較特殊的是H3,H3位于窩棚式房屋建筑F1內部,根據其形狀及出土遺物推測可能為F1的簡易火膛。房屋是人類生活起居的場所,與人的行為密切相關。H3出土了農作物、懸鉤子屬等可食用類植物,農作物均為不帶殼的谷粒,未見稃殼、基盤、穗軸等農作物加工的副產品,根據H3出土遺物,我們推測F1很可能是人們對食物進行消費的場所。
三、相關問題討論
官田遺址是湖南地區漢晉時期首個開展植物考古研究的聚落遺址,為我們了解遺址及湘西地區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產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下文將根據此次浮選結果,并結合相關史料,對湘西漢晉時期的農業特點及其背后的動因進行探討。
(一)聚落農業
官田遺址浮選結果顯示,東漢至三國時期先民農業生產對象包括粟、黍、稻、大豆、綠豆、大麥和小麥七種農作物,五谷俱全,作物種類多樣。其中,粟的數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均遠高于其他作物,是聚落中最主要的農作物,表明農業生產以種植旱作物粟為主。稻的數量比例雖然與粟相差較大,但也具有相對較高的出土概率,應是聚落生活中較為重要的農作物。其他五種作物百分比和出土概率都不高,揭示其在先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如粟和稻,種植規模可能較小,但也起到重要的補充作用。總的來看,官田聚落農業呈現出以粟為主、稻次之并同時種植多種作物的特點。
官田遺址樣品量少,本次浮選結果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遺址的真實情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筆者擬結合史料加以佐證。《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云“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可見春秋時期湖南已有集中的粟米產地。里耶秦簡載 “粟米千五百九十四石四斗(8-1332)”、“□□沅陵輸遷陵粟二千石書(8-1618)”[14](P166、213),說明秦代時湘西地區粟的種 植已具規模。漢至唐,湘西的農業狀況不見于史冊,宋代以后,記載漸多。《云谷雜紀》載“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 ,且多 在岡 阜”[15](P76);《老 學 庵筆 記 》載“辰、沅、靖州蠻有仡伶…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16](P42-57)。萬歷《慈利縣志》卷七載慈利境內谷物包括稻、黍、粟、高粱、麥、蕎麥、豆、麻,麥為五谷之貴。乾隆《永順縣志》卷七云“各處所種,以小米糝子為主,不甚種稻谷,即種亦不知耕耨”;同治《桑植縣志》卷二載“邑多山宜種雜糧…包谷遍種山谷間,至秋熟價不足當粟米之半…麥有大小二種”;光緒《乾州廳志》卷七載“苗食日常兩餐,春夏三餐。所食多粟米、苞谷,或以雜糧為餌”。結合文獻,我們發現官田遺址浮選結果所體現的農業特點與文獻記載是相吻合的,湘西地區以種植旱地作物為主和多種作物并植的農業生產模式至遲在東漢時就已經形成了,且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
就單種作物看,湖南作為稻作農業起源地之一 ,自 舊 石 器 時 代 晚 期 就 開 始 栽 培 稻[17](P282-289),至遲到湯家崗文化時期就已發展了較為成熟的稻作農業[18](P164-169)。與之相較,其他幾種作物 并非湖南本地起源,傳入到湖南的時間不同,各時期比重也有所變化。為進一步研究官田遺址的農業特點和旱地作物在湖南的傳播,下面擬對粟、黍、大豆、綠豆、大麥和小麥作一專門考察。
粟作為北方地區最主要的農作物品種之一,大約在距今6000年前大溪文化時期就已傳入到湖南[19](P1-14),孫家崗遺址后石家河文化堆積中也有粟出土[20](P104-109),但其在農業中所占比例始終較低,并未對稻作農業的主體地位產生影響。商周時期,湖南暫未公布相關資料,但從鄰近的江漢平原看,粟的比重相比史前有明顯提升,但地位仍未超越稻[21]。春秋至秦漢時期,湖南已普遍種植粟,在馬王堆漢墓中發現粟實物[22](P7),《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和里耶秦簡中也都有湖南產粟米的記載,且規模可能并不小。官田遺址的浮選結果顯示,粟是聚落最主要的農業生產對象,這與文獻記載的情況大致相符。
相比于粟,黍的發現并不多。先秦時期湖南的黍遺存見于孫家崗遺址,僅2粒[20](P104-109),馬王堆漢墓出土有黍粒和黍餅,比例不明[22](P6),虎溪山漢墓出土簡牘中有關于黍的描述[23](P36-55),但隨葬品中未發現實物[24](P578-582)。從出土黍的遺址和黍的量化數值看,湖南地區黍的種植規模可能一直都較小,官田遺址的量化分析數據也顯示出同樣的結果。
研究表明,黃河中下游地區最早開始栽培和馴化大豆[25](P18-25),最遲到戰國時期大豆傳入到江漢平原[26](P116-124)。湖南境內最早 的栽培大豆 實物見于馬王堆漢墓,與大豆同出 的還有豆豉[22](P7)。虎溪山一號漢墓出土簡牘中還有關于制作豆醬汁的記載[23](P36-55)。這一時期人們不僅直接食用大豆,還制作豆制品,但由于無量化數據,尚不清楚大豆在農業中的地位。官田遺址出土的大豆數量多于黍、稻、大麥、小麥,在農業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為研究湖南地區大豆的種植和推廣提供了新證。
綠豆作為一種雜糧,通常是作為谷物的補充。湖南尚未出土秦漢以前的綠豆遺存,相關記載也較少。官田遺址出土的綠豆為研究南方地區綠豆的栽培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
麥類作物方面,大麥和小麥起源于西亞的新月形地帶[27](P316),大 約距今4000年前龍山文化時期 經 中 亞 傳 入 中 國[28](P11-20),是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反映。以往研究顯示,南朝時期麥作在南方大面積 種 植 ,之 后 出 現 萎 縮[29](P16-22),一 直 到 南 宋 時期,又在南方大規模推廣種植[30](P353-357)。新近有學者根據走馬樓吳簡記載,推測孫吳時期麥作可能已在長沙一帶推廣,但主要是為軍事上的需要,并非食用[8](P48-52)。湖南出土的麥遺存實物并不多,已公布的資料僅見于馬王堆一號漢墓,包括大、小麥[22](P4-5)。官田遺址出土大麥和小麥的數量都很少,推測麥作種植規模并不大,這一方面可能與麥冬春需要灌溉不易種植有關,另一方面東漢時石磨未在南方普及[31],麥飯適口性較差,可能導致人們對種麥缺乏積極性。
(二)旱地作物發展原因蠡測
長江中游地區屬中國南方稻作農業傳統[32](P19-31)。植物考古研究顯示,洞庭湖平原地區新石器時代農業是以稻作農業為主導,旱作物傳入后并未影響稻作農業的主體地位[33]。漢晉時期,這一地區尚無植物考古研究資料,文獻記載“荊州,谷 宜 稻 ”[34](P1541)、 “ 楚 越 之 地 … … 飯 稻 羹 魚 ”[35](P3270)。現今水稻仍是湖南最主要的糧食,稻谷產量占湖南糧食總產量的85%以上[36](P704-708)。然位于湘西山區的官田遺址卻主要從事旱作農業,旱地作物表現出更明顯的優勢,其原因可從自然和人文因素兩方面探討。
自然條件方面,包括地理環境和氣候環境兩個因素。從地理環境看,官田遺址所在的桑植縣位于武陵山區北麓,鄂西山地南端,境內山地丘陵占全縣總面積的93%,平地和崗地僅占7%,且集中在澧水兩岸[37](P2)。以山地丘陵為主的地貌類型增加了土地平整的難度,且不易蓄水和灌溉,為水稻大規模種植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粟、黍雖為北方優勢作物,但因其具有耐寒、耐旱、耐脊、適應范圍廣的特點,在山坡或干旱地區均可種植[38](P205、217),麥類作物亦適宜在相對干燥的高地栽種[39](P209),大豆被認為是旱澇 保收的作物[40](P129)。因而在水利設施條件較差的漢晉時期,湘西地區的先民因地制宜地廣植旱地作物。
氣候環境方面,有研究顯示,漢晉時期,氣候波動明顯,冷熱交替,東漢末至孫吳時期,正屬于寒冷期[41]。《后漢書》和《三國志》也有相關記載,如“永建三年(128)…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42](P2034)、“初平四年(193)六月,寒風如冬時”[43](P3313)、“黃初六年(225)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44](P85)。氣候波動,導致自然 災 害 頻 發[45](P15-57)。在 生 產 力 比 較 落 后 的 情 況下,多種作物并植是降低風險、應對災荒的重要舉措,《漢書·食貨志》也載“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人們的喜好往往影響著農作物種植的種類,北人南遷可能是旱地作物得到進一步發展的主要人文因素。官田遺址作為一處冶煉遺址,它的人員構成本身就可能比較復雜。另外東漢時期,中原動蕩,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北方人民紛紛南遷[46](P591-612)。官田遺址所在的桑植縣在東漢和三國時屬武陵郡管轄,隸屬荊州[47],《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志》記載西漢綏和十年(2年)至東漢永和五年(140年)武陵郡的人口數從157108增加到250913,而此時北方大部分郡縣人口數都在下降[48](P33)。從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北方人口向南方移民達到一個高潮[49](P271-282),衛覬在與荀彧書信中提到當時“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余萬家”[50](P610)。北人南遷帶來的最終結果是北方物種、文化的南播,從而促進了旱地作物的發展,同時也為旱作農業生產提供了技術保障。
四、結語
以往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時期,而較少關注秦漢及以后的遺址。盡管這一時期關于農業的史料相對豐富,但多數涉及的區域范圍廣,時間跨度大,僅靠這些文獻記載很難復原特定時空范圍內的農業經濟,我們仍需借助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官田遺址作為湘西地區一處重要的冶煉遺址,雖然取樣量不多,但與墓葬相比,它的浮選結果更真實地反映了這一地區農業經濟的狀況。分析結果顯示,聚落農業生產呈現出以粟為主、稻次之、并同時種植多種作物的特點,為深入研究漢晉時期湘西山區農業生產模式、生業經濟、人地關系等問題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本次開展的植物考古研究雖然使我們獲得了一些重要的認識,但畢竟只是基于有限樣品分析的結果。未來的研究工作中,我們希望繼續在湘西地區相關遺址開展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獲取更多的樣品,進一步探討該地區的農業發展狀況。
附記:官田遺址植物遺存的鑒定得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劉長江先生的幫助,在此致以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