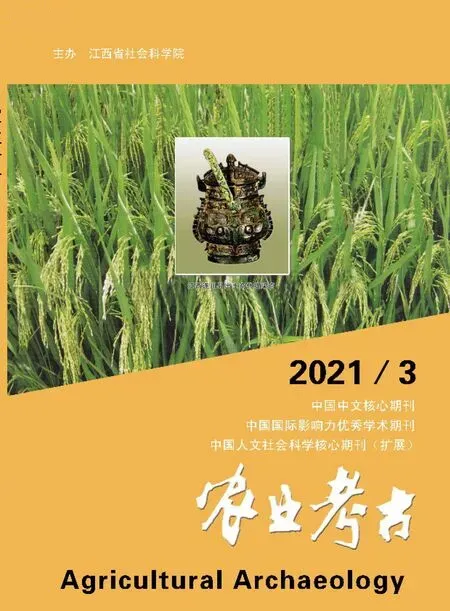現代水田微體植物遺存分析*
邱振威
一、引言
水田,在《辭海》中被解釋為“周圍有隆起的田埂,能蓄水的耕地”[1],《現代漢語詞典》中一般指“周圍有隆起的田埂,能蓄水的耕地,多用來種植水稻”[2](P1221),即從事 稻作農業(yè)生產的主要 場所,這也是狹義的水田范疇。古水田的發(fā)掘與研究,有助于復原稻作農業(yè)歷史及其與古代社會發(fā)展的關系[3]。目前發(fā)現的中國境內新石器時代水田遺跡,分布地域涵蓋長江中下游、淮河下游和黃河下游,時間跨度從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前。尤以長江三角洲地區(qū)良渚文化時期的水田為代表,水田面積較大(施岙遺址古稻田總面積約90萬平方米[4]),單塊田塊面積達到上千平方米(茅山遺址出土了近2000平方米的水田[5](P31-39)),發(fā)展出河流、水溝、池塘、儲水坑、水井等組成的灌溉系統(tǒng)。
有學者嘗試對比古水田和現代水田的水稻土[6]有機化學組分,發(fā)現綽墩遺址水田遺跡S27堆積最上層(100-116cm)的土壤有機質濃度與太湖流域現代水田的 土壤有機質濃度[7](P695-701)相當,但是較之其最下層堆積高約5倍[8](P232-236)。我們曾對馬家浜、崧澤和良渚文化時期的江蘇昆山姜里[9]和朱墓村[10](P57-67)遺址出土古水田開 展 了較為系統(tǒng)的植物遺存分析,重點從大植物、植硅體和孢粉等植物遺存的角度進行考察,尤其是設計了結合文化堆積的連續(xù)梯度取樣與分析單元,對認識古水田的堆積形成過程、水田農耕生產方式(水田管理與水稻收割方式等)、水田生態(tài)景觀等提供了較好的研究范例與討論空間(如我們提出“輪休”制度、除草等田間管理措施、水稻收割方式的轉變等在植硅體上應該有所反映)。華南地區(qū)現代野生稻生長地和水稻田的表土植硅體開展了專題分析[11](Pe0141255),進一步證實水稻扇型植硅體魚鱗狀紋飾(大于等于9者的百分比)用于判斷水稻馴化過程具有重要的指示意義[12]。
但是,我們對水田遺跡自身的判斷、水田堆積的性質和形成過程、水田的發(fā)展演變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仍處于初步階段。因此,萌生了對現代水田土壤(水稻土犁耕層)進行嘗試性研究的想法,初步設定是對特定現代水田的耕作層進行微體植物遺存的提取與分析,尋找是否存在一定規(guī)律性。該案例與嘗試或將有助于反思已經分析的一些古水田堆積[13],并為今后的研究提供思路。
二、樣品采集與實驗分析
(一)樣品采集
我們選取江蘇無錫一處二十世紀末仍作為水田種植水稻的地點進行嘗試分析,該地點系在進行楊家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工作過程中偶然發(fā)現。該水田堆積正處于現代綠化林表土和考古文化層之間,厚達46cm,很容易辨別并獲取樣品。為了與考古遺址出土的“水田”遺跡進行對比,我們設定的取樣梯度是2cm,共計獲取23個梯度單位樣品(圖1),其中耕作層14個,犁底層9個。
(二)植硅體提取與分析
植硅體類型主要包括:扇型、方型、長方型、平滑棒型、突起棒型、刺狀棒型、尖型、帽型、長鞍型、短鞍型、啞鈴型、水稻雙峰型、木本型和導管等(見次頁圖2)。總體上,各梯度深度的植硅體基本均以扇型、平滑棒型、長鞍型和啞鈴型為主。鑒定出的植物種類有水稻 (Oryza sativa)、蘆葦(Phragmitesaustralis)、竹亞科(Bambusoideae)、早熟禾亞科(Pooideae)等。此外,還發(fā)現少量海綿骨針(sponge spicules)和硅藻(diatoms)。根據植硅體百分比和濃度圖式,結合水田堆積的土質土色,將水田梯度堆積的水稻植硅體分兩部分進行描述(見次頁圖3、4)。
犁底層:水稻扇型植硅體百分比平均約4.1%(2.8%-7.7%),平 均 濃 度 約14476個/克 干 樣(6607-24777個/克干樣);水稻雙峰型植硅體百分比平均約3.4%(0-6.6%),平均濃度約11695個/克干樣(0-24777個/克干樣)。
耕作層:水稻扇型植硅體百分比略有降低,平均約3.9%(1.6%-8.5%);同時濃度趨于增加,平均約18259個/克干樣(3717-44599個/克干樣)。水稻雙峰型植硅體百分比增加至平均約4.9%(0.7%-9.7%),濃度也大幅增加,平均約24416個/克干樣(1239-56988個/克干樣)。
(三)孢粉提取與分析
實驗提取到的孢粉類型包括:裸子植物主要是松屬(Pinus);被子植物木本類型主要有櫟屬(Quercus)、栲屬(Castanopsis)、楓香樹屬(Liquidambar)、榆屬(Ulmus)、榿木屬(Alnus)、榛屬(Corylus)、鵝耳櫟屬(Carpinus)、樺木屬(Betula)、桃金娘科(Myrtaceae)、殼斗科(Fagaceae)、胡桃屬(Juglans)等;陸生草本和灌木類主要是陸生的禾本科(Poaceae)、 豆 科 (Fabaceae)、 蒿 屬(Artemisia)、車 前 草 屬(Plantago)、莎 草科 (Cyperaceaea)、 藜 科(Chenopodiaceae)、紫菀型菊科(Aster-type Asteraceae)、石竹科(Caryophyllaceae)、瑞香科(Thymelaeaceae)、 蓼 屬(Polygonum)、毛茛屬(Ranunculus)等,另有水生草本香蒲(Typha)和狐尾藻屬(Myriophyllum);蕨類孢子主要是水蕨屬(Ceratopteris)、水龍骨科(Polypodiaceae)、鳳尾蕨屬(Pteris)和其他三縫孢(Triletes)、單縫孢(Monoletes)等(圖5)。
總體上,該堆積中揭示的是櫟屬—栲屬—水稻型禾本科—野生型禾本科的孢粉組合。陸生花粉總濃度平均為2618個/克干樣(見次頁圖7)。孢粉組合(見次頁圖6)以陸生草本為主,其中禾本科平均百分比約59.9%(45.5%-71.6%)且總體較為穩(wěn)定;犁底層有一定量的車前草屬(平均約2.5%)、蒿屬(平均約3.7%)和藜科(平均約4.0%)。喬木類以闊葉的櫟屬和栲屬為主體,平均百分比分別11.9%(0-21.7%)和8.0%(0-50%);另有少量針葉的松屬(平均約2.9%)等。水生草本總濃度為824個/克干樣,其主要為香蒲(平均約2.3%)。蕨類孢子總濃度為13621個/克干樣,以三縫孢為主。下面對禾本科花粉分層做重點描述。
犁底層:陸生花粉總濃度平均為306個/克干樣。水稻型花粉百分比平均約36.0%(13.3%-61.5%),平均濃度約132個/克干樣(5-542個/克干樣);野生禾本科花粉百分比平均約17.3%(0-40%),平均濃度約49個/克干樣(0-224個/克干樣)。
耕作層:陸生花粉總濃度驟增,平均為4104個/克干樣。水稻型花粉百分比大幅增加,平均含量約50.3%(41.8%-62.4%);濃度驟增,達到平均約2133個/克干樣(588-5051個/克干樣)。野生禾本科花粉百分比有所減少,平均約13.8%(7.6%-62.4%);濃度也有大幅增加,平均約546個/克干樣(92-1477個/克干樣)。
三、討論
孢粉和植硅體分析表明,該采樣點及其附近的地帶性植被系以櫟屬和栲屬為代表的常綠—落葉闊葉混交林,并混生有少量的楓香樹屬、榆屬、榿木屬、榛屬、鵝耳櫟屬、樺木屬、桃金娘科、胡桃屬等。林緣開闊地除了人為栽培的大量水稻外,還生長一些野生的禾本科、竹亞科、早熟禾亞科、蘆葦、藜科、蒿屬、車前草屬等陸生草本植物。河湖邊緣、沼澤濕地等處生長一定量的水生香蒲屬植物和少量狐尾藻屬等漂浮植物。林下分布有一定量蕨類(如水蕨、鳳尾蕨、水龍骨)孢子。以上通過孢粉和植硅體構建的植被景觀,與采樣點附近現在的植被分布具有很好地一致性,總體呈現溫暖濕潤的氣候特點。雖然水田耕作層受到人為耕作的影響,但一定程度和尺度上仍可以用來構建地方性植被景觀。這一點與考古遺址人為堆積及其附近自然沉積所揭示的相似地方性植被景觀不謀而合[14](P9306),區(qū)別只是已經存在歷史的過去和即將成為歷史的現在罷了。
在本次取樣點46cm厚的水田堆積中,水稻扇型植硅體和水稻雙峰型植硅體的百分比相對較低,但是濃度非常高且呈現出自下而上趨于增加的特點,與我們在馬家浜文化時期姜里遺址 水 田 堆 積 中 觀 察 到 的 現 象 基 本 一 致[15](P374-386)。現代水田堆積中,水稻扇型植硅體除了兩個堆積單元外,均達到了水田植硅體的判別標準(5000個水稻扇型植硅體/克干樣)[16],但是其濃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很可能是受到間歇性的輪作(種植它作物,如棉花、油菜等)和機械化的耕作造成土壤上下翻動相對劇烈的影響。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證實了我們對姜里遺址馬家浜文化水田耕作方式的分析與判斷[17]。
一般認為禾本科花粉具有低代表性[18],因此現代水田堆積單元(特別是耕作層)中水稻型禾本科花粉較高的含量(平均超過50%)和濃度(高達5051個/克干樣)應是水稻種植行為的直接反應。這與現代稻作區(qū)表土中禾本科花粉的含量特點[19](P262-272),以及古水田堆積中水稻 型禾本科花粉的含量與濃度分布[20](Pe86816)具有較好地協同性。
由上,通過植硅體與孢粉這兩個指標的分析,可以判斷現代水田取樣點附近一度存在較為長期頻繁的水稻種植活動。
四、問題與展望
對現代水田堆積的植硅體和孢粉分析,一方面從技術層面加深了對水稻扇型植硅體、雙峰植硅體和水稻型花粉形態(tài)的認識,有助于對考古遺址文化堆積中提取到的可能與水稻相關的植硅體和花粉進行甄別和形態(tài)對比;另一方面,對于古水田的判定、研究以及稻作農業(yè)發(fā)展程度的評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以上主要是基于一處(無錫)現代水田(地點)的植硅體和孢粉分析得到的初步結論。為了驗證其普適性和有效性,還需考慮同一水田不同采樣點、區(qū)域不同地點、多個地區(qū)、不同性質(土壤性質、供水系統(tǒng)、種植強度等)的水田堆積,進行更加系統(tǒng)科學的比較研究,這也是今后工作的重點。同時,現代水稻種植的旱田系統(tǒng)情況如何、其與水田系統(tǒng)是否存在差別、土壤形態(tài)上能否進行有效區(qū)分等,也需要考慮。此外,還應考慮將現代野生稻居群生長地的自然沉積物納入分析與比較研究范疇。
附記:本文分析的現代水田樣品采集于2013年6月,系在筆者開展博士論文研究工作涉及一處馬家浜文化遺址之時,為開展對比研究附帶采集所得。感謝無錫市文化遺產保護和考古研究所劉寶山研究員、李一全研究員及無錫闔閭城遺址博物館丁蘭蘭女士對本研究的支持,感謝中國科學院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系蔣洪恩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陳相龍博士在樣品采集過程中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