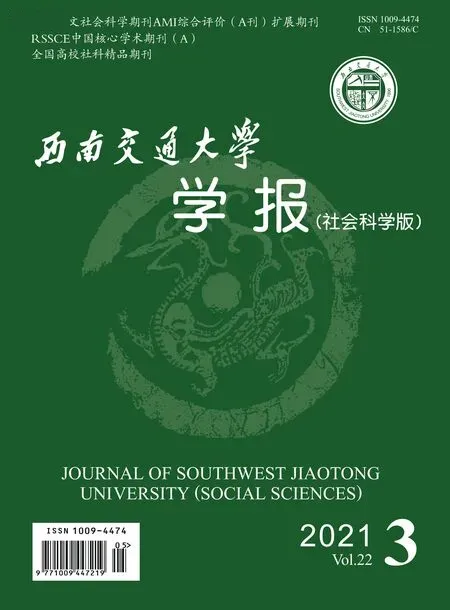詩歌翻譯中意象的語義場視角闡釋
——兼析李白《月下獨酌》四種英文譯本
余 霞, 王維民
一、引言
李白詩歌在唐詩中浮翠流丹、熠熠奪目,國內外譯者對李白詩歌的翻譯可謂情有獨鐘,各種譯本雜陳。國外譯者中,對李白詩歌譯介影響較大的是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日本學者小畑薰良。阿瑟·韋利是20世紀上半葉英國最杰出的漢學家、翻譯家,一生致力于東方文學的譯介,其譯詩風格簡約、輕快流暢、意象清新,獲得了國內外學者和眾多讀者的認可,他對“詩仙”李白的認知和李白詩歌的意象保留著自己獨到的見解;韋利的前輩翟理斯也為中國語言文學的傳播作了很大貢獻,20世紀初期他就與當時的后起之秀韋利多次就漢詩翻譯展開過爭論,他翻譯的李白詩歌《月下獨酌》受到大家的肯定,其譯詩中的韻體經常被分析和研究,他認為詩歌翻譯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傳達原詩的意義;小畑薰良英譯的《李白詩集》是英語世界的第一部李白詩集單行本,是世界上最早的李白詩譯文集,他翻譯的《月下獨酌》深受英文讀者歡迎,在西方頗有影響。三位國外漢學家在譯學界對李白詩歌的英譯影響深遠,對當今的詩歌翻譯仍具有借鑒意義。中國國內翻譯泰斗許淵沖也曾翻譯過《月下獨酌》,其譯詩將原詩的意象和形式還原得淋漓盡致,譯本在國內外廣泛流傳。
詩人通過意象構建賦予詩歌以豐厚的藝術魅力,譯者則挖掘詩歌的文化底蘊,圍繞詩題對原文由低至高的語言單位含義進行“重建”,盡可能地還原詩歌中的意象系統。以上四位譯者的作品在對原文意象構建上都各具特色、各有所長,本文擬運用表達性語義場理論將《月下獨酌》的原詩與四位譯者的英譯本進行對比分析,重點探析譯詩中的意象構建,揭示這四種譯本在表達詩歌主題方面的得失。
二、《月下獨酌》主題與意象
《月下獨酌》是李白抒情詩中極具神韻的傳世佳作,構思新穎, 想象奇妙,引人深思。這首詩大約作于公元744年,當時在長安的李白政治上很失意,心中愁苦、郁郁寡歡,但仍渴求光明與自由,想要掙脫現實的桎梏,于是在詩中將這種愁苦與希冀表現為對太陽和月亮的抒懷與贊美。特別是明月對李白來說,是虔誠的信仰,是純潔的友誼、思念的故鄉,也是絕望中的希冀。《月下獨酌》這首詩,描寫了詩人自己在花間月下舉杯獨酌的場景,李白運用豐富的想象力,描寫了一段與月、與影酌酒的情景,向讀者展示出了一種由孤獨到不孤獨,再由不孤獨到孤獨的情感。這首詩的“詩眼”在一個“獨”字上,從他的詩里我們可以聽到一個孤獨的靈魂在夜晚的吶喊,這吶喊聲飽含著對自由的向往和對掙脫世俗的渴望。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詩歌的開始就點出主題“獨”字:獨自飲酒,顯得心中郁悶、孤寂,只好“舉杯”邀請“明月”和“影子”作陪,這樣就相當于三個人在飲酒了。然而,明月和影子是不會喝酒的,只會默默地陪著自己,相比真正友人們的暢飲,此情此景就更顯孤寂了。但是,有“人”陪伴始終是好的,“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詩人選擇了珍惜這段想象中的友誼。飲酒快到結束時,“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詩人說趁著清醒的時候“三人”趕快結交成好友,害怕醉后不省人事而又各自分散。李白是舍不得這段幻想中的友情的,他對友情是極度渴望的。詩的最后兩句說:“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可見李白希望能永遠盡情漫游于天地,和月亮、影子在茫茫的天河中相見。“無情”是不沾染世情的意思,表達出了李白想要擺脫世俗、和天上的月亮以及自己的影子約會、希望友情天長地久的愿望。這兩句詩所表達的寄托和出世思想,把月亮和影子擬人化,與本不存在的“人”作伴,更加折射出詩人在茫茫人海、蒼茫世間的伶仃孤苦、形單影只、空虛寂寥。
三、《月下獨酌》意象之語義場構建
在詩歌中意象是詩歌審美的核心,詩歌意象的翻譯過程本質上就是意象再次生成的過程。著名翻譯家江楓認為:“翻譯應該是在對原作形象或意象逐漸形成概念的同時使用譯入語的詞語和結構營造對應形式的過程”〔1〕,“如果譯者能從意象的語義信息、審美形式和深層意境結合原詩作者的創作意圖、背景及社會文化語境多層次多角度的挖掘詩歌的語義及審美信息……未嘗不能神形兼備地接近原詩之美”〔2〕。可見,確立《月下獨酌》中關鍵語義場義素,便是正確翻譯該詩意象的著眼點。
“獨酌”作為《月下獨酌》的精髓,為作品立下了中心意象。《莊暴見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此處的“獨”為單獨;《趙威后問齊使》:“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禮記·大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這里的“獨”為老而無子這樣一種狀態;《史記·游俠列傳序》:“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與朱元思書》:“奇山異水,天下絕”,這里的“獨”指獨特、特殊;《赤壁之戰》:“獨卿與子敬與孤”,此處的“獨”指只是、僅僅;《石鐘山記》:“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而此獨以鐘名,何哉”,此處的“獨”還指唯獨。再看“酌”字,通常指飲酒,例如《歸去來辭》:“引壺觴以自酌”。“酌”也指經過衡量取舍,“酌量”就是考慮、估量之意。由此可見,詩題的“獨酌”指的是詩人自斟自飲,月下獨自飲酒,體現了詩人孤獨寂寞的心境。
根據語義場(semantic field)理論,某個詞義是由構成這一意義的各種關聯義素(meaning component)組成,而詞義的確定是由該詞與其他詞義所構成的縱聚合和橫組合關系搭配決定的〔3〕。近年來,學者們又注意到了“表達性語義場(semantic field of expression)”〔4〕,即具有動態性、即時性、新穎性但又合理、合情、合俗的語義場〔5〕,這對詩歌意象意義的解讀具有很好的解釋力。詩中“獨酌”意象的“獨”與“酌”本來不在同一語義場,但從表達語義場視角來看,兩者在此處在同一語義場,彼此產生了意義的滲透、兼容和互義的表達效果,構建起了特定的語義場意象。
根據《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獨”被定義為: single(單), solitary(孤), unique(特),only(唯);“酌”被定義為:drink(飲酒),consider(考慮)〔6〕。 由此,“獨”和“酌”的義素可分別描寫為:

在《月下獨酌》中,“獨”“酌”在特定的意境下構成了表達性搭配,故而兩詞原有的義素相互滲透、相互參照、相互釋義,構成了“不完全規約性”的表達性語義場〔4〕,如表1所示。

表1 義素與意象的滲透
“獨”的相關義素包含了“單”“孤”“特”“唯”,每個義素在原詩中都能組成相關的意象。“單”指“一”,即“一壺”,“各分散”中的“各”;“孤”指無人陪伴,即“無相親”;“特”指的是某種行為,詩中的相關意象有“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無情游”;“唯”是“僅僅”“只”,月亮和影子緊隨詩人,體現在“隨我身”、“月徘徊”和“影凌亂”中。
“酌”的相關義素包含了“飲酒”“考慮”,根據義素本意,原詩中這些義素的相關意象指舉杯飲酒的有“不解飲”“行樂”“同交歡”“舉杯”,從側面體現“考慮”和“思索”的相關意象是 “暫伴”“及春”“永結”“相期”。
圍繞“獨酌”這一中心意象,作者精心設置了一系列關聯意象,而關聯意象的表達性語義場必然與中心意象的表達性語義場契合,譯者只有透徹分析中心意象,才能把握關聯意象與中心意象之關系,從而凸顯詩題。
四、《月下獨酌》譯本之關聯意象
《月下獨酌》以豐富獨特的想象、虛實結合的意象轉換,細致入微地刻畫了詩人心理狀態和生活現實。本文選最能體現整體詩歌脈絡及故事發展情節的典型意象“無相親”、“邀明月”、“月徘徊”、“影凌亂”和“無情游”作為主要分析對象,以英國漢學家韋利、翟理斯,日本學者小畑薰良以及許淵沖先生的英譯文為分析文本,以探究詩歌翻譯中意象與義素的關系,并通過“解碼”義素,判斷出譯者是否較為準確地重構原詩意象。
1.無相親
“無相親”描述的是詩人獨自飲酒、周圍并無旁人的場景。“無相親”的“親”字可以作為父母,如“馮公有親乎”(《馮諼客親(親)孟嘗君》);“親”可以為親人,如“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芙蓉樓送辛漸》);“親”也可以指親近、接近,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出師表》);“親”還可以指親近的人,如“疏而不親還是不說罷”〔7〕(《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新世紀漢英大詞典》將“親”解釋為: “intimate”“close”“parent”“relative”“kiss” “marriage”“ try to be close to”〔6〕。根據詩歌中心意象“獨酌”的語義場推斷,此處的“相親”義素成分為:

“無相親”表達性語義場當為“沒有親近的人陪伴”。四種譯文描述“無相親”分別有韋利譯文“no friends is near”〔8〕、翟里斯譯文“no companion is mine”〔9〕、小畑薰良譯文“where are my friends? Ah,the moon above looks down on me”〔10〕和許淵沖譯文“beneath the bright moonshine”〔11〕。其語義場分別為:韋利譯文中“friends”所含義素“assistant”“fellow”“aid”,此外,“near”含有義素 “familiar”“close”“next”。翟里斯譯文中“companion”所含義素 “friend”“guide”“fellow”“manual”“notebook”。小畑薰良譯文中“Ah” 表驚奇、高興、贊賞、同情或不同意的語氣詞,作“啊、呀”,這里的“Ah”是表達同情,小畑薰良把原詩譯作“唉,只有月亮俯視著我”,其中“the moon”所含義素為“bright”“quiet”“alone”。許淵沖譯文中“the bright moonshine”只翻譯了背景意象“皎潔的月光”。對比“相親”的義素,小畑薰良譯文和許淵沖譯文在表達“無相親”時用“月亮”和“月光”表述,不符合“無相親”的中心意象語義場,譯者沒有考慮“無相親”中“親”字的內涵意義,所以韋利譯文的“friend” 和翟里斯譯文的“companion”描述“無相親”的“親”更為妥帖。
2.邀明月
李白從小鐘情于明月,他在《古朗月行》中說:“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青云端。”在李白幼小的心靈里,明月是光明皎潔的,他常常借明月寄托自己的理想,熱切地追求著月亮。在他的詩作中有許多有關明月的描寫。在《把酒問月》里:“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里:“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明月也常常使李白回憶起他的故鄉,《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明月也使他思念家鄉,“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一看到明月就想起峨眉,想起家鄉四川來。明月對于李白也是一位親密的朋友:“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夢游天姥吟留別》);“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可見李白一直把月亮視為友人。
“邀”,有邀請的意思,如《琵琶行》:“移船相近邀相見”。“邀”可指半路攔截,如《晉書·陶潛傳》:“于半道邀之”。“邀”還指求取,如王充《論衡·自然》:“不作功邀”。“邀”還可指要挾,如《教戰守策》:“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7〕。 “月”,月亮,如《赤壁賦》:“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新漢英大辭典》的“邀”為:“invite”“request”“seek approval”“ask permission”“serve”“calling”“intercept”〔12〕。《牛津詞典》、《柯林斯英漢雙解大詞典》和《新漢英大辭典》分別把“明月”闡釋為“a full moon”“a big moon”“a giant moon”“a bright moon”。由此可知,此處“邀”的動態義素和“明月”的義素分別為:


“邀明月”達成的表達性語義場的四種譯文分別為:韋利譯文“beckon the bright moon”〔8〕、翟里斯譯文“the moon sheds her rays”〔9〕、小畑薰良譯文“call his brightness”〔10〕和許淵沖譯文“invite the Moon”〔11〕。“邀”從上述語義場來看,許淵沖譯文中“invite”的語義場除 “召喚”含義之外,還具有“邀”語義范疇中的“邀請”“誠邀”“約請”的含義;而翟里斯譯文,僅用“the moon sheds her rays”,變賓語為主語,未能準確還原意象。韋利譯文和小畑薰良譯文中“beckon”和“call”僅有“號召”“召喚”“吸引”的含義,用“beckon”和“call”來表達“邀”字,其語義內涵不夠精確,均不能較準確地重構原詩意象。因此,比較四種譯文,許淵沖譯文中“invite”表達“邀”更為貼切。“明月”,從上述語義場來看,韋利譯文中的“the bright moon”較為貼切,突出了明月高懸、皓月當空、月明如鏡的皎潔感。
3.月徘徊
“月徘徊”是詩人想象中月亮隨他的歌聲來回游蕩的場景。《古漢語常用字字典》中“徘徊”有來回地走動、猶豫不決、心緒不定的含義〔7〕。如方苞《贈魏方甸序》:“次年春滏陽公按試諸郡,惟余與生留舍署之西偏庭,空無人時蔭高樹俯清池徘徊草露間”,指的是庭院空寂沒有人,我們時常在高樹下乘涼,俯看清池,在草露之間徘徊流連。《新漢英大辭典》中“徘徊”為: “pace up and down” “linger about”“tramp”“hesitate”“waver”“hover”〔12〕。因此,“徘徊”的語義場如下:

“月徘徊”這樣的表達性語義場,在翻譯中應考慮其“語義場效應的關聯性”〔13〕。對此的四種譯文分別為:韋利譯文“the moon flickers her beams”〔8〕、翟里斯譯文“she dances response to”〔9〕、小畑薰良譯文“the wild moon wanders the sky”〔10〕和許淵沖譯文“the Moon lingers to hear”〔11〕。從上述“徘徊”的語義列表來看,小畑薰良譯文中“wander”有徘徊、漫步、游蕩的含義,許淵沖譯文中“linger”有緩慢度過、消磨時光的意義,所以這兩個詞比較貼合原詩意象。“徘徊”之中并無“顫動”、“搖曳”和“舞蹈”的意思,所以韋利譯文中的“flicker”和翟里斯譯文中的“dance”偏離了主題意象。
4.影零亂
根據《古漢語常用字字典》,“零”可指下雨,如《詩經》:“零雨其濛”;“零”也可表達淚水等像雨一樣落下,如《出師表》:“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零”是凋落、凋謝,如《秋聲賦》:“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余烈”;“零”還可以是零碎的、零散的,如《高祖還鄉》:“零支子米麥無重數”。再觀“亂”字,《曹劌論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此處的“亂”表示紊亂,沒有秩序、沒有條理;《答謝中書書》:“曉霧將歇,猿鳥亂鳴”,此處的“亂”表示混雜、混淆;《教戰守策》:“使其耳目習于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此處的“亂”指慌亂、零亂;《陋室銘》:“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這里的“亂”指的是擾亂、破壞〔7〕。而《新漢英大辭典》中“零亂”指 “all over the shop /place/show”“in disorder” “in a mess”“ untidy”〔12〕。由此可知,“零亂”的義素成分為:

“影零亂”的四種譯文分別為:韋利譯文“my shadow tangles and breaks”〔8〕、翟里斯譯文“my shadow-it dances so lightly”〔9〕、小畑薰良譯文“my shadow goes tumbling”〔10〕和許淵沖譯文“my shadow’s a mess”〔11〕。根據中心語義場分析,韋利譯文中“tangles and breaks”可表示詩人在跳舞時光影重重、相互交織,形成了影子亂糟糟的意象。許淵沖譯文中“mess”也有混雜、紊亂的含義。因此,這兩個單詞較為貼合地表達了“零亂”之意,也與“我歌月徘徊”組成了歌舞交融的語義場。“零亂”并沒有“起舞”和“摔倒”的義素,與“影”構成的語義場不能兼容,所以翟里斯譯文中的“dance”和小畑薰良譯文中的“tumbling”有些偏離了原詩意象。
5.無情游
朱諫對“無情游”注:“無情者,月與我雖曰三人,然月與影本無情也。”(1)〔明〕朱諫《李詩選注十三卷》之十二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全申刊本第80頁。“月”與“影”都是自然永恒的物象,人亦可以寄予情。詩人寄情于月亮和影子,想要忘卻世俗情感去追求出世的、長久的友誼。這里的“無情”是一種歷久彌新、永恒而真摯的感情。“無情”在本詩中的義素為:

“無情游”語義場的四種譯文分別為:韋利譯文“our odd ,inanimate feast”〔8〕、翟里斯譯文“a greeting with-out a goodbye”〔9〕、小畑薰良譯文“a friendship no mortals know”〔10〕和許淵沖譯文“our friendship will outshine all earthly love”〔11〕。韋利譯文中“inanimate”在《柯林斯英漢雙解大詞典》中釋義為“dead ”“lifeless”,“odd”所含義素有“strange”“remaining”“extraordinary”“temporary”“surplus”“residual”,“inanimate”與“odd”這兩個單詞的義素都與“無情”的主題意象語義場無關,偏離了語義中心。小畑薰良譯文中“no mortals know”和翟里斯譯文中“with-out a goodbye”,均沒有表達出詩人的情感,模糊了原詩意象。因此,針對“無情游”的翻譯,只有許淵沖譯文“our friendship will outshine all earthly love”的意象與原詩意象貼合,并與詩歌的前幾句中“drink alone”“friends”“the moon”“my shadow”相呼應,形成了完整的表達性語義場。
五、結語
譯詩難,譯中國古詩難度更甚,從義素與語義場的角度分析四位大家的翻譯不失為一種詩歌翻譯分析方法。詩歌的翻譯,需要譯者深入挖掘詩歌意象的表達性語義場,探究詩歌的主題和蘊含文化細節,把握詩歌中心意象,圍繞中心意象對相關意象進行理解和解讀。在這一過程中,譯者要以嚴謹的態度探究詞句的淵源,通過把握基礎義素,充分感知詩歌的詞句,感知原文所描寫的意象,將譯詩融于原詩所構成的完整表達性語義場中,真正展現出原詩的完整表達性意象。只有當譯者融入詩歌的意境中,層層探尋義素,融“詞”入“境”,才能讓讀者深刻理解詩人所表達的“詩情”以及詩人想要向讀者展示的“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