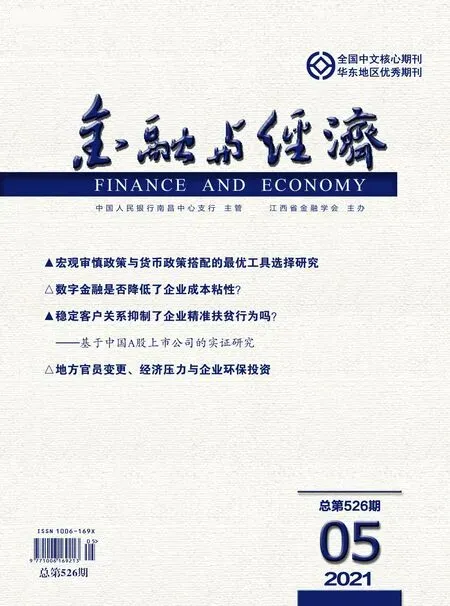人民幣匯率預(yù)期對(duì)短期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的動(dòng)態(tài)分析
■龐 川,楊 光
一、引言與文獻(xiàn)綜述
自20世紀(jì)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匯率波動(dòng)的頻率和幅度加劇,呈現(xiàn)出同資產(chǎn)價(jià)格變化相似的特點(diǎn),傳統(tǒng)宏觀匯率決定理論已很難解釋這一現(xiàn)象。匯率決定的資產(chǎn)市場(chǎng)說(shuō)出現(xiàn)后,人們開始關(guān)注預(yù)期在外匯市場(chǎng)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最早的預(yù)期理論是理性預(yù)期假設(shè),由Muth于1960年提出,他認(rèn)為理性人在對(duì)某個(gè)經(jīng)濟(jì)變量做估計(jì)時(shí),會(huì)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有效信息。然而,現(xiàn)實(shí)世界中信息獲取費(fèi)用的差異必然會(huì)導(dǎo)致信息不對(duì)稱,進(jìn)而使不同信息主體產(chǎn)生不同的預(yù)期。此后,學(xué)者們又先后提出了外推型匯率預(yù)期、適應(yīng)性匯率預(yù)期、回歸型匯率預(yù)期和混合模型。上述分析方法都隱含了一個(gè)假設(shè)前提,即:外匯市場(chǎng)參與者擁有相同的公共信息,且對(duì)這些信息的理解無(wú)差異,也就是具有相同的預(yù)期。這一隱含的假設(shè)引起了廣大學(xué)者的質(zhì)疑,Ito(1990)的分析發(fā)現(xiàn),市場(chǎng)主體的預(yù)期具有明顯的差異。Benassy et al.(2003)分別利用面板數(shù)據(jù)的固定效應(yīng)模型與隨機(jī)效應(yīng)模型對(duì)四種不同匯率預(yù)期模型進(jìn)行分析,發(fā)現(xiàn)四種不同匯率預(yù)期模型會(huì)被不同市場(chǎng)參與者在匯率預(yù)測(cè)過(guò)程中所采用,即使采用同一預(yù)期模型的市場(chǎng)參與者,也會(huì)對(duì)信息集賦予不同的權(quán)重。這表明市場(chǎng)參與者不僅在信息獲取上不對(duì)稱,對(duì)同一信息也持有不同理念。Derger&Stdatmnan(2008)在上述研究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考察了引起匯率預(yù)期異質(zhì)性的信息來(lái)源。他們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jì)基本面預(yù)期差異是匯率預(yù)期差異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同時(shí)指出這無(wú)法解釋參與者匯率預(yù)期差異的原因,市場(chǎng)參與者的匯率預(yù)期異質(zhì)性是由多種原因共同構(gòu)成。
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驅(qū)動(dòng)因素一直都是國(guó)際資本市場(chǎng)研究的熱點(diǎn)之一。早期關(guān)于跨境資本流動(dòng)驅(qū)動(dòng)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率、匯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和資產(chǎn)收益率以及制度因素和結(jié)構(gòu)性等因素上。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學(xué)者們發(fā)現(xiàn)匯率預(yù)期在影響短期跨境資本流動(dòng)因素中扮演著越來(lái)越重要的角色。陳浪南和陳云(2009)通過(guò)建立ARDL—ECM模型,將匯率預(yù)期作為影響因素,發(fā)現(xiàn)人民幣匯率預(yù)期對(duì)我國(guó)短期資本流動(dòng)具有長(zhǎng)期顯著影響。田濤(2016)研究發(fā)現(xiàn)在2005年及2010年匯改后短期國(guó)際資本流動(dòng)與人民幣匯率預(yù)期變動(dòng)率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顯著性增強(qiáng)。朱孟楠等(2017)發(fā)現(xiàn)匯率預(yù)期會(huì)通過(guò)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房?jī)r(jià),具體為人民幣匯率預(yù)期升值會(huì)促使跨境資本流入,而流入的資本對(duì)房?jī)r(jià)的影響卻與匯率預(yù)期的波動(dòng)強(qiáng)度有關(guān)。戴淑庚和余博(2019)基于半?yún)?shù)平滑系數(shù)模型從市場(chǎng)參與者獲取匯差、利差的動(dòng)機(jī)角度分析發(fā)現(xiàn),人民幣預(yù)期貶值會(huì)負(fù)向影響短期資本流動(dòng),特別是從2012年開始,人民幣預(yù)期貶值的影響大幅提升。
上述研究從不同角度證實(shí)了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具有顯著的作用,但都并沒(méi)有脫離傳統(tǒng)理性預(yù)期的分析框架,特別是沒(méi)有從市場(chǎng)參與者在不確定性狀態(tài)下,預(yù)期變化引起的風(fēng)險(xiǎn)偏好轉(zhuǎn)變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動(dòng)態(tài)影響的角度去探討。本文從微觀個(gè)體行為以及產(chǎn)生這種行為的心理動(dòng)因研究匯率預(yù)期形成機(jī)制,再分析該機(jī)制下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影響。
二、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的模型推導(dǎo)
考慮在外匯交易市場(chǎng)上,St為t時(shí)期的人民幣即期匯率,St+1-St為在t期投資的收益率,假設(shè)其分布函數(shù)為離散的,即:

市場(chǎng)參與者偏好包含以下三個(gè)組成部分:
第一,以預(yù)期價(jià)值最大化為目標(biāo)。與效用理論不同的是,預(yù)期價(jià)值最大化認(rèn)為人們?cè)谠u(píng)判效用時(shí),關(guān)注的不是財(cái)富最終量,而是財(cái)富的相對(duì)變化量,價(jià)值效用取決于財(cái)富值和參考點(diǎn)的差值,即所謂參照依賴。在選擇參照點(diǎn)時(shí),從時(shí)間維度上看具有即時(shí)效應(yīng)(immediacy effect),決策者偏好將近期事件作為參照點(diǎn)。從交易層面來(lái)說(shuō),大部分市場(chǎng)參與者對(duì)投資風(fēng)險(xiǎn)收益特征所形成的印象來(lái)源于近期的收益時(shí)間序列,更重要的是,市場(chǎng)參與者潛意識(shí)總是覺(jué)得過(guò)去的收益特征可以在未來(lái)進(jìn)行外推應(yīng)用。因此,本文假設(shè)市場(chǎng)參與者的參考點(diǎn)為人民幣即期匯率,當(dāng)市場(chǎng)參與者的收益大于0時(shí),投資給市場(chǎng)參與者帶來(lái)正效用;當(dāng)市場(chǎng)參與者的收益小于0時(shí),投資給市場(chǎng)參與者帶來(lái)負(fù)效用。第二,u+和u-分別表示投資收益的正、負(fù)效用函數(shù)。第三,在投資參考點(diǎn)上的概率權(quán)重函數(shù)分別為ω+和ω-,定義為市場(chǎng)參與者對(duì)投資收益的累計(jì)正值和負(fù)值的扭曲。
累計(jì)分布假定:
1.投資收益滿足0<Pr(St+1-St>0)<1。
2.市場(chǎng)參與者是損失規(guī)避的,投資收益的效用函數(shù)為對(duì)收益內(nèi)凹,對(duì)損失外凸,損失時(shí)的斜率比收益時(shí)的更加陡峭。
3.權(quán)重函數(shù)ω+和ω-不是單一的事件來(lái)計(jì)算分布函數(shù),即每個(gè)結(jié)果x不是以它發(fā)生的概率進(jìn)行加權(quán),而是以優(yōu)于或等于x的結(jié)果的累計(jì)概率和次于或等于x的結(jié)果的累計(jì)概率進(jìn)行加權(quán);ω+和ω-滿足:在[0,1]單增,且ω±(0)=0,ω±(1)=1。
4.設(shè)e為收益率,其中e1>e2>…>em≥0>em+1>…>en,m為收益率取值為正負(fù)的分界點(diǎn)。
離散形式的價(jià)值函數(shù)為:

其中,m(θ)為滿足em(θ)≥0>em(θ)+1的正整數(shù)(如果不存在m(θ)使得此式成立,則令m(θ)=n)。
本文采用Kahneman&Tversky(1992)提出的冪函數(shù)作為價(jià)值函數(shù):

其中,0<β<α<1,分別用來(lái)衡量收益和損失的價(jià)值函數(shù)的曲率,γ是損失厭惡系數(shù),越大代表市場(chǎng)參與者的損失厭惡越明顯。

其中,基于Kahneman&Tversky(1992)的心理實(shí)驗(yàn),選取該實(shí)驗(yàn)結(jié)果所對(duì)應(yīng)的扭曲程度來(lái)模擬市場(chǎng)參與者心理權(quán)重分布。具體公式為:

看各參數(shù)對(duì)需求的具體影響:
1.當(dāng)市場(chǎng)參與者情緒樂(lè)觀時(shí),其未來(lái)收益預(yù)期的分布會(huì)發(fā)生改變,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一是整體均值右偏,即(1)式中m(θ)增加,情緒極度樂(lè)觀時(shí)m(θ)=n,即市場(chǎng)參與者預(yù)期未來(lái)收益只會(huì)上升不會(huì)下跌,因此會(huì)不斷買入資產(chǎn),反之則下跌。這與傳統(tǒng)理性預(yù)期一致。
2.概率配權(quán)過(guò)程中,決策權(quán)重的大小取決于人們的擔(dān)憂程度,這被稱為“可能性效應(yīng)”。根據(jù)Abdellaoui(2000)實(shí)驗(yàn)結(jié)果,對(duì)(2)式參數(shù)賦值γ=0.61,δ=0.69,做圖1:

圖1 概率估算函數(shù)
當(dāng)重大金融事件發(fā)生時(shí),人們的情緒受到影響,特別是當(dāng)恐慌情緒或極度樂(lè)觀情緒主導(dǎo)時(shí),人們往往會(huì)對(duì)小概率極端事件賦予較大權(quán)重。在這種情況下,重大金融事件發(fā)生時(shí),即使基本面沒(méi)有發(fā)生顯著變化,市場(chǎng)參與者也會(huì)高估事件對(duì)未來(lái)的影響。
3.α、β代表收益和損失的邊際敏感度。相對(duì)于財(cái)富的增加,市場(chǎng)參與者對(duì)于同等程度的財(cái)富減少更為敏感,即β>α。同時(shí),γ損失厭惡系數(shù)使得市場(chǎng)參與者面對(duì)損失時(shí)容易產(chǎn)生恐慌心理,放大損失預(yù)期的影響。由此可知,因預(yù)期本幣升值所導(dǎo)致買入量遠(yuǎn)低于同等程度本幣貶值預(yù)期所導(dǎo)致的本幣賣出量,即在升值期和貶值期,匯率預(yù)期對(duì)本幣持有量的影響呈現(xiàn)非對(duì)稱性。
4.根據(jù)前景理論,由于損失厭惡的存在,大多數(shù)人在面臨獲利的時(shí)候是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的,即在確定的收益和“賭一把”之間,人們總是傾向于確定的收益這被稱為“確定性效用”;而在面對(duì)未來(lái)大概率損失和“賭一把”之間,人們又是風(fēng)險(xiǎn)偏好的,會(huì)選擇“賭一把”,這被稱為“反射效應(yīng)”。Thaler&Johnson(1990)通過(guò)研究二階段框架下被試選擇風(fēng)險(xiǎn)選項(xiàng)發(fā)現(xiàn),與前景理論相反,由于“私房錢效應(yīng)”,先前獲益的二階段框架下決策者風(fēng)險(xiǎn)偏好更高,即所謂“追漲”。而在面臨損失時(shí),除非未來(lái)預(yù)期收益大概率能挽回先前損失,否則人們將是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的。而本文的理論推導(dǎo)結(jié)論與Thaler&Johnson(1990)一致。
三、風(fēng)險(xiǎn)偏好檢驗(yàn)
(一)模型的檢驗(yàn)
近些年來(lái),隨機(jī)占優(yōu)準(zhǔn)則是衡量市場(chǎng)參與者投資決策普遍認(rèn)可的準(zhǔn)則。通過(guò)運(yùn)用二階隨機(jī)占優(yōu)理論,不需要對(duì)投資者需要規(guī)避的風(fēng)險(xiǎn)因子以及風(fēng)險(xiǎn)資產(chǎn)收益的分布做太多假設(shè),就可以對(duì)風(fēng)險(xiǎn)資產(chǎn)進(jìn)行排序并且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對(duì)所有的理性投資者都是適用的。他可以很好地驗(yàn)證市場(chǎng)參與者的投資決策特征。
假設(shè)F(x)和G(x)分別是兩個(gè)不同資產(chǎn)的累積概率分布,x為不確定的收益,U表示效用函數(shù)。若F(x)<G(x),則認(rèn)為F占優(yōu)G,因?yàn)樵谌魏螚l件下,F(xiàn)資產(chǎn)收益大于x的累積概率均大于G資產(chǎn)。
對(duì)于風(fēng)險(xiǎn)厭惡者(即滿足U(x)′>0,U(x)″<0)來(lái)說(shuō),若F占優(yōu)G,則二階隨機(jī)占優(yōu)為:

本文主要按照Davidson&Duclos(2000)提出的隨機(jī)占優(yōu)改進(jìn)方法(以下簡(jiǎn)稱DD方法)對(duì)外匯市場(chǎng)是否符合前景理論開展實(shí)證檢驗(yàn)。具體步驟如下:

風(fēng)險(xiǎn)資產(chǎn)收益rji同理。
一階隨機(jī)占優(yōu)主要針對(duì)目標(biāo)效用最大化且永遠(yuǎn)不知滿足的投資者;二階隨機(jī)占優(yōu)針對(duì)永不滿足且風(fēng)險(xiǎn)厭惡的投資;根據(jù)前文的理論假設(shè),本文主要通過(guò)二階隨機(jī)占優(yōu)檢驗(yàn)。假設(shè)提出如下:

如果H0成立則表明風(fēng)險(xiǎn)資產(chǎn)占優(yōu),此時(shí)市場(chǎng)參與者風(fēng)險(xiǎn)偏好增大,損失厭惡系數(shù)γ變小,損失的邊際敏感度β也降低,收益的邊際敏感度α增加。若H1成立則表明相對(duì)于風(fēng)險(xiǎn)資產(chǎn),無(wú)風(fēng)險(xiǎn)資產(chǎn)占優(yōu),這表明此時(shí)市場(chǎng)參與者損失厭惡系數(shù)γ增大,損失的邊際敏感度β也增大。構(gòu)造統(tǒng)計(jì)變量如下:


Davidson&Duclos(2000)已經(jīng)證明Ts(x)漸進(jìn)服從studentized最大模分布(SMM分布)。當(dāng)Ts(x)顯著為正,則表示市場(chǎng)參與者風(fēng)險(xiǎn)偏好增加,傾向買入風(fēng)險(xiǎn)資產(chǎn)。
(二)實(shí)證檢驗(yàn)
為深入探究我國(guó)外匯市場(chǎng)市場(chǎng)參與者的決策偏好特征,采用DD隨機(jī)占優(yōu)方法,選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作為風(fēng)險(xiǎn)資產(chǎn),三年期存款利率作為無(wú)風(fēng)險(xiǎn)資產(chǎn)。同時(shí),結(jié)合前面的理論模型分析,將實(shí)證檢驗(yàn)分為樣本期、人民幣匯率上漲期和人民幣匯率下跌期。2006年1月—2008年12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主要處于單邊升值階段。2015年4月—2017年3月,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經(jīng)濟(jì)正處于三期疊加,再加上“8·11”匯改后,境外一些投機(jī)力量渲染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悲觀前景,通過(guò)加杠桿增持人民幣空倉(cāng),共同造成人民幣貶值走勢(shì)。2018年8月—2019年5月,受中美貿(mào)易摩擦沖擊人民幣快速貶值。本文將上述三期分別代表人民幣匯率上漲階段和下跌階段期間進(jìn)行實(shí)證檢驗(yàn)。

表1 二階隨機(jī)占優(yōu)DD統(tǒng)計(jì)量
從表1的二階隨機(jī)占優(yōu)進(jìn)行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在整個(gè)樣本期間的DD統(tǒng)計(jì)量都顯著為負(fù),表明總體上看市場(chǎng)參與者是風(fēng)險(xiǎn)厭惡的。分區(qū)段看,在人民幣匯率上漲期,DD統(tǒng)計(jì)量顯著為正,這表明受樂(lè)觀預(yù)期影響市場(chǎng)參與者風(fēng)險(xiǎn)偏好增加,買入本幣資產(chǎn)是占優(yōu)策略。而在兩個(gè)下跌區(qū)段,DD統(tǒng)計(jì)量均顯著為負(fù)。這表明面對(duì)損失時(shí),市場(chǎng)參與者表現(xiàn)為風(fēng)險(xiǎn)厭惡。實(shí)證結(jié)果表明我國(guó)外匯市場(chǎng)參與者風(fēng)險(xiǎn)偏好與理論模型分析一致。
四、實(shí)證研究
(一)模型框架
為驗(yàn)證外匯市場(chǎng)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影響,根據(jù)匯率形成機(jī)制及現(xiàn)有研究文獻(xiàn),設(shè)定短期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匯率預(yù)期、利差情況、產(chǎn)出、美國(guó)貨幣政策環(huán)境和央行外匯干預(yù),并據(jù)此建立實(shí)證模型的基本框架:

其中,下標(biāo)t表示時(shí)間,cf表示跨境資本流動(dòng)情況,e表示匯率預(yù)期,rate表示利差情況,gdp表示產(chǎn)出,us表示美國(guó)貨幣政策,int表示央行外匯干預(yù)。
選取如下主要指標(biāo):
衡量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指標(biāo)(Y)。本文將銀行結(jié)售匯差額作為度量資本流動(dòng)的指標(biāo)。
市場(chǎng)參與者匯率預(yù)期(X1)。本文假定外匯市場(chǎng)參與者在選擇參照點(diǎn)時(shí)存在“即時(shí)效應(yīng)”,參照點(diǎn)為即期匯率。X1采用1年期與參照點(diǎn)當(dāng)期匯率差值表示。
美聯(lián)儲(chǔ)貨幣政策變化(X2)。本文采用美國(guó)圣路易斯金融壓力指數(shù)變化來(lái)反映,該指數(shù)能很好地衡量美聯(lián)儲(chǔ)貨幣政策變化導(dǎo)致的美元融資條件變化。金融壓力指數(shù)變化采用當(dāng)期壓力指數(shù)減去上一期指數(shù)。
中美利差變化(X3)。鑒于銀行間同業(yè)拆借市場(chǎng)交易日趨頻繁,規(guī)模日益擴(kuò)大,能反映信貸市場(chǎng)資金豐裕或短缺的風(fēng)向,因而選擇隔夜拆借利率指標(biāo)作為本國(guó)利率的替代指標(biāo),國(guó)外利率用美國(guó)聯(lián)邦基金利率,國(guó)內(nèi)外利差采用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與聯(lián)邦基金利率之差表示,國(guó)內(nèi)外利差變化采用當(dāng)期利差減去上一期。
國(guó)內(nèi)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情況(X4)。由于數(shù)據(jù)頻率限制和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現(xiàn)狀,本文采用工業(yè)增加值增速來(lái)衡量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情況。
外匯干預(yù)(X5)。由于央行并未公布外匯市場(chǎng)干預(yù)具體數(shù)據(jù),因此采用測(cè)算方法,測(cè)算方式為外匯儲(chǔ)備變動(dòng)減去境外投資收益①一般而言,央行外匯干預(yù)是外匯儲(chǔ)備余額變動(dòng)的主導(dǎo)因素,央行外匯儲(chǔ)備余額變動(dòng)量被較多學(xué)者用來(lái)衡量央行外匯干預(yù)。,其中境外投資收益等于我國(guó)持有的美國(guó)國(guó)債乘以美國(guó)聯(lián)邦基金利率。
本文所選樣本數(shù)據(jù)均來(lái)自Wind數(shù)據(jù)庫(kù),樣本數(shù)據(jù)期限為2006年1年月—2019年5月。所有數(shù)據(jù)樣本的頻率均為月度值。部分缺失的數(shù)據(jù)(主要為個(gè)別利率數(shù)據(jù))采用三期移動(dòng)平均進(jìn)行填補(bǔ)。
(二)建模思路及估計(jì)結(jié)果
首先,采用單位根檢驗(yàn)來(lái)判斷平穩(wěn)性,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各變量均為平穩(wěn)變量。其次,考察自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問(wèn)題。從變量間相關(guān)系數(shù)矩陣可以發(fā)現(xiàn),變量間相關(guān)系數(shù)均顯著低于1,因此可以認(rèn)為解釋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最后,在前文理論模型的基礎(chǔ)上,分為三步:第一,從簡(jiǎn)單線性回歸分析入手,驗(yàn)證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具有顯著性。第二,將匯率預(yù)期的影響彈性放松,設(shè)立變化門檻,建立門限回歸模型,驗(yàn)證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效應(yīng)具有變化性。第三,進(jìn)一步建立可變參數(shù)狀態(tài)空間模型,驗(yàn)證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效應(yīng)的時(shí)變特點(diǎn)。
基本回歸分析結(jié)果見表2。從結(jié)果看出,回歸方程各系數(shù)基本顯著,回歸方程通過(guò)檢驗(yàn),方程可決系數(shù)達(dá)到0.64。從匯率預(yù)期指標(biāo)X1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影響看,其影響系數(shù)為-371.28,p值為0.0003,表明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具有顯著負(fù)向影響。更進(jìn)一步,普通線性回歸方程可決系數(shù)為0.64仍然較低,模型并不具有特別好的擬合度。結(jié)合實(shí)際情況看,根據(jù)前景理論,市場(chǎng)參與者匯率預(yù)期具有一定變化性。為此,在簡(jiǎn)單回歸模型基礎(chǔ)上,設(shè)定預(yù)期指標(biāo)X1具有門限特點(diǎn),建立門限回歸模型。經(jīng)AIC、SCI信息準(zhǔn)則檢驗(yàn),模型具有1個(gè)門限,X1取值0.133為門限,各變量參數(shù)和模型均通過(guò)檢驗(yàn),回歸結(jié)果見表2。

表2 跨境資本流動(dòng)基本回歸和門限回歸模型比較
結(jié)果顯示,當(dāng)考慮預(yù)期對(duì)匯率預(yù)期的影響不固定時(shí),模型的估計(jì)精度得到提升,這表明x1具有門限的假定是合理的,這也驗(yàn)證了匯率預(yù)期可變的論斷。從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影響看,匯率預(yù)期指標(biāo)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系數(shù)波動(dòng)具有明顯異質(zhì)性。值得關(guān)注的是,市場(chǎng)參與者的參照點(diǎn)并不是0,而是以0.133為參照點(diǎn),這是因?yàn)槟壳爸袊?guó)還存在一定的資本管制,跨境資本流動(dòng)具有交易成本,只有預(yù)期未來(lái)匯率上漲能夠超過(guò)交易成本其收益才為正。當(dāng)X1>0.133時(shí),也就是具有較強(qiáng)升值預(yù)期時(shí),其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影響系數(shù)為-168.59,當(dāng)X1<0.133時(shí)則影響系數(shù)為-1417.7,下跌預(yù)期的影響系數(shù)明顯強(qiáng)于上升預(yù)期,這也進(jìn)一步體現(xiàn)了前文理論分析中市場(chǎng)參與者風(fēng)險(xiǎn)厭惡的特點(diǎn)。
更進(jìn)一步,考慮到2005年以來(lái)我國(guó)外匯管理體制發(fā)生較大變化,特別是國(guó)際金融危機(jī)沖擊下,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發(fā)生較大調(diào)整,各影響因素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影響也會(huì)有變化。市場(chǎng)參與者預(yù)期不僅會(huì)影響跨境資金流動(dòng)方向,同時(shí),受參照點(diǎn)、權(quán)重函數(shù)、邊際敏感度、損失厭惡系數(shù)變化影響,其彈性系數(shù)大小也會(huì)具有時(shí)變性。從實(shí)際情況看,2006年以來(lái)市場(chǎng)參與者匯率預(yù)期也呈現(xiàn)明顯的變化,貶值期(2006—2012年)的標(biāo)準(zhǔn)差為0.202,而在預(yù)期升值期(2012年以來(lái))標(biāo)準(zhǔn)差僅為0.07,預(yù)期貶值期波動(dòng)更明顯;在金融危機(jī)(2008—2009年)沖擊時(shí)期,匯率預(yù)期波動(dòng)標(biāo)準(zhǔn)差為0.269,事件沖擊時(shí)波動(dòng)加劇,這也充分驗(yàn)證了市場(chǎng)參與者在對(duì)概率事件賦權(quán)時(shí)具有“可能性”效應(yīng)的特征。基于這些考慮,采用固定參數(shù)的模型就無(wú)法得到相對(duì)準(zhǔn)確的刻畫。
因此,進(jìn)一步采用可變參數(shù)狀態(tài)空間模型估計(jì)匯率預(yù)期對(duì)持匯行為影響。在構(gòu)建模型時(shí),本文認(rèn)為匯率預(yù)期除了受月度數(shù)據(jù)遞歸關(guān)系影響外,還受到政策引導(dǎo)等外在沖擊,因此對(duì)于匯率預(yù)期的轉(zhuǎn)態(tài)方程設(shè)定了隨機(jī)沖擊,即服從隨機(jī)游走過(guò)程,而對(duì)于其他影響變量,本文認(rèn)為主要受月度遞歸關(guān)系影響,因此設(shè)定為遞歸過(guò)程。具體模型如下:
信號(hào)方程:

采用卡爾曼濾波對(duì)方程進(jìn)行動(dòng)態(tài)分析和求解,選擇Marquardt算法,進(jìn)行12次迭代后成功收斂,結(jié)果顯示sv1—sv5均顯著,對(duì)模型進(jìn)行Wald系數(shù)檢驗(yàn),在5%顯著性水平上通過(guò)檢驗(yàn)。因此,狀態(tài)空間模型具有較好的擬合效果,能夠揭示各因素對(duì)于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沖擊。

圖2 各因素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系數(shù)的時(shí)變情況
(三)結(jié)果分析
1.匯率預(yù)期影響的時(shí)變特點(diǎn)
從影響跨境資本流動(dòng)各因素的可變系數(shù)看,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影響系數(shù)呈現(xiàn)明顯的時(shí)變特點(diǎn),并且隨著時(shí)間變化波動(dòng)越來(lái)越明顯,而其他變量則在前期出現(xiàn)明顯波動(dòng),后期則呈現(xiàn)收斂。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系數(shù)為負(fù)值,這表明當(dāng)預(yù)期人民幣升值時(shí),市場(chǎng)參與者會(huì)買入人民幣拋售美元,反之則不是。預(yù)期系數(shù)通過(guò)顯著性檢驗(yàn)也驗(yàn)證了理論模型中關(guān)于參照點(diǎn)的假設(shè):價(jià)值效用取決于財(cái)富值和參考點(diǎn)的比較,由于“即時(shí)效應(yīng)”的影響,外匯市場(chǎng)參與者做決策時(shí)以即期匯率作為參考點(diǎn)。
2.事件沖擊對(duì)預(yù)期系數(shù)的影響
從匯率預(yù)期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影響的彈性系數(shù)看,2010年前影響系數(shù)總體較為平穩(wěn),但2010年后出現(xiàn)波動(dòng)加大,特別是2015年下半年波動(dòng)進(jìn)一步明顯(見圖3)。斷點(diǎn)檢驗(yàn)發(fā)現(xiàn),最顯著的三個(gè)斷點(diǎn)出現(xiàn)在2010年12月、2013年1月和2015年4月。
從圖4看,第一階段2010年12月—2013年1月期間,人民幣持續(xù)升值,樂(lè)觀情緒主導(dǎo)市場(chǎng),市場(chǎng)參與者對(duì)人民幣匯率積極的小概率事件賦予了較高的權(quán)重,與前期相比,即期匯率相同幅度的升值情況下,市場(chǎng)參與者會(huì)持有更多的人民幣(結(jié)匯),彈性系數(shù)不斷變大。

圖3 匯率預(yù)期系數(shù)與即期匯率

圖4 匯率預(yù)期系數(shù)與央行外匯干預(yù)
第二階段2013年1月—2015年4月,匯率預(yù)期的彈性系數(shù)迅速縮小。一方面,相比前期,人民幣升值幅度放緩,2014年1月—2014年6月一度出現(xiàn)貶值;另一方面,結(jié)合圖4看,此階段央行加大了對(duì)外匯市場(chǎng)的干預(yù),有效的干預(yù)措施減弱了匯率預(yù)期的彈性系數(sh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12月—2015年4月間,人民幣匯率出現(xiàn)明顯的貶值,匯率預(yù)期的彈性系數(shù)迅速擴(kuò)大,盡管在此期間央行也進(jìn)行了干預(yù),但未能如前期升值階段那樣減弱匯率預(yù)期的彈性系數(shù)。升值階段與貶值階段預(yù)期彈性系數(shù)變化的不對(duì)稱性,充分驗(yàn)證了損失厭惡的假設(shè),即市場(chǎng)參與者對(duì)于同等程度的財(cái)富減少比增加更為敏感。相比于樂(lè)觀情緒,當(dāng)恐慌情緒主導(dǎo)市場(chǎng)時(shí),市場(chǎng)參與者的行為更加非理性。
第三階段2015年4月—2019年1月,匯率預(yù)期的彈性系數(shù)迅速變大,并在2015年12月達(dá)到整個(gè)樣本的最大值。這一階段匯率預(yù)期的彈性系數(shù)急劇變化主要有幾個(gè)重要事件導(dǎo)致:一是人民幣進(jìn)入貶值階段,損失厭惡加劇以及邊際敏感度比值擴(kuò)的影響下,市場(chǎng)參與者對(duì)人民幣貶值極度敏感;二是2015年8月啟動(dòng)8·11匯改,人民銀行宣布調(diào)整人民幣對(duì)美元匯率中間價(jià)報(bào)價(jià)機(jī)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jià)機(jī)制進(jìn)一步市場(chǎng)化,更加真實(shí)地反映了當(dāng)期外匯市場(chǎng)的關(guān)系,匯率波動(dòng)加劇。此后,人民銀行通過(guò)拋售美元買入人民幣、提高離岸人民幣的拆借成本以及征收20%的外匯風(fēng)險(xiǎn)準(zhǔn)備金等方式對(duì)市場(chǎng)進(jìn)行干預(yù),匯率預(yù)期的彈性系數(shù)在2015年12月后逐步縮小。具體分析銀行結(jié)售匯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2015年12月—2016年1月,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幅度為3.06%,同期銀行結(jié)售匯逆差規(guī)模達(dá)到月均4666億元;2016年5月—6月,貶值幅度為2.6%,同期銀行結(jié)售匯逆差規(guī)模僅為月均832億元。兩次基本相同的貶值幅度,后者僅為前者的1/5。這也充分反映了“逆向調(diào)節(jié)”能夠降低市場(chǎng)參與者的敏感度,進(jìn)而達(dá)到穩(wěn)定匯率的目的。
3.中美貿(mào)易摩擦對(duì)匯率預(yù)期的影響

圖5 中美貿(mào)易摩擦期間匯率預(yù)期影響系數(shù)
盡管由于數(shù)據(jù)量原因,斷點(diǎn)檢驗(yàn)尚未顯示出2018年出現(xiàn)斷點(diǎn),但從匯率預(yù)期影響系數(shù)圖看,2018年下半年以來(lái)匯率預(yù)期影響出現(xiàn)放大的趨勢(shì)。同時(shí),匯率預(yù)期標(biāo)準(zhǔn)差僅為0.04,這表明市場(chǎng)參與者預(yù)期趨于一致,對(duì)貿(mào)易摩擦的負(fù)面影響賦予了較高的權(quán)重。
五、結(jié)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從外匯市場(chǎng)參與者的心理角度入手,通過(guò)理論和實(shí)證分析發(fā)現(xiàn):相較于傳統(tǒng)理論強(qiáng)調(diào)宏觀基本面因素,心理預(yù)期已成為影響短期跨境資本流動(dòng)重要因素,特別是在8·11匯改后,這一影響更加顯著。外匯市場(chǎng)參與者的“私房錢效應(yīng)”、損失規(guī)避效應(yīng)以及可能性效用的假設(shè)在實(shí)證中得到檢驗(yàn),這些因素導(dǎo)致市場(chǎng)參與者預(yù)期波動(dòng)并進(jìn)而導(dǎo)致短期跨境資本流動(dòng)的波動(dòng)。但其影響具有非對(duì)稱性,在人民幣匯率貶值期間,相較于升值期市場(chǎng)參與者更加敏感和非理性。同時(shí),實(shí)證中發(fā)現(xiàn)人民銀行在外匯市場(chǎng)的干預(yù)一定程度上能夠穩(wěn)定預(yù)期,進(jìn)而平抑匯率波動(dòng)。
基于研究結(jié)論,可以得出以下四點(diǎn)啟示:一是上述應(yīng)高度關(guān)注外匯市場(chǎng)預(yù)期的變化及其可能對(duì)跨境資本流動(dòng)產(chǎn)生的影響。二是外匯市場(chǎng)上,市場(chǎng)參與者普遍將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jià)視為匯率參照點(diǎn),而不重視人民幣兌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因此,應(yīng)進(jìn)一步完善“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雙錨匯率形成機(jī)制,引導(dǎo)市場(chǎng)參與者由單一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jià)作為參考點(diǎn)向更全面的指標(biāo)轉(zhuǎn)變。三是在遇到重大金融事件,市場(chǎng)預(yù)期波動(dòng)加劇時(shí),應(yīng)審慎、適當(dāng)?shù)鼐C合運(yùn)用市場(chǎng)溝通、央行干預(yù)等方式穩(wěn)定市場(chǎng)預(yù)期。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人民幣升值和貶值期,匯率預(yù)期彈性系數(shù)以及匯率預(yù)期本身變動(dòng)的非對(duì)稱性,因此在不同階段干預(yù)力度應(yīng)有所區(qū)別。四是要保持政策的穩(wěn)定性。只有外匯市場(chǎng)政策保持穩(wěn)定性和連貫性,市場(chǎng)主體才能更加相信中央銀行政策行為。倘若頻繁調(diào)整外匯政策,會(huì)造成市場(chǎng)預(yù)期的混亂,出現(xiàn)短期套利的投機(jī)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