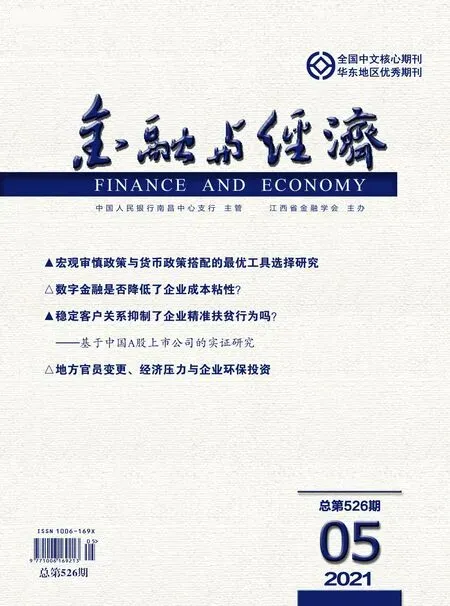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制度之審思與重構(gòu)
■鄭丁灝
一、引言
近年來,食品安全、環(huán)境污染與疫苗造假等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事件引發(fā)了社會(huì)各界的關(guān)注,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制度被我國列為貫徹新發(fā)展理念、構(gòu)建綠色金融體系的基礎(chǔ)性工作之一。同時(shí),2020年3月新出臺(tái)的《證券法》對(du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標(biāo)準(zhǔn)和更細(xì)的要求,為投資者全面獲取上市公司信息提供了權(quán)威的法律保障。然而,實(shí)踐中缺乏強(qiáng)制性效力與程序性規(guī)則的制度規(guī)范使我國上市公司的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呈現(xiàn)自愿性、任意性的特征,令投資者陷入逆向選擇的“檸檬市場”,難以實(shí)現(xiàn)信息披露的制度價(jià)值。因此,構(gòu)建以投資者為導(dǎo)向的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制度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從現(xiàn)有研究看,國外學(xué)者主要圍繞上市公司的“環(huán)境、社會(huì)與公司治理”(Environment,Society,Governance,ESG)信息披露體系展開探討。例如ESG信息的重大性認(rèn)定(Ruth Jebe,2019)、證券交易所在ESG信息披露中的定位(Federico Fornasari,2020)以及美國證券交易所的ESG信息披露改革(Roberta S.Karmel,2016)等,嘗試通過對(duì)ESG信息披露的理論解構(gòu)與規(guī)范剖析,探究其內(nèi)在的法理基礎(chǔ)與社會(huì)價(jià)值,并據(jù)此提出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制度完善路徑。相較之下,我國學(xué)術(shù)界有關(guān)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制度的針對(duì)性研究卻尚屬空白,雖有學(xué)者已關(guān)注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的信息披露問題(馮果,2020;袁利平,2020),但并未結(jié)合上市公司的組織特點(diǎn)及其監(jiān)管規(guī)范予以充分論述。鑒此,本文以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制度為研究對(duì)象,審思我國現(xiàn)有制度規(guī)范與2020年《證券法》中“投資者保護(hù)”目標(biāo)之間的差距,并結(jié)合歐盟與我國香港地區(qū)的制度經(jīng)驗(yàn),探尋重構(gòu)我國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法治路徑。
二、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
(一)強(qiáng)化上市公司主體責(zé)任的現(xiàn)實(shí)需求
強(qiáng)化上市公司主體責(zé)任是推動(dòng)上市公司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工作重點(diǎn)。基于上市公司的公眾特質(zhì),其在支配社會(huì)因素的能力上尤為突出,對(duì)環(huán)境、社會(huì)與內(nèi)部治理均產(chǎn)生實(shí)質(zhì)影響,故其主體責(zé)任理應(yīng)涵蓋以維護(hù)公共利益為宗旨的社會(huì)責(zé)任。為此,對(duì)上市公司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的行為施以信息披露要求,強(qiáng)制其實(shí)行更高程度的“社會(huì)透明”,是資本市場法治在上市公司主體責(zé)任建設(shè)層面的制度體現(xiàn),有助于形成公司治理的內(nèi)部約束,迫使其考量利益相關(guān)方及社會(huì)成員的權(quán)益,在回應(yīng)社會(huì)監(jiān)督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良性發(fā)展(Gill North,2018)。同時(shí),信息披露所設(shè)定的各項(xiàng)指標(biāo)為上市公司監(jiān)管提供更加清晰的參照譜系,使監(jiān)管機(jī)構(gòu)從“社會(huì)投資者”角度更廣泛地關(guān)注上市公司行為的社會(huì)和環(huán)境影響,加強(qiáng)對(duì)上市公司的外部約束。
(二)完善資本市場多元監(jiān)管的信息保障
在監(jiān)管主體上,由于上市公司的社會(huì)責(zé)任既包含公司治理因素,也涉及氣候變化、勞工保護(hù)與產(chǎn)品責(zé)任等因素,這決定了社會(huì)責(zé)任監(jiān)管不僅由證券監(jiān)管部門執(zhí)行,而且需要生態(tài)環(huán)境部門、質(zhì)量監(jiān)督管理部門等多方機(jī)構(gòu)協(xié)作完成。為充分發(fā)揮監(jiān)管合力,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協(xié)調(diào)監(jiān)管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因?yàn)橹挥性谏鲜泄镜纳鐣?huì)責(zé)任信息被完整、準(zhǔn)確披露的前提下,各監(jiān)管機(jī)構(gòu)方可從中獲取全面的監(jiān)管數(shù)據(jù),進(jìn)行信息共享,并據(jù)此在其職權(quán)范圍內(nèi)追究上市公司內(nèi)部違法行為人的相關(guān)責(zé)任。此外,從監(jiān)管的規(guī)范體系看,將各監(jiān)管機(jī)構(gòu)分散的規(guī)制條文予以整合并形成統(tǒng)一的信息披露機(jī)制,可避免在多方參與的監(jiān)管協(xié)調(diào)體系中發(fā)生政出多門的尷尬境況,提高監(jiān)管效率。
(三)緩解投資者信息不對(duì)稱的制度工具
由于缺乏強(qiáng)制性的規(guī)制體系及主動(dòng)披露的激勵(lì)機(jī)制,我國上市公司往往疏于披露包括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在內(nèi)的非財(cái)務(wù)信息,使投資者處于信息不對(duì)稱的地位。但對(duì)于投資者而言,非財(cái)務(wù)信息同樣是影響其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首先,財(cái)務(wù)信息主要是歷史數(shù)據(jù),而非財(cái)務(wù)信息則更多關(guān)注上市公司未來發(fā)展信息,符合投資者長期決策需要;其次,非財(cái)務(wù)信息中的公司內(nèi)部數(shù)據(jù)可能是投資決策的預(yù)警器,特別是公司股東變動(dòng)、董事規(guī)模等因素;最后,非財(cái)務(wù)信息對(duì)財(cái)務(wù)信息起補(bǔ)充作用,可提升財(cái)務(wù)指標(biāo)的解釋能力,促進(jìn)投資者對(duì)相關(guān)財(cái)務(wù)信息的理解。因此,上市公司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不僅可以解決其與投資者之間的非財(cái)務(wù)信息不對(duì)稱,縮小投資者在內(nèi)的社會(huì)群體與上市公司之間的信息鴻溝,使社會(huì)公眾得以全面評(píng)估上市公司的社會(huì)影響,還有助于投資者更加準(zhǔn)確地對(duì)其證券進(jìn)行估值,以便及時(shí)調(diào)整投資組合。
綜上,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是2020年《證券法》實(shí)施背景下提升投資者保護(hù)水平的應(yīng)然選擇。然而在我國現(xiàn)行制度下,仍需考察其是否具備實(shí)現(xiàn)上述目標(biāo)的實(shí)然規(guī)范。
三、我國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制度檢視
(一)中國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規(guī)范體系
理論上,上市公司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的外部動(dòng)機(jī)主要源于利益相關(guān)者理論下的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及合法性理論下的政府管制。在我國,由于缺乏專業(yè)知識(shí)與組織的利益相關(guān)者尚不足以約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為,故由國家機(jī)關(guān)頒布的管制性規(guī)范成為上市公司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的主要推動(dòng)力。表1列出了2006年至今中國有關(guān)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制度文件。
縱觀上述制度文件,可以從中歸納出如下三個(gè)基本特點(diǎn):
一是規(guī)范形式以部門規(guī)章或行業(yè)規(guī)范為主,未有法律明文規(guī)定。雖然我國《民法典》與《公司法》均規(guī)定營利法人或公司“應(yīng)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①《民法典》第86條規(guī)定,“營利法人從事經(jīng)營活動(dòng),應(yīng)當(dāng)遵守商業(yè)道德,維護(hù)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會(huì)的監(jiān)督,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公司法》第5條規(guī)定,“公司從事經(jīng)營活動(dòng),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guī),遵守社會(huì)公德、商業(yè)道德,誠實(shí)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huì)公眾的監(jiān)督,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公司的合法權(quán)益受法律保護(hù),不受侵犯。”,并且新《證券法》也對(duì)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義務(wù)提出更高要求,但上述法律均未明確上市公司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的法定義務(wù)。相反,當(dāng)前規(guī)范體系是以各行政部門及交易所出臺(tái)的規(guī)范性文件為主導(dǎo),總體效力層級(jí)偏低。

表1 2006—2020年涉及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規(guī)范性文件
二是整體效力由自愿性走向強(qiáng)制性。在最初的交易所指引中,其表述為“鼓勵(lì)”上市公司發(fā)布報(bào)告,并未對(duì)其進(jìn)行強(qiáng)制性約束,而在《關(guān)于構(gòu)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dǎo)意見》中,針對(duì)屬于重點(diǎn)排污單位的上市公司開始被要求“嚴(yán)格執(zhí)行”環(huán)境信息披露,之后,《上市公司治理準(zhǔn)則》的相關(guān)條文均轉(zhuǎn)變?yōu)榱x務(wù)性規(guī)范,對(duì)上市公司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施以強(qiáng)制性要求。
三是規(guī)范目的由穩(wěn)定股價(jià)轉(zhuǎn)向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早期制度旨在化解社會(huì)、環(huán)境因素對(duì)上市公司股價(jià)的負(fù)面影響,例如,《關(guān)于加強(qiáng)上市公司環(huán)境保護(hù)監(jiān)督管理工作的指導(dǎo)意見》即規(guī)定僅在發(fā)生可能對(duì)證券交易價(jià)格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時(shí),上市公司需立即披露相關(guān)信息。但2015年后的制度則多從社會(huì)責(zé)任或資本市場發(fā)展的角度對(duì)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提出要求,反映了監(jiān)管層在宏觀層面加強(qiáng)信息披露監(jiān)管所做出的努力。
(二)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制度審查
1.強(qiáng)制性效力不足且標(biāo)準(zhǔn)各異
雖然《上市公司治理準(zhǔn)則》確立了具有強(qiáng)制性的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框架,但因該準(zhǔn)則缺乏對(duì)公司治理實(shí)踐的具體指導(dǎo),并且2018年至今仍沒有相關(guān)部門及自律組織出臺(tái)配套的實(shí)施細(xì)則,上述框架處于被“架空”狀態(tài),實(shí)踐中仍以自愿披露為主。截至2020年6月30日,共有961家上市公司發(fā)布了2019年度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在A股市場僅占25.44%,依然有超7成的上市公司未進(jìn)行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
同時(shí),上述制度文件的強(qiáng)制性效力規(guī)范存在相互矛盾之處。首先,在《上市公司治理準(zhǔn)則》頒布后,中國證監(jiān)會(huì)并未據(jù)此修改《公開發(fā)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nèi)容與格式準(zhǔn)則第2號(hào)——年度報(bào)告的內(nèi)容與格式》(以下簡稱“信息披露準(zhǔn)則”)相關(guān)條款,該文件對(duì)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依然持“鼓勵(lì)”態(tài)度,難免在實(shí)踐中給上市公司造成自愿披露的誤導(dǎo)。其次,根據(jù)上交所《科創(chuàng)板股票上市規(guī)則》第4.4.1條,上市公司應(yīng)當(dāng)在年度報(bào)告中披露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的情況,然而在其《科創(chuàng)板上市公司自律監(jiān)管規(guī)則適用指引第2號(hào)》中卻將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列入自愿披露的范圍,由科創(chuàng)公司自主決定是否披露。最后,兩大交易所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也存在明顯不一致的地方。例如,依上交所《上市公司定期報(bào)告業(yè)務(wù)指南》第三節(jié),上市公司應(yīng)當(dāng)充分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但在深交所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中,主動(dòng)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僅為加分項(xiàng)之一,若未披露則并不減分,導(dǎo)致深證100公司的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表現(xiàn)遠(yuǎn)低于上證50的平均水平(王曉光和肖紅軍,2020)。
2.信息披露形式與內(nèi)容缺乏具體約束
上述規(guī)范性文件增加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隨意性及投資者對(duì)比信息的難度。實(shí)踐中,上市公司既可單獨(dú)發(fā)布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也可將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內(nèi)嵌于年度報(bào)告之中;從單獨(dú)發(fā)布報(bào)告的名稱看,既有“ESG報(bào)告”,也有“可持續(xù)發(fā)展報(bào)告”“可持續(xù)性報(bào)告”等,令投資者眼花繚亂。
在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內(nèi)容上,其存在如下困境:其一,定性與定量指標(biāo)覆蓋率差距較大,且定性指標(biāo)大于定量指標(biāo)。相關(guān)報(bào)告表明A股上市公司樣本中定性指標(biāo)披露覆蓋率最低為12%,最高為90%;定量指標(biāo)披露覆蓋率最低為2%,最高為83%,使投資者難以進(jìn)行相應(yīng)指標(biāo)的橫向與縱向?qū)Ρ取F涠男畔⑴吨笜?biāo)使上市公司對(duì)其存在不同理解。例如,中行、工行與建行在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中將“金融科技業(yè)務(wù)”單獨(dú)列為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下的一類項(xiàng)目并予以重點(diǎn)披露,而同為國有銀行的農(nóng)行與交行則將其列入“服務(wù)實(shí)體經(jīng)濟(jì)”項(xiàng)下的二類項(xiàng)目并僅以半頁紙的內(nèi)容簡短帶過,無疑為投資者比較相關(guān)指標(biāo)造成障礙。其三,上市公司可選擇披露積極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但忽略或故意遺漏消極信息。以上海振華重工案為例,雖然其在2016年已收到中央環(huán)保督察組的整改通知,但其后續(xù)兩年的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卻故意隱瞞該信息,最終被生態(tài)環(huán)境部列為典型案例予以公開通報(bào)。
3.信息披露的程序性規(guī)則空白
除前述實(shí)體標(biāo)準(zhǔn)缺失外,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程序性規(guī)則同樣處于空白狀態(tài)。例如,在刊登方式上,上市公司是否需要在其官網(wǎng)與證券交易所網(wǎng)站同時(shí)發(fā)布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是否需要另行發(fā)布紙質(zhì)媒介的報(bào)告?在發(fā)布時(shí)間上,上市公司應(yīng)于會(huì)計(jì)年度結(jié)束后多長時(shí)間內(nèi)發(fā)布報(bào)告?諸如此類規(guī)定均尚付闕如。
此外,在自愿披露背景下,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保證披露內(nèi)容真實(shí)性與過程完備性的外部審計(jì)(Virginia Harper Ho,2017)。然而,我國目前卻幾乎未對(duì)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的第三方鑒證機(jī)制提出合規(guī)性要求。在2019年度961家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的上市公司中,僅有25家聘請(qǐng)了外部第三方鑒證,且其中多為銀行業(yè)和非銀金融業(yè)的上市公司。缺乏外部性審驗(yàn)的社會(huì)責(zé)任報(bào)告使其公信力顯著降低,加之其內(nèi)容以定性指標(biāo)居多,供投資者進(jìn)行評(píng)估的量化數(shù)據(jù)無處可尋,故投資者難以通過有效途徑確認(rèn)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實(shí)性。
四、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制度之借鑒與啟示
隨著綠色金融蓬勃發(fā)展,全球各大經(jīng)濟(jì)體已建立起以ESG為核心的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機(jī)制,諸多擁有成熟資本市場的國家(地區(qū))在該領(lǐng)域的表現(xiàn)尤為突出。鑒于歐盟在主流機(jī)構(gòu)的平均得分最高且政策體系最為健全,而中國香港的制度規(guī)范對(duì)內(nèi)地資本市場發(fā)展則有較為直接的借鑒意義,下文分別對(duì)歐盟與中國香港的制度規(guī)范進(jìn)行剖析,以期對(duì)我國完善2020年《證券法》實(shí)施背景下的ESG信息披露制度有所助益。
(一)歐盟
由于各成員國的資本市場發(fā)展程度不盡相同,歐盟的ESG信息披露機(jī)制并非依賴于一整套特定規(guī)則,而是在《非財(cái)務(wù)報(bào)告指令》的框架下不斷細(xì)化并最終轉(zhuǎn)化為各成員國法律而實(shí)施的。《非財(cái)務(wù)報(bào)告指令》(以下簡稱“指令”)系歐盟首次將ESG要素列入信息披露指令的法律文件,其采用“不披露就解釋”(comply or explain)原則對(duì)上市公司施以強(qiáng)制性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要求,即“上市公司可不執(zhí)行上述一項(xiàng)或多項(xiàng)議題,但其應(yīng)對(duì)不執(zhí)行的議題作出明確且合理的解釋”。同時(shí),其明確環(huán)境議題的關(guān)鍵績效指標(biāo),并提出社會(huì)和公司治理議題的參考披露內(nèi)容,為各成員國結(jié)合本國實(shí)際制定具體標(biāo)準(zhǔn)奠定基礎(chǔ)框架。
在上述框架內(nèi),歐盟著重從以下方面搭建ESG信息披露機(jī)制,具體來說:一是發(fā)布《非財(cái)務(wù)信息披露指南》及相關(guān)指引文件。該指南確立了“相關(guān)性、實(shí)用性與可比性”的信息披露原則,并通過展示最佳實(shí)踐的方式,對(duì)信息重大性認(rèn)定、非財(cái)務(wù)信息與財(cái)務(wù)信息關(guān)聯(lián)性等內(nèi)容作出不具約束力的指引性規(guī)定。此外,在2018年發(fā)布《可持續(xù)金融行動(dòng)計(jì)劃》后,歐盟委員會(huì)開始采用在線咨詢文件的形式搜集利益相關(guān)方針對(duì)指南提出的改進(jìn)意見,以便進(jìn)行更新和補(bǔ)充。2019年,其下設(shè)的技術(shù)專家組已根據(jù)相關(guān)意見正式發(fā)布第一份補(bǔ)充文件。信息披露指南在補(bǔ)強(qiáng)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一致性的同時(shí)也兼顧政策法規(guī)的時(shí)效性以及利益相關(guān)方的信息接受程度,避免無價(jià)值的行政負(fù)擔(dān)及單向披露。
二是對(duì)特定行業(yè)予以特殊規(guī)制。例如,從事金融服務(wù)的歐盟上市公司除需遵守上述指令外,還應(yīng)根據(jù)歐盟委員會(huì)發(fā)布的《金融服務(wù)業(yè)可持續(xù)性相關(guān)披露條例》披露與金融產(chǎn)品相關(guān)的ESG信息。同時(shí),該條例將金融產(chǎn)品分為對(duì)環(huán)境、社會(huì)具有一般影響或積極影響兩大類,針對(duì)具有一般影響的金融產(chǎn)品,上市公司應(yīng)披露與之相關(guān)的特定指數(shù)、可持續(xù)性指數(shù)及其與指數(shù)的一致程度,而針對(duì)具有積極影響的金融產(chǎn)品,則僅需披露其衡量該產(chǎn)品是否符合可持續(xù)指標(biāo)的參考標(biāo)準(zhǔn)。此種差異化的信息披露制度促使金融機(jī)構(gòu)(或其母公司)積極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降低投資者的信息不對(duì)稱。
三是在政策體系內(nèi)積極引入相關(guān)國際標(biāo)準(zhǔn)。以環(huán)境信息披露為例,在《非財(cái)務(wù)報(bào)告指南:氣候相關(guān)資訊的補(bǔ)充》中,歐盟委員會(huì)指出該指南不僅僅是對(duì)指令規(guī)則的補(bǔ)充,并且旨在將金融穩(wěn)定理事會(huì)(FSB)發(fā)起的氣候相關(guān)財(cái)務(wù)信息披露(TCFD)工作組的披露標(biāo)準(zhǔn)予以整合。在指南第三部分“建議披露事項(xiàng)”中,多數(shù)條款均被注明其與TCFD相關(guān)標(biāo)準(zhǔn)的重合之處,例如,“描述董事會(huì)針對(duì)氣候相關(guān)風(fēng)險(xiǎn)的監(jiān)督”即涵蓋了TCFD“治理”板塊下的a建議。上述規(guī)定有助于增強(qiáng)歐盟與國際標(biāo)準(zhǔn)之間的互聯(lián)互通,使其上市公司的ESG報(bào)告在全球獲得廣泛的認(rèn)可。
(二)中國香港
我國香港地區(qū)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包括香港聯(lián)合交易所(以下簡稱“聯(lián)交所”)發(fā)布的《環(huán)境、社會(huì)及管治報(bào)告指引》(以下簡稱“指引”)及其配套指南。通過對(duì)其規(guī)范內(nèi)容的考察,其制度優(yōu)勢在于強(qiáng)制性的披露效力、定性與定量結(jié)合的具體指標(biāo)以及實(shí)用的程序指引。
首先,指引的制度沿革見證了強(qiáng)制性效力的漸進(jìn)式升級(jí)。在首版指引中,其僅對(duì)上市公司發(fā)布ESG信息披露持鼓勵(lì)態(tài)度。自2015年第二版起,指引開始引入“不遵守就解釋”條文,最后在2019年發(fā)布的第三版中明確其僅涵蓋“強(qiáng)制披露規(guī)定”與“不遵守就解釋”條文,要求對(duì)所有指標(biāo)進(jìn)行披露或解釋。隨著上述條文的實(shí)施,中國香港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的數(shù)量穩(wěn)步增長,截至2019年9月,共有1868家上市公司發(fā)布上一財(cái)年的ESG報(bào)告,已達(dá)地區(qū)內(nèi)上市公司總數(shù)的80%。如此高的信息披露水平無疑說明強(qiáng)制性的規(guī)范要求是提高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意識(shí)與合規(guī)能力的必要前提。
其次,設(shè)置定性與定量相結(jié)合的信息披露指標(biāo)。在指引中,其將董事會(huì)的ESG管治架構(gòu)、匯報(bào)原則與匯報(bào)范圍三類定性指標(biāo)列為強(qiáng)制披露規(guī)定,要求上市公司首先告知投資者其ESG報(bào)告的價(jià)值所在。而在“不遵守就解釋”條文中,指引則將定性指標(biāo)與定量指標(biāo)相結(jié)合,在要求披露各層面定性指標(biāo)的基礎(chǔ)上,要求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包含定量因素的關(guān)鍵績效指標(biāo),并對(duì)定量指標(biāo)的計(jì)算單位作出規(guī)定。例如,在A2層面“資源使用”中,上市公司不僅應(yīng)披露有效使用資源的政策(定性指標(biāo)),還應(yīng)披露該層面下設(shè)置的五個(gè)關(guān)鍵績效指標(biāo)。這令上市公司所披露的ESG信息更具可比性,為投資者對(duì)比信息提供更加完整的數(shù)據(jù)。
最后,提供明晰的程序指引及操作程序指南。指引A部分第4條即對(duì)上市公司ESG報(bào)告的刊發(fā)載體、形式以及期限等作出明確規(guī)定,例如,第(2)款d項(xiàng)規(guī)定,發(fā)行人應(yīng)盡可能在接近財(cái)政年度結(jié)束的時(shí)間,而不遲于該財(cái)政年度結(jié)束后五個(gè)月刊發(fā)報(bào)告。根據(jù)聯(lián)交所2019年發(fā)布的審閱報(bào)告,所有被審閱樣本發(fā)行人均在財(cái)政年度結(jié)束后三個(gè)月內(nèi)發(fā)布ESG報(bào)告,63%的樣本發(fā)行人在刊發(fā)年報(bào)的同一日發(fā)布。同時(shí),聯(lián)交所于2020年3月發(fā)布《ESG匯報(bào)指南》,針對(duì)報(bào)告編制步驟提出詳細(xì)的程序指引,以供上市公司參考。該指南還對(duì)第三方獨(dú)立鑒證作出補(bǔ)充規(guī)定,要求上市公司在挑選獨(dú)立鑒證機(jī)構(gòu)時(shí)考量其股東構(gòu)成、工作資質(zhì)等因素,以保障第三方鑒證的可靠性。
五、我國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制度的重構(gòu)
(一)統(tǒng)一信息披露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
因缺乏與《上市公司治理準(zhǔn)則》強(qiáng)制性要求相匹配的實(shí)施細(xì)則,導(dǎo)致我國上市公司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的積極性不足,披露內(nèi)容差異較大,無法將強(qiáng)制性要求有效轉(zhuǎn)化為受益投資者的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相比之下,前述國家(地區(qū))均在其強(qiáng)制性披露框架下明確上市公司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的整體方針、披露原則及具體指標(biāo),設(shè)定了“不披露就解釋”的最低標(biāo)準(zhǔn),中國香港還依據(jù)強(qiáng)制效力的不同對(duì)具體指標(biāo)進(jìn)行效力分層并在各層面內(nèi)設(shè)置關(guān)鍵績效指標(biāo),以突出信息披露的重點(diǎn)。這種一體化適用的信息披露框架既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披露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的內(nèi)部成本,也使投資者得以全面獲取所需信息。
因此,為提高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水平,應(yīng)首先通過出臺(tái)具有權(quán)威性的法律法規(guī),統(tǒng)一資本市場規(guī)范體系中的強(qiáng)制性條款,強(qiáng)制所有上市公司必須依據(jù)《上市公司治理準(zhǔn)則》所搭建的基本框架內(nèi)進(jìn)行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的總結(jié)與披露。其次,在實(shí)施細(xì)則的選擇上,雖然《上市公司治理準(zhǔn)則》提出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框架,但由于其缺乏具體的信息披露細(xì)則及法律責(zé)任規(guī)定,故在實(shí)踐中難以對(duì)上市公司形成強(qiáng)制性約束。當(dāng)前,我國證監(jiān)會(huì)主要依據(j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進(jìn)行信息披露事務(wù)管理,且該辦法因2020年新《證券法》的實(shí)施現(xiàn)正處于修訂階段,故可借此契機(jī)于該辦法第三章“定期報(bào)告”中再次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強(qiáng)制性效力,并對(duì)信息披露準(zhǔn)則予以修訂,將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單列一節(jié)規(guī)定其具體披露標(biāo)準(zhǔn)。最后,在統(tǒng)一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后,可根據(jù)上市公司的行業(yè)歸屬、公司規(guī)模等因素,在具體規(guī)范中明確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可在特定指標(biāo)上選擇“不披露就解釋”規(guī)則,增加制度規(guī)范的靈活性。例如,針對(duì)科創(chuàng)板的初創(chuàng)型上市公司,其通常不具有較高的社會(huì)責(zé)任履行能力,且信息技術(shù)服務(wù)的公共性也較低,若對(duì)其統(tǒng)一使用強(qiáng)制性條款則明顯加重其合規(guī)負(fù)擔(dān),故其在環(huán)境、社區(qū)參與等社會(huì)責(zé)任指標(biāo)上即可選擇適用“不披露就解釋”規(guī)則。
(二)規(guī)范信息披露的具體內(nèi)容
1.參考國內(nèi)外相關(guān)標(biāo)準(zhǔn)
2015年,我國曾發(fā)布《社會(huì)責(zé)任指南》(GB/T 36000—2015)國家標(biāo)準(zhǔn)。該指南依據(jù)國際標(biāo)準(zhǔn)化組織的ISO26000標(biāo)準(zhǔn)制訂,將社會(huì)組織的社會(huì)責(zé)任核心主題分為包括組織治理、人權(quán)、勞工實(shí)踐以及環(huán)境等七大類。上述內(nèi)容已基本涵蓋社會(huì)責(zé)任的核心議題,并與ESG的基礎(chǔ)框架相契合,可作為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主題的參考標(biāo)準(zhǔn)。
同時(shí),由于上述國家標(biāo)準(zhǔn)的出臺(tái)時(shí)間較早,僅涵蓋各主題下的基本內(nèi)容,無法全面囊括現(xiàn)階段的社會(huì)責(zé)任議題,故還應(yīng)參照常態(tài)化更新的國際標(biāo)準(zhǔn)對(duì)內(nèi)部指標(biāo)加以補(bǔ)充與完善。例如,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消費(fèi)者隱私和數(shù)據(jù)安全與上市公司的社會(huì)責(zé)任密切相關(guān),上市公司應(yīng)披露數(shù)據(jù)安全管理規(guī)范、受網(wǎng)絡(luò)安全攻擊次數(shù)以及客戶信息數(shù)據(jù)泄露情況等與之相關(guān)的信息,但“數(shù)據(jù)與隱私安全”指標(biāo)卻未被我國國家標(biāo)準(zhǔn)所收錄。對(duì)此,在設(shè)定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指標(biāo)時(shí)建議參照國際評(píng)級(jí)機(jī)構(gòu)明晟ESG評(píng)級(jí)指標(biāo)體系進(jìn)行相應(yīng)補(bǔ)充,該指標(biāo)根據(jù)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問題進(jìn)行不定期調(diào)整,最新一次的指標(biāo)調(diào)整時(shí)間為2020年10月。
2.適當(dāng)增加量化指標(biāo)
在確定核心主題與具體指標(biāo)的基礎(chǔ)上,適當(dāng)增加量化指標(biāo)的比例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的可比性。針對(duì)量化指標(biāo)的構(gòu)建工作,本文認(rèn)為可從如下兩個(gè)方面予以推進(jìn):一是明確絕對(duì)量化指標(biāo)的度量標(biāo)準(zhǔn)(如指標(biāo)單位)以及相對(duì)量化指標(biāo)的計(jì)算公式。同時(shí),制度規(guī)范還應(yīng)對(duì)量化指標(biāo)進(jìn)行準(zhǔn)確描述,減少模糊性語言,避免歧義。以上文提及的指引中指標(biāo)B2.1為例,即由第二版“因工作關(guān)系而死亡的人數(shù)及比率”修改為第三版“過去三年(包括匯報(bào)年度)每年因公亡故的人數(shù)及比率”,這使上市公司得以向投資者提供更加簡明、直觀的數(shù)據(jù)。二是要求上市公司提供量化數(shù)據(jù)的相關(guān)來源,證明所披露數(shù)據(jù)來源于內(nèi)部可靠記錄或其他可靠統(tǒng)計(jì),以幫助投資者科學(xué)準(zhǔn)確地鑒別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從而優(yōu)化投資決策(桂荷發(fā)和郭苑,2018)。若該數(shù)據(jù)由于商業(yè)隱私原因無法披露或存在不確定性無法測算時(shí),上市公司應(yīng)提供相關(guān)解釋說明或第三方鑒證報(bào)告以免于披露。
3.適時(shí)發(fā)布補(bǔ)充指南
除在法律法規(guī)中對(duì)信息披露指標(biāo)加以明確外,以證券交易所、中國證券業(yè)協(xié)會(huì)為主的自律性組織還可以基于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現(xiàn)實(shí)問題,通過發(fā)布解釋性指南或行業(yè)指南的形式,構(gòu)建約束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軟法規(guī)范,增加對(duì)硬法規(guī)則的詮釋。解釋性指南旨在通過反饋上市公司編制報(bào)告中的常見錯(cuò)誤、為上市公司編制報(bào)告提供更加具體的步驟指引等方式,以彌補(bǔ)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在實(shí)踐操作中的缺陷。而行業(yè)指南的內(nèi)容則可參考?xì)W盟發(fā)布的《金融服務(wù)業(yè)可持續(xù)性相關(guān)披露條例》,結(jié)合公共服務(wù)業(yè)、重污染行業(yè)的業(yè)務(wù)特點(diǎn),對(duì)各行業(yè)內(nèi)的重要信息予以重點(diǎn)關(guān)注,促使行業(yè)內(nèi)部形成自我約束,充分發(fā)揮自律功能并倒逼法律法規(guī)的完善。
(三)制定信息披露的程序性規(guī)則
在披露形式上,我國應(yīng)確立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的整合型披露方式,要求其將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整合至其年度報(bào)告中一并披露。整合型披露的優(yōu)勢在于:一是我國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制度已規(guī)定于《年度報(bào)告準(zhǔn)則》中,可沿用其刊登方式與發(fā)布時(shí)間的規(guī)定,并且無需另行設(shè)立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平臺(tái)。二是有助于加強(qiáng)非財(cái)務(wù)信息與財(cái)務(wù)信息之間的聯(lián)系,使投資者或利益相關(guān)者能夠更為全面地分析上市公司信息。
此外,引入第三方鑒證機(jī)制是提高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可靠性的有效手段。我國現(xiàn)階段的首要工作應(yīng)是完善配套制度,填補(bǔ)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編報(bào)基礎(chǔ)的空白。相關(guān)部門可借鑒國際經(jīng)驗(yàn),如國際審計(jì)與鑒證準(zhǔn)則委員會(huì)發(fā)布的ISAE3000標(biāo)準(zhǔn)以及由社會(huì)和倫理責(zé)任協(xié)會(huì)發(fā)布的AA1000審驗(yàn)標(biāo)準(zhǔn)等,并結(jié)合我國非財(cái)務(wù)信息的審計(jì)實(shí)踐,制定上市公司的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鑒證標(biāo)準(zhǔn)。其次,統(tǒng)一明確會(huì)計(jì)師事務(wù)所為第三方鑒證機(jī)構(gòu),充分發(fā)揮注冊(cè)會(huì)計(jì)師鑒證的獨(dú)立性,并建議其在鑒證人員中吸收與鑒證對(duì)象同行業(yè)的專家參與,提高鑒證的專業(yè)性。最后,鼓勵(lì)上市公司在披露第三方鑒證結(jié)果的同時(shí)披露鑒證的具體內(nèi)容與過程,以幫助投資者對(duì)鑒證的客觀性作出合理判斷。
綜上,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在2020年《證券法》實(shí)施背景已下不言而喻,但處于監(jiān)管“聚光燈”下的卻只有上市公司的財(cái)務(wù)會(huì)計(jì)信息,而缺乏對(duì)其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的關(guān)注,進(jìn)而導(dǎo)致其在制度規(guī)范上存在強(qiáng)制性效力標(biāo)準(zhǔn)各異、信息披露指標(biāo)缺乏明確指引以及程序性規(guī)則空白等缺陷,造成自愿性、任意性的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占據(jù)主流,加劇了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duì)稱。為此,在2020年新出臺(tái)的《證券法》實(shí)施的背景下,亟需從實(shí)體與程序維度重構(gòu)我國上市公司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制度,補(bǔ)齊監(jiān)管短板。結(jié)合歐盟與香港地區(qū)的制度經(jīng)驗(yàn),我國應(yīng)從規(guī)范效力入手,補(bǔ)強(qiáng)并統(tǒng)一社會(huì)責(zé)任信息披露的效力規(guī)定,并在此基礎(chǔ)上完善核心議題、關(guān)鍵指標(biāo)等披露內(nèi)容。同時(shí),在程序上應(yīng)明確信息披露方式、建立第三方鑒證機(jī)制,多措并舉提升信息披露質(zhì)量,切實(shí)保障投資者權(quán)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