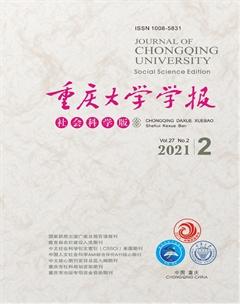互聯網平臺侵害知識產權的新治理模式
摘要:第三代互聯網的興起,形成了平臺經濟。平臺企業連接了全球范圍內的用戶,改變了傳統產業的結構。平臺經濟具有規模經濟、更少閑置、精準定價、信息動態化等特點,在提供便利的同時,平臺經濟也帶來了更多知識產權侵權風險。已有的研究,對平臺企業的規制多集中在損害發生后的賠償責任。但由于平臺企業自我規制動力不足,事后規制模式存在局限。為避免互聯網平臺侵害知識產權風險的擴大,采用事后規制與事前規制相結合、政府規制與平臺企業自治、法律與行業規范相結合的多元治理模式更為科學。
關鍵詞:平臺企業;規模經濟;知識產權;侵權責任;多元治理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1)02015511
經濟學家認為,信息不對稱是造成人類交往不暢的重要原因。在那種時代,限于昂貴的搜索成本,人們難以形成關于供需的市場,交易很難達成[1]。互聯網的興起,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和APP的結合,大大改變了這一狀態。由此,人類的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交易能力明顯提高。此外,加上傳感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的配合,互聯網經濟迅猛發展,互聯網科技公司茁壯成長,并因此改變了人類的商業模式和生活方式。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第一代互聯網經濟web1.0產生了谷歌、百度這樣的搜索引擎,它給我們提供了合作、交流和共享信息的平臺;第二代互聯網經濟web2.0擴大了搜索和交流的范圍,形成了京東、亞馬遜等這樣的在線市場;第三代互聯網經濟web3.0正在改變服務業,它大大降低了線下交易的成本,并深刻改革了線下市場的物質基礎架構[2]。
在第三代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巴巴、美團、滴滴等公司是其先鋒。這些公司為用戶提供信息平臺,用戶根據平臺的要求,通過注冊所需要的信息,便可以登錄平臺,最后達成交易。以美團公司為例,公司提供網站或APP,用戶僅需要提供相應信息,便可注冊一個賬戶。登錄賬戶后,商家與用戶便可達成交易,美團公司的平臺主要發揮的作用是提供信息。這一提供信息的行為憑借移動互聯網,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并迅速遍及全球。目前,平臺服務已經進軍大量行業,如影視(YouTube)、餐飲(美團)、運輸(滴滴)等。這些平臺具有實物分享的特點,把一方或者多方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在用戶之間進行匹配,大大改變了傳統產業的形式和結構[2],給傳統產業帶來了深刻的變化。依托于云服務的幫助,這些平臺更具有跨國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平臺經濟甚至重塑了全球化本身[3]。它激活了那些閑置的財產,把閑置的物品用于出售,把自己不用的汽車用于運輸,把自己的空余時間用于送達,增加了社會總供給。提供這些平臺的企業被稱為平臺企業,由于企業提供的這種服務產生了巨大價值,有人稱之為平臺經濟。
互聯網平臺在給社會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風險,如熱播網劇盜版泛濫、假冒商品屢禁不止。平臺企業與傳統的私人企業性質不同,很難用商品的價值進行衡量,其價值的估算方法和治理模式也與傳統的企業存在差異[4]。更重要的是,這些風險是平臺經濟的必然伴生品,它伴隨著平臺經濟的發展而系統地增加。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中,人們在積累財富和享受便利的同時,必然要承擔其帶來的風險。用烏爾里希·貝克的話說,這種風險是自反性的,它是現代化自身引發的危險和不安,風險以自身的方式塑造著現代化的模式[5]。我們能做到的只是盡可能地降低而不是消除風險。反過來,對風險的防范也會影響平臺經濟的發展。平臺經濟的效益依賴于規模,對風險的防范不僅增加了平臺企業的運營成本,還會限制平臺規模的增長。試想,移除互聯網平臺內具有(知識產權)侵權之虞的商品,其直接結果是減少平臺可能之供給。對此,平臺企業應當對風險的產生承擔何種責任呢?換句話說,在互聯網平臺給我們帶來便利的同時,應當如何界定平臺企業的注意義務,如何明確廓清平臺企業和使用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如何對平臺企業進行合理的治理,就是我們必須面臨的問題。
一、平臺企業侵害知識產權風險的管窺
(一)平臺企業的特點
平臺企業呈現出與傳統企業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與平臺本身密切相關。有學者將平臺經濟的特點進行了總結,認為平臺經濟包括規模經濟、更少閑置、交易單元的定制、人人均為資本家、從標準化到定制、接觸勝過擁有、運營成本較低、精準定價、信息動態化等特點[2]。正是由于這些特點,平臺企業在陌生人之間建立了溝通渠道,形成了規模經濟。
在前平臺經濟,由于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我國已開始了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化,但由于通信技術的束縛,陌生人之間的交往受到了較大的限制。由于信息不對稱,在前平臺時代,大量資源閑置,如多余的房間、閑置的物品、空閑的勞動力。因為無法發現相應市場,這些要素無法發揮最大的功能。平臺企業為這些閑置的資源提供了供求途徑,激活了大量的閑置資源和勞動力。在平臺經濟下,每個人都是平臺的消費者,也可能同時是平臺上的商戶。阿里巴巴就是靠大量的小商戶支持了公司的運行。之前大市場、大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依賴關系被打破,私人所有的每件東西都具有了價格,休息時間可以兌換為對別人的服務,私人空間可以兌換為別人的客棧。“平臺讓每個人、每件東西都具有了價格”[2]。 德國思想家桑巴特曾經指出,包括性自由在內的感官快樂促成了奢侈消費,而奢侈又在組織結構上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形成[6]。與此相關,平臺使每一件東西都變成了消費品,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資本主義的范圍,形成了全民資本主義的浪潮。平臺經濟還具有信息動態化的特點。在前平臺經濟時代,信息不對稱導致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無法獲得確定的認知。在平臺經濟模式下,消費者憑借移動互聯網上的APP,可以隨時關注自己商品的動態,并可以通過商品的評價、評級和其他信息,減少不確定性,實現商品信息的動態化。
在前平臺經濟時代,對社會經濟發揮更大作用的是大企業。原因在于,大企業在市場上提供了大量產品,其質量與信譽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當消費者與大企業進行交易達成協議的時候,更多依賴的是大企業之前的信譽。這里呈現的關系是一個或幾個大企業與多數消費者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種“一對多”的交易模式。對大企業而言,它依賴的是消費量的增加。通過體驗性消費,消費者慢慢熟悉了大企業,并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供需關系。由于大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標準化的特點,消費者選擇的余地較小。
與之不同,在平臺經濟模式下,諸多用戶可以
調動自己閑置的資源,并在平臺上展示;而更多的消費者可以在平臺上曬出自己的需求。信息的對稱性提供了把消費者從對大企業的依賴中解放出來的條件和可能。用戶對平臺信息的依賴,形成了巨大的市場,與之前大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一對多關系不同,這里呈現的是多對多的關系,在這個關系中,沒有中心,沒有固定的角色,人人都既可能是消費者,也可能是供應商。
(二)平臺經濟增大知識產權侵權風險
平臺把諸多的陌生人集合在一起,在增進交易量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多危險。在博弈論看來,交易雙方在初次博弈中,為了自己的利益,博弈雙方達成的結果并不是最優的。博弈雙方為了自己的利益,更多地會去侵害他人的利益[7]。平臺上的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很多體現了這種初次博弈的結果,知識產權侵權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大體說來,平臺經濟增加了商品或服務提供者侵犯知識產權之可能。
平臺經濟下,交易的雙方多是陌生人。在陌生人的初次交往中,投機心理比較普遍。陌生人之間的交往,沒有之前的信息,沒有共同的規范約束,多是一次性交易。在信息經濟學上,陌生人之間的一次性交易,相比熟人之間的多次交易,更容易產生僥幸心理。在一個社區被認為道德高尚的人,到了一個陌生地方很可能會違法,反應的就是這個道理[8]。中國古代的“慎獨”一詞在一定意義上也反映了這個道理。近年來,電商平臺上屢禁不止的盜版、假冒、仿冒商品,就說明了這一點。盡管這些行為也經常發生在線下,但在平臺環境下,這些行為更呈現了自己的特色。在線下,銷售盜版、假冒商品并不依賴于第三人的信息,侵權交易的發生多以特定地域為前提。而在平臺經濟模式下,由于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一方了解消費者的部分信息(交易意愿、配送地址),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發生,超越了地域的限制,這意味著侵權商品消費量增加的可能。試想,如果沒有平臺提供的信息,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即使知道特定地域外存在不少消費需求,也無法達成交易。
在前平臺經濟時代,跨地域銷售多由大企業促成,依賴于供應鏈的優勢地位,它可直接要求其他企業遵守硬性的責任標準[9],防范可能涉及的侵權風險。在平臺經濟模式下,信息對稱的結果,是幫助雙邊用戶(供應商、消費者)跨越自己無法或難以跨越的銷售(或消費)網絡邊界,形成雙邊市場[10]。受限于經營規模,雙邊市場中的小商戶無法投入足夠成本防范知識產權侵權之風險。又或者說,平臺經濟模式下的信息對稱,使得以(知識產權)侵權作為營利手段的生意,更為有利可圖。借助于平臺企業的信息,侵權交易屢屢促成。一方面,平臺企業的角色并非中性,商戶進駐的要求、交易規則的設定、用戶賬戶的管理,使平臺企業具備干預雙邊市場實際供需的能力。另一方面,雙邊用戶對平臺服務的需求,成為維系雙邊市場的基礎,由此,平臺企業在雙邊市場中,并不具備大企業在供應鏈中的優勢地位,過分苛責平臺企業的結果,可能是產生新的信息不對稱,沖擊平臺經濟的基礎。如此,對平臺帶來的風險,它自己如何承擔相應的義務。
二、平臺侵害知識產權責任模式的闡釋與檢討
(一)侵害知識產權的平臺責任
平臺經濟模式產生的風險,包括平臺企業產生的風險,以及利用平臺服務的用戶行為產生的風險。在平臺經濟帶來的挑戰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平臺企業和用戶之間的關系,不如傳統企業那樣具有更為直接的監管關系,因此,平臺企業更難以控制用戶之間的關系。在探索平臺經濟的風險控制時,更應該采取結構化的而非單一的控制方式。
有關互聯網平臺的責任,各國立法走過了一條漫長探索的道路。早在1996年,《美國通訊規范法》第230條明確規定,互聯網平臺不對通過其服務從事的侵權行為承擔間接責任,國會在相關的立法文件中指出,該條文的初衷是將互聯網平臺和傳統的出版社、電視臺進行區分。需注意的是,這一條并不適用于侵害著作權的行為,該法律也沒有規定通知―刪除機制。也就是說,《美國通訊規范法》第230條的規定,除了用戶侵害他人的著作權外,互聯網平臺不對用戶的任何行為負責。1997年,美國的《數字千年版權法》(DMCA)專門為傳播作品的互聯網平臺作出規定,第512條要求網絡服務提供商在適當情形下終止向嚴重侵權的用戶、賬號持有人提供服務的政策,同時為短暫傳輸、系統緩存、信息存儲、信息定位行為提供避風港免責,只要在權利人提供了合理的侵權通知之后刪除了有關鏈接和內容,就不承擔責任。但網絡服務商在實際知道侵權活動或者依照有關情形明顯意識到侵權活動時,如不斷開有關鏈接和內容,應當認定其沒有履行相應的注意義務,應當承擔責任。顯然,美國采納的是二元模式,美國只針對提供作品傳播服務的網絡服務商提出了要求,其設計的“通知―刪除規則”和“避風港規則”并不適用于其他領域。我國2006年制定2013年修訂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也基本上吸收了這種做法,將“通知―刪除”規則適用于侵害著作權的領域。但2010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擴大了“通知―刪除”規則的適用范圍,從著作權領域擴大到所有的民事侵權領域。并納入《民法典》中。歐盟2000年的《電子商務條例》和我國的《電子商務法》也將“通知—刪除”規則適用于所有的民事侵權領域。這意味著,理論上,至少在所有的民事領域,平臺企業如果沒有履行相應的義務,就要對平臺用戶的行為負責。
大致說來,目前關于互聯網平臺的責任,主要體現了以下特點:第一,秉持技術中立的基本立場。由于互聯網上海量信息的傳播,互聯網平臺沒有能力對網上涉嫌侵害他人權利的用戶行為進行主動審查。如果要求互聯網平臺具有主動審查的義務,將會影響互聯網的本質。第二,互聯網平臺沒有主動審查的義務,并不意味著沒有注意義務,因之,如果侵權人在互聯網平臺的行為具有明顯的侵權事實,或者依相關情況,互聯網平臺應當能夠判斷侵權事實的存在,此時,它如果不斷開連接,就被認為沒有履行注意義務,仍然要承擔共同侵權的責任。第三,“通知―刪除”規則適用于所有的民事侵權領域,如果互聯網平臺收到了權利主體的合理通知,如著作權人、商標權人、專利權人、名譽權人等,互聯網平臺沒有刪除相關內容,斷開鏈接,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第四,平臺行為不同,注意義務也應當不同,如互聯網平臺在用戶行為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設置了榜單、進行了選擇編輯推薦等人工干預行為,其注意義務就應適當提高。第五,平臺服務不同,注意義務也應當有所不同,如接入、自動存儲、緩存等服務,與鏈接、搜索等定位服務,與信息存儲空間服務的注意義務就應當存在差別。相對于社交平臺,由于電商平臺對用戶的控制和交易的介入較深,也應當承擔更強的注意義務。
(二)平臺責任模式的檢討
1.事后規制模式的有限
大致說來,目前已有的關于互聯網平臺責任的討論多數集中在事后的規制,亦即當發生侵權行為時,考量的是平臺應當如何彌補權利人的損失,具有被動的性質,體現的是一種矯正正義。并且,相較于侵權法上共同侵權的一般規則,互聯網平臺負擔著更低的注意義務[11]。對此,事后規制的困難在于,法院需要考量,科以過高的注意義務是否會過分加重互聯網平臺負擔,同時也擔心,平臺企業利用例外規則,刻意放縱侵權行為。表面上,這是設置合理注意義務的智識資源不足造成的,因為很難測量基于注意義務的高低,平臺經濟創造的社會總福利是否超過權利人遭受的整體損害。實際上,注意義務的設置是否合理,隱含著一個事實,即社會公眾對盜版、假冒商品的需求。無論權利保護的價值有多高,低價或者零成本獲取商品或服務的需求,總是持續存在著。
抑制侵權商品的供給,增大合規產品的需求,總體可欲。因此,問題不在于民事裁決應當如何度量平臺企業為抑制侵權商品所花費的成本,而在于加重平臺企業(侵害知識產權)的民事責任是否屬于達致以上目標的理想途徑。例如,在現行規范體系內,通過擴張解釋《電子商務法》第45條“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必要措施”兩項術語,把設定(侵害知識產權)的技術過濾措施作為平臺企業應盡的注意義務,增大平臺企業的連帶責任范圍,似乎具備可行性。但令人生疑的是:第一,就目前的技術而言,無法比對、過濾專利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等內容。第二,盡管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的分析、索引、比對技術日益精確,但是,技術門檻、成本仍較高,注意義務水平的增加,是否會激發權利人及其代理人對中小型平臺企業的訴訟熱情、增加非執業實體(NPEs)對平臺企業的經濟侵蝕,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第三,為免訴累,增加注意義務,是否會轉化為平臺用戶新的形式負擔,例如,每上架新的商品或服務均需出具無侵權聲明,增大交易成本。第四,平臺監管責任的提高,是否會加重平臺錯誤判斷侵權行為的不良后果,惡化平臺內競爭生態。第五,強制性要求屏蔽特定形式要素,是否會損害平臺內交流,限制用戶言論自由,產生“寒蟬效應”。
總體而言,包括技術過濾在內的平臺治理措施,存在合理性,在業界實踐中也取得成效[12]。但是,通過加重事后責任,“倒逼”平臺企業增加治理力度,并非是必然的不二選擇。相較于規避侵害知識產權風險,它更有可能造成的結果是,打破平臺內運轉的自生秩序,擾亂平臺企業對雙邊價格的再分配。為此,相關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條)至今保持審慎的態度。
2.平臺企業自我規制的動力不足
平臺內網絡交易的達成,一般依賴于五種權利義務內容,包括提供網絡交易場所、發布信息流、價金托管支付、物流配送、交易信用評價[13]。換言之,知識產權保護,并非維持網絡交易關系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更重要的是,在平臺內,一組用戶(供應商)所得利益取決于平臺吸引另一組用戶(消費者)的能力,如果特定侵權情形的產生(如人身安全、食品質量)會嚴重削弱平臺的用戶吸引力,對此,平臺企業存在自我規制的激勵。與此相悖的是,侵害知識產權商品或服務的供應,會增加(而非削弱)平臺的用戶吸引力。因而,平臺企業對侵害知識產權風險治理的激勵,存在天然的不足。此外,侵權(知識產權)交易的達成,多數并非由消費者不知情促成的,而是交易雙方的共謀,侵權交易具備隱蔽性。換言之,平臺企業對侵害知識產權風險治理的能力和成本,均受到考驗。
為應對平臺企業自我規制的天然不足,“通知―刪除”規制和有限注意義務的適用,成為平臺責任的基本范式。盡管各國解釋相應規則時,寬嚴相異,但尚未有成例,把平臺承擔普遍的主動監管義務,納入平臺責任體系。現有的平臺責任模式,依存于微弱的平衡:確保權利人的維權措施得到平臺的有效回應,并在不影響平臺準入、信息交互的前提下,要求平臺采取(低成本的)侵權風險防范措施,侵權人則在(權利人)發現成本和(平臺)責任縫隙間從事相應業務。隨著實踐經驗的累積,逐步得到承認的是,平臺企業的責任間隙,并不如預設的狹小,部分國家法院試圖擴大解釋“應該知道”,引入“故意視而不見”情節SEB S.A.v.Montgomery Ward amp; Co.,594 F.3d 1360( Fed.Cir.2010). ,但對于平臺企業的實際影響,仍有待觀察。正如前面提到的,繼續加重事后規制的力度,并非良方,依靠平臺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自主加強規制措施,更缺乏理論和實踐的可行依據。因之,對平臺企業科以何樣的義務,設置何樣的機制,督促其防患于未然,更多地體現分配正義,就成了立法和行政部門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互聯網平臺的新治理模式:邁向一種多元治理
(一)多元治理的必要性
我國《民法典》、知識產權法都有關于互聯網平臺履行一定注意義務的規定。這種追究法律責任的方式,體現了法律作為治理手段的重要性,是立法部門對某些社會活動的持續性控制,其目的在于追求一種符合國家價值導向的公共政策。它體現的是一種規制的模式,重在強調國家公共部門對非政府部門行動的控制。然而,隨著互聯網社會和全球化的到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國家機構與非國家機構之間的關系和互動的新形勢出現了,之前那種立體化、科層化的工作模式,逐漸代之以扁平化的去中心的工作模式。此時,非政府主體將承擔更多的政府職能,因之,新治理理念強調國家與非國家主體之間的相互依賴,強調治理發生于較少科層而更多網絡體系之中的趨勢[14]。由此,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是互聯網領域的一個新特點,它認識到政府能力的局限,承認非政府主體的價值,認為二者的互動合作對于秩序更為重要。這種治理模式承認非政府主體的自我規制體系,并對其進行觀察,在此基礎上認可后者的規制結果,或者對其結果進行干預,但這種干預不是直接而為,而是對其進行調控或者激勵。這種治理模式被稱為元規制[15]。
元規制強調在制定規則、監督、執行規則等方面的多元參與,意圖確保平臺企業運用被賦予的裁量權,實現公共政策目標,而非自身的私人利益。元規制模式下,法律對互聯網平臺科加的行政責任,是政府主體進行調控或者激勵的主要手段。但是,政府監管并不是元規制的唯一調控機制,市場機制與社群參與同樣可對互聯網平臺施加壓力。因之,互聯網平臺的元規制是一種多元治理體系。多元治理體系優于單一政府監管的地方在于:規制的智識障礙更少、獲取的信息成本更低、執行更為靈活有效[16]。通過外部監管的威懾,多元治理體系,克服了平臺企業自我規制動機不足的問題;相較于科責更高的注意義務,多元治理體系,為平臺企業保有內部調整的治理空間,減少因嚴格的外部責任,沖擊平臺內確保良善行為的基礎和獨立能力。
(二)事先預防:算法治理的可能與規制
就平臺的自我規制而言,算法治理路徑,被頻頻提及[17]。這一思路更著眼于技術,認為平臺應當運用算法,實現內部自查,算法治理的實施依賴于一個強大的數據庫,為平臺審查其接受的服務或內容的合法性。這種思路與通過法律的事后規制相比,它可以把糾紛化解于發生之前。在過去,平臺企業多數辯稱,這種技術給互聯網平臺帶來過多的負擔,它迫使平臺去雇傭更多的員工,對用戶傳至平臺的內容進行事先審查。然而,在互聯網空間,算法設計具有實際約束力,它是程序設計的一系列計算過程,通過輸入(值)向輸出(值)的轉換,算法回應了“怎么做”的問題,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步驟。理論上,互聯網平臺通過算法設計,自動剔除(而非人工篩選)具有侵權之虞的商品或服務,是可欲的。困難之處在于,如何運用計算機等具備信息處理能力的裝置精確識別侵權特征,并確保算法對商品或提供商品行為的性質判斷,與善良管理者基本一致,成為算法治理的障礙。
大數據技術的產生與運用,使算法治理被賦予新的期待。大數據技術并非簡單改變數據的排列或呈遞方式,而是通過處理與分析底層數據,生成推斷性信息,它可為人們提供觸摸、理解和逼近現實復雜系統的可能性[18]。換言之,經由結構化處理和數據集訓練,利用算法精確識別侵權特征、判斷行為性質,成為可能。事實上,以算法實施為基礎的自動化侵權檢測技術,已然落地。美國YouTube公司開發內容ID(Content ID)系統,利用儲存有版權內容(多為影片)的數據庫,交互比對用戶上傳的視頻內容,自動識別、剔除侵權內容。我國百度公司針對百度文庫開發的版權過濾系統(DNA反盜版文檔識別系統),實施自動化侵權檢測技術。限于技術能力,自動化侵權檢測技術較多運用于商標和版權,甚少適用于專利侵權檢測,因為平臺用戶甚少上傳與專利相關的數據內容用以比對發現侵權產品。
算法治理的實現,意味著互聯網平臺負擔著高于法定的注意義務。與其說這是平臺企業社會責任感的提高,倒不如說,是多元治理網絡的實施表現。具有說服力的事實是,百度文庫大批量下架涉嫌版權侵權文檔,開發版權過濾系統,并非由于著作權法修改或管理層結構更迭,而是國家版權局在2010年整治侵權盜版專項行動(劍網行動)的實施。與之相類似,2014年國家工商總局披露《關于對阿里巴巴集團進行行政指導工作情況的白皮書》,要求“充分運用信息網絡技術進行內部管理”。隨后,阿里巴巴集團打通“Aliprotect”和“Taoprotect”兩個平臺,成立阿里巴巴知識產權平臺(IPP),開發“知產保護科技大腦”算法系統,主動攔截侵權商品。反過來,算法治理的實施,為執法部門提供侵權嫌疑人線索以及電子證據采集,形成共治的合力。
多元治理網絡初見成效,但令人生疑的是,平臺企業對侵害知識產權的行政責任邊界何在。依據《電子商務法》第84條,平臺企業承擔的行政責任范圍,與民事責任相近,包括履行“通知―刪除”規則和注意義務,但是,(行政責任項下)注意義務的設定,是否應與現行(針對民事責任)司法解釋保持一致,尚未明確。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國家工商總局出臺《網絡交易管理辦法》,該辦法第26條要求,平臺企業對平臺內發布的商品或服務建立檢查監控制度,與之相配套的《網絡交易平臺經營者履行社會責任指引》第17條規定,“網絡交易平臺經營者應采取技術手段屏蔽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等違法商品信息”。誠然,“社會責任指引”并非強制性行政規范,但考慮執行、解釋上位規定時,可能“不經意”地創設新的義務,以下因素應當納入考量:第一,原則上,只有當平臺企業沒有或者缺乏足夠的動力去控制違法行為時,通過強化行政責任的激勵控制,才是必要的;第二,注意義務設定的前提,是平臺企業能夠以合理的成本阻止相關違法行為;第三,應當注意平臺企業履行義務時,與其他主體的關系,特別是對未違法者施加的限制[19]。依此,行政機關是否要求平臺企業履行普遍的主動審查義務,作為行政上的履責前提,應當保持謙抑。
(三)多元治理的規范保障
平臺的行為、服務不同,注意義務也有所差別,對這種差別的發現與運用,并不關乎法律之規定,而是依賴于差別形成背后依托的知識,即如何在保障平臺企業平穩運營的同時,有效抑制侵權產品市場的需求。這種知識的有效運用,并非來源于某個智識超群的個體或機構的先見,而是依賴于經驗積累衍生的共識。例如,淘寶網針對出售假冒商品實行“三振出局”制,即賣家每次出售假冒商品的行為(同時刪除相關信息)記為一振,若同一賣家出售假冒商品累計達三振,將被查封賬戶。這種自主細化規則的做法,便是經驗知識累積的結果。“政府監管+平臺自治”模式有助于以上共識的產生,它關注平臺經濟風險的動態演進,盡管政府監管權能同樣授權于法律,但平臺企業在多元治理體系中,更多面臨行政指令與社群參與帶來的壓力。
因之,在多元治理體系下,對互聯網平臺侵害知識產權的治理,并不苛求法律強制的徹底貫徹,而是尋求一種多元對話。規則適用的穩定性與可預期,并非多元治理體系的實施目標,相反,通過構建對話平臺并參與對話,多元治理體系在一定外部壓力的作用下,形成接受度更高的規制結果。這也是為何在多元治理體系下超越法定注意義務的實施是可欲的原因。在此過程中,多元主體(政府、社群)的外部監督不可或缺,它是事先治理(平臺自我規制)落實的直接推動力,問題在于,如何確保多元治理體系的實施,源于外部監督力量與平臺企業的互動合作,而非具有計劃色彩的指令結果。由此,(多元治理)規范保障的可取途徑,并非試圖精確地類型化平臺義務,再加以推進,而是確保平臺企業、平臺內社群、政府的治理合力,是有效且可持續的。后者依賴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制度供給:第一,信息保障機制的建立。多元治理合力的形成,源于規制與激勵相容,它打破科層化治理模式中,由于內部相對封閉,(平臺企業、平臺內社群、政府)經由成員間的相互默許,維持高侵權風險的運作。多元治理的前提是信息的充分保障,通過加重合規的利益張力,激勵不同主體參與治理。由此,應供給以下信息——用戶遞交投訴的機制,刪除、屏蔽(侵害知識產權)商品或服務的判斷標準,平臺內的投訴數量,處理投訴的人員組織情況,最終被刪除或者屏蔽的信息數量,用戶申訴的情況,轉遞其他專門機構的處理情況,平臺處理的周期,以及通知和反通知的適用情況。2017年,德國通過《網絡執行法》,要求收到100起以上投訴的平臺企業,負有制作報告之義務,每半年制作一次,完成后一個月內公布在聯邦司法部和網站主頁,報告內容與前述信息大體相同[20]。第二,算法解釋權的構建。平臺主動承擔審查義務的技術依托,是算法治理,基于相關性而非因果關聯,算法能夠低成本和高效率地索引、篩查、處理侵害知識產權風險,但其背后的風險是,由于無從知曉背后的運算邏輯,人們難以有效挑戰和回應算法決策。一旦平臺用戶遭遇算法歧視,其將被結構性地鎖定,并面臨系統性的不利影響[21]。算法治理只有是可理解的,才是可控制的。為此,算法控制者(平臺企業)應負有解釋算法的義務,尤其針對影響平臺用戶實際權益的自動化決策(或人機輔助),應當作出易讀、可驗證的解釋。必要時,這一解釋還應當符合反設事實標準,即回答什么是決策中與事實具有因果影響的重要因素,否則,將難以裁決算法決策的失誤,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目前,歐洲《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第22條、第35(3)(a)條規定,數據控制者負有算法解釋之義務,但由于未明確解釋標準,尚存流于形式之虞[22]。
(四)補充措施:信任機制的促成
在這種多元主體形成的治理網絡中,信任機制的建立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參與主體形成穩定的關系,并促進學習和知識的交流[23]。良好的信任機制可以增加人們的可預期性,并緩解互聯網平臺的風險。反過來,信任的形成又源于治理網絡的形成。
平臺企業對在基礎結構層采取了一些防范風險的措施。除了京東、阿里巴巴等平臺企業采取的“申訴+投訴+處理”等事后機制之外,這些措施還包括事先的機制。(1)實名注冊制。在用戶使用平臺服務時,用戶必須輸入真實信息,實名賬戶搭建了網絡空間與現實世界聯系的橋梁,而在實名要求下,認證與識別發生混同。一方面,可供認證的身份信息成為平臺監管的起點,平臺用戶需對自身行為負責;另一方面,可識別身份信息的供給,造成平臺用戶隱私的持續威脅。任何平臺監管行為,均在可識別身份信息的使用下展開,為避免侵權之虞,互聯網平臺一般會通過格式合同,遵循 “用戶明示原則”+“最少夠用原則”,要求平臺用戶同意使用其個人信息。這里存在的問題是,同意使用后,平臺用戶是否可進一步干預或控制個人信息的用途,以避免日常安寧受到侵擾。在歐洲,曾有議案提出數據主體的被遺忘權,亦即消費者有權在不接受某種服務后,從相關企業刪去其個人信息的權利。(2)事先調查與事后評價。在平臺服務中,平臺企業在為用戶提供服務時,平臺企業均會對商品或服務提供方進行背景調查,如他作為商家的過往記錄,有無犯罪前科,有無侵權行為等背景,這些背景知識為平臺對用戶的監管提供了針對性。在提供商品或服務的過程中,平臺可以依賴定位技術和系統記錄對商家或服務提供者進行監控,商品是否發貨、商家銷售記錄等都可以讓消費者在移動APP上了解。在商品交易完成或服務結束以后,接受商品或服務的一方可以對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一方進行評價,通常,最滿意的是五星評價。通過平臺內部的獎懲機制、穩定評價體系對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一方在增設壓力的同時也對其有所激勵,使其為用戶提供較好的服務。(3)平臺內的信息共享。平臺企業不止自己積累這些用戶的信息,還可以在平臺內共享這些信息,由此,為平臺內用戶提供查詢商品或服務提供方的可能性。通過平臺內信息的共享,客戶可非常便捷地熟悉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的類型或習性,如是否準時交貨、是否提供售后等。與事后評價不同,平臺內的信息共享,應由互聯網平臺供給,而非其他平臺用戶,如此,可減少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為爭取交易機會而降低信息的可信度、準確度。平臺企業在基礎結構層的這些措施在一定范圍內建立了信任,為用戶的交易形成和風險防范提供了參考。
除此之外,互聯網行業協會也應該完善相應的行業規范。2001年成立的中國互聯網協會在組織結構上設立了行業自律工作委員會、個人信息工作委員會、標準工作委員會、反垃圾工作委員會。中國互聯網協會還通過了《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互聯網搜索引擎服務自律公約》。這些自律公約規定了很多自律內容,對互聯網平臺企業的行為提供了規范要求。但是,由于這些規范要求是自律性的,并不具有強制性,如果平臺企業不執行這些規范,也只是在行業內受到其他企業的差評而已。互聯網平臺如果違反了這些自律協議或者行業規范,該如何定性?實踐中,有法院判決,這種行為構成了不正當競爭。由于行業規范不是法律,也不是商業道德,如果平臺企業沒有遵守行業規范,還不宜直接認定其行為就構成了不正當競爭[24],也不宜直接認為其違反了注意義務而應當對用戶的行為承擔責任,只能將其作為一個認定是否構成過失的考量要素。
多元治理體系的建立,必須突破傳統的通過司法保護和通過技術規范的缺點,邁向一種規制治理的新模式。從手段上看,既要發揮通過法律、技術進行治理的優勢,又要超越法律、技術的不足。從主體上看,既要依賴政府部門,又要依賴互聯網平臺企業等主體的自制,從而形成一個事先治理與事后救濟相結合的治理框架。對平臺企業,采取一種公私合作的多元治理模式[25],是一種較為合理的選擇。
互聯網已經構成了人們生活的一種方式,互聯網平臺在人們的日常交往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帶來的風險具有自反性。這種風險與互聯網本身共生存。由于互聯網平臺具有扁平化去中心的特點,對其僅采用通過法律責任進行治理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在互聯網平臺為人類帶來便利的同時,我們應當采用一種超越法律的互聯網平臺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應當帶有多元性的特點,應當吸收政府主體和非政府主體的積極參與。
參考文獻:
[1]COASE R H.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96.
[2]LOBEL O.The law of the platform[J].Minnesota Law Review,2016,101(1):87-166.
[3]KENNEY M,ZYSMAN J.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J].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6,32(3):61-69.
[4]周學峰,李平.網絡平臺治理與法律責任[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19.
[5]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M].張文杰,何博聞,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18:7.
[6]維爾納·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M].王燕平,侯小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6.
[7]張維迎.博弈與社會講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79.
[8]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7.
[9]吳定玉.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3(2):55-63.
[10]ARMSTRONG M.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7(3):668-691.
[11]崔國斌.網絡服務商共同侵權制度之重塑[J].法學研究,2013(4):138-159.
[12]崔國斌.論網絡服務商版權內容過濾義務[J].中國法學,2017(2):215-237.
[13]楊立新.網絡交易法律關系構造[J].中國社會科學,2016(2):114-137,206-207.
[14]ABBOTT K,SNIDAL D.The governance triangle: Regulatory standards institutions and the shadow of the state[M]//MATTLI W, WOODS N.The politics of global regul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44-88.
[15]科林·斯科特.規制、治理與法律:前沿問題研究[M].安永康,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6.
[16]BALDWIN R,CAVE M,LODGE M.Understanding regulation:Theory,strategy,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39.
[17]張吉豫.智能社會法律的算法實施及其規制的法理基礎:以著作權領域在線內容分享平臺的自動侵權檢測為例[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6):81-98.
[18]HEY T,TANSLEY S,TOLLE K.第四范式:數據密集型科學發現[M].潘教峰,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4.
[19]KRAAKMAN R H.Gatekeepers: The anatomy of a third-party enforcement strategy[J].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86,2(1):53-104.
[20]查云飛.德國對網絡平臺的行政法規制:邁向合規審查之路徑[J].德國研究,2018(3):72-87.
[21]BALKIN J M.The three laws of robo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J].Ohio State Law Journal,2017,78(5):1217-1241.
[22]張欣.算法解釋權與算法治理路徑研究[J].中外法學,2019(6):1425-1445.
[23]KLIJIN E.治理網絡中的信任[M]//包憲國,譯.斯蒂芬·奧斯本.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新觀點.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295.
[24]李雨峰.互聯網領域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判定[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25-30.
[25]章志遠.邁向公私合作型行政法[J].法學研究,2019(2):137-153.
Anew governance model for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y internet platforms: Towards a multiple governance
LI Yufeng, DENG Sidi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nternet has formed a platform economy. Platform companies connect us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es of scale, less idle, accurate pricing, and information dynamics. While providing convenience, the platform economy also brings more risk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Existing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regulation of platform companies on the liability for compensation after the damage.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self-regulation of platform companies, the post-regulation model has limitations. In order to avoid the expansion of the risk of internet platforms infringing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combination of post-regulation and pre-regulati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platform enterprise autonomy, and law and industry norms are adopted. The model is more scientific.
Key words:" platform enterprises; economies of sca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fringement liability; multiple governance
(責任編輯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