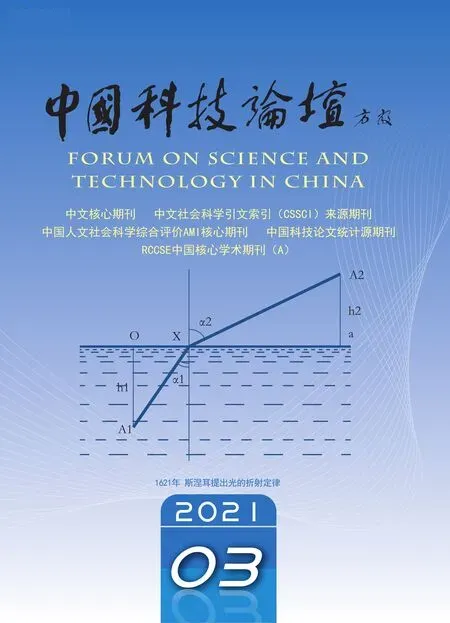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對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的影響分析
閻海峰,王墨林,蘇 聰
(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上海 200237)
0 引言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和大眾產權意識的提高,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性逐漸凸顯。作為國家設立的保護企業(yè)知識資產的核心制度安排,知識產權制度是影響企業(yè)實施國際化戰(zhàn)略,實現(xiàn)知識轉移、轉化的重要因素[1]。但是,目前各國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依然存在巨大差異,有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利弊爭論也日漸激烈[2]。對于知識產權制度薄弱的發(fā)展中國家,企業(yè)在跨國經營過程中常常要面臨由此引發(fā)的“來源國劣勢”,受到東道國政府機構的“特別關注”,如2018年美國政府制裁中興和華為事件[3]。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儼然成為影響企業(yè)對外投資的重要因素。
那么,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如何影響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截至目前,鮮有學者關注這方面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學者從宏觀國家層面給予解答,如Hasan等[4]、Alimov等[5]指出加強知識產權制度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跨國并購活動,且這種制度影響在高新技術行業(yè)更顯著。也有學者從微觀企業(yè)層面探究知識產權制度與并購股權比例之間的關系,Ahammad等[6]、劉煜等[7]都以發(fā)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yè)為樣本,發(fā)現(xiàn)企業(yè)在知識產權制度完善的東道國投資時傾向于選擇高股權并購模式。現(xiàn)有研究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之間的關系,但仍有以下不足:①現(xiàn)有文獻大都關注宏觀層面,對知識產權制度或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如何影響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過程的微觀機制研究較少;②現(xiàn)有微觀機制研究都未對并購類型進行詳細區(qū)分,國家設立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是為了保護個人或企業(yè)的專有知識資產不受侵犯,其是否會對除以技術尋求為目的之外的并購活動產生影響仍未可知;③現(xiàn)有研究過度強調東道國知識產權制度質量的影響作用,如減少不確定性、抑制機會主義和降低交易成本等,忽略了企業(yè)在跨國并購時因制度差異而造成的合法性問題及不同的戰(zhàn)略選擇[8-10],因此相較之下使用知識產權制度距離更易于探析跨國企業(yè)如何應對多重且復雜的知識產權制度壓力;④現(xiàn)有文獻的研究對象多為發(fā)達國家企業(yè),而隨著發(fā)展中國家企業(yè)海外資產尋求熱情的持續(xù)高漲,探索發(fā)展中國家 (特別是中國)情境下的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對跨國技術并購過程的影響有著重要意義。
本文選取2005—2018年中國企業(yè)實施的249個跨國技術并購事件為研究對象,探討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如何影響中國企業(yè)的跨國技術并購過程 (并購持續(xù)時間和并購股權選擇)。研究發(fā)現(xiàn):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并購持續(xù)時間呈倒U型關系,即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中國企業(yè)海外經營的合法性問題凸顯,當其感知到制度壓力時,本身強烈的資產尋求動機促使跨國技術并購的快速、成功實施;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并購股權比例呈U型關系,即在知識產權制度相似和差異較大的東道國,中國企業(yè)通常會選擇高股權并購模式。由此可見,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和股權選擇呈非線性關系,其本身并未完全阻礙中國企業(yè)的跨國技術并購。本文的貢獻在于:聚焦制度理論,從微觀機制出發(fā)回答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如何影響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過程,豐富了制度距離與企業(yè)跨國并購的相關研究,識別出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影響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和股權選擇的拐點。
1 理論基礎和研究假設
跨國技術并購是指主并企業(yè)為獲得國外目標企業(yè)的技術知識和能力而實施的跨國并購行為[11]。一般來說,并購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并購前 (公開宣告前的初步協(xié)商時期、公開宣告后的交易完成時期)和并購后 (財務績效、創(chuàng)新績效和人員整合等情況)[12]。相較于企業(yè)常規(guī)的對外投資活動,跨國技術并購因其顯著的戰(zhàn)略資產尋求動機促使并購雙方越發(fā)謹慎地對待交易活動,如開展更詳盡的盡職調查和審計評估等相關工作。同時,若并購方來自發(fā)展中國家或被并購方涉及東道國敏感行業(yè),交易活動也有可能遭到當?shù)卣块T的“特殊審查”、阻撓或叫停,如2016年中國國家電網75億美元收購澳大利亞最大電網公司Ausgrid的項目,以威脅“國家安全利益”為由被強制叫停。
目前,有關跨國技術并購的相關研究多集中于并購后整合階段,如財務績效、創(chuàng)新績效和人員整合等,對中間過程如持續(xù)時間、并購溢價和股權選擇等研究較少[11,13]。在研究影響跨國技術并購過程的前因因素文獻中,多關注企業(yè)創(chuàng)新能力、并購經驗和文化距離等,缺乏對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影響機制的認識[6,14]。因此,本文聚焦制度理論,結合其他理論如組織慣例、跳板理論,闡釋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如何影響中國企業(yè)實施跨國技術并購。
1.1 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
并購持續(xù)時間是交易公告日至交易完成日的日期。在這個中間時期,并購雙方通常需要做大量準備工作,如提供詳細的公司背景材料、了解利益相關者訴求、制定整合策略等[15]。由于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的戰(zhàn)略資產尋求特點,并購持續(xù)時間很容易受到兩國知識產權制度差異的影響。
當中國企業(yè)在臨近母國知識產權制度水平的國家投資時,各國之間知識產權制度的差異較小,能夠對并購的有益作用微乎其微[16]。Hagedoorn等[17]指出,國家之間知識產權保護的差異取決于立法和執(zhí)法的有效性,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可極大降低企業(yè)從事各種國際投資活動時的風險和成本。隨著知識產權制度 (規(guī)制、規(guī)范和認知)距離的增大,由于缺乏對東道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guī)、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相關市場信息的了解,企業(yè)進行跨國技術并購面臨巨大不確定性和風險[18],這不僅使中國企業(yè)更難于正確解讀當?shù)丶夹g并購的相關制度、條例和規(guī)定,也增加了并購方的交易成本[19]。
由知識產權制度差異引起的合法性問題也不容忽視。合法性是在特定規(guī)范、認知、價值觀和信念體系等制度框架下,個人或組織的行為被視為是合適的、可取的、適當?shù)囊环N認可或感知[20]。Greenwood等[21]提出,組織長期在一個特定環(huán)境經營時,會形成特殊的組織慣例或組織結構。這種根植于組織中的制度規(guī)范很難隨著制度環(huán)境的變化而發(fā)生改變,并可能導致管理者在認知變革和實施變革中出現(xiàn)困難[22-23]。因此,制度嵌入性越強,阻止企業(yè)變革的粘性或慣性就越大。中國企業(yè)在與母國制度環(huán)境類似的東道國進行技術并購時,能夠有效利用國內形成的經驗、慣例,在東道國熟練地運營,縮減并購持續(xù)時間[9-10]。但是,長期在國內薄弱的知識產權制度中經營會導致企業(yè)在知識產權創(chuàng)造、保護和運用等方面存在不足,無法使用有效手段應對持續(xù)增長的跨國經營劣勢。伴隨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中國企業(yè)獲取“合法性”的難度和跨國技術并購交易成本急劇上升,而組織經驗、慣例的有效性卻逐步減少,直至企業(yè)管理者感知到東道國知識產權制度壓力實施變革[24]。因此,中國企業(yè)在臨近母國知識產權制度水平的國家進行跨國技術并購時,并購持續(xù)時間會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而變長。
制度理論指出,制度是外生的,并可以被經濟行為個體客觀觀察到[8]。東道國制度質量的感知取決于個體或組織對制度信號的客觀翻譯和獨特認識[25]。因此,當企業(yè)在遠離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國家投資時,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經過某一拐點時企業(yè)管理者明顯感知到外界的制度壓力,意識到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制度同構、制度創(chuàng)業(yè)以實現(xiàn)組織變革,獲得合法性[26]。此外,與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差異較大的國家,往往是那些知識產權保護更加嚴格、戰(zhàn)略資源豐富的發(fā)達國家,如美國、德國和瑞典等。東道國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不僅可以保障整合期并購雙方技術知識順利地轉移、轉化,也能使并購程序更加公開、透明,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的積極性[16]。同時,Yadong等[27]指出新興市場企業(yè)利用國際擴張作為跳板,獲取關鍵資源,以更有效地與國內外對手進行競爭,降低他們在國內受到的制度脆弱性和市場約束。跨國技術并購是中國企業(yè)獲取國外戰(zhàn)略資源如專利、技術秘密和商標等,實現(xiàn)技術趕超的重要手段,受到國內各利益相關者的大力支持[28]。賈鏡渝等[29]指出,中國企業(yè)的海外技術并購行為不僅歸因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更源于企業(yè)自身對國外技術知識等戰(zhàn)略資源的強烈渴求。鑒于此,為了快速、有效地完成跨國技術并購,獲取發(fā)達國家的戰(zhàn)略資源,中國企業(yè)往往會竭盡所能,如高溢價并購、咨詢專業(yè)機構等。因此,中國企業(yè)在遠離母國知識產權制度水平的國家進行跨國技術并購時,經過某一拐點后,并購持續(xù)時間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而變短。
綜上,結合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實際情況,企業(yè)在實施跨國技術并購時,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并購持續(xù)時間會經歷一小段上升后到達拐點,然后逐漸降低,即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呈倒U型關系。基于此,提出假設1: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呈倒U型關系。
1.2 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跨國技術并購股權比例
前期研究關于制度距離與跨國并購股權選擇的結論尚未達成一致,其中原因可能包括未劃分并購類型、未區(qū)分并購方來源國以及未區(qū)分臨近、遠離母國制度距離的情形等[14]。
Papageorgiadis等[30]指出,中國企業(yè)非常熟悉如何在國內薄弱的知識產權執(zhí)法制度中經營,因此他們可以更有效地將母國成功的商業(yè)模式復制到東道國。當中國企業(yè)在知識產權制度相似的東道國進行跨國技術并購活動時,熟悉的制度環(huán)境使企業(yè)更易于在當?shù)亟洜I,并且高股權比例有助于跨國企業(yè)充分控制被并購企業(yè),有效保護跨國技術并購過程中獲得的無形資產[6,9]。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跨國企業(yè)的經營劣勢逐漸凸顯,組織慣例、經驗的適用性慢慢減弱。面對這種情況,并購方往往會選擇部分或低股權并購模式獲取東道國合法性,從而使組織間技術、組織慣例和資源的轉移更方便、快捷[9,14]。此外,臨近中國知識產權制度水平的國家往往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同樣存在嚴重缺陷。在這種制度環(huán)境下,收購方可能難以保護被收購的技術和處理低效的資本、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為了應對這些挑戰(zhàn),并購方需利用東道國關系、知識等資源,尤其是目標企業(yè)的員工和社交網絡來獲取合法性,確保員工之間最大限度的合作,這也有可能導致其選擇部分或低股權并購模式。因此,當中國企業(yè)在臨近母國知識產權制度水平的國家進行跨國技術并購時,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并購方的股權選擇模式可能會由高股權收購逐漸轉向低股權收購。
跨國技術并購被中國企業(yè)視作獲取先進技術、實現(xiàn)創(chuàng)新能力快速躍升的助推器,其中的核心環(huán)節(jié)便是對被并購方技術的有效整合[27]。伴隨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東道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經濟發(fā)展水平也將進一步提高。中國企業(yè)若繼續(xù)采取部分股權并購模式,將可能因被并購方的先進技術而產生權力失衡,以及因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創(chuàng)新文化的差異影響并購雙方順利開展工作,增加企業(yè)面臨的并購整合成本。此時,由于東道國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保障并購方對被并購企業(yè)價值的占有和利用,中國企業(yè)采取高股權并購模式更易獲得高投資回報,進一步提升競爭優(yōu)勢[6]。另外,兩國之間較大的制度差異以及技術資產在轉移過程中的知識粘性嚴重阻礙跨國企業(yè)母子公司之間知識的轉移、轉化[31]。因此,為了有效控制和利用被并購方的戰(zhàn)略資產,促進并購雙方在整合過程中的交流合作,降低技術知識轉移過程中的風險,在遠離母國知識產權制度水平的東道國進行跨國技術并購時,隨著制度距離的增大,中國企業(yè)股權選擇模式可能會由低股權收購逐漸轉向高股權收購。
綜上,結合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實際情況,企業(yè)在實施跨國技術并購時,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并購方的股權選擇會經歷一小段下降后到達拐點,然后逐漸上升,即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股權選擇呈U型關系。基于此,提出假設2: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股權比例呈U型關系。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數(shù)據
本文的樣本來源于BvD-Zephyr數(shù)據庫,選取2005—2018年宣告發(fā)生且已完成的中國企業(yè)海外并購樣本,初始事件數(shù)量為816個。按照如下標準篩選:①并購方公開發(fā)布的并購公告中須明確表明是以技術獲取為動機的海外并購樣本;②為了保證數(shù)據的可獲取性,并購方須是在中國 (大陸及香港)上市的企業(yè),并剔除被并購方為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中國澳門等樣本;③剔除存在關聯(lián)交易、并購方為個人和并購信息不完全等的樣本;④剔除并購雙方注冊地為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的交易。經篩選,最終獲得249起中國企業(yè)在美國、瑞典、泰國等25個國家的醫(yī)藥制造業(yè)、造紙和紙制品業(yè)、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yè)等31個行業(yè)的跨國技術并購事件。知識產權制度距離數(shù)據來源于產權聯(lián)盟發(fā)布的各國知識產權指數(shù)。其他變量數(shù)據來源于國泰安數(shù)據庫、國家外匯管理局、聯(lián)合國商品貿易統(tǒng)計數(shù)據庫等。
2.2 變量測量
(1)因變量。因變量有兩個:①并購持續(xù)時間:借鑒Dikova等[19]的研究,采用從并購公開宣布日期到完成交易的生效日期之間的時間長短;②并購股權比例:借鑒Guadalupe等[32]的研究,使用連續(xù)型數(shù)值指標測量該變量,即并購股份占被并購企業(yè)總股份的比例。
(2)自變量: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在國家知識產權制度的相關研究中,Park[33]開發(fā)的測量方法得到廣泛應用。該方法主要是基于專利立法測算得出,忽略了知識產權司法執(zhí)行等方面的因素。因此,綜合考慮國家知識產權制度的立法和執(zhí)法兩個方面,數(shù)據分別來源于GP指數(shù)和BSA Global Software Survey中的版權盜版調查。知識產權制度距離采用差值距離法計算,即兩個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立法和執(zhí)法的得分之和相減后取絕對值。
(3)控制變量。參照相關跨國并購文獻,控制變量主要涉及企業(yè)、行業(yè)、國家和交易情況4個層面的因素[19,34]。企業(yè)層面:①企業(yè)性質,衡量并購方企業(yè)性質,國企賦值為1,否則為0;②資產回報率,衡量并購企業(yè)的盈利能力,采用并購方樣本事件上一年的數(shù)據,計算方式為:凈利潤/總資產;③資產負債率,衡量并購企業(yè)的負債水平,采用并購方樣本事件上一年的數(shù)據;④跨國并購經驗,并購方在樣本事件之前有跨國并購經驗賦值為1,否則為0。國家層面:①雙邊經濟關系,衡量中國與并購目標所在國之間的經濟關聯(lián)度,采用并購方樣本事件上一年的數(shù)據,計算方式為:對中國與并購目標所在國的進出口總值取對數(shù);②地理距離,衡量中國與并購目標所在國之間的球面距離;③文化距離,衡量中國與并購目標所在國之間的文化差異,采用Hofstede等[35]開發(fā)的6個文化價值觀維度和Kogut等[36]的文化距離公式測量兩國之間的文化距離。行業(yè)和交易層面:①行業(yè)集中度,以被并購企業(yè)所在行業(yè)中上一年前4家最大的企業(yè)所占的市場份額之和來衡量;②匯率,以樣本中并購事件完成當天交易使用貨幣與人民幣的匯率來衡量。
2.3 模型設定
由于假設1的因變量為跨國并購持續(xù)時間,是一個連續(xù)型變量,因此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進行檢驗。假設2的因變量是并購股權比例,是一個最小值為0.01、最大值為1的連續(xù)型有限因變量,因此使用Tobit回歸模型進行檢驗。在回歸之前,計算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以及方差膨脹因子分析,見表1。由表1可見,VIF值均小于5,變量間的相關系數(shù)最高為0.555,表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1 描述性統(tǒng)計
3 實證結果
3.1 回歸分析
首先,為了減少研究偏差,借鑒Haans等[37]提出的3個檢驗U型和倒U型成立的標準:①二次項系數(shù)顯著為正或負;②定義域兩端的斜率要顯著為正或負;③轉折點 (TP)95%水平的置信區(qū)間需落在定義域范圍內。經檢驗,見表2和表3、圖1和圖2。本文研究結果符合上述要求。

圖1 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關系

圖2 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跨國技術并購股權比例關系

表2 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的回歸結果
由表2可見,模型 (1)為研究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關系的基準組,僅加入控制變量。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礎上加入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一次項,系數(shù)顯著為正 (β=0.665,p<0.05),與Dikova等[19]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即制度距離正向影響跨國并購持續(xù)時間。模型 (3)在模型 (2)的基礎上加入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二次項,系數(shù)顯著為負 (β=-1.376,p<0.001),且從整體模型的擬合程度看,模型 (3)是最優(yōu)的。因此,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遞增關系,而是呈現(xiàn)顯著的倒U型關系,驗證了假設1,即在與中國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臨近的國家,由于知識產權制度的相似性和母國制度的嵌入阻礙了企業(yè)管理者感知外界的制度壓力,使其無法實施有效變革,延長了并購持續(xù)時間。但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進一步增大,制度壓力也將急劇上升,當?shù)竭_某一程度 (轉折點2.2)之后,企業(yè)管理者明顯感知到制度壓力,會采取制度同構和制度創(chuàng)業(yè)等一系列變革來獲得外部組織合法性,縮短并購持續(xù)時間。中國企業(yè)在遠離母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國家進行跨國技術并購時,為了快速、有效獲取被并購方技術知識,一般都會不計得失,如采取高溢價并購等行為。
由表3可見,模型 (4)為研究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跨國技術并購股權比例的基準組。模型 (5)在模型 (4)的基礎上加入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一次項,系數(shù)顯著為正 (β=0.230,p<0.001)。模型 (6)在模型 (5)的基礎上加入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二次項,系數(shù)同樣顯著為正 (β=0.300,p<0.05),且從擬合程度看,模型 (6)的解釋力更強,即在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臨近的國家進行跨國技術并購時,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增大,中國企業(yè)逐漸由高股權并購轉向低股權并購。當?shù)竭_某一臨界點 (轉折點1.6)之后,東道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創(chuàng)新水平也進一步提升,為了保證對被并購方技術知識的有效控制,中國企業(yè)轉而采取高股權并購模式。

表3 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跨國技術并購股權比例的回歸結果
3.2 穩(wěn)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確認上述研究結論的可靠性,采用以下兩種方法進行穩(wěn)健性檢驗,見表4。

表4 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股權比例的穩(wěn)健性檢驗
(1)使用世界經濟論壇 (WEF)公布的 《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數(shù)作為自變量的替代變量進行穩(wěn)健性檢驗。結果如模型 (7)和 (8)所示,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二次項與跨國并購持續(xù)時間、股權比例分別在1%、5%水平上呈負相關和正相關關系,與上述結論一致。
(2)變換模型檢驗。借鑒Deng等[38]的方法,采用Cox風險比例風險模型檢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對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的影響。結果如模型 (9)所示,在Cox模型中,如果回歸系數(shù)小于0則代表該變量是保護因素 (延長持續(xù)時間);反之,大于0則為減少持續(xù)時間。本文也計算了風險比率,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一次項的HR為0.010,二次項的HR為2.877,當HR<1是保護因素,延長持續(xù)時間;當HR >1是減少持續(xù)時間,因此印證了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之間的關系。借鑒Lahiri等[34]的方法,將并購股權比例大于95%的視為完全并購,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采用Logit回歸模型驗證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跨國技術并購股權比例之間的關系。結果如模型 (10)所示,結論依然穩(wěn)健。
依據上述穩(wěn)健性檢驗過程,得出結論:知識產權制度距離依次與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股權比例呈倒U型和U型關系得到了驗證。
4 結論與討論
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如何影響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的微觀過程?面對理論上的爭議和實證檢驗的缺乏,本文選取2005—2018年之間中國企業(yè)實施的249起跨國技術并購事件,聚焦制度理論,實證檢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和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股權選擇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與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呈倒U型關系,與股權比例呈U型關系。本研究的理論貢獻有以下4個方面:①從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的微觀過程方面回答了“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如何影響跨國技術并購”問題,識別出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影響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過程的轉折點;②豐富了制度距離影響跨國并購持續(xù)時間的研究,前期研究雖實證檢驗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離對跨國并購的影響,但鮮有研究關注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對跨國技術并購持續(xù)時間的作用;③解答了有關制度距離與跨國并購股權選擇之間的爭論,現(xiàn)有研究一直非常關注各種制度距離如何影響跨國并購股權選擇,且爭議不斷,本研究從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角度彌補了該缺口;④考察了中國情境下的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對跨國技術并購中間過程的影響,這也是對現(xiàn)有研究的一種拓展。
本研究的實踐意義在于:①中國政府應更加重視跨國技術并購,將其作為提升我國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完善相關產業(yè)鏈的重大戰(zhàn)略舉措。目前,中國雖然已通過吸引外資的方式成為了全球制造業(yè)大國,但距離成為制造業(yè)強國還有一定距離。海外技術并購正是中國企業(yè)獲取戰(zhàn)略資源、突破創(chuàng)新能力桎梏、實現(xiàn)技術趕超的有效途徑。②知識產權制度是影響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的重要因素,中國企業(yè)在實施跨國技術并購的過程中應注意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非線性影響作用。雖然發(fā)達國家在知識產權立法、司法和執(zhí)法方面較為嚴格,中國企業(yè)在跨國技術并購過程中可能會因國家安全等原因受到限制,但中國企業(yè)強烈的戰(zhàn)略資產尋求動機、發(fā)達國家前沿的技術知識和公開、透明的審查流程等諸多因素使中國企業(yè)免受知識產權制度距離的消極影響。因此,中國企業(yè)要謹慎對待實施跨國技術并購的區(qū)位,盡量選擇那些與母國知識產權制度距離較遠、創(chuàng)新資源更加豐富的發(fā)達國家進行投資。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①本文只著重研究知識產權制度距離對中國企業(yè)跨國技術并購 (持續(xù)時間和股權選擇)中間過程的主效應,對其中可能存在調節(jié)、中介因素及并購后的整合過程未展開研究;②本文只關注中國企業(yè)的跨國技術并購過程,未包括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等。因此,未來研究可在以上方面適當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