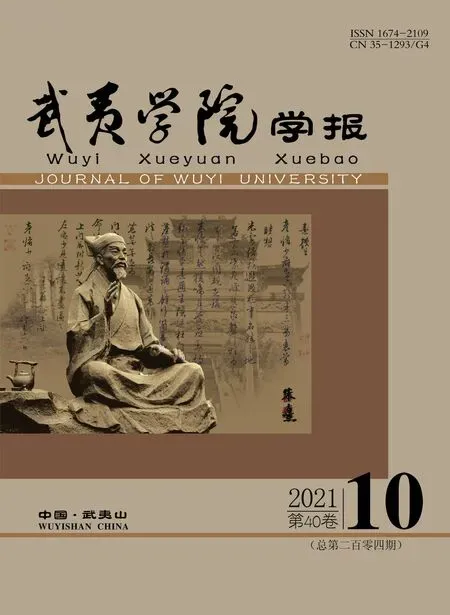瑞巖喚醒主人公,把手經行禁綱中
——瑞巖古佛的“惺惺”禪法與朱子理學
黎曉鈴
(武夷學院 朱子學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一、瑞巖扣冰古佛的“惺惺”禪法
武夷山瑞巖扣冰古佛,法號藻光,但是又常被稱為辟支古佛。所謂辟支,是獨覺、自悟成佛的意思。其中,以自問自答作為其主要形式的“惺惺”禪法,就是扣冰辟支古佛獨自領悟到的與眾不同的禪法。所謂“惺惺”,“惺”是“醒悟”“清醒”的意思。瑞巖扣冰藻光禪師每日都會自問“惺惺否”,即扣問自己的內在的主人翁是否處于清醒的狀態。得證悟后,扣冰藻光禪師則會自答“惺惺”。這其實是一種對內觀照和內省的工夫,與佛教華嚴宗強調向外學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佛教華嚴宗常用“月印萬川”比喻的佛法與現實的關系。佛法智慧如同人們所能看到的天上皎潔無暇的月亮。然而若佛法智慧只能是高懸飄渺空中,又當如何讓現實中人去習得呢?對此,華嚴宗強調“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佛教的最高智慧可以印照在現實之中,人們可以其實可以通過探究現實從而領悟最高的智慧。
應當說,十分重視向外學習的華嚴宗思想在當時佛教界已經非常流行,扣冰藻光禪師早年的師父行全和尚或許就曾一再對藻光禪師強調了類似的思想。因此,早年的藻光禪師曾自嘲“徒守一塢白云”的自己可能會變成見識淺陋的“戀甕酰雞”,更立下了“周覽大千世界,以收千江明月”[1]的志向,并開始云游四方,參訪大德,希望通過增加見識的途徑,從而真正地領悟到佛法。然而,在跋涉四方的過程中,瑞巖扣冰禪師忽然又領悟到“云遏千山靜,月明到處通”“欲會千江明月,只在一輪光處,何用捕形捉影于千巖萬壑,以踏破芒履耶?”[1]也就是說,向外學習其實還是“捕形捉影”,“內證”才是領悟最高佛法的最終途徑。于是,瑞巖扣冰禪師停止了云游,開啟了長久的“惺惺”內證修行。
可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禪師們對此形式進行了相當猛烈的攻擊。比如,風穴延沼就認為“自拈自弄有什么難?”[2]大慧宗杲認為,“瑞巖家風,呼主人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2]無門評唱:“瑞巖老子,自買自賣,弄出許多神頭鬼面,何故聻?一個喚底,一個應底。一個惺惺底,一個不受人瞞底。認著依前還不是,若亦效他,總是野狐見解。”[3]回觀后代禪師們對藻光的批評,我們發現他們都是對扣冰藻光脫離現實而自問自答的方式頗為不滿。但是,聯系瑞巖扣冰藻光禪師更多的話頭和事跡,我們會發現扣冰藻光的“惺惺”禪,并不是表面形式上的如此簡單。我們可以從扣冰藻光禪師年輕時參謁雪峰義存禪師說起。
扣冰古佛早年參謁的第一位大德就是當時名震四方的雪峰義存禪師。唐咸通十年(公元869 年)雪峰義存48 歲,已經游方求道,遍歷名山,北游吳、楚、梁、宋、燕、秦等地,曾參拜過莆田的慶玄律師、福州的宏照禪師、安徽的大同禪師、浙江的洞山良價禪師、湖南的德山宣鑒禪師,最后回到福州。而扣冰藻光那時才26 歲,主要在武夷地區活動。
雪峰義存見到扣冰藻光的第一眼就對他大喝一聲:“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在此,雪峰義存其實是模擬人們在現實中陷入世俗慣性邏輯而進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對此,人們常常煩亂不堪、不知所措,甚至陷入抑郁和精神障礙。但是扣冰藻光卻不慌不忙地回答:“橫行幾步有何妨?”扣冰藻光的“橫行幾步”指的是,人們其實可以暫時從外在越繃越緊的慣性邏輯中抽離出來,反觀內在,從而使自己能夠有更廣闊的視角和智慧控制眼前的局面。而從“幾步”我們也能夠看出,扣冰藻光并不是要求人們永久地逃離現實,而是指示人們可以從自己的內在挖掘應對現實的力量。此外,雪峰義存還以藻光帶來的鳧茈與米醬做為話題追問藻光關于內在的修行。
師時攜鳧茈一包、米醬一瓿為話頭。雪峰見曰:包中何物?師曰:鳧茈。雪峰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來。雪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雪峰曰:還更有麼?師曰:轉深轉有。又問:瓿中何物?師曰:醬。雪峰曰:何處得來?師曰:自合得。雪峰曰:還熟也未?師曰:不較多熟。[1]
鳧茈即荸薺,雪峰將話題由荸薺引向泥土,意在問什么樣的條件才能滋潤培養出香甜可口的荸薺,其實是緊接著藻光剛剛回答的“橫行幾步”問藻光向內挖掘可達的深度,也就是人們內在的潛力。“轉深轉有”的答案則意味著人們內在的潛力是無限的。而“自合得”的米醬“不較多熟”其實又指示著雖然人們內在潛力無限,但是又需要符合客觀條件才能在現實中運籌帷幄。
雪峰不語,良久又問曰:汝自舟來?陸來?師曰:順流鼓,不假跋涉。雪峰曰:千里而來不亦勞乎?師曰:既不假涉雪又(何)勞之有?雪峰曰:地僻山林,四畔風雪,何自而入?師曰:荊榛既辟,自無不入。[1]
緊接著,雪峰又以藻光如何到來為引,導向了如何運用客觀條件達成目標的討論。千里而來,長途跋涉會非常疲勞。但是藻光卻沒有選擇跋涉山林的費力方法,而是選擇乘舟順流而下,輕松抵達。這其實代表著只有充分開發人的主觀能動性才能合理運用客觀條件輕松達成目標。而“地僻山林,四畔風雪,何自而入?荊榛既辟,自無不入”則代表著人們是不可能通過躲入偏僻的深山老林的方式躲過世俗風雪的侵擾。如此可以看出,扣冰藻光禪師所主張的“惺惺禪”并沒有主張逃避現實,反而,我們能夠看到藻光禪師所努力的方向其實是探索如何挖掘內在的潛力和智慧,超越現實把握現實。
此外,扣冰古佛之所以得名“扣冰”,是因其持之以恒且堅強的意志力。武夷山的冬天異常濕冷,寒風刺骨,一般人穿著厚厚的棉衣,烤著火爐都難以抵擋嚴寒,而夏季常常酷暑難耐。可是藻光禪師回武夷山后,冬天再也不用火爐,夏天也不用扇子,一年四季穿著厚厚的破棉襖,唯獨通過控制呼吸砥礪內行。后在藻光四十歲左右,更在寒冷的冬天修煉到“扣堅冰而浴,略無寒色”因此,被人們稱為“扣冰和尚”。有句俗語叫“心靜自然涼”,同樣,通過心境的把握也同樣能夠抵御寒冷。而扣冰藻光禪師正是通過對心的把握克服外界對內在自我的影響,從而達到內在潛力的深度挖掘。
二、朱子惺惺法之來源
朱子也曾探訪過瑞巖寺,并寫下了《題瑞巖》的詩句:“踏破千林黃葉堆,林間臺殿郁崔巍。谷泉噴薄秋愈響,山翠空蒙畫不開。一壑只今藏勝概,一生疇昔記曾來。解衣正作留連計,未許山靈便卻回。”[1]其中“解衣正作留連計,未許山靈便卻回”展示的是朱子差點就沉迷于佛教寧靜而空靈的世界,但是現實中的使命感使他轉過身來,積極面對現實的世界。但是,朱子為面對現實而創立的理學工夫體系中卻給“惺惺法”留有了重要的位置。朱子在闡述“心”之內涵時說:“心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心治一個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4]。很顯然,朱子理學的“喚醒”吸收了瑞巖扣冰古佛的“惺惺”禪法。
而朱子理學工夫中惺惺法的直接來源是劉子翚所極力推崇的“不遠復”。“不遠復”是劉子翚向朱熹傳授復卦的“入德之門”,是身心修養的“三字符”。劉子翚在臨終前對朱子說:“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凈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后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于《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 不遠復’ 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5]可見,劉子翚是以“不遠復”融合儒佛,并將此交代給了朱子。“不遠復”源自《易經》卦二十四:“不遠之復,無袛悔,元吉。”《小象辭》 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不遠復”從字面上理解是“沒走多遠就要停下來回頭看”,其內涵是自我反省,及時糾正偏差,才不會在前行的道路上迷失方向,與瑞巖扣冰古佛的“惺惺”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若再往前推,我們會發現,“惺惺”禪的源頭其實是孟子的思想。孟子主張“性善論”,他更多地并不是在講人“性”如何,而是在講人“心”若何[6]。孟子強調,人的良心如同自然界的植物,若沒有外界的破壞會自然顯現出本然良善的一面,但是如果受到外界的干擾和破壞而沒有及時存養,良心就會被蒙蔽,從而使人淪為禽獸的狀態。因此,如何存養良心就成為了孟子學說中最大的命題。儒家對人的要求不僅僅是“獨善其身”,更要面對現實“開萬世之太平”。外界的侵擾若會蒙蔽內在良心,又當如何在外界的“槍林彈雨”中存養良心呢?孟子要求在夜晚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存夜氣”,劉子翚所提倡的“不遠復”要求的是面對外在不久就需要回到內在涵養。但是,其中的良心一直處于被動的狀態。
在孟子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于內在“良心”思考并沒有在儒學中繼續展開,反而是中國佛教哲學對此進行了更積極的探討。如何使內在的良心發揮作用抵御外界的干擾就是瑞巖扣冰古佛緊接著孟子的存養良心以及“不遠復”之命題的繼續探討和深入實踐。“云遏千山靜,月明到處通”,其中“云遏”并不代表月亮不存在,而是月亮被云朵遮蔽;而“月明”則代表月光發揮了作用穿透了遮蔽的云朵,也就是孟子學說中良心發揮了能動性掃除了來自外界的影響。因此瑞巖扣冰古佛看重的是如何使人內在的良心主動地發揮作用。“惺惺否”的扣問,代表著內在的良心并不是被動地等待外界侵擾的消退,而是能夠喚醒,并主動積極地發揮作用,以摒棄來自外界的侵擾。
而宋明理學家的出現,繼承和拓展了“惺惺”法,使之逐漸演變為理學家修養工夫的重要內容。二程特別推崇“敬”的涵養工夫,提出了關于身的“整齊嚴肅”和關于心的“主一無適”。其中“主一無適”就是指內心的專一、無雜念,所繼承的正是孟子的不被外物雜念打擾的“夜氣”說。而二程的弟子謝良佐則直接用瑞巖禪師的“惺惺”內涵創造性地闡釋了二程“敬”。謝良佐說:“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7]謝良佐明白,瑞巖禪師的“惺惺”并不是事事放下的空無,反而是要求十分清醒地面對現實。
三、朱子工夫體系中的惺惺法
朱熹對謝良佐就“惺惺”法的闡釋并不十分滿意。他說:“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5]這里的“仁”指的朱子理學體系中屬于“已發”的知覺和意識。朱子認為,謝良佐的“常惺惺”是在已發上做的工夫,并無涵養心內、涵養未發之意[4]。對此,朱漢民教授指出,“朱熹所提的問題又基于他自身理論建構的需要,因此他對謝氏‘常惺惺法’的評價未免失之偏頗。”[8]那么,惺惺法在朱子理學工夫的建構中又處于怎樣的地位呢?
應當說,朱子對瑞巖“惺惺”禪法的解讀是有自己創造性的構建的。朱子將心之狀態分析為“未發”“已發”以及“未發”至“已發”的三個階段,“惺惺”法也有相對應的三個階段。所謂“未發”是指思慮未萌、心下無事之時,也就是謝良佐所說的“心齋”之時,此時“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個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里,靜不是睡著了”[4];“未發”至“已發”時,“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4];已發時“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過”[4]。就此,我們可以看出朱子思想與謝良佐、瑞巖扣冰以及孟子的不同。孟子要求從“夜氣”也就是無事打擾、即朱子所謂的“未發”的時候去感受完好無損的良心,并加以存養,使之在有事之時也能夠如無事打擾的狀態一樣心平氣和地處理恰當。瑞巖扣冰和謝良佐重視用喚醒的方式使“良心”在應對事物之時能夠以清醒的狀態應對得當。
而朱子的細分,其實構建了孟子的“良心”以及瑞巖扣冰和謝良佐的“常惺惺”。孟子的“無事之時”,才是不被打擾的“心平氣和”的“清醒”之時,而朱子的“無事之時”卻有可能是睡著了,需要“惺惺”的提醒,使之保持覺悟。“未發”至“已發”,孟子、瑞巖扣冰、謝良佐都沒有這樣的提法。孟子只是要求將不被打擾的心平氣和的狀態存養好,使其能夠運用到應對事物之中。瑞巖扣冰和謝良佐則是喚醒在現實中被打擾反而懶得發揮作用而“睡著”的“良心”,使之清醒過來發揮作用,勇敢地應對現實。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區別呢?筆者以為,這應當與朱子努力構建的與物欲相對的天理論聯系起來理解。朱子使用“惺惺”法的目的就是通過“惺惺”的方法與物欲保持距離,“惺惺”不過是“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4]。如此才需要將心的狀態分為三個階段,在三個階段中同時摒棄物欲,從而才能貫通天理,實現朱子理想中的合理化和秩序化。所以朱子批評瑞巖古佛說:“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個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惺惺’字則同,所做工夫則異。”[4]朱子在“惺惺”的基礎上,更強調“動而中理”,以實現現實中合理化的理想。
明代朱子學繼承者薛敬軒說:“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9],生動地展示了朱子學者對“惺惺”禪法向現實合理化轉化的意向。其實,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使佛教面對現實、構建現實的過程。儒佛的爭論,本質上是方法論的爭論。所以,當我們談論佛教中國化或者理學家“以禪證儒”時,或許不應當過度糾結其中的概念和思想究竟屬于哪一家哪一派。正如宋釋紹曇在《瑞巖喚醒主人公》的偈頌中所唱“瑞巖喚醒主人公,把手經行禁綱中”,其中“把手”是拉起手的意思,經行是指動中修定慧,“禁綱”指的是世俗中的綱常倫理。喚醒內在的主人公,拉起他的手,一起在現實中建構完善的現實世界。這應當是中國佛學與儒學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