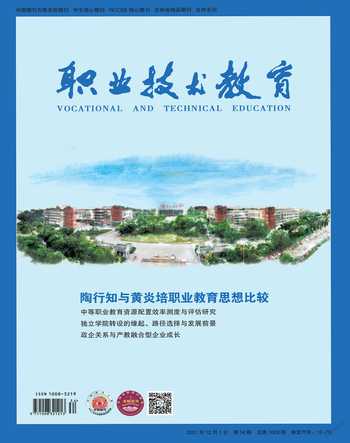政企關系與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
曹靖 魏曉紅 臺鄭哲
摘 要 政企關系是政府干預微觀經濟行為的重要手段,也是決定企業行為和績效的重要因素。政企關系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有四種“理想化”狀況:政府奠定基礎,強化企業“既想又能”;政府革新制度,扭轉企業“只想不能”;政府組合激勵,改善企業“不能不想”;政府規約引導,校正企業“雖能不想”。政企關系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亦有四種“情境化”表現:自由裁量約束,企業淪落被控境地;政治關聯偏頗,企業謀求短期利好;制度環境缺憾,企業要素變革停滯;地方政績誘導,企業俘虜公共利益。政企關系未來的走向與趨勢是“協作共進”。政企雙方可以通過強化制度執行,推動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通過預防制度衰退,促進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通過協助制度轉型,護衛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
關鍵詞 政企關系;產教融合型企業;企業成長;制度環境
中圖分類號 G71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1)34-0052-08
政府是企業價值創造的必然參與者,企業是政府借以實現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之一[1]。政企關系是政府干預微觀經濟行為的重要手段[2],也是決定企業行為和績效的重要因素[3]。由政企關系衍生出的制度環境對于企業在“能力建設”與“政治關聯”兩種成長策略選擇的影響深遠[4]。特別是在正式制度不夠完善的環境中,以政治關聯、聲譽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對中國企業生存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5],得到了相關研究的廣泛證實。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孕育、生成和成長受我國產業形態、經濟轉型和職業教育發展水平的影響,而經濟轉型過程是重構政府和企業之間關系的過程,亦是制度環境對產教融合型企業“制度支持多樣性、制度執行率不一致性和政治關系的多重性”[6]交錯影響的真實寫照。本文借用“積極差別制度環境”的視域,將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過程中出現的“理想化”狀況與“情境化”表現之間的“不對稱”看作是政企關系失調,對產教融合型企業通過應對政企關系失調來推進組織成長的過程進行觀照,并借此探討產教融合型企業何以在積極差別制度環境中發揮能動性,實現可持續成長。
一、政企關系與制度環境: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的搭建
政企關系是政府通過一些政策(如補貼、規制、稅收)與轄區企業在博弈過程中形成的某種互動模式。它強調地方政府對某個行業或某一類企業采取的政策或行為模式[7]。目前,關于政企關系的類型有兩種觀點:一是三類型說,包括權威關系型、關系依存型和規則依存型[8];二是四類型說,包括政企合作、政企分治、政企傷害及政企合謀[9]。政企關系亦有政治家與企業主、國營資本與民營資本、體制環境與企業關系三個層次[10]。在政企關系中,企業的逐利本質要求企業獲取其賞識并為之帶來價值報酬的政府資源獲益;而政府的行為亦具有二重性,即“政府的公共利益性與自身利益性”[11],如“留資于企”是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秘方,政府的價值追求同樣在客觀上加強了其對企業的依賴程度[12]。因此,“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認為,政企關系應該是相對的、多維度的、動態演化的[13]。“制度”是涉及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行為規則,且被用于支配特定的相互關系和行為模式。在政企關系中,制度既約束著雙方行動的可能性邊界,成為雙方互動的規則;也會充當資源,成為雙方互動的內容[14]。“制度環境”是指一系列制度建設、實施和運行的場域與空間,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集合體[15]。制度環境由管制、規范和認知三個維度構成,三個維度的“同構性”調和成了特定的場域[16],場域的同構力是影響著產教融合型企業的“使命運動”及“韌性成長”。
從政府層面研判,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建設培育理應成為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的重要承載體。產教融合型企業從孕育之初起,其生產要素中如“資本”要素褪去“功利性”色調,向企業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技術支持、信息咨詢等領域流入;其“土地”要素出現變革,喚醒“塵封已久”的企業教育功能;其“勞動力”要素協調企業人力資源需求側供給,既為職業教育活動提供市場需求預測、專業建設指導、學生實訓基地等支撐條件,也使企業的優質資源得到有效利用,“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產教融合特色能夠顯現。在政府與產教融合型企業互動的過程中,政府客觀上都處于主導位置:不論是政府強制性的制度安排還是誘導性的行為,均會對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政企關系的變遷主要受到政府追求主導目標實現的內在動力驅動以及主體嵌入之中的結構環境約束”[17]。因此,理解政企關系如何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邏輯可以從政府為實現自身的主導目標和適應結構環境而制定、執行的各項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來加以探究。
從企業視角來看,“產教融合型企業”的研究應重視政府行為的異質性,我國現有供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制度環境質量并不高,“產教融合制度設計不協同、行業組織作用發揮不充分、校企合作利益機制不健全、國企辦學存在諸多問題與障礙”[18]。同時,產教融合型企業也有可能使政府難以實現其原本的政策目標。產教融合型企業在生成之時即以“企業家才能”為驅動“牽引著”其他傳統的企業生產要素變革,而制度環境對于企業家才能影響的機制主要來自“法制水平、金融發展、政府管制及腐敗”[19]。因此,“企業家才能”是制度環境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生成、并“想不想”“能不能”持續成長的微觀作用機制。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內生于其所處的制度環境,是在既定制度環境下的理性選擇。“制度條件能夠改變企業家從事某一行業的收益,從而影響企業家的決策偏好”[20]。不同制度環境下所誘導的“企業家才能”配置的結果可能最終體現為差異化的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軌跡。
二、政企關系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理想化”狀況
產教融合型企業處在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其從孕育、生成到成長的過程要受到政策法規、產業形態、行業需求、社會期許、企業自身發展愿景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政企關系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有以下四種“理想化”的狀況。
(一)政府奠定基礎,強化企業“既想又能”
《中國制造2025》要求:“堅持把結構調整作為建設制造強國的關鍵環節,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201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指出,深化產教融合,對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培養經濟發展新動能具有重要意義。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即是實現產業升級,通過企業技術革新重點發展高端制造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產業升級“需要國家確立旨在引導企業提升產品質量的產業意識形態,制定并及時推出促進產業升級的新型企業治理模式”[21],保證企業在當前經濟運行模式之下擁有自主發展積極性的同時,對市場規則進行調整,引導企業以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行動來優化生產工藝質量、提升員工技術技能水準、完善管理成效進而獲取利潤。
產教融合型企業應是主動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優質企業。從《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規定的建設培育條件來看,成為產教融合型企業需要滿足“在中國境內注冊成立的企業”“具備6項條件之一”“智能制造、高端裝備等急需產業領域企業”“緊密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技術技能人才需求旺盛,主動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發展潛力大,履行社會責任貢獻突出的企業”等條件。特別是“智能制造、高端裝備等急需產業領域企業”的要求,反映出當前對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建設培育聚焦在先進制造業,要有“實業”作為依托。企業被認定為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核心指標是衡量其在職業教育活動中的出資狀況,包括貨幣性資產投入總額與非貨幣性資產投入總額等。產教融合型企業在生成之后,可依據企業生產要素變革劃分為教育服務型、獨立辦學型、培訓就業型這三種“絕對化”類型以引導其持續成長。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政策利好的驅動之下,被激發出與職業教育發展相適宜的辦學、從教、育人動機,形成與生產對接的培訓,開發與產業吻合的專業,找尋與產業共進的愿景。
(二)政府革新制度,扭轉企業“只想不能”
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出現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新產業形態下的職業教育發展需要在對企業的市場行為有所規約的社會及經濟環境中才能得以實現,而企業應有的角色則是“在保證自主發展積極性的前提下,使之從純粹逐利的市場主體轉變為多方力量制衡下的社會福利締造者”[22]。
政府應革新相關制度設計,扭轉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的“只想不能”。一是借用政策工具驅動。一方面,引導傳統商業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或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進入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建設培育目錄,推動入庫企業積極參與到產教融合之中;另一方面,政策工具的使用會吸引更多來自行業、產業界的協助及發展創新的可能,使產教融合型企業的相關現行政策推動呈現出更為全面的效果,助力其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社會福利締造者”角色的塑造。二是優化企業財務選項。政府出資設立產教融合型企業基金以優化其財務選項、專門支持其發展。該基金的運營特點為:一方面,關注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差異化發展。在其孕育之初最需要的動力費用可能以基礎設施投建為主,而在產教融合型企業生成之后,為使其經費支持更具針對性,需要根據產教融合型企業的不同類型、發展階段、所處環境等提供“個性化”的財務資助方案;另一方面,對產教融合型企業的財務資助采取階段性支持,以引導產教融合型企業自孕育到成長過程中逐漸轉向獨立運營的途徑,減少對政府資助的依賴。三是設立專責管理部門。政府設立部、會層面的溝通協調平臺或專責的管理部門,促進相關政策工具、財務選項的組合、選擇及推行,便于對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實施較為合理的“賦能”舉措。
(三)政府組合激勵,改善企業“不能不想”
《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明確提出:厚植企業承擔職業教育責任的社會環境,推動職業院校和行業企業形成命運共同體。國家產業政策與產教融合型企業價值主張之間的契合程度由企業在產教融合過程中通過各項活動所形成的整體風險承擔能力所表征:產教融合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活動也懼怕經濟成本受損以及外部環境缺失,如企業決策風險、設施設備受損、核心技術泄露、人才流失、頂崗實習學生人身安全、政府優惠政策執行不到位等。因而,有部分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會因長期收益無法保障而“不能也不想”再參與職業教育活動。
政府采取針對性措施增強產教融合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活動的熱情,或引導不同類型企業以不同形態參與職業教育活動,推進產教融合的發生、促成校企合作形成;又或是鞭策校企加強融入、融通、融合等途徑,防范和化解產教融合型企業在參與或舉辦職業教育時所面臨的風險。政府的組合激勵涉及:第一,稅收減免。為產教融合型企業“量身打造”多樣化的稅收減免政策。除《辦法》中已提及的抵免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還可以對產教融合型企業用于職業學校投資和捐贈支出予以稅前扣除等,激發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如完善落實原有稅收優惠并出臺更具前瞻性的、可操作性的具體稅種優惠政策;在國家稅務部門網站設立“產教融合型企業稅收優惠”專欄并及時更新;稅務部門主動與產教融合型企業納稅人員溝通,幫助其了解、掌握、運用相關稅收優惠等。第二,經費投入。經費投入是企業舉辦和參與職業教育的保障。如企業接納學生實習實訓,政府可以通過生均撥款的方式,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進行補貼;政府加大對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專項經費投入,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應設立相應的經費項目支持,且專項經費以吻合人才培養質量和教育服務質量的原則劃撥。第三,行政保護。落實政府通過“購買”的形式支持產教融合型企業所提供的高質量職業教育服務,費用由中央財政和地方政府按比例支付。加大產教融合型企業在科研、人才引進、征地、舉辦學校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按產教融合型企業的經營規模確定其應承擔的職業教育“工作量”,并折算為等值金額繳入企業所屬行業的“職業教育發展基金”中,用于行業內的職業教育補貼。此外,以法律文本的形式確定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權力、責任及義務,從根本上襄助企業參與產教融合的意愿和能力。
(四)政府規約引導,校正企業“雖能不想”
企業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機制”,完全經濟理性的假設決定了企業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發展目標,即其經濟動機;企業通過承擔社會責任進一步提升企業形象、履行企業義務、實現社會價值,即其道德動機。企業進入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培育目錄之后,對參與職業教育、介入產教融合的“雖能不想”,即是其經濟動機和道德動機的“沖突”。
通過政府的規約引導,可以校正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雖能不想”的行為。一是保持相關政策的連續及穩定。扶持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培育的良好政策,也是有效配置企業家資源的重要舉措,有助于將企業家才能的發揮引導到幫扶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上來。同時,政府要保障相關政策的相對穩定,以避免政策波動轉變為企業家才能發揮的“桎梏”。二是夯實企業發展預期,提振企業家信心。明確產教融合政策倡導產業形態、經濟運行模式及職業教育發展三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產教融合型企業的企業家對未來以高端制造業為核心的產業形態選擇、協調的市場經濟運行模式的預期及對自身能力的自信,也是未來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推動力。三是運用大眾媒體引導。首先,建立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更好地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征信體系。其次,支持大眾媒體加大宣傳國家對產教融合型企業的財政補貼政策,以便拓寬企業爭取產教融合型企業財政補貼的輿論廣度。這也會加劇同類型企業間的競爭行為,使真正愿意實行產教融合的企業得到財政補貼支持,用于舉辦或從事職業教育,提高對財政補貼政策運用的效果。再次,借助社會大眾的監督作用,合理合法地使用自媒體等手段,對已生成產教融合型企業的行為進行監督,通過社會大眾監管的“去偽存真”,使真正有意愿進入產教融合企業認證目錄的企業得到支持,促進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健康成長。
三、政企關系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情境化”表現
政府行為是企業成長的重要外部環境——政府基于權力調配各類資源影響企業發展,而受傳統“熟人社會”文化的影響,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在真實情境中的體現更為微妙。政企關系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有四種“情境化”的表現。
(一)自由裁量約束,企業淪落被控境地
“自由裁量權是一種不受強制羈束的決定權力,或雖有羈束限制,但將實施的時間、方法和程度的裁量讓渡于決定者。自由裁量權可以區分為行政自由裁量權和企業自由裁量權。”[23]就政府的自由裁量權而言,“一個公共官員擁有的自由裁量權,意味著無論對他的權力有怎樣的限制,他依然具有在作為和不作為的可能系列中作出選擇的自由。”[24]在“管制”情境中,地方政府可以憑借行政權力的實施、國有銀行及金融機構的控制,并利用已設置的“條條框框”達到“左右”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目的。
企業的自由裁量權表現為企業的經營決策權與資本收益權,一般需要企業明確其“成本—收益”核算,“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成本收益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性,有近一半的企業處于虧損狀態”[25]。即便如此,仍可能會有企業選擇承受“短期傷痛”,秉持“將來會好”的信念,在短期成本虧損、長期收益無法保障的情況下仍“執著”參與職業教育活動。但是,若政府通過資源及政策分配推動企業內部控制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培育及內部控制執行必然會趨向于依賴于政府。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政府的行為對企業而言可能是“利好接踵”,也可能是“羈絆連連”。政府推行一系列高強度的管制制度,將影響“企業家才能”的配置,進而使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陷入到“被控”境遇。“企業家可能會消耗過多企業資源,卻忽視了企業自身建設,讓企業把握住了政策風險卻面臨更大的市場風險”[26]。因此,企業的自由裁量權“失真”,一味地被動接受和順應,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還將面臨如下情形:過于迎合地方政府的發展策略而漠視自身的“經濟理性”,或過于依賴政府的補助和支持而喪失獨立經營管理的能力而最終導致企業成長出現停滯不前的情況。
(二)政治關聯偏頗,企業謀求短期利好
政治關聯對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政治關聯可以為產教融合型企業帶來如政府補貼、稅收優惠、融資便利、政治身份及市場準入許可等一系列利好。特別是“身份效應”,其是產教融合型企業在與政府政治關聯中最為“外顯性”的表達,更是供其自身成長的重要資源。這些效應在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初期效果極其顯著,其根源在于政府官員與企業家都在短期內渴望對政績、業績大幅度提升的動機。
地方政府與產教融合型企業的關系在制度環境不夠優渥的情形下,可能會體現出既“疏離”又“合謀”的關系:一方面,政府與產教融合型企業,如民營企業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因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溝通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疏離狀態。如2019年教育部先期重點建設培育的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議名單中,民營企業就表現出較為“低迷”的態勢;另一方面,若缺乏第三方監督,政府與產教融合型企業都會在“經濟理性”的驅使之下利用“信息不對稱”謀求互惠而對社會公共利益置若罔聞。“與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聯系的民營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與企業績效及社會績效負相關”[27]。這表明,民營企業可能會“劍走偏鋒”,通過俘獲政府官員來獲得相關財政補貼,其政治關聯即為尋租“埋下伏筆”。因此,有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格外重視政治策略的制定與實施,如先進入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培育目錄,短期內先為自身發展獲取各類資源,同時運用政治關聯為應對所處外部環境的變化積蓄力量。
(三)制度環境缺憾,企業要素變革停滯
制度環境決定企業家是尋租還是尋利、是投資或是投機,進而作用于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路徑與成效。同時,產教融合型企業在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的參與意愿、辦學動因、行為表征等均能看到“企業家才能”引導其他企業傳統生產要素變革的“痕跡”。不完善的制度環境,如過高的企業融資成本,影響企業的融資效率,過高的企業交易成本,抑制“企業家才能”配置,不連貫的政策推行,加劇企業家參與產教融合的后顧之憂,無助于“企業家才能”的發揮。
在上述制度環境下,首先,企業投資職業教育存在資本投入短期與實際見效長期的矛盾以及資本投入顯性與實際見效隱性的矛盾,將在企業參與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過程中被“無限放大”。其次,企業獨立舉辦職業教育的相應支持機制還未完全建立,因其“身份不明”而無法得到相應政策的覆蓋,進而保障其辦學的可持續性更是“譬如朝露”。再次,企業是直接引進所需的人才和技術,還是通過產教融合,與職業院校、科研機構共同開發人才和技術,又或是在獲得勞動力方面采用“搭便車”“挖墻腳”的手段等,將成為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在經濟理性作用下能否持續成長的又一“枷鎖”。從產教融合型企業的經濟價值獲取來看,其參與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亦可被看作是一種交易過程。不良制度環境的浸染使政府無法保證產教融合型企業的人力資本專用性、投資外部性等問題,同時企業傳統認知中的“政府主導的發展策略,往往在發展初期績效卓著”[28]會更進一步強化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介入職業教育、參與產教融合的“不想不能”行為。
(四)地方政績誘導,企業俘虜公共利益
地方政府“GDP錦標賽”間的競爭誘使政府透露出“逐利”的傾向,政府對于企業和企業家同樣會產生依賴:“中國的企業家往往不是通過內部合作來追求目標的實現,而是通過與更高地位和權力的個人進行交換來追求個人目標。”[29]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建設培育能夠迎合地方政府需求,有利于地方政府政績的顯著提升。因此,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并非完全都是企業自然而然的行為選擇。
有關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制度支持與制度執行仍在完備中,企業主體多樣性特征依舊客觀存在,這意味著企業即便是進入到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建設培育目錄之中,也不一定按照既定預設的邏輯運營。在政府“支持”的誘導之下,潛在企業進入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培育目錄是一種理性行為,而政府對產教融合型企業行為監管存在不小的困難,且政府對企業在產教融合中的失范行為懲罰力度也不足,大部分企業可能會把“支持”用于與產教融合推進無關的方面。如《辦法》指出,“在申請認證、年度報告或考核過程中弄虛作假,故意提供虛假不實信息的;在資格期內發生重大環保、安全、質量事故,存在違法違規經營行為的;侵犯學生人身權利或其他合法權利的;列入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的”,僅是取消資格且5年內不得再行申報。企業較低的“犯錯成本”使得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由新制度裹挾著企業運營舊習俗“踉蹌行走”。此外,“企業越具有‘政治嵌入性’而非‘自主性’便越具有政策影響力”[30]。國有企業的“政治嵌入性”不言而喻,其因承接國家戰略產業發展任務并能從相關政策中獲益[31],而國有企業的政治行為越多,在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過程中反而會演變為其自利的“借口”或尋租的“理由”,甚至造成政府被“俘獲”的局面,從而導致公共利益的損失。
四、政企關系影響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使然路徑
政企關系未來的走向與趨勢是“協作共進”,良好的制度環境是產教融合型企業順利成長的“膏腴之壤”。政企雙方可以通過強化制度執行、預防制度衰退、協助制度轉型來引導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
(一)強化制度執行,推動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
1.明確政府角色定位
促進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需要明確政府在“新形勢”需求下——產業形態以高端制造業為主體、經濟運行對企業的市場行為有所限定、職業教育要向高水平發展的角色定位。第一,政府要做好引導者。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需要一個穩定、連續的制度環境,政府要引導資源在不同類型產教融合型企業孕育、生成及成長過程中的投入,積極應對多樣化產教融合型企業培育模式的識別和建設創新模式的支持。第二,政府要做好供應者。為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提供優質制度環境,盡可能減少對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不必要、不合理的干預。第三,政府要做好協調者。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需要多元主體的參與,完善政府與多元主體間的互動關系,進一步激發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活力。同時,政府還需協調產教融合型企業群體內部的企業個體差異性訴求。
2.通曉企業制度地位
不同類型的企業在實際生產經營活動中擁有不同的制度地位,企業的所有制特征、所從屬行業類別、所隸屬不同層級政府等因素造就了產教融合型企業所擁有“真實的”制度地位。例如,我國產業發展離不開國有企業對戰略核心產業的控制,國有企業在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培育過程中的“天然優勢”明顯;而政府對民營企業在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過程中的制度性溝通渠道仍有待進一步加強。因此,制度地位不同的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政府導向”或“市場導向”的抉擇下會表現出差異性的行為。
3.政企強化制度執行
“制度執行體現了制度環境中公平執行的一致性和持續性,有利于企業在動態復雜的環境中降低長久創新所面臨的風險預期。”[32]明確政府角色定位、通曉企業制度定位既降低了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預期,也保障了產教融合相關制度支持運行的效率。制度執行能夠提高企業對產教融合政策的信任度,降低企業渴望通過尋租獲取制度支持的動機。同時,制度執行強化了產教融合型企業運營過程中的價值主張——既觸及社會價值的創造,也強調經濟價值的獲取;保障了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價值——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破解從教“身份困境”、紓解就業“模式困難”;規約了產教融合型企業的價值獲取——源于政策優惠、來自技能培訓獲利、斬獲運營長期回饋。
(二)預防制度衰退,促進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
1.界定政府職能范圍
第一,建議地方政府采用“負面清單”制度,以便更有效地發揮政府在引導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方面的作用。對政府的權力進行合理、有效的約束,意在為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創設良性的制度環境。“負面清單制度有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有利于政府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有利于推動相關審批體制、投資體制、監管機制、社會信用體系和激勵懲戒機制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33]第二,政府在采用“負面清單”制度的同時,還應通過行政法規的制定、修訂及終止來引導自身職能的轉變,朝向“不越位”的有限政府、“不缺位”的責任政府、“不錯位”的效能政府發展,為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創造更好的政策與體制環境。第三,采用“負面清單”制度會引導政府職能方式轉換和管理邊界后移,政府應及時借用制度和法律政策的形式將職能轉變的成果加以鞏固,并推薦和引導自身職能的進一步轉變。
2.尊重企業能力意愿
地方保護與區域競爭是各級地方政府繞不開的“客觀實際”,在這種隱性制度環境下,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優惠基本都給予“有能力”的企業,并加持其發展。企業能力的大小是其應對政府制度制定和制度執行過程中能否獲取“特殊對待”或“下不為例”的重要“砝碼”,企業亦可主動把控在“扮演”產教融合型企業角色時的實際節奏。此外,企業外部勞動力市場同樣影響著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在企業實際生產過程中,“勞動力”要素的投入使用在于創造出大于自身價值的價值,因而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更偏好高技術含量的勞動力。企業獲取勞動力的過程不僅能夠分析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也能揭示出勞動力資源配置的規律。產教融合型企業是企業的經濟理性與社會理性的結合體,一般都會以實現企業成長收益最大化為其行為準則。
3.政企預防制度衰退
“制度不僅僅只是游戲規則,更是‘社會博弈所商定的規則’”[34]。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動力源于企業內在意愿和支持產教融合相關制度的吸引。但產教融合型企業在運營過程中若過于強調社會責任,企業在經濟價值鏈上的可持續性則無法保障;若以傳統商業企業的邏輯行為,又與一般的財富創造機制無異,這些都會導致其成長方向的偏離。因此,在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過程中,需要通過界定政府的職能范圍、在尊重企業客觀能力意愿的基礎上進行制度調適,預防制度衰退。首先,落實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培育“有進有出”的動態管理,使其在成長過程中規約行為質量——行為既要規范合理也要具有社會教育性。其次,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將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社會服務等社會價值創造凝練成為其發展的核心價值理念,才可以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運轉更為順暢。再次,產教融合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需要使長期社會價值創造與短期經濟價值獲取達到和諧狀態,還需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特點,在產教融合過程中主動作為,化解企業生產要素投入短期性和實踐見效長期性的“沖突”;厘清企業資本注入顯性與實際收益隱性的“關系”;緩和企業人才和技術直接引進與合作研發的“矛盾”。
(三)協助制度轉型,護衛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
1.刷新政府行政方式
政府若以強制性、單向性的行政方式向產教融合型企業投入各類社會資本,就無法跳脫片面追逐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的“老路”,不會達到產教融合總體價值最優。因此,刷新政府的行政方式要凸顯出“共贏”與“導引”的特性。一方面,實施合作式的行政方式: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方式折射出“權威型”的政企關系,易使政府與企業陷入到“對立”的狀態,以合作式為導向的行政方式,是政府與企業在不損害社會公共福利的情況下共生共贏,有利于引導和協調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另一方面,實施互動式的行政方式:摒棄“自上而下”的單向式政府行政方式,強調政府在平等互動的政企關系基礎上發揮主導作用,營造政府與產教融合型企業順暢溝通、交流的氛圍。
2.變革企業管理傳統
企業基于已有核心價值觀、管理模式及戰略定位所生成的管理傳統有所不同,決定了即便企業的制度地位與能力意愿相匹配,其在產教融合過程中也會體現出截然不同的行為選擇。企業家在研判所處外部環境后并不一定能夠迅速改變管理傳統,因為企業的管理傳統一旦形成,就會使企業的運行出現慣性并逐漸產生路徑依賴。產教融合型企業的成長過程,也是企業家要基于所獲取的資源進行合理的企業管理傳統變革,使產教融合對企業的價值訴求以新的組合、新的程度、新的方式融入到各生產要素之中。在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之時,“企業家才能”要素的變革詮釋企業家在企業各項活動中的能動性,在配置各類生產要素時將社會價值創造作為重要的組織發展戰略并予以執行。
3.政企協助制度轉型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正式制度和法律體系也會隨之不斷完善,整個社會網絡將由強關系網絡向弱關系網絡變遷。”[35]因此,制度轉型需要經歷從關系治理向規則治理邁進,并以政企良性互動作為重要基礎。在制度轉型期間,政府積極推進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正式制度改革,能夠節省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所付出的交易費用,減弱產教融合型企業政治關聯的動機,消釋政府尋租、設租的利益源頭,并使產教融合型企業成長的路徑重置于企業家在產教融合過程中的有為與不為。刷新政府行政方式、變革企業管理傳統,是協助制度轉型的關鍵,亦是建立新型政企關系的落腳點。產教融合型企業群體內部的個體間、產教融合型企業與政府間的行為互動模式應該是一種平等的合同關系,雙方基于法律規約和道德準繩承擔相應責任、履行對應義務。政府與產教融合型企業更應在制度轉型過程中建立起制度化的溝通渠道來加強互動合作。
參 考 文 獻
[1]杜媛,王竹泉.政企關系再觀察:一個理性視角[J].改革,2014(11):127-136.
[2]張龍鵬,蔣為.政企關系是否影響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產能利用率?[J].產業經濟研究,2015(6):82-90.
[3]于文超,政企關系重構如何影響企業創新[J].經濟評論,2019(1):33-45.
[4]汲昌霖,韓潔平.制度環境與企業成長——基于政治關聯抑或能力建設的策略選擇[J].江漢論壇,2017(7):11-16.
[5]ALLEN, F,? J. QIAN and M. QIA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1):57-116.
[6][32]劉小花,高行山.復雜制度環境中制度要素對企業突破式創新的影響機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20(11):117-131.
[7][9]聶輝華.從政企謀和到政企合作——一個初步的動態政企關系分析框架[J].學術月刊,2020(6):44-56.
[8]青木昌彥,等.經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M].魏加寧,等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243-244.
[10]高勇強,楊斌.從“私人關系”到“組織關系”[J].北大商業評論,2010(11):51-57.
[11]潘石,莫衍.政企關系問題的本質:政府參與二重性的外化[J].長白學刊,2005(1):70-73.
[12][14]金太軍,袁建軍.政府與企業的交換模式及其演變規律——觀察腐敗深層機制的微觀視角[J].中國社會科學,2011(1):102-118.
[13]夏小林.政企關系:有分有合——從國際視角評切割政企關系的“改革”陷阱[J].管理學刊,2015(6):1-19.
[15]宋增偉.制度環境與人性完善[J].理論探討,2019(4):50-54.
[16] Suchman M C.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3):571-610.
[17]李漢林,魏欽恭.嵌入過程中的主體與結構:對政企關系變遷的社會分析[J].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13(4):51-61.
[18]周鳳華.職業教育多元辦學格局的現狀與發展策略[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1(12):75-81.
[19]陳怡安,趙雪蘋.制度環境與企業家精神:機制、效益及政策研究[J].科研管理,2019(5):90-99.
[20]張自卿,邵傳林,裴志偉.制度環境與企業家精神:一個文獻綜述[J].商業經濟研究,2015(7):94-96.
[21][22]徐國慶.我國二元經濟政策與職業教育發展的二元困境——經濟社會學的視角[J].教育研究,2019(1):102-110.
[23]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M].王逸舟,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231.
[24]米切爾·黑堯.現代國家的政策過程[M].趙成根 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158.
[25]冉云芳.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內部收益率分析及政策啟示[J].教育研究,2017(4):55-63.
[26]楊其靜.企業成長:政治關聯還是能力建設?[J].經濟研究,2011(10):54-66.
[27]余明桂,回雅甫,潘紅波.政治聯系、尋租與地方政府財政補貼有效性[J].經濟研究,2010(3):65-77.
[28]陳瑋,耿曙.政府介入與發展階段:發展策略的新制度分析[J].政治學研究,2017(6):103-128.
[29]Choi, E. KYONG & KATE ZHOU. Entrepreneurs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rent-seeking[J].The China Review, 2001(1):154-173.
[30]黃冬婭.企業家如何影響地方政策過程——基于國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類型建構[J].社會學研究,2013(5):172-196.
[31]PEARSON M. State-Owned business and Party-State regulation in China’s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C]//.In NAUGHTON B. and TSAI K.S.,eds. State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Chinese Mirac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10-22.
[33]新華社.非禁即入!我國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EB/OL].(2018-12-25)[2021-05-11].http://www.gov.cn/xinwen/2018-12/25/content_5351924.htm.
[34]劉守英,汪廣龍.中國奇跡的政治經濟邏輯[J].學術月刊,2021(1):48-62.
[35]PENG, M. & ZHOU, J. How network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evolve in Asia[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22):321-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