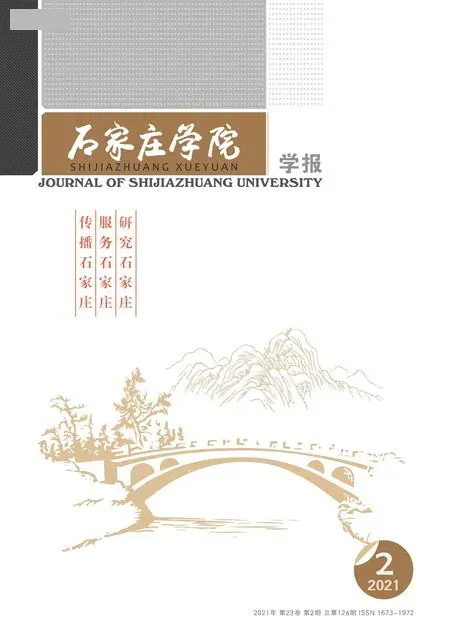土地、夢與鄉村的兩種景觀
——論《陌上》的鄉土書寫
李保森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430072)
《陌上》是作家付秀瑩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講述了華北平原上一個叫做“芳村”的村莊故事。在此之前,“芳村”曾多次出現在付秀瑩的作品中①如《愛情到處流傳》(《紅豆》2009年第10期)、《舊院》(《十月》2010年第1期)、《六月半》(《人民文學》2010年第12期)、《錦繡年代》(《天涯》2011年第1期)、《秋風引》(《江南》2012年第1期)、《笑忘書》(《十月》2012年第2期)、《有時歲月徒有虛名》(《光明日報》2012年2月10日)、《小年過》(《芳草》2013年第5期)、《找小瑞》(《芳草》2015年第6期)等。其中,《小年過》正是《陌上》的第一章《翠臺打了個寒噤》,《找小瑞》則是《陌上》的第二十四章。。這些文本足夠使“芳村”成為付秀瑩的個人標識,正如歇馬山莊之于孫惠芬、東壩之于魯敏、罕村之于尹學蕓。
在以往的“芳村”中,付秀瑩主要表現出兩種情感傾向:一是對往事的深情懷舊,一是對現實冷峻而不失溫暖的注目。在《陌上》中,付秀瑩用后一種筆墨對當下的中國鄉村現實進行觀照和呈現,尤其是鄉村的精神狀況。若按照當代文學中形成的“村莊里的中國”②這有大量的文本作為支撐,如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賈平凹的《秦腔》、孫惠芬的《上塘書》、劉慶邦的《我們的村莊》、梁鴻的《中國在梁莊》等。這一文化邏輯,“我們講述中國鄉村的故事就是在講述中國的故事,只有中國鄉村故事才是最為深刻豐富的‘中國故事’”[1],可以說,付秀瑩的《陌上》對認識當下的中國有著重要的作用,這也恰恰是作者本人的寫作寄寓:“芳村那些人,那些男男女女的隱秘心事,也是鄉土中國在大時代里的隱秘心事。”[2]提及學者王宇對新世紀女性作家鄉土敘事的學理觀察和發現:“新世紀女性鄉土敘事一方面將性別意識帶入一向由男性主導的鄉土敘事領域,呈現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鄉土經驗,提示鄉土經驗的復數形態;另一方面,它又將鄉土經驗帶入女性文學中,提示女性經驗的復數形態,從而構成與20世紀鄉土文學傳統和女性文學傳統的雙向對話”[3],則可以發現《陌上》在女性鄉土敘事潮流中的積極意義。此外,從作家代際之間的創作差異出發,批評家孟繁華有過如此表述:“當下文學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不僅僅是空間或區域、場景和人物的變化,它更是一種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大變化。而對這一變化的表達或處理是由‘60后’、‘70后’作家實現的。‘50后’作家還會用創作證明自己的價值,但是,當他們的創作不再與當下現實和精神狀況建立關系時,終結他們構建的隱性意識形態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4],而付秀瑩正是“70后”作家中的一員。這幾個理論坐標和因素,使《陌上》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
那么,《陌上》究竟描摹了怎樣的鄉村現實,“芳村”的精神狀況是什么樣的,作者的女性經驗和視角如何參與和影響了對“芳村”的塑型,《陌上》又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書寫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的重任呢?
一、文學意象“陌上”與“有意味的形式”
以“陌上”為這部小說命名,可能是付秀瑩有意征用這個語詞背后的文化資源,凸顯鄉村的田園特性,召喚久遠的鄉村記憶,表達懷舊、感傷的情感。
“陌上”①在古代社會,南北走向的田間小路被稱為“阡”,東西走向的田間小路則被稱作“陌”。指的是田間,是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一個意象。在早期,“陌上”主要作為空間載體在詩歌中出現,先后有漢樂府的《陌上桑》,曹氏父子、李白等人的同名詩作。及至吳越王錢镠在給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表達他對歸寧的夫人的思念,寓情于景、言辭懇切、情感充沛,“這里有對美的贊嘆,還有在急景流年中心靈敏感的悸動,面對良辰美景、如美花眷而發自內心的憐愛”[5]。這句話受到了人們的稱許,在后世廣泛流傳,成為一段被人艷羨的愛情佳話、一個被多面解釋和借用的歷史典故,其中的“陌上花”也對“陌上”進行了擴展,開始成為一個文學意象、一個詞牌。
宋代大文豪蘇軾路過吳地,聽到了當地民歌《陌上花》,據此創作了三首題為《陌上花》的絕句,以俗入詩、化俗為雅,提升了“陌上花”的文學品質。蘇軾的學生晁補之作八首《陌上花》,也是圍繞這個故事展開,反復鋪陳和渲染了王妃既思君又戀鄉的矛盾心情。
在宋人王庭珪、謝翱,金代趙秉文,元代方回等人的創作中,他們有意借花詠史,給“陌上花”賦予了新的意義,增添了懷舊感傷的情感指向。在《題羅疇老家明妃辭漢圖》中,王珪庭取材于漢代明妃王昭君出塞的歷史故事,借助“陌上花”,以樂景寫哀情,在情感基調上已與前述有著顯著不同。元代的張翥的《陌上花·有懷》中雖未出現“陌上”一詞,但以內容和情感上的懷舊演繹了“陌上花”詞牌的文化風格和情感脈絡。明代的唐文鳳、石珝等也在詩詞中借助“陌上花”表達情感上的哀傷。
時至今日,“陌上花”依舊活躍在大眾文化的視野里。2012年,胡星導演的微電影《陌上花開》上映,該片講述了1930年代苗族兒女一段凄美感人的情感故事;2017年,由張艾嘉導演的電影《相愛相親》上映,電影主題曲是《陌上花開》②這首歌由林珺帆作詞、黃韻玲作曲、譚維維演唱。。歌曲以女性視角講述了在期待中等待、在等待中徘徊的愛情心路,情緒低緩,傳達出一種又無奈又達觀的矛盾心情。
通過上述簡單的梳理發現,經由歷代文人和藝術作品的渲染,“陌上”從一個指示地理空間的名詞,借助“陌上花”的意義,增值而伸展為一個有著特定文化意味和情感指向的文學意象,使“陌上”在指向清新明麗的田園風格之外又添了一層對歲月逝去的感傷氣息。聯系當下鄉村的實況,《陌上》對“陌上”的借用是適宜的。
付秀瑩的《陌上》可謂是文學意象“陌上”開出的新花。但僅僅從符號的借鑒和象征來對《陌上》的淵源有自作出說明,顯然是不夠的。對于這朵新花是如何綻放的、又是怎么樣的考察,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味。這首先要從《陌上》的呈現方式談起。
在結構安排和敘事策略上,《陌上》采用了“互見法”這一中國古典小說敘事傳統。這一敘事方法是司馬遷在《史記》中的創造性運用,又被稱作“旁見側出法”,指在一個人物傳記中著重表現該人物的主要特征,而他的其他特征則在其他人的傳記中顯示。這種敘事策略便于寫作者選擇、安排材料,突出重點,塑造人物形象,接近于典型化手段。靳德俊對此總結為:“一事所系數人,一人有關數事,若為詳載,則繁復不堪,詳此略彼,詳彼略此,則互文相足尚焉。”[6]14面對龐雜的寫作內容,這種處理方式具有化繁為簡、眉清目晰的作用。《陌上》也是以人物作為小說的組織方式,每一章節都以一個特定人物為中心,著重講述該人物的日常生活、大事小情和周邊交往,以具象化的方式展示該人物的性格性情和鄉村生活狀況。《陌上》的各章節獨立成篇,取消了時間在小說敘述中的隱性線索功能,前后沒有因果邏輯關聯,章節的順序可以調整,數量上可以進行加減增刪,這時的小說文本呈現為開放狀態。但它們彼此又有交叉、重合的部分,使小說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并將“芳村”落實為最終的主人公,成為書寫的主要對象。而這也是新世紀以來鄉土書寫的常見寫法,即“寫的不再是一個或幾個人物,而是寫了一個村莊、一個文化群落、一種生存狀態”[7]。
這一結構方式,使這部長篇小說中的內容呈現方式具有段落化、碎片化的特點。這并非是對寫作對象的有意割裂和強行處理,而是與寫作對象的契合。按照“有意味的形式”這一觀點來看,這種形式恰恰反映和說明了當下鄉村的時代特征。在整個社會去政治化的語境中,鄉村同樣也在經歷個人化、私密化、日常化的轉變過程。今日的鄉村和民眾已然難以如某個歷史時期那樣,可以輕易地實現大規模的動員和組織。他們在自然時間的流淌中經歷著生活的紛繁復雜,體驗著生命的悲歡離合。就這點而言,《陌上》找到了進入當下“鄉村”的恰當方式,“不理解新的觀察形式,也就無法正確理解借助這一形式在生活中所初次看到和發現的東西。如果能正確地理解藝術形式,那它不該是為已經找到的現成內容作包裝,而是應能幫助人們首次發現和看到特定的內容”[8]58。
當然,這一敘事方法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不能像線性敘事那樣呈現一個頭尾完整、線索明晰的故事,完成主題建構和意圖傳達,甚至還可能因為寫作者的馬虎和大意造成前后不一、互相矛盾的現象①如《陌上》第25頁提到翠臺的女兒二妞時說“有什么要緊的工作,非要熬到年根兒底下呢?”而在第57頁卻又寫到“二妞年紀還小,又念著書”;第140頁中提及和瓶子媳婦好上的鄉政府秘書是劉銀栓,而在第355頁中,卻被寫作耿秘書;第204頁中,臭菊的兒子小見,而在第223頁中,寫成了海亮;等等。,這就要求寫作者務必做到總覽全局、瞻前顧后。
在話語方式上,抒情話語在小說中顯然占據主導性位置,“抒情話語是一種表現性話語。它具有象征性表現情感的功能,通過類似音樂的聲音組織和富有意蘊的畫面組織來體現難以言傳的主觀感受過程”[9]286,使得這部小說具有濃厚的散文化風格。小說的散文化,是中國現代小說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重要審美創造②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廢名的《竹林的故事》、沈從文的《邊城》、蕭紅的《呼蘭河傳》、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陳小手》、林斤瀾的《矮板凳風情》、張潔的《從森林里來的孩子》、賈平凹的《商州初錄》等。。這種藝術風格弱化了小說的情節成分,少有戲劇性沖突,營造了自然、和諧的敘事氛圍,保證了敘述人的自由跳躍。在《陌上》中,作者以嫻熟的筆墨進行了大量的景色描寫,月亮、星星、花草樹木果蔬、莊稼等自然意象也即傳統鄉村意象更是高頻率地出現。這些描寫不僅創設了鄉村特有的靜謐、安寧的氛圍即小說的氛圍,展示了鄉村本該有的濃厚詩意,也稀釋了小說中的情節敘述,實現了動靜結合、以靜制動的美學效果,使抒情成為小說的主導性風格。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在每一章前,作者有意放置了流露個人情緒、傳達個人所思的小詩,雖只有幾行,但與正文恰可構成互文關系。
此外,小說在對鄉村小食、人物衣飾等若干細節上灑下的濃墨,尤其可見作者的藝術技巧和良苦用心。對這些鄉村生活細節的鋪排和渲染,顯示著女性作者在深入生活內部肌理時特有的敏感、細膩。
二、土地與鄉村的自然社會景觀
土地是鄉村的物質性根基,是民眾賴以生存的主要資源,更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重要文化符碼,“即使在中國人的較為單純的感知中,它(引者注:指大地)往往也同時是空間化的時間,物態化的歷史,凝結為巨大板塊的‘文化’,甚至儼若可供觸摸的民族肌體;文學藝術更普遍地以之為對象化了的人類自我”[10]4。
進入現代社會以后,鄉村原先那種相對靜止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屢次被卷入時代的主潮之中,土地的面目開始不斷地遭到改寫,這與其在鄉村生活中的支配性力量有關,“在很大程度上,土地是鄉村生活和社會關系環繞的軸心”[11]。曾幾何時,擁有土地是一代代農民的夢想,構成了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動力和目標。梁斌的《紅旗譜》講述了幾個家族之間為爭奪土地而展開殊死搏斗的故事。地主階級和貧農階級之間的斗爭,預示了鄉村革命之火的燃燒和蔓延。在1950年代前后的土改小說中,如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人們為了獲得土地展開了艱難的反抗和斗爭,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最終獲取了勝利,開啟了新的歷史紀元;在合作化小說中,如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李準的《李雙雙小傳》等,互助組、生產隊等組織相繼出現,人們在新的生產關系中熱火朝天地勞作著,展現出繁忙的景象,顯示出此時鄉村的蓬勃生機。當然,這種生機也埋伏著危機,但此中人們的真誠至少不應該被嘲笑;在新時期小說中,如何士光的《種谷的老人》、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等,深情謳歌了民眾對土地的熱愛、對勞作的投入。但是,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新世紀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決意離開土地,紛紛進城打工,造成了土地的荒蕪和村莊的空心化。
還有一些村莊雖然并沒有空心化,但已經不是留存在許多人記憶中的村莊形態,也不再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那個樣子,而是生出了新的時代景觀——“景觀是一個由人創造或改造的空間的綜合體,是人類存在的基礎和背景。……在‘景觀’一詞的現代用法中,景觀不僅強調了我們的存在和個性,還揭示了我們的歷史”[12]18。這些景觀在推動鄉村的現代性進程時,也使鄉村的面目日漸模糊。
《陌上》在對芳村的環境進行介紹時寫道:“村北這一帶,如今是芳村的開發區。皮革加工廠,皮具廠,養雞場,養豬場,有大的,有小的,大大小小,都在這一片。早先其實都是田地。如今,田地都變成了一片片廠房。”[13]72這其中正“揭示了我們的歷史”。
從田地到廠房的變遷,是鄉村遭遇城市化、工業化大潮的結果,導致了農民置身其中的環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是土地使用方式的變化,同時還引發了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情感傾向等多個方面的變化。這也意味著,原來體現人和自然緊密關聯的媒介之物——土地,開始在新的層面體現它的價值,并由此伸展出新的社會關系。土地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在這里完成了接替,并開始“制造”新的鄉村社會景觀。
由于這種變化,鄉村民眾的生活內容和方式也隨之相應地調整:從之前的整日在農田辛勤勞作變為如今的按時上下班,越來越像職業工人。眾所周知,“傳統農業社會,土地是農民生產、生活的核心,土地的不可移動性,使農戶不僅常年系于土地,而且農戶以農業生產為核心的生產活動不出耕地所在范圍”[14]150。當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工廠后,就擺脫了土地對他們身心的束縛,他們開始走向開放、自由的生活。香羅在城里從事色情行業,素臺可以去石家莊做美容,改田開車帶勇子去城里玩,小瑞跑到了東北……鄉村的內部封閉狀況已然向外部敞開,并“占領”城市。當然,這只是攫取了財富的一小部分人,更多的人則在工廠里辛勤地工作,但這已經和以前的生活有了明顯的不同。
農民的收入不再從田地中獲得,而主要通過進廠打工賺取。在這一語境中,賺錢、致富成為人們關心的主要事務,也因此引發了他們的苦惱和憂慮。原來鄉村中基于血緣、婚姻、宗族、鄰里等關系形成的脈脈溫情,漸漸受到侵蝕。翠臺為嫁娶時女方臨時要的汽車而苦惱;大全把鄉里鄉親僅僅視作打工的,嚴格管理;團聚辦廠,卻被自己的弟弟和小姨子給“坑”了,以至于連工人的工資都快發不出了,而弟弟卻買樓買車;由于發不出工資,原來求著進廠的根蓮,找上門來向團聚索要工資,惹得兩方都煩;喜針為過節花錢犯愁,不得不貼錢給兒媳婦回娘家,兒子還嫌給得少;鳳奶奶指責開超市的秋保兩口子壞了良心;狗娃責問耀宗藥物報銷情況;父親對耀宗收費因人而異有所不滿;由于廠里沒活,軍旗在家歇著,卻受到了媳婦臭菊的指責,臭菊由于少了每天一二百的進項而顯得不安;建信的村主任職位是和大全互相勾結獲得的,顯示政治與資本在鄉村的權威性以及兩者的互相倚重。在任期間,建信蓋起了三層小樓,又在縣城買了小區房;在新一輪兩委選舉時,擴軍公開在村子里免費發放物品,意在求得選票,獲得村長一職……以上種種,都可見鄉村的物化程度。
由于辦了皮革廠,村子里的水被污染了,人們不敢喝水,只好買水喝。有的人舍不得買,結果吃出了毛病;空氣也因此遭到了破壞,一些人都不敢進村,因為進村就會出現胸悶、喘不過氣等癥狀;在廠里工作的人,胳膊上出現了一些斑斑點點。“芳村”(鄉村)的環境狀況由此可見一斑。
趙本夫在《無土時代》中,以體現鄉土中國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土”的消失為隱喻,象征了現代城市高速發展的文明病態,表現了人們對回歸自然的渴望。如今,這種文明病又蔓延至鄉村。小說中的“芳村”,人們的新房子蓋得都很氣派,出門就是水泥地,有的還鋪上了瓷磚或大理石,以至于想要找一小塊泥土地都很難。許多人把樹都砍了,新房子干巴巴的,鄉村也因此變得干巴巴的。
談論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實質是在談論鄉村和自然的關系。農民雖然并不應該天然地固守于土地之上,但鄉村失去了和自然的聯結,沒有了往日兩者的和諧相處,少了自然的庇護,人和自然將會兩敗俱傷。由上述可以看到,土地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的交替并未如人所愿那般帶來美好。對自然性的漠視乃至否定,終于帶來了代價,那就是威脅到人們的健康和生存,而這正是如今鄉村的現實:“自然性和社會性,這兩重性身份迥異甚至有時相互矛盾,卻相互作用產生了景觀——那些被某個持久存在的人類群體改變的環境。”[12]22
農事曾經是鄉村生活的重要內容,莊稼是民眾極為看重的財富,但由于時代主題的變更和耕作效益的減弱,如前所述,土地的使用方式已經不同往日,而莊稼也相應地由有“用”之物變為可“看”之物。在《陌上》中,敘事者多次寫到了莊稼,且非常用心、細致地進行了描繪,如:
麥子們已經秀了穗,正是灌漿的時候。風吹過來,麥田里綠浪翻滾,一忽是深綠,一忽是淺綠,一忽呢,竟是有深也有淺,復雜了。有黃的白的蝶子,隨著麥浪起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殷勤地飛。偶爾有一兩只落在淡粉的花姑娘上,留連半晌不去。不知什么地方,傳來鷓鴣的叫聲,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13]36
麥子已經收完了。麥茬里面,玉米苗子早躥起來,有一尺高了。細細長長的葉子,在風里招展著。偶爾,有青綠的螞蚱蹦起來,從這個棵子繃到那個棵子,又蹦到另一個棵子。一塊云彩悠悠飛過來,轉眼間卻又飛走了。玉米這東西,長得瘋,要不了幾天,莊稼地就深起來了吧。[13]122
芳村這地方,管玉米地叫大莊稼地。大莊稼嘛,就是高大的意思。大莊稼們已經吐纓子了,深紅的纓子絲絲縷縷垂下來。過了大莊稼地,有一小塊棉田,大大小小的棉花桃子,綠鈴鐺一樣,風一吹,好像滿田就格朗格朗響起來了。天藍藍的,有一塊云彩停在遠處的一棵大樹尖子上。[13]210
在這些描寫中,熱鬧、繁忙、緊張的勞作場景被一語帶過,土地上的若干景象構成了一幅幅清新、自然、可供欣賞的圖畫。麥子、玉米、莊稼地等意象,無疑是對這幅田園景象的生動點綴。這種有意的略寫或者說用心的寫實,大大弱化了人和土地的聯系,恢復了土地的自然性面貌,以描述風景的方式傳達了構成鄉村基礎性、關鍵性存在之物的時代之變。從文學角度而言,這些描寫不可謂不生動、不細致。但這里的觀察主體顯然不是整日與土地、勞作為伴的農民,欣賞的姿態意外地暴露了視覺主體的外來者身份和悠閑從容的心境。
不獨莊稼被風景化,小說中還用了大量的筆墨描寫了芳村的夜晚、月亮、星光、風和云,還寫到了花香、蟬聲,語言優美、氛圍和諧。但在這些場景中,人和自然是分離的,芳村中的人并沒有在這些屬于芳村的景觀中投射自我,建立起人與自然的有機聯系。在此,自然僅僅充當了小說的背景,正如巴赫金所言:“這些片斷的美景,只可能一幅幅單獨地嵌進形諸語言的封閉的景致里去。”[15]338
在《陌上》中,我們幾乎沒有看到關于民眾侍弄莊稼、繁忙勞作的情節描寫。此種闕如,自然不能意味著鄉村的消逝,但顯然這個鄉村已經不再是人們熟悉的那個鄉村。這當然不是《陌上》對鄉村的歪曲或簡化,而是鄉村自身在時代洪流中的移步換景,決定了《陌上》只能作出如此這般的處理。這一時代的鄉村似乎只是一個空間性的標識,而其內里正在進行著大規模的改寫與置換。人對土地的依附關系正在被新的社會關系所替代。就此而言,這種風景化的處理方式更像是一種諷刺!
我們從土地使用方式的變化到人們日常生活內容的調整可以看到,鄉村的重心正在進行著由生產、勞動轉向生活、消費的歷史性轉變。對此,有學者提出了“后生產主義鄉村”概念,認為:“后生產主義鄉村的發展過程中,城鄉要素從單向流出向雙向流動演變,鄉村要素組成發生變化,進而鄉村功能不斷改變,并由此帶來多元價值空間的重構。”[16]很顯然,“芳村”里的種種跡象都是對這一概念的現實演繹。
綜上,《陌上》通過對土地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彼此交替的歷史過程、互相矛盾的現實狀況展開的敘述,尤其是對鄉村民眾生活狀況的敘述以及對鄉村事物的風景化處理,完成了對當下中國鄉村的塑型,描摹了普通民眾的生活圖景。
三、夢與鄉村的精神景觀
由于土地的空間變化,鄉村處于被重構的狀態,傳統中人與土地的關系遭遇了改寫,農民的身份和社會角色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由此生成了新的鄉村現實,“制造”了新的鄉村精神景觀。在呈現精神景觀時,作者有意借助“夢”這一連接真實經驗和心理反饋的媒介。在付秀瑩此前此后的小說創作中,“夢”敘述就多次出現。可以說,這已經構成了她的常用寫法和藝術特色,并有力地體現出女性在感知鄉村時的細膩、敏感。
(一)夢、日常生活與文學
盡管夢是無意識形成的,但在文學作品中,說它們是人造的夢更為合適。畢竟,作品是由作家創作而成的。文學作品中的這些夢,是作者有意附著于作品人物的文字景觀,是體現人物性格特征和精神狀況的一種方式,承載著作者的特定表達意圖。人們常說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表明了個體日常生活與夢之間的隱秘關聯:當個體陷于日常的繁瑣事務之中時,無法冷靜地沉思、追問這些事務,只能作出機械的應對。靜謐的夜晚提供了思考的契機,而夢中的場景把其中深刻的部分抽取出來并予以單獨呈現。文學作品中的“夢”更是以強行的方式,巧妙地對作品中人物的心理作出描摹。因此,文學作品中的這些夢未必就是多余的閑筆,而是值得關注與分析的細節,是對現實的另一種表達。
從精神分析學的觀點來看,夢是個體排解精神壓抑的一種方式,“夢是某種愿望幻想式的滿足,它是通過幻覺式的滿足來排除干擾睡眠的心里刺激的一種經歷”[17]115。國內學者趙毅衡在論述夢時也提到,“夢是媒介化(心像)的符號文本再現,而不是直接經驗”[18]47。由此來看,夢可被視作觀察和反映個體精神狀況的有效癥候。
因此,無論是作為寫作策略,還是作為精神現象,我們都不能忽視“夢”在《陌上》主題建構中的作用。簡單而言,《陌上》中對于夢的書寫,正是在書寫這個時代的鄉村精神景觀,是對當下中國鄉村倫理狀況和人心的真實寫照,同時也借此實現和現實的對話,進而認識和修正現實。“無論夢是真實世界人類本能欲望的滿足還是只是對個人過去經歷、記憶的重新組織,可以肯定的是夢跟所有虛構型敘述一樣錨定于經驗世界。我們可以通過夢世界去建構各種可能世界,從而更好地認識經驗世界。”[19]146
(二)《陌上》中的夢
小說先后講述了素臺、愛梨、銀花、建信媳婦、老蓮嬸子、耀宗、亂耕、建信、勇子、小梨等人的夢。從代際來看,這些人可以分為年老一輩和年輕一代兩類。其中,年老一輩的夢多以歷時性為主,或者表現為過去往事的再現,或者表現為兩代人之間的沖突;年輕一代的夢則多以共時性為主,主要是對現實經驗的精神反饋,是欲望的投射。前者在相互映照、對立的狀態中表明了鄉村價值觀念的變化和更迭,后者在彼此呼應中共同展示了鄉村的現實境況。在年輕一代中,又可看出性別上的差異:女性的夢多以焦慮、恐慌等消極情緒的流露為主,男性的夢則以欲望的表達為主。前者以愛梨、素臺、建新媳婦為例,后者體現在耀宗、建信等的夢中。當然,這里也有例外。如:第五章《小鸞是個巧人兒》中的小鸞年輕時做過風花雪月的夢,如今被金戒指喚醒了,此處的“夢”顯然是指欲望和憧憬;第二十四章《找呀么找小瑞》中的勇子做的夢就折射了他的焦慮。
1.日常焦慮的顯影
想到增志昨晚在床上的所作所為,素臺很生氣,覺得增志在外面學壞了,較從前的低眉順耳有了不小的變化。小說中描述了素臺從生氣、流淚到發呆的過程。當素臺對著鏡子發呆時,她夢見了站在自己身邊的增志,帶著一副祈求、饑渴的神態。看著增志這個樣子,素臺心軟了。夢中還有閃電和雨點向素臺襲來,她使勁跑,卻從懸崖上墜了下去。在一陣驚慌中,素臺從夢中回到了現實。她在夢中的遭遇映射了她在現實中的焦慮和緊張,是她精神狀況的展示。之所以如此,主要來自她聽到的關于增志的傳言以及增志本人的不正常表現。
建信媳婦做的夢是望日蓮——一個她向來躲著的人找她,并和她談話。望日蓮向她申訴了自己的苦楚,接著建議她找大全擺平事情,然后又談及建信(或者說男人)的拈花惹草。建信媳婦問她該怎么辦時,望日蓮說用剪子把那招是惹非的玩意兒剪了,便拿出剪刀,并把自己的心掏了出來。建信媳婦隨之被嚇醒。建信媳婦的焦慮來自建信的胡作非為。
勇子的媳婦小瑞是芳村的人尖子。早年的小瑞少見世面,遇人臉紅,甚至話都說不利索。后來的小瑞一直在外頭跑,經常不著家,甚至過年時也不回家,以至于有風言風語傳出,讓勇子又羞又惱。在夢中,勇子騎著摩托車,小瑞坐在后面抱著他,很是幸福,突然迎面撞上了一輛車。勇子在夢中喊著小瑞,一下子就喊醒了。這個夢正是對勇子內心焦慮的反映。
2.欲望的投射
愛梨是大坡的媳婦。懷孕后的愛梨在午后曬太陽時胡思亂想,很快就入睡了,并做了一個“荒唐亂夢”。在夢中,她起初以為是在和大坡親熱,但聽那人的聲音卻不像是大坡。她越掙扎,對方越來勁兒,她也越見此中的妙處。但由于又氣又怕,在試圖逃跑時被門檻子絆了一下,然后醒來了。夢后,愛梨只記得一股子好聞的香水味。后來,在素臺(大坡的小姨)的車上,愛梨又聞到了同樣的味道。此處暗示出愛梨夢中的那個人正是大坡的小姨父增志。串親戚回來后,愛梨裝作無意卻又是有意地向大坡問起了小姨和小姨父的情況。
建信也做了一個香艷的夢,夢中的欲望對象是四明媳婦。耀宗的夢,同樣是如此。在他的夢中,欲望對象不知是三杈還是小梨。三杈是耀宗的妻子,小梨是他忘不掉的喜歡對象。
3.代際的沖突
臭菊的夢主要是她和兒子的對話,內容則圍繞找“相好”好不好、能不能找等展開。小見說了自己老板的事情后,臭菊勸他莫要這樣子做。可小見認為,這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自己想學老板還學不了呢。雖然臭菊忙說給他找媳婦,卻安撫不了小見。小見揚言要去城里的發廊找小姐,引來了臭菊的慌張,勸他道,那可不是好人家的孩子該去的地方。可小見哪里肯聽,說著就往外走。臭菊忙去拉小見,卻把自己拉醒了。當臭菊試圖用傳統道德觀念勸服小見時,小見卻已經被身邊的社會現實收編了。兩代人之間的沖突源自對同一現象的不同理解,也與他們各自所處的文化環境有關。兩相對比,可以發現傳統道德觀念的威力已經有所損耗。
上述這些夢與其說與性有關,毋寧說,性以最直接的方式暴露了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復雜曖昧的關系,并在夢中傳達出人們內心的不安。“外部的改變與破壞固然令人觸目驚心,但因此造成的內心創傷與損毀則是這一現代性進程給中國鄉村和農民留下的更為深重、難以抹去的痕跡。”[20]越來越多的人來找小別扭媳婦銀花,讓這個民間識破①“識破”是河北無極一帶的說法,通常人們以“巫婆”指稱在民間燒香占卜預測禍福的人,如趙樹理小說《小二黑結婚》中的三仙姑。幫她們祈福去災,同樣顯示了她們的內心不安和對未來的猶疑、不確定。
作為日常生活的延續,這些夢和日常生活共同刻畫和反映了搖擺不定的鄉村秩序,主要是倫理道德方面的。人們在參與創造鄉村社會新現實的同時,也被新的現實創造著。小說先后描寫了大全和香羅、大全和望日蓮、小鸞和中樹、小閨和銀栓、建信和春米、增志和瓶子媳婦、蘭群和彩巧、耀宗和小螞蚱媳婦等男女之間的不正常關系……“芳村”中的這些枝枝杈杈,看似力量微薄,卻在不斷地晃動著鄉村的文化之基。這些人已經失去了反省、反思、返璞歸真的能力和意愿,放棄了對傳統倫理秩序的服從和堅守。
(三)夢與鄉村精神的映現
從當代文學史來看,男女之間的情感糾葛是民間和民間書寫的重要內容,如莫言的《紅高粱家族》中的“我爺爺”余占鰲和“我奶奶”戴鳳蓮、李杭育的《最后一個人漁撈兒》中的福奎和阿七、賈平凹的《天狗》中的天狗和師娘、劉恒的《伏羲伏羲》中的楊天青和王菊豆等。但與這些小說中裹挾著的原始野性和對生命力的宣揚有所不同的是,《陌上》中的描寫顯然要直接、輕松、簡單得多,尤其是少有意義的灌注更接近食色男女的本來面目。和畢飛宇的小說《玉米》中的王連方借助權力與鄉村女性建立關系相比,《陌上》中食色男女的面目更為顯豁,少有壓迫和反抗,多的是主動迎合。進一步從鄉土文學譜系中來看,賈平凹的《秦腔》中農村風氣開化出現的亂象以及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貧困青年曠開田在富裕之后的為非作歹等,都涉及到男女關系,但這些人物是受到了強烈道德譴責的,傳達出的是對鄉村現代性的批判,體現了敘事者對中國傳統倫理的服膺和堅守。從這點來看,《陌上》中的這些人和事已經和城市文學中的欲望敘事同聲呼應,并借助微信等通訊手段更為隱蔽、便利。這自然可以看作是鄉村卷入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后的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如今這年頭,風氣都開了,電視網絡手機,芳村的婦女們,心都變野了。”[13]337一個“野”字,從心理和行為兩個方面描述了鄉村女性的變化。顯然,這不是一個積極的變化。不過,從男性視角作出的這一描述和評價使女性成為替罪羊,未免有失偏頗。應該說,這是對整個鄉村新一代人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形容。考慮到鄉村在中國社會歷史上在倫理道德秩序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這種變化的確稱得上是重大的。
在《陌上》中,由于社會變動造成的倫理失序不僅體現在夫妻之間,在其他方面也多有表現。婆媳之爭歷來是鄉村社會的常見現象,但現如今兩者的位置發生了歷史性的顛倒。俗話說“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形象地點明了媳婦的艱難和婆婆的優越。但處在新時代中的這些婆婆們非但沒有享受若干優等待遇,反而處處受到兒媳婦們的種種刁難。從翠臺張羅給大坡娶媳婦、翠臺做飯等大坡兩口子來吃、喜針的憤憤不平、二嬸子無奈留下的眼淚、老蓮嬸子年老獨居等多處情節,可以看到:盡管這些“新”婆婆們的角色已然變更,但經受的內容似乎一切如舊。這究竟是她們這一代人的不幸所致,還是更年輕一代女性自我解放的顯示,抑或是時代之手的撥弄?即便傳統的倫理秩序有許多不合理之處,但尊老愛老敬老的美德也不需要了嗎?
當鄉村精神變得越來有彈性而缺乏價值共識時,鄉村的根基就逐漸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所謂的堅守也就變成了美好的想象,成為了少數人的徒勞。這時候的鄉村最終會走向何處呢?因此說,《陌上》中的這些夢是來自于真實經驗的精神投射,構成了對世道人心的精準寫照,恰當而生動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鄉村倫理狀況。
四、結語
《陌上》中對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社會景觀和以夢為表征的精神景觀的雙重書寫,從外在形態和內在價值兩種視域對當今的鄉村社會進行了勾勒和塑型。從自然景觀而言,鄉村變得日益空洞;從精神景觀而言,鄉村日益走向繁雜。兩種景觀的歷時性變化和彼此參照,恰當而不失準確地表現了鄉村的時代之變和時代之景,其中藏匿著小人物的悲歡離合,顯示著時代的起伏不定,展示了鄉村命運的盲目不安。在她的文字間,憂傷與溫暖同在,悲痛與歡笑相連,失望與希望并存,落魄與活力俱生。
鄉村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社會空間,還是一個情感空間、記憶空間。在系統地考察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鄉村形象譜系后,南帆寫道:“農耕文化的確進入了尾聲,然而鄉村的廣袤地域仍然存在,農民仍然是社會成員之中最大的一個群體,鄉村保存的古老文化仍然隱含著許多富有潛力的命題。鄉村與農民將在農耕文化與現代性交接中形成哪些新的景觀?”[11]或許可以說,借助土地和夢等展開的敘述,付秀瑩在《陌上》中對這“新的景觀”已經有所揭示,并對當下的鄉土寫作具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