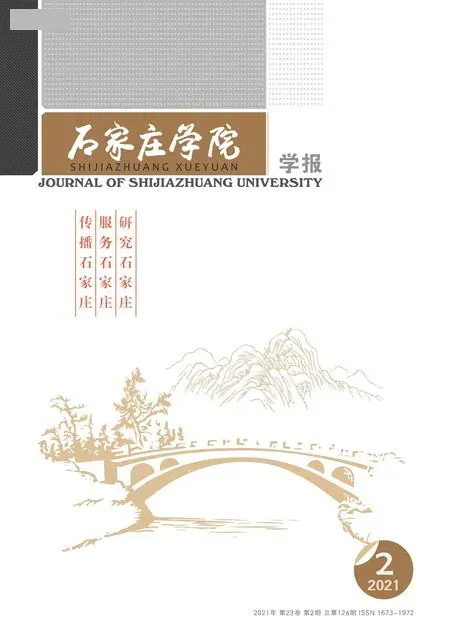朱筠與袁枚交游簡考
張金杰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150080)
朱筠(1729-1781年),字竹君,號笥河,人稱“竹君先生”,是乾嘉時期的學者、藏書家,在詩文、小學、金石方面頗有成就。袁枚(1716-1798年),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等,是乾嘉時期的代表詩人,與趙翼、蔣士銓合稱為“乾嘉三大家”,與趙翼、張問陶并稱“性靈派三大家”。作為清乾嘉文壇時期的領袖人物,朱筠與袁枚的相遇相知,對其自身以及當時的文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朱筠與袁枚之相識
朱筠第一次見袁枚時,是于一個較為特殊的地點,時間為乾隆三年戊午(1738年)秋,那時朱筠還是10歲孩童,袁枚此時已經23歲。乾隆三年(1738年)八月十日,朱筠見袁枚在貢院牌坊下誦讀試文,其在《與袁簡齋前輩(壬辰)》書中寫道:“戊午之秋八月十日,先生冠長纓,立貢院牌坊下,自誦其試文。時常熟趙先生貴彤,自龍門出,就先生語。時筠年甫十齡,一望見識之。后長大相聞,不復見。二十五六為館中后進,先生方出官。”[1]朱筠《為袁簡齋前輩題隨園雅集圖用十八隊韻(癸巳)》又云:“袁先生人豪,早歲抗前輩。我小聞而識,出自棘闈內。倚柱哦其文,若無人窺背。河漢聽莫極,氣盛波刷塊。入館掉兩臂,一麾縣印佩。”[2]卷十一
張俊嶺《朱筠年譜新編》乾隆三年(1738年)譜“八月十日”條按語云:“朱筠見袁枚在鄉試第一場后。十年袁枚二十三歲,朱筠十歲,二人尚無交游可言。”[3]16此處,張俊嶺所言即是,此時二人確實未有交游。朱筠早歲時,在貢院牌坊下偶遇袁枚在誦讀試文,并遠遠望見趙貴彤與之言語,但并未走近,而此時袁枚并不知朱筠,也未看見朱筠,從“早歲抗前輩”“一望見識之”可證。又“我小聞而識”“后長大相聞,不復見”,可知,朱筠只是與袁枚有單方面的一面之緣,直至朱筠長大之后,仍未相見,此從兩人的往來書札中亦可得知一二。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與朱竹君學士書》中云:“雖然,枚當知公,公不當知枚,何也?天之卿云,朝陽之鳴鳳,雖山澤之癯,仰而窺所共見者也。若夫江湖間老物散材,要惟耦居者,知之其高而麗于天者,未必降階越境,以存之也。”[4]卷十九可見,兩人此時仍未見面,但袁枚早已耳聞朱筠,對朱筠也有所了解,但不知朱筠是否知道自己。書札末其又言:“公之未見其人,而為之道地者,果孰賢也。”[4]卷十九也進一步說明,兩人并未正式見過面。
此之后,在壬辰(1772年)仲夏時,朱筠給袁枚回復了一封書札《與袁簡齋前輩》,書札中說到了壬午(1738年)之秋,見袁枚在貢院牌坊下誦讀試文之事。書札末又言:“昨冬過訪隨園,不得見,投刺悵悵而去,如有所失。大著固愿見,尤愿得侍坐于左右,一談其累年之未得見也。辱再賜于書,秦學士問寄者,筠出都始獲讀之,孟陬所寄,又未遑即答。往來于心,欲一致其區區而言之,不知其起止。頃將往徽、歙間,不能已于言,輒敢陳之余,再以書奉。”[1]朱筠所言是指辛卯年(1771年),其將赴安徽任職學政,途過南京,前去拜訪袁枚,但袁枚已于十月至杭州,二人遂不得見,而此時朱筠已經43歲,袁枚也已經56歲。
后袁枚言其與朱筠不得相見,乃是天意使然。《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答朱竹君學士書》云:“仲夏讀執事書,錯落奧衍。愛執事之文之古,苦言至意,敬執事之心之古,道枚冠長纓。試京兆時,曾早目之,正如執事之仁風,枚亦早耳之也。三十年來,兩相思兩不知,天若欲兩人者相見,而使執事持節來,又若欲兩人者不輕相見。而使見訪時,枚又避宅他適,毋乃故郁其心,支閡其意見以誘其所欲言者,而俾之兩相益乎?”[4]卷十九亦可證明,朱筠在10歲時與袁枚一面之緣之后,30年來二人從未相見。
直到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筠任職安徽學政期滿,歸京時,再次路過南京,又去拜訪袁枚,二人才最終相見。借此,朱筠特為袁枚題《隨園雅集圖》,作《為袁簡齋前輩題〈隨園雅集圖〉用十八隊韻》,詩云:“我來九千后,乙癸空甲隈。喜得覯先生,雞鳴雨如晦。”[2]卷十一袁枚《隨園詩話》卷十四亦云:“朱筠學士督學皖江,來山中論詩,與余意合。因自述其序池州太守張芝亭詩,曰:‘《三百篇》專主性情,性情有厚薄之分,則詩亦有淺深之別。性情薄者詞深而轉淺,性情厚者詞淺而轉深。’余道:‘學士腹笥最富,而何以論詩之清妙若此?’竹君曰:‘某所論,即詩家唐宋所由分也。’”[5]卷十四袁枚此處言“與余意合”,應是溢美之詞,因其在《隨園詩話》卷十又云:“朱學士筠,字竹君,考據博雅,不甚吟詩。”[5]卷十即其對朱筠作詩思想及手法并不欣賞。
多年后,朱筠再次在詩中回憶二人相交,感慨萬千,其在《連日宴飲明翠閣大觀樓即席口占四絕句呈簡齋太守》詩中云:“知音漫向齒牙求,一串明珠澈妙淚。解道玉茗詞里意,一生心醉大觀樓。”[6]此首詩歌作于庚子年(1780年)二月二十四日,朱筠已經52歲,袁枚已經65歲,道盡了二人相見恨晚之情。
二、朱筠護持袁枚一二事
朱筠與袁枚雖然相知,亦經常有書信往來,但在幾十年里幾乎未曾相見。在朱筠仕途達到人生頂點的時候,而袁枚已經隱居深巷,但朱筠對袁枚的情況卻一直較為關注。袁枚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親老乞養辭去江寧知縣職,在南京小倉山購買舊宅,改建成“隨園”,就此隱居。雖乾隆十七年(1752年)一度銓官陜西知縣,但未及一年復歸,從此在隨園“賦閑居”時間長達45年。由于袁枚是性情中人,耿直狷介,即使未身處官場,仍招來他人的誹謗與議論,但朱筠總是挺身而出,為其辯解并解圍。
如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秋,謠傳江寧知府劉墉欲逐袁枚歸杭,朱筠為之挺身說人,袁枚《隨園詩話·補遺》云:“乾隆己丑,今亞相劉崇如先生出守江寧,風聲甚峻,人望而畏之。相傳有見逐之信,鄰里都來送行,余故有世誼,聞此言,偏不走謁,相安逾年。公托廣文劉某要余代撰《江南恩科謝表》,備申宛款,方知前說都無風影也。”[7]卷六章學誠《文史通義·論文辨偽》亦云:“石庵相公官江寧時,欲法誅之,可謂知所務矣,而竹君先生為解脫之,遂令術逢顯要,登高而呼,號召無知士女,凡可以敗人倫而傷風化者,無所不為。竹君先生天性坦易,平日固多汰許之病,石君先生似近方嚴,然亦嘗與此人書問往來。余疑問之,則云:‘狎客耳,何遽不容?’噫!賢者如此,況他人乎?”[8]卷七章學誠由于對袁枚有偏見,此處將劉墉驅逐袁枚一事,寫成“欲法誅之”,是章學誠之夸張之說,但對朱筠為袁枚解脫之事,是客觀真實記述。
為此,袁枚特寄書朱筠,并將自己30年的著述贈與朱筠,以感激朱筠的正義相助及知遇之恩。袁枚《與朱竹君學士書》云:“不意秀才陳熙來,道公問枚甚悉。進士程沅來,又道公為護持枚故,挺身說人,嘻枚之與公,名紙未嘗通也,謦咳未嘗接也。縱左右之人,妄有稱引,又安知非阿所好以誑公?而胡乃眷私若是?然則使枚竟幸而得近顏行,布露所畜,抱三十年著述,拜獻于中衢之車下,不知公之矜寵而教督之者,又將何似也。昔孔北海為楊彪緩頰,裴監州為傅蘭碩通兩家之好,皆卓卓史冊間,然皆先狎交之后,覆露之較,公之未見其人,而為之道地者,果孰賢也。”[4]卷十九朱錫庚《椒花吟舫書目》中載:“《隨園詩話》,六本;《小倉山房集》,二十二本。”[9]可能即是袁枚所贈朱筠本。陳熙是袁枚和朱筠弟子,朱筠曾薦其闈卷,陳熙《甲午秋闈報罷,學士竹君先生過寓慰問,兼招游西山感賦二首》:“曾賦《阿房》薦牧之,蹉跎一舉六年遲。”[10]卷五又《騰嘯軒詩抄》卷二十八《追題椒唫花 舫圖感笥河先生(并序)》:“余受知最深,感恩最重者,簡齋師而外,惟薦師朱笥河學士。兩公徂謝,皆有挽歌。”[10]卷二十八另《騰嘯軒詩抄》卷九有《挽薦師竹君學士》詩。
又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在朱筠任職安徽學政時,幕中章學誠因與洪亮吉不和,而洪亮吉又與袁枚有知遇之交,袁枚遂遭到章學誠的攻擊,而朱筠此時又為袁枚辯解。章學誠《文史通義·論文辨偽》云:“昔者竹君先生視學安徽,幕中有妄人出某甲門下者,戛戛自詡,同列無不鄙之。其人初某甲為乃父所撰墓志,矜示于人。余時未識某甲行徑,一見其文,遂生厭惡,指摘其文紕謬,其人怫然,竹君先生解之,陰謂余曰:‘流俗習必已久,豈可以吾輩法度繩之。’則朱氏論文,必無許可某甲之說。”[8]卷七文中的“某甲”指袁枚,因為《論文辨偽》一文主要是批評袁枚。幕府中“妄人”應指洪亮吉。張俊嶺《朱筠年譜新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譜按語云:“此時幕府中人物符合‘妄人’性格特征者應是洪亮吉、黃景仁二人,二人都與袁枚有交游,而涉及墓志事者為洪亮吉。……洪亮吉在入朱筠幕的次年,曾先后乞邵晉涵、朱筠為其父作行狀、權厝銘,《笥河文集》卷十四《國子監生洪君權厝碣銘》:‘明年春三月,禮吉乞余姚邵進士晉涵為其尊甫君狀,請余銘。’所以,‘妄人’應指洪亮吉。”[3]190-191
嘉慶二年丁巳(1797年)十一月十七日袁枚卒,從是年起,章學誠開始撰寫數篇文章攻擊袁枚。胡適著、姚名達訂補《清章實齋先生學誠年譜》嘉慶二年(1797年)譜:“是年袁枚死,年八十二。先生對于同時的三個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貶辭。但先生對戴震,尚時有很誠懇的贊語;對汪中,也深讃其文學;獨對袁枚,則始終存一種深惡痛絕的態度。《遺書》中專攻擊袁枚之文,凡有五篇:《婦學》《婦學篇書后》《詩話》《書仿刻詩話后》《論文辨偽》。攻袁之端始見于此年。”[11]129
嘉慶三年戊午(1798年)六月,章學誠又致書朱珪,言之前在蘇州見袁枚尺牘,有誣朱筠、朱珪論文之事,章學誠遂作《論文辨偽》以辯之。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上石君先生書(戊午六月)》:“五月在蘇州……惟于蘇州城市,偶見坊刻尺牘,其人其書,極可賤惡,乃有誣閣下與彼論文,大加傾倒,且附和其人,譏及先師。因嘆小人之無忌憚,至于斯極,而君子遭辱,則不可謂無因也。因取其言辨之,謹錄奉上,所謂蒼蠅玷父兄面,不容不拭。要之其人何足責哉,正恐君子受辱有由,則古人所恃,將以集廣思而分旌麾者,或無暇及矣。”[8]81-82
章學誠作為朱筠較為得意之門生,其對袁枚充滿敵意,但朱筠仍然不妄加咨議袁枚。從此也可以看出,袁枚作為長輩,朱筠甚是敬仰和尊重,即使對其詩文理論和風格有不同看法,但也是采取較為溫婉的態度包容之。這正如章學誠所言,朱筠在論文時,從未贊同袁枚之說,也未否定其說,而是采取了避而不論之態度,這也顯示了朱筠對袁枚這位老學者的尊重之情。
三、袁枚對朱筠詩文之評價
袁枚對朱筠贊賞非常之少,尤其對朱筠詩文創作方面皆有異議,其僅在為感謝朱筠為其辯誣的書札中,對朱筠有少量美言。袁枚《與朱竹君學士書》云:“公昆季以文學卓行,同翔天衢,為海內所讋服。公又束修其躬,志古人之所志,學古人之所學,士林中靡不齊其口,異音同嘆。江南高才生,為枚所目色者,不北行則已,茍北行試京兆禮部,必一一被公羅取。”[4]卷十九袁枚在此雖然對朱筠有所稱頌,但也是籠統贊揚,主要還是贊頌朱筠門徒之盛,對其詩文僅客觀評價曰“志古人之所志,學古人之所學”,并未進一步頌揚。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六月二十一日,程晉芳卒于西安,袁枚為其作墓志銘,又稱及朱筠喜交游之事,程晉芳《勉行堂詩集》卷首袁枚《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并序》云:“……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12]卷首此處袁枚也僅頌揚了朱筠交游之廣、門徒之盛,未言及其詩文學術。
袁枚之所以盛贊朱筠交游,是因為其也是喜交游之人,門徒眾多,因此王昶對朱筠和袁枚二人廣招門徒之事頗有訾議。陳康祺《士大夫歸田后之規范》云:“王蘭泉侍郎在京師時,與笥河學士互主騷壇,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目。罷官歸田后,往來吳門,賓從益盛。……然其時袁簡齋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若騖,侍郎痛詆之,收召門徒,隱然樹敵,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黏,皆與齒錄,頗有惜其太邱之道廣者。”[13]卷十二
王昶雖然批評二人門徒之盛,但是自己似乎亦如此,遂遭到江藩的責問。嘉慶四年己未(1799年),江藩至杭州謁王昶于萬松書院,言其門徒之廣,盛于朱筠,王昶則默不作答。江藩在《王蘭泉先生》中云:“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于萬松書院,從容言曰:‘……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14]卷四而陳康祺對王昶用廣招門徒來表達對袁枚的不滿,也較有異議,其在《士大夫歸田后之規范》云:“康祺竊謂隨園之所為,不過假以梯貴游,攫金帛,以自適其園林聲伎之好,侍郎何苦詆之。若錢、王二先生之遺榮志古,內介外和,獎掖后賢,不立門戶,則誠士大夫歸田之規范也。”[13]卷十二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正月十八日,為教育諸生識字通經,朱筠重刻《說文解字》,并作《〈說文解字〉敘》,敘云:“大清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筠奉使者關防,來安徽視學。明年,按試諸府州屬,輒舉五經本文,與諸生月日提示講習。病今學者無師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其狎見尤甚者……點畫淆亂,音訓泯棼。是則何以通先圣之經,而能言其義邪?既試歲且一周,又明年春,用先舉許君《說文解字》舊本,重刻周布,俾諸生人人諷之,庶知為文自識字始。”[15]卷五朱筠重刻《說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其認為讀書須識字,不識字無以通經,因此購得宋汲古閣本許慎《說文解字》,讓王念孫等人校正,且親自作《重刻〈說文解字〉敘》,以教徽士。洪亮吉《書朱學士遺事》云:“先生以讀書必先識字,病士子不習音訓,購得汲古閣許氏《說文》初印本,延高郵王孝廉念孫等校正刊行。孝廉為戴吉士震高弟,精于小學者也。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錢市之。先生性寛仁,不能御下,校官輩又借此抑勒,并于定值外需索,以是不無怨聲,然許氏之學由此大行。”[16]卷四朱筠所重刻《說文解字》之版本,為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開雕椒花吟舫板,由江寧顧晴崖刻字,宛平徐瀚校字。
朱筠所作《〈說文解字〉敘》中辨別六書之思想,皆咨詢于王念孫,且承用其言。章學誠《文史通義·答沈楓墀論學》云:“昔朱竹君先生善古文辭,其于六書未嘗精研,而心知其意。王君懷祖固以六書之學專門名家者也,朱先生序刻《說文》,中間辨別六書要旨,皆咨于懷祖而承用其言。仆稱先生諸序此為第一,非不知此言本懷祖也,而世或譏之,此不可語于古人為文之大體也。”[8]331臞但閔爾昌《王石 先生年譜》中認為《〈說文解字〉敘》是王念孫代筆之作,此仍需商議。因朱筠在文字方面雖然沒有王念孫功力深厚,但其學識應足以寫出此篇序言,此篇序言朱筠寫畢之后,很可能請王念孫進行了修改潤色。章學誠云“非不知此言本懷祖也”,是指序言中所言六書宗旨,皆是王念孫之思想,而并不是指序言內容。
朱筠在《〈說文解字〉敘》中提倡六書之學,受到時人的慕效,但也遭受到了時人的批評。李威《從游記》云:“六書之學,不絕如線。近代著作家,或以楷晝,效篆體為書,蓋楷法難明倉史遺意,往往從類不分,故不得不雜篆法為之,波折縱橫,并出新意。先生深病學者不明文字所由生,其敘刻《說文》,推論原委,有半訛全訛之嘆,故亦喜為此書。每摹勒入碑版,古趣盎然,見者輒不能句讀。先生嘗言吾非嗜奇,欲得古人制字意耳。及出視學,士爭慕效,不知故而貌襲之,詭異乖違,若瓦缶與彝鼎,并陳鱔鰍與螭龍同舞。”[15]卷首朱筠好古文奇字,洪亮吉也受其影響,文中多用奇字僻字,則受到了袁枚的批評,從而也間接地批評了朱筠。
袁枚《答洪華峰書》云:“頃接手書,讀古文及詩,嘆足下才健氣猛,抱萬夫之稟,而又新學笥河學士之學,一點一畫不從今書,駁駁落落,如得斷簡于蒼崖石壁之間。仆初不能識,徐測以意,考之書,方始得其音義,足下真古之人歟?……足下為唐宋以后之文,而作唐宋以前之字……讀書愈多,矜奇愈甚,他日對策王廷,諸衡文官必無好古如笥河者,少見多怪,徒遭駁放。……《上笥河學士一百十韻》搜盡僻字,仆尤不以為然,詩重性情,不重該博,古之訓也。”[4]卷十九袁枚對洪亮吉與朱筠的批評確實有一定道理,尤其說到詩歌應當“重性情”,而不是“該博”。對此,洪亮吉似乎也有所接受,也得到了教訓,洪亮吉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會試中,似乎并未用古文奇字,而珪朱 等人以為文中多古文奇字者,必為洪亮吉卷,開卷后卻是他人,而洪亮吉的名次僅為第26名。此在陳康祺《郎潛紀聞》卷十四《朱石君橫文之精》、呂佩等的《洪北江先生年譜》中皆有記載。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秋冬之際,程晉芳致書袁枚,認為朱筠、袁枚、姚鼐、朱仕琇、諸洛、錢大昕及其自己等人之古文可傳,然袁枚認為朱筠古文自發理論者最少,尚遜少許。程晉芳《上簡齋前輩書》云:“近今海內,為散古文而信其可傳者,有數人焉。敝老師竹君先生、姚比部鼐、諸秀才洛、福建朱太史琇仕 、錢太史辛楣,仆亦廁其末,足下當為一大宗,諸家各有短長,不能駕足下而上也。”[17]卷二程晉芳《上簡齋前輩書·又》亦云:“竹君先生終是古文可傳,然視足下恐尚恐遜少許,以生平自發議論者最少。古文自以碑版多為第一,而議論文亦不可無。昌黎之五原、老蘇之策論,不如是不足以罄其胸中所學也。……兄自是一代傳人,終以古文為第一,詩必交與弟再加榷選更妙。海內文人、學人可二十余。學人以辛楣先生為第一,文人則足下高據一席,不容讓也。……戴東原一病而殂,誠為可痛,著述七十卷,使其不死,閑居二十年,當不止是。人皆推其為近人第一,以弟平心論之,其成就仍在綿翁之下耳。”[17]卷二
另袁枚在丙午年(1786年)與朱珪論古文時,又言及朱筠古文弊病,其《小倉山房尺牘》卷三《覆家實堂》云:“去冬在杭州見朱石君侍郎,蒙其推許,云古文有十弊,惟隨園能掃而空之,余問其目……余笑答曰:‘此外尚有三弊。’侍郎驚問,余曰:‘征書數典,瑣碎零星,誤以注疏為古文,一弊也;馳騁雜亂,自夸氣力,甘作粗才,二弊也。尚有一弊,某不敢言。’侍郎再三詢,曰:‘寫《說文》篆隸,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覺笑之。”[18]卷三袁枚所講第三弊,指朱筠作文好用古文奇字之弊。簡而言之,袁枚對朱筠的評價從文學創作角度來看,還是較為客觀中肯,其并未對朱筠的詩文創作思想進行夸大的批評,或者過分的指責,僅僅是指出了其存在的弊端。
四、余論
朱筠的詩文創作思想與宗旨,雖然受到袁枚的指責,但其詩文創作有其突出之處。對于朱筠的詩文創作宗旨和理念,朱錫庚在其《先大夫文集后序》中有所論及,因朱錫庚對其父朱筠的詩文創作宗旨較為了解,且有所繼承,當最能反映朱筠的真實創作思想。朱錫庚言“故集中之文,不越考古、記事二端,而不為論辯”,這便有力地回擊了袁枚批評朱筠“以生平自發議論者最少”的論斷。具體引之如下:
昔者先子有言曰:“文無常律,唯求其是。”又曰:“有意為文,絕非真文。”故集中之文,不越考古、記事二端,而不為論辯。夫考古者,經之遺也;記事者,史之職也。不為論辯者,六藝而外,有述無作也。嘗謂經學不明,良由訓詁不通,通經必先識字。庶幾兩漢諸儒所講之經可以明,而后世望文生義之弊絶,欲仿揚雄《訓纂》而撰《纂詁》。又謂:“學者不通古音,無以遠稽古訓。”故劉熙《釋名》,因聲求詁;揚子《方言》,遍 輶歷 軒。可以異域之言,而證近正之訓,亦可以殊方之音,以推往古之音。庶幾周秦、漢魏音聲逓變之故可以通,欲仿《方言》而撰《方音》。禮起于未然,制莫精于喪禮、撰禮、意禮,莫古于儀禮。苦節文之難,讀撰釋例,所輯金石遺文,漢唐以及元明不下千通,謂金石文字,上可輔經,下可繹史。嘗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撰《五代史補注》若干卷,既成,為人誤毀。凡所纂著,缺而不錄,第其微言遺旨,往往錯見于簡篇,好學深思,自可按而窺也。[19]
朱筠作詩文之宗旨,確有其優點,亦又有其弊端。因為作為受教于朱筠的門生章學誠,對其師朱筠的文章也存有自己的看法。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年(1778年),章學誠在《與錢獻之書》中云:“戴東原氏之訓詁,朱竹君氏之文章,皆無今古于胸中者也。其病則戴氏好勝而強所不知,朱氏貪多而不守統要,然而與風氣為趨避,則無之矣。”[20]794其又在給徐書受所作的《徐尚之古文跋》中云:“徐尚之少牧,嘗學古文辭于大興朱氏……近日辭章盛,而鮮為古文辭者,大興朱氏教人古文義法,所言至在淺盡,而人猶誑不信,蓋為者少,知之者則愈難也。”[20]596
總之,朱筠和袁枚雖然在文學創作方面的理論宗旨有所不同,但是各有其長處,又加之二人皆喜交游,友人弟子遍布天下,像洪亮吉、阮元、伊秉受、蔣士銓等皆是二人共同之友人,且交游密切。也正因為如此,二人的詩文創作理念對其周圍的門人弟子及友人,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對清代文壇皆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當朱筠去逝之后,袁枚作《哭朱竹君學士》以悼之,詩云:“古人今不作,古道竟非宜。聽說文星墜,空增吾黨悲。持身盧子干,好客鄭當時。奇字三蒼纂,窮經六籍披。請開書四庫(自注:聞上開四庫館,奏始于公),漸白鬢千絲。學博天能鑒,心清水共知。龍門今逝矣,寒士欲何之?大雅扶輪者,長安剩有誰!”[4]卷二十八從詩中不難看出,袁枚在朱筠生前對其詩文雖有不滿,但當朱筠去逝后,卻并未對朱筠進行更深入的指責與批評,而是對朱筠一生的學術及功績進行了盛贊,給予了朱筠較高的評價,此亦足見袁枚對朱筠之學問亦有欣賞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