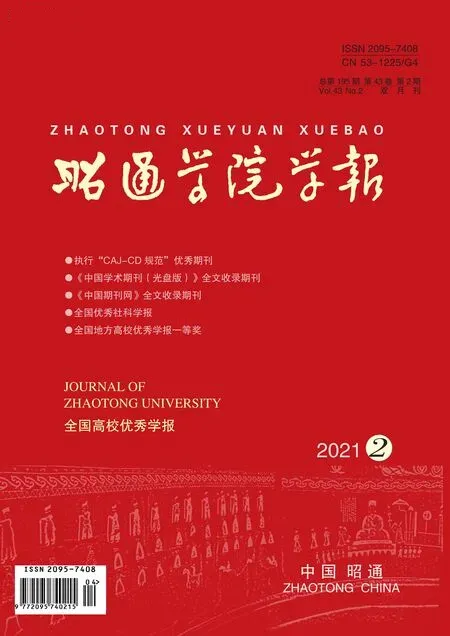《野草》中的“夢”
——以巴赫金“精神心理實驗”為視角
李富倫
(云南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一、引言
文本中異常的夢境,巴赫金稱之為“精神心理實驗”,其認為這種現象“不僅僅只有狹隘的題材意義,還具有形式上的意義,體裁上的意義。”[1]魯迅先生的散文詩集《野草》[2]之中,存在大量夢境藝術的處理,筆法盡顯荒誕離奇,在諸如死亡、地獄等異事物、異域時空的描繪中運筆,以“夢”作為連接這些亦幻亦真的魔幻世界的中間橋梁,從而使得構思順暢而不顯突兀。以巴赫金梅尼普體論述中的“精神心理實驗”為視角,這些夢境藝術不管從具體內容還是藝術形式來看都具有深刻的深層寓意。
《野草》中有11篇有關夢境的文本,占據全冊近一半的篇幅,故而有學者認為“如果夸大一點來說,作家是以開篇《夜》入夢,到終篇《一覺》才‘忽而驚覺’的”[3]。在這些文本當中,《秋夜》中是小粉紅花、落葉與棗樹的夢,《影的告別》是不著痕跡的睡夢處理,是自我分身的影子的奇特獨白。《好的故事》將記憶與想象編制在一起,呈現出奇妙的夢游之旅,而《死火》《狗的駁詰》《失掉的好地獄》《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立論》《死后》等幾篇更是直接以“我夢見……”起筆,將夢境的營造作為了行文的主要框架。最終,以《一覺》的“在無名的思想中靜靜地合了眼睛,看見很長的夢”[2]62停筆,無疑,夢境的營造成就了本書在形式與內容上重要的獨到之處。
夢境,在生理現象的身份之外,它還作為人類意識領域的一種獨特現象。其擺脫了時空的束縛,有著極其自由的流動性。進入文本之中,這種流動與自由的屬性使得夢境在作家的筆下得以盡情施展,從而形成較實體空間另類獨特的具有異質性特征的空間。在這十余場夢境之中,或視角奇異或空間怪誕均以一“異”立文。
同時,夢境所造就的異質空間使得個體擁有了可以與之對話的對象,這也就是巴赫金所謂的夢境“使人和人的命運無法獲得史詩和悲劇中的那種整體性”[1]153的特征,這種整體性的破滅直接形成了文本之中的各種對話書寫。《野草》之中,有《影的告別》中與自身影子的對話,有《死后》與自己的對話,也有《狗的駁詰》中與狗的辯解……這些都與夢境有著直接的關系。
二、時空的異質性
較現實時空而言,夢境時空具有更大更自由的流動性,在夢里,時間可以根據情節需要進行任意改動,空間亦可根據想象進行無限虛構。俄羅斯學者葉菲莫娃(Е.С.Ефимова)認為:“在文學作品中運用夢境描寫手法的作用在于,它在一個空間中創造了另一個更深層次的空間,而被創造出的這個空間最終上升為世界的真正本質。”[4]
《野草》的11篇有關夢境的文本中,夢境時空與現實相近的只有《立論》一篇:“我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其余或視角奇異或空間怪誕均以一“異”立文。《秋夜》乃物之夢,是小粉紅花、棗樹以及落葉的夢,《好的故事》引領讀者走進作家記憶與想象編織而成的世界,《頹敗線的顫動》設計了夢中之夢,《失掉的好地獄》走進地獄,與惡鬼交流……
視角與空間的獨特性使得《野草》中的夢境呈現出異乎尋常的詭譎特征,這種特征進一步加強夢境與現實的差異性,創造出了一個個深層次的空間。在這些空間中,既有《好的故事》中美麗、優雅、有趣的“夢游”場景,也有《失掉的好地獄》中魑魅魍魎橫行的阿修羅地獄。但是,即使是在《好的故事》中,作者也并沒有將重點著眼于這“美麗、優雅、有趣”之上,而是在文末通過自己的夢醒揭開夢境與現實的巨大鴻溝:“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云錦也已皺蹙,凌亂,仿佛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2]25。故而,《野草》之中并不關涉夢之美與幻,而是著眼于其異與怪。這種與現實近乎對立的設置使得夢境與現實具有了對話的條件,這是夢境營造在文本形式上形成的對話屬性,借夢境之形,話現實之實。這種對話并不需要雙方坐下來交談,只需要在對立之中便可顯現,即夢境越是詭譎其意蘊便越是深刻。
夢境空間服務于作家所需,其極強的可塑性使得作家可以得心應手地對其進行自己需要的無任何限制的改造。于是,無論是曼妙無比還是光怪陸離也就都能得到接受。魯迅在《野草》中主要選擇了夢境奇異怪誕的一面進行呈現,所謂怪異均是較現實而言,夢越荒誕,其與現實越趨異,也就越能引來注視。這些荒誕怪異的夢境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巴赫金所謂“顛倒的世界”[5],是作為日常現實空間的模擬與戲仿。擺脫了現實的種種束縛,作者自己造就的夢境空間就擁有了自由,并且始終由自己掌控。
也就是說,文本中這些夢境空間無疑成為了作家自我建造的“樹洞”,它承載著作家的真實意志,儲藏了作家內心最深處的意愿,在與現實空間的對照之下顯示出其隱藏在荒誕之下的深刻。
《野草》凡24篇均是魯迅于北洋軍閥統治期間所作,是“碰了很多釘子之后”寫出來的,又“因為那時難于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6]。于是,現實境遇之下,奇異的夢境成為了寄托自我與真實的獨特隱秘空間。
三、結構與內容的對話性
巴赫金認為:“夢境幻想、癲狂——它們使人和人的命運無法獲得史詩和悲劇中的那種整體性……梅尼普體中出現了人物對自己本身的對話態度(其結果是個性的分裂),這也促使人物失去了整體性和完成性。”[1]153-154如上文所言,在文本的形式結構上構成與現實時空的對話之外,奇異的夢境也令文本內容具有了對話屬性。夢境文本之中的人物由于失去了個體的整體性與完整性,其迫切需要與世界甚至是自己展開對話。《野草》中,“我”正是失掉了個體的完整性而出現了自我分裂,這種完整性的破滅借由夢境中獨特的對話進行展現。
在《野草》相關夢境書寫中,無論是內容上《死火》中與“死火”的對談、《影的告別》中影子的道別,《墓碣文》里死去的自己的話語還是結構上兩種空間的并立,作家眾多夢境文本之中均充滿著對話屬性。這些對話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對話,在奇異的夢境中,對話擁有日常話語所不具備的深刻。夢境文本中的對話是具有“從人間轉到奧林匹斯山,轉到地獄里去”的三點式結構的,此對話是“邊沿上的對話”,是在地獄入口的“死人的談話”[1]153-154。正如學者宋靜思所言:“魯迅在夢境中使用反向、顛倒、嘲弄、貶低、諷刺等手法來顛覆原有的社會秩序,直指黑暗的現實,撕開了它的偽裝,形成了一種狂歡式的交往和對話。”[7]
在結構上,夢境空間始終與現實空間對立且作者直接在文本之中挑明二者的界線。《狗的駁詰》中,在無力應答之后,自己“一徑逃走……直到逃出夢境,躺在自己的床上。”《墓碣文》中“我疾走,不敢反顧”,《頹敗線的顫動》中自己“用盡平生之力要將那通向夢魘的沉重之手挪去”……這種界限分明的對立關系無形之中也就成為了一種對話關系,通過對照而達成言說的最終目的。夢境成為現實空間的反向世界,二者只有相伴而行在對照或者對話中才能呈現出作家欲言明的真實圖景。表面上,夢境越是詭異則真實性越是疏離,實際上,詭譎的夢境與平淡無奇的現實是一種二律背反的關系。夢境越是奇異則作家的意圖越是明顯,其詭異表面上是掩飾的帷幔,實際上正是揭示的鑰匙與指向標。
在內容上,夢境文本呈現出的對話性就更加明顯。11篇夢境文本不僅有與死火、狗等對話的外部對話還有著與影子、自己等對話的內部對話。
《失掉的好地獄》中,“我”與地獄中的魔鬼發生對話,從中知道地獄殘酷的現狀乃人類所致,人類已然超越了惡魔所具備的邪惡程度。而在《死火》中,“我”喚醒了死火,由于意見未達一致而沒有將其帶出冰谷。到了《狗的駁詰》之中,“我”甚至直接與狗爭論了起來。這些對話借著夢境的荒誕成功撕開了現實的偽裝,達到述說真相的效果。正是借著狗的口表明現實中人的勢利,在與魔鬼的對話里突出人的現實面目,在死后與眾人的對話中凸顯現實的荒誕離奇。顯然,《野草》著重于地獄入口的對話。《墓碣文》《死后》《失掉的好地獄》等都是與死亡或者地獄直接展開對話,這種“死人的談話”顛覆了人間的種種秩序,給人強烈的沖擊之感。
同時,文本之中人物在面對個體自我之時,其分裂性也時刻存在。《墓碣文》中,“我”和死去的自己展開了對話,《影的告別》中,“我”借著影子的身份自己與自己對話。在夢境的基礎上,這些分裂的對話突兀感驟降,同時還能透過自我對話展現作家真實的自我,以自我型的對話充分呈現出“我”只能選擇在“黑暗里彷徨于無地”的分裂無助之感。
四、詼諧成分(狂歡式的笑)
作為“顛倒的世界”,一切在人間被“加冕”的嚴肅與神圣在夢境尤其是奇異詭譎的夢境之中,全部被“脫冕”,這也正是所謂狂歡式的笑的功用之一。同時,在夢境文本之中,詼諧成分并非是簡單的插科打諢,其具有非常明顯的雙重性。巴赫金認為“它既是歡樂的、興奮的,同時也是譏笑的、冷嘲熱諷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5]14
《死火》中,“我”在被碾死在車輪之下后得意地笑著說:“哈哈!你們是再也遇不著死火了!”[2]36,此處的“笑”顯然不是普通的笑,它具有沉重的屬性,是哀傷之笑、含淚的笑。《狗的駁詰》在形式上便是一種反諷,同時,被“我”認為勢力的狗卻嘲笑說:“嘻嘻!愧不如人呢”[2]37,這是強有力的諷刺。這詼諧的手法以及狗的笑都是對人間與人的嘲弄、譏笑。
同樣,在《死后》之中,面對已經死去的“我”,勃古齋舊書鋪的小伙計的反應是詢問:“您好?您死了嗎?”[2]50并一味只想向我兜售《公羊傳》。在這詼諧之后,人間的荒誕性不言而喻。這些詼諧成分伴隨著極強的雙重性,它不關涉笑與詼諧本身,而是指涉更為隱蔽的對立面。
不同于普通的笑與詼諧,巴赫金認為“這種詼諧也針對取笑者本身”[5]14,普通的否定式的笑是不針對發笑者本身的,是一種孤立自身的笑。但是夢境中這種笑是不與施笑者分離的,它是從整體的角度通過詼諧認知世界,故而其笑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于是我們看見,在《狗的駁詰》之中,狗駁斥的既是慌亂逃走的“我”也是“我”所在的整個世界。以詼諧及笑的形式,借其雙重屬性,作家不斷對人間與現實進行揭露。
五、結語
在梅尼普體中“最大膽的最不著邊際的幻想、驚險故事,也可以得到內在的說明、解釋、論證,因為它們服從一個純粹是思想和哲理方面的目的——創造出異乎尋常的境遇,以引發并考驗哲理的思想……幻想用在這里不是為了從正面體現真理,是為了尋找它,引發它……為了這個目的,主人公上天堂,人地獄,游歷人所罕知的幻想國度,面對異乎尋常的人生境遇。”[1]150
怪異詭譎的夢境,是魯迅《野草》里為了展現真實自我選擇的獨特工具,其荒誕不僅成為了“樹洞”的外在保護色,同時其與現實的巨大差異也在與現實空間形成著對話。看似怪誕離奇的“游地獄”“與狗對話”等經歷遭遇是作家特意以夢境的方式呈現出來的異乎尋常的“顛倒的世界”。
簡而言之,《野草》中的這些詭譎夢境首先造就了與現實空間相左的反向世界,并通過大量結構與內容上的對話引發與揭示作家的現實關照以及內心真我,借由狂歡式的詼諧來認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