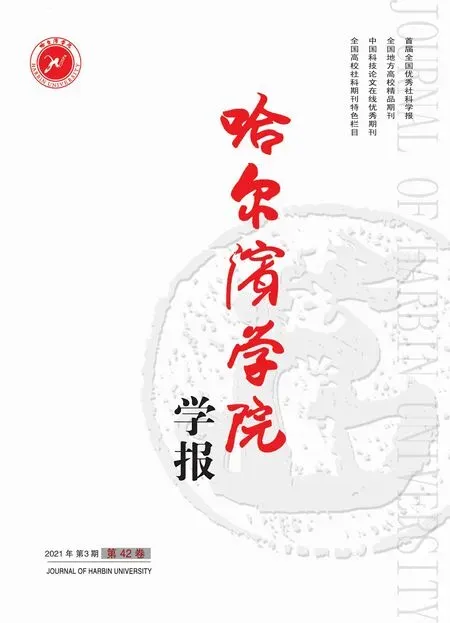《三國演義》譯介模式與中國文學典籍之“走出去”
韓名利,陳德用
(安徽科技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滁州 233100)
中國文學典籍匯聚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精髓。通過翻譯把文學典籍介紹給世界,對國家國際形象的塑造十分重要。為了提升文學典籍的國際影響力,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起相繼推出了“熊貓叢書”“大中華文庫”“經典中國出版工程”等一系列出版項目與工程,然而卻“未能取得預期效果”。[1]這與當前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并不相符。在國家形象塑造日益重要的今天,構建有效的譯介模式對于中國文學典籍真正“走出去”意義重大。
翻譯“在本質上也是一種傳播”。[2]翻譯文本產生前有選擇翻譯對象的問題,此后還有“交流、影響、接受、傳播等問題”。[3]我國文學典籍的譯介必須符合傳播規律才能真正地“走出去”。從傳播學視閾比較不同成功案例能夠為中國文學典籍的對外傳播提供寶貴經驗。本文選取《三國演義》羅慕士譯本和虞蘇美譯本為研究對象,從傳播學角度比較兩者傳播要素如何各自有機協調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總結中國文學典籍更為有效傳播的經驗與啟示。
一、拉斯韋爾“5W”傳播模式下的譯介模式
美國傳播學奠基人哈羅德·拉斯韋爾提出了“5W”傳播模式:誰—說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對誰——取得什么效果。[4]“誰”即是傳播者,依據其傳播意圖收集、加工和傳遞信息;“說什么”是指傳播內容,是傳播者根據需求收集、加工制作后發送的信息;“渠道”是諸如書籍、報紙、電視等的信息傳遞中介;“對誰”是指受眾,是傳播活動存在的前提,同時又是傳播者積極主動的接近者和反饋者;“效果”是指傳播活動的意圖或目標達到的程度。基于該模式可構建文學典籍的傳播學譯介模式,涵蓋“譯介主體”“譯介受眾”“譯介內容”“譯介渠道”和“譯介效果”五個方面。譯介主體即為文學典籍翻譯活動的贊助人及譯者等,決定著譯介的內容、策略和渠道,其被認可度也會影響受眾對譯本的選擇。譯介受眾是文學典籍對外傳播的接受者和反饋者。譯介渠道是譯作進入目標文化的傳播媒介,發行與出版當屬文學典籍“走出去”的首要媒介。依據媒介依賴理論,使用目標受眾依賴的媒介來傳播信息被受眾接受并產生作用的可能性便會相應增加。[4]可見,選擇譯介受眾所依賴的出版機構也是實現傳播效果的一個關鍵。譯介效果是文學典籍傳播意圖的實現程度。拉斯韋爾“5W”傳播模式下的譯介模式條理化地展示了傳播鏈條中五個要素之間的有機聯系,對于實現我國文學典籍的有效傳播具有指導意義。
二、《三國演義》譯介模式分析
《三國演義》是我國古典小說的扛鼎之作,蘊含著豐富的中國社會傳統文化、歷史知識和軍事謀略,目前英語世界中主要全譯本有羅慕士譯本和虞蘇美譯本。羅譯本自1991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及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以來,在英語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被認為是“學術翻譯的典范”。[5]虞譯本2014年由新加坡塔托出版公司出版,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在該譯本的基礎上于2017年9月推出英漢對照版本,稱其“必將進一步促進中國文化的傳播和推廣,展示中華文化的精髓”,標志著其成為《三國演義》標準英譯本之一。二者良好的傳播效果均來源于傳播要素間的有機協調互動。
(一)推崇中國文化的譯介主體
羅慕士是美國著名漢學家,多年來在紐約大學從事漢語教學與研究。他在訪談中提到羅譯本的實質贊助人是北京外文出版社。[6]2000年,《大中華文庫》將羅譯本《三國演義》收入其中,目的是“把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系統地介紹到全世界,既是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礎工程,是深層次的對外宣傳工作,也是對世界文化發展的重大貢獻,意義深遠、重大”。[7]可見,外文出版社出版《三國演義》的目的是對外傳播中國文化,塑造中國文明大國的形象。羅慕士翻譯《三國演義》亦并非被動接受,而是其自身選擇的結果。訪談中,他提到對中國文化帶有一種使命感,希望通過翻譯解開美國社會對中國的誤解,認識中國的真實形象。
虞譯本贊助人是美國漢學家羅納德·艾弗森。他曾多次來華,組織過故宮文物首次赴美展覽,其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及在美國的影響力可見一斑。虞譯本后記中這樣介紹譯本產生原因:“艾弗森初到中國便認識到《三國演義》在中國文化中舉足輕重的地位。發現現有《三國演義》英譯本存在缺陷,艾弗森決定資助虞蘇美重譯,希望生動地向讀者傳達原著的精彩故事和文化內核。”[8]可見,艾弗森的譯介意圖是出于對其文化價值的欣賞。譯者虞蘇美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多年從事英語教學及翻譯工作,希望通過翻譯促進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對于翻譯《三國演義》邀請的接受說明其與贊助人的譯介意圖一致。
曹明倫提出中國文學典籍的翻譯工作“主要應該由外國漢學家和學貫中西的雙語作家來做”。[9]外國漢學家對譯入語國家及其文化有相當的了解,能夠準確把握譯介受眾的閱讀習慣和興趣,與其合作是我國文學典籍海外傳播的理想模式。此外,國內出版作品往往容易被海外受眾認為帶有政治宣傳動機而受到抵觸,更應鼓勵熱愛中國文學典籍的海外個人或出版社參與我國文學典籍的海外出版和傳播,將單一的譯出模式轉變為譯出與引入多元互補的模式。
(二)閱讀層次分明的譯介受眾
羅譯本產生背景是改革開放初期,當時的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化了解較少。外文出版社選擇漢學教授羅慕士作為譯者反映其受眾定位為專業讀者。羅慕士漢語功底深厚,在教學過程中便曾節選《三國演義》章節進行翻譯并于1976年出版作為大學課本使用。在1991年譯本的“致謝”中他曾指出1976年譯本有其局限,并“期望有一天會有機會翻譯整部作品”。[10]因此,其譯介受眾定位是漢語言文字相關專業的外國學生或漢學研究者,這也決定了羅慕士在面對中西文化差異時,更愿意保留源語文化的特色,引導讀者接近源語文化。
虞譯本誕生于2014年。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人們希望更為深入地了解中國文化。艾弗森的譯介目的是以不同于當前主流譯本的翻譯方法推出新譯本,注重再現原著引人入勝的故事。因此,其目標讀者并非專業讀者而是普通讀者。故事情節發展、人物個性是吸引讀者閱讀的主要原因。虞譯本需要將源語文化主動靠近讀者,更多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流暢地再現原著精彩的故事情節及謀略智慧。
(三)恰當處理的譯介內容
《三國演義》人物眾多,故事情節錯綜復雜,且包含各種古典文化知識。傳播意圖與譯介受眾定位不同,羅慕士和虞蘇美對于譯介內容的處理策略也大為不同。羅慕士在敘述故事之外非常重視傳播漢語言文字所蘊含的中國歷史和文化,偏向異化來滿足專業讀者的閱讀需求;虞蘇美則更重視故事情節的流暢發展和譯文的可讀性,偏向歸化來迎合普通讀者。
結構上,《三國演義》原著一百二十回,羅慕士逐一忠實地對應翻譯成一百二十回。虞蘇美則將整本書分成三冊,分別在題名后加上副標題:“TheSacredOath”“TheSleepingDragon”“WelcometheTiger”,分別凸顯劉關張、諸葛亮和曹操三組人物,更突出個人主義的故事主題,迎合普通讀者的閱讀口味。
語言處理上,兩個譯本也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羅慕士以異化為主,向西方讀者展示漢語文字的獨特音形結構及蘊含的文化;虞蘇美取歸化為主,使譯文更接近西方讀者。如下例:
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第一回)
羅譯:“The surname”,the man replied,“is Zhang;given name,Fei;style,Yide.”(注釋:Fei means“to fly”;yide means“wings [assisting]virtue.”De,“virtue,”is also part of Xuande’s name.)
虞譯:“Zhang Fei is my name and I am usually called Yi-de,”replied the man.
原著中人物除姓、名之外,還有字,往往作為較為正式的稱呼。張飛作為故事的主要人物之一,其字的意義對于人物形象的樹立有著重要作用。兩個譯本都保留了其字“翼德”的讀音,羅慕士在注釋中用“style”對應“字”的涵義,添加注釋“wings”“virtue”直譯出“翼”“德”的意義,增譯“assisting”將“翼德”涵義與劉備的字“德”的意義聯系起來,幫助讀者理解中國古代獨特的人名稱謂文化及張、劉二人的臣主輔助關系。直譯加注的翻譯方法能夠準確地傳達漢字文化,體現其對專業讀者接受需求的考量。虞蘇美則采用文內意譯的方式,用“I am usually called”使讀者了解這是中國古代一種稱呼方式的同時保證其能夠流暢地理解故事的發展。
翻譯策略的選擇受到傳播意圖和受眾定位的影響,必須采取相對應的策略,才能保證文學典籍“走出去”的理想效果。與主流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文化影響力尚處于弱勢。在文學典籍的翻譯過程中,我們既需要偏向異化的翻譯也需要偏向歸化的翻譯,二者并行更有利于我國文學典籍“走出去”。
(四)受眾影響力強的譯介渠道
羅譯本的出版機構為加州大學出版社。該出版社是美國最早成立的一批大學出版社之一,恪守嚴謹的學術規范,因而出版書籍在世界范圍內具有深遠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力。《紐約時報》評價道:“亞洲研究、文學批評和社會學研究是加州大學出版社的強項。”[11]羅譯本在專業讀者中的廣泛接受離不開該出版社成熟的市場運作和良好學術聲譽。虞譯本由新加坡塔托出版公司出版。其秉承“溝通東方和西方”的經營理念,旨在向西方讀者傳播東方文化、歷史及藝術,進而促進雙方的相互理解。虞譯本在普通讀者中的廣泛接受離不開該出版社在西方讀者中的影響。
汪寶榮指出,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譯作可滿足專業讀者的閱讀需求,大眾讀者則更青睞商業出版社出版的書。[12]羅譯本和虞譯本的成功因素之一便是其譯介渠道的恰當選擇。海外一流出版社熟悉不同層次海外讀者的閱讀需求和習慣,且其出版發行的英譯本有其潛在的讀者群,更具針對性。我國文學典籍的海外傳播可采取中外合作模式或“借帆出海”實現中國文學典籍的有效傳播。
(五)在受眾中的成功譯介效果
羅譯本出版后贏得了西方專業學者的高度評價。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魏斐德評價道:“羅慕士對中國最重要的歷史演義的優雅有力的翻譯恰當地傳達了原作史詩般的描寫。”芝加哥大學教授余國藩認為,“羅慕士譯本是非凡超群、無可挑剔的學術精品,在將來很多年中都會為西方讀者帶來樂趣。”[13]漢學家魏安評價羅譯本“是一項罕有的偉大成就,它既是仔細嚴謹的學術性翻譯的典范,也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小說”。[14]上述評論是羅譯本在海外專業讀者中取得成功傳播的有力證明。
作為全球領先的網上書店,亞馬遜網站具有數量可觀的讀者書評,能夠直接體現譯本在海外普通讀者中的譯介效果。該網站上虞譯本得到了海外普通讀者的廣泛贊許。“可讀性強”“流暢”“引人入勝”是評論中大量出現的字眼。一些讀者贊嘆中國古代非凡的軍事謀略,也有些讀者深刻地認識了中國社會的集體主義思想,并進而批判性地反思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可見,虞譯本不僅向世界介紹了中國文學,同時也在加深普通讀者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三、對中國文學典籍“走出去”的啟示
《三國演義》羅慕士譯本和虞蘇美譯本的成功傳播離不開對傳播學各要素的正確判斷和協調把控。兩者的成功經驗表明:第一,我國文學典籍的譯介主體除政府外宣機構推出、西方漢學家翻譯的形式,應鼓勵推崇中國文化的西方個人或出版社資助本土譯者進行譯介,在準確把握海外讀者的閱讀興趣和需求的同時準確傳達中國文化;第二,需明確譯介受眾,充分了解其閱讀習慣和接受能力,相應地選擇翻譯策略;第三,譯介渠道應選擇在目標受眾中有影響力的西方學術或商業出版社,借助其成熟的傳播模式和豐富的市場資源,吸引海外專家與目標受眾的關注,拓寬推介和銷售渠道。
文學典籍對于塑造我國文明大國的形象意義重大,其英譯必須嚴謹對待。只有把文學典籍英譯看作一個系統傳播工程,對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受眾、譯介渠道做出正確判斷,建立各個傳播環節高效協調的運作機制,才能實現理想的傳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