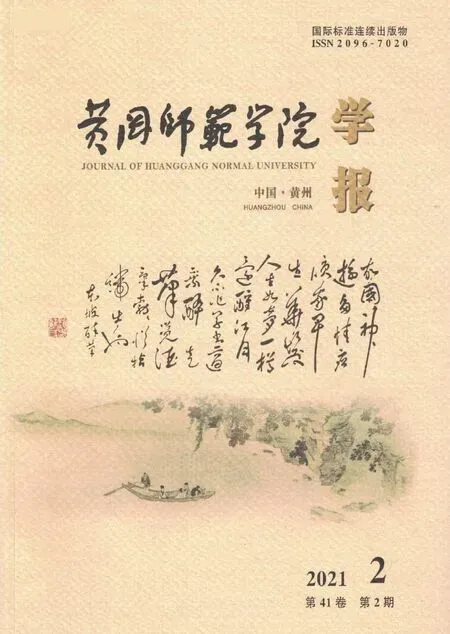網絡“群體標簽”的類型特征與生成機制探究
胡沈明,周韓薇
(江西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研究緣起
伴隨著互聯網的蓬勃發展,新媒體技術正朝著縱深維度日漸成熟,惠及著越來越多的民眾。作為時下最為重要的信息互通工具,新媒體搭建交流平臺,為廣大用戶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態度創設機遇窗口,塑造出各種新興媒體形態,勾勒出了遠超傳統媒體時期的傳播速度和輿論控制難度的全新傳播生態。
現如今,數字通訊技術生成了手機、平板電腦、個人化手表等多種訊息接收終端,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使用這些移動終端產品來實現信息的實時發布、接收和互動。整個社會的信息流通逐步高效化,“話語權”已不再是少數高階群體所擁有的稀缺資源,線上線下的信息傳播正逐步形成一種“對等傳播”的話語生態。與此同時,傳播內容也開始呈現出“碎片化”特征,多數信息都以凝練的話語方式來呈現,“詞語”以及視覺化文本成為主要意義承載工具。
當下,越來越多的輿論事件、人物被賦予“標簽”,出現在大眾視閾,以簡短、易懂的方式讓更多的人接受。互聯網使得網絡用戶群體習慣于信息易得,由此用戶不易主動思索探究,而是被動接受易懂的信息,獲得知識增幅。新興媒體平臺以及經營者察覺到這一問題,感知到那些表面、簡短但卻不失份量的詞匯往往比那些長篇大論的語句段落來得更能抓取受眾眼球。因此,無論是在新聞報道還是在輿論中,不少傳媒機構平臺極力生產標簽。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網絡用戶也開始紛紛加入“群體標簽”詞匯創作和傳播的隊列,他們將社會上的大小事件、典型人物以詞語概括,形成標簽。群體標簽開始在各類新媒體平臺上層出不窮,內容呈現出多維度、多層次的特點。而后,“詞”開始成為一種媒體,逐步演化,生成標簽,獨具傳播力。“詞語”不僅能解釋一個問題,還能反映一種社會現象,縱而形成一種傳播形態,比如近期走火的“打工人”“尾款人”。這類網絡流行語,它們呈現的是一種網絡文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時下的社會現狀及問題。研究現網絡群體標簽,不僅可理解社會現狀,更能發掘社會思維方式和社會問題。
二、“群體標簽”賦予主體:從他人到自我
標簽原指“貼在或系在物品上,標明品名、用途、價格等的紙片”[1],它的存在是對所指對象的表現、特點等進行概括性描述,以便受眾記憶。
梳理過去熱點人物的“標簽”,大部分都構建于“刻板印象”之上,且通常會被泛化成特殊群體的標簽。也就是說,現代社會上的多數標簽所指向的客體已不再局限于個體范疇,而是拓展至一個群體。通過“群體標簽”去表征輿論,引發關乎事件內容的探討,以及對牽涉主體行為表現的分析,從而實現“貼標者”的認知、態度與情感傳達。
值得關注的是,新媒體時代“群體標簽”的使用與意義建構已發生了較大變化。在早期互聯網剛普及時,多數網民的“話語權”被重新建構,由此在網絡社會上掀起了一幕幕“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進行“貼標”的逆向泛標簽化現象。這是對之前傳統市民社會僅能由“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進行標簽化行動的一種顛覆,也是社會話語逐漸發展至“平等互動”的體現。微博、自媒體等社交媒體平臺的涌現,為廣大網民提供了更為寬泛的標簽創作平臺,網絡群體標簽在生成層面開始折射出由此前的“他人賦予標簽”演化為“自我賦予標簽”的趨勢。
(一)他人賦予:標簽污名化與逆向泛標簽化 在傳統理論場域下,群體標簽主要是強者對弱者進行單向性賦予,即擁有一定社會資本(權力、資產、話語等)的社會精英階層對普通階層貼標簽,以表達對標簽人物或現象的認知與態度,部分標簽甚至帶有一絲歧視色彩。而在互聯網普及后,群體標簽的賦予邏輯開始呈“異樣”演變,標簽創作主體的范圍在不斷擴大,逆向泛標簽化態勢逐步形成。
1.強者對弱者的定義。當個人的行為流露出一絲“越軌”傾向時,周邊群體將會利用標簽對該人物及其行為進行概括、解釋,且所用詞匯常常帶有“社會減等”色彩。這一現象與社會學家戈夫曼所提出的“污名”概念不謀而合,該理論認為,“污名”即被冠以“受損的身份,并將污名歸類于社會歧視標簽”[2]。例如“盲流”這一群體標簽,它是中國社會進行現代化建設中的時代性產物。在現代化進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向城市遷移,給“遷入城市”帶來一系列關乎人口激增與環境壓力的社會問題,當地居民因對此產生反感而給這些移居群體貼上“盲流”標簽,使其處于邊緣化地位,以此來排遣心中不滿。在該過程中,作為強勢群體存在的當地居民對離鄉的“弱勢群體”所進行的標簽化行為,會讓“盲流”群體因礙于生存壓力而被迫選擇“失聲”,不過這種“失聲”大多是暫時性的,他們的忍耐情緒積累了一段時間后,會試圖在“微觀領域”做出反抗行為來發泄怨憤,例如在各自小家庭中爆發一系列“越軌行為”,導致家中妻兒在社會、家庭的雙重去權,這間接反映出了前期的標簽化行為所暗含的弊端。
2.對越軌群體的區隔。對他者與我的身份進行區隔也是群體標簽的使用動機之一,如對班級的消極群體的“標簽化”賦予行為。當一個班級中那些擾亂班級秩序的同學被賦予“壞學生”標簽,也就形成了他們與普通學生之間的“身份區隔”。那些被貼以“壞學生”標簽的群體會在不知不覺中,用外界對自身態度行為的評價來暗示自我身份,同時實現自我“越軌”預言,形成群體認同。可以明確的是,群體認同在一定程度上將會緩解自身越軌行動而產生的心理負罪感,而這有可能導致負面行為的強化,這也就說明了“貼標簽”會阻礙教師對班級中這類“消極學生群體”的教育與規訓。
3.逆向標簽的賦予。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話語權力”已逐步下放至普通民眾手中,這使得群體標簽的賦予邏輯向“泛逆向化”態勢演變,不同階級間也呈現出“雙向塑構”的貼標關系。如大眾所熟知的“富二代”這類群體標簽,它們算是“逆向泛標簽化”的典型。在社會分層的背景下,貧富狀態體現出一定的“銜接性”,即上一代人的社會資本狀況會直接體現在下一代身上,階層固化逐之形成。一些社會底層群眾因敵視那些行為乖張的富二代群體但又無奈于現狀,于是試圖通過利用負面色彩的話語在網絡虛擬世界中表達“反抗”,塑構出“富二代”等概念詞匯來實現我與富二代群體的不同與分隔。
(二)自我賦予:標簽中性 新技術的蓬勃發展衍生出了各類社交媒體平臺,它們的存在讓用戶間的交流更為便捷、通暢。現如今愈來愈多的普通公眾能夠借助于社交媒體來表達對社會或自我的認識與情感,并已深深習慣于在“虛擬境況”中進行精神建構與自我實現的生活狀態。在這一背景下,“群體標簽”的意蘊變得更加泛化,它不僅僅停留于最初的借“我對他人的印象”用來區隔他者而使用,現在被貼標者用以進行“自我賦予”行為,以滿足自身某種情感的彌補與宣泄。
近期走紅的“打工人”,正是標簽自我賦予的典型案例。“打工人”一詞最早其實也是作為形容弱勢群體的邊緣身份存在,指代基層務工者這一群體,而今天網絡上對這一身份標簽的使用,更多的是網絡用戶集體用來暗示自我“打工”身份來進行現實職場焦慮的釋放。在思想涌動匯通的當下,不少公眾都開始意識到所謂“雞湯成功學”理論是資本家忽悠普羅大眾的外衣,無論“金領”或“農民工”,大家其實都是打工仔,都在為謀生而勞碌著。這一話題因引起“三低”群體的情感共鳴被廣泛討論,而后“打工人”這一帶有黑色幽默的標簽流行語在社交媒體上生成。網民將其賦予自我,實現身份定位,一方面用以自嘲來舒緩壓力,另一方面也是聊表自己迎難而上的態度來激勵自我。
三、“群體標簽”的使用場景:從排斥到展示
在社會交往越來越密切之時,“群體標簽”使用場景也越來越寬泛,從早期的社會排斥性使用到如今的自我展示,“群體標簽”已逐漸發展成為一種信息傳播和社會心態展現的載體,體現出一種言在詞外的意蘊。
(一)社會排斥型標簽 早期的群體標簽生成具有區隔的特性。將不同的社會階層區分開來,是網絡話語強勢群體為了實現身份區隔而對弱勢群體進行消極偏向標簽“單向”賦予的手段。而社交媒體的興起,讓很多社會底層群眾也有了表達對強勢群體的排斥和對社會分層固化現狀的看法的渠道。
常見的排斥有:經濟排斥,如“土豪”“暴發戶”“官二代”“富二代”等;道德排斥,如“廣場舞大媽”“貪官”等;階層排斥,如“盲流”“保安”等;能力排斥,如“女司機”“月光族”等。單從這些詞匯的表層含義就可以看出標簽創作主體對“被貼標”客體的消極話語偏向。這些標簽用詞往往是依據客體在年齡、社會地位、行為層面等體現的特點來構建,因此具備一定的特指性。這類標簽詞因新銳、凝練而常被應用于新聞領域,來奪取受眾眼球。
拿“土豪”這一群體標簽來分析,曾在2013年,一條有關“土豪大媽背旅行袋裝金條買賓利豪車”的微博被發出,原文為“見過用黃金買房的,沒見過馱一包黃金來買車的,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黃金大媽嗎?”這條消息一經傳播迅速引發熱議,這其中所生成的群體標簽詞即為“土豪”。該詞原指封建社會中以土地擁有量為財富來源的大地主階級,將其作為一個消極標簽,貼向現代社會中那類同原大地主階級資源擁有程度相似,但審美普遍不高,消費特點物質化的群體,能夠言簡意賅地揭示出這類群體的炫耀式消費行為將會帶來侵占公共空間,損害公眾利益的后果。但需引起注意的是,負面偏向性標簽的廣泛傳播,可能會導致受眾對標簽群體的認知形成刻板印象,并逐漸固化。
(二)行為倡導型標簽 行為倡導型標簽即詞匯屬積極偏向色彩。所謂積極偏向,可以理解為對所指對象本身或其行為飽含贊揚態度,并予以肯定與期待。時代在變,但引領社會好風尚、弘揚社會主旋律永遠都是每個時代的核心大主題,而我們說時代發展的好壞與否,取決于這個時代中的人,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是否起始于善,又是否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和推動社會發展,這些都是每個時代下的人所應該關注的公共性問題。而社會媒體所承擔的職責,就是引領大眾為社會建設做出行動,精神面貌向善看齊。這一職責目標的實現離不開社會的正面宣傳,正面宣傳的重要性在于可以通過語言藝術的魅力面向整個社會去傳播那些蘊含積極力量的人物事跡,來引起其他社會成員的贊同與行動附和,最終推動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
通過運用標簽化思維進行多元化正面報道宣傳,更便于受眾理解和記憶,能使得宣傳效果放至最大。如“最美鄉村教師”“最美司機”“十佳好軍嫂”“雷鋒”“最美逆行者”等,這些贊揚性詞匯在這種積極偏向的領域帶來的群體認知是正功能性的,通過將這些榮譽標簽賦予社會杰出群體的同時,更是在潛移默化的激發出其他群眾對于該份榮譽的向往,并轉化為行動力,自覺走進推動社會發展的建設之中。
(三)心態展現型標簽 群體標簽的產生基于人們對社會現狀的感知和剖析,因此標簽詞能反映出此時人們的心理狀態和行為,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對現實問題和發展做出一個探測和診斷。
近些年,一系列用以展現自我社會心態的標簽詞匯在網絡社交媒體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例如“社畜”“打工人”“尾款人”“996”“當代女大學生”“考研狗”“體制狗”等等,和原先的“他人賦予”式標簽有所不同,這些心態展現型標簽大多都是標簽創作主體進行的“自我賦予”行為的產物,這一演變體現出了這個時代下主流互聯網語境所發生的微妙變化。以“打工人”為例,2020年9月23日,b站主播“帶籃子”在其個人專區發布了多條以“早安,打工人”為主題的系列短視頻,其經典語錄“朋友們累嗎,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有錢人的,早安,打工人!”在短期間迅速走紅,此后,“打工人”被越來越多的青年網絡群體借以自喻而爆火于各大網絡媒體平臺。從低線勞動者到金領群體,他們都紛紛借用這一具有黑色幽默的標簽詞匯予以自嘲,嘲笑自己都是為老板打工的賺錢機器,也是一種苦中作樂的表現。
標簽“自我賦予”可以被認為是職場人士找尋輕松的出口,但同時也是職場群體在社會壓力下所形成的退縮式反抗現象。可以明晰的是,現代主流互聯網語境開始轉向該類用以自嘲并同時形成自我激勵的這樣一種話語模式,這對于個體進行自我社會心態的展現與安撫有著極為強大的作用,從長遠來看,這有利于社會建設更好的發展。
四、“群體標簽”的生成機制:個體、群體和平臺三方共同推廣
群體標簽式傳播是一種較為典型的互聯網傳播語境現象,它是網絡技術發展推動的產物,是普通群眾展現自我心態的便捷途徑。當然,網絡時代之前,標簽化思維方式就已經形成,如早期《羊城晚報》上所曝光的“賣花姑娘”事件等。只是在當時,標簽化傳播并未形成氣候,且大多都是主流群體對他人賦予標簽的形式出現,普通群體只能被動接受,無法參與標簽塑構,落入“暫時性失語”狀態。直到新媒體技術逐漸盛行之后,大眾社會交往方式和空間得以拓展,普通社會群體擁有了話語輸出通道,“標簽互構”式傳播才得以形成規模。現如今,群體標簽被廣泛使用,這背后的生成動機可從個體、群體、平臺三個層面展開分析。
(一)個人排斥與情感反抗 在上文的標簽類型中,有提到過社會身份排斥型的標簽,如“盲流” “富二代”等,它們大多帶有消極色彩的標簽,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貼標者對于標簽對象的“排斥”情感。通過把握對象特點去找尋一個恰當的詞語對其進行貼標行為,以實現身份識別作用,這通常是標簽創作主體為了將標簽對象與自身差異開,以實現區隔他者,展現自身價值取向的獨立性。該行為動機實際上是源于個人對于標簽對象的刻板印象與認知偏見,當標簽對象的一些語言或行為帶有“越軌”傾向時,就會引起貼標群體的反感,不愿與之牽涉任何關系,由于在現實中難以擺脫,而試圖在線上采取標簽化思維實現自身與“越軌群體”的身份區隔,這既能夠表達對越軌群體的排斥心理,又維護了自身的純潔性。
群體標簽還是標簽主體個人釋放對于社會現狀反抗情感。在美國作家克萊·舍基筆下,未來社會是濕的。他認為,目前或未來社會的組織方式將突破“干性社會”關系,人與人之間將會憑借一種微妙的關系相互吸引、組合、結合、嫁接, 相互分享、協同合作[3]。“濕性社會”是一個以情感黏合的社會,這一特點在青年群體的網絡標簽互貼行為中得到詮釋。新媒體技術為越來越多的年輕群體提供了釋放個人情感的平臺,一些關乎社會心態的討論總能在短期內發展至高潮。比如上文所提及的“打工人”標簽,它是當下青年群體對于社會工作壓力表示反抗情緒的一次集體釋放。該詞表面上似乎只是貼標者對自身工作現狀的自嘲和焦慮排遣,在更深層次意義上還有著試圖表達對當下“內卷化”工作模式的抗爭情感,“在社會階層分化和利益博弈關系的轉變這一過程中生成,弱勢群體普遍被剝奪感也同時不斷強化”[4],進而形成對相關標簽的認同。
(二)群體認同 社會結構因素是“群體標簽”生成的核心動力機制。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格局呈現出一種分層并逐步固化的狀態,家中長輩在財力、社會資源等方面的優劣狀況會順承表現在后輩身上,群體的特定“圈層”伴之出現。那些處于較高社會地位的圈層群體也開始漸漸對其他群體產生排外性,但同時,社會普通群眾也在通過在新媒體平臺表達對社會資源配資和分層的看法。其言論文本中常常會涉及各類“群體標簽”詞匯,通過利用這種標簽化思維去代指他人,進行一個意見討論的行為,往往會形成一種對“非我方”群體的概化,而后社會群體在線上線下逐步被分化成“我群”與“他群”[5]態勢。
這一態勢的顯現主要還是歸于社會分層固化因素。拿“富二代”來說,“它原指代繼承家巨額財富的富家子女”,有“知識成功型”“艱苦奮斗型”“紈绔子弟型”三種。而該詞在網絡社會語境中被應用最多的類型為“紈绔子弟型”,通常由那些普通人用該標簽來代指那些坐擁各種先天優勢資本,行為乖張的紈绔子弟。在資源利益分配不平衡、階層分化加劇的社會背景下,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群體的社會心態開始滋生不公平感,認為自己在生活各方面都難以與那些“強勢群體”平等競爭,從而形成結構性“怨恨”。由于網絡空間的“匿名性”,網民可以拋開社會身份的約束來排遣消極心理,于是在線上以貼標簽的方式將“強勢群體”區隔為與“我群”不同的“他群”,一方面用以表達“我群”對“他群”的不滿和對社會不平等的反抗傾情緒,另一方面也使得“我群”產生情感共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個人心態的不平衡感。
(三)平臺追逐流量 新詞語本身自帶流量,標簽本身就是媒體,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向“流量經濟”傾斜。可以看到,不只是社會群眾在網絡平臺的自發討論,還有很多新媒體也同樣在使用群體標簽來進行新聞或信息的報道。在如今的“眼球經濟”時代下,不論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它們都開始學會從繁瑣的新聞材料中挑選出最博得關注的內容,在新聞文本中以新銳詞匯來凸顯,以此適應眼球經濟的生存法則。
在新媒體時代,受眾享受著網絡紅利帶來的信息便捷化獲取,并愈發開始習慣“碎片信息”的快餐式閱讀方式,不少自媒體都紛紛注意到了這一點。為了追逐流量,它們瘋狂采取標簽化思維來迎合受眾心理,有時為了占據優勢,甚至還對標簽進行妖魔化處理,再賦予給熱點人物或事件,以博得受眾關注。可以說當下的部分妖魔化標簽是資本競爭下的操縱產物,各類媒體平臺為了追求所謂時效性,在沒有對報道事實進行全面、客觀的核查就對其貼標簽并進行負面解讀,這往往會導致新聞失實,甚至帶偏整個社會輿論的走向。
五、結語
社交媒體平臺給予網絡用戶提供了暢通的表達渠道,推動“詞語”媒體化,但同時,社會信任風險危機也伴之出現。媒體、受眾在網絡平臺對“群體標簽”的不恰當、過度化使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加速了當下的社會共識的瓦解,增設了“刻板印象”的負面影響。
可以明確的是,在網絡社會中,無論是群體標簽還是媒體平臺的生存,它都是基于對抗和社會撕裂這樣一種邏輯產生。貼標者在對部分群體進行標簽化處理時,實際上是在制造差異、表達對抗情緒,從而形成參與感。當群體標簽生成后,則形成了“二元對立”,這時新媒體平臺就為對立后所誘發的群體間反抗行為提供了活動空間,從這一角度看,網絡群體標簽在某種意義上還是資本操縱的產物,它并非是對輿論本身的操縱,而是直接操縱人們的行為甚至是社會心態,而資本操控、商業運行等因素實際上就在不知不覺中對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產生了一定影響,當前平臺經濟和技術經濟所引發的社會撕裂感,提示著社會需要嚴格對它產生關注并進行適當的政策引導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