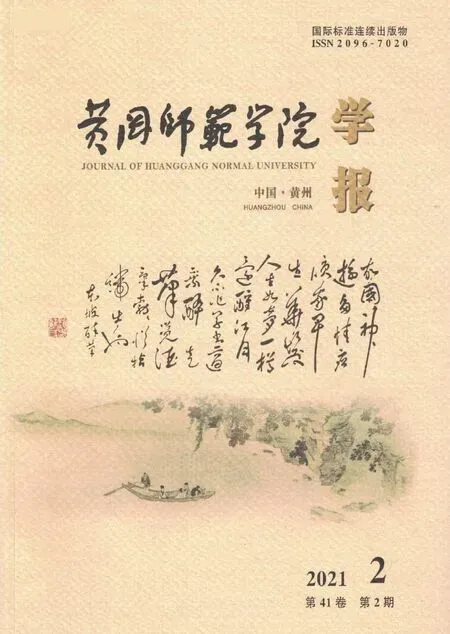大思政視角下世界史教學課堂模式研究
齊子通
(中南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近年來“大思政”理念備受關注,對高校教學而言,要求不再局限于馬克思主義學院所提供的公共思政課程。其他專業教師也要積極樹立思政意識,并貫穿到專業課程教學中,時刻牢記“培養什么人、如何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根本問題,在潛移默化中積極引導學生。歷史教育與思政工作關系密切,大學生是否擁有正確的歷史觀直接關系到高校思政的工作成效,而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又與國家意識形態政治安全息息相關。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與現實的關系有大量重要闡述,視野宏大,發出振聾發聵的時代強音。在當前中國社會,歷史虛無主義現象時常發生,必須把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來看待。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兩會”期間指出,“大思政課”我們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現實結合起來。由于西方話語體系的長期影響,世界史教材編撰、教學多少存在某些問題,世界史教學長期面臨如何克服西方中心論的現實困境,高校不少學生對西方歷史文化存在種種誤解。在這種背景下,高校世界史教學積極響應“大思政” 理念,探索新的課堂教學模式,也就成為新時代的迫切要求。然而,筆者目力所見,大思政理念與世界史相結合的課堂教學研究僅停留在中學階段,高校世界史教學融入大思政理念的研究所見寥寥。因此,大思政視角下世界史教學改革與課堂模式的探討具有重要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今結合自身教學經驗,試對此問題作一探討,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西方中心論理論批判與課堂教學相結合
人類對“世界”的認識隨著人類活動范圍擴大而不斷變化。古代歷史學家所記錄的歷史,往往是他們當時所認識的“世界”范圍,希羅多德所著《歷史》涉及地中海地區、兩河流域、波斯、北非埃及等地,司馬遷的《史記》記錄范圍則東起朝鮮,西至安息。從絲綢之路到人類地理大發現,人類對“世界”的認識能力不斷提升。中世紀歐洲史學深受基督神學的影響,伏爾泰《風教通義》廢洪水創世之說。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歐洲思想家對中國文明保持崇拜心理。斯塔夫里阿諾斯寫道:“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國由于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業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范文明。”[1]當然,啟蒙時代的歐洲思想界需要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以批判歐洲封建社會。當時的中國并非他們描述的那樣完美,相比正在崛起的歐洲,中國國勢已呈日趨下降之勢。進入19 世紀,隨著歐洲工業化和殖民擴張的深入展開,歐洲人的觀念和態度發生巨大變化,歐洲人對亞洲特別是中國文明的崇拜也是從這個時期發生逆轉的[2]。“歐洲中心論”思想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構成了西方強勢的話語體系,并影響至今。
要而言之,歐洲中心論者認為歐洲是世界歷史發展中心,他們用歐洲的價值觀念衡量世界的一切。一大批思想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等在各自的學科領域中,成為“歐洲中心論”的鼓吹者和倡導者。黑格爾《歷史哲學》認為只有歐洲和歐洲民族才是世界歷史的中心[3]。這種史觀的嚴重后果就是很容易將世界史等同歐洲史,貶低其他人類文明及其貢獻。此后,倡導實證主義史學的朗克并沒有實事求是。他的《世界歷史》甚至無視東歐的存在,認為世界的發展是以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為主角。20世紀之初,劍橋三史都是堅持歐洲中心論的基本觀點。所以,無論地理知識如何擴大,歷史文獻如何積累和傳播,都不能保證近代西方對于世界史的研究具有全面的世界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人的文明自信受到巨大打擊,出現了一批反思歐洲文明的先行者和相關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有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湯因比《歷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與民族獨立運動空前高漲,在史學領域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有了進一步發展。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并非歐洲一隅所推動,而是整個世界體系互動而形成的結果[4]。一批學者嘗試以“全球史”視角超越“歐洲中心論”,提出要從全球的視角對世界各地區文明的產生和發展進行考察,國際學術界開始越來越注重歐洲以外其他地區與文明在世界近代史道路中的地位。 但遺憾的是,目前所見的世界史,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即使備受國內推崇的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巴勒克拉夫認為它依然是以西方為中心,是“經過掩飾的西方中心論”[5]馬克垚先生指出,二戰后出現了眾多的世界史編撰體系。由于對世界歷史的較成熟的認知體系還未產生, 這些世界史著述在開創之初都面臨如何克服歐洲中心論的問題。許多學者批評歐洲中心論, 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史, 可是仍未獲得顯著成績。因為我們的世界史體系是由西方學者建立的, 是根據歐洲經驗得出的, 其中有客觀的一面, 也有歐洲中心論的一面。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史學, 是學習西方史學后建立的, 缺乏從自己的歷史出發建立的理論。現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種準世界史[6]。趙汀陽先生甚至認為,世界史是一個可疑的概念,是一種虛構性誤導,是歐洲擴張史冒充世界史,是至今流行的所謂世界史的模板[7]。
而梳理歷史,結合現實,不難發現,歷史與現實從來不是孤立而是密切關聯,我們當下很多習以為常的事情,背后往往有深厚的歷史背景。西方中心論本質是西方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設計的很多“概念”是維持西方話語體系的組成部分,而西方某些國家長期對非西方世界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借以維持其世界霸權,已是不爭的事實。西方中心論潛移默化的影響仍然存在。當然,形勢在發生積極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兩會”上指出,年輕人心態在變,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
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雷海宗先生早在1928年就對西方中心論進行了系統揭露,特別是對韋爾斯著《世界史綱》有深刻批判[8]。雷海宗先生指出,韋爾斯《世界史綱》習慣以歐洲為主體,囿于種族和階級成見,不能以世界為一全局,因而也就不能如實地考察世界的歷史,只談雅典的價值影響而忽視其他文明。韋爾斯《世界史綱》共26 章,西洋史就占了16 章。雷海宗先生還指出,韋爾斯以隨意選材、牽強附會、掩抹史實等手段貶低其他文明,最后告誡學人 “研究歷史時,最好讀別的書,對韋爾斯的書愈少過問愈好。”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化盛行時期,雷海宗先生能對“歐洲中心論”作出如此深刻批評,尤為難能可貴。但遺憾的是,韋爾斯《世界史綱》的影響仍然存在。2001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舊譯本, 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梁思成譯本, 2008年上海三聯書店則出版了顏世俊、劉仲達的譯本。由此可見,西方中心論理論批判任重道遠,世界史教學課程思政亟須高度重視起來。為此,世界史教學應注意從理論高度對西方中心論批判,從而減少其消極負面影響。筆者講授《世界古代史》這門課時,會在緒論部分先講授對世界史的理論認識;西方中心論理論產生背景、影響及其批判;學習世界史的態度等內容。這樣可以自然地將思政理念嵌入課堂,同時也有助于學生對世界史的基礎學習,開拓學生的學術視野,學生反饋認為很有收獲,如此一來,思政理念融入世界史課堂得以實現。雖然世界史教學應該高度重視思政思想的融入,但不能簡單化為思政而思政,將思政變成口號,出現形式主義。否則會容易引起學生的反感,使學生產生排斥心理,從而影響學生的接受程度,最終反而削弱了課堂思政建設的初衷。為此,課程思政應高度重視學術性,從學術理性的角度向學生傳遞思想。
二、西方中心論批判意識與具體史實相結合
對世界史課程思政與課堂改革而言,僅僅在緒論部分對西方中心論進行理論批判是遠遠不夠的。授課老師應該切實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認識到高等院校特別是民族院校承擔的特殊使命,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深刻認識到歷史教育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中的重要內容。為此,世界史教師還應當將批判西方中心論的思想意識貫串于整個課堂教學,從學術理性視角,與具體史實相結合,從而厘清學生對西方歷史文化的盲目崇拜。例如,筆者在課堂上調研發現,不少學生對希臘歷史文化存在很多誤解,這種誤解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由于近代以來的特殊原因,國人對希臘文化過度崇拜,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指出:“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9]改革開放以來,“言必稱希臘”的風氣一度抬頭,不少學生受此影響。事實上,很多希臘歷史文化被過度美化了。
例如,關于波希戰爭的直接原因,一般認為是雅典人援助小亞細亞伊奧尼亞人起義,而波斯人借機報復。筆者曾在課堂調研學生對希波戰爭爆發原因的認識,幾乎大部分同學認為希臘是正義一方。很多歷史讀物與傳媒信息也幾乎都是對希臘戰勝波斯的歌頌和贊美。客觀地說,波希戰爭的起因,確實與波斯對外擴張有關,但我們應鼓勵學生轉化觀察視角,以看到另一番歷史景觀。事實上,包括伊奧尼亞人在內的小亞細亞希臘人在起義之前,已被波斯人統治了近半個世紀。公元前546年,波斯征服呂底亞,米利都見風使舵,在其他小亞細亞希臘城邦猶疑觀望之際,率先主動歸服波斯開國君主居魯士。公元前500年,正是米利都首倡發動了反波斯起義,雅典人支援小亞細亞希臘人的暴動。波斯早已在小亞細亞設置行省,從波斯人的視角看來,雅典人的行為是對波斯內部事務的干涉和對波斯邊疆區域的襲掠,對于波斯而言,這是不可容忍的。
筆者在課堂上曾讓學生對同時期的希臘與戰國進行比較,很多學生認為,希臘經濟形態是商品經濟,戰國則是自然經濟。學生之所以產生這種誤解,折射出社會輿論風氣的重大問題。由于西方諸國海外殖民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經濟領域里占主導地位,他們認為古代希臘人的移民,有如近代西歐的海外移民一樣, 主要目的是為了商業利益,在海外建立商業據點和開辟貿易市場。近代以來,很多國人接受了西方的這種觀點,并影響至今。事實上,隨著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深入,西方絕大多數學者已不贊同上述觀點,以M·菲 尼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認為希臘農業始終占主導地位。早期移民的主要目的不在商業,而在尋找土地和新居住地,“ 移民” 一詞在希臘語中為“Aπσικι‘δ”其中“ Aπσ”為離開之意。“σικι‘δ”為“居住地”。拉丁語中,“colonia”(移民)源于“Colo”(耕種土地)和“colonus”(耕地的人)。顯然,從希臘語、拉丁語等語言詞源角度分析,“移民”具有濃厚的農業色彩。縱觀古代歷史,農業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通用的世界史教材也認為,近代英國資本主義發展也最早滲透在農業領域。而戰國時期,中國農業高度發達,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對春秋戰國時期發達的商品經濟有詳細論述,認為“論規模,論總人口,論都市數字,(春秋戰國)中國古代的都市發展是罕有比倫的”[10]。
事實上,希臘文明大量吸收了西亞北非的文化成果,這方面的考古及文獻證據非常多。早期希臘哲學家幾乎全都來自小亞細亞。希羅多德《歷史》記載,埃及的太陽歷比希臘的歷法準確;希臘字母是從腓尼基人那里學來的;希臘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倫人發明。在希臘神話中,烏拉諾斯是第一代神,克羅諾斯是第二代神,宙斯是第三代神,他們之間的權力斗爭故事原型來自西亞的庫馬比神話故事,《荷馬史詩》不少故事情節也來自西亞《吉爾伽美什》《阿特拉哈西斯》等早史詩。在講授希臘史時,筆者常向學生介紹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或者推薦相關研究專著。例如,我曾給學生推薦阮煒所著《另一個希臘》。阮煒曾留學曼徹斯特大學、愛丁堡大學,也是哈佛大學與劍橋大學的訪問學者,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深圳大學、湖南師范大學,西學積累豐厚。很多學生讀后都紛紛表示深受啟發,打破了以往對希臘歷史文化的固化認識。
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先哲對雅典“民主”皆持批判態度。希臘城邦民主的背后有著極為殘酷的一面。以雅典為例,雅典城邦的奴隸毫無權利,遭受種種剝削壓迫,雅典對其他城邦特別是提洛同盟的盟邦極端專橫殘暴,毫無民主可言。弱小城邦彌羅斯曾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保持中立,雅典民主投票決定對彌羅斯島居民進行滅族性大屠殺。類似由民粹極端主義所產生的“罪惡”“悲劇”還有很多。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竟因“敗壞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被以“民主”的形式處死。不久之后,主張處死蘇格拉底的民主派領袖美勒托本人又被其他派系以“民主”的形式處以極刑。雅典式民主最終導致了社會秩序混亂,也弱化了國家力量。對希臘世界來說,希臘城邦之間混戰只是城邦民主擴大化的另一種表現,其結果就是希臘城邦世界陷入失序狀態,最終元氣大傷,被崛起的馬其頓所滅。
隨著城邦危機加深,以伊索克拉底、色諾芬人極端仇視波斯,將非希臘人描述為野蠻、缺乏理性、天生奴性、屈從于專制統治和等級制,將希臘人描述為文明、理性、自由,由此產生“泛希臘主義”。 色諾芬的“泛希臘主義”不是符合客觀歷史的文化思想,而是希臘城邦危機背景下的一種政治現實需要。但18世紀后期建立起來的古典學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古典希臘的諸多理想化元素,他們在研究中將希臘完美化,錯誤地將色諾芬、伊索克拉底等的褊狹言論成為論證西方具有自由民主傳統的證據,并把東方文明描述成現代性價值的反面典型。西方中心論者對希臘的完美描述并非來自客觀史事,而是源于對其他文明的文化偏見與希臘歷史的想象構建。
從人類文明歷史考察,西方議會制度僅是偶然、特殊的產物,并不具備普遍歷史意義。英國議會制度可追溯到中世紀,當時由教俗封建主組成的“大會議”,負責向國王提出建議,討論稅收等重大事項。而封建主與國王的政治斗爭間接導致騎士、市民參與國事討論,被稱為英國國會的開始。此后經歷漫長過程,至14世紀形成上下兩院,構成英國封建制度的組成部分。但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后仍然沿用上下兩院議會制度。也就是說,英國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僅是脫胎于其封建制度之母體,僅是對自身歷史傳統的繼承表現,僅是歷史偶然特殊產物,并不具備一般規律性,根本談不上某些人鼓吹的“歷史潮流”。 只不過在后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中,英國議會制度成為其他國家爭相模仿的對象,從而造成“普遍性假相”。而這種“普遍性假相”與“歐洲中心論”有很大關系。歷史與現實總是密切關聯,“西方中心論”早已經嚴重滲透在目前“世界史”的某些具體敘事之中,有時候并不是中國知識分子主觀上存在立場問題,而是很容易被西方的概念體系“纏繞”其中,于不知不覺中落入思維陷阱,久而久之,成為習慣認識。正如馬克垚先生所說,世界史著述在開創之初就面臨如何克服歐洲中心論的問題,我們的世界史體系是由西方學者建立。因此,世界史話語體系的構建仍任重道遠,但在教學方面,世界史教師應該時刻保持警醒態度,這也是強調將西方中心論批判意識貫串于整個課堂教學的重要原因。只有樹立這種意識,才能夠注意從具體史實層面,點點滴滴去瓦解“西方中心論”所虛構的空中樓閣。
三、樹立正確的世界史觀
按照我國的學科劃分,歷史學的三大一級學科分別是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受這種專業劃分的影響,人們習慣于把中國史和世界史對舉,很容易把世界歷史當作為中國之外的歷史代稱。事實上,中國歷史也是世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實際的高校世界史課堂教學中,很多教師重點教授內容仍是西方史,也難免受到西方中心論的消極影響。因此在世界史教學過程中,應注意同時期東西方的差異比較。如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的比較、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沖擊的東西方比較、西方圣象破壞運動與中國佛教法難的比較等等。在這種比較中,有助于學生樹立全局的眼光看待歷史問題,從而認識人類歷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世界史也應該是人類全球史,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密切聯系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探討和闡述,以世界全局的視野,綜合考察各地區、各國、各民族的歷史,運用相關學科如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的成果,研究和闡明人類歷史的演變,揭示演變的規律和趨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人類歷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鑒、融合的宏偉畫卷。”人類文明因交流互鑒而豐富多彩,這一論斷恰恰指出了世界史應有的本來面目。假如離開了交流互動,就不會有今天的人類歷史。2018年,悉尼大學考古系賈偉明教授來中南民族大學作學術講座,他指出,目前根據人類學、考古學、基因科技等多手段綜合研究表明,澳洲土著人是澳大利亞古人類的直系后代,古人類移民到澳洲是一次性的,移入之后,便于外部基本隔絕。但是,令筆者感到震驚的是,當18世紀末英國殖民者來到這片土地上時,那里的土著居民還停留在原始舊石器時代,因為長期的封閉狀態,使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失去了同外部世界其他民族、文明進行交流的可能。隔絕、封閉的歷史境遇,拉開了澳大利亞人同其他大陸居民間的距離,造成了經濟文化發展的嚴重滯后。相比之下,無論是人類新石器時代,還是人類文明誕生以后,亞歐大陸始終存在頻繁的族群遷徙,交流互動。亞歐大陸因此也成為人類歷史的中心。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指出,研究世界史繞不開歐洲大陸。由此可見,人類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是何等重要。
深入考察歷史也會發現,任何一個早期文明中心的形成幾乎都是周邊多種文化互動影響長期累積之結果。例如,古代埃及文明的創造者是由講哈姆語的北非土著和講塞姆語的來自西亞的人種融合而成的。考古表明,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文明也是在吸收北部山地文化(諸如哈遜納文化、哈雷夫文化)基礎上形成的。華夏早期文明也是“滿天星斗”的不同文化區碰撞形成的。考古發現,舊石器時期后期,歐亞大陸就發展了交流互動。對于先秦上古時期歐亞大陸青銅文化的傳播,學界將其定義為“青銅之路”。眾多研究也表明青銅技術的傳播并不是孤立的現象,而與小麥、綿羊、羊毛、牛、牛奶、馬、馬車等技術的傳播密切相關。除了青銅之路,還有自東向西傳播的彩陶之路,可見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外來人群及其文化在多數情況下都存在與當地人群及其文化碰撞與融合的現象。我們必須承認,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本土文化,也沒有絕對的外來文化,自從人類誕生以來,人類不同地域族群就一直進行著交往交流交融,人類歷史由此徐徐鋪展開來。不同民族在不同時段對人類文明都作出過重要貢獻,但我們很難說哪個文明是高級的,哪個文明是低級的。不同的民族創造了不同的歷史文化,都有著自身獨特的價值,這種價值是平等的。我們要堅持尊重、平等對待每一種文明,文化差異不應該成為世界沖突的根源,而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為此,樹立平等、包容、多元互鑒的世界史觀指導課堂教學,也就顯得尤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