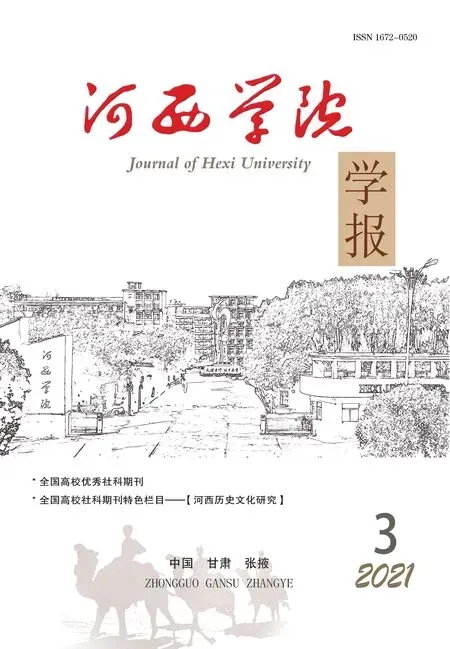元代孫悟空故事的文本譜系及文學史意義
2021-01-14 03:51:20李山嶺
河西學院學報
2021年3期
李山嶺
(亳州學院中文系,安徽 亳州 236800)
小說《西游記》是世代層累形成的文學文本,從《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游記》雜劇、《西游記平話》,到《西游記》章回小說,形成了具有連續演進關系的文本系列,跨越宋、元、明時期,歷經話本、雜劇、小說等文本形態的變遷。其中在元代,出現了多個相關聯的故事文本,成為一個譜系,在孫悟空故事的演變中承前啟后,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一、元代孫悟空故事文本的譜系性
元代與孫悟空有關聯的故事文本有:楊景賢《西游記》雜劇①、《時真人四圣鎖白猿》雜劇(佚名)、《二郎神鎖齊天大圣》雜劇(闕名)、《陳從善梅嶺失渾家》(《喻世明言》卷20)。這些文本對孫行者出身、特征的描述具有沿襲性,呈現出鮮明的譜系特征。
(一)對孫行者出身描述的一致性
楊景賢《西游記》雜劇里孫行者有弟兄、姊妹五人。在第三本第九出“神佛降孫”中,孫行者自報家門:“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驪山老母,二妹巫枝祗圣母,大兄齊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1]438第十出“收孫演咒”中交代:“這座山是花果山。山下有一洞,是紫云羅洞。洞中有一魔君,號曰‘通天大圣’,惱得三界圣賢,不得安寧。”山神唱:“他是驪山老母兄弟,巫枝祗是姊妹。”[1]445
楊本雜劇中孫行者稱“通天大圣”,他的大兄稱“齊天大圣”,在《陳從善梅嶺失渾家》中有幾乎相同的說法:“且說梅嶺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陽洞。洞中有一怪,號曰申陽公,乃猢猻精也。弟兄三人:一個是通天大圣,一個是彌天大圣,一個是齊天大圣。小妹便是泗州圣母。……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甘肅教育(2020年8期)2020-06-11 06:10:02
制造技術與機床(2019年10期)2019-10-26 02:48:08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電子制作(2018年18期)2018-11-14 01:48:06
小學教學參考(2015年20期)2016-01-15 08:44:38
人間(2015年20期)2016-01-04 12:47:10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