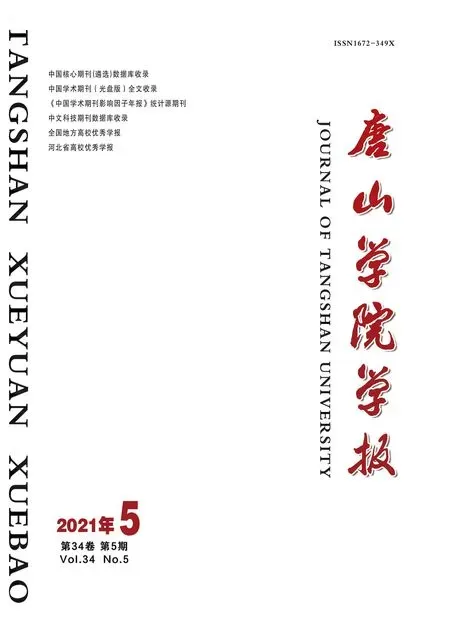來自韓松科幻小說中“異時(shí)空”的回響
季春雨
(蘭州大學(xué) 文學(xué)院,蘭州 730000)
科幻小說以文字作媒介,以閱讀想象為感知方式,打開了一扇面向新世界的窗口。作家韓松在其科幻小說中創(chuàng)造了奇幻瑰麗的異時(shí)空,從中短篇小說到長篇小說,他對(duì)人類思想以及社會(huì)進(jìn)化過程的反思、對(duì)人性善惡的是非辯證、對(duì)烏合之眾的諷刺和批判、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有力諷喻,都流露在看似怪誕不羈的故事里。在長篇小說《紅色海洋》《地鐵》《亡靈》以及中短篇小說集《宇宙墓碑》的故事中,人或者類人生物的生存與繁衍本能占據(jù)了行動(dòng)指南的絕對(duì)主導(dǎo)位置,有意或無知地傳播擴(kuò)散荒謬言論以及人云亦云和墨守成規(guī)都是異時(shí)空的常態(tài),而出現(xiàn)的超智靈魂仿佛是混沌世界里的一束光芒,照亮了黑暗的谷底。
一、繁衍生息的兩性生命
韓松的科幻小說追溯了文明的前行如何將女性從被動(dòng)生殖中解放出來,借由平行的異空間中的兩性關(guān)系展望著兩性生命的進(jìn)化式發(fā)展。《紅色海洋》里人類全面退化后形成的水棲人的日常生活就是不平等兩性關(guān)系的縮影。在水棲人的世界中,男性占據(jù)絕對(duì)的霸權(quán)地位,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品或所有物。處于弱勢(shì)的女性為從男性那里獲得所需而不得已或者已經(jīng)習(xí)慣了“偽裝”。當(dāng)主人公很小的時(shí)候,他的母親為了活命,妥協(xié)于一個(gè)又一個(gè)前來求歡的男人,誕下數(shù)十個(gè)孩子。這些孩子成長后對(duì)女性心生鄙夷并妄想控制女性,甚至支配自己的母親。水棲人的性放縱和性失衡不僅意味著繁衍后代的原始本能,也意味著女性對(duì)男性強(qiáng)權(quán)的臣服。主人公曾遇上一群游蕩的“強(qiáng)盜”,他們把女人當(dāng)作享樂的戰(zhàn)利品,肆意蹂躪后隨即殺掉。這種血腥殘忍的性暴力行為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主人公理智的覺醒。人類性本能確實(shí)能夠激發(fā)人類的諸多潛能。年少的主人公遇到那個(gè)曾使他心動(dòng)的女孩后,就一直惦記著她,對(duì)她的愛慕和拯救的愿望激發(fā)起他的英雄主義精神,要拯救女性,拯救水棲人的未來。和諧的兩性關(guān)系是繁衍生息的基礎(chǔ),異時(shí)空中的混亂遭際恰從反面印證了這一點(diǎn)。
性別認(rèn)知里自有繁衍種族的意識(shí),這種生物本能能夠激發(fā)起延續(xù)種族的責(zé)任感。繁衍對(duì)于幻想具有時(shí)空的意義,即存在的意義。有延續(xù)就有希望,即使在四面楚歌的悲哀境況下能夠預(yù)料到結(jié)局的慘烈,也不想放棄最后一搏的機(jī)會(huì)。繁衍是生生不息的表現(xiàn)形式,人對(duì)未來的渴望能夠超乎一切想象,子孫后代所保留的基因和血液仿佛是靈魂得以茍延殘喘的一種方式。《地鐵·驚變》中瀕臨死亡的眾人在絕望的境地里以性放縱來擺脫死亡的陰影,卻因性放縱而急速退化了智商,徹底抹去了對(duì)生命末日的恐慌。“性”在這個(gè)怪誕世界里成了致使人類退化的因。在脫軌的地鐵車廂中,隨著駛向愈加黑暗與深邃的異時(shí)空,只想放縱性欲的人類最終退化成了滿地的螻蟻。小說的直觀沖擊效果顯著,警示著人類文明社會(huì)在前進(jìn)中應(yīng)有所約束、有所規(guī)劃,要秉持理性,謀求可持續(xù)性發(fā)展。
韓松的科幻小說通過狂放不羈的性描述,反思人類的來路和去處,以及人所承受的一系列的主觀行為帶來的嚴(yán)峻后果。《紅色海洋》中棲息在紅色海洋底的男性群體既狂妄自大,又嗜好屠殺,由此招致了繁衍的危機(jī)以及情感與智商的退化。女性是啟蒙智慧的化身,扼殺掉女性,男性將無法獨(dú)存。種群之間的相互殘殺,是危害其整體延續(xù)的重要因素,水棲人的命運(yùn)悲劇來自種群之間的阻隔、殘殺,來自男性對(duì)女性的殘暴控制,也來自他們的傲慢放縱。小說中構(gòu)建的水棲人的命運(yùn)走向像是人類發(fā)展的另一條平行線,他們的世界和社會(huì)關(guān)系預(yù)示著無節(jié)制的行事和不擇手段的掠奪終將導(dǎo)致追悔莫及的悲劇,警喻著人類社會(huì)應(yīng)該規(guī)避。《美女狩獵指南》描述了一個(gè)令無數(shù)男人向往的神秘島嶼,那里飼養(yǎng)著生物基因工程批量生產(chǎn)的女人,她們作為男人狩獵的對(duì)象,可以任意被屠殺。男人們瘋狂地捕獲著“真正的女人”——處女,或直接獵殺她們或縱欲后殘忍地殺掉,因而遭到女人們的報(bào)復(fù)性圍攻,最終變成兩性之間的相互殘殺,形成對(duì)立的局面。
女人是視覺動(dòng)物,不僅審視他人和自己,也被他人審視。評(píng)價(jià)一個(gè)女人,往往從最可見的部分開始,這是生殖沖動(dòng)的源起之一。《美女狩獵指南》里為追求性刺激登島的男人首先看到的是人造女性的胴體,這使他們像瘋了一般地去狩獵女人。但那些外表看起來柔軟嬌俏的女人卻沒有想象中那般聽話、好對(duì)付。她們的外表是一種致命的誘惑,將男人引向死亡的祭壇。在幸存者小昭的視角里,那些女人喜歡女人,至少是雙性戀,這讓他心生障礙,對(duì)性產(chǎn)生了難言的拒絕情緒。《紅色海洋》塑造的母親形象以性愛與繁殖作為存在的最大動(dòng)力,這滿足了她對(duì)男人的幻想以及對(duì)世界與自我之間存在的價(jià)值關(guān)系的最大幻想。她作為一個(gè)比較單純的生殖機(jī)器而存在,為等待男人、飼養(yǎng)孩子而生,死即是生的宿命。女性被刻畫成性欲望的犧牲品,更是性放縱下的復(fù)仇者。她們是視覺的焦點(diǎn),卻成為交易或搶奪的對(duì)象。
分段式長篇小說《地鐵·驚變》恰恰相反,被困在車廂里的人類以理智意識(shí)到當(dāng)下無法扭轉(zhuǎn)的窘境,由此激發(fā)起讓人類延續(xù)下去的愿望,于是通過性交進(jìn)行種族繁衍的任務(wù)迫在眉睫。但性活動(dòng)的狂縱恣肆擾亂了這出于本能的繁衍智性,最終性迷亂代替了理性發(fā)展,將人類推向急速退化的萬劫不復(fù)的深淵。“文化發(fā)展的動(dòng)力,絕大部分是靠對(duì)性興奮中所謂的‘錯(cuò)亂’成分的壓抑獲取的。”[1]倫理道德觀念在失智的人群中變得一文不值,進(jìn)化了漫長時(shí)間的人類智慧也被擱置一旁,剩下的只有肉體的狂歡和放縱。人類自私的本性暴露無遺,來自神秘空間的神秘力量隱喻著人類面臨著的所有未知的強(qiáng)大誘惑,如果放松了對(duì)它們的警惕或者輕易地上鉤,將追悔莫及。荒誕的故事里充斥著荒誕的性活動(dòng),性本身變成了制造荒誕并承擔(dān)荒誕后果的載體,也變成了一切罪惡的助推劑。這是故事呈現(xiàn)出的人類本能,如果完全按照本能發(fā)展下去,人類群體將會(huì)陷入混亂無序的境地。幻想中荒唐的性行為恰恰是最為合理的人類活動(dòng),它來自人類本能,又產(chǎn)生著本能該產(chǎn)生的繁衍作用;它與文明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既助推著文明的延續(xù),又可能致使文明向原始的方向退化。
脫軌地鐵車廂里的荒誕世界揭示了一心想放縱享樂、顛倒黑白的人類所面臨的前路是一片黑暗空虛的沒有出路的時(shí)空深淵,隨著人類進(jìn)化上億年的智慧與肉體被吞噬,人類最終退化成了任人宰割、一文不值的螻蟻。所以在物欲膨脹的驅(qū)使下,拋棄理智和道德將是人類前路上最大的歧途。對(duì)物質(zhì)的狂熱化追求等過度行為并不是人類進(jìn)化的積極動(dòng)力,只有真善美才能創(chuàng)造光明的未來。人類雖然在宇宙中處于孤獨(dú)的境地,但是前路的開拓權(quán)在人類自己手里,不能因?yàn)椴淮_定就放棄。人類總會(huì)有看似合理的本性表現(xiàn),可人類的生理本能在決定人類社會(huì)的倫理標(biāo)準(zhǔn)中占據(jù)多大的比重,當(dāng)追溯這一問題的答案時(shí),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的落腳點(diǎn)還有未確切的地方。是在對(duì)人類生物性的理解中,還是在人類已經(jīng)產(chǎn)生的普遍道德觀念中,抑或是哪一方更占據(jù)優(yōu)勢(shì)?在兩性問題中,一切存在似乎都具有可解釋性,文學(xué)的時(shí)空卻無法任憑所謂的現(xiàn)實(shí)理據(jù)來解釋,否則費(fèi)盡心思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空間可能將面臨失去純粹審美價(jià)值的風(fēng)險(xiǎn)。
二、超智靈魂的時(shí)空透視
超智靈魂以上帝的視野,俯瞰著異時(shí)空中荒謬的人世。它是理性的代表、正義的力量,亦是希望的光芒。《紅色海洋》的敘事主人公“我”從一出生就可以思考,從看見小的生存空間到發(fā)現(xiàn)更大的世界及規(guī)則,他的思想逐步地成熟,一系列悲慘的故事使他得到成長,遇到的那些男人和女人也使他更清楚地認(rèn)識(shí)自己。他像是水棲人混沌世界中忽然現(xiàn)身的上帝,審度著一切不合常理的荒謬的社會(huì)秩序,內(nèi)心充滿了智慧生命體在進(jìn)化過程中會(huì)產(chǎn)生的焦慮、鄙夷、憐憫、孤獨(dú)等復(fù)雜的情緒。他的眼神從稚嫩變得格外的鋒利和冷漠,雖對(duì)混亂的水棲人的生活產(chǎn)生不滿和質(zhì)疑,但因無能為力不得不袖手旁觀。在他的眼前仿佛時(shí)時(shí)刻刻上演著一場(chǎng)場(chǎng)滑稽又殘暴的大戲劇,然而擁有上帝思想的他只是個(gè)冷眼的旁觀者。水棲人的發(fā)展歷史充滿了奇幻色彩,他們的過去和過去的過去都是富有寓言性的假說,在可能與不可能、是與不是之間搖擺。而小說第四部的“未來”是在中國的歷史故事中延續(xù),告別了荒誕式的繁衍和流浪式的掠奪,仿佛被另一個(gè)世界的文明重新席卷。當(dāng)水棲人與陸生人在被顛覆的歷史中相遇,已存在種族的區(qū)隔,水棲人回歸家園的路滿是坎坷。
智慧的眼睛在故事里總是冷靜地存在著,既打量著自己,又審度著對(duì)方,是作者的眼睛,也是讀者的眼睛。《地鐵·驚變》里被眾人推出車廂的攀巖者小寂絲毫沒有受到車廂內(nèi)人類退化趨勢(shì)的波及,當(dāng)他勘察車廂重新往回爬時(shí),車廂內(nèi)的世界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dāng)初他被眾人選中被推出車廂時(shí),不知道是幸運(yùn)還是不幸。他像一個(gè)歷史演變的旁觀者,在混亂的世界之外孤獨(dú)而獨(dú)立,面對(duì)同伴退化的亂象卻無能為力。這預(yù)示著人類的孤獨(dú)處境,在絕望中總有所希望。兩個(gè)空間構(gòu)成了對(duì)比鮮明的兩個(gè)世界,令人震驚。這趟地鐵就像是一個(gè)解不開的魔咒,詛咒著人類即將脫軌的結(jié)局。它把不幸被選中的人和其他人相分隔,使他們走向彼此不再相交的路線,形成了判若云泥的命運(yùn)結(jié)局。歸來人的理智仿佛是作家和讀者注視著的犀利目光,和脫軌的另一部分構(gòu)成二元對(duì)立的關(guān)系。空間的區(qū)隔帶來人的區(qū)隔,人的區(qū)隔造成文明的區(qū)隔,文明的區(qū)隔最終導(dǎo)致不同人類種群的命運(yùn)區(qū)隔。韓松以第一人稱為敘事者,借由人物在主觀思維上對(duì)人類在生存?zhèn)涫芡{的境地里無助掙扎的認(rèn)知及態(tài)度,書寫超智生命力圖在最糟糕的境況中奮起的精神。
超智靈魂與愚昧陳腐的思想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甚至前者成為神一般的存在,自帶理性神圣的光輝。地鐵車廂里的退化人類就像一群不辨是非黑白的烏合之眾,盲目瘋狂,最終將自己推向覆滅的時(shí)空深淵。“群體的信念有著盲目服從、殘忍的固執(zhí)以及要求狂熱的宣傳等”[2]44特點(diǎn),因此“他們首先需要的是一個(gè)神”[2]46。居于紅色海洋偏僻一隅里只聽別人言說、從不思考的男人和女人就是一群惡魔的幫兇,是危害他人和自身的烏合之眾,無法被叫醒,不管他們是真睡還是假寐。超智靈魂仿佛是一道驅(qū)散晦暗、照亮未來的光,清晰地暗示著讀者:這世界是多么荒唐。暴政的幫兇是最為沉默的一群,沉默是示弱,是默許,是服從,缺少生命該有的獨(dú)立思考和發(fā)展活力。人類對(duì)理性思想的期待、對(duì)超凡智慧的崇敬始終伴隨著社會(huì)文明的進(jìn)程。人類意識(shí)到理性思想的成熟需要經(jīng)歷一定的過程,就像人類歷史中出現(xiàn)的那些血腥故事一樣,超越了時(shí)間和空間的局限,在歷史的未來階段回望,才會(huì)發(fā)現(xiàn)真理在那里發(fā)著光。理性思想使人類對(duì)自我和世界的認(rèn)識(shí)更為深刻,對(duì)未來的諸種情況有所準(zhǔn)備和預(yù)測(cè)。
短篇小說《逃出憂山》是從主人公韓愈的視角而寫的。他與妻子關(guān)系惡化正在鬧離婚,他卻陷入幻覺,感覺這世界只剩下他們二人。他們重游憂山,韓愈卻只想逃出去。其實(shí)憂山只不過是虛幻的世界,是實(shí)驗(yàn)室創(chuàng)造的人工環(huán)境。一場(chǎng)莫名其妙的大火燒醒了韓愈,他還在實(shí)驗(yàn)室里,幻覺里的憂山不過是他面前的巨大沙盤。在他游歷憂山時(shí),實(shí)驗(yàn)室可能已被篡權(quán)了。他慌張地要逃走卻遇見了妻子,她手中握著剛剛在幻覺里看到的佛像,佛像的嘴角仿佛掛著譏笑,她告訴他大街上熱鬧的人群都在迎接佛骨。幻覺里的佛像仿佛蠱惑了眾人,唯一清醒的他嘔吐得更厲害了。在小說集《宇宙墓碑》的后記《邂逅科技時(shí)代的文學(xué)》中,韓松講到,我們的祖先富有想象力,能把不同的東西拼接在一起,并在洞穴的巖石上畫畫,“表明他們不僅生存在自然的現(xiàn)實(shí)世界里,還生活在他們腦海中的想象世界里。這后一個(gè)世界能賦予人類以無限進(jìn)步的能力,而它的一個(gè)分支就是科幻”[3]。幻覺世界中的理智思想勾勒出故事的筋脈,與現(xiàn)實(shí)緊密相連,是可以完整理解小說的重要視角。
從一個(gè)超智生命的經(jīng)歷上可以看出諸多智慧體的命運(yùn)大概延伸的路徑。人類的理想生活在科幻小說中得以實(shí)現(xiàn),不愿意面對(duì)的糟糕情境也在這里上演,超智的靈魂既看到了美好未來的方向,又被警醒著歧途荊棘的蔓延。超智的眼睛可能是作者的眼睛,可能是讀者的眼睛,也可能是任何一個(gè)人物的眼睛。它變成一種獨(dú)立思想的載體,衡量著時(shí)間和空間,見證著茫茫宇宙的一瞬千年。但是超智靈魂真的是絕對(duì)的超智嗎?準(zhǔn)確地說,超智是相對(duì)的,在無數(shù)個(gè)科幻故事里,超智靈魂的存在由對(duì)比凸顯出來,它不一定比作者更聰明,或者比讀者更智慧。現(xiàn)世的哲學(xué)都教人積極地面對(duì)生活,科幻小說則在描述人應(yīng)該努力或者規(guī)避的方向。超智靈魂本身就是科幻的重要元素,在詭異多變的科幻世界中,超智靈魂的存在使讀者更有上帝視角的代入感,清醒的思考恰能引向那些該規(guī)避的路,教人及時(shí)折返。
三、變形時(shí)空的警喻擬象
科幻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實(shí)現(xiàn)不可能,滿足人類掙脫流離在線性時(shí)間中的無奈和傷感。在韓松一系列科幻小說中的漫漫的時(shí)間長河和廣闊的空間區(qū)域里,無論是人類在與自身命運(yùn)的斗爭中、與外星侵犯者的戰(zhàn)爭中,還是與未知時(shí)空的抗?fàn)幹校汲涑庵祟愐驅(qū)Πl(fā)展前景和世界終極的不確定性而產(chǎn)生的幽長哀傷和隱隱絕望。科幻小說給了讀者以無限的希望和可能,呈現(xiàn)出一個(gè)全新的世界,這個(gè)世界伴隨著不可預(yù)知的災(zāi)難性故事,伴隨著對(duì)消極行為趨勢(shì)的嚴(yán)峻假設(shè)。科幻不是構(gòu)造一個(gè)完美的童話世界,而是映照人類的來處和去向。科幻故事不局限于常規(guī)的時(shí)空概念,而是在被變形、被拉伸的時(shí)空里任意地穿梭,尋找所有可能的啟示。韓松小說中的異時(shí)空自帶結(jié)界,自成一體,相對(duì)獨(dú)立,小到一家醫(yī)院,大到整個(gè)宇宙,異時(shí)空內(nèi)的風(fēng)云變幻將讀者席卷到一個(gè)富含隱喻意義的另類世界。人物的夸張行為是對(duì)典型社會(huì)人物偏執(zhí)行為的放大,不合常理的荒誕現(xiàn)象是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映射。
《紅色海洋》等作品的敘事時(shí)間跨度非常大,故事空間轉(zhuǎn)移迅速,作家構(gòu)建了數(shù)個(gè)大框架,將對(duì)人類本性的反思和對(duì)人類命運(yùn)的憂慮摻入其中。這仿佛是一場(chǎng)奇幻的旅行,既能回到漫漫的過去,又能穿越到遙遠(yuǎn)的未來,但對(duì)真理的探索和尋找從未停歇過。發(fā)生于遠(yuǎn)古的歷史事件是人類文明厚重積淀的條件,是地球文明得以萌發(fā)前進(jìn)的搖籃,而遙遠(yuǎn)的未來是人類文明的歸處,是現(xiàn)代人對(duì)人類前景的展望和揣測(cè)。《沒有答案的航程》中丟失了記憶的生物和同類孤獨(dú)地漂泊在茫然的宇宙中,因猜忌而相互殘殺,待生物終于意識(shí)到同類的性別,一切為時(shí)已晚。作家對(duì)未來世界的勾勒則基于理性的考量,描述出一種人類命運(yùn)的前路狀況,給讀者無限的想象留白。跨越式敘事無限拓展了時(shí)間與空間的邊界,在這種情境設(shè)定下,人物的跨時(shí)空轉(zhuǎn)移變得非常簡單,富有戲劇性,大開大合的藝術(shù)空間亦獨(dú)具魅力,展現(xiàn)出一個(gè)異于常態(tài)的奇幻世界。《劫》的故事敘述從公元前開始,歷史可能因一起書生被害的案件而改寫,時(shí)空也為此混亂。名為“詩人”的機(jī)器人穿越時(shí)間的河流回到過去驗(yàn)證考古發(fā)現(xiàn),并留在歷史的某個(gè)時(shí)刻里。自由穿梭于任意時(shí)空中,將個(gè)人情懷提升到人類種族情懷的高度,這是普通人抱有的英雄夢(mèng)一般的愿景。在變異的時(shí)空里,個(gè)體不僅是個(gè)體,還是整體的縮影,其命運(yùn)昭示著整體的結(jié)局。
時(shí)間的流速在空間阻隔的內(nèi)外發(fā)生差異,變得扭曲。《地鐵·驚變》將故事背景設(shè)定在一個(gè)固定的空間里,即地鐵車廂,但其外圍空間極為神秘,時(shí)間就像脫軌的列車一般飛馳,一轉(zhuǎn)眼難以計(jì)量的時(shí)間已然逝去。作家將人類退化的歷史極其精煉地描述出來,就像是追溯億萬年來的人類發(fā)展歷史,這個(gè)過程卻與進(jìn)化相反,向著最為原始的人類本能飛速地退化。時(shí)間的變形加劇了小說的怪誕性,增強(qiáng)了迅速退化帶來的沖擊力。人在開放的空間中感受到的可能性或許更多,而相對(duì)封閉隔離的空間更能凸顯沖突性,給人以禁錮感和幽閉感,沖破難度大。車廂內(nèi)的人從未勇敢地走出去,最終將生命耗盡;車廂外的人冒險(xiǎn)回到車廂卻瞬間被時(shí)間的空洞吞噬掉,剎那間的老去顯示了超智靈魂的無能為力。小說實(shí)現(xiàn)了人類瞬間移動(dòng)、穿越時(shí)空的體驗(yàn)渴望。車廂外的人和車廂里的人被區(qū)隔開了,車廂內(nèi)外形成了兩個(gè)維度的世界,彼此獨(dú)立。在科幻小說的世界里,一瞬間可以發(fā)生許許多多的故事,能從過去瞬移到未來、從一個(gè)宇宙轉(zhuǎn)移到另一個(gè)宇宙、從嬰幼兒到耄耋老人。穿梭于時(shí)間和空間的河流中,人類生命不受單行線限制的愿望在科幻空間中得到了補(bǔ)償。跳脫到時(shí)間和空間之外,人類超越了物質(zhì)禁錮、實(shí)現(xiàn)了長久生存的夢(mèng)想。韓松筆下的故事常常出人意料,將區(qū)隔出來的時(shí)空變成埋葬人類的墳?zāi)埂?/p>
時(shí)空對(duì)于人類的意義是誕生與發(fā)展,亦是想象和突破。在《亡靈》這種另類故事里,人與靈魂實(shí)現(xiàn)了共存。醫(yī)院里的亡靈在某一個(gè)時(shí)刻又重新“復(fù)活”,重復(fù)著自己生前的沖動(dòng),為無法釋懷的死發(fā)起復(fù)仇。自私的人與復(fù)仇的鬼混戰(zhàn)成一片,已經(jīng)分不清誰是人,誰是鬼,亦分不清到底是人更可怕,還是鬼更可怕。處于暗處的鬼生前是受害者,而處在明處的人是施害者,世事難料,此刻的人變成鬼魂鬧事的受害者,鬼卻成了肇事者。正所謂“種下什么樣的因,終究得什么樣的果”,人種下惡果,鬼就找上門來了。活人與怨靈共在,是因果報(bào)應(yīng)的典型范例。“為了進(jìn)入時(shí)間,必須具備一定的場(chǎng)合,沒有這種場(chǎng)合,人永遠(yuǎn)不可能‘跨越一個(gè)如此巨大的間隔’。”[4]韓松將陰陽兩界的界限沖破,打破了時(shí)間的線性走向,讓死去的靈魂在醫(yī)院的場(chǎng)景下重新顯現(xiàn),使人與鬼再續(xù)過去的糾纏故事。物質(zhì)的絕對(duì)性被鬼的出現(xiàn)沖破,超乎物質(zhì)之外的靈魂獨(dú)自重現(xiàn),自古在中國志怪小說中就有,但是科幻小說的不同是賦予鬼以物質(zhì)性,讓他們來擾亂內(nèi)心有鬼的人,還給鬼的“復(fù)生”賦予合理性,借鬼的意外出現(xiàn)來挑明醫(yī)護(hù)人員的失職行為,亦借鬼之口吻來質(zhì)疑烏合之眾的愚昧與可怕。
韓松的科幻小說成功打破了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物質(zhì)的阻隔,實(shí)現(xiàn)了人類思想的自由穿梭,時(shí)常有移花接木般的巧妙、有排山倒海般的氣勢(shì)。故事中一切物質(zhì)均可變成流動(dòng)的,時(shí)間的絲線相互纏繞,空間被肆意地扭曲,人的靈魂和思想被放大特征。異時(shí)空中的自由與約束共存,它將人物卷入時(shí)空扭曲的旋渦,面對(duì)異樣的現(xiàn)象,所有的不適應(yīng)和手足無措都變成一定的行為趨向,招致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后果。時(shí)空的不斷轉(zhuǎn)移造成了多重空間的出現(xiàn),構(gòu)成了多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又相互疊加的時(shí)空,給人物活動(dòng)提供了不同的場(chǎng)所。在時(shí)間線性延伸中產(chǎn)生的無聊、疑惑、恐懼、好奇等情緒,促使人在自己的思維中將時(shí)間或空間進(jìn)行加工折疊,最后變形的不只是時(shí)間與空間,還有人自身。時(shí)空的概念始終在人的觀念中,時(shí)間的計(jì)量和空間的定位以人的意愿為轉(zhuǎn)移,那些能夠察覺時(shí)空異變的眼睛,在突如其來的變故里仍存有智慧的光芒。異時(shí)空不再是冰冷的牢籠,而成為人迫切需要的庇護(hù)所。“空間在其本身也許是原始賜予的,但空間的組織和意義卻是社會(huì)變化、社會(huì)轉(zhuǎn)型和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的產(chǎn)物。”[5]在文學(xué)想象中所有奇怪的事件皆有了合理的解釋,科幻文學(xué)的時(shí)空是人造的時(shí)空,在不同審美主體的觀照下,呈現(xiàn)出不同的帶有強(qiáng)烈主觀色彩的樣態(tài)。
四、烏合之眾的存亡命運(yùn)
韓松的科幻小說中烏合之眾是通過與超智靈魂的對(duì)比顯現(xiàn)出來的,對(duì)人類文明的智慧發(fā)展來講,真理恰恰在此顯現(xiàn)。對(duì)讀者來說,在兩方的對(duì)比下,更能看清作家想要表達(dá)的觀點(diǎn)及立場(chǎng)。烏合之眾不僅是因自身的愚昧和無知,亦是生存環(huán)境所致,他們的被動(dòng)地位難以通過暫時(shí)的反抗來改變,為了眼下的生存不得不忍氣吞聲。烏合之眾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存亡歷程將他們自己困在了沒有出路的孤島上,這也可能造成對(duì)整個(gè)族群的嚴(yán)重威脅。《紅色海洋》中的大多數(shù)物種將兩性的失衡和不同種族間的高低貴賤視為理所當(dāng)然的事情,這是歷史延續(xù)下來的游戲規(guī)則。他們沒有想過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自覺與自主意識(shí)還在沉睡。臣服于暴政的多數(shù)女性很多時(shí)候只能想到自保,處于艱難的弱勢(shì)地位,沒有條件覺醒,也沒有能力反抗。她們猶如菜板上的魚肉,但卻是冷眼漠視的助長暴力的旁觀者。《亡靈》里造成醫(yī)療事故的醫(yī)護(hù)人員不是無辜的,總需要擔(dān)負(fù)部分亡靈生前死在醫(yī)院里的責(zé)任。在個(gè)別亡靈的慫恿和煽動(dòng)下,這群死去的靈魂仍然具有烏合之眾的屬性:沖動(dòng)、易變、急躁、偏執(zhí)、輕信且易受暗示。站在對(duì)立面的醫(yī)護(hù)人員本以救死扶傷為天職,可看到個(gè)別人員玩忽職守卻依然獲利不少時(shí),他們爭相效仿,毫無原則和底線。這是烏合之眾的典型,缺乏理性思考而易被眼前的利益誘惑,拋棄了職業(yè)道德。
韓松的科幻小說描繪出人類對(duì)于未來世界或平行世界的無限遐想,極具揭露諷刺的意味和現(xiàn)實(shí)映照的意義。他將人性融入奇幻怪誕的藝術(shù)世界里,將對(duì)人類自私行為后果的反思融入對(duì)未來地球圖景的想象中。故事框架跨度大,敘事手法多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對(duì)孤獨(dú)地漂泊于茫茫宇宙中的地球命運(yùn)預(yù)設(shè)得多樣化且具有理性依據(jù)。同時(shí),將現(xiàn)實(shí)的內(nèi)核放在充滿幻想元素的故事中,使閱讀體驗(yàn)更為豐富而深刻。科幻世界一定程度上猶如烏托邦社會(huì),科幻小說和烏托邦小說相較,二者均在講述變化,“當(dāng)代科幻小說的主題是變化:人類在變,社會(huì)在變。當(dāng)代科幻小說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完美永遠(yuǎn)不可及,但它是我們追求和努力的目標(biāo)”[6]。科幻文學(xué)的理想目標(biāo)一方面在于滿足人類對(duì)未知世界的想象和期待,另一方面在于追求文學(xué)藝術(shù)的審美價(jià)值和現(xiàn)實(shí)意義。《地鐵·末班》中即將退休的老人發(fā)現(xiàn)了在地鐵車廂里搬運(yùn)乘客的怪人,他同別人講這件事,可沒人相信,人們寧愿沉浸在共同營造的美好氛圍中,也不愿面對(duì)潛在的威脅。科幻小說意不在描繪烏托邦社會(huì),而是在映射目前人們以肉眼無法直觀的世界或是遙望未來,那里有極致的美與和諧,也有極致的惡與殘酷。
除了大時(shí)空的故事架構(gòu),在另外一些以固定地理空間為背景展開的小說里,作家對(duì)烏合之眾的講述同樣充滿了神秘感,細(xì)膩而動(dòng)情。小說《醫(yī)院》以病患主人公在醫(yī)院里的荒誕遭際,揭示出醫(yī)院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各個(gè)科室之間的相互推諉、互不負(fù)責(zé)任的惡劣行徑。故事充滿了刻骨的現(xiàn)實(shí)感,亦在現(xiàn)實(shí)感中融入荒誕的元素,不斷地解構(gòu)著荒誕的文學(xué)世界。幽默的語言讓人啼笑皆非,又讓人深感主人公處境的悲哀,他四處碰壁又不得不尋醫(yī)問診,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荒唐遭遇下耽擱了病情。他被死死地困在了醫(yī)院這個(gè)“結(jié)界”當(dāng)中,猶如噩夢(mèng)里的“鬼打墻”,找不到任何的出路。《亡靈》以病患亡靈的復(fù)仇計(jì)劃為線索展開,類似于現(xiàn)實(shí)中出現(xiàn)的醫(yī)鬧事件,只是將事件主體放在了發(fā)生靈異事件的醫(yī)院里,主人公是一群心懷怨念的亡靈。死去的人重新回到這家醫(yī)院,不接受活人之間的妥協(xié)交易,要為自己曾經(jīng)所受到的傷害發(fā)聲,討回所謂的公道。每個(gè)人物,無論活人還是鬼魂,皆是播種惡的一分子,同時(shí)又是承擔(dān)惡果的一分子。空間的局限將他們密切地聯(lián)系在一起,誰都逃不掉,必須面對(duì)自己的過失并付出相應(yīng)的代價(jià)。
透過科幻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獨(dú)具的思想和思考能力的重要性,以及故事本身對(duì)現(xiàn)代人的生活啟示。《紅色海洋》里海與陸從分隔到交匯、從對(duì)抗到妥協(xié)、從完整到殘破,人性被挖掘得徹底,所有活動(dòng)都在人性觸及的范圍之內(nèi)。那僅存的超智靈魂哀傷地發(fā)出來自遠(yuǎn)古的聲音,人像動(dòng)物那般悲鳴,在浩瀚的海面激起波濤。在沒有目的地的跋涉中,生命的意義發(fā)生了扭曲,就像整個(gè)宇宙的真相被揭露,真實(shí)生命的根開始腐爛。兩性的戰(zhàn)爭愈演愈烈,似乎誰都不是勝利者,但欲望泛濫激起的仇恨卻撕裂了人類的陣營。《青春的跌宕》里的人生可以依照人的意愿被改變,實(shí)現(xiàn)永葆青春,人們對(duì)此習(xí)以為常,罕有對(duì)這種清一色青年人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是否合理感到懷疑的。反青春同盟則反其道而行之,直接跳躍到中老年階段,但他們卻最終在疾病和無聊的圍攻下懷念青春,“自然人”的狀態(tài)倒成了不可得的奢望。“在群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dòng)皆有其傳染性,其程度足以使個(gè)人隨時(shí)可以為了集體的利益而犧牲他的個(gè)人利益。”[2]9像在那穿梭時(shí)空的地鐵上,人群中的人不再是人,靈魂不再是靈魂。“烏合之眾”一詞出現(xiàn)很久了,幾十年前就被討論,韓松現(xiàn)借作品重返烏合之眾的場(chǎng)所,目睹眾人的盲從性選擇,追究“烏合”的原因,感慨人類本能的力量有多么強(qiáng)大創(chuàng)造的文明力量便有多么強(qiáng)大。
現(xiàn)實(shí)總是殘酷的,而幻想的世界更加殘酷。人類獲得了多少,也將付出多少代價(jià)。在《軌道》中的陰謀策劃下的虛擬世界里,所謂的末日只是陰謀集團(tuán)的一個(gè)主意。《地鐵·符號(hào)》中的覺醒者試圖潛入地下以揭開地上城市是個(gè)實(shí)驗(yàn)場(chǎng)的秘密,《地鐵·天堂》徹底地將人類轉(zhuǎn)移到地下開始與鼠為伴的生活,《地鐵·廢墟》則將人類先輩遺留的重要機(jī)密隱藏在地球廢棄的地鐵世界里,地鐵的意象既為人類打開了通向外星文明的隧道,又成為人類最后的庇護(hù)所。像《楚門的世界》一樣,世界內(nèi)的人不知情,在孤獨(dú)的處境中掙扎,世界外的人在冷眼旁觀。科技所制造出來的假象欺騙了世界內(nèi)的所有人,但科技的漏洞同時(shí)威脅著人類的發(fā)展,在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新世界的同時(shí),也給人類自身制造了可能被顛覆的隱患。“關(guān)于未來的科幻是當(dāng)下正在醞釀的諸多歷史可能性之一。”[7]科幻文學(xué)面向未來的意愿部分源自人類對(duì)自身發(fā)展的先見憂慮,基于已有的經(jīng)驗(yàn)而順理成章地衍生出各種可能的未來局面。21世紀(jì)初問世的《火星照耀美國》將故事背景設(shè)定在2066年,雖然在日新月異的今天看來,2066的世界并不遙遠(yuǎn),根據(jù)當(dāng)代科技發(fā)展的狀況即可預(yù)想,但小說勾勒的未來世界,更像是平行的異時(shí)空。故事中人類徹底實(shí)現(xiàn)了共同體的命運(yùn),在此基礎(chǔ)上,全球各地各族的人類共同奮斗,對(duì)抗未知的外太空生物的侵犯。
回顧中國科幻小說的歷史,那些對(duì)于異時(shí)空的奇幻想象,正是科幻文學(xué)的無窮魅力所在。人類前進(jìn)的路不是通達(dá)筆直的,而是曲折起伏的。韓松科幻小說的藝術(shù)世界包羅萬象,自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一直具有啟示意義。在人類對(duì)于未來的想象中,人類對(duì)外物的依托和對(duì)自身的信心變得不那么可預(yù)測(cè)。科幻文學(xué)其實(shí)具有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性,過去的不需要再哀悼,將來的一定要認(rèn)真面對(duì),這是我們能從中感悟到的。人類的世界終究以人類的心智和行為進(jìn)行塑造,它的開端和終端都把握在人類手里。回望過去,曾經(jīng)的歷史傳來諄諄警示,而未來不可先知地正在那里等待著,當(dāng)所謂的將來都變成了過去,所有時(shí)空的可能都成為既定的事實(shí),一切就都引向了難以掌控的未來。未知正因“未知”才異常神秘、格外迷人,人類亦因?qū)ψ约号c世界的不確定而變得多樣。在韓松科幻小說的異時(shí)空里,體驗(yàn)到詫異也好、預(yù)料之中也好,仿佛一段重新被開掘的歷史故事,在所有喧嘩落幕后,都?xì)w于平靜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