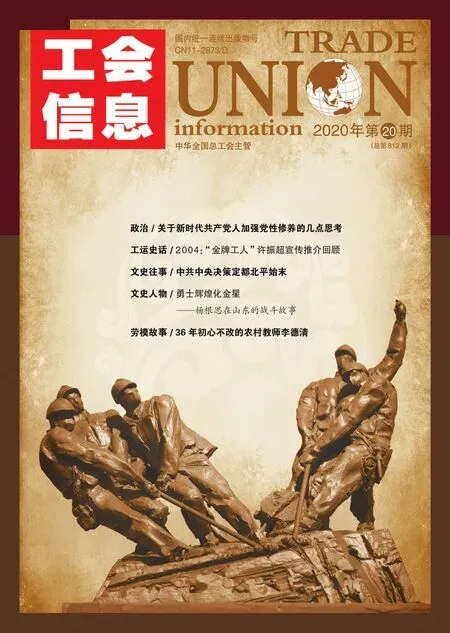臧克家:“生活是詩的土壤”
2020-12-25 06:40:54半山
工會信息
2020年20期
文/半山

著名詩人臧克家,山東諸城人,生于1905年10月。1923年入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習。1926年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1930年至1934年在國立山東大學中文系讀書。1937年至1942年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秘書、戰時文化工作團團長,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三十軍參議,三一出版社副社長。1942年至1946年任重慶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候補理事。1946年至1948年任上海《僑聲報》文藝副刊、《文訊》月刊、《創造詩叢》主編。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人民出版社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詩刊》主編。自1929年發表處女作,50多年里,著有詩歌、散文、小說、回憶錄、詩論集《自己的寫照》《運河》《從軍行》《泥土的歌》《生命的零度》《凱旋》《懷人集》《詩與生活》《學詩斷想 》等 50 余本。2000年1月獲首屆“中國詩人獎終生成就獎”。2004年2月5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9歲。
童年生活是詩的搖籃
臧克家曾經說:“如果說,童年環境的氣氛對于一個人的事業與愛好有著重大的關系,如果說,遺傳對于一個人的氣質、性情、天才有著極大的影響,那么,我將把我學詩的故事在這上面扎根了。”
臧克家的故鄉是山東諸城,位于膠東半島。這個縣屬古瑯玡,秦始皇東巡,曾在這兒刻石記功,這就是有名的瑯玡刻石。臧克家所居住的村子——臧家莊,離城18里路,盤踞在一個小嶺頭上,樹木不多,干旱缺水。他家門口,對著兩座青山,一座是常山,一座是馬耳山。蘇東坡在密州做知州時,曾到常山打獵,也寫下了“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的詩句。臧家莊,自然風光并不優勝,但臧克家生在這里,長在這里,自然對它的感情是頗深的。……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