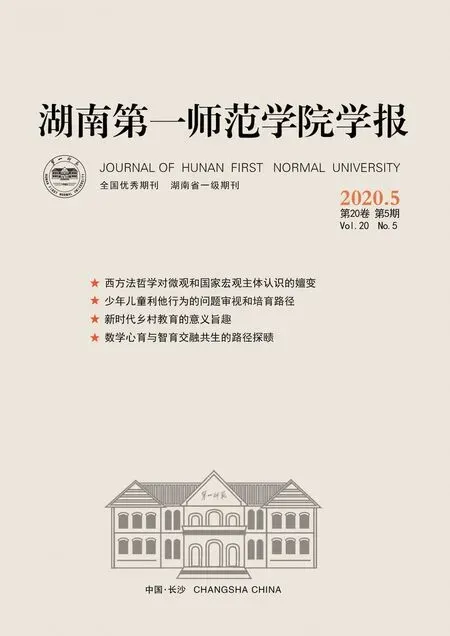新時代鄉村教育的意義旨趣
——基于生產邏輯的審視
王 巍,曾芙蓉
(中共滁州市委黨校,安徽 滁州 239000)
“三農”工作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課題,鄉村教育是新時代農村工作的重要內容,是做好新時代農村工作的重要支撐[1]。做好新時代鄉村教育不僅是緩和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重要舉措,也是推進鄉村文化振興、夯實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基礎的重要要求,更是促進鄉村復歸主體性、實現“現代意義”轉型的重要路徑[2]。因此,從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生產性視角”,從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生產邏輯”層面探究新時代鄉村教育的意義旨趣有助于明確新時代鄉村教育的重要意義指向與價值旨歸。
一、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生產邏輯內涵
生產是生產要素輸入生產系統內,經過生產與作業過程,轉換為有形的和無形的產品,從本質上而言是資源輸入——產品輸出的過程,生產邏輯就是資源經過生產系統轉換為產品的內在機理和產出程序[3]。在新時代語境下,鄉村教育也具有新時代生產邏輯向度。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生產邏輯是新時代條件下在鄉村場域中通過向鄉村教育系統輸入資源產出具有“鄉土”特征的價值、知識、情感、制度和符號產品的內在過程機理。
二、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生產邏輯
(一)鄉土價值生產邏輯
在新時代語境下,鄉村教育逐漸擺脫了學校教育的單一主體模式,形成了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多元協同的教育發展格局。在鄉村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雙向協作下,以立德樹人為主要目標,以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愛國主義信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忠信孝悌的“仁愛”之道為重要內容,通過道德課堂、道德實踐、典型示范和激勵引導促成鄉土道德場景和鄉土道德空間的建構,實現鄉土道德價值的生產。一方面,以學校教育為主,以家庭教育為輔,通過愛國主義教育、文明禮儀養成教育、勞動教育等課堂教育和文明校園創建、禮儀評比、志愿活動等主題實踐催化鄉村公共德育空間的建構,促進鄉土公共道德的生成與實踐,實現鄉土“公德價值”的生產與擴散。另一方面,以家庭教育為主,以學校教育為輔,通過家風家訓親子傳承、村規民約口口相授、傳統文化隱性浸染、家庭德育日常實踐、鄉村家庭教育培訓和鄉村新父母學校建設,依托鄉土“差序性”人際關系格局,充分發揮鄉土傳統倫理力量,催化鄉村私人德育空間的建構,促進鄉土私德的生成與實踐,實現鄉土“私德價值”的生產與擴散。進一步而言,鄉土道德價值生產性命題也內嵌鄉土秩序價值生產性命題。在鄉村教育建構公共德育空間和私人德育空間實現“公德價值”和“私德價值”的生產過程中,“公德”和“私德”的有效養成與內化是對鄉村公共規范和私人規范的認同,是對鄉村公共秩序和私人秩序的遵守,是對鄉村“公域”和“私域”人際互動規則的確認,是對鄉村人際交往預期性與確定性的重構,更是對鄉土秩序價值的“生產”確證。從一定意義上說,鄉土秩序價值生產隱蔽性邏輯內嵌于鄉土道德價值生產邏輯之中,這促使新時代鄉村教育具有鄉土道德價值生產與鄉土秩序價值生產的二重性。
(二)鄉土知識生產邏輯
在鄉村振興戰略和精準扶貧戰略背景下,新時代鄉村教育具有扶智、扶志和扶技三重意義向度。在鄉村學校教育和社區教育雙向協同下,以提升鄉村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為主要目標,以鄉土生活常識、鄉土農技知識、學科專業知識、就業技能知識、職業技術知識為重要內容,以鄉村學前教育、義務教育、普高教育和職成教育四級教育體系為主要依托,通過集體課堂教學、遠程在線教學、個性化定制教學、情景模擬教學、線下實訓演練促成鄉土知識生產和實踐空間的建構。一方面,新時代鄉村教育通過社區教育的主體嵌入、鄉土資源的內容納入、鄉土技藝的意義重構、鄉土場景的功能再造、傳統工藝的價值復歸,建構了鄉土技術知識生產場景與實踐空間,以及鄉土技術知識生產——消費——再生產鏈路,有效延展了鄉土技術知識生產區間,助推了鄉土技術知識的“新時代生產”與“再生產”。另一方面,新時代鄉村教育通過鄉土文化場景的“設置”與“消費”、鄉土文化實踐的推進與再構、鄉土倫理秩序的文化釋義、鄉土社會變遷的歷史展示、鄉土邏輯的學理闡釋與文化溯源、鄉土風俗和鄉土慣習的時代賦意,建構了鄉土文化知識和鄉土社會知識生產場景與實踐空間,助推了鄉村古建遺存的文化保護與開發、鄉土傳說故事和名人傳記的代際傳遞與演繹、村規民約和風俗習慣的內化與傳承,促成鄉土文化知識和鄉土社會知識的“新時代生產”與“再生產”。
(三)鄉土情感生產邏輯
新時代鄉村教育不僅具有知識生產和價值生產的內在邏輯,而且具有情感生產的意義向度,具有鄉土情懷的生產性指向。在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三元協同下,以增強情感回應為主要目標,以新媒體技術為主要依托,以鄉土歷史、鄉土民俗、鄉土人文、鄉土文脈、生命體悟為重要內容,通過歷史教學、人文課堂、民俗活動、社區共育、結對幫扶、生命教育促成鄉土情感的生產與鄉土情感空間的建構。一方面,在新時代語境下,鄉鎮政府和鄉村學校緊密協同,通過在鄉村古建筑、文化遺址的“歷史場景”中開展情景教學,有效發揮鄉土情境的營造力、鄉土物像的感召力、鄉土文化的感染力,建構了鄉土文化符號表達空間,催化受教者對鄉土文化的認同感、歸屬感與眷戀感。同時,通過對鄉土文化的現代闡釋和對民俗活動的現場演繹,有效地喚醒了受教者鄉土文化集體記憶,激活了受教者沉睡的鄉土文化基因,增強了受教者對鄉土文化身份的歸屬感,從而有效地破除了文化“無根感”和情感“無依感”,重構了鄉土情感空間,催化了鄉土歸屬感的生產。一方面,鄉村家庭結構遭遇“現代性”沖擊變得日益“碎片化”,父母陪伴日益缺失,通過構建政府、學校、社區、教育公益組織多主體協同的鄉村家庭教育支持體系、以鄉村學校為中心的教育監護體系、鄉村學校構建類家庭人際關系、社區與教育公益組織開展鄉村“社區共育”和“結對幫扶”活動,有效填補了鄉村家庭教育的主體“缺失”,重構了鄉村兒童的“家庭”情感空間,催化了“家”的歸屬感的“再生產”。另一方面,在鄉村學校教育與社區教育雙向協同下,通過鄉村生命教育的課程實踐,引導受教者生命體悟,“觸發”受教者對自我主體價值與生命意義的內向“追思”,促成受教者對自我主體價值的“復歸”與“確認”,建構主體性情感空間,確認自我“在場”,催化鄉土自豪感與自信心的生產。
(四)鄉土制度生產邏輯
新時代鄉村教育不僅具有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發展制度生產的意義向度,而且具有教化制度和調解制度生產的意義指向。政府、學校、家庭、社區、社會組織多元主體協作,以提升鄉村教育綜合收益為主要目標,以教育管理、教育發展與教育治理能力為主要內容,通過教育實踐、主體納入、關系重構、空間嵌入,促成了鄉土制度的(再)生產和制度空間的(再)建構。一方面,新時代鄉村教育通過完善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健全以政府、社會、社區、學校、家庭五方聯動為基礎的校委會制度,建立教代會制度和家校協同管理制度,健全教育督導制度和監督制約制度,建立教學評估和考核制度,完善鄉村學前教育發展制度、義務教育發展制度、普高教育發展制度和職成教育發展制度,構造了鄉村教育管理和教育發展制度體系,完善了鄉村教育管理和教育發展制度空間,同時在制度空間內以教育實踐和制度實踐為基礎、以教育消費和制度收益為動力實現了制度空間的“再生產”。作為生產邏輯結果,帶來的是新時代鄉村教育管理水平和鄉村教育治理能力的躍升。另一方面,在鄉村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發展制度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也內嵌了教化制度和調解制度生產的隱性邏輯。在推進鄉村教育管理和教育發展過程中,家庭被“納入”鄉村教育主體性視閾。在當前“半熟人化”的鄉土社會,雖然鄉村家庭結構遭受“現代性”的肢解,但是傳統的家庭倫理和家規族訓并未完全消弭,長輩對晚輩的循循善誘和諄諄教導仍然是家庭教化的主要方式,長輩對晚輩的教育懲戒仍然是家庭教化的主要手段[4]67-68。當家庭被納入鄉村教育管理和教育發展的主體性范疇時,“教化”方式(手段)被吸納到鄉村教育管理和教育發展的實現(或實踐)方式之中,并被賦予(鄉村教育管理和教育發展)制度空間生產的功能向度,家庭與學校被賦予教育協同關系的意義向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家庭教化空間被嵌入鄉村教育管理和教育發展空間之中并作為實現鄉村教育管理和教育發展空間“再生產”的重要方式。因此,鄉村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發展制度的生產過程也就有了教化制度生產的內在邏輯。進一步而言,教化過程也是一種調解過程[4]69,教化是對對象進行規則和規范的“言說”,是對行為規范的“標定”,是對對象行為與規范之間“間距”的“指說”,是對對象行為過失的“譴責”,也是對對象行為之間間距的“彌合”(向對象提出行為規范要求并使之膺服)與矛盾的調和,在顯性層面表現為調解原則、程序和方式的隱蔽性“生產”和非正式“確認”,在邏輯結果上表現為對調解力量和教化力量的隱性“認同”。從這一點上來講,調解是“教化”的衍生性功能,調解作為“教化”的衍生性功能被納入到“教化”過程之中,調解空間被嵌入“教化”空間之中并作為實現“教化”空間“再生產”的主要方式,教化制度的生產過程因而也就有了調解制度生產的內在邏輯意義。
(五)鄉土符號生產邏輯
新時代鄉村教育不僅具有鄉土價值生產、鄉土知識生產、鄉土情感生產和鄉土制度生產邏輯意義,而且具有鄉土符號生產邏輯向度。新時代鄉村教育在實現鄉土“道德”和鄉土“秩序”價值生產過程中,鄉村道德課堂(講堂)的設立不僅建構了鄉土價值生產空間,而且搭建了“可視化”的鄉土價值場景;關于鄉村道德公約的圖畫、鄉村典型道德人物的圖像、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畫不僅繪制了“可視化”的鄉土價值愿景(圖景),而且激活了隱匿的道德欲望、激發了潛在的道德夢想,從這一意義上說,在鄉土價值生產過程中通過價值場景的“呈現”與價值愿景(圖景)的“繪制”構造了鄉土價值生產的視覺符號,實現了鄉土符號的生產。新時代鄉村教育在實現鄉土技術知識、鄉土文化知識和鄉土社會知識生產過程中,為“適應”鄉土場景的知識消費需求,鄉土技術知識逐漸轉換為“鄉土文字化”表達、“鄉土言語化”表述;通過鄉土倫理的文化闡釋、鄉土傳說故事和名人傳記的敘述、鄉土風俗和鄉土慣習的時代賦意,建構了鄉土知識生產的意義框架。因此,可以說在鄉土知識生產過程中通過文字轉換、文化闡釋、故事敘述、時代賦意進行二次編碼構造了鄉土知識生產的言語符號,實現了鄉土符號的生產。新時代鄉村教育在實現鄉土歸屬感、“家”的歸屬感與鄉土自豪感和自信心生產過程中,鄉村歷史場景、祭祖民俗儀式、結對幫扶儀式在建構鄉土情感空間之時,也實現了對象化情感體驗、心理賦能與身份再構,促成了(特定)儀式動作指示性意義的生成。換而言之,在鄉土情感生產過程中通過場景設置和儀式建構賦予了(特定)儀式動作的指示性魅力構造了鄉土情感生產的動作符號[5],實現了鄉土符號的生產。新時代鄉村教育在實現鄉村教育管理制度、鄉村教育發展制度、家庭教化制度和鄉村調解制度生產過程中,經隱蔽性“生產”和非正式“確認”的家庭教化和鄉村調解的原則、程序和方法被賦予了“懲戒、約束、規范與管理”的功能性意義向度(被賦予了功能性標志),催生了功能符號化意義生產空間。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在鄉土制度生產過程中通過“規范”功能的生產與確認構造了鄉土制度生產的功能符號,實現了鄉土符號的生產。從本質特征上而言,鄉土視覺、言語、動作和功能符號生產導源于鄉土價值、知識、情感和制度生產邏輯,這促使鄉土符號生產具有內嵌性、附著性、間接性與表征性的特點。
三、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生產邏輯關系
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生產邏輯不只具有單向度關系,各生產邏輯鏈條之間存在著“交互性”與“關聯性”。從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縱向生產邏輯關系上看,存在著鄉村教育——鄉土價值生產——鄉土視覺符號生產邏輯鏈條、鄉村教育——鄉土知識生產——鄉土言語符號生產邏輯鏈條、鄉村教育——鄉土制度生產——鄉土功能符號生產邏輯鏈條、鄉村教育——鄉土情感生產——鄉土動作符號生產邏輯鏈條。這四重縱向生產邏輯是鄉村教育“生產深化”的邏輯結果,并呈現“層疊嵌套”的基本特征。
從新時代鄉村教育的橫向生產邏輯關系上看,鄉土“道德”價值與鄉土“秩序”價值生產過程也是鄉土文化知識和鄉土社會知識的生產過程,鄉土文化知識和鄉土社會知識的生產過程也內含“鄉土道德”與“公序良俗”價值的生產性隱喻,因而存在著鄉土價值生產與鄉土知識生產的“交互性”與“關聯性”;鄉土文化知識和鄉土社會知識生產過程也是對鄉土制度邏輯的感知與習得過程,也是鄉土制度獲得“合法性”實現“自我確證”的過程,同時,鄉村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發展制度與鄉村調解制度生產過程也是對鄉土文化知識和鄉土社會知識的運用、實踐與“檢視”過程,也是鄉土知識體系的完善過程,因而存在著鄉土知識生產與鄉土制度生產的“交互性”與“關聯性”;家庭教化制度與鄉村調解制度的生產過程也是培育鄉土規則依賴感、(鄉村)人際交往協調感和鄉村教育獲得感的(情感化)過程,同時,鄉土歸屬感與鄉土自豪感生產過程也是對鄉村教育主體性和自主性的回歸,也是對鄉村教育原則、程序、規范和方式的確認,因而存在著鄉土制度生產與鄉土情感生產的“交互性”與“關聯性”;鄉土歸屬感與鄉土自豪感生產過程也是對鄉土德性和鄉土內生秩序的認同與內化過程,也是對鄉土內在價值的確認過程,同時,鄉土“道德”價值與鄉土“秩序”價值生產過程也是建構鄉土價值共同體的過程,也是增強鄉土凝聚力與感召力的過程,也是鄉土價值回歸的過程,也是促進鄉土情感“留駐”與鄉土身份重構的過程,因而存在著鄉土情感生產與鄉土價值生產的“交互性”與“關聯性”。這四重橫向生產邏輯是鄉村教育“生產擴散”的邏輯結果,并呈現“交互融嵌”的基本特征[6]。縱向生產邏輯和橫向生產邏輯一同構成了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立體式“生產邏輯網絡”(如圖 1)。

圖1 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生產邏輯關系
新時代鄉村教育的鄉土價值生產邏輯、鄉土知識生產邏輯、鄉土情感生產邏輯、鄉土制度生產邏輯、鄉土符號生產邏輯之間相互影響、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在縱向和橫向維度上形成的“生產關聯”具有“層疊嵌套”與“交互融嵌”的基本特征。
結語
新時代鄉村教育具有“新時代意義”與“新時代價值”,具有“人本”意義向度[7],具有文化和倫理重構的意義表征[8]。從生產邏輯上看,新時代鄉村教育具有鄉土“道德”價值和鄉土“秩序”價值生產邏輯向度,具有鄉土技術知識、鄉土文化知識和鄉土社會知識生產邏輯向度,具有鄉土歸屬感、“家”的歸屬感與鄉土自豪感和自信心生產邏輯向度,具有鄉村教育管理制度、鄉村教育發展制度、教化制度和調解制度生產邏輯向度,具有鄉土視覺符號、鄉土言語符號、鄉土動作符號和鄉土功能符號生產邏輯向度。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生產邏輯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立體式“生產邏輯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