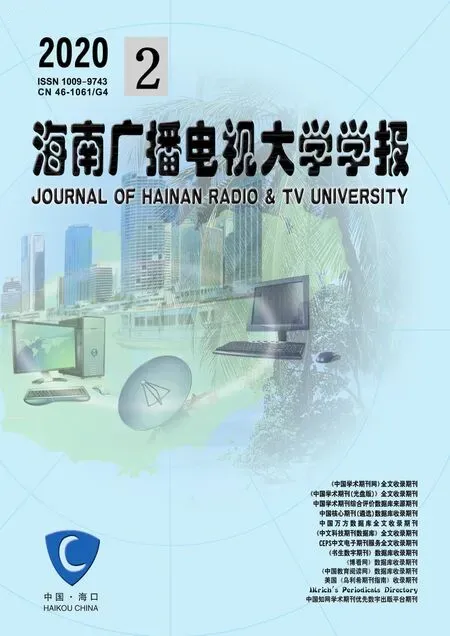數字化生活下“存在焦慮”問題分析及對策
林嘉雯
(福建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0)
數字化生活下,卡斯特曾劃分出的網絡工作者、被網絡連結者、網絡之外勞動者之間界線逐漸消失,所有人在享受數字化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面臨著陷入精神困境的危險。越來越多的存在焦慮“患者”伴隨著數字化生活的不斷推進而出現,在網絡的飛速發展下,無論是“網癮”行為或是“離網”行為的表現背后,都蘊含著急待紓解的存在焦慮問題。
一、網絡“形象危機”與“離網”行為背后的存在焦慮
19世紀,英格蘭一名紡織工勒德因自己的特殊才能即將被新發明的織布機所取代,于是他破壞了工廠設備并砸毀了新發明,來抵制新技術對工廠的改變。時至今日,極端的“勒德分子”行為在現實中較難見到,但不可否認,數字化環境下,無論是深陷于網絡或是迫切希望逃離網絡的行為背后,仍帶有類似對于自身存在的焦慮感。
(一)存在焦慮與網絡形象危機
對深陷于網絡的群體來說,“形象危機”似乎總在發生。和現實生活可見可感的立體形象不同,網絡世界的形象更容易由自己隨心所欲的塑造,比如現實生活中內向敏感的人很可能在社交網絡中開朗健談。但是這種在數字化環境下形象塑造雖然易成型,但卻不易表現出個性。相對扁平化的人物特征,易使這些“被網絡連結者”被打上標簽,比如“飯圈女孩” “哈哈黨”等,直接歸入某類網絡群體中。當數字化環境下的正常表達因大量同質化言論而被淹沒,劍走偏鋒成為一些人的選擇。某些“被標簽化”的網絡個體為了在網絡中留下自己的痕跡,開始追求一種求異表達,沉迷于在網絡上發表意見,以證明自己的獨特,比如一些反社會言論,或是傳播一些未經證實的惡意信息。追求異見的背后,帶有一種數字化環境下對于個體存在的不安和焦慮感。
而另一部分人的存在焦慮則使其在網絡世界中脫穎而出的執念越來越深,為此塑造成“讓別人更想看的形象”成為一種追求。有時這種形象未必符合自己的美學,但卻能迎合網絡上的審美標準,于是他人的評價取代了自己對美的定義,比如白皮膚、尖下巴、大眼睛的“網紅臉”逐漸成為一種美的模板。人們越來越習慣用“美顏”來修飾自己,并把數字美顏后的形象展示在社交平臺上。不僅如此,這種他人的評價也可能改變人的現實行為。對于被網絡連結者來說,網絡跟風已成為一種日常,熱播劇、熱門景點、熱門美食……網絡上別人說好的就一定要體驗,不跟風反而成為異類。而數字化環境下,視頻博客作為記錄自己生活的新興方式,因其生動直觀而廣受歡迎。然而一些視頻博主為了打造別人更想看到的形象,由分享自己的生活轉變為讓粉絲決定自己的視頻內容,隱瞞真實的自我而只展示出粉絲想看的部分。這些行為背后不可否認帶有一種試圖擺脫同質化,突出個人色彩的意味,但卻往往因為數字化環境更新迭代速度太快而又迅速淹沒于同質化內容中,最后往往使得人們越來越深陷于這種循環中不可自拔。
(二)存在焦慮與“離網”行為
存在焦慮感不僅導致易使人越陷越深的“網絡形象危機”,甚至有時影響到了現實生活。當個體的生活完全與網絡捆綁,大多數事務都離不開手機、平板或者電腦時,這些我們用來與外界交流的工具仿佛變成了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因此當人們放下這些電子產品時常常會出現“大腦空白”“短暫失憶”癥狀。而個體往往會將這種“退化”歸咎于工具的過度使用,繼而引發一些對網絡或手機使用的溫和抵制行為,比如一些“離網”行動或者是回歸“慢生活”、不使用手機或電腦的行為。然而相比對于電子產品的討伐,個體對于無法實現自由意志和個人價值所產生的存在焦慮感,才是導致這些試圖逃離網絡行為的源動力。數字化環境下個體的社會價值和社會角色逐步被機器智能所取代,比如過去冥思苦想的文案及配圖,現在只需要智能系統就能自動進行關鍵詞采集,智能編輯、智能配圖、甚至是智能推送和智能分類都能依序做好。不僅是在創作上,在決策環節上,人們也逐步從參與者到最終決策者甚至最終退出決策環節,全權交由人工智能來決定。當機器的運行時間代替了人類勞動時間,人工智能成為正式的“人替”時,對于回歸現實,回歸自我思考的呼聲越來越高,甚至某些科技還在電子產品上推出了屏幕控制時間程序。表面上看數字化產品使用時長的控制、離網行動的發生是為了擺脫網絡束縛,實際上這些行為都是源于個體的存在焦慮。當個體對于其生存價值產生質疑,但又受困于網絡無法脫身時,訴諸于電子媒介的擺脫成為其中一種選擇,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行為。
但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媒介社會是“大腦在頭骨之外,神經在皮膚之外”的社會,被網絡所捆綁但又無法離開的情況往往是生活常態。人們了解過多的沉迷網絡社交易患上抑郁癥,然而這則信息本身就需要登錄網絡社交平臺才能了解。“逃離網絡”更像是一種暫時的躲避,存在焦慮無法得到緩解,甚至因為手機沒電沒WiFi而導致的崩潰狀態時有發生。
二、數字化環境下存在焦慮的生成分析
雖然我們能夠預見某些技術的發展,但往往真實的未來遠超我們的幻想。比如二維碼出現時,沒人會預測到最后它會運用在支付手段上。就影響程度來說,當前某些數字化產品的誕生甚至直接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當原本用于改善生活或協助人類發展的科技手段超出個體所能接受的范圍,甚至改變了個體生存狀態及生存價值,存在焦慮悄然而生。
(一)人際交往中的情感抽離
首先,人類在生產與交往過程中,意識和語言因需要而產生,因此意識和語言具有社會性。然而這種社會性在機器思維面前正不斷被抽離。數字化環境下的機器思維,省略了自然進化中意識誕生的漫長歷史與曲折歷程,其本質和表達被簡化為算法、數據和代碼,缺乏意義的維度(1)吳勝峰:《馬克思主義意識理論視域下的人工智能技術批判》,《哲學動態》2019年第4期。。而當這種機器思維方式指涉現實生活時,首先就可能因其形式化的處理模式,使得現實交往中的個人情感不斷被抽離。快節奏的生活下,如果能用形式化的處理方式應對日常生活,效率自然能大大提高,但日復一日的形式化易使個體陷入一種固定模式,不需要多余的情感來降低效率。長此以往,抽離情感的生活方式易使得個體的內在驅動力不斷減弱,對于自我的無意義感則不斷增強,存在焦慮也因此產生。只聽相同的觀點,只看自己所關注的模式化個體,在數字化生活中,似乎更容易被私人訂制的算法和信息推送束縛住,從而困在信息繭房中不可自拔,不僅無法化解已有的存在焦慮,更可能使之不斷加深。
其次,就網絡世界人與人交往來說,雙方不對等的情感輸出易造成“空場”。隨著數字化的不斷發展,為了使虛擬身份更加有信服力,不僅是電子文本,圖片和視頻等方式也被用于塑造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使得個體能夠創造出一個與現實中不同的自我。然而與現實身份的產生會附帶某些人格特質不同,個體在網絡世界中的身份全憑虛構,由于缺少了應有的經歷,其附帶的人格特質只能通過想象來進行補充。當雙方進行交流時,對于沉浸在虛擬人格特質的一方來說,其情感的產生和輸出同樣建立在對這些特質的認識上,但對于虛構出這些特質的一方來說,卻未必能做出真實回應,長此以往雙方交流情感上的不對等,使得交往中的“空場”范圍越來越大。而當個體本身長期沉浸在這種虛構特質時,很可能在回歸現實后產生挫折感。無論是虛擬空間難以得到的情感回應或是虛擬與現實情感間的巨大差距,都易產生對自我存在的不確定性與焦慮感。
(二)生活目標的設定偏差
首先,數字和符號搭建起來的虛擬空間為個體提供了一個可以暢游其中的場所,個體無時無刻不在其中接收著新信息。然而海量信息的涌入在打亂原有生活節奏的同時,也使得生活目標面臨現實與虛擬的錯位。虛擬空間給予了一個無需成本和時間就能逃離現實的避風港,個體在網絡上“無根化”的飄移和游走常使其陷入精神上的一種放空和滿足感(2)蔣建國:《網絡媒體的價值沖突與文化反思》,《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然而當轉回現實生活時,時空感的回歸使其感受到“正在襲來”的壓力,導致出現這樣的錯覺:現實生活僅僅只是為了維持生存而進行的,只有網絡生活才是真正歸自我所有的。于是有些人的生活目標出現了偏差,無止境的網絡游蕩和信息搜尋取代了現實目標的逐步完成。然而當這種錯位造成的違和感越來越明顯:網絡信息的獲取意義不明,導致網絡生活目標始終找不到落腳點;而現實生活目標雖然可實現卻一事無成,由此個體產生了生存焦慮感。
其次,個體缺乏穩定內核,易使生活目標的設定受到外界影響。個體的穩定內核來自于對生活本身的一種追求,然而數字化環境下這種穩定內核的生成受到了影響。越來越多販賣焦慮的“生活現實”“毒雞湯”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平臺,入侵數字化用戶的思維,腐蝕個體對于生活的信仰。個體對于生活的專注力正在被迫轉向別處,對于他人生活的熱情蓋過了對于自己生活的熱情,而數字化環境又為窺探別人生活提供了便利,因而線上線下瘋狂的“吃瓜”群眾成為一種常見群體。人們對于生活本身的追求被各種各樣的信息持續性打斷,對于生活的動力和熱情也被慢慢消磨,從而導致個體穩定內核的難以生成,生活目標的設定也易受外界干擾。在被互聯網的多種觀念和偏離自己生活的欲望蠱惑時,前一秒剛產生的生活目標很可能在這一秒被打破重構。長此以往,由于搖擺不定的生活目標與經常面臨重建的生活信仰,易增加個體對于生存的焦慮感。
(三)數字化環境下的認知顛覆
數字化環境下對于自身、對于科技與人的關系的認知顛覆,也是引起我們焦慮感的原因之一。首先,焦慮感來自于個體意識到的自身能力退化。馬克思曾經對人的異化做出過這樣的評價,即工人在從事動物性的、本能性的活動時,他們像人。 工人在從事屬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時,他們像動物。這樣的情況在當下仍然存在。科技的迅速發展給我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我們的生存狀態。當我們在從事“自由自覺”活動時,由于自身能力的退化,我們被“馴服”并按照智能所指引的方向前進。我們逐步習慣了微博140字內的表達或者是抖音、快手15秒內的表演,習慣了用碎片時間取代完整時間進行閱讀或思考。正如麥克盧漢所說,“如果說曾經的我是一個徜徉在文字海洋中的潛水員,那么現在的我就像一個滑翔在海面的快艇手(3)何王吉:《尼古拉斯·卡爾.谷歌會不會使我們變笨?》,《世界科學》2018年第11期。。”保持專注的能力正逐漸消失,更多時候我們作為一種圖像閱讀器,文字反而成為阻攔我們獲取信息的攔路虎。然而對于現在的人們來說,這種能力退化卻并非不可感知,甚至是在按智能所指引的操作過程中,人們也能感受到能力退化帶來的一種違和感。無處不在的表情包代替了真實情感的表達,交友軟件通過算法進行匹配的方式取代了實際交流,個體的分析能力、表達能力也正在不斷退化,甚至是方向感都因對GPS的無限依賴而逐步喪失。當自身能力的退化而導致個體不得不與技術時時刻刻聯系在一起時,對能力退化的感知,使得個體違和感不斷累加的同時,也使得個體對于所在時空的陌生感和對于自身的無意義感不斷加深,從而產生并不斷加重存在焦慮感。
其次,對于未來確定性的喪失,也導致個體存在焦慮的不斷加深。智能機器最初誕生的目的是為了輔助人類,節約更多時間留給個體的自由活動,人機關系發展趨向的確定性還能為人所把握。然而隨著數字化環境下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在各種領域拓展,原有的未來發展趨向在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面前變得不再確定,對于“人應該置于何種地位”的質疑使得個體對自身的反思和焦慮感不斷增加。比如對于“機器換人”問題,“人機互補”是我們的理想預設,然而現實中出現的種種跡象促使我們意識到“人機對立”的可能性。未來的人機關系會走向競爭還是合作?人工智能究竟是人造物還是已經生出其自主意識?類似的不確定性取代了可預見性,甚至引發了一部分人對于“人類地位最終被取代”的悲觀情緒,由此加深了存在焦慮感。
三、數字化生活下存在焦慮的紓解
存在焦慮并非數字化生活下專有癥狀,但其對數字化生活的沖擊和影響卻可能遠超我們的想象。要進一步推進數字化生活,就必須正視數字化環境下出現的精神困境,并找到有效紓解方法。
(一)社會層面:科技人文情懷的回歸
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無論是從日常生活中或者是精神上,都會帶來一種沖擊感,但是這一種感受及其帶來的一些影響并不能作為指控“發展原罪”的依據,這一過程是邁向更便捷更智能生活的必經之路。人們對于轉型的接納需經過一個調試過程,因此要緩解轉型中帶來的焦慮感,首先要正視這種“轉型陣痛期”。既要避免對于“陣痛期”的過分強調,使得“技術災變論者”數量急劇增加;同時也要加強對于“陣痛期”前后的預測,對可能產生的變化有一定應對方法。其次,在“陣痛期”中,有效緩解個體存在焦慮,實現個體的有效關懷,就必須要關切個體的內在需要。比如對于數字化生活中的人際交往問題,不僅要通過輿論引導等方式,促進個體自我思考與關注生活,更要重視社會氛圍的塑造,以喚醒個體的情感表達欲望,有效跳脫出語言、思維匱乏的交往模式,擺脫機器思維對我們的過分干預。要盡力將模式化的勞動讓位或轉化為富有情感交流的勞動,促使勞動者能夠在勞動過程中獲得自我滿足感及精神超越,從而有效避免“空場化”、模式化交往的不斷加劇。再次,要增加個體的體驗感及獲得感,把偏向展示性的數字化技術真正轉化為便民性,從而化解價值鴻溝下的存在焦慮感。隨著硬件及軟件設施的不斷更新,數字化用戶在信息的接收與輸出上的差距已經逐漸縮小,而由于價值觀不同所導致的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差距卻在不斷拉大。要縮小這一差距,就必須避免工具理性主導,加強民眾的參與感,從而合理塑造人們在轉型期的價值觀,注入人文情懷,安撫存在焦慮。
(二)個人層面:思維的突破與價值抉擇
數字化生活下,要有效緩解存在焦慮癥狀,不僅是社會層面,從個人層面上也需積極探索紓解方法。康德曾提出關于“人”的四個追問,即我能認識什么、我應當做什么、我能期望什么、人是什么,這四個追問對于緩解數字化生活下的存在焦慮仍有重要啟示。首先,就“人是什么”和“能期望什么”的追問來說,唯有正視“人是什么”這一問題并合理期待人的進一步進化,才能突破思維上的局限。人的創造和發展的前提就是確證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和價值,以及生存和發展的根據和意義(4)韓水法:《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主義》,《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終是推動科技創造與發展的源動力。我們對于未來更好生活的期望應該是建立在對“人”的清醒認知之上,不僅是要避免科技盲從朝著各個領域不斷擴展,更要避免信息崇拜對于個體穩定內核的不斷消耗。科技或許能夠提升我們肉體上有限的能力,使我們變成“半合成人”“合成人”去完成過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永遠不能代替人類進行思考或創造出人的情感體驗。因此,唯有對人抱有合理認識與合理期待,才能緩解缺乏確定性與認同感所帶來的存在焦慮。
其次,就“能認識什么”和“應當做什么”的追問來說,如何做出數字化生活下的價值抉擇值得我們深思。數字化生活下我們既看到了碎片化對我們生活狀態的改變,甚至常常有“世界上不缺少也不在乎一個只有碎片價值的個人”的焦慮,但我們同時也對碎片化時代下保持著完整自我的人充滿憧憬與向往。要緩解存在焦慮,不僅要有對價值的合理取舍,在保持自己完整性的同時適應碎片化時代的特性,同時更需要無止境的學習來為價值的合理取舍和有效目標的設定做鋪墊,而不是困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中等待未來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