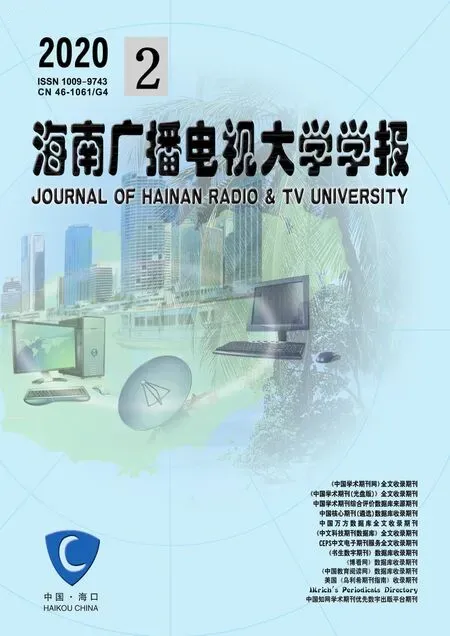建立我國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研究
馮顯咪
(中移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部法務 長沙 410000)
一、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內涵和意義
(一)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內涵
非婚生子女是指非于婚姻關系存續中受胎所生的子女,非婚生子女認領依通說可分為任意認領和強制認領兩種。任意認領也稱為自愿認領,是指生父主動向非婚生子女承認自己為其生父行為。強制認領是指生父不主動任意認領時,相關利害關系人有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子女與生父存在血緣關系,并經訴訟程序責令生父認領。認領權的行使,本不以訴訟方式為必要,只是在現實生活中,要使生父主動認領其非婚生子女并非易事,為逃避對子女的撫養而拒絕行使認領權的男方也不占少數,強制認領仍有存在的實益。認領之訴的功能在于使非婚生子女經由訴訟,將之視為婚生子女,且此效力溯及于其出生之時。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出現,可以彌補子女無法被推定或經準正制度而成為婚生子女的缺陷,是通過法定程序使非婚生子女實現與婚生子女同等權利的重要途徑(1)鄧學仁:《親屬法修正后之親子關系》,《月旦法學雜志》2007年第146期,第149頁。。我國法律并無明文規定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審判實踐中也存在子女或其生母請求生父履行撫養義務或生父請求確認與子女親子關系的案件,但由于尚不構成一個獨立案由,法院往往將其作為請求給付撫養費或贍養費糾紛立案審理。然由于缺乏統一明確的法律適用規則,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中許多程序問題和實體爭議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在執行過程中步履維艱,因此,建立我國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制度仍有其必要性。
(二)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意義
1.強制實現法律上的親子關系
隨著社會理念的多元化,非婚生子、婚外生子、通奸生子等現象在生活中屢見不鮮。但要期待生父自愿認領其子女并非易事,如果不設置一個具有法律強制力的親子關系實現機制,難以保障非婚生子女合法權益。有鑒于此,各國都在立法上確立了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即使非婚生子女與生父具有事實上的血緣關系,若未經過強制認領之訴或生父任意認領,則二者之間也不能發生法律上的親子關系。強制認領須以訴訟方式為之,通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能夠基于事實上的血緣關系強制創設并實現法律上的親子關系,并且這一確定判決的既判力對任何第三人都生效,因而又被稱為強制認領。這一訴訟的首要意義在于強調并貫徹血緣主義,使子女與生父在血緣上與法律上關系趨于一致(2)覃海逢:《非婚生子女認領制度的若干理論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第3期,第155頁。。
2.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實體權益
我國《婚姻法》的相關規定雖然明確了非婚生子女權利受法律保障,但在現實生活中,非婚生子女仍存在著一定差別待遇,例如,涉及子女房產的處分情形,就很難使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護,因為未成年子女房產的處分應由其父母共同決定,若其生母想出售該房產,而其生父下落不明無法為任意認領,若不通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將很難認定生父與子女親子關系(3)戴炎輝,戴東雄:《中國親屬法概要》,臺北:三文印書館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83頁。。通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這一程序,將使非婚生子女與其生父的身份關系從事實關系轉換為法律關系,既不必觸動傳統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尊重了家庭內部秩序的和諧穩定;也從客觀上規制了生父為逃避法律責任,拒不承擔子女撫養教育義務等情形出現。
3.符合認領制度向客觀主義轉變的法進化方向
就非婚生父子女關系的確定,從傳統到現在主要呈現為兩種不同的立法態度,即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主觀主義強調必須經過生父做出認領子女的意思表示行為,始能承認父子女直接有親子關系。主觀主義完全站在父權主義立場,對非婚生子女認領設置了較高準入門檻。自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通過后,絕大多數國家的非婚生子女認領制度已開始向客觀主義修正。客觀主義強調,即使未經任意認領,只要存在父子女血緣關系的事實,就可確立二者之間親子關系,因此也被稱為血統主義。客觀主義承認強制認領對任意認領的補充性,如美國《統一父母身份法案》便規定了確認生父需依法提起民事訴訟。因此引入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彰顯了子女本位的現代親子法思想,符合認領制度向客觀主義轉變的法進化方向。
二、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性質爭議及小結
(一)確認之訴說
將認領訴訟看作確認之訴的學者認為,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是子女要求其生父確認自己為其子女的訴訟;是以請求法院確認父子女關系存在為目的的確認,并認為自然的血緣關系基礎是發生法律上親子關系的前提(4)王甲乙等:《民事訴訟法新論》,臺北:三民書局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836頁。。此說學者認為認領是事實通知或觀念通知,親子關系的存否取決于有無血緣關系的事實,而不在于有無認領行為,如果生父拒絕主動認領的意思時,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可以提起認領之訴。因此,只要能確定父子女在自然上血緣聯系的存在,法律關系也應隨之而生。確認之訴說從客觀主義立場出發,將認領的性質看作血緣關系的“通知”,認領訴訟是法院以判決代替生父認領或不認領的確認宣言。如果法院確認子女與生父存在血緣關系,則應當以原告勝訴的判決代替生父認領;反之,如果法院無法認定血緣關系事實存在,則應當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亦即不問原告是否勝訴,認領之訴在性質上都是確認之訴。
(二)給付之訴說
給付之訴說認為,認領在性質上屬于意思表示,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是訴請法院以強制判決形式命生父對子女做出認領的意思表示(5)[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林劍鋒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頁。。并認為自然上血緣的關聯須經生父認領才能發生法律上的關系,法律上的親子關系未發生則不能成為確認之訴的對象。在給付判決確定后,對于此類判決的執行屬于意思表示請求權的執行,可直接以法律擬制方式予以實現,無論生父是否做出了意思表示,自判決確定時法律視為生父已作出認領子女的意思表示行為。給付之訴說一經形成,對其最廣泛的批判便是身份行為的認領不宜通過訴訟及法院判決加以強制進行,但是,若將認領理解為是對存在自然血緣關系的事實加以認可,而非意思表示的話,這樣的批判亦顯得不夠恰當。然而,隨著現代多數國家開始導入死后認領制度,給付之訴說已顯然無法適應死后認領訴訟的需要,因為當父親出現死亡情況時,認領請求人已無法請求死者作出關于認領的任何意思表示行為。因此,時至今日,已幾乎沒有學者主張給付之訴說的觀點了。
(三)形成之訴說
形成之訴說認為,認領之訴是基于血緣上的親子關系,而以在二者間形成法律上的親子關系為目的的訴訟(6)陳棋炎等:《民法親屬新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86頁。。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多著眼于確認之訴說與給付之訴說對于定性認領訴訟的矛盾之處,從認領訴訟提起的條件、事實關系變動的原因、判決的法律效力出發,批判前兩種學說的不周延之處,進而得出形成之訴說的結論。如學者吳明軒認為,認領之訴的目的在于請求生父主動作出認領子女的意思表示,在形式上雖然與給付之訴最類似,但此訴一經法院命生父認領的判決確定,即發生與任意認領同一的效力,其結果足以創設親子間身份關系,這種性質與一般的給付之訴有區別,在實質上仍是形成之訴。日本學者山木戶克指出,僅由于現實的血緣關系并不能當然地認可法律上親子關系的存在,依判決僅對血緣上的父子女關系加以確認是不夠的。另有學者認為,考慮到認領之訴對于欠缺意思表示能力的人也可提起,甚至對于已死亡的生父也可為之,給付訴訟說顯然不太可采(7)陳愛武:《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釋精釋精解》,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頁。。
(四)小結
關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性質學說,在學界可謂觀點林立,尚未形成通說。筆者認為形成之訴說最可采。首先,大多數國家、地區都已承認了死后認領訴訟,如法國親子法340條、日本人事訴訟法第42條、我國臺灣地區于2007年民法修法時也增訂死后認領訴訟。因此將認領之訴定位為請求生父做出意思表示的給付之訴說并不妥當。其次,確認之訴說認為法律上的父子女關系本質系因自然血緣關系的存在而發生,認領判決只不過是對此事實加以確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確認判決是對現在的法律關系所做的確認,其效力是相對的,僅是對基準時的權利義務狀態加以固定,而認領判決效力可及于第三人,在判決前不允許做出以父子女關系為前提的主張;并且認領訴訟是在非婚生子女與生父之間創設法律上的親子關系,其作用并不僅限于確認。認領之訴的判決對第三人亦有效力,且具有創設法律關系的效力,即形成效力;故本文認為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是規范親子關系發生的訴訟,以法律上的親子關系為訴訟標的,經過認領判決的法律擬制,將作為事實上的親子關系變成具有拘束力的法律關系,生父對子女便具有了撫養、監護等具體義務,子女對生父取得了繼承權。
三、我國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立法與司法實踐現狀
(一)立法現狀
我國對于非婚生子女保護的立法原則很先進,早在1985年的《繼承法》就賦予非婚生子女法定繼承權,2001年修訂的《婚姻法》第25條還專門對非婚生子女權利做出了規定。這與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世界潮流相一致,但我國在非婚生子女認領領域,缺乏周全的具體制度來落實這些原則,立法上有關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程序規范更是呈現缺失的狀態,并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且因為非婚生子女認領事關雙方當事人血緣關系,繼而引起非婚生子女利益保護、現存家庭感情沖突及諸多潛在關系人的利益沖突,對家庭、社會的穩定亦有重要關系(8)羅杰:“中國民法典之親子關系立法模式的改進”,《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第166頁。,因此,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在當事人適格、證明、訴訟時效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按現有子女撫養糾紛或監護權糾紛等訴訟來處理,均難以全面保障非婚生子女權益。
其實早在1939年,我國《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中就有過對強制認領的規定,根據該條例第16條,非婚生子女經生母提出證據證實其生父者,得強制其生父認領,與結婚所生子女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制訂的司法文件《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第三部分第250條還明確將“生身父母確認糾紛”列為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由下的獨立性案由。但遺憾的是,2007年10月通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最終將原試行規定中的“生身父母確認糾紛”這一案由取消了,直到2011年2月通過的現行《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也未明確對非婚生子女認領糾紛進行規定。其后的這一類型糾紛僅能附隨在其他婚姻家庭、繼承糾紛的案由中來處理。然而隨之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 年7月出臺了《婚姻法解釋(三)》,其中第2條第2款填補了我國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中責任推定法則運用的空白,可以說是我國強制認領的雛形,但其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技術導致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適用法理、程序規則、具體內容等諸多必要問題被忽略;況且,我國民事訴訟法與實體法上規定多有捍格,《婚姻法解釋(三)》中有關于非婚生子女確認的規定,而訴訟法上卻無相應之訴訟種類,這些都造成司法實踐中的不便和同案不同判情況的頻現。
非婚生子女儼然已成為不可回避的社會問題,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將對子女與生父的身份關系、財產關系產生重大影響。這不僅關系到子女對生父的繼承權和贍養義務以及生父對子女的親權和撫養義務,還涉及到作為訴外第三人的婚生子女程序保障問題,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意義重大。為了適應我國日趨復雜和多元化的親子關系實踐需要,更好地維護家庭關系中非婚生子女合法權益,有必要改變立法上只作宣示性規定的做法、細化親子關系訴訟類型,補充訴請認領非婚生子女的具體制度,構建程序完備的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
(二)司法實踐現狀
近年來,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在我國大陸地區的審判實踐中也愈發頻現,比如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請求認領的訴訟,以及少量在夫妻離婚后、由生父提起的要求認領子女并變更撫養之訴。但由于我國在立法上并沒有明確規定此類訴訟,對于訴請認領的適用條件和具體程序幾乎是一個空白,有關親子關系證明方面的一些技術性規范也很粗淺,導致司法實踐的不便和司法裁判的混亂。試看以下幾個案例。
案例1:甲男與乙女未婚生育一子丙,且雙方在丙出生前已分手。后甲男否認與丙之間存在親子關系,乙女遂訴至法院,要求確認甲男為丙的生父、并為丙辦理出生證及落戶事宜并支付生育費、撫養費。法院按撫養費糾紛立案,在審理過程中甲男未按約到場進行親子鑒定,法院依《婚姻法解釋(三)》第2條第2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2條,推定甲男與丙之間存在親子關系并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9)參見“卓某與簡某某撫養費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新余市渝水區人民法院(2014)渝民初字第01888號。。
案例2:甲的生父乙于2011年7月因交通事故死亡,甲于2011年11月出生,是乙的未婚遺腹子,乙生前曾與前妻共同購買住房一套并生育一子丙,后二人于2012年6月協議離婚,目前房屋產權證所有人姓名仍為乙的前妻并由其實際占有。甲以乙的繼承人丙為被告訴至法院,主張乙為自己生父并要求依法分割乙去世后留下的該住房遺產。法院以繼承糾紛立案,由于乙已死亡,甲訴請所需的直接證據DNA樣本無法取得,甲遂申請對丙進行血親鑒定,丙拒絕。法院認為《婚姻法解釋(三)》第2條第2款“是法院處理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規定,涉及的是親子關系糾紛,而非血親關系糾紛”,因此不能適用親子關系的間接強制,認為甲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甲乙之間存在父子關系,甲不具有繼承人身份,以原告不適格為由駁回了甲的起訴(10)參見“陳某甲與趙某甲、趙某乙、宋某繼承糾紛一審民事裁定書”,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法院(2014)中少民初字第131號。。
案例3:某有婦之夫甲與一女子相戀并發生關系,該女子于1996年生育一子乙,經協商,甲同意借錢給女子作為乙在職高、大專期間的生活和學習費用。后由于甲未兌現此承諾,乙于2012年訴至法院,請求確認原、被告間父子關系,并由被告補償原告讀書期間所有學費,并按月支付生活費2000元直至原告能獨立生活為止。對此,甲對與乙之間的父子關系不予認可。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甲乙之間是否存在親生血緣關系,最終按婚姻家庭糾紛立案,并根據甲一直與乙的生母就乙的生活、學習費用進行協商以及拒絕做親子鑒定行為,認定本案舉證責任轉移至被告甲承擔。且由于甲未能提供有效證據否認甲乙間存在親子關系,故推定原告請求確認親子關系的主張成立。為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被告應承擔對原告的撫養和教育義務(11)參見“周某甲與徐某婚姻家庭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浙杭民終字第1888號。。
以上3個案例爭議焦點都是非婚生子女與生父之間親子關系的確認,實質為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且法院都引用了《婚姻法解釋(三)》第2條第2款作為判決依據,案例1為生母訴請生父認領其非婚生子并主張相應撫養費用;案例2為非婚生子在生父死亡后,向生父的第一順位法定繼承人訴請認領并主張遺產繼承權,即死后認領訴訟;案例3為非婚生子訴請生父承認與自己具有親子關系,并向其主張生活、學習等費用。但法院分別將其認定為撫養費糾紛、繼承糾紛、婚姻家庭糾紛來處理,且認定非婚生子女與生父之間親子關系存否時的程序標準并不統一。案例1的法院依據被告拒絕鑒定行為,直接推定原告主張的親子關系存在;案例2的法院認為法條規定的間接強制不能適用于血親關系確認,認領訴訟中生父已死亡的,《婚姻法解釋(三)》第2條第2款并無適用余地;案例3的法院認為被告的拒絕鑒定行為將導致親子關系舉證責任由原告轉移至被告,被告無法否認親子關系的,始承擔親子關系存在被認定的不利后果,在運用責任推定法條決定是否認定親子關系存在時,還結合了被告在生活中曾以非婚生子女父親身份行事的表現等間接事實。從以上案例可知,各地法院對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處理方式各異,對于《婚姻法解釋(三)》的適用方式也并不統一,這些都反應了我國親子關系法立法的相對滯后。現行民事訴訟法關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仍存在管轄原則不明確、當事人資格范圍與適格標準不統一、證明方法與證明標準不明確、時效規定過于片面等重大缺陷,對其依民事訴訟法的一般性規定加以解釋難以解決司法實踐中諸多問題。這就需要我國借鑒域外程序立法經驗,并結合我國家事審判特點對上述問題做適當調整,以對完善我國的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有所助益。
四、我國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完善建議
(一)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管轄原則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多發生于該身份關系生活的中心,即非婚生子女、父母住所地,為了維護公益并方便調查取證,規定此類訴訟的專屬管轄原則,有利于當事人提起認領之訴,且顧及子女最佳利益及婦女權益。我國法律對于親子關系案件并沒有諸如家事事件法或人事事件法的整體程序規范(12)王琦:《聚焦我國家事審判改革的幾個面向》,《政法論叢》2018年第1期,第105頁。,對于認領之訴的管轄問題也沒有特別規定,僅在2005年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建議稿中提及了對親子關系案件的專屬管轄,其中第437條指出,要求確認生父母的訴訟由子女住所地或者其死亡時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但是這些修改條文沒有被我國立法機關接受,最終并未出現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中。鑒于親子關系糾紛與一般民事糾紛相比所具有的倫理性、公益性等特性,應當把包括認領之訴在內的人事訴訟管轄,從一般管轄中分離出來,明確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案件適用特殊地域管轄乃至專屬管轄原則。考察比較法上的相關規定發現,我國臺灣地區規定了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專屬于子女住所地法院或者父、母住所地法院管轄。香港地區法院則將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歸為確定當事人身份的特殊對物訴訟,依據當事人住所地或慣常居所地確定管轄權(13)秦瑞亭:《國際私法(第2版)》,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70頁。。日本關于子女認領,專屬于子女一方普通審判籍地的法院管轄(14)郝振江,趙秀舉譯:《德日家事事件與非訟事件程序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頁。。建議我國將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管轄法院規定為,原則上由非婚生子女所在地法院專屬管轄,非婚生子女所在地包括非婚生子女住所地或其死亡時住所地;由生母提起認領之訴的,生母所在地法院也有管轄權;如果非婚生子女與生母在國內均沒有住所的,以生父所在地法院為管轄法院;如果依上述規定仍不能確定管轄的,則由最高法院指定管轄,或者由法律明確規定歸某個法院管轄。
(二)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當事人
首先,應當明確認領之訴當事人的特別資格 民事行為能力受限制的成年子女,如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成年子女,在認領之訴中,也應認可其具有訴訟行為能力,但這一點不適用于未成年子女。因此已滿十八周歲的非婚生子女,在認領案件中,具有訴訟行為能力,可以作為原告獨立提起認領之訴;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和無民事行為能力的非婚生子女,不具有認領之訴的訴訟行為能力,但認領之訴不像離婚之訴只能由身份關系本人提起,因此在以認領父子女身份關系為標的法律爭議中,可以由法定代理人代理無訴訟行為能力之人提起和進行訴訟。又考慮到身份行為的特殊性,若訴訟內容會使無訴訟行為能力的人與其法定代理人產生利益沖突時,為保護非婚生子女利益,可以由當事人申請或法院依職權選任律師、非婚生子女居住地居委會、村委會代表等為其訴訟代理人。
其次,應當對認領之訴中當事人的適格標準進行界定 非婚生子女本人是認領之訴的當然適格原告,因為子女對該訴訟有著最直接的訴之利益。子女的生母或其他近親屬在子女死亡或喪失民事行為能力、以及作為未成年子女代理人的兩種情況下可提起認領之訴。考慮到《婚姻法解釋(三)》對于認領之訴的主體表述為“當事人一方”,并沒有對胎兒的訴權進行限制,而我國現實生活中也確實存在由生母作為法定代理人起訴請求確認尚未出生的胎兒與男方具有親子關系情形,因此應承認胎兒也具有認領之訴的原告適格。對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適格被告,原則上應確定為生父。此外,由于訴訟標的是父子女間身份關系,本案法律爭議并不會因當事人之一方的死亡而終結,若原告死亡的,于其死亡后一定期限內有權續行訴訟者可承受訴訟。若非婚生子女起訴時推定的生父已經死亡,則可由生父的直系血親卑親屬等承繼被告資格,無上述血親作為繼承人的,如果按照目前我國的當事人適格理論,訴訟對審結構中的被告已不存在,該非婚生子女的權益難以救濟,此時應借鑒國外將檢察官引入人事訴訟的立法例,規定將檢察官作為此種情況下認領之訴的被告。
(三)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證明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中,最關鍵的問題在于父性關系如何被有效證明。《婚姻法解釋(三)》規定了親子關系存在的法律推定方法,該款是《證據規定》第75條在非婚生子女的認定程序中的具體適用。這種證明方法是基于間接事實來確定親子關系,原告需對親子關系存在的前提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即可導致難以證明的父子女關系存在的原因事實獲得認定。由于親子關系中的推定仍存在一定或然性,因此在運用此證明方法時,除了具備司法解釋規定的條件,法院還應權衡支持原告訴訟請求對未成年子女的影響、子女是否因年幼適宜隨母親生活等情況,綜合考量是否判決親子關系存在。親子關系推定是認領之訴的一種間接證明方法,另一種直接證明親子關系的方法為親子鑒定,即利用DNA鑒定取得科學性證據,法官在此基礎上自由心證做出認定。由于親子鑒定對于肯定性父子女關系證明準確率超過99.85%,現今各國多運用親子鑒定取代間接證明;我國《婚姻法解釋(三)》的出臺賦予了親子鑒定合法的依據。
對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是否應為其規定高于一般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各國規定及實務態度不盡一致。德國認為確認生父身份案件的證明標準與一般民事訴訟相同;而英、美兩國對其要求比一般民事訴訟適用的證據優越原則更高的標準;而日本又有裁判認為須“依據任何人均不能懷疑的證據。”筆者認為,證明標準的設定不僅應根據案件類型決定之,也要考慮到當事人證據收集能力、法律本身的價值判斷等。《民訴解釋》第108條實際上確立了我國一般民事訴訟案件“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8],該標準較英美法系普通民事訴訟的“優勢證明標準”已經相對為高,而具體到我國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由于引入了法律推定制度,原告的舉證負擔將大大減緩,對于其基礎事實之證明采用與一般民事訴訟相同的標準不致過于嚴苛,也能平衡親子關系訴訟中尊重血統真實的觀點。因此,對我國認領之訴的證明標準可從兩方面來把握:第一,按照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即使當事人所舉證據并不充分,若足以使法官對于可能存在親子關系的事實達到內心確信,則已滿足舉證責任轉換條件;第二,在適用親子關系推定時,應在間接證據之間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使裁判者達到內心確信。(四)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訴訟時效
我國并無關于認領訴訟行使期間的規定,域外是否對該期間加以限制及對其長短的規定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徑庭。在對認領訴訟規定了起訴期間的國家,對該期間性質的界定也不盡相同,大致有訴訟時效和除斥期間兩種。鑒于認領權具有形成權性質,其行使本不以訴訟為必要,一般也不嚴格受消滅時效和起訴期間的限制(15)邵明:《論法院民事預決事實的效力及其采用規則》,《人民司法》2009年第15期,第78頁。,同樣,即使原告未在法定期間提起認領訴訟,也并不妨礙其于訴訟外請求生父認領;加之當今各國親子關系法對于強制認領原因,已趨于向概括主義立法模式轉變,舊時法定主義模式下的弊病已隱而不顯。基于此,筆者認為應將認領訴權行使期間的性質界定為訴訟時效,而非逾法定期間未行使將導致權利消滅的除斥期間,作此解釋不僅能在最大程度上維護非婚生子女與婦女權益,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利害關系人積極行使法定訴權。
我國將來對于非婚生子女認領之訴的訴訟時效規定,應著眼于認領的客觀主義與身份關系安定性平衡。由于生父主動認領子女并無期間限制,且通過訴訟強制認領的前提是真實血緣關系的存在,因為血緣關系的存在情況并不會隨時效期間的經過而改變。對于當事人在生父尚生存時提起的認領訴訟,亦不應受一定法定期間限制。但對于生父死亡后的認領訴訟,由于生父死亡將對繼承產生相當影響,對第三人既得權利也影響甚巨,如果經過時間太久,由于事實關系不明易產生弊病。因此,此時親子關系的身份安定性考量應放在首位,對死后認領訴訟規定一定時效期間的限制,規制欠缺訴的利益而頻繁提起的濫訴情況之出現。建議參考日本立法例,區分生前認領與死后認領的訴訟時效適用模式。對生前認領訴訟原則上不設訴訟時效加以限制,只要是在生父生前提起認領訴訟的,被告不得提出已逾訴訟時效期間的抗辯;而對死后認領訴訟的請求權設置三年訴訟時效期間的限制,以兼顧身份關系動態安全與靜態安全的平衡,督促適格原告在生父死亡后盡早提起認領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