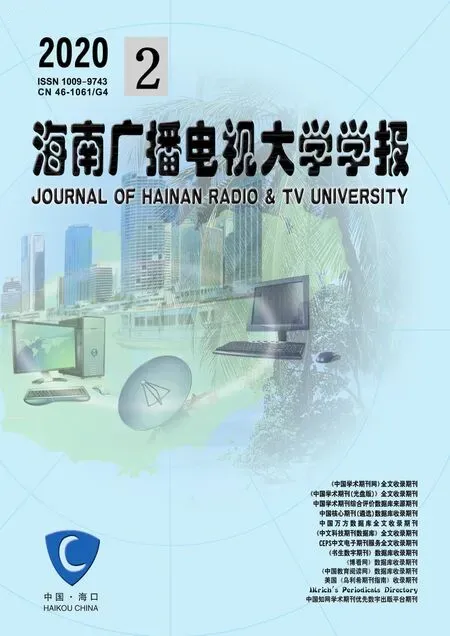《都柏林人》婚姻生活研究
呂舒婷
(浙江旅游職業學院 外語系,浙江 杭州 311231)
愛爾蘭作家、詩人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被譽為意識流文學的開山鼻祖、后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其久負盛名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1914)由15個故事匯集而成,描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都柏林各個年齡段的中下層人民的生活。不同于喬伊斯其他晦澀難懂的意識流作品,《都柏林人》相對易讀,語言以白描為主。然而這部看似簡單易懂的作品其實承載了喬伊斯很大的野心,他在給這本小說集出版商的書信中曾這樣寫道:
“我的目的是書寫祖國道德歷史的一個篇章,選擇都柏林作為小說背景是因為這座城市似乎正是癱瘓的中心。”[1]134
其實書中看似簡單直白的語言乃“欺騙性的直白[2]32”。喬伊斯所言的都柏林的“癱瘓”正是在細節描寫中得以展現。都柏林人沉悶壓抑的日常生活在方方面面都散發出了“癱瘓”的氣息,這種癥狀在“婚姻”中最為明顯。以“婚姻”為切入點,剖析都柏林人的婚姻特征,并結合喬伊斯本人的婚姻觀和愛爾蘭的歷史背景,可揭示作者在這部小說集中描寫都柏林人癱瘓婚姻的意圖。
一、《都柏林人》婚姻生活
都柏林人的“精神癱瘓”從其婚姻生活中便可見一斑。喬伊斯并未對都柏林人的婚姻下結論性的評價,但婚姻各方面的細節描寫呈現的是一個又一個充斥著酗酒與家暴、剝削與寄生、鄙視與怨恨、愛之無能的“癱瘓”婚姻。
(一)酗酒與家暴
家暴——尤其是酗酒引發的家暴,是《都柏林人》中大部分婚姻的必備原料。《無獨有偶》中主人公傅林敦和妻子的關系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的:
“男人清醒時,她便呼幺喝六,而男人爛醉時,她便忍氣吞聲。”[3]97
清醒的時候,窮困潦倒、一事無成的丈夫遭受妻子的語言暴力;喝了酒之后,在公司唯唯諾諾的丈夫就回家用拳頭向妻子和孩子發泄怒火。書中并未直接描寫夫妻之間的家暴細節,但從丈夫對孩子的冷血毒打與孩子的苦苦哀求中不難想象妻子平日所遭受的虐待:
“‘哼,看你下次再讓火熄掉!’那漢子說,一面用拐棍狠揍,‘打死你這狗崽子!’
棍子打傷了孩子的腿,他痛得發出一聲尖利的哀叫。孩子緊攥雙手,伸向空中,聲音顫抖地哀求。”[3]98
《圣恩》中克南夫婦看似和平的婚姻生活里也充斥著酗酒和暴力:
“對于丈夫酗酒的惡習,她安之若素。他一躺倒,她便盡責地護理他,老是督促他吃早飯。她想,別人的丈夫興許更糟糕呢。自從孩子們長大后,他從來沒有粗暴過……”[3]167
克南太太之所以能容忍丈夫酗酒,一是因為當時的都柏林男人酗酒十有八九,酒醉后動手打老婆孩子的也是再常見不過;二來兩個兒子都長大到可以保護母親了,丈夫就不敢對她再動拳頭了。克南太太的心滿意足源自她對婚姻極低的期待。我們不禁要問,等兒子們都離家后,他酗酒的丈夫會不會變回那個暴戾的家暴者呢?
《寄宿》中的精明狡猾的穆尼太太也沒能躲過被酒鬼丈夫家暴的命運:
“可是,丈人一死,穆尼先生便胡搞起來。他酗酒、把錢柜洗劫一空,欠下一屁股債。叫他發誓改過也沒用,幾天后他必定故態復萌。他當著顧客的面打老婆,老是買臭肉來賣,生意全給砸了。有一天晚上,他提著切肉刀去找老婆,她只得躲到鄰居家去睡了。 從此兩人分居。”[3]58
《伊芙琳》的女主人公面臨著與水手私奔還是留在家中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抉擇時,其內心掙扎的獨白如下:
“可是,在新的家,在那遙遠的陌生的地方,情況會多么不同啊!她將結婚——正是她,伊芙琳,人們將尊重她。她不會像媽媽生前那樣遭到虐待。她已經十九歲出頭了,但即使現在,她有時還會覺得受到父親暴虐的威脅。她曉得,正是這種感覺使自己心驚膽戰的。”[3]33
盡管書中并未出現對伊芙琳父母婚姻生活的直接描寫,但從這段獨白中我們仍能推測出暴力在其婚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伊芙琳的父親是一個經常用暴力虐待妻子的丈夫,我們甚至可以推測母親的早逝與家暴也不無關系。成長于充滿暴力的家庭環境,伊芙琳害怕自己會重蹈母親的覆轍,因此她無比渴望能擁有一樁完全不同的婚姻——沒有暴力,只有幸福與尊重的婚姻。
(二)剝削與寄生
很多婚姻在《都柏林人》中不過是關于剝削和寄生的冰冷交易,而非充滿愛與甜蜜的神圣結合。婚姻的殘酷真相在《死者》中被年紀輕輕卻早已看透一切的莉莉一語道破:“現在的男人都只會說廢話,把你身上能騙走的東西全騙走[3]195。”《兩個浪子》中的科利一門心思就想著怎么占女孩子便宜,而且已經得手多次。出于對科利的崇拜,萊內漢成了他忠實的“門徒[3]57”。他倆終日游蕩在街上,搜尋著頭腦簡單、可能上鉤的獵物。科利恬不知恥地向徒弟吹噓著自己輝煌的戰績:
“我把她帶到多涅布魯克,鉆進田野里……真不賴,老弟。她每晚都帶香煙給我,來回的車錢也是她付。嚯,有一天夜里,她給我捎來兩只高檔大雪茄——嗬,真的呱呱叫,你懂嘛,老煙鬼常抽的那種……可我擔心,老弟,她會鬧著要嫁給我呢。不過,她的鬼花樣可多哪。”[3]47
科利的過人之處是能從姑娘那兒占到肉體和物質的便宜,并且還不用付出“婚姻”的代價,而這正是萊內漢崇拜和嫉妒他的關鍵所在。其實“窮愁潦倒”的萊內漢對“家庭”也充滿了渴望:
“到十一月,他滿三十一歲了。難道永遠找不到好的職業嗎?永遠沒有自己的家?他想,要是能坐在暖烘烘的火爐邊,桌上擺滿佳肴,那該多好啊!他同伙伴們和娘兒們在街上逛夠了……生活的磨練早已使他憤世嫉俗。但他還是懷著一線希望……如果他能遇到一個有點兒錢的心地單純的好姑娘,興許還能建立起一個舒適的小家庭,過幸福的日子呢。”[3]54
萊內漢認為理想結婚對象的首要條件是“有點錢”,其次是“心地單純”,換句話說就是能傻乎乎地讓他像寄生蟲一樣去剝削、去壓榨,不勞而獲。如果沒有金錢,婚姻對這兩個寄生蟲來說簡直就是“辛苦”與“付出”的代名詞。
《寄宿》中多倫先生和波莉的婚事其實是波莉和母親的一場陰謀。在母親的默許和慫恿下,女兒負責引誘多倫先生,工于心計的母親則看準時機向老實的多倫提出賠償——結婚。母親之所以急著把女兒嫁給多倫,是因為“她知道他薪金不少,并且猜想他還有些積蓄[3]62”。至于未來女婿的品格、他是否對女兒真心,統統都不在母親的考慮范圍內。對于母親甚至是波莉而言,多倫先生更像是一筆可以搜刮的財富,而不是一個可以去愛的人。
《一片浮云》中衣錦還鄉的加拉赫向其已婚的崇拜者錢德勒宣稱,自己不急著結婚,不急著“把麻袋套在頭上[3]80”: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套上了,你可以用最后一塊錢打賭,我絕不會卿卿我我、談情說愛的。我一定要同金錢結婚。她必須在銀行里有大筆存款,要不然,我可不領教。”[3]80
對功利的加拉赫而言,婚姻就是一個陷阱,只有金錢才能讓他心甘情愿地跳進去。
(三)鄙視與怨恨
夫婦間的鄙視和怨恨在《一片浮云》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丈夫錢德勒無法實現當詩人的夢想,郁郁不得志從而把婚姻當作罪魁禍首——“他終生變成囚犯了[3]84”“啥也做不成[3]84”。婚姻于他而言等同于一堆分期付款的家具、一個無休止哭鬧的孩子以及一個“冷淡的[3]82”的妻子。而妻子則是最他怨恨的中心:
“他冷淡地瞅著照片上那雙眼睛,它們也冷淡地回看他……眼光如此沉靜,使他厭煩。那雙眼睛排斥他,向他挑戰;眼神中不含激情,沒有狂喜……為什么他當初娶了照片上那雙眼睛呢?”[3]82
正如錢德勒感受到的一樣,妻子安妮的確打心底里瞧不起這個生性怯懦、收入微薄又好高騖遠的丈夫。當丈夫回家晚了還忘了買她交代的咖啡時,“她自然要發脾氣,頂撞他[3]81”。當孩子在丈夫懷里嚎啕大哭時,她則是邊訓斥邊一把“奪過[3]84”孩子。辛苦維持生計、獨自照顧年幼的孩子,這一切都讓妻子疲憊不堪,眼神自然“激情”不再。丈夫“面對這咄咄逼人的目光,愣了一會兒,隨即看出那目光中無限的憎恨,于是他的心抽緊了[3]85。”這是一對彼此關閉心門的年輕夫婦,互相鄙視與怨恨是婚姻的主旋律。
類似的婚姻雛形也可在《寄宿》中被找到,被誘騙進婚姻的多倫先生面對這個“粗俗[3]63”的未婚妻,“說不上自己喜歡她還是鄙視她[3]63”。他的直覺是對的,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像錢德勒與安妮那樣的悲劇式婚姻。
(四)愛之無能
《都柏林人》中的一種典型形象是一輩子未婚的女人,其中有憧憬愛情的少女、風華不再的中年女人,也有風燭殘年的老年女人。她們的共同點是都為家人付出了青春年華,對于愛情渴望卻又無法去愛,最終的歸宿往往是“嫁給”上帝。
伊芙琳是最典型的為照顧家人而犧牲個人幸福的年輕未婚女性:
“不過,奇怪的是,偏偏今夜晚傳來了這樂聲——使她想起了自己對媽媽許下的諾言:保證盡力支撐這個家。”[3]35
母親死后,年少的伊芙琳替母親扛起了照顧兄弟姐妹和父親生活的重擔。生活的艱辛讓她想要逃離,然而當幸福真正向她伸出雙手的時候,她卻石化了,留在原地動彈不得,而很大的原因就是對母親臨終前的誓言。因此盡管痛苦,她最后還是沒有和水手上船,而是留在了不幸的原生家庭中。而等待這位風華正茂的姑娘的命運很可能是成為老姑娘——孤獨終老。
除了無法走進婚姻的年輕姑娘,《都柏林人》中還有各色單身一輩子的中老年婦女。
《姐妹們》中南尼和伊莉莎與她們的兄弟弗林神父一起生活了一輩子。弗林神父去世后,年事已高的兩姐妹忙里忙外操辦后事,始終沒有提到有其他親戚來幫忙,這也暗示他們三人都無子嗣。伊麗莎一直被稱為“伊莉莎小姐”,說明她并未結婚。回憶起神父的生前,伊莉莎說:“他沒給我們帶來很多煩惱。同現在一樣,他生前在家里也是聲息全無的[3]9。”從此可推斷,姐妹倆與生前的弗林神父一直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她還提到弗林神父去世前總想著要帶姐妹倆回去看看他們出生的老房子,其中并未提及其他家人,由此也可推測出三人都是單身老人。
《土》中善良溫和的洗衣工瑪利亞亦是一個年歲漸長卻保持單身的女人——“她既不要戒指,也不要男人[3]101”。雖然已人過中年,但一聽到和結婚相關的詞,她都會變得尷尬和羞愧。僅僅是被蛋糕店的售貨員詢問是否要買結婚蛋糕,瑪利亞就會“臉上一陣緋紅[3]102”。在電車上,一位紳士給她讓座并和她聊了幾句,她便感到“惶惑[3]104”,以致于把重要的蛋糕落在了電車上,她“感到又羞又惱又沮喪,不禁滿面通紅[3]104”。這些與瑪利亞年齡不匹配的行為舉止都標明她對自己單身狀態的介意以及對婚姻的渴望。但當她在蒙眼抓物的游戲中摸到一本祈禱書的時候,她的命運就已經明了——“瑪利亞不到年底就要進修道院的[3]105”。就像伊芙琳,瑪利亞是又一個無法去愛任何人也無法走進婚姻的女人,在辛苦勞作中耗盡青春后,她的歸宿就是住進修道院,嫁給上帝。
《死者》中與侄女兒一起生活了30年之久的單身姨媽凱特和茱莉亞也是類似形象。
二、喬伊斯的診斷與反擊
(一)對“癱瘓”婚姻的診斷
《都柏林人》被喬伊斯稱為“他祖國道德歷史的一個章節[1]134”,他在其中描繪都柏林人可悲婚姻的意圖也值得探討。
喬伊斯對婚姻的否定和排斥是一個主要原因。他與愛人Nora Barnacle于1904年的私奔行為是他厭惡與反叛婚姻傳統的最好證明。兩人非婚同居了27年后才結婚,而且結婚的決定并不是對傳統婚姻觀念的妥協,而是為了“保護他們孩子的身份地位[4]11”。
Richard Brown在他的《詹姆斯·喬伊斯與性欲》(JamesJoyceandSexuality)一書中分析了喬伊斯對婚姻的排斥。在第一章節“婚姻與愛”中,Brown介紹了“婚姻觀念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5]13”,而這一轉變的標志就是《1857法案》,從此“審判離婚在英國首次變得可能[5]12”。性欲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強調,而非基督教形而上學的一些理念。盡管喬伊斯是在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家庭長大,但他“支持當代對婚姻理性的拋棄[5]13”。他與愛人非婚同居27年之久的行為正是“對從神權到人權這一更大的轉變的呼應[5]16”,宣告他對天主教的反叛。
身為一名對婚姻傳統的高調背叛者,喬伊斯在私奔后的一年(1905)創作了《都柏林人》的大部分,并在書中像醫生一樣解剖了都柏林人“癱瘓”的婚姻生活。雪上加霜的是,這些被囚禁于癱瘓婚姻的都柏林人在當時卻無法申請離婚。因為當時“愛爾蘭的羅馬天主教信徒被教會法禁止離婚[6]62”。羅馬天主教剝奪了愛爾蘭人逃離癱瘓婚姻的最后一個機會。都柏林人婚姻中無可救藥的“癱瘓”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喬伊斯把都柏林稱為“癱瘓的中心[1]134”。
(二)為巴涅爾發起的反擊
在喬伊斯的作品,如《都柏林人》中的“紀念日,在委員會辦公室”、《尤利西斯》以及《一個年輕藝術家的畫像》中,都有一個如幽靈般存在的歷史人物查爾斯·斯圖爾特·巴涅爾(Charles Stewart Parnell):
“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19世紀后期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英國國會議員(1875-91)、愛爾蘭自治運動領導人。1889到1890年間因被指控與Katherine O’Shea通奸而被趕下臺(后與其結婚),結束了政治生涯”[7]。
致力于帶領愛爾蘭人民走向獨立的偉大政治領袖被迫下臺,只因其“通奸”而為羅馬天主教及其虔誠的信徒——愛爾蘭人民所不容。崇拜巴涅爾的喬伊斯對此事件憤憤不平:
“喬伊斯宣布,在英國人的背信棄義和愛爾蘭人的自我背叛之下,一個新的鬼魂將游蕩于這一新的國家……喬伊斯崇拜巴涅爾的品質,崇拜他面對通奸指控或敵意時的冷漠……”[1]319-320
巴涅爾郁郁而終時,年僅九歲的喬伊斯悲恨交加作詩一首“Et Tu, Healy[1]34”譴責背叛巴涅爾的愚蠢叛徒。
在《都柏林人》中,喬伊斯無情揭露了愛爾蘭人的癱瘓的婚姻慘狀,這就像一記響亮的耳光重重打在高呼巴涅爾通奸而把他趕下臺的叛徒臉上。他借此向那些虛偽的愛爾蘭人拋出了一連串的質問:作為癱瘓婚姻的囚徒,你是否有資格去譴責巴涅爾的通奸罪?你的婚姻生活是否真的比巴涅爾與他情人的生活更加幸福?你們對自己婚姻中的丑行與痛苦視而不見,為什么要去對巴涅爾咄咄相逼?所謂的婚姻傳統真的比民族獨立更重要嗎?
相信這些質問都會讓巴涅爾的背叛者啞口無言和羞愧不已。喬伊斯就是這樣對巴涅爾的背叛者進行了有力反擊。
三、結 論
作為天主教與婚姻傳統的反叛者,喬伊斯抓住“婚姻”這一人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以此切入,用冷靜客觀的語言向讀者呈現了一幅都柏林人千瘡百孔的婚姻全景圖,而這種婚姻生活全面癱瘓的現象正印證了都柏林是“癱瘓的中心”。正是這些掙扎于癱瘓婚姻而無法自救的愛爾蘭人民占領了道德制高點,不顧民族利益,以“通奸”罪名把民族獨立領袖巴涅爾趕下了臺,這種無情的諷刺正是喬伊斯為巴涅爾發起的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