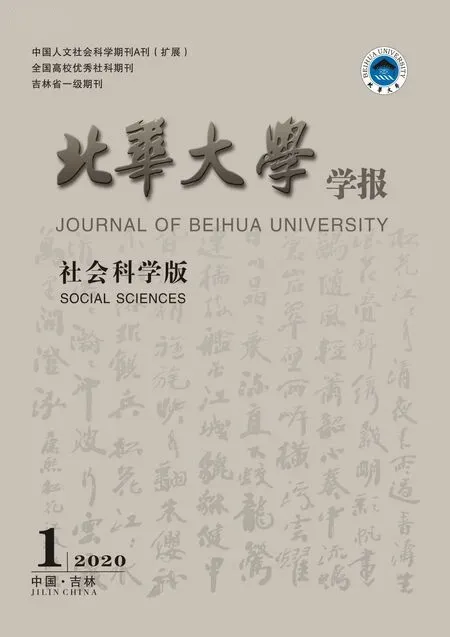盧卡奇、恩格斯與“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
竭長光 張貝可
在當代,全面理解、掌握“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對于正確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于客觀評價恩格斯的哲學貢獻,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需要反思的。“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雖然是辯證法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但是,它既可能是一種具有“唯物主義”性質的辯證法,也可能是一種具有“唯心主義”性質的辯證法。換言之,如何讓“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成為“唯物辯證法”理論體系的一部分,是一個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界認真對待的重要理論問題。
一、盧卡奇與“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
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認為辯證法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1]51。由此出發,盧卡奇對恩格斯有如下批評:“他(指恩格斯,引者注)認為,辯證法是由一個規定轉變為另一個規定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矛盾的不斷揚棄,不斷相互轉換,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關系必定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他對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連提都沒有提到,更不要說把它置于與它相稱的方法論的中心地位了。”[1]50概言之,盧卡奇認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適用范圍是“歷史”領域和“社會”領域;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錯誤地將辯證法擴大到“自然”(純粹自然)領域;應該把“自然”理解為一個社會范疇。
盧卡奇的這些觀點對后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法國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南斯拉夫的著名的“實踐派”以及英美等國家的“新左派”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那些對“恩格斯辯證法”(這里“恩格斯辯證法”是指恩格斯在辯證法方面的理論與觀點的總稱)持批判態度的西方學者,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以另一種形式追隨和再現了盧卡奇的觀點。例如,悉尼·胡克贊成盧卡奇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主要的適用范圍是“歷史”領域和“社會”領域,因此,恩格斯的研究純粹自然的“自然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辯證法是不相容的。此外,悉尼·胡克認為自然只有它在與社會和歷史中的人的活動方式有關的時候,才同辯證法產生關系。再比如,在萊文看來,馬克思的辯證法不是關于“自然”的辯證法,而是研究“社會”和“人類行動”的辯證法,辯證法的意義在于使人們認識到人的行動在干預歷史進程方面的效果。由此出發,萊文認為,如果馬克思也研究“自然辯證法”的話,那么,這種“自然辯證法”必定不是表現于純粹自然的運動,而是表現于一種主觀(思想)與客觀(自然界)之間的相互作用。又比如,A·施密特認為辯證法的存在是與人的存在相聯系的,隨著人的消失,辯證法也就消失了,據此,A·施密特認為“純粹自然”中所以不存在“辯證法”的原因,是因為它不具備辯證法所必需的一切最本質的要素。與萊文等西方學者一樣,A.施密特也認為“自然辯證法”只有在“勞動主體”與“自然”之間發生“相互作用”時才是可能的。
“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的核心和靈魂是“主體能動性”原則。盧卡奇之所以強調要從“主客體的相互作用”出發解讀辯證法,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凸顯“主體能動性”原則。在盧卡奇看來,“唯物主義辯證法是一種革命的辯證法”[1]48,“對辯證方法說來,中心問題乃是改變現實”[1]50,由此,如果不從“主客體的相互作用”出發理解,不強調主體能動地改造客體,那么,辯證法就不能解釋如何改變世界的問題,“辯證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了”[1]50。受盧卡奇的影響,部分國內外學者也從這個層面批評恩格斯,認為恩格斯的辯證法中沒有體現出“主體能動性”原則。
然而,問題在于“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雖然高揚了主體能動性,但是它所高揚的卻是一種“費希特式”的能動性。眾所周知,費希特的“自我”學說表達了這樣一種能動性原理,即從“自我設定自我”,到“自我設定非我”,再到“自我實現自我與非我的統一”。費希特的這種能動性原理的缺點在于它張揚了一種“主觀主義+行動主義”的邏輯。因此,當“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以費希特為模板去解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時,也同樣會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蛻變為一種表達“主觀主義+行動主義”的邏輯的理論。這一點,正如盧卡奇后來在其“自傳”中所承認的那樣:《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他對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的解釋還停留于一種“主觀主義的行動主義”[2]。實際上,在1967年《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新版序言中,盧卡奇在理論層面曾對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主張的“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盧卡奇承認:由于當時他未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問題,未能對“書中的核心概念——實踐”作正確的理解,反而使實踐概念“遭到歪曲,并變得狹隘了”,致使他關于“資本主義矛盾”和“無產階級革命化”的論述帶上了“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盧卡奇反省到:“在這本書中,革命的實踐概念表現為一種夸張的高調,與其說它符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莫若講它更接近當時流行于共產主義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1]12“我沒有認識到……過度夸張實踐概念可以走向其反面:重新陷入唯心主義的直觀之中”[1]12。 “我那本身是正確的愿望之所以會走向它的反面,仍是由于剛才提到的那種抽象的、唯心主義的實踐概念”[1]13。
當前,國內部分學者在未能認清盧卡奇的“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的理論缺陷的情況下,不但盲目跟隨和不加批判地宣傳盧卡奇的這種觀點,而且加入到了否定、質疑恩格斯辯證法的隊伍當中去了。以至于,隨著盧卡奇的“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在國內的傳播,國內理論界在如何評價恩格斯以及如何定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等問題上出現了某種混亂。這種情形的出現是應當引起理論界的重視和思考的。
二、恩格斯與強調“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人化自然辯證法”
盧卡奇認為恩格斯“連提都沒有提到”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的辯證法,這是不公允的。那種認為恩格斯僅僅以“非實踐的”和“排除人的作用”的角度理解自然,認為恩格斯總是在撇開“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的意義上來談論自然的想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恩格斯既肯定作為自然科學對象的“純粹自然”的存在,也強調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人與自然相互作用”觀點的重大意義。然而,盧卡奇、A·施密特等人卻從“自然是一個社會范疇”的判斷出發,認為沒有純粹的自然,只有人化的自然。于是,他們要么斷定恩格斯沒有關注到人化自然和主客體的相互作用,要么,認為在恩格斯那里雖然也有人化自然理論,但卻與恩格斯關于“純粹自然”的理論不能相容。例如,A·施密特就曾表達過這樣的困惑,他說:“在恩格斯那里,被社會中介過的自然概念和獨斷的、形而上學的自然概念(即純粹自然——引者注)確實毫無聯系地并存著。”[3]不難看出,A·施密特的困惑不過是由于他僅僅從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出發理解恩格斯辯證法的結果。
實際上,在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方面,恩格斯與馬克思是一樣的,兩人都強調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自然史和人類史的相互作用。換言之,在“人化自然辯證法”方面,二者是一致的。眾所周知,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視由于工業活動而實現的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與“統一”。例如,馬克思恩格斯批評了布魯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的錯誤觀點。在這個問題上,布魯諾將自然和歷史對立起來,在布魯諾那里自然和歷史好像是兩種不相關的事物,好像不會有基于歷史和自然的相互作用的“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布魯諾的問題就在于不懂得“人和自然的統一”[4]529的理論,不懂得這種“統一”會隨著工業的發展而發生改變。再比如,恩格斯還批判了那種只知道強調自然界和自然條件制約人的活動,而看不到人的活動也可以主動地改變自然的“自然主義歷史觀”。恩格斯指出:“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學家或多或少持有的這種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5]在恩格斯看來,由于人的活動的作用,地球上的動物界、植物界以至于整個地球表面和氣候都發生了變化,以至于對于一些國家(如“德意志”)的“自然界”而言,不受人的活動影響的原始的自然界已經很少了。
一些西方學者批評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在他們看來“自然辯證法”所研究的“自然”是撇開了“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的“純粹自然”。不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對象的確是“純粹自然”,在這個意義上,“自然辯證法”是為同樣研究“純粹自然”的自然科學服務的。當然,在自然科學最終是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服務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自然科學也是與人類有關系的,甚至我們也可以說自然科學本質上也是一門“關于人的科學”。然而,這種“有關系”并不排斥或否定自然科學家在研究自然的時候要以“純粹自然”為對象,做到直面“純粹自然”本身,把握“純粹自然”背后的規律。這一點也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區別。實際上,關于自然科學的這一特點的理解,馬克思與恩格斯是一致的。例如,馬克思曾指出:“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觀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6]
盧卡奇等西方學者與恩格斯(也包括馬克思)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從“主客體的相互作用”出發理解辯證法的,而后者是從“矛盾”即“對立的相互作用”出發理解辯證法的。實際上,“主客體的相互作用”只是“對立的相互作用”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的意義上,談到了“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遺傳和適應的相互作用”等多種“對立的相互作用”形式;在“社會辯證法”或“歷史辯證法”的意義上,談到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相互作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等多種“對立的相互作用”形式。換言之,“主客體的相互作用”在它被正確理解的意義上也只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而不是全部。盧卡奇等西方學者的一個錯誤在于把“主客體的相互作用辯證法”當成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唯一表現形式,并且用這種唯一的形式排斥其他形式,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
三、恩格斯與“主體能動性”原則
既然“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的核心和靈魂是“主體能動性”原則,那么,從恩格斯對于“主體能動性”的態度中可以更清楚準確地看出恩格斯與“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的關系。
首先,就恩格斯而言,他是否真的像有些學者說的那樣不強調“主體能動性”原則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4]545“實踐的唯物主義者”的根本任務在于改變“現存世界”和“現存的事物”[4]527。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強調革命活動對于改變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意義。19世紀90年代,為了批判巴爾特等人將歷史唯物主義歪曲為只是強調經濟的自動作用的“經濟唯物主義”,恩格斯在著名的“晚年書信”中著重強調了主體能動性的發揮在改變社會歷史中的作用。例如,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恩格斯強調:“并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像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7]668無疑,恩格斯對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強調,就包含著對“主體能動性”的強調。
其次,與那些抽象地強調“主體能動性”原則的學者相反,恩格斯反對那種無條件地夸大“主體能動性”的做法。例如,盡管恩格斯多次強調“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同時強調以下兩點:
其一,這種創造是在既定的條件下的創造,因此,這種創造不是無限可能的。實際上馬克思也多次強調這一點。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曾強調指出,“這種創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8]
其二,這種創造是“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7]592。
實際上,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恩格斯都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從抽象的個人出發,把人的主體能動性理解為一種不受制約的、完全“自覺的”和“自主的”活動。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受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的影響,曾抽象地談論人的“自覺”的、“自主”的活動,并把這種活動視為人的“類本質”。學界一致認為這種觀點是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的觀點。學界普遍公認《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的標志。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理解,實現了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抽象的人”到“現實的人”的根本轉變。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現實的人是“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4]525,“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4]524。從“現實的人”出發去思考主體能動性,那么,關于人的活動的理解就不能脫離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一旦脫離了客觀條件去理解人的主體能動性,把這種主體能動性建立在“抽象的人”的抽象的實踐活動的基礎上,那么,就會在實踐中導致失敗或造成損失。
四、“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的統一何以可能?
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1967年新版序言中的反省已經提示人們,從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出發,并不必然得出一種具有“唯物主義”性質的理論,相反,卻完全有滑向一種具有“唯心主義”性質的理論的可能。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唯物辯證法”,它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有機統一,這是學界多年來的一個基本結論。然而,關于“什么是唯物主義”的問題,卻是一個在當前并沒有獲得應有重視的問題。更有甚者,國外和國內的某些學者認為這是一個過了時的和無關緊要的問題,這一點表現在辯證法上,就是他們否認“唯物辯證法”,亦即否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性質。因此,探討“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能否與“唯物主義”相統一的問題,絕不是一個無關宏旨的小問題,而是一個事關問題之根本的大問題。換言之,“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能否成為“唯物辯證法”理論體系的一部分,關鍵在于看它能否實現與“唯物主義”的統一。
“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造的,然而,在一些西方學者(如卡弗)看來,它是恩格斯“發明”并強加給馬克思的。其實,那些曲解“唯物辯證法”的學者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不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真正內涵。為此,要還原恩格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的本來面目,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還原“唯物主義”理論的本來含義。
在關于“唯物主義”內涵的解釋與澄清方面,恩格斯無疑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下簡稱《終結》)中的許多經典表述成為日后人們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重要理論依據。在《終結》的“第二部分”中恩格斯指出,“本原”問題是劃分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標準。筆者曾就這如何理解《終結》中的“本原”問題,表達如下觀點:
首先,恩格斯這里的“本原”的含義就是在“因果”關系上追問世界的“終極原因”,亦即追問世界的“根據”或“根源”。簡言之,“本原”即在終極原因的意義上追問世界的根據、根源。
其次,唯物主義的“自然界是本原”[9]278表明“自然界”(世界)就是根據、根源。換言之,“自然界”(世界)不是什么外在于“自然界”(世界)的“神”創造的,而是自我創造的,是以自身為根據和根源的。
最后,由于唯物主義認為世界的根據、根源在世界自身之中,因而堅持“從世界本身來說明世界”,最終將世界解釋為一種自我創造的存在物,因此,在方法論上,唯物主義意味著“自因”、“內因”和“自我決定”的觀點。與之相反,由于唯心主義“斷定精神對自然界來說是本原”[9]278,亦即認為世界(自然界)的根據、根源不在世界之中而在世界之外,最終將世界解釋為一種由“精神”(神、上帝)創造的存在物,因此,在方法論上,唯心主義意味著“他因”、“外因”和“非自我決定”的觀點。
在這個意義上,能否實現“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的統一,關鍵是看在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中能否體現出唯物主義所要求的“自因”、“內因”和“自我決定”的觀點。
第一,“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與“自因”觀點的統一。要想使主客體的相互作用體現“自因”觀點,就要使感性客體的運動成為一種基于“自因”而非“他因”的運動。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主體的實踐活動雖然是一種“有目的”的活動,但是,主體的“目的”“愿望”并不具有獨立性。實際上,那種真正“合理”的“目的”“愿望”必然是從感性客體出發的產物,也就是說必然積淀著對感性客體的特點、規定性及其可能的具體把握。在這個意義上,“合理”的“目的”與其說是來自主體那里,不如說是來自感性客體那里。換言之,“合理”的“目的”“愿望”是以“主觀”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感性客體內部包含的“客觀”要求與可能,因而,也必然是堅持“自因”觀點的產物。
第二,“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與“內因”觀點的統一。要想使主客體的相互作用體現“內因”的觀點,就要使感性客體的運動成為一種基于“內因”而非“外因”的運動。正如毛澤東強調的那樣,“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本,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10]。換言之,由于導致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內因而不是外因,因此,要想實現促進事物發展的目的,那么,就要善于把“外在”的主體能動性轉化成客體發展所需要的“內在”條件。這樣才能做到將主體的能動活動與“內因”的觀點統一起來,做到在“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中堅持唯物主義。
第三,“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與“自我決定”觀點的統一。要想使主客體的相互作用體現“自我決定”的觀點,就要使感性客體的運動、發展的泉源基于自身。例如,黨中央強調要多以“造血式”扶貧取代“輸血式”扶貧。“教育和引導廣大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實現脫貧致富”[11]。“造血式”的扶貧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這種主要基于群眾自己的辛勤勞動所實現的富裕,是一種以自身為泉源的、具有“自我決定”性質的富裕,因此,這種富裕也是一種能夠持久的富裕。換言之,這種具有“自我決定”性質的富裕才是真富裕,也才是真正體現了唯物主義的“自我決定”觀點。
總之,作為“西馬”“鼻祖”的盧卡奇斷言恩格斯沒有提到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是有悖于客觀事實的。恩格斯之所以沒有像盧卡奇那樣把“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置于“方法論的中心地位”,并不是因為在恩格斯那里沒有“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也不是因為恩格斯不理解“實踐”的重要意義,而是因為恩格斯(馬克思)將矛盾即“對立的相互作用”置于“方法論的中心地位”。此外,在恩格斯(馬克思)看來,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即實踐作為一種具體的、歷史的對象性活動,是有條件的、受制約的,因此,不能僅僅從主體的活動所具有的“目的性”“能動性”出發,將其夸大為一種似乎可以任意主宰、掌控客體變化的節奏與方向的抽象活動。盧卡奇的自我反省就清楚地告訴人們:一旦將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建立在“抽象的、唯心主義的實踐概念”的基礎上,那么就會滑向“主觀主義的行動主義”。“主客體相互作用辯證法”只有體現出唯物主義的“自因”、“內因”和“自我決定”的觀點,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理論體系的內在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