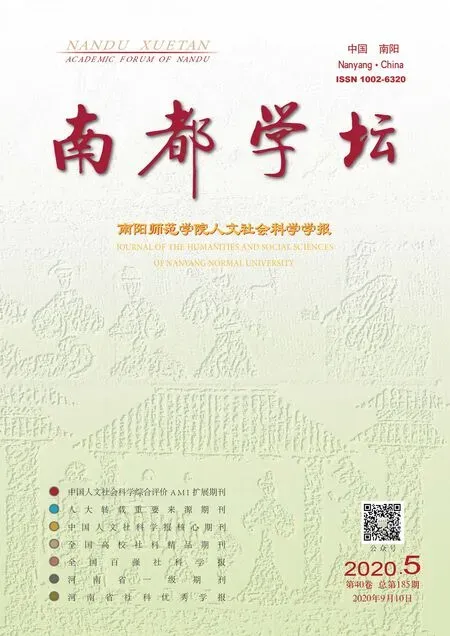從蘭臺、東觀看漢代檔案管理的發展演變
王 春 陽
(南陽師范學院 文史學院,河南 南陽 473061)
在中國檔案史上,蘭臺和東觀是兩個繞不過去的關鍵詞。清代學者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后,圖籍盛于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1]后代學者多沿其說。但對于修史、著述之所由蘭臺移入東觀的原因,學界則少有論述。本文擬從檔案發展史的角度對蘭臺、東觀作為漢代早期的檔案館的關系及其在職能、性質上的變化進行考察,從而探究東漢修史、著述之所從蘭臺移入東觀的原因及其漢代檔案管理的發展演變。
一、蘭臺與東觀作為官方藏書機構的性質與職能
(一)蘭臺“圖籍秘書”的職責
東漢立國后,文書的運行成為行政運轉之樞機。故王充在《論衡》中指出“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漢代遂“以文書御天下”[2]。而文書運行的機構,在西漢主要是由御史大夫負責的,史載:“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為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余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也。”[3]又“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4]725。根據以上文獻所述,御史大夫的職能主要有三:副丞相,與丞相共掌政務;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人,負責監察;皇帝的秘書長,在皇帝和百官之間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而御史大夫的屬員一分為二,其中15人從御史大夫衙署中獨立出來,由御史中丞帶領進駐禁內,在殿中蘭臺辦公,作為秘書機構,服侍皇帝左右。這時候,蘭臺是隸屬于御史大夫的,而根據以上所引述材料,則可歸納出御史中丞職掌的文書工作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制詔,負責皇帝詔令的擬定和印制;二是負責章奏轉呈,奏請文書要經由御史核查,所言不善者、內容虛浮者屏去不報,余者上呈等待批復;三是檔案的保存,皇帝的詔令、朝臣和地方官員的章奏及皇帝的批復等文書材料,都必須由御史登記并保存起來。除此
之外,朝廷頒布的法律條令、制作的輿圖、地方報送的上計材料等,也交由御史保存。蘭臺作為御史大夫屬官御史中丞的治事之所,是皇帝秘書機構的所在地,因此不僅承載著大量文書檔案的收集轉呈,而且自身亦是大量文書檔案的產生地。又因為要擬定文書,以備皇帝咨詢顧問,所以大量文書檔案也就留存于此了。故蘭臺又成為文書檔案的保存之所。同時又由于其處禁內,地位相當重要,以至于“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日夜都有官員輪班值守,所以“典冊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5]。這也反映了蘭臺的重要性。
隨著職官制度的變遷,西漢末成哀之際,御史大夫轉為司空,負責水土營造事務,完全成為政事官,其作為皇帝秘書長以及監察百官的職能為御史中丞所取代,其治事之所蘭臺被稱為御史臺。東漢初年,光武帝循舊制由御史中丞領監察和秘書事,并提高了御史中丞的地位,“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6]3600。作為皇帝秘書機構的負責人,御史中丞仍然留在禁內辦公,其屬員有治書御史、侍御史和蘭臺令史。其中治書御史2人負責法律解釋,侍御史15人負責查舉非法并接受群臣奏事,蘭臺令史無定員,主要“掌奏及印工文書”。根據分工的不同可以看出,御史中丞所承擔的監察職能主要由御史負責,而秘書職責主要由蘭臺令史掌管。因此一直由御史中丞掌管的“圖籍秘書”也自然由蘭臺令史直接負責管理了,則蘭臺就成為御史臺部門檔案館的代稱。
(二)東觀收藏檔案典籍和校勘著述的職能
東觀是東漢都城洛陽一處建筑物的名稱,屬于南宮建筑群的一部分。作為東漢時期檔案存貯最為集中的地方,東觀也成為東漢時期的學術文化中心。由最高統治者頒布詔令,中央政府組織了一批批著名文人學士在東觀進行大規模的校書修史活動,而東觀也因承載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動而留名史冊。一是東觀的系列修史活動。漢明帝時期,詔命班固修著《漢書》,但是未完成,班固就去世了。漢和帝把續修《漢書》的任務交給了其妹班昭,“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6]2784,班昭在東觀完成了《漢書》八表和《天文志》的續修工作。東漢末年,掌管檔案的秘書監荀悅按照獻帝詔命,以班固《漢書》為依據,經過剪裁刪潤,去繁就簡,在東觀歷時數年,完成了編年體史書《漢紀》的修撰工作。從明帝開始一直到東漢末年,在朝廷支持下,經班固、劉珍、李尤、伏無忌、蔡邕等著名學者的前赴后繼,歷經100多年,完成了《東觀漢記》的修撰工作。之所以命名為《東觀漢記》,就是由于這部史書主要是在東觀完成的。由此可見,《漢書》《漢紀》和《東觀漢記》主要是在東觀完成的。二是東觀的系列校書活動。安帝永初四年(110),由于“惑于經書謬誤”,鄧太后詔令劉珍等50余人校書于東觀,并令蔡倫監典其事。順帝永和元年(136),詔命侍中屯騎校尉伏無忌、議郎黃景等人于東觀校定中書、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靈帝建寧三年(170),召拜蔡邕為郎中,校書東觀。三是最高統治者在東觀開展的系列讀書、學習活動。漢和帝多次親臨東觀參觀學習,如:“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6]188;“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6]2546。元和元年(84)漢章帝詔命“天下無雙,江夏黃童”黃香到東觀“讀所未嘗見書”[6]2614。安帝永初三年“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的和熹鄧太后詔令“中官近臣于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6]424。東觀之所以成為東漢時期的學術、文化中心,與東觀作為國家檔案館的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而東觀作為東漢“圖籍秘書”的組成部分,也歸屬于蘭臺令史,由其負責管理。
(三)蘭臺和東觀在性質、職能上的差別
東漢時期,雖然蘭臺與東觀都是檔案館,但是二者還是存在差異的。一是蘭臺與東觀的性質不同。蘭臺是皇帝秘書機構治事之所,蘭臺之所以成為檔案館是由蘭臺所駐機構的性質所決定的,因此蘭臺不是獨立的檔案機構,而是附屬于御史臺的部門檔案館,具有較強的依附性。它隨著皇帝辦公地點的轉移而轉移,隨著機構職能的變化而變化。而東觀是專門用以存貯檔案的場所,不依附于任何機構,只存在歸誰管理的問題,具有明顯的獨立性,是獨立的檔案館。二是蘭臺與東觀的職能不同。作為御史臺的部門檔案館,蘭臺存貯的檔案與御史臺職能密切相關,主要收藏與其職能相對應的檔案以及作為秘書機構所產生的文書檔案。由于秘書機構的運轉不斷產生新檔案,蘭臺檔案累積到一定體量的時候,就必須對部分檔案進行移存,以便有足夠空間來貯存新產生的檔案。因此蘭臺館藏檔案具有時效性、臨時性、部門性的特點。而東觀作為獨立的國家檔案館,其收藏檔案的范圍相當廣泛,不但存貯前代檔案,而且存貯國家搜求以及學者進獻的圖書檔案,還接收其他部門移交過來的各種專門檔案。東觀所藏檔案具有綜合性、穩定性和永久性的特點。由于性質和職能不同,作為檔案館,蘭臺無論是場館的空間還是收藏檔案的規模、類別都是無法和東觀相提并論的。
二、蘭臺、東觀作為漢代檔案管理機構職能的演變
對于蘭臺與東觀二者之間的關系,歷代學者普遍認為東漢時期檔案館藏有一個從蘭臺到東觀在空間上的轉移過程,甚至有“班固先在蘭臺修史,劉珍等移至東觀”[7]的判斷。之所以會產生如此的判斷,主要是論者只注意到東漢前期從事校書修史活動的班固、賈逵皆有蘭臺令史的任職經歷,而忽略了蘭臺機構職能以及蘭臺令史職責的變化。
(一)尚書臺秘書職能的增強
漢武帝時,為加強皇權,開始重用尚書,并通過內廷尚書署來親自處理政務。漢成帝時,將尚書署改為尚書臺。東漢光武帝進一步提高了尚書臺的地位,“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并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6]927。隨著尚書地位的提高,尚書臺的組織也日益擴大。從秦到漢初,尚書的名額都不過4人。漢武帝時增加到5人,成帝時增加到6人。東漢光武帝時期,尚書臺設尚書令1人、尚書仆射1人,尚書6人,尚書丞12人,侍郎36人。其中尚書令負責“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尚書“掌錄文書期會”,侍郎“主作文書起草”。
尚書最初的職責不過是“在殿中主法書”或“掌通章奏”而已,也就是收發章奏或者向各機關傳達章奏。漢武帝以后,尚書的職權由“通章奏”而“讀章奏”,由“讀章奏”而“裁決章奏”,由“裁決章奏”而直接“下章”[8]。到了東漢時期,尚書臺更是成為詔書起草、制作、下發的唯一機構,也是上行文書的匯集之所[9]。尚書作為皇帝的喉舌,出入帝命,不僅詔令由尚書宣達,而且群臣的奏章也必須經由尚書呈遞。很顯然,東漢時尚書臺演變為皇帝的私人秘書機構,尚書令成為皇帝的秘書長,掌管章奏文書,負責起草詔令,在皇帝和百官之間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當時的大臣只有帶“錄尚書事”“領尚書事”才能真正握有實權,逐漸形成“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的局面。
(二)蘭臺秘書職能的喪失
與尚書臺秘書職權不斷增強相對應的則是御史臺秘書權的逐漸喪失。東漢光武帝時,御史中丞帶領侍御史、治書御史和蘭臺令史,作為皇帝的秘書機構仍駐殿中蘭臺,掌握監察和秘書大權。但是隨著尚書臺秘書職能的進一步增強,御史臺的秘書職能逐漸喪失,其工作重心日益集中于監察職能,成為職能單一的中央監察機關。隨著御史臺機構職能的變化,其治事之所也有了變化。光武帝“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6]25,南宮遂成為東漢初的政治中心和朝賀議政之地。明帝時期開始修建北宮并移到北宮居住,此后歷代皇帝多居于此,北宮逐漸成為帝國心臟。因為御史臺機構職能的變化,御史臺未能隨皇帝遷到北宮,而是留在了南宮。御史中丞及其屬員失去了在禁省辦公的權力,由皇帝身邊近臣而逐漸變為外臣,蘭臺令史作為皇帝機要秘書的身份隨之喪失。明帝時期,蘭臺令史“掌奏及印工文書”的秘書職責已逐漸淡化。和帝永元三年(91),增尚書令史員,“皆選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煉有吏能為之”[6]3596,尚書臺完全取代御史臺成為溝通內外的唯一機構。蘭臺令史開始分流,一部分選入尚書臺,繼續作為皇帝機要秘書。“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10]蘭臺令史憑借自己的業務素質,可以通過轉任尚書令史進入禁內,再次成為皇帝的機要秘書班子成員,并沿著蘭臺令史、尚書令史、尚書郎、尚書一路升遷發展。另一部分進入東觀成為專職修史校書人員。“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于世。”[11]由于蘭臺令史具體負責圖書檔案的管理,其職責開始向修史校書轉變,并沿著蘭臺令史、校書郎、校書郎中一路升遷發展。
蘭臺作為檔案館是依附于御史臺的,隨著御史臺作為皇帝秘書機構職能的喪失,其存貯機要文書等檔案的功能也隨之消失,作為部門檔案館亦不復存在。蘭臺令史掌管蘭臺檔案的職責也已名存實亡。因此,在東漢和帝以后,“不要說‘蘭臺令史’校書事,連‘蘭臺令史’這一名稱似乎也不再見于史書了”[12]。由此可見,東漢時期的蘭臺和東觀作為檔案館是共時性關系,在客觀上并不存在檔案館藏中心從蘭臺到東觀的轉移。章、和以后東觀取代蘭臺成為學術中心,是由于蘭臺機構職能變化而使蘭臺作為部門檔案館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而蘭臺令史也被調配至東觀去校書修史所致。隨著專職管理機構和檔案管理者的出現,蘭臺與檔案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性聯系。
三、漢代檔案管理思想的變化
(一)統治者檔案利用意識的形成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4]1701漢代統治者已經意識到檔案對王朝興衰有著重要作用,因此特別重視對檔案的利用。一是將檔案整理作為統一思想的手段。漢武帝時期,通過儒家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實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目的。但是儒學內部卻紛爭不斷,特別是今古文經學之爭曠日持久,雖經石渠閣會議和白虎觀會議統一思想,仍未能解決思想界的混亂狀態。漢代統治者主導的校書和修史活動,就是要利用檔案的特殊價值,通過檔案整理達到思想統一和文化認同的目的。例如蔡邕將整理校定的七部儒家經典刻石公布,為天下讀書人取資,本身就有著統一思想的功用。二是利用檔案制定禮儀以規范現實。禮制是維護統治秩序的手段,也是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因循。“為國以禮”“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是儒家的一貫主張。但是時代變換,朝代輪序,禮制必須因時而變,“大漢當自制禮”[6]1201。東觀典藏的典章、故事就成為制定漢家禮儀制度的重要依據,如“永初中,謁者仆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6]1940。三是將檔案作為教化的重要載體。東漢統治者認為“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因此下令“中官近臣于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6]424。靈帝時,褒獎典范,當曾經校書東觀的高彪升遷后,在東觀為其畫像以勸學者。統治者將檔案作為教化的載體,從而達到“美教化、易風俗”的目的。
(二)檔案管理由分散到集中
西漢時期,御史中丞、太史、太常、博士、太仆、理官等衙署,既是檔案的產生機構,又是檔案存貯機構。這些衙署都會根據其職掌收藏皇帝詔命、地圖戶冊、人口賦稅、祭祀禮儀、天文歷法、法律條令、典章制度等各種檔案,形成了為數眾多的具有依附性的部門檔案館,其中以蘭臺最為著名。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專門用以存貯檔案的獨立檔案館,其中以石渠閣、天祿閣和麒麟閣等最為出名。但是眾多部門檔案館與獨立檔案館沒有明確的隸屬關系,處于分散管理狀態。東漢時期,雖仍有“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但是除蘭臺之外,已經沒有西漢時眾多部門檔案館并存的情況。而專門的大型獨立性檔案館,也僅有東觀一處。可見,在東漢時期政府已經實現了對諸多檔案的統一規劃和統一管理。沈約《宋書》卷四十記載:“漢西京圖籍所藏有天府、石渠、蘭臺、石室、延閣、廣內之府是也,東京圖書在東觀。”杜佑《通典》卷二十六也說:“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于內禁。后漢圖書在東觀。”[13]由此可以看出西漢與東漢時期檔案管理上存在的不同之處。作為獨立的中央綜合檔案館,東觀的檔案種類宏富,不但藏有各類圖書,而且還藏有歷朝注記、尚書所掌檔案以及功臣功狀和前朝舊典等檔案。正是由于東漢檔案集中藏于東觀,張衡才上書皇帝“愿得專于東觀,畢力于紀記”,而蔡邕亦上書皇帝請求參閱東觀所藏檔案,“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由張衡與蔡邕二人事例可以看出東漢時期檔案與西漢時期檔案管理相比較,已經實現了集中管理。與這種管理相適應,則出現了專門的檔案管理人員和檔案管理機構,“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于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14]。東漢桓帝時期,更是設立秘書監統一掌管所有檔案,“自后漢置秘書監,而典司圖籍設有專官,歷代相同,未嘗改作”[15]。
(三)官方組織檔案整理常態化
與重視檔案征求與收集相應,漢代王朝對檔案的整理十分重視。西漢立國不久,漢高祖就命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對前代檔案進行整理。武帝時期,又詔命楊仆整理兵書文獻。成帝命著名學者、光祿大夫劉向、劉歆父子先后領校秘書,數十年間,對漢代館藏檔案進行大規模整理,在整理過程中編制了我國第一部綜合性的系統反映國家藏書的分類目錄《七略》。東漢光武帝肇基,百廢待舉,即詔命尹敏和薛漢二人領銜整理館藏讖緯檔案。從明帝、章帝時期,政府檔案整理便成為日常工作,由校書郎中、校書郎專職負責。安帝時,著名學者劉珍等50余人整理東觀全部檔案,7年后,劉珍等人再次整理東觀收藏的檔案。順帝、靈帝時,亦承續有檔案整理。漢代政府組織檔案整理的常態化、日常化,使東漢的檔案管理取得了顯著成績,《漢書》《東觀漢記》《漢紀》三部史書在一定意義上均是東漢檔案整理的成果。
東漢檔案館藏中心從蘭臺到東觀的轉移,不僅是蘭臺機構職能的變化,更是檔案管理制度的創新。政府開始對檔案收藏進行統一規劃并實現了集中管理,開創了政府系統整理檔案、利用檔案的先例。這不僅拓展了檔案功能,使檔案具有了干預社會、服務社會的作用,同時還引起檔案功能觀的巨大轉變,對古代檔案事業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