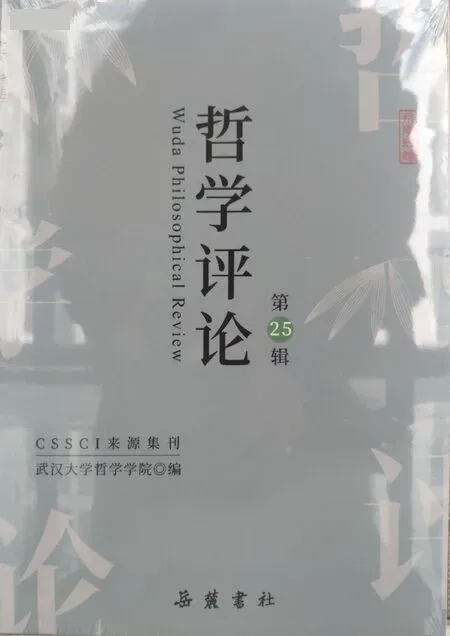全球化與啟蒙:彌合分歧
[德]漢斯·費格爾/文 晏臨風/譯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我的論題關涉到這樣一個問題:現代性之中的種種關系,文明化的進程,以及(主要由社會學家們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已經做了考察的)暴力[1]參見 Hans Feger, Hans-Georg Pott, Chr. Wolf: Terror und Erl?sung. Robert Musil und der Gewaltdiskurs der Zwischenkriegszeit. Musil-Studien Bd. 37. München 2009。這篇文章是對Bruce Matthews 的Kant’s Utopian Imperative and the Global Marshall Plan Initiative(載于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for the Common Good, 2006)一文所作的批評和重新解讀。是否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啟蒙的作為。如果確實如此,我們如何讓這些作為之間的關系變得可被理解,即便事物的秩序已經被整個顛倒了過來。在這關系之中附屬著這個有爭議的論點:始于上個世紀并被我們如今作為人類文明一大進步而歌頌的全球化,首先幾乎就是其對立面:一種權力和恐怖的全球化(a globalization of power and terror)[1]關于全球化與暴力之間的關系問題,目前正有許多學者和理論家在進行著爭論,包括Baudrillard, Enzensberger, Guéhenno 以及Rancière。對于嚴格意義上的前面提到的論題,參見Rudolph J. Rummel, Statistics of Democide.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New Brunswick, London & Münster, 1998; Death by Government, New Brunswick,London & Münster, 1994。。現代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把恐怖視作現代性的一種內在效應[2]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他的著作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1989, deutsch 1992)中正是這樣宣稱的。。這些論點,以其當前的形態,同(例如)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理論完全相反,對他來說歐洲歷史的長期發展表現出的是和解以及暴力的減少。但這些論點同樣與馬克思·韋伯傳統之下的那些理論相對立:根據韋伯,現代性等同于一種分化的進程,即合理化管理和教育,以及民主建制,因而在20世紀出現的暴力的肆虐實際上是現代性的反面。“現代文明杜絕暴力的特性”,如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所云,“只是一種幻覺,一種帶著申辯—理想化功能的神話”[3]Bauman, 1992, S. 111.。無論如何,必須要指出的是,當前的諸種解讀模式把恐怖更多地看作是一種外在的,經驗性的,以及統計學上可被描述的現象。由此,迫害的非人道性屬于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這種現代性是一種我們正在經歷的但仍未完成的啟蒙;諸如國家主義、種族主義以及“社會凈化”(social hygiene)之類的意識形態架構都可歸屬于那種起源于19世紀的、[建立]民族國家的咄咄逼人的沖動。甚至缺乏管控機制,或者說缺乏一種具備有效分權的發達的民主,也并不能被解釋為恐怖獨一的前提。[4]關于這個論題的探討,參見Hartmut B?hme: Gewalt im 20. Jahrhundert. Demozide in der Sicht von Erinnerungsliteratur, Statistik und qualitativer Sozialanalyse. In: figurationen 0(1999) , S. 139-157。如果有人把全球化實證地(positively)解讀為一種只能夠通過經驗事實和統計數據來考察的現象,那么一定是對恐怖視而不見。今天,我們已經首先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重新發現了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限制著國家行動的范圍并且似乎在一個毫無法律的空間中運行;我們看到全球化導致了高失業率,福利國家行動空間的喪失,以及富裕與貧困之間鴻溝的擴大這類后果。“富裕者是全球的,困苦者是地方的。”[1]Zygmunt Bauman: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New York: Columbia, 1998,S. 74.這種“全球化”顯然是一個神話,它對經濟自由主義而言具有一種秩序建構的功能,但與此同時在其受害者中散播著畏懼與恐怖。它把社會兩極化為參與者和純然被影響者,分化為勞動者與消費者。呂迪格·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提出,“當思維企圖把握整全的時候,它就掉入了一種全球化的陷阱”。[2]Rüdiger Safranski: Wieviel Globalisierung vertr?gt der Mensch. München 2002.按照他的看法,“全球化”是一種世界觀,它始于實際存在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政治、交流和信息的一體化,接著從這些無可爭辯的進程中得出一種驅動這同一個全球一體化前行的道德要求——單單因為它是善的,值得為之而努力。所以,它只是一種“過度要求的癥候”,這種癥候忽略個體,甚至侵犯個體的價值領域。
與此相對立的是從對“啟蒙的傳統”的關切中得出的“啟蒙的規劃”(Project of Enlightenment);也就是說,關切導向人類權利、社會正義與自由的普遍價值系統。由于諸如國家認同、敵友分化以及反現代性的生活觀念等其他觀點的支配地位,這些價值已經被削弱了。恐怖,尤其以其行動的全球性方式[3]當代恐怖主義意識到了文明復雜進程的脆弱性,并且它迫使我們采取(然而并非以實用主義的方式)只能夠在國際性法律觀點的立場下才能應付的反制措施。作為一種國際行動網絡,這些恐怖組織大概在由全球化本身所產生的沖突中有著它們的根源。因此它也可以只以國際的方式作戰。但正是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到一個從啟蒙的批判性理解而來的思維上的轉變:對國際恐怖主義宣戰是一種contradictio in adjiecto(即自相矛盾。好比下面這個陳述:對于自由的敵人而言不存在自由)。只使用軍事力量來打擊恐怖主義會讓我們陷入一個尷尬的邏輯,不得不利用同我們的敵人一樣的手段。這就意味著自殺式恐怖主義的那種背信棄義最終也適用于我們自己,也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如今被界定為“啟蒙的規劃”最大的敵人。這迫使我們批判地考察啟蒙的理念。在這個背景下,如康德所做的一樣,在“啟蒙的規劃”內部做出某種區分是很有助益的,也就是說,要理解如果不首先對自我進行啟蒙,啟蒙就完全無從談起。啟蒙可以簡單地被生產出來,這種幼稚的觀點是需要被批判的;一如全球化就其自身而言就有價值這種幼稚的觀點一樣。康德規定了啟蒙不僅僅是被消極地理解為從迷信中獲得解放,而是應該超越這種懷疑論并被理解為一種有待于在實踐中實現出來的[理性]成熟的形態。出于這個理由,啟蒙必須被界定為一種探求而不是一種現實的占有物:“所以如果這么問:‘我們目前是生活在一個已啟蒙的時代嗎?’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但是我們卻是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1]Immanuel Kant, Was ist Aufkl?rung? AK VIII, S. 40.譯者按:引文中譯參見康德《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康德著作全集》第8 卷,李秋零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5 頁。
如果我們想要讓這個理解啟蒙的新路徑有助于我們當前對全球化的理解,那就值得去考慮康德在他自己的晚期著作中如何描繪出世界—歷史的烏托邦前景。當康德于1784年出版他的《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的理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Cosmopolitan Intent)之時,不可能想象得到他超國家的和世界主義的思想會被隨后兩個世紀的歷史編撰所采納。充盈著啟蒙的樂觀主義,他展望了一個理性的世界公民的時代;對這些世界公民而言,一個未來的世界主義社會和世界國家近在咫尺,其進展現在就可以得到彰顯,而其前史現在可以被勾勒出來。雖然沒有使用“全球化”這個概念,康德主張“人類種族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應該被視為‘一個隱秘計劃’的實現”。我首先想要探求這一“隱秘計劃”同那顯見之物亦即同現實之間的關系。
一、全球化的現實
康德的全球化觀念是建立在人類自由這脆弱的本質之上的,尤其是建立在自由的正確運用同樣包括了它的全然誤用這個觀念之上,而只有批判的倫理學之先驗的合法程序,才能夠防止人類自由的自然的誤用。(康德以世界公民的法權狀態來表述的)全球化的進程不應該由利己主義和經驗性的動因(這是自然的誤用)所主導,而應該只基于我們道德法則的自律。
利己并不是一種指導我們的可行原則。它已經把我們帶入了當下的境地——按現代的說法——一個基于“自我中心”觀念的消費主義社會,它投入到掠奪資源的戰爭之中,其過度消費產生的廢物讓我們與我們的星球陷入病態。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導向來指引我們脫離當下的危機。讓我們擁抱康德的觀念吧,這樣一種命令向我們展現了超越利己主義崇拜的道路。由于對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入到戰爭中大肆自相殘殺的習性感到反感和困擾,康德的文章《論永久和平》(1795)為創建一種全球國家聯盟進行了論證,聯盟會用法律的統治取代刀劍的統治,從而把共同善的共享利益提升到單個民族國家競爭性的利己主義之上。世界公眾論壇要求一種顧及每一個人立場的思想層次[1]“世界公共領域體現了這種不受限制的溝通形式,這是康德的人類共識理想所要求的。”(James Bohman: Die ?ffentlichkeit des Weltbürgers: über Kants? negatives Surrogat’.In: M. Lutz-Bachmann et al., Frieden durch Recht. Ibid. p. 95.)——也就是一種我們每個人都應當以定言命令來思維的踐行普遍化準則的層次。一如不可剝奪的人類權利概念一樣,我們甚至用了兩百多年時間才嘗試著去實現康德的這個遠見,首先以國際聯盟,繼而以聯合國的形式。
那么,利己究竟有什么危險?任何人想要質疑一種全球人權體系所具有的強制本性,或者只是質疑一種跨國家的倫理規則,他就得回撤到由自己的民族國家所提供的作為導向的價值以及個人的文化—政治觀念。質疑某種全球法律體系的懷疑論者,使用了一種托馬斯·霍布斯已經在他的社會契約理論中提出過的論證:只有如同一頭巨龍(神話中的利維坦)一樣的國家,向外部發起對抗其他所有國家的戰爭,才能夠在內部維持一種人為組織起來的、勉強確保個體自由的秩序。馬基雅維利也已給出如下信條:只有采取將威懾最大化的政策才能維持一種可以保全自由的秩序。這些立場都不能為這種懷疑論提供達成全球法治下的和平的理由。國家之間的戰爭狀態,正如人與人之間的自然狀態,在這類理論中都成了某種自明的原則。基于這個前提條件,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倫理就不可能被拓展到跨政府的層面上。康德的結論是:對人們之間的和平共存有效的那些原則是可以拓展的;它們也對國家之間的和平共存有效。并不存在(如同休謨所主張的分別適用于人際關系和國際關系的)兩種不同的倫理規則,恰恰相反,它們原則上是一致的。存在于霍布斯和馬基雅維利觀念中的那種對全球化的倫理規則的懷疑論被康德轉換成了它的對立面:只有當它的原則能超越社群和國家的邊界得到適用,一種倫理規則才能同時適用于人們的共存[1]詳細內容可參見由沃爾夫岡·凱爾斯汀(Wolfgang Kersting)在一種“世界公民認知主義”“有效性理論語境主義”和“特殊倫理論題”之懷疑論中所提出的這種懷疑論的類型學。(Wolfgang Kersting: Recht, Gerechtigkeit und demokratische Tugend. Abhandlungen zu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am Main 1997, pp. 243-256.)。在霍布斯式的世界里,“國家的首腦對人民不存在契約性的義務,他不可能對公民行不義,卻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置他們”;這就是其行為的準則在政治領域所導致的結果。康德認為這“十分可怕”,因為這不可避免地導向對國內的專制主義和對外部的永久戰爭[2]Immanuel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by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84.。
由此我們到達了問題的核心:一種利己主義的政治,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合作參與(cooperative engagement)的可能性。這種合作卻是任何形式的和平與持續共存的條件。所需要的是另一種選項,一種超越利己主義的政治,它會轉而成為一種原則的政治,這會使關切不限于自我而是指向更重大之物,并由此超越自我的直接的經驗性欲求。雖然這個利益的重新導向并非忽略經驗性自我的欲望,但確實使其隸屬于那些超越它們的事物,這對康德而言就是道德法則。根據康德,只有對自我的重新導向,通過犧牲利己走向對道德法則的義務,人類才會確證實現永久和平事業的可能性。
遵守承諾要求對道德法則的義務。“應當”這個動詞所具有的定言力量(categorical power)表達了這種命令。作為一種要求,這一“應當”不僅意味著我們還未真正地踐行道德法則,而且也表達了道德法則所產生的敬重與敬畏,以召喚我們去實踐我們的義務的約束性力量,這類情感共同強化了義務的要求。對康德而言這是一個根本要點:道德法則只有通過我們對其產生的敬重和敬畏才能夠提供約束力,因為只有通過敬重和敬畏道德法則才能夠驅動(compelling),而非強制(coercing)行動,由此我們的自主性得到了保存。這種自由選擇的驅動力是對責任和義務的感受(feeling),它通向道德法則的“應當”所具有的無條件的要求;在康德這里,一種對責任和義務的感受是一切道德行為的必要條件。
對康德而言,信守承諾的義務并不是以經驗性的意志(empirical will)作為其條件的;這種意志是他律的,由其決斷的后果所驅動,因而它只會服從于畏懼和強迫,這是因為只有畏懼要比對感官愉悅的欲求更強。與此相反,理性的意志(rational will)是自律的,因為它可以自由地決定自己根據道德法則而不是行為的后果來行動。為理性的意志提供動機的并非恐懼,而是對正義的敬重、興趣和尊敬,甚至是對正義的愛。理性的意志不是由行為的可能后果所決定的,而是它自身對于道德法則的忠誠和敬重。
因此,只有那些擁有這樣一種對道德法則的敬重的國家才有能力遵守承諾。這些國家將由能夠超越其自身利益的領導人所引領。不同于(以優秀的馬基雅維利式風尚)根據他們自身的利益來理解“政治明智原則”的政治的道德家(political moralist),康德把這樣的政治家稱為“道德的政治家”(moral politician),他們如此解釋和應用政治明智的原則,以使得“它們能夠與道德相一致”[1]Kant, (1991) , 128.。這作為一種極其艱難并且幾乎是超脫現世的任務,迫使我們現在轉而去考察康德的事業中的烏托邦維度。
二、全球化的烏托邦層面
康德主張,指引我們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法則是神圣的,并由此應當得到敬重。為何如此?因為對康德而言,只有通過把我們的生活約束在道德法則的指引下,我們才能夠意識到我們存在的終極意義和目的,那正是配享幸福,而幸福也就是在亞里士多德主義意義上的Eudaimonia[2]譯者按:古希臘文的幸福。或人類的興盛(human flourishing)。盡管存在一種普遍的誤解,但康德的定言命令并不是一種想要在可感行為的相互性之中表達人類洞見的行為指導方針,而是一種使得道德行為得以可能就必須要達成的條件。定言命令不應該以邏輯一貫性的方式[3]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確地避免談及由意志的決斷所引發的后果。他只在一個地方(V 24)談到了這一點,但也只是為了反對把永福(blissful happiness)看作是絕對的意志決斷的一種可能后果。被理解為可應用于特定情境中的道德行為的一種普遍規則(它在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中就常常被這樣誤解);它是一種自由的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 of freedom)的法則,如果一個人想要道德地行動,這種法則就必須要得到滿足,無論這一行動究竟是怎樣進行的。
一般來說,這種理性的實踐概念為理性的秩序以及合作的協調一致提供了形而上學基礎。這是作為一種互惠的政治權利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它外化進入全球事務的世界,為一個國際法權和永久和平的道德世界提供了條件。簡而言之,政治權利將道德法則外在化為一種要求為他者承擔義務的政治法則。在此,法則通過他者而被給予,并得到強制實行,它們被制定成要對行為進行指引和判定,并要求強制性的參與。這樣,法律系統和社會約束必須被用來使政治法則的要求得以實現。必須使用強力(power),但只能在符合法律的情況下使用。這種對強力的使用與其說是一個道德問題(內在的自我決斷),而毋寧說是一個政治問題(外在的決斷)。保障我們權利的唯一方式是我們同意服從法律的外在引導。
相當于把個體自由地服從一個國家的正義法律而生活的同樣方式推廣到國際關系的全球層面,康德的政治權利觀念要求各個國家自由地同意去服從一種類似外在規則的約束力,也就是服從國際法的約束力。如果自律的個體應當自由地使其自身利益服從道德法則的命令,那么同樣地,國家也應當自由地服從國際法的要求。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康德憧憬著真正的人以及人道的文明,在其中正義掌控了野蠻的力量和破壞,與一種同我們這個種族一樣古老的渴望達到和諧一致。
為了實現這一點,康德承認我們必須有理由去期望其可能性。康德在他的《人類歷史起源臆測》(Conjectures on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1786)中如是說:“最為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滿足于天意(providence),即便它為我們在世間安排的道路終究艱苦。”(A23)為此我們需要一種我所謂的烏托邦的設想,因為就像康德主張的,為了讓我們擁有對配享幸福的可能性的希望,我們必須把我們的經驗世界看作仿佛是一個道德的世界,他所描述的“作為理性存在者在感官世界中的一個神秘體(corpus mysticum)”;他對這個世界進一步的界定是,在其中“每個存在者的自由任意在道德律之下具有既和自己也和每個別人的自由任意普遍而系統地相統一的特點”。[1]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 836, trans. N. K. Smith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64) . 譯者按:引文中譯參考《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4 頁。康德提出,為了超越個體性的目的,試圖產生一種道德世界的反思性理念的實踐理性需要創造出歷史的一幅道德圖景。這是他全球化觀念的重中之重。關鍵問題是:人類歷史中的行動者們,當他們想要堅持一種自由的立場時,必須要有一種與那些還受困于當下歷史的限制之中并且僅以經驗主義為基礎來理解它的人們完全不同的歷史圖景。這種自由決斷的行動者的世界觀需要一種不同的體制:這種體制不是按照因果性原則而組織起來的,而是描繪了一種圍繞著其行動未受限定的行動者以合目的方式組織起來的關系[2]參見 Pauline Kleingeld: Fortschritt und Vernunft: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 Kants, Würzburg 1995, p. 91.。這種關于一個道德世界(一種神秘體)的理念,只適用于我們想象和思想的世界,因為它只是一個“純然的理念”,其作用是幫助我們把現實世界變得“盡可能同理念相一致”[3]Ibid.。并且只是就這個理念在何種程度上有助于我們去實現它,此一理念才具有客觀現實性。
在17 和18世紀,一向有著眾多作品敢于推出對于可能的未來社會和國家的浮想聯翩,它們建立在同支配著歷史上的人與國家亦即現實世界的權力原則顯然相悖的另一些原則之上:首先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Nova Atlantis, 1627)以及萊布尼茲的《法律大全》(Corpus Juris Pentium, 1693)。與我們的主題更直接相關的是,我們不可忘記第一個國際法庭和國家聯盟的計劃,該計劃由圣皮耶爾神父(Abbé de Saint Pierre)在他的《永久和平計劃》(Projet de Paix Perpétuelle, 1713)中有所概述。〔這部作品被盧梭在他自己題為《永久和平方案》(1761)的文章中做了最為忠實的學習和模仿。〕這樣,烏托邦讓我們面對一種比樸素和貧乏的日常現實要更加堅實和充滿意義的生活和世界之遠景(vision);的確,它同當下日常現實就處在一種渴望得到實現的關系中。它將會考驗人類的可能性,并支撐我們對于幸福與美的要求。烏托邦的意義在于一個尚未存在的未來;它的力量在于想象力,從而批判地拒絕一種壓抑的現實,而偏好一種有可能成為現實的遠景。而且正是烏托邦遠景中這一非現實的維度使得康德做出批判,論證它并不具有顛覆的和解放的力量。將這樣一種烏托邦式的遠景整合入我們自己的社會,并不會促成一種超越我們經驗現實的具體限制的力量。這樣一種烏托邦式的遠景并不能推動我們的想象力以此方式同時也聲稱自己正在促進道德的歷史。與此相反,我想要說明,烏托邦的命令(utopian imperative)在康德的作品中乃是要求理性去培養“烏托邦的良知”(utopian conscience),而并不需要在創造一個不同于我們過去的未來這件事上,將想象甚至是幻象(illusion)中具有的價值和必然性付諸實現[1]Pauline Kleingeld: Fortschritt und Vernunft: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 Kants, Würz-burg 1995, p. 14.。在康德的觀念中,烏托邦的設想是確定性和幼稚的樂觀主義的反面,因為它包含著風險和可能的祛魅:希望要成為希望就必然有失望的可能。
為此我們要求一種尚未存在的道德世界的理念,因為只有通過對道德完善世界的可能性的信念,我們才能擁有去實現我們對道德法則的義務所需要的“希望”;道德法則要求我們相信人類有能力走在實現“其生存的道德目的”的進程上[2]Kant, (1991) , 128.。康德寫道:“我的論證基于我天生的、要以實現長久進步的方式影響我的后人的義務,而且這個義務也許能在這個序列的一個又一個成員之中正當地被傳遞下去。”[3]Ibid.依據定言命令的形式,我們可以說他的烏托邦設想不在于去預想一個更完美的世界的義務,而在于以實現一個更完美的世界的方式去行動的義務。
三、彌合分歧
就此,我想推進到對這思想的烏托邦設想做一個非常簡略的概述,在這里全球化自身表現為以一種轉變我們意識的預言性的召喚,由此自我的興趣被導向對它自身經驗性的、短期利益的超越。隨著人權的發展,我們站在了一個時代的開端,這個時代自我不再是被宗族、種族、身份、教條或者國家所指引,而是服從于義務和承諾。推進這個過程需要一種新的看待我們自己的方式,既把自己視為個體,也視為世界共同體的公民;這種意識的轉變會在政治角力場中產生一種新的競技者和力量,也就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種新的政治力量是公民之間相互聯結的結果,他們不受國家身份、宗教信條或者種族身份的束縛。這樣,公民社會甚至會成為能夠同既有的企業和政府權力相提并論的政治力量,但是拒絕由利潤和權力構成的自身利益的指導,而是選擇按照道德法則的命令行動。只有公民社會的信念和行動,通過提供一個道德原則組織起來的世界這樣一種烏托邦遠景,而不是出于利潤或者個體國家對權力的興趣,才能展示商業和政府的真正利益。
這聽上去十分理想化。所以我們要回到康德在1784年提出的世界主義觀念的實質。
在他的文章《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理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Cosmopolitan Intent, 1784)中,康德表明一種“非社會的社會性(unsocial sociability)”會促進通向一個更好社會的歷史進程。康德的歷史期望建立在有可能升華為道德傾向的非道德動機上。但這種人性的稟賦如何導向道德的改善?我們如何彌合分歧?而且當我們的歷史和全球化圖景總是經驗性地聚焦于全球沖突的殘酷性之上,我們如何相信這一進程確實是一種道德的進程?在其晚期的作品,即《系科之爭》(Contest of the Faculties, 1798)這部作品中,康德重拾了這類問題并主張:盡管我們無法經驗到道德進程的歷史,從而證實(verify)我們的歷史在走向一個世界主義終點的期望,但我們也許可以在一個謹慎但可及的事件中找到一種“歷史跡象”(Geschichts zeichen),這個事件有可能展現或者“指向”一種道德進步的趨勢。我們只能夠把種種歷史事件堅定地重新解釋為“歷史跡象”,才能對全球化這一道德進程的實現具有信心,并拒斥一種普遍的誤解:它不能被理解為一種將道德拓展到極致的行為。而且康德給了我們一個例子:在法國大革命的觀察者們“普遍然而冷靜的同情”中,這樣一種跡象被揭示出來了。我想要主張的是,只有審美的反思或者說一種審美的“思維模式”才能夠關注到走向更好社會的歷史導向。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中,康德把這一點解釋成為進行一種“世界直觀”(Weltanschauung)[1]Kant KdU B 91 (§ 26) . Weltanschauung 這個術語亦可翻譯為“世界觀” 。所做的審美的美化;現在我們也許會稱其為神話思維(mythological thinking)。
我們要對這個非常有趣的主題作更切近的觀察:不是針對將革命意識視作法國大革命的原因的經驗觀點,而是針對將其反思為象征性的事件的審美觀點,這種審美觀點才能夠看出1789年這個歷史跡象所具有的導向的意義。這種指向一種普遍、必然但從時間上無法確認的因果性的跡象,鑒于它所起到的是為所有三種時間性的綻出(all three temporal ecstacies)提供證據的作用,必須被界定為一種回顧性的、展示性的和預測性的跡象(signum rememorativum, demonstrativum and prognosticon)。作為一種自然的跡象,它同時是歷史中的人類理性的一種代表性的表達(deputizing expression),因此它是一種出自自由的因果性實際存在的證據。“以自然的方式做出預言”,它標志著從自然的歷史轉向理性的歷史的崇高轉折點,或者按我的表述:從暴力轉向自由的崇高轉折點。大革命事件顯示了自由的因果性已然總是(回溯性的)、現在正是(顯現性的)、將會始終是(預言性的)有效的,但只對于那些領會到它并且不把它當作某種事實本身(暴力事件)來反思的人而言,這些人帶著旁觀者的熱情將其視為一種審美現象。它并非一種經驗意義上的客觀知識,使得我們由此而確信全球化的進程正處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而是一種在道德圖景下賦予這個進程某種理性基礎的主觀的正當化(subjective legitimation)。這種贊同和偏愛甚至能夠被并未參與其中的那些人所感覺到[2]“這場革命,照我說,畢竟按照希望在所有旁觀者(他們自己并沒有卷入這場演出)的內心中發現了一種近乎狂熱的同情……”(Kant, Contest of the Faculties, A 144, ed.Reiss, p. 182.)譯者按:此處引文中譯參考《論教育學·系科之爭》,楊云飛,鄧曉芒譯,鄧曉芒校,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9年,第191 頁。,這說明創造出適用于每一個人的目標這件事突然規定了個體的行動。“公開地暴露出來,并且透露對一方的演出者的一種如此普遍卻又無私的同情,但卻反對另一方的演出者”[3]Kant, Contest of the Faculties, A 143, ed. Reiss, p. 182. 譯者按:引文中譯參考《論教育學·系科之爭》,第190 頁。,這揭示出了全球化的歷史中的一種近乎狂熱(enthusiasm)的公共精神,而對康德來說,這種狂熱只有在審美反思的時刻才會發生。在對大革命事件的審美反思之中,這段歷史的戲劇性讓這位批判哲學家得以確信,獨立的理性“把在感官事物中向我們隱藏著的事物秩序建立起來,維持下來和完成起來”[1]Kant, KdrV, B 842. 譯者按:引文中譯參考《純粹理性批判》,2004年,第618 頁。。這不僅是一個大自然有計劃地展開,以便通過歷史的道德圖景支持實踐理性的過程;對他而言,歷史的戲劇被轉化為一種哲學的戲劇。
我們在這里做一些總結:將全球化的意識解釋為一種反思判斷的行為,就可以彌合啟蒙與全球化的分歧。將那些“最微弱的跡象”[2]在這個方面,康德使用“事件的循環”這個術語用以探討他的歷史哲學中的解釋學循環,它所展現的是“這條路徑最微弱的跡象”,為了在“漫長的時間中”這種“事件的循環”能夠“得到完成”(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Cosmopolitan Intent, A 404)。在這里主導性的比喻意象依舊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據此,觀察者自身旋轉,恒星則保持靜止,從而強迫自然回答觀察者的問題 (KdrV, B XIII) 。這些向著改善前進的跡象,這些他通過“人類天賦中……惡與善的混雜”,經由“否定的智慧”(negative wisdom)之論證 (Contest of the Faculties, A 160)所得出的跡象,其實無非意味著: 人們并未擁有某種穩固的品格,但他依舊不得不去創造出這樣一種作為“轉折點”(punctum flexus contrarii)的品格。集合在一起,這些跡象就可以被解讀為一種證據,也就是啟蒙的進程是不可逆的,而關于全球化的歷史如何被必然書寫的計劃,甚至已經影響了這段歷史的結果。從康德的歷史批判的設想出發,它們是“這條路徑最微弱的跡象”[3]Kant,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Cosmopolitan Intent, A 405 (=8th Sentence) , ed.Reiss, p. 50.,這些跡象有可能被解釋為自然的計劃可以被啟發式地采納的證據。這樣,“如果只是間接地”作為“理性的支持”而言[4]Kant,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Cosmopolitan Intent, A 405 (=8th Sentence) . 在《系科之爭》中,康德對自己提問:“單純通過哪種秩序讓我們有可能去期待一種通向改善的進程?回答是:不是通過自下而上,而是通過自上而下的事物進程。”譯者按:引文中譯參考《論教育學·系科之爭》,第200 頁。,歷史的目的論圖景的理念已經證明了自己的意義。
以這種方式,文化發展、公民自由或者自由貿易就展現了進步本身——只要它還在這樣的程度上被確保:倒退只會導致對每一個人的不利——但這類進步并非不會導致任何后果。與此同時,這個過程所引發的后果是不斷地企圖從傳統的束縛中獨立,轉向一種系統的進步過程,并且持續產生新的、“在過去不存在先例”[1]Kant,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Cosmopolitan Intent, A 406 (= 8th Sentence) , ed.Reiss, p. 51.的關系。在這個不再允許過去同未來相聯系的加速過程中,歷史最終達到了自然的自我指涉的無盡的分界點(endless break point of natural self reference);在某個轉折點上,康德已經就意志自律而言在他的《實踐理性批判》[2]例如參見Kant, KdpV, A131.中將其典范性地描述為一種自我規定的行為。這種行為可以被理解為自我決斷(self-referentia),也就是一種只依賴于立法形式的行為。而這種立法不再具有恒久不變的自然規律的特征;相反,它是一種由未來所產生的、接納自律帶來的挑戰的狀態。它通過一種指令的形式使得我們有意識地以如下方式行動:仿佛存在著一種對所有人都有效并具有約束力的自然規律。
最后,在康德的《遺著》(Opus posthumum)中,他依舊認為歷史進程的根源隱藏在某種自然因果之中。當然,能夠被發現的只是一種進步的能力。道德進步在歷史中確實有其效果——這種希望勝過了一切概念。理性無法像占有某個有形的所有物那樣占有善,毋寧說,理性只能夠產生善。這就是為何理性如果想要具有全球性就必須依賴于歷史的道德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