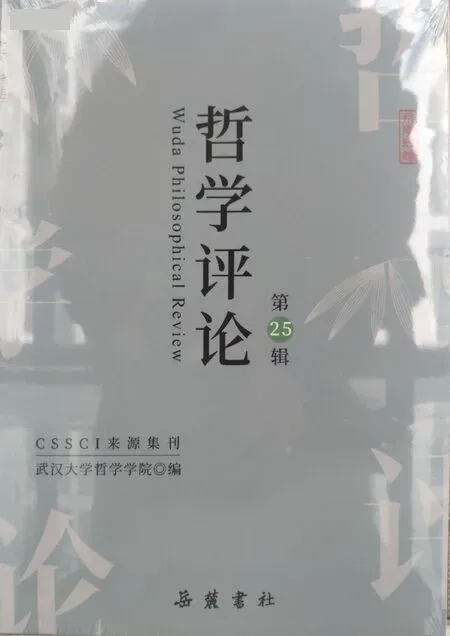一幅黑格爾法哲學的導游圖
——評里德爾《在傳統與革命之間:黑格爾法哲學研究》
朱學平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自面世以來,即成為學界紛爭不已的淵藪。人們從各自的立場和觀點出發,或對其提出經常是極其嚴厲的批判,或極力為之辯護。相反,從黑格爾法哲學本身出發對其進行同情理解的作品,實屬罕見。是故德國當代哲學名家里德爾(Manfred Riedel, 1936—2009)的名作《在傳統與革命之間:黑格爾法哲學研究》[1]Manfred Riedel, 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Erw. Neuausg.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2. 此書中文版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就顯得彌足珍貴。1969年,此書初版以《黑格爾法哲學研究》之名面世,收入作者上世紀60年代撰寫的5 篇文章。次年旋即再版。1982年第3 版又收入了70年代的三篇文章,除最后完成的“制度中的辯證法”外,其余兩篇(“自由法則和自然的統治”和“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進步與辯證法”)均取自他1973年出版的《歷史與體系》一書。[1]這兩篇文章見Manfred Riedel, System und Geschichte: Studien zum historischen Standort von Hegels Philosophie, Frankfo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3, 第40—64 頁和第96—120 頁。這三篇文章使本書的品質得到了全面升華。總體來說,此書實為作者長達15年之久的潛心研究和深入思考的結晶。
作者在“初版前言”中明言,此著旨在拋開“流俗理解之下的《法哲學原理》的效果史及其對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納粹主義這些全球性意識形態的諸般影響所提供的歷史觀”,而是“想要像作者理解他本人一樣去理解他,由此出發進行解釋”,因此,他便不得不面對“黑格爾的問題”,并“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及霍布斯、盧梭和康德的眼光去重新閱讀黑格爾法哲學”[2]Manfred Riedel, 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Stuttgart:Klett-Cotta, 1982, p.5.,以收撥亂反正之效。1982年的“新版前言”中,作者進一步強調指出理解黑格爾法哲學的兩個基本維度,即亞里士多德所建立的西方政治哲學傳統和歐洲近代自然法傳統。作者明言,黑格爾法哲學與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之間的關系證明了黑格爾并不是從19世紀的海謀到20世紀的波普爾所攻擊的保守派或者威權主義者。[3]Ibid, p.7.顯然,里德爾意在擱置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由黑格爾法哲學所衍生的各類學術塵積,直面問題與思想本身,對其做出盡量忠實的理解和解釋。
就內容上看,此書最早的三篇文章構成了里德爾研究的第一個階段。全書的主題一開始即已明確提出,但作者此時顯然處在前人的巨大影響之下,并試圖對前人做出一個綜合與超越。從這一時期的文章可以看出,最初對他的理解產生最大影響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馬克思,一個是乃師卡爾·洛維特。最早寫成的獻給洛維特65 歲大壽的“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傳統與革命”一文實際上是從洛維特的觀點出發,而與馬克思的一個對話。此文意在糾正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片面理解。是以他一方面高度評價馬克思,說他是“在他的時代唯一如其所是地對待1821年《法哲學原理》的人”,并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19世紀黑格爾傳承中對法哲學所做的唯一一部與黑格爾的論述處于同等水平、有時在歷史方面還相當深刻的評論”;[1]Manfred Riedel, 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Stuttgart:Klett-Cotta, 1982, pp. 172-173.另一方面則又明確指出,馬克思并未“提出黑格爾法哲學在政治哲學傳統中的地位問題,按其歷史意圖,它根本就不可能提出這個問題”。[2]Ibid, p.173.顯然,作者意在馬克思之外,加上“傳統”的視角(這是洛維特所強調的),以更加貼近黑格爾法哲學本身。由于里德爾相信馬克思已經對黑格爾與革命的關系做出了充分論述,因而此文重點便落在黑格爾與“傳統”的關系上。里德爾通過對“倫理”部分的分析,指出黑格爾法哲學一方面回歸了歐洲政治學傳統思維方式,從倫理的角度出發思考法哲學問題,另一方面則又通過市民社會理論徹底摧毀了傳統,從而與傳統根本決裂。由此,里德爾就在揭示傳統的背景下,重新發現了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所具有的至關重要的革命意義。于是,市民社會也就成為他在傳統與革命的雙重視角下審視和評價黑格爾法哲學的核心。他接下來發表的“‘市民社會’概念及其歷史起源問題”一文即轉入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分析和討論。
在此之前,學界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理解。一是主流見解。從黑格爾下一代的洛倫茨·馮·施泰因、馬克思、布魯諾·鮑威爾等青年黑格爾派,經拉薩爾、滕尼斯,到20世紀的學界大咖馬爾庫塞、盧卡奇和里特爾等人,基本上都是從經濟學出發理解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并將其與近代自然法理論(尤其是霍布斯的理論)混淆起來,從而實際上誤解了黑格爾“市民社會”概念的根本含義。二是羅森茨威格的看法。羅氏認為黑格爾是從舒爾策、弗格森等人那里接受了這一概念。里德爾明言,這兩條理解進路都不能令人信服。第三種理解來自洛維特。洛維特從古代和基督教的二元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的對照與調和出發理解黑格爾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問題。[3]參見[德]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326 頁以下。顯然,這是里德爾理解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基本前提。但他又不完全遵從洛維特的解釋,因為洛維特一方面主要從盧梭出發理解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另一方面也僅僅將黑格爾與傳統的關系的理解限于柏拉圖的《理想國》,從而既未充分理解黑格爾市民社會概念的現代與革命的因素,亦未充分理解它與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關系。
里德爾一方面堅持之前對馬克思的超越(即補全黑格爾法哲學的“傳統”因素),另一方面又用馬克思等人的社會歷史因素豐富洛維特的見解。通過揭示黑格爾法哲學的“傳統”因素,他提出并回答了馬克思當年“不可能提出”的問題,即“黑格爾法哲學在政治哲學傳統中的地位問題”,指明黑格爾法哲學的偉大貢獻在于,它在新的社會變革的背景下,提出全新的“市民社會”概念,將國家與市民社會明確區分開來,從而確立了他作為德國社會理論真正創始人的地位:德國的社會學理論,不僅要追溯到洛倫茨·馮·施泰因和馬克思,而且要追溯到他們的老師黑格爾。可以說,這是里德爾本書最重大的成果。相對于前人(如19世紀的海謀和20世紀的新黑格爾主義以及英美學界的波普爾等人)主要從黑格爾的國家學說去評斷其法哲學來說,里德爾的工作更有意義:他揭示出黑格爾法哲學的真正功績在于通過市民社會理論,開創了社會理論的新傳統;黑格爾將因此而在人類思想史上擁有不朽的地位。里德爾的這種評價,現已成為德國學界的基本共識。當代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考夫曼(F.X.Kaufman)在其《社會政治思想的德國傳統》中追隨里德爾,明言“正是在黑格爾法哲學中,政治和社會第一次出現為兩個分離的領域”,并指出“這種理論,特別是通過帕森斯和盧曼的著作而成為現代社會理論最重要的范式之一”,[1]F. X. Kaufman, Thinking About Social Policy, Berlin [u.a.] : Springer, 2013, pp. 29, 30.實際上指證了黑格爾作為德國社會學創始人的崇高歷史地位及其對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奠基性意義。可見,里德爾此文的意義在于,在用社會歷史內容豐富洛維特古今視角的基礎上,修正了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基本評斷,指明黑格爾法哲學(尤其是其“市民社會”理論)在西方政治哲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它與傳統的關系。
如果說作者最早的兩篇文章主要在于修正馬克思的話,那么“對國民經濟學的接受”一文則是旨在修正與超越洛維特的見解。之前,里德爾曾指出:“只有在洛維特這里,黑格爾法哲學的市民社會似乎才第一次得到全面考察,因為他將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區分……與古代和基督教的二元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柏拉圖的《理想國》聯系起來。”[1][德]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141 頁。現在他卻不點名地批判道:“當政治學與自然法的對比限于盧梭《社會契約論》和柏拉圖《理想國》的原則上的對照、限于‘個別性’和‘普遍性’的環節時,真正說來,這算不上是真正具有原創性的對比。”[2]同上書,第116 頁。可見,經過前述研究之后,里德爾不再贊成洛維特的觀點(“黑格爾法哲學是古今的調和”),而堅持黑格爾與傳統的根本“斷裂”。在他看來,黑格爾法哲學既超出了古典政治學傳統,也超出了近代自然法。對于黑格爾為何能夠超出二者這一問題,里德爾訴諸黑格爾對經濟學的接受。換言之,他轉而通過馬克思的觀點(即將市民社會歸結于經濟學)來回答這一問題,認為正是對經濟學的接受導致了黑格爾與“傳統”(包括西方古典政治學傳統與近代自然法)的斷裂。顯然,對黑格爾法哲學與古典經濟學關系的考察使里德爾擺脫了洛維特的“調和論”,但黑格爾擺脫傳統是否真的就是他接受經濟學的結果,卻是一個問題。因為如果接受經濟學是黑格爾走出傳統的根源的話,那么黑格爾為何要在研習經濟學多年之后才逐漸形成其市民社會理論,而不是從開始接受經濟學起即與傳統斷裂呢?
可以說,里德爾最早的研究游走于馬克思的經濟社會解釋模式與洛維特的古今調和模式之間,一方面用后者所具有的傳統維度修正馬克思的觀點,另一方面也通過前者來克服后者的基本見解,指明黑格爾法哲學的本質不是古今的調和,而是與傳統的斷裂與開新,而其論域則基本上沒有跳出(馬克思的)經濟與社會視角之外。60年代后期的“對自然法的批判”一文是里德爾理解上的一個質的飛躍,標志著他的研究進入第二個階段。此時,他開始轉向從更深的本體論層面出發理解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傳統與革命的關系。
在深入理解德國觀念論哲學的基礎上,里德爾更深地領會到,在黑格爾這里,西方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對立的本質在于自由與自然的對立。由此他便在觀念論哲學的基礎上,對黑格爾與傳統的斷裂做出了全新的解釋。他認為,這種斷裂的根本原因是哲學上的,而非經濟學上的:黑格爾在耶拿后期通過對康德和費希特自由哲學的接納,擺脫了謝林自然哲學的影響。耶拿后期的黑格爾一改之前對康德、費希特個體主義立場的完全否定,承認“自我”“人格”乃是現代精神的表達,將其作為構建法哲學的真正前提和出發點,由此而與亞里士多德所創建的古典政治學傳統決裂。顯然,里德爾的這種新的見解一方面更新了黑格爾哲學中古今對立的內涵,即這種對立不是洛維特所言的盧梭和柏拉圖之間的對立,而是以費希特和康德為代表的主體原則與以謝林、斯賓諾莎為代表的實體原則之間的根本對立,從而極大地深化了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根本本質的理解;但另一方面卻將黑格爾解釋成一名康德主義者或者費希特主義者,沒有對黑格爾與康德、費希特做出原則上的區分。這樣,作者實際上就只是指出黑格爾走出了古典政治學傳統,而未說明他對近代自然法傳統的超越。同時,馬克思所代表的主流解釋傳統所揭示的經濟學因素對黑格爾法哲學到底有何作用,也是里德爾在轉向形而上學的解釋路線之后不得不重新思考的一個問題。
里德爾接下來在“客觀精神與實踐哲學”一文中開始回答這些問題。此文標志著他的研究進到第三個時期。這一時期,他的研究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和深化,開始真正進入黑格爾法哲學的內核。如標題所示,該文的目的就是要處理黑格爾與歐洲傳統實踐哲學的關系,后者既包含了亞里士多德創建的古典政治學傳統,也包含了從霍布斯到康德、費希特的西方近代自然法傳統。基于對歐洲實踐哲學歷史的全面梳理,里德爾指明康德的實踐哲學構成了歐洲實踐哲學發展的最新階段,它將實踐哲學建立在自由法則(而非自然規律)之上,從而徹底摧毀了之前的整個實踐哲學。而黑格爾的客觀精神及其辯證法則在康德實踐哲學的基礎上,進一步超越并且瓦解了歐洲實踐哲學傳統。在他看來,康德的自由理論只是黑格爾超越并摧毀傳統的第一個必要條件。他進一步指出了其余兩個條件:1)把現代國民經濟學納入實踐哲學的構建中;2)將實踐哲學擴展到歷史領域。里德爾指出,通過前兩個條件的結合,黑格爾一方面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主奴關系辯證法,從而徹底解決了亞里士多德傳統中的主奴關系問題;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對經濟學的接納使得勞動概念成為黑格爾精神哲學中的核心概念,通過勞動概念,黑格爾瓦解了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為止的傳統實踐哲學中對制造與行動之間的關系的理解,而將其哲學建立在“(精神的)勞動”,而非“行動”之上。同時,隨著黑格爾將實踐哲學擴展到歷史領域,實踐哲學的概念便進入歷史的辯證運動之中,由此“概念”與“歷史”在“(精神的)勞動”中獲得了內在統一。
顯然,里德爾由此將之前的兩條重要解釋路徑(概念—形而上學的解釋路徑和經濟—社會的解釋路徑)內在地貫通了起來。通過“自由”“勞動”與“歷史”的結合,里德爾將他對黑格爾法哲學的理解提升到了黑格爾的精神本體論和辯證法的高度,由此出發重新理解黑格爾與傳統和現代的關系。里德爾據此分析指出,黑格爾超越康德實踐哲學之處在于,他將康德的主觀自我提升為精神自我,其本質為概念與歷史、邏輯與經驗的內在統一。在“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進步與辯證法”一文中,里德爾通過對比分析康德與黑格爾的法國大革命觀,指出與康德將自我、概念與時間、歷史截然分開不同,黑格爾將康德的“我思”與歷史和時間內在地統一起來,由此,自我(或“概念”)就不再是“空洞的統一性”,而是包含了“普遍性”“特殊性”“個別性”三個環節的具體統一,并且直接出現于時間和歷史中。黑格爾不僅由此突破了康德的“自我”的抽象性,而且實現了“體系向歷史的突破”。同時,就法哲學方面而言,里德爾指明黑格爾一方面繼承了近代自然法理論的自由法立場,并在它的基礎上進一步建構其法哲學體系,因此他不是“取消”,而是“強化”了近代自然法;[1]Manfred Riedel, 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Stuttgart:Klett-Cotta, 1982, p. 76.另一方面,黑格爾法哲學的邏輯學前提——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使得黑格爾將“法”從抽象的自由概念理解為“自由的理念”,也就是“概念和現實的統一”,由此自由也就不再是一個“應當”,從而超出了康德、費希特的自由法體系。
另一方面,就黑格爾與傳統的關系而言,由于黑格爾將“勞動”規定為精神自我的本質,從而與以“實踐”或“行動”為核心的傳統實踐哲學發生根本斷裂。里德爾的這種看法可謂與青年馬克思不謀而合。眾所周知,馬克思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精辟地批判指出:黑格爾“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化的人、現實的、因而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黑格爾唯一知道并且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 頁。然而,里德爾并未追隨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精神勞動理論的激烈批判,而是指出黑格爾哲學與傳統發生斷裂的本質在于,精神如何通過作為其自身之本質的勞作走出傳統自然精神,進入超越自然的自由精神。由此,就與古典政治學傳統的關系而言,近代自然法由于未能確認勞動在現代社會的關鍵地位,無法對市民社會與國家進行區分,從而重新落入傳統的窠臼之中,無法真正走出“自然”。相反,黑格爾則通過肯認這種分離而告別以國家或公民社會(也就是以“實踐”)為中心的西方法哲學傳統。由此,作者便在“勞動”的基礎上,又一次對黑格爾法哲學與傳統和現代(革命)的關系做出了新的解釋。
“制度中的辯證法”是本書中最后完成的一篇,也是其壓軸之作,它構成了作者研究的最后階段。正如“傳統與革命”一文可以視為全書的“導言”一樣,此文可以視為其“結語”和“完成”。但它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小結,而是進一步將黑格爾法哲學由邏輯、概念的層面推向制度的層面,由此將其對黑格爾法哲學的理解和解釋推向最高潮:法的概念(或曰“自由”)的本質在于制度,自由理念的實現在于自由(或理性)制度的構建,黑格爾法哲學體系根本而言為一自由的制度體系。作者明言,黑格爾“哲學法學的方法上的創新并不在于從規范性的法原則推演出超歷史的法規范體系,而是把通達理念的道路理解為各種制度的歷史形成過程”。[2]Manfred Riedel, 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Stuttgart:Klett-Cotta, 1982, p.42.這一論斷意味著作者將黑格爾法哲學對近代自然法的超越進一步從(邏輯與本體層面的)概念與歷史的統一推到制度的層面。作者的探討由此進入黑格爾法哲學的最深處。
從制度的角度出發,黑格爾法哲學與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再次呈現出新的面目。就其與現代自然法理論的關系而言,黑格爾法體系本質上就不僅僅是規范性體系,而是制度性體系。法的本質不僅在于保障個體自由的規范性權利,更在于保障實現此種權利的制度體系的奠立。黑格爾法哲學獨具特色的倫理部分即在于用制度性體系超越并揚棄作為現代自然法之體現的“抽象法”和“道德”部分。同樣,在黑格爾法哲學與現實(革命)的關系上,里德爾也從制度的角度出發回應馬克思的基本觀點,明言“黑格爾立足于現代革命及其制憲和立法的基地之上,現代革命的制憲與立法將自然法實定化了”。[1]Manfred Riedel, 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Stuttgart:Klett-Cotta, 1982, p. 48.
在與傳統的關系上,里德爾一方面重申之前的看法,指出“黑格爾的倫理理論仍然意味著把一個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學的范疇重新引入到《法哲學》之中”,[2]Ibid, p. 52.即是說,它依然基于古典政治學傳統。同時又指出,它并非對古典倫理的簡單的照搬照抄,而是基于當前歐洲社會的倫理革命(里德爾說它“記錄了從18世紀轉向19世紀時在政治—社會世界建構中已經完成的根本變化”[3]Ibid, p. 53.),構建當下的制度性倫理體系。
黑格爾的“倫理”作為制度性倫理體系,最鮮明地體現了黑格爾法哲學與傳統和現代的關系。一方面,作為其法哲學的核心,基于傳統的“倫理”克服了近代自然法的抽象的個體主義;另一方面,它又將傳統倫理現代化、制度化了,從而超越了傳統。在黑格爾的倫理體系中,市民社會理論將這種關系最為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一方面,基于現代自然法和革命之上的市民社會完全突破了傳統國家的體系結構,“改變了古典政治學和近代自然法數世紀以來一以貫之地予以闡述的家庭和國家的體制”,[4]Ibid, p. 61.從而在繼承倫理傳統的形式下對其做出了徹底的改造;另一方面,它又完全超出了近代自然法的契約理論,在經濟學的基礎上,構建起一個以勞動和需要的體系為基礎的制度性體系,克服了自然法理論的形式性、抽象性,并且獲得了倫理的意義。
概言之,里德爾的研究主要從洛維特和馬克思的對勘出發,經過日益深入的探討,最終完全超越了兩者的觀點,對黑格爾法哲學做出了獨特而又深刻的解釋。就其與洛維特的關系而言,洛維特的古今對比(即“傳統”與“革命”)的視角構成了里德爾理解黑格爾法哲學的基本前提和出發點,同時也是貫穿全書的基本框架。盡管如此,他并未堅持洛維特的“調和論”,而是很早就提出,黑格爾法哲學不是古今的“調和”,而是與傳統的斷裂與開新,從而對其做出了全新的歷史評價:黑格爾以其市民社會理論,實現了與亞里士多德以來包括近代自然法理論在內的傳統的根本斷裂,開創了社會理論的新境界,黑格爾由此獲得了與亞里士多德平起平坐的、甚至超出了西方近代自然權利理論奠基人霍布斯的崇高地位。
顯然,里德爾之所以能夠超出洛維特的觀點,與其接受以馬克思為代表的主流的經濟解釋模式直接相關。但他并未簡單停留在這種解釋模式上,而是由此出發,步步深入,從青年黑格爾對康德、費希特的接受,到成熟黑格爾以勞動為核心的精神本體論,最終追溯到《法哲學原理》的制度倫理理論,對黑格爾法哲學與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做出了立體、豐富、深入的解釋。里德爾的研究幾乎展示了理解黑格爾法哲學的整條光譜,將其精要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基本實現了他要“像作者理解他本人一樣去理解他”的目標,為讀者進入黑格爾法哲學提供了最好的指南。同時,這一研究也為后學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啟示(或曰“警示”):一方面,從后人(包括馬克思和洛維特等人在內)出發理解黑格爾法哲學,可能依然不得要領;另一方面,即使從黑格爾本人出發(如僅僅從青年黑格爾出發或是僅僅從黑格爾晚年的邏輯學出發)也不一定能夠達到對黑格爾法哲學本身的本真理解。相反,要真正理解它,不僅要像馬克思那樣洞見到黑格爾的勞動理論,也要透徹理解其邏輯學和制度倫理理論。里德爾超出馬克思之處在于,一方面將黑格爾的勞動理論放到西方實踐哲學的大傳統的背景下,從而深刻地揭示出它對傳統實踐哲學的顛覆,同時深刻地揭示出它是馬克思勞動理論的直接前提和來源;另一方面,他對黑格爾法哲學的多維解釋也凸顯了馬克思將黑格爾法哲學僅僅視為其邏輯學的簡單運用之不足。邏輯學固然是理解黑格爾法哲學的前提,但制度、傳統與歷史等方面的理解也同樣不可或缺。[1]英美學界近些年涌現出來的布蘭頓、斯特恩、萊蒂尼等人對黑格爾法哲學的規范性解讀,著眼于黑格爾法哲學中的規范的社會性維度,以彌補康德的建構性規范理論之不足。他們或從概念出發(如布蘭頓),或從歷史出發(如斯特恩)提出不同的闡釋,但是都不能夠像里德爾那樣將黑格爾法哲學的各個方面的因素(經濟的、社會的、邏輯的、歷史的以及制度的因素)綜合起來進行考慮,從而難免導致邏輯學與法哲學、概念與歷史等方面的脫節。布蘭頓等人的觀點及其缺陷,參見馬晨:《概念、社會與規范性——黑格爾的規范性理論之爭》,《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 期,第36—42 頁。
總之,如果我們依照作者的成文次序閱讀此書,最終不免生發出“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到金”的感嘆。此書一方面對《法哲學原理》出版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從19世紀黑格爾身后第一代門人馮·施泰因、馬克思到作者寫作前的洛維特、里特爾等人當中的效果史盡收眼底;另一方面又遙接二千年以外,將黑格爾法哲學置于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傳統政治哲學和近代自然法理論的深遠背景之下,深刻地揭示出黑格爾法哲學“前接古人、后開來者”以及“融貫古今、超越古今”的恢弘氣度與廣闊胸襟。歷史如此吊詭,從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到馬克思以降的批判,再到里德爾從馬克思出發、經洛維特而最終回到《法哲學原理》,恰好走完整整一圈。在作者筆下,我們看到,黑格爾之后,各路英豪盡顯身手,對其法哲學提出種種批判和挑戰,然而黑格爾終究屹立不倒,雄視今古。尤需一提的是,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這是《法哲學原理》遭受的最嚴厲的攻擊之一):神秘的泛邏輯主義、法哲學不過邏輯學的簡單運用、黑格爾法哲學為現代國家觀念的反映與表達等等,作者都一一暗中回應。盡管馬克思構成了作者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出發點,但他卻超出馬克思的視域,小心翼翼地追隨黑格爾本人的腳步,回到其所面臨的古與今、自然與自由的對立,回到德國觀念論哲學,回到黑格爾邏輯學、歷史哲學與法哲學,深刻揭示出其法哲學對西方傳統政治哲學的完全顛覆以及對近代自然法的根本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