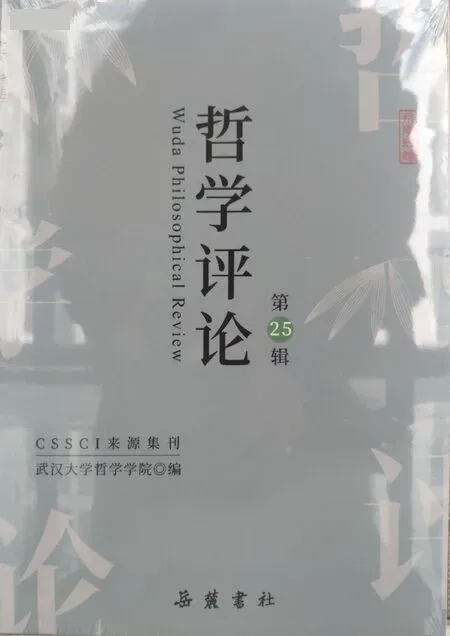納斯鮑姆對自然主義女性角色論的批評
左 稀
在《女性與人類發展》一書中,納斯鮑姆對有關女性角色(女性是愛與關懷的給予者)的自然主義觀點展開了批評,并嘗試論證所謂女性專屬情感和行為模式的社會建構性。她指出,無論自由主義的還是非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都存在將女性角色看作自然的存在,否認習俗、法律和制度在塑造這些情感及相關行為方面的作用。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是,1871年,布雷德利法官在支持伊利諾伊州一項禁止女性從事法務工作的法律時陳述了下述理由:“女人特有的那種自然的、適當的膽怯和嬌柔顯然使她們不適于從事許多與公民事務相關的職業。家庭組織結構建立在神圣法令和事物本性之上,它表明家庭是恰當歸屬于女人的領域和職能范圍……女人最重要的命運和使命就是履行賢妻良母這個高貴而良善的職責。這是造物主頒布的律法。公民社會的規則必須適應事物的一般結構。”[1]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53.納斯鮑姆認為,自然主義者若要避免在“關系R 自然存在”的幾種不同含義間來回推導,只能承諾某種目的論的理論框架。布雷德利法官關于女性家庭角色的這段論述之所以是融貫的,恰恰因其承諾了一種有關自然秩序的宗教目的論解釋。為了澄清這一點,我們不妨從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入手。
一、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
依據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自然”是自然物因其本性而非偶性運動和靜止的根源。自然物包括動物及其各個部分、植物以及一些簡單的物體(土、火、水、氣),人造物不是自然物,因為它產生的根源不在自身之內。自然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質料的自然,即每一個擁有自身運動變化根源的事物所具有的直接基礎質料。例如,如果種下一張床,腐爛的木頭若能長出幼芽,它一定會長成一棵樹而不是一張床,決定這種運動變化的原因在于床的質料——木頭。另一種是形式的自然,即事物的定義所規定的它的形式,形式是一個事物成熟的自然形態,對于事物本身而言,達到它的成熟形態被視作善的,在這個意義上,一個事物的自然形式也就是它整個生成過程的目的。兩相比較,把形式作為“自然”更為確當,形式自然才是自然的本真含義。(《物理學》192b8-193b10)[2]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苗力田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0 頁。自然哲學家主要研究第一個意義上的自然,他們常常通過質料或質料之間的關系來解釋事物的運動變化,但亞里士多德認為,訴諸質料的自然原則不足以解釋所有的運動變化。比如,當溫暖濕潤的東西(產生動物胎兒的東西)受到雄性精液中水狀的、可活動的東西的影響時,按照自然哲學家的自然原則,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兩種東西會產生一定的凝固效果,卻沒有充足理由認為,這種凝固必定會形成一個動物胎兒。要解釋這個轉化過程,必須訴諸自然生物通過繁殖保持自身存在的基本傾向,這種傾向無法被還原為質料的力量或特性,它只能是目的論的。
約翰·庫珀認為,“亞里士多德正是基于物種永存的原則,才最終確立起對自然目的的一般信念”[1]John M. Cooper, “Aristotle on natural teleology” , in Language and Logos: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presented to G.E.L.Owen, ed. Malcolm Schofield and Martha Craven Nussba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16.。物種永存的假設對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具有重要意義,它容納了對生物的全面功能主義分析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目的論論證,并允許關于物理環境、物種之間相互作用的各種目的論解釋,甚至容許這種主張:有益于某一物種存續的物種是為了這個物種而存在的。盡管亞里士多德對物種之間相互作用的單向分析在庫珀看來是值得懷疑的,“但倘若物種永存的一般原則為真,那么植物和動物為了彼此而生存的基本觀念就是合理的”。[2]John M. Cooper, “Aristotle on natural teleology”, pp. 219.然而,在《論動物部分》和《論動物構造》中,亞里士多德對動物的器官或其他部分所處位置給出一種頗為不同的目的論解釋,此種解釋并不訴諸物種永存原則,而是訴諸某種一般性的“高貴”原則,其所傳達的大致意思是,前面比后面好,上邊比下邊好,右側比左側好。(《論動物部分》658a15-658b15)[3]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苗力田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8 頁。亞里士多德把這種一般性的“高貴”原則視為另一個基本的自然原則,即自然界會服從優先滿足物種永存的原則,以便使自身趨向任何事物的前部、頂部和右側。庫珀以為,與訴諸物種永存原則的低層次自然目的論相比,訴諸高貴原則的自然目的論似乎是更高層次的。更重要的是,低層次自然目的論所蘊含的目的構成個體生命物自身的目的,因為任何一種生命物都有維持生存或實現良好功能發揮的目的,高層次自然目的論所蘊含的目的卻并不構成個體生命物自身的目的。[4]John M. Cooper, “Aristotle on natural teleology”, pp. 220.對于這兩個不同層級的自然目的論,我們無法提供統一的解釋。但是,兩種自然目的論是彼此分離的,對高層次自然目的論的質疑并不影響我們承認低層次自然目的論的合理性。
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思想貫穿于他對女性角色的論證中。首先,在低層次自然目的論體系中,由于人類這個物種同樣具有通過繁殖維持自身存在的基本傾向,生育便構成男女兩性的一個重要功能,擁有這種功能并實現它對兩性來說都是一種善。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可以說家庭是自然的,它意味著家庭的產生源于人類渴望維持自身物種永存的自然傾向。不過我們很快發現,在涉及女性問題時,亞里士多德除了采用這種低層次自然目的論解釋家庭的產生之外,幾乎不再運用過它,取而代之的是訴諸一般性“高貴”原則的高層次自然目的論。例如,在《政治學》第一卷他便指出,自然的特性表現為,一切聯合的事物和由不同部分構成的事物都存在統治元素和被統治元素的區分。很明顯,他有意重申其自然哲學中的基本觀點:自然界的運動變化不僅受到物種永存原則的驅使,同時(或許更重要的是)受到偏好更高貴元素的自然傾向的驅使。正如生長在動物身體頂部的器官優越于生長在其底部的器官一樣,人類作為由不同部分構成的生物,其各部分之間必然也存在高貴與低賤的區分。譬如,人有肉體和靈魂,靈魂因為擁有形式而高于肉體,并以專制的方式統治肉體;鑒于靈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而情欲往往與肉體相連,所以靈魂對肉體的統治便是理性對情欲的統治。
緊接著,亞里士多德說雄性更高貴,雌性較低賤,而相關論證卻呈現在《論動物生成》中:在物種繁殖的活動中,雄性貢獻的是擁有潛能的形式和運動的本原(精液),雌性貢獻的僅僅是被動接受形式的某種質料(構成月經的東西)。(《論動物生成》737a15-35)[1]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第265 頁。就任何一種生命體而言,賦予肉體以形式的靈魂都是生命的本原,因此靈魂對肉體的統治是天經地義的。就人類而言,這表明兩點:第一,男性天然地趨近心靈和理性,女性則出于本性地親近肉體和情欲;第二,男性更高貴并占據統治地位,女性更低賤,受男性統治。把這種生物學結論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心理學結論延伸至人類政治生活領域,亞里士多德很快證明了男性對女性統治的天然合理性。他說:“男人在本性上比女人更適合于發號施令,除非是偏離自然的偶發情況,這就像年長者和成年人要比年輕者和未成年人更優秀一樣……然而,一旦有人統治而另外的人被統治,人們便會竭力在形象、言語和名位上造出差別來,正如阿馬西斯就他的腳盆所說過的話,男女之間的關系永遠都是這種關系。”(《政治學》1259b1-10)[1]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顏一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6 頁。例如,嫻靜是女人的本分,不是男人的本分。發號施令是男人的勇敢,不是女人的勇敢,女人的勇敢表現為服從。像婦人那般勇敢的男人是懦夫,像男子那般自我約束的女人是多嘴多舌、不思節制之人。女人是操持家務的人,男人是享用家務勞動成果的人。公共事務是男人的職能領域,女人不宜涉足,否則就會像斯巴達那樣招致政權衰落。之所以呈現這些差異,主要還是因為男人和女人天生分有不同德性。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德性的養成除了習慣化也要遵循自然的邏輯,正如靈魂理性部分的德性和非理性部分的德性是不一樣的,男人和女人的德性也是不一樣的。男人的靈魂服從理性的指引,他需要也能擁有統治者所應有的完美的倫理德性——實踐智慧;女人的靈魂盡管有理性部分,但由于受肉體情欲束縛,終究缺乏權威,她不需要也不能擁有統治者所應有的完美德性,只要擁有適合她們自己的德性即可。
亞里士多德不僅僅認為政治生活中的這種安排是自然的,而且也認為它是有益的。類似自然哲學中兩種不同層級的自然目的論,政治學中也涉及兩種不同層級的目的論。在較低層次,政治共同體滿足人類想要生活得好的自然本能和沖動;[2]詳見劉瑋:《亞里士多德論人自然的政治性》,《哲學研究》2019年第5 期。在較高層次,政治共同體自然地趨向更高尚的理性。[3]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1333a21-1333b2:“較為低劣的事物總是以較為優越的事物為目的,這種情況無論是在技術造成的事物還是在自然造成的事物中都極為明顯;而優越在于具備理性。根據習慣的劃分理性又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實踐的理性,一是思辨的理性。如此一來,靈魂的部分顯然也必須作進一步的劃分。行為也就有了類同于此的區分,那些有能力實施靈魂的全部三部分或其中兩部分的相應操行的人必定更加愿意選取本性上更為優越的行為……一個政治家在擬定法律時應當注意到以上所有事項,并且要考慮到靈魂的部分以及相應這些部分的操行,尤其是那些更為優越的作為最終目的的事物。”〔譯文參考顏一編,《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不僅如此,這兩個層級的目的論同樣存在一種不對稱性。想要生活得好明顯構成每個政治共同體成員自身的目的,但趨向更高尚的理性卻很難被理解成每個共同體成員自身的目的。更要緊的是,就女性(和奴隸)而言,為何安于現狀、俯首聽命才構成趨向更高尚理性的正確方式呢?
為回應這種質疑,亞里士多德很可能回到他的生物學立場:女性天生無能、低賤,她們沒有能力改變現狀。況且,維持現狀對她們來說是有益的。在《尼各馬可倫理學》關于友愛的論述中,丈夫和妻子的友愛關系便被視為施惠者與受惠者之間的友愛關系,亞里士多德認為施惠者更愛受惠者的原因在于,他把受惠者看成自身活動的產品,產品往往體現實現活動過程中制作者的存在自身,所以施惠者會如同熱愛自身存在那樣去熱愛受惠者。亞里士多德的門徒曾經在《家政論》中說道,“妻子必須服從丈夫,并勤勉地服侍丈夫的原因是,‘他確實以極大的代價買下了她,在他的生活和孩子的生育上建立了伙伴關系;沒有什么比這更偉大或更神圣的了’”。[1]Susan Moller Okin,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Debra Satz,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88.一言以蔽之,男性賜予的恩惠是如此這般偉大和神圣,以至于妻子希望自己的愛獲得同等回報看起來都很可笑,因為兩種愛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不僅如此,通過對斯巴達政體的經驗研究,亞里士多德一早得出結論,放縱女性會導致政治災難,有害于政治共同體成員的幸福,因此確保她們接受男性的統治不僅對她們而且對全體共同體成員都是有益的。基于上述理由,亞里士多德證明了對于女性來說,扮演自身角色、順從男性統治、發揮專屬功能、實現適合于自身的德性不僅是自然的、必然的、永久的,而且是應當的。
二、納斯鮑姆:女性角色并非“自然的”
在反對自然主義女性角色論時,納斯鮑姆將批評的矛頭指向有關女性情感角色的自然主義解釋——女性天生就是愛與關懷的給予者。理解這一點并不難,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女性的家庭和社會定位確實建立在心理層面的兩性差異之上。對男人是理性的動物、女人是情感的動物的普遍認知,使得女性常常被認為只適于從事與情感關系密切的學問和行業。對母愛這種情感的關注致使人們認為,她們在家中給予愛與關懷是順應本性、理所應當的。除此以外,承認此種情感心理的兩性差異,也意味著支持相應的行為模式和品德規范。譬如,由于女人是情感的動物、天生富有母愛,因此她應當是溫順的、嫻靜的、慈愛的、大度的,她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撫養孩子、照料家庭方面,并且不求回報地關懷和支持她的丈夫。就這些方面來看,選擇從對女性情感角色的自然主義解釋入手顯然是選擇從問題根基處入手。
納斯鮑姆首先指出,在女性問題上,訴諸“自然”是一個極端狡猾的策略,因為“自然”一詞的含義非常模糊。當人們說某種行事方式R“自然地”存在時,可能涉及以下幾種含義[1]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pp. 254.:
生物學的:R 建立在一種先天的稟賦或傾向之上。
傳統的:R 是我們知曉的唯一方式;事情總是這個樣子。
必然的:R 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事情不可能是其他樣子。
規范的:R 是正確且恰當的,事情應當是這個樣子。
對密爾《自然》一文以及《婦女的屈從地位》的考察,使我們獲知在政治論證的過程中,人們常常不加論證地從其中一種含義滑向另一種含義。譬如,因為R 是一種先天稟賦,所以情況必然是這個樣子,也應當是這個樣子;因為在某個社會中,R 歷來如此,所以R 具有某種生物學基礎,或者R 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又或者是正確且恰當的方式。納斯鮑姆贊同密爾的意見,認為這類推論沒有一個是合理的。首先,某件事是傳統的,并不意味著它建立在某種先天稟賦之上,某事具有一種先天的基礎也并不總是意味著它會成為一種慣例。嬰兒出生時總會攜帶許多自然傾向,但其中一部分會在其成長過程中改變或消失。其次,認為某事源于先天稟賦或者某種傳統,也不意味著它必然如此且不可更改。譬如,沒有人認為一個先天近視的孩子應該滿足現狀,我們總會想盡一切辦法來為他/她提供良好的視力(接受手術、佩戴眼鏡等等)。最后,從前述三種含義中的任何一種含義出發,都無法合理地推導出規范性含義。對于一些有缺陷的或不好的先天傾向,我們會試圖加以糾正。對于無法促進福祉或實現正義的傳統,我們可能采取同樣的態度。對于必然性,我們并不總是通過使它成為一種規范來視之為善,人類肉體的脆弱性和有朽性是必然的,但這種必然性本身并不是一種善。反過來,說某事是正確且恰當的,也不能說明它是先天的、傳統的或必然的。[1]Martha C. Nussbaum, Sex and Soci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55.由此可見,從女性具有愛與關懷的自然傾向直接推導出女性必然且應當扮演愛與關懷的給予者角色,是何其任意、武斷甚至居心叵測的一個推論。
濫用自然主義論證常常是根基不穩的,那么如何看待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呢?納斯鮑姆明確表示過,只有“在一種宗教性或其他規范性意義上理解生物學傾向,把它看作事情應有的樣子,我們才能從第一點穩步推進到第四點。但那種對自然的理解在主要宗教中極富爭議,必定不能充當政治的重疊共識的基礎”。[2]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pp. 254.在低層次自然目的論中,由于亞里士多德關注的是形式的自然(形式因與目的因合一),因而在自然哲學領域,他得以從“物種永存的自然傾向”中推出“維持物種永恒存在是正確而恰當的”,在倫理政治領域,他得以從“人類追尋美好生活的自然傾向”中推出“追尋美好生活是正確而恰當的”。然而,高層次自然目的論中的情形不太一樣。由于亞里士多德對自然原則的假設內在隱含某種等級制劃分,因此,這個假設是站不住腳的,它所推導出來的結論不可能在低層次自然目的論的意義上被看作是每個成員自身的善。納斯鮑姆自然不會贊同高層次自然目的論及其蘊含的等級制度。對于低層次自然目的論,考慮到她所支持的羅爾斯式政治自由主義理念,以及一些宗教徒(他們構成達成政治重疊共識的多方主體)對此種自然觀念的拒斥,她不得不棄之不用。納斯鮑姆對自然主義目的論的全面拒斥,致使其能力進路的政治理論帶有濃厚的直覺主義色彩,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學說是“瘦身”之后的格勞秀斯自然法理論、亞里士多德關于人類尊嚴的功能主義解釋以及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理念的結合體。
總而言之,以某種關系或某種行事方式的“自然性”為出發點展開倫理和政治論證是值得懷疑的。一方面,這種論證極可能具有武斷性,無法應對各種反例的挑戰;另一方面,即便這種論證是精致的(如亞里士多德低層次自然目的論),在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它也無法滿足政治自由主義的基本要求。然而,關于女性情感角色的自然主義解釋不單單呈現出論證薄弱或缺乏辯護的問題,更重要的在于,這種所謂自然的情感以及行為模式完全是人為創造的東西。納斯鮑姆當然不否認女性在撫養孩子和照料家庭方面的情感和行為傾向可能有其生物學基礎,但有關人類這個物種的研究終究太少,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很難獲得十分可信的答案。即便兩性之間存在生物學差異,也只是傾向上的差異,這并未給我們提供充分理由去推廣或壓制它。關于女性情感角色的社會建構性,納斯鮑姆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論證。
第一,訴諸情感概念。認為情感是“自然的”“與生俱來的”“肉體性的”觀點常常與非認知性的情感觀聯系在一起。事實上,情感包含有關情感對象的評價性信念,這類信念構成情感的意向性成分。情感涉及那些被我們珍視的、不完全在我們控制范圍之內的人或物,它是對此類需求和依賴的承認。對情感概念的澄清使我們發現,情感之所以與女性而非男性關聯起來,一方面是因為,女性從小接受的教育使她們相信,對他人產生強烈依附感是正確的,她們自身的善應當呈現為某種極具關系性的善;另一方面是因為,男性和女性在社會自主和社會控制方面存在非常大的能力差異,女性對自身環境缺乏控制的強烈無力感往往造就了她們豐富的情緒感受。[1]Martha C. Nussbaum, “Emotions and Women’s Capabilities”, in Wome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 Study of Human Capabilities, ed. Martha C. Nussbaum and Jonathan Glov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90.
愛與關懷的情感都包含大量信念。譬如,關于哪些人或事物具有重要性和價值的信念,關于什么是正確的和恰當的信念,以及其他一些關聯信念。其中許多信念都具有規范性,它們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后天習得的。即便這些信念可能建立在某種先天稟賦上,后天訓練也激活了此種稟賦,給社會解釋和文化多樣性創造了很大的運作空間。關于母愛,納斯鮑姆則認為,人的部分情感形成于嬰幼兒階段,此階段涉及大量復雜的社會互動和情感體驗,但由于這些互動和體驗出現的時間過早,且常常達到意識分析難以企及的心理層次,因此這個階段形成的情感模式構成人格結構的一部分。對于這些情感,我們雖無法簡單通過指向在兒童可識別的社會化過程中獲得的行為模式來進行解釋,卻也絕不意味著它們是某種與生俱來的“天性”。母愛正是以這種方式代代相傳的。在育兒過程中,父母與女嬰的互動會重現母性人格,使女嬰認為成熟意味著某種親密的養育關系;相反,父母與男嬰的互動傾向于使男嬰認為,成熟和獨立是通過否定需求和依賴來實現的。[1]Martha C. Nussbaum, “Emotions and Women’s Capabilities”, pp. 393.
第二,訴諸文化影響的廣泛存在。這個論證較為簡潔。納斯鮑姆大致認為,環境對人格發展的影響充斥于各個領域,在性別差異領域,我們擁有大量關于早期文化影響的證據。當然,在有關愛與關懷的問題上,我們可能無法運用早期文化影響的證據來徹底排除生物學差異的影響,但考慮到母愛情感形成的方式,那些容易被我們視為與生俱來的“天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早期的和隱性的文化影響,我們其實并不十分清楚。
第三,訴諸文化差異。自然主義者認為,女性天生就是情感的動物,她們是愛與關懷的給予者。說這種現象是“自然的”,意思是它的產生和形成具有某種穩固的、普遍的生理原因,不會受到社會文化及其特殊性的影響。然而,經驗研究表明,女性在給予愛與關懷的過程中呈現出文化差異(即便在一個國家之內)已是不爭的事實。首先,由于受到階級和地域文化的影響,人們在表達這類情感時所遵循的規則常常是不一樣的。其次,關于什么是愛的典范,什么是良好的親子關系,西方女性和印度女性會呈現出規范性判斷方面的差異。最后,人們關于愛與關懷的恰當對象的看法也經常受到不同文化和環境的影響。
第四,訴諸家庭的社會建構性。有些人從家庭組織具有某種固定的習俗性質得出家庭是一種自然存在的結論,納斯鮑姆認為這種觀點完全不合情理。美國家庭由于不同的種族來源和地域來源,常常呈現出巨大的結構多樣性,印度的家庭女性在不同習俗和法律的影響下產生截然不同的家庭觀念,并且不論是相關習俗還是法律都在持續地變化中。家庭實際上是國家行為的產物,無論其結構形成還是成員權利都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塑造。“結婚從一開始就是一項公開的、受國家管制的儀式。有一些國家法律對它下定義,這些法律對進入那個特權領域作了限制。國家不只是對結婚進行外部監管,它還宣布人們結婚。其他不符合國家要求的非常相似的人不能算作已婚,即使他們符合一切私人的甚至是宗教的婚姻標準。”[1]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pp. 263.相較于宗教組織和教育機構,家庭以更為深入的方式受到國家法律的影響。倘若“家庭”即便在統一的意義上也非“自然的”,那么任何獨特的家庭形式便都非必要且必然的。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認為,家庭作為愛與關懷的私人領域,天然地屬于女人的職能領域和勢力范圍。
三、掙脫思想漩渦:性別本質論與反本質論
試圖把女性看作一個“種類”統一起來的女性主義者常常面臨“女性共同屬性”是什么的問題。一部分女性主義者會走向亞里士多德式“生理決定論”,即相信某種心理屬性(如關懷)之所以構成女性共同的特點或本質,是因為它建立在自然的生理差異之上。人們常常把這種觀點稱之為“性別本質論”。性別本質論者一般都是生理決定論者,她們主張男女兩性存在本質性差異,這種差異是自然的而非建構的。然而,性別本質論面臨廣泛的批評。其一,這種理論承認了父權制文化中的二元對立。其二,作為本質的屬性因獨立于人類歷史和文化的影響而常常容納不了現實的變化。其三,作為本質的屬性很難囊括一切情形而具備普遍性。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受到后現代理論家的影響,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若要徹底推翻父權制文化,首先就得消除性別本質論的二元劃分。女性群體中呈現的多樣性足以表明,普遍的女性本質是不存在的,一切生理差異和心理差異都具有社會建構性。可是,這些性別反本質論者同樣遭遇棘手的問題——代表問題(representation question)。女性主義不是也不應當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它擁有獨特的政治訴求,如果不存在某種普遍的女性本質,那么,在什么意義上我們仍可以將理論標榜為“女性”主義的呢?更重要的是,在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我們又該團結誰,孤立誰,和誰保持一致,共同來反抗誰呢?
為了解決生理本質主義遭遇的“共性問題”(commonality question)以及反本質主義遭遇的“代表問題”,一些女性主義者主張,女人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存在的,但使她們統一起來的根源是社會性的而非生理性的。例如,南希·喬多羅(Nancy Chodorow)將男女兩性的差異理解為男性重視分離性的自我意識和女性重視關系性的自我意識的差異;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A.Mackinnon)則把女性的統一性理解為性屈從的經驗,這種經驗并不基于某種生理事實,而是通過偶然的社會制度來表達,如色情文學。然而,這些社會本質主義者顯然與生理本質主義者一樣面臨“共性問題”。為了解決上述難題,薩利·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的“社會客觀主義”理論應運而生:第一,根據抽象的關系屬性來定義女性,使女性定義能夠靈活容納多樣性;第二,把“客觀性”作為一個薄的形而上概念來加以使用,表明女性仍然構成一個客觀種類,從而解決代表不足的問題。有人質疑說,這種非本質主義的性別概念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呈現某種實在的結構,以區別于單純建構性的性別分類呢?哈斯蘭格回應道,我們不需要把種類的客觀性想象得過于神秘,就像我們可以通過辦公桌上的各個物件都“在辦公桌上”這個共同特性,把它們看作是客觀的一類事物,我們也可以在類似意義上理解女性類別的客觀性。[1]Theodore Bach, “Gender Is a Natural Kind with a Historical Essence”, Ethics 122 (January 2012) : 231-272, pp. 238.批評者或許會說,把書桌上的物件看作統一的一類事物,本就是觀察者有意屏蔽視野中任何其他物件以及相對位置的一個結果,在什么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這種統一性具有與人類意識建構無關的客觀性呢?哈斯蘭格傾向于告訴我們,在建構世界的過程中,我們會把某些特性看得比另外一些特性更重要,但這些特性是什么仍然不由我們決定。當我試圖收拾辦公室準備離開時,在我桌上擺放著的這些東西就會具有某種特別的重要性而使我忽略其他、將它們看作一個集合,但是這些東西“在辦公桌上”這一共同特性并不是由我主觀構建的,在這個意義上,它具有一種客觀性。[1]薩利·哈斯蘭格:《形而上學中的女性主義——對本性的討論》,收錄于米蘭達·弗里克、詹尼弗·霍恩斯比編,肖巍、宋建麗、馬曉燕譯,《女性主義哲學指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 頁。類似地,某些人被認為是女性,常常源于政治和法律上的重要性。出于斗爭需要,我們會把在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等方面處于從屬地位的人們稱之為女性,盡管她們各有不同,我們也難以找到某種共同的“本質”來描述她們,但她們仍會呈現出某些非建構的客觀特征,例如,體現她們在生殖中的生物學角色的那些被觀察到或被想象到的身體特征。哈斯蘭格相信,“性別可以被富有成效地理解為一個更高階的種類,它不僅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等級制社會地位,而且還潛在地包括其他非等級的社會地位,這些地位一定程度上是由生殖功能來定義的”[2]Sally Haslanger, “Gender and Race: (What) Are They? (What) Do We Want Them to Be?”, No?s, Vol. 34, No. 1 (Mar., 2000) : 31-55, pp. 43.。
當這些女性主義者都忙于捍衛、批判或重構一個既定社會中兩種實際的規范時,納斯鮑姆把注意力投向了其他地方。她認為,這些理論家都忽視了男女兩性同為人類這一事實。在女性問題上,如果我們需要某種規范,那將是超出兩種實際規范(分別適用于男女兩性)的某種單一規范——人性規范。這種規范之所以單一,是因為它“雌雄同體”或“不分男女”,但它并不是具體的一套有關男女兩性如何生活的理想規范。為了顧及女性視角中那些可能具有獨特性和有價值的東西,它“作為對所建議的生活方式和倫理原則的一種限制,以一種不很具體的、否定性的方式起作用”[3]朱麗亞·安娜斯:《婦女與生活質量:兩種規范還是一種?》,收錄于阿瑪蒂亞·森、瑪莎·納斯鮑姆主編,龔群、聶敏里、王文東、肖美、唐震煊譯,《生活質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 頁。安娜斯在文中表示,她的許多思想受益于納斯鮑姆。。這就是納斯鮑姆開列出來的核心人類能力清單。這份清單是“厚實的”,同時是“不明確的”,它雖不試圖告訴女性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完全正義的生活,但確實告訴她們什么樣的生活是絕對不正義的、不值得過且不應當過的生活。它充分尊重女性的多樣性,在接受實踐理性和依附能力所施加的基本限制之下,允許根據不同的地方性觀念或個人化觀念對清單中的某些條目做出具體規定和說明。
在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爭論中,納斯鮑姆基于核心人類能力的人性說明承諾了某種內在主義的本質主義立場。納斯鮑姆認為,采取反本質主義的立場是行不通的,因為對本質主義的徹底拒斥會走向主觀主義。采取形而上的、實在論的本質主義同樣行不通,由于這種本質主義認為世界的真實面目必定以某種確定的方式有別于生物的認知功能所給出的解釋,存在著一些先在的、獨立的形而上實體來決定世界的本質,它引發了最廣泛的懷疑論:一個獨立的形而上實體的存在是值得懷疑的,即使假定它存在,我們也無法認識它。就人類的本質而言,我們無法從人類在歷史中的自我解釋和自我評價之外獲得有關人性的說明,即使有某個獨立的存在者給出這樣一種說明,它也無法把捉到真實的人類生活特征。受亞里士多德本質主義和“現象”方法的影響,納斯鮑姆主張通過有關人類歷史和經驗的內在考察來解釋人性,這要求我們對人類自身展開倫理探詢,詢問哪些是人的本質屬性,哪些是人的偶然屬性,只要一個人尚且具備被界定出來的本質屬性(如推理能力、回應他者的能力或選擇、行動的能力等等),我們就可認為他仍在過著一種屬人的生活。
反對者會說,一旦給出確定的有關人性的觀念,并賦予這種觀念以道德的和政治的規范性力量,在適用觀念時,我們首先就得詢問哪些存在者能被恰當地歸于“人類”這一概念之下。如此一來,別有用心之人便可據此將少數人群和弱勢群體排除在這個概念之外。例如,亞里士多德便從強調理性的人性觀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婦女、野蠻人和奴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對此,納斯鮑姆做出如下回應:能力清單是一個更高層次的人類能力(綜合能力)清單,它構成對最低限度的美好人類生活的說明,即便某些人未能滿足這個規范,我們也不能據此否認他們的“人類”身份。應當說,“兩個人類父母的每一個后代都擁有一些基本能力,除非并直到長期的經驗使我們確信,這個人遭受到如此巨大的傷害,以至于無論如何巨大的資源支出都不可能使他達到更高的能力水平”[1]Martha C. Nussbaum, “Human Functioning and Social Justice: In Defense of Aristotelian Essentialism”, 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2 (May. 1992) : 202-246, pp. 228.。至于亞里士多德為何沒能免于此種批評,那是因為他沒有一如既往地貫徹他的內在主義的“現象”方法,只要他深入考察人類的日常信念,就會發現婦女、野蠻人和奴隸都無法被排除在“人類”概念之外。受歷史與文化局限的亞里士多德始終相信,家庭和親人是人類美德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婦女對于維護家庭結構來說極為關鍵,他無法想象一種既能維護家庭的重要性,又能使婦女得到同等的教育和從事卓越活動的機會的生活結構,故而為婦女的家庭角色尋來了一種形而上的、實在論的本質主義解釋。
作為最低限度的本質主義的人性說明將在何種意義上解決女性主義者面臨的問題呢?對于“共性問題”,雌雄同體的單一人性規范展現出巨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容納各種群體,同時也與任意兩種有關人的實際規范(如男性規范和女性規范)相容;對于“代表問題”,它主張無論女性還是男性少數群體都以人類名義爭取正常功能發揮所需核心能力,反抗一切反人類的壓迫者和剝削者。由此可知,納斯鮑姆雖批評自然主義女性角色論,但并不反對女性主動選擇愛與關懷的給予者角色。不過,女性的選擇空間始終是由關于人性的最低限度規范——核心人類能力清單所提供的。納斯鮑姆明顯認為,深陷性別本質論和反本質論爭議的女性主義者都忽視了根本問題,性別差異(以及性向差異)本身并不值得憂心,值得憂心的是將差異關聯于一種等級制度,只要我們確保底線意義的平等,讓所有人都享有基本的人格尊嚴,那么各類差異均可相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