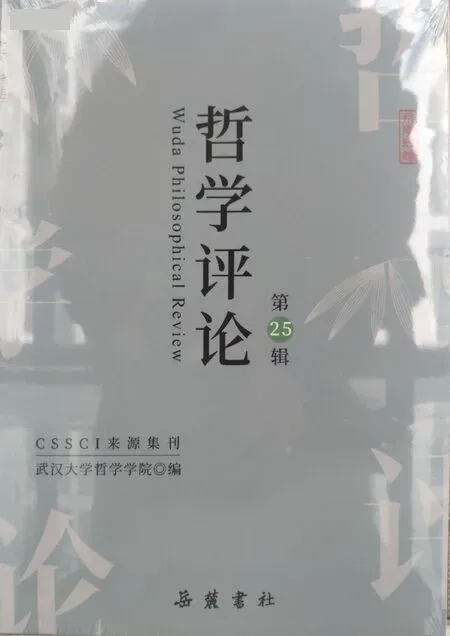黑格爾“力”范疇的牛頓力學關涉
李逸超
黑格爾在“力與知性”一章,明確提及牛頓的“萬有引力”。[1]G. W. F.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21.盡管他在贊賞開普勒天體力學的同時,對以純粹數學為方法的牛頓力學提出嚴厲的批評;[2]Vgl. G. W. F. Hegel, Enzyklop?die II,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96.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對牛頓的力學成就有著清楚的認知:“牛頓[……]卓越地對此作出了貢獻,即將對力的諸多反思規定(Reflexionsbestimmungen)引入物理學之中;他將科學提高到了反思的立場,取代現象的規律他確立了諸多力的規律。”[3]G. W. F. Hegel, Vorlesung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I, Frankfurt am Main,1971. S. 231.可見在黑格爾看來,牛頓的貢獻主要在于將“反思”這一思維形式引入科學并在此基礎上建構其物理學。反思是牛頓力學基底的思維架構,構成牛頓力學的諸多力的形式規律建基于此。反思之思維特性及其在牛頓力學中的特征表現,因而便是一個重要問題。
黑格爾在“力與知性”中,確實將“力”概念與“知性”概念加以綜合討論。但僅囿于“知性”概念與康德先驗哲學之“知性立場”的“字面相關性”,便像埃蒙茨(D.Emundts)和沃克斯(E.Watkins)那樣將“力與知性”中的主要相關內容視為黑格爾對康德哲學的批判,[1]Vgl. Dina Emundts, Erfahren und Erkennen, Frankfurt am Main, 2012. S. 430.; Eric.Watkins, Hegel’s Critique of Kant in “Kraft und Verstand”, Hegel-Jahrbuch, 2016. S. 366-370.卻不免失諸正鵠。因為其一,據黑格爾的觀點,物理學之內核也同樣是一種知性形而上學,[2]Vgl. G. W. F. Hegel, Enzyklop?die II,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20.牛頓也與康德一樣是“從他的諸多經驗中導出他的知性命題”。[3]G. W. F. Hegel, Vorlesung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I, Frankfurt am Main,1971. S. 223.其二,雖然知性對力的最初經驗映射著康德對物質的形而上學建構,[4]詳參李逸超《黑格爾靜態“超感官世界”的邏輯生成》,《哲學研究》2020年第3期,第109—110 頁。但總體而言,黑格爾對康德“規律”概念的批判,其實側重于對作為真理之標準的“規律”的批判。康德的規律是普遍意義上的“規律”,而不是“力與知性”一章如此具體的“力的規律”。此外,盡管不能說黑格爾的力概念全然與赫爾德的力概念無關,[5]Vgl. Miriam Bienenstock, Zu Hegels erstem Begriff des Geistes (1803/04). Herdersche Einflüsse oder Aristotelische Erbe, Hegel-Studien, Bd. 24, 1989. S. 27-54.; M. Forster,Ursprung und Wesen des Hegelschen Geistesbegriffs, Hegel-Jahrbuch, 2011(1) . S. 213-229.但是,赫爾德的力、原力(Urkraft)等概念中更多地內含著宗教神學、經驗心理學等維度,它因而基本上無涉于黑格爾在物理學層面上所討論的、與物質及其運動現象以及物理規律相關的“力”。
如前所述,牛頓對于力的理解,在黑格爾看來基于“反思”這一知性思維形式。牛頓是從物質的運動現象出發,在知性思維這一“鏡像中介”中去“映射”(反思:reflectere)那隱匿于物質之紛繁運動現象背后的“力本身”:“因為哲學的整個困難看起來在于:從運動的現象我們研究自然界的力,然后從這些力我們證明其他的現象。”[6]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趙振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7 頁。以下簡稱《原理》。由此可見:第一,牛頓將自然哲學的任務規定為研究那內嵌于自然現象之中的、作為其本質的“力”,并“反過來”(re-)用“力”的規律來統攝和“反映”(re-flectere)現象世界。第二,在知性意識的上述目的設定中,“反思”實際上就發生于“現象”和“力”這兩個極端之間。
知性意識的“反思”與真正哲學的思辨(Spekulation),在黑格爾體系中具有根本區別——反思不能直觀內嵌事物之中的、創生著(erschaffend)的“生命力”(Lebendigkeit)。因而,純然通過“反思”來認識“力”這一客觀實在,便無法徹底通達它的真正“概念”。恰由此,黑格爾才對牛頓力學及其方法論加以批評:“ [牛頓][……]在概念上是徹頭徹尾的野蠻人”[1]G. W. F. Hegel, Vorlesung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I, Frankfurt am Main,1971. S. 232.,“ [……]牛頓像把持感性物那樣把持概念[……]”[2]Ebd. S. 231.。與科學界的主流觀點相反,相較于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黑格爾更推崇開普勒的行星運動定律——尤其是第三定律。[3]G. W. F. Hegel, Enzyklop?die II,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96ff.因為在他看來,自然規律之“時空冪次”規定表達著“規律”之向“概念”自身的回歸[4]Ebd. S. 78.。第三定律之時間性(周期T)和空間性(面積a)的“冪次”規定,因而完滿表達了天體力學中的“時空概念”規定。可見,“反思”與“概念”在黑格爾哲學中具有不同等級的真理內涵。因而為了映襯“反思”的規定性限制,我們需要理會黑格爾的“概念”。而為了把握“概念”,我們則需要在黑格爾“力”范疇的牛頓力學關涉中回答如下重要問題:一、牛頓的“反思”究竟具有何種具體形態?二、“反思”與“思辨”何以具有這一本質差異?三、力的“概念”在思辨中具有何種真理性的規定?
一、牛頓對“力”范疇的定義以及其中的“反思”
黑格爾在《哲學全書》“導言”的第5、7、9 節和第10 節談到了“Nachdenken”這一認識形式,并實質上將它與Reflexion 區別開來。雖然二者往往都被譯作“反思”,但它們卻具有本質上不同的意義。“Reflexion”是一種中介返還[1]Reflexion 的動詞不定式是reflektieren。其前綴“re”源于拉丁語前綴“re”,意為“返回”(zurück)、“再”(wieder)。詞干“flektieren”源自拉丁語“flectere”,意為“使彎曲、使扭曲”(biegen,beugen)。綜上可知,“反思”的本源意義為“使再彎曲”,引申為一種“中介返還”。,現象世界中光的“反射”實即一種“中介返還”現象。與此相似,哲學“反思”是通過思維“媒介”去“反映”自在對象的真理。“Reflexion”具有間接性的特性,它可以基于“遠距”的“中介”、經過不乏“顛倒”和“彎曲”的“鏡像反映”來認知對象。與此相反,因為“Nachdenken”的“nach”之最原初的意義是“接近”(nahebei, in der N?he von etwas)某物,所以它是通過“逼近”對象來認知對象。在《哲學全書》“第二版前言”中,黑格爾在對“Reflexion”和“Nachdenken”[2]鄧曉芒也對“Reflexion”和“Nachdenken”的詞源學意義加以分析,并且指出“Reflexion”的“鏡像反映”意義。在對“Nachdenken”的探討中,他批判了將“Nachdenken”譯為“后思”的觀點,指出“nach”的意義為“追溯”。詳參鄧曉芒《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345—347 頁。因為“nachdenken”原意為“追尋”“切近”某物的“思”,所以似可譯為“尋思”。如果說“追思”在漢語語境中因有另外的意義而不適合用以翻譯“Nachdenken”的話,那么譯作“尋思”不失為一種嘗試。因為這既保留了德文詞源構詞的原意,又同時符合漢語和德語的一般日常用法。的區分中,明確指出了前者之缺陷:“物理的或者精神的、尤其還有宗教的生命性的實在(Faktum),為那種沒有能力去把握它的反思(Reflexion)所扭曲(verunstalten)。”[3]G. W. F. Hegel, Enzyklop?die I,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7.這里的“扭曲”,事實上是內含于“反思”(reflectere)中的“彎曲、扭曲”(biegen, beugen)維度的必然顯現。反思尚且不是思辨思維,不是切近事物本質、通達事物內在核心的理智直觀,它尚且停留于外在性、間接相對性的“鏡像反映”階段,因而不能把握事物的真正“實在”。
牛頓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對“力”加以定義。在規定了“質量”和“動量”之后,他便緊接著定義了力的三種形式——“物質的固有的力”(推動力和阻力)、“外加的力”和“向心力”(并且將“重力”和“磁力”歸結為“向心力”):
“物質的固有的力(vis insita)是一種抵抗的能力,由它每個物體盡可能地保持它自身的或者靜止的或者一直向前均勻地運動的狀態。”
“外加的力是施加于一個物體上的作用,以改變它的靜止或者一直向前均勻地運動的狀態。”
“向心力是[一種作用],由它物體被拖向、推向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趨向作為中心的某個點。”[1]《原理》,第2—3 頁。
由上可知,“力”被牛頓理解為一種“能力”(power)和“作用”(action)。在他看來,“作用”無非是“能力”的“轉化”或“表現”。因為其一,牛頓將物質固有的力理解為慣性力,它只在外力施加于蘊涵著它的那個物體時才發揮出來;[2]“但是一個物體僅在它自身的狀態被一個施加于它的力改變時才使用這個力。”《原理》,第2 頁。其二,外加的力只存在于作用中,而不保留于物體中。[3]“這個力只存在于作用之中,作用之后并不留存在物體中。”《原理》,第3 頁。牛頓對“外加的力”和“物質的固有的力”的“對立性定義”,與黑格爾所謂的“誘導的力”(sollizitierende Kraft)和“被誘導的力”(sollizitierte Kraft)緊密相關。在黑格爾看來,首先二者具有“內容上的區別”:“被誘導的力”是“反思到自身中的力”(insichreflektierte Kraft),“誘導的力”是“物質的媒介”(Medium der Materien)。其次,“誘導的力”和“被誘導的力”也具有“形式上的區別”:“前者是能動的,后者是被動的。”[4]G. W. F.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14.在二者的聯動關系中,“誘導的力”是一個通過另外的物質媒介外在施加的力。經由這個外力的“作用”,“被誘導的力”作為隱藏在物質之內的“能力”而被“表現”(?u?erung)出來。與此相應,牛頓定義的“慣性力”也通過外加力才以“阻力”和“推動力”的形式表現出來。另外,一個物體的慣性力可以通過外加力的形式,能動地作用于另一個物體的慣性力。并且根據牛頓運動第三定律F=-F’[5]兩個物體之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同一直線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黑格爾也指出:“特定的運動和特定的抗阻是同一者。”G. W. F. Hegel, Enzyklop?die II,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68.,對于一個非封閉系統而言,外加的力表現為物體運動狀態的“變化”(加速度):F=m·a。可見,黑格爾對“誘導的力”和“被誘導的力”的區分與牛頓“外加的力”和“物質的固有的力”具有內容和形式上的對應關系。
但是,不同于牛頓對“反思”思維的“日用而不知”,黑格爾在其中敏銳指出了“反思”這一思維形式:那“被誘導的”、物質的“固有力”,其實是“反思進自身的力”。與此相似,牛頓力學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其實也是對運動現象加以反思的結果。反作用力作為抗力,其根源還是內在的“物質的固有的力”這一物質之能動的“自為存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事實上只是同一個理念性的力被強行分解到反思表象之兩端。[1]Ebd. S. 67f.反作用著的抗力,因而實即在運動現象中被反思到的力本身——“被逼回自身的力”(zurückgedr?ngte Kraft)[2]雖如此,但直接將“反作用力”絕對等同于“被逼回自身的力”,依然不免偏頗。因為在黑格爾語境中,“力和力的表現”具有對立關系。“被逼回自身的力”,實際上是力從它的外在表現“?u?erungen”返回到它自身。因此,黑格爾將“被逼回自身的力”稱作“根本力”(die eigentliche Kraft)。Vgl. G. W. F.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10. 但因為在牛頓的定義中,“物質的固有的力”“慣性力”和“反作用力”都可被視作與“外加的力”“向心力”(運動、力的表現)相對立的力,也即它們都趨向內嵌于物質中的“力本身”這一自為存在。所以,它們作為“根本力”便與“被逼回自身的力”本質上相一致。。但在牛頓力學的“反思”框架下,因為其一,運動作為力的表現,來源于外物(外加力)的推動,其二,運動的變化作為力在時間中的變化(加速度),表現為物體動量[3]《原理》,第1 頁。之抵消作用——Ft=mv’ -mv=p’ -p: 力在時間中的變化等于動量變化(沖量)[4]物體所受合力的沖量,等于物體的動量變化。(根據相對論,在低于光速的狀態下)物體的速度變化不引起質量的變化,所以動量的變化是基于加速度的變化。因為其一,加速度是物體運動狀態(速度)的變化,其二,根據牛頓對力的定義(外加力),力就是其所引起的物體狀態的變化。所以,力作為動量變化,即是運動在時間中的變化。;所以一方面,一個力來自于一個另外的力,并且它可以無限向外推求以至于上帝的第一推動,另一方面,力表現在運動物體之間相互對立作用的“反思結構”之中——誘導的力和被誘導的力、表現出來的力和被逼回自身的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等等。在對立相關項之反思結構中,內嵌于牛頓力學中的反思之“外在性”和“相對性”規定,得以顯現出來。一方面,在“外在性”之極端化中,他最終要假定力之“至外無外”的絕對來源——上帝。另一方面,在真正有效準的反思關系中,他事實上僅僅停留于力的相對性來源——物體相互的對立作用所引起的運動現象。
上帝的第一推動,只是可有可無的假說。因為它事實上來自一種無窮推論,所以它理應沒有終點,但牛頓卻強行為它設定了一個終點。內在的慣性力(物質固有的力、被誘導的力、被逼回自身的力),通過外加力(誘導的力)才進入其表現環節。為“力和力的表現的關系”這一邏輯范疇所規定的力本身,因而同時具有“內在”和“外在”這一對立性的反思關系。力本身一旦“外化”出來,就同時“消逝”(Verschwindung)并被逼回“內在”自身:“ [……]力只存在于作用之中,作用之后并不留存在物體中。”[1]《原理》,第3 頁。。“消逝”并非從有到無,而是從“顯發”轉化為“隱藏”。因為,力本身不是虛無,而是知性在運動現象中經由其抽象和反思作用而把握到的超感官實存——隱匿于現象背后的本質。力的消逝,因此僅僅是消逝到反思中去。由此,它證明自身不屬于感官世界。“感官世界”和“超感官世界”的對立,在力的消逝中便被呈現出來。“超感官世界”作為“世界”,是以超感官的方式——知性的抽象反思方式——加以把握的“感官世界”。力不具有在感官世界的物理實存,它在此僅只呈現于反思中:“[……]實際上力本身是此反思進自身的存在(Insichreflektiertsein),或表現之揚棄了的存在(Aufgehobensein der ?u?erung)。”[2]G. W. F.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10.綜上可知,整個牛頓力學是通過對感官世界的“反思”而被建構在一個超感官世界中,并借由“知性”的鏡像中介(例如萬有引力定律)來“反映”現象世界的“本質”。
二、“萬有引力定律”以及黑格爾對知性意識“反思”的批判
對于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黑格爾批判道:“知性必須更進一步將諸多規律總括到一個規律中,正如落體規律和天體運動的規律已經被把握為一個規律那樣。然而因為這種融合(Ineinanderfallen)諸規律卻失掉了其規定性;規律變得更加浮泛,并且因此被發現的實際上不是諸規定下來的規律的統一,而是一個取消著諸多規定下來的規律的規定性的規律;正如一個將地球上和太空中運動的兩個落體規律統一到自身中的規律實際上并沒有在自身中將二者表達出來那樣。”[1]Ebd. S. 121.黑格爾實際上借此影射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對伽利略的落體定律和開普勒的行星運動定律的統一。但他同時指出:在此統一中,落體定律和行星運動定律的“具體規定”,卻都被“取消”并“轉化”為不同的規定。黑格爾的這一慎思明辨確屬精當確切,因為在萬有引力定律false 的諸多區別(G、M1、M2、R2等)作為規律的規定要素中,我們確實既看不到伽利略false,也看不到開普勒中的諸多源初規定。因而,就各個規律之區別要素的直接定在而言,萬有引力定律與其說是對落體定律和行星運動定律的“統一”,不如說是對它們的“取代”。
黑格爾進一步指出:“一切規律之統一于萬有引力之中,唯除表達了在諸規律中被設定為存在著的規律的單純概念本身之外,并未有進一步的內容。”[2]G. W. F.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21.對于規律的單純概念及其在此的空虛性,他接著闡述道:“ [……]萬有引力抑或規律之單純概念便與規定下來的諸規律相對立。就此純粹概念作為本質或作為真正的內在者而被考察而言,規定下來的規律的規定性本身尚且歸屬于現象甚至感性的存在。然而規律的純粹概念不僅僅超出于本身是規定下來的、與其它的規律相對立的規律,而且也超出于規律自身。”[3]Ebd. S. 122.規律的純粹概念和具體的規定下來的規律具有“對立”關系,這一對立可以概括為規律的“概念”和規律的“存在”的對立,因為“規定下來的規律”就是定在的、存在著的規律,也即規律之存在。如果說規律的單純概念是內嵌于規律中的絕對同一性訴求,那么規律的存在則相反只具有“相對的”同一性。規律“存在”的“相對性”與它們的“概念”之“絕對性”的對立悖反,構成了知性規律之不可揚棄的缺陷。
規律中的“映像”構件,根本上來自純粹反思作用對感性物的絕對離析和抽象。[4]詳參李逸超《黑格爾靜態“超感官世界”的邏輯生成》,《哲學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4—117 頁。它們雖然歸屬于超感官世界,但是感官物的雜多性和對立性并未從根本上被揚棄。映像之“感性殘余”,首先使得“規定下來的規律的規定性本身尚且歸屬于現象甚至感性的存在”[1]G. W. F.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22.,其次使得諸多規律因此從原則上無法被真正統一。它們依舊沿襲著感性物之各自獨立的“雜多性”和“對立性”,正如海德格爾所指出的那樣:“每個規律自身僅僅是一個在其他諸規律之中的一個個別的規律。”[2]M. Heidegger, Hegels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97. S. 175.囿于諸多規律的上述本質“個別性”,它們無法被真正統一。因此,形式規律諸如false 或者諸多源初規定性本身,在false 中便只能被“取消”而成為“消逝著的環節”。黑格爾之所以批判萬有引力定律之空疏,不是因為他以為萬有引力定律沒有內容(G、M1、M2、R2等要素皆為充實的內容),而是因為他洞見了規律概念和規律存在之間的絕對“悖反”。科學范式之在科學史中的“更替”,事實上只是規律這一內在“本性”的現象性顯現。
規律的“概念”追求絕對必然性,它要求規律的通約跟統一。黑格爾將規律的這一“單純同一性”(einfache Einheit)稱作“規律的內在必然性”[3]G. W. F.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22.。但規律的“存在”卻是“規律的雜多”(Vielheit der Gesetze)[4]Ebd. S. 121. 黑格爾指出,知性的原則是追求“自在普遍的同一性”(an sich allgemeine Einheit)。牛頓的“萬有引力”,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都可以被視作知性的這一原則在科學研究中的具體例證。。出于知性“反思”本身顯諸“映像”之上的限制,諸多形式規律的“不可通約性”以及“離散性”最終無法被揚棄。它們的終極“大一統”,因而便是原則上根本無法實現的“理想”。形式規律追求不違背矛盾律的“確定性”、機械的“必然性”。但在黑格爾的哲學認知中,真正統一一切實在的、作為“具體事物之靈魂”[5]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Frankfurt am Main, 1969. S. 276.的“普遍者”(Allgemeine),作為規律之“真正”的“概念”,卻是自身矛盾著的、并因而不能以形式規律加以把握的、也即“ [……]超出于規律自身”[6]G. W. F.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22.的“生命性”或“創生性”(Erschaffenheit)。它不是來自對感性對象的抽象對象化,也不是來自知性之間接相對性和外在性的“反思”。
三、“力”范疇在黑格爾理智直觀中的基本規定及其意義
黑格爾之所以認定知性意識之統治著牛頓力學和其他形式規律的“反思”思維,無法從根本上把握“力”這一超感官存在,是因為力之根源在Nachdenken 或“理智直觀”中被最終歸結到絕對創生著的(erschaffend)精神實體之上。“精神”不僅是主體的思維能動性,更是存在于物理客體之內核中的創生性——正如黑格爾將“作為絕對否定性的概念”(Bergriffals absolute Negativit?t)稱為“塑形者”(das Formierende)和“創生者”(das Erschaffende)[1]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Frankfurt am Main, 1969. S. 277.一樣。這一普遍的否定性概念——“作為真正的絕對概念被把握為無限精神的理念,這種概念的被設定的存在是無限的、透明的實在性(Realit?t),在其中概念直觀到它的創生(Sch?pfung)并且在它的創造中直觀到它自身。”[2]Ebd. S. 279.感官物之所以在黑格爾的理智直觀中是“無限的、透明的實在性”,是因為內在于事物中的、使事物“是其所是”的“創生”(Sch?pfung)本身被明證性地納入到直觀之中:“在哲學的知識中被直觀到的東西是理智和自然、意識和無意識者同樣的能動性。”[3]G. W. F. Hegel, Jenaer Schriften 1801-1807,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42.
內嵌于感官物中的絕對創生性,在理智直觀中被黑格爾認定為“物理力”的絕對根基。早在其《差異》中,他實際上就已對牛頓力學在物質和力之認知上的貧乏加以批評:“力學已經用引力和反作用力的貧乏豐富了物質;因為力是一個生產著外在者的內在者,是一個等同于自我(Ich)的自身設定自身者,而一個這樣的東西,從純粹[主觀]觀念論的立場出發,是不能歸屬于物質的。”[4]Ebd. S. 104.區別于“力”范疇在康德“純粹觀念論”中的知性規定,因為它在黑格爾“絕對觀念論”中是一個“生產(produzieren)著外在者的內在者”,所以它實際上表達著精神“實體”之自我更新、自我創造的“主體”屬性。在后來的《邏輯學》中,承繼“力和力的表現的關系”的是“外在和內在的關系”。黑格爾把“力”規定為“生產著外在者的內在者”,一方面在遠處的絕對本原意義上,把“精神本體”之“生產著”的“創生性”納入到“力”范疇的本質規定中;另一方面,在邏輯環節之級次序列中,也即在“外在和內在的關系”這一近處和具體的邏輯脈絡中,將“力”進一步具體化為“生產著外在者的內在者”。
物理自然之“生產”著的創生性,也同樣存在于精神界的人類意識中。黑格爾認為,“思辨思維”是“生產著的意識”。[1]思辨著的思維是創生著的思維,黑格爾稱這種思維是“意識的生產”(Produzieren des Bewusstseins)Vgl. Ebd. S. 43.他當然不可能臆想單只通過人類意識的思辨思想,就可以創造、生產出自然界的物理物。意識的“生產”,在此處當指人類主體意識在其思辨中與精神本體之創生活動相一致、甚或相同步的“思想生成”。其中,主體跟客體、意識者與無意識者之相同的“能動性”,都被安置在此一被本體化了的、絕對創生著的“主體——實體”理念中。它在《邏輯學》中就是絕對理念,在宗教中被表象為“上帝”。不同于牛頓之來自于間接“反思”的“上帝第一推動”,“生產著的意識”在理智直觀之“切問近思”中所明見的事物,是“絕對創生著的”精神實體之“創生”本身作為“力”的絕對根源。在接續其絕對根源作為“源頭活水”的前提上,“力”范疇才最終在邏輯級次序列中被確定規定為“生產著外在者的內在者”。
黑格爾積極看待近代以來的科學和文學藝術之復興、資本之興起、啟蒙和人本主義之價值。[2]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I, Frankfurt am Main,1971. S. 11f.一方面,他看到了知性及其統治著的精確科學的積極價值;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其缺陷并為其劃定范圍。[3]莊振華基于謝林自然哲學所觸及的“事情本身之開端的原初同一性”,指出了人工智能這一計算機科學之在形式思維層面的界限。詳參莊振華《略論謝林自然哲學的開端》,《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 期,第29 頁。在“力與知性”中,他對主導著科學研究的知性“反思”思維的批判,最終會歸于“自我意識”對“物理客體”的主觀“解釋”行為之中。[4]G. W. F. 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125.在與創生實體的自在聯絡中,物理客體自身呈現出“絕對的變換”這一客觀的矛盾性本質——“無限性的概念”。[5]Ebd. S. 133f.但因為知性意識固執地堅守客體自身的“同一性”,并將此“矛盾性”單置于意識之能動的認知活動中,這一“矛盾性”因而才最終只被設定為意識的“解釋”行為。[1]Ebd.知性意識雖然回避客體的矛盾本性,但是這一矛盾著的創生性卻將意識逼到對它所固持的“抽象同一性”客體之“解釋”的矛盾性中:“ [……]它[無限性]首先作為解釋而自由地呈現出來。”[2]Ebd.解釋行為中的一切環節和要素,尚且停留于知性之抽象和反思行為中,規律實即其解釋行為的意向軸心。諸多形式規律作為“ [……]第一個超感官世界只是被知覺世界之直接提高到普遍的要素之中”[3]Ebd. S. 128.:在萬有引力定律false 中,M 表達了物理物之被抽象為“質量”,天體之間的引力現象被抽象為普遍的F,如此等等。但諸如M1、M2、R2等具有反思關系的“普遍要素”,在形式規律中卻并沒有與創生著的精神實體建立本原性的聯絡。盡管按照符合論[4]關于符合論這一真理標準之歷史沿革、理論困境等等問題,詳參王增福《真理符合論的邏輯演進、學理困境與可能出路》,《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29—33 頁。的真理觀,知性所反思到的科學知識最初被規定為與客體相符合的真理(Wahrheit)。但在“解釋”行為中,“科學”實為一種“解釋學”,其“真理性”實為一種“或然性”(Wahrscheinlichkeit)。那表達著客體之絕對矛盾這一終極真理的“變換”,只是知性的解釋本身作為一種“活動”,而非具有反思關系的、諸多被解釋了的靜態“普遍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