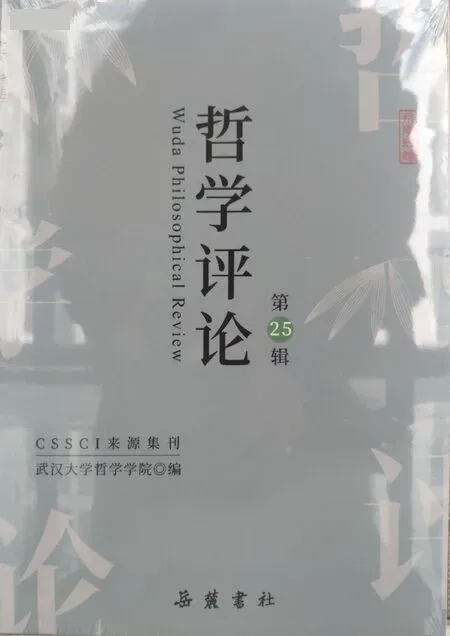“吾有知乎哉?”
——孔子的問與知
伍曉明
提要:人類共同體的基礎和起點是本原的人—我關系。在這一關系之中,我面對他人,因而需要對之做出回應,而做出回應已經就是對他人做出應承,為他人負起責任。這就是“responsibility”一詞所蘊含者:回應,應答,應承,承擔,責任!做出回應是向他人敞開自己。在這一敞開之中,我將自己暴露給他人,奉獻給他人,為他人所用,為他人服務。沒有這一敞開,我與他人就不可能真正接近。與所有人——全人類——的關系,或一個公正的人類共同體,最終必須建立在這一本原的我向他人敞開并因而為他人負責的倫理關系之上。本文將從一個特定的儒家文本——從這一文本的具體細節——來探討人類共同體之構建這一宏大問題。這一文本在《論語·子罕》篇中。孔子承認,面對一鄉野之人(“鄙夫”)的提問,他感到自己無知。他雖有此自覺,卻又感到有“責任”做出應答。這一“責任感”來自面對他人這一簡單而純粹的事實,而非來自任何制度化的規定。在他人之問前,孔子首先讓自己敞開。他進而以一種“叩其兩端”的形式來與他人“共同”解決問題。這里或許就有著人類共同體的構建活動的本原形態。本文將分析這一現象的深刻復雜含義。
一、問之為問
作為本文標題的問句取自《論語·子罕》篇第八章。[1]本文為提交給紀念孔子誕辰257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六屆會員大會之會議論文的修改稿。該次會議的主題是“儒學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此章僅短短二十八字。全文如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2]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9 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將《子罕》篇第六與第七章合并為一章,遂使本章成為第八章。本文以下所引《論語》之語皆僅以括號中數字標明引語之篇章。對于本章的傳統詮釋,朱熹之說有代表性:“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于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0 頁。)劉寶楠《論語正義》也有類似解釋:“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遂謂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謙言‘無知’也。”(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32 頁。)至于“兩端”,焦循的解釋似比朱熹的解釋更有助于理解:“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后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問焉。”(劉寶楠《論語正義》引,第333 頁。)筆者對此章的閱讀在尊重前人解釋的同時試圖另辟蹊徑。筆者亦將另文分析孔子“叩其兩端而竭焉”的答問方式。
這是本文將具體分析的文本。“吾有知乎哉”以第一人稱代詞“吾”為主語,因此顯然是一個關于“吾”或“我”的問題。既然發問者是孔子,這一問題就是關于孔子自己的問題。《論語》中很少記載孔子發問。我們常看到別人問孔子,卻幾乎從來不見孔子問別人,除了進入太廟的那一次。[3]“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3.15)但在此章中,我們卻看到孔子在問:“吾有知乎哉?”問題雖是關于自己的問題,但他是在問誰呢?如果沒有上下文,就很難知道孔子是在問別人還是問自己。因此,雖然這是一個關于孔子自己的問題,但不一定是一個向自己提出的問題。我其實很可以問別人一個關于自己的問題。例如,“我有病嗎”是關于自己的問題,卻可以不是向自己而是向醫生提出的問題。但我們看到,在問出“吾有知乎哉”這一問題之后,孔子立即就做了回答:“無知也。”據此看來,這一有關自己的問題確實是向自己而非別人提出的問題。然而,仍然不能排除的是,孔子開始時也很有可能是在問別人,卻沒有得到回答。沒有得到回答也許是因為,被問之人大約不知如何回答,就像子路被人問到孔子是怎樣的人時那樣。[1]“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7.19)于是孔子就自己回答了自己是否有知的問題,以免讓問者陷于尷尬境地。
“吾有知乎哉?”一個向自己提出的關于自己的問題!但孔子為何會向自己發此一問?孔子說過:“疑思問。”(16.10)孔子可能是有了對于自己是否有知的某種疑惑,所以才會想要問自己是否有知,而問就是為了釋疑解惑,從而求得對自己之是否有知的確切回答。換言之,問是為了知,而孔子之所問又恰是為了欲知自己之是否有知,于是孔子的這一問題本身就將問與知以一種可能并非偶然的方式聯系在一起。這一聯系將可以為我們對孔子的問與知以及二者之關系的思考提供一個有用的出發點。
思考孔子的問與知,首先需要提出“問是什么”與“知是什么”這樣的一般問題,但此二問題之間似乎有著某種循環。因為,“問是什么”這一問題是欲知何為問,而這一欲知何為問之知本身又是“知是什么”這一問題之所問者。如果追求語言上的形式對稱,以上所言就可以被表述為:“問是什么”欲知何為問,“知是什么”則欲問何為知。我們以問求知,但我們以問所求之知當然也必須包括知何為問,知為何有問,知為何要問。換言之,我們以問求知,而這也必然包括通過問來求得有關何為問本身之知。因此,在這一“欲問何為知”與“欲知何為問”的貌似對稱之中,在問與知的循環之中,如欲找到一個可以開始之處,我們必須回到問。問是知的起點。由于懷疑自己可能無知,并為了知己之確否有知,孔子才會問:“吾有知乎哉?”然而,首先,孔子為何會懷疑自己可能無知?其次,孔子又為何欲確定自己是否有知?換言之,孔子為何竟會發此“吾有知乎哉”之問?
既然問是起點,而我們又需要知道何為這一作為起點的問,那就讓我們先問:“何為問?”問有其所問。問之所問是動詞“問”的直接賓語。《論語》中有問仁、問知、問孝、問君子、問津等,現代漢語中也會說“問路”等。問也必然要有一個“問于……”,即向某人發問,如在《論語》中“太宰問于子貢”(9.6),“鄙夫問于我”(9.8),“哀公問于有若”(12.9),“南宮適問于孔子”(14.5)等。問之問于者是動詞“問”的間接賓語[1]在現代漢語中,問之問于者即被問到者是直接賓語,所問者才是間接賓語,如“我問他天氣如何”。此與古代漢語有所不同。。問之所問者與問之問于者,再加上問所必然蘊含的問者本身,就構成問的基本結構:問者問某事某物于某人,或就某事某物向某人發問,如“哀公問社于宰我”(8.21),“葉公問孔子于子路”(7.19),“齊景公問政于孔子”(12.11),“衛靈公問陳于孔子”(15.1),“子張問仁于孔子”(17.5),“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19.3)等。問之所問者以“何”即“什么”表示:“問何”或“問什么”。問之問于者則是某人:“問于誰”(《論語》的句式)或“問誰”(現代漢語)。但問之結構中也包含一個“之所以問”或“何所以問”,亦即,為何要問此問題,為何會問此問題,或此問之目的為何。上文其實已經回答了這一問題:之所以問是因為欲知或欲求有所知。[2]“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求知的途徑是學,而學的途徑是問,是以學與問密不可分:“敏而好學,不恥下問”,這就是孔子所理解的“問”的意義。《中庸》的“博學之,審問之”所表示的也是學與問的密不可分。問仁就是欲知何為仁,問知就是欲知何為知,所以回答總以“……是什么”為基本形式,也即總可以還原為“……是什么”這樣一個現代形式。例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12.22)樊遲以此二問而求有關仁與知(或智)之知。孔子的回答省略了所謂主語。如以完整的現代漢語句式來說,這一回答就是,仁是愛人,知是知人。如果樊遲理解孔子的回答,他即可因其所問而求得有關仁與知之知。如果不解,他還可以繼續追問孔子:何謂也?當然,不言而喻的是,問必總有問者。在《論語》中,就孔子而言,向他發問者多為弟子,也有公卿(如魯哀公、齊景公)大夫(如孟懿子、季康子)和時人。但成為問者尤其是一個好的問者其實并非易事。我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而不會、不能或不欲問,所以“不恥下問”(5.15)才是孔子稱贊的美德,所以有些問才會被孔子嘆為“善哉”“大哉”[3]“樊遲從游于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12.21)“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3.4),而孔子自己的“入太廟每事問”也所以才會因為不被理解而遭到恥笑。
有問題是因為有疑惑。問自己“吾有知乎哉”是疑惑于自己之是否有知,假如我們相信孔子的這一問題不是純粹的自謙或欲揚先抑的反問的話。然而,孔子為何會疑惑于自己之是否有知?他不是有博學而無所不知之名嗎?[1]“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9.2)又,《孔子家語·子貢問》記載了子路因問孔子魯大夫是否知禮但沒有得到回答,遂對子貢說:“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問過孔子后告訴子路,孔子當時沒有回答他只是因為身在魯國而非議魯國大夫不合乎禮:“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荀子·子道》中此句略有不同:“女〔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孔子之所以會疑惑于自己是否有知,是因為有他人。他人來到我之面前,我即需要做出反應,他人有問于我,我就必須進行回答,即使此人之問可能并不合適,并不恰當,并不應該向我提出,并不應該由我回答,或即使其問很有可能置我于覺得自己“空空如也”的尷尬境地。如果回應他人之問是已經落在我身上而無法推卸之事,那只是因為,無論我做出回應還是拒絕回應,我其實都已經回應他人了,即使是以一句拒絕回應的言語或一個拒絕理睬的姿態而傳達的“我不回應你”之意,例如說一句“我不知道”的話或做一個掉頭不顧之態。但即使是這樣的以拒絕——無論口頭的還是姿態的——為形式的回應,也已經將我置于一個無法推卸的責任之中。什么責任?從何而來?責任從作為問者的他人而來,責任是我對作為問者的他人的責任。這一責任意味著,在他之面前,面對他的問題,我必須做出回應,而且已然做出回應,即使是以全然的無視為形式。但為何必須?為何已然?我不是完全可以不回應嗎?我不是完全可以不理這一發問的他人和這一他人的發問嗎?因為,我很可以有某種理由認為,我不該跟此人說話,例如這位似乎沒頭沒腦闖到我面前發問的“鄙夫”或鄉野之人。他與我何干?值得我為其浪費口舌嗎?我怎么知道他是我可以跟他說話的人呢?孔子不是已經教導過,如果“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人就會“失言”嗎?
那么,如果確有理由,我就真可以不應他人之問嗎?唯唯,否否,不然![2]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我們可以先退一步假定,在他人向我發問之前,在他人以其向我所發之問而將自己的疑惑交托給我之前,我似乎確實沒有任何對他的責任。我很可以自信地以為,他與我無關,因而我也與他無關。然而,他卻到來了。這就是那位來到孔子面前的“鄙夫”,那位有問于孔子的鄉野之人。他帶著問題出現在我面前(他也許甚至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一個需要我為之解決的問題,就像那個在齊國的饑荒中來到給餓者發放食物的黔敖面前的餓者[1]事見《禮記·檀弓下》。參見以下關于“嗟來之食”的注釋。)。他有問于我。他以自己之問表明,他乃有求于我者。他以自己之問向我敞開,他暴露自己,自己的無知,自己的匱乏。他以向我發問而將自己置于我之面前,或我之足下。確實,是我之足下,因為他很有可能會自謙地尊稱我為“足下”。[2]當然,“足下”一語作為謙稱不見于《論語》《孟子》。但已見于《韓非子》。例如其《內儲說下》:“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余瀝乎?’”在這一例句中,“足下”直接就是對于他人的尊稱。在《史記·項羽本紀》的下述例句“張良謝曰:‘……謹使良奉白璧一雙,再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之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足下”這一尊稱或謙稱的起源。這一稱呼因為使用太久,人或早已忘其意味深長之曖昧。足下:誰為足下?誰之足下?足下:自稱還是他稱?謙稱還是尊稱?也許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因為“足下”表示的是一種關系,而關系至少連接兩項。但不論怎樣,這一稱呼在使用者口中都有一個謙卑的“在您足下”之意。他人之問是有求于我,無論問之目的是欲獲取信息還是求得知識,懇請錢財或謀取幫助。正是問所表示的多重意義上的求——作為問之求和作為求之問——將我立即置于對他的責任之下或責任之中。
但求與責任何干?先說責。《說文》對“責”的解釋是:責,求也。責意味著求。反之,求亦蘊含著責。有求于我就是有責于我。“有責于我”在此意味著,責成我為之做某事或給某物。求之所以是責是因為,單音字“求”的意義有兩面性:既可是乞求之求,也可是責求之求。乞求之求偏于乞,讓人想到謙卑。責求之求則偏于責,讓人想到謙卑的反面。但這一反面并不是驕橫,而是一種由擁有提出要求之權利而來的堅決。作為求之問可以非常謙卑,可以是在我面前或在我足下的他人的恭順的乞求。但這一恭順的乞求甚至求乞對我來說卻有其不容拒絕性。不是因為他人擁有某種我若不應——回應,應答,應許,應承——就可以威脅到我的力量,而是因為他根本性的軟弱無力。這一軟弱無力表現為我似乎可以隨時隨意拒絕他——拒絕他的提問,拒絕他的乞求。然而,這一軟弱無力卻讓他靠在我身上,或倒入我懷中,從而成為我的負擔。古漢語表示“負擔”的詞即“任”。所謂“任重而道遠”,說的就是負擔很重而路途很長。
他人因其軟弱無力而靠在我身上或倒入我懷中,我因而不得不把他扶起或抱住,亦即不得不把他以某種方式擔負起來。而這也就是說,不得不以他為己之任,卻還必須尊重他之為他,而不能自以為我是在施恩行善。[1]關于他人為我之任或是我之“負擔”而我還必須對他謙恭不懈,敬重有加,《禮記·檀弓下》中有一個典型例子:“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而且,即使我因不想管他而把靠在我身上或倒入我懷中的他推開或扔下,我也還是已經承認了此一己任或此一負擔,盡管是以否定的方式。這樣,問、求、責、任四者就有意義地聯系在一起了。他人之問是求,求使我有責,而責——被責成,被要求——乃我之任。而此任就是那一在我面前或在我足下的他人本身。他人既已到我面前,我就不可能不對他說話,無論是耐心回答他的發問,還是仔細探詢他的請求,甚或只是粗暴地告訴他這里沒有地方,讓他走開。我當然也可以假裝不見,掉頭而去。但即便如此,我也還是已經對這一他人的到來和這一到來的他人做出了回應。的確,是回應,而不是發問或質詢或對話。因為,即使是我首先開口詢問他人此來何干,那也已經是對于他人之到來本身的回應,并且就在這一意義上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而我之回應,我對他人的到來本身的回響和反應,則已經就是對他的應承:應答——承擔。責任就是我對他人的應承。
回到我們分析的文本之上。我們已經看到,在《論語》中,正是那位帶著自己之問而來的鄙夫或鄉野之人,讓孔子不得不做出反應,做出應承,而這也就是說,應承他的到來,負起對他的責任。這一責任在此就具體表現為孔子感到自己必須回答這位鄉野之人提出的問題。而正是這一回答他人之問的必要,才開始讓孔子自問“吾有知乎哉”,并讓他感到自己“無知”,感到自己“空空如也”。只是孔子的自謙嗎?也許。因為這也是對孔子之自問的一種可能解釋。但是,如果從我對他人的責任來說,那么我在面對他人之時其實必然始終都是“空空如也”的。因為,相對于責任之無限而言,我始終都是不足的、不夠的、“空空如也”的、力不從心的。這并不是經驗層面上的欠缺,某種可以用“學而不倦”來彌補的不足,而是由于他人是從根本上即超出我者。他人并不是我的認識對象,而是要求我之應承者。應承則具有這樣一種結構:我越是應承,就越是要做出更多應承。[1]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身處愛中之人為例。愛是對他人的回應。《紅樓夢》中寶玉與黛玉相愛。就作為愛者的寶玉而言,他知道黛玉需要他對她的感情做出回應,但寶玉越是回應,黛玉就越是需要更多的回應。相對于黛玉的愛的要求,寶玉的作為愛的回應或作為回應的愛必然始終是不足不夠的。就黛玉而言,作為被愛者,她越是知道寶玉愛她,就越是需要更多的愛的表示和愛的保證,直至于她在自己的夢中看到寶玉為了讓黛玉相信自己而竟掏出心來:“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著,就拿著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著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么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著,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黛玉拼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鵑叫道:‘姑娘,姑娘!怎么魘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紅樓夢》第八十二回“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然而,盡管必然“無知”,必然“空空如也”,但由于對于他人的無法推卸的責任,孔子又感到自己對于這位鄉野之人所發之問雖然并無所知卻必須回答。于是孔子回答了在他面前的鄙夫之問,并非僅僅出自禮貌,更不是由于虛偽,而是因為對他人之責任的無可推卸。但如果自己“無知”,如果自己“空空如也”,那又如何能回答他人之問?孔子為自己發明了一種在這樣的情況下回答問題的方式。他對鄙夫之問“叩其兩端而竭焉”。就是說,不是坦言自己之無知[2]這應該是孔子對自己所不知者的基本態度。孔子曾教訓弟子子路說:“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13.3)在另一場合,他叮囑子路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2.17)。,更不是強不知以為知,而是以回問對方為求知之徑。通過回問,孔子幫助這位提問者自己進行分析,讓他從“兩端”(即問題之正反兩面)看清自己之問中所必然蘊含者(這就好像是把問題作為一個分析命題來對待)。于是,鄙夫之問就可以無孔子之正面回答而自解,因為孔子“叩其兩端而竭焉”的回答方式乃是一種答而無答,而孔子自己也會通過這一對他人之問“叩其兩端而竭焉”的方法增加新知。
二、知之為知
因此,我需要知是因為有他人問于我。更根本地說,我需要知是因為有他人。如果沒有他人,我自己或許完全可以“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正是他人的到來,他人的問題,才促使我問自己是否有知。但首先讓我們問,何謂知?
在《論語》中,知的意義不一而足,而孔子有關知的唯一近乎定義的說法就是“知人”。這是在回答弟子之問時做出的:“樊遲問知。子曰:‘知人。’”(12.22)通觀《論語》中涉及知的章節,知人當然不是孔子所理解的唯一的知,卻可能是最重要的知,因為知人是一切知的落實之處,是知的實踐或實踐的知。在中國傳統中,知當然也有現象學所說的“theoria”(theory,理論)的意義,亦即通過對于事物的觀照而獲得的認識,一種《禮記·大學》中所說的需要通過格物而至之知,但孔子并未明確說到這樣的知。孔子談論自己之知時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就像《論語》中大部分的話一樣,此語也是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對某人說的,而我們這些現代讀者如今已經無從得知其確切的原初語境了。這種由于對過去的時代和事物的熱愛而努力求得的知不是“物格而后知至”之知,也不是知人之知,盡管知人當然也可以包括對過去之人的知。從孔子此語本身看,他說的應該是我們如今會用“歷史知識”和“文化知識”來概括的知。雖然孔子也說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卻并不認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而只是次一等的“學而知之者”(16.9)。也許孔子其實從未認為真有所謂“生而知之者”,因為他似乎沒有為我們舉過任何生而知之者的例子。孔子認為自己的這些知來自過去——古。過去之為過去就是不在現在,亦即不在可以直接當下為人所知。能從過去之中求得的知識是以各種方式書寫在典籍之中和銘刻在流傳至今的制度和器物之中的知識。這樣的知意味著學——《論語》中那個經常與知對舉的重要觀念。學則離不開問。孔子當時之有知禮者之譽,就是因為他的孜孜以求的學與謙恭有禮的問。但這樣的學與問有時卻使他在別人眼中像個無知者。“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3.15)
對于孔子來說,知之終極或知的最高境界應該還是“知命”。《論語》的終末之篇的終末之章的第一句話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20.3)對于此語中“命”之含義,古今中外論者雖有不同理解,但大致不過天命與命運之別,這點此處可以暫且不論。[1]參見拙作《“天命:之謂性!”——片讀〈中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至于知命對于孔子何以如此重要,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簡單地假設,知命之所以為終極之知,是因為此知不可能是某種直接領略,某種瞬間頓悟,或某種即刻靈感,而必以全部可求之知為基礎。孔子感嘆自己不為他人所知時說自己既“不怨天”,也“不尤人”,而是“下學而上達”(14.35),所以大概只有天才知道他(“知我者其天乎”)。雖然關于“下學而上達”的意思從古至今頗有不同解釋,但皇侃《論語義疏》中說的“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卻似乎是最說得通而且也頗適合我們此處論述的解釋。當然,這一解釋本身并沒有將“下學”與“上達”因果地聯系在一起,因此我們仍不明了解釋者心目中二者之間的關系。但“下學而上達”句中這個多義多能的連詞“而”字卻容許我們將之理解為通過下學而上達。正因為如此,知命之知才必然是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過程。而如果我們可將知命之命理解為天命的話,那么孔子之言自己五十歲才知天命,就正表明著這樣的求知所需要的時間之長——從十五歲到五十歲——及努力之勤。
然而,《論語》終末之章的終末之言卻不是知命而是知人,或更準確地說,是通過知言而知人:“不知言,無以知人也。”(20.3)一篇以“知命”開始的話卻以“知人”結束,這似乎與上文解釋的那一通過下學而上達的過程的方向相反。如果我們并不認為孔子說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只是三個不同論斷不分軒輊的并列,那么就可以說,在孔子關于知命、知禮、知人的思想中存在著一個有意義的循環。下學是為了上達,但上達卻必須回到下學,落實于下學之中。我所能知之天命始終只能通過他人而來,因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天命也必然自我民命。天命由人——由他人——而來,因為他人才是可以命我者,故必知人以知命,知命則落實于知人。[1]在《禮記·中庸》和《孔子家語·哀公問政》中,孔子說:“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可以理解為知命。為了知人,即須知天,但知天要落實于知人與事親。為了知人,即須知言。如果《論語》各篇各章的次序安排并非純屬偶然,那么排在最后一篇最后一章最后一句中的“知人”甚至可以視為孔子對我們的最終遺囑,最終命令。在《論語》全書中,這一最后的“知人”呼應著《顏淵》篇中的“知人”。這樣聯系起來看,孔子在回答弟子樊遲的問題時將“知”規定為“知人”,就并非只是針對特定弟子做出的特定回答而已。在孔子這里,知人這一要求可說不僅具有普遍意義,甚至具有終極意義。
弟子樊遲從老師孔子得到的關于何為知的回答只是“知人”(而且我們知道樊遲當時并未馬上理解)。《論語》中最后的“知人”則指出了知人的路徑或方法。人如何可知?可由其言而知。[2]當然,孔子也認為,知人不能止于知言。為了具體地知人,亦即,知經驗關系中之人,還必須將其言與其行聯系起來:“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5.20)但言始終都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表明人之為人。然而,言有各式各樣,知言又談何容易。[3]《論語》中對言有不同的形容:巧言(1.3,5.25,15.27),信言(1.7,15.6),忠言(15.6),慎言(1.14,2.18),訥言(4.24),雅言(7.18),善言(8.4),便言(10.1),侃言(10.1),訚言(10.1),疾言(10.25),不讓之言(11.24),不順之言(13.3),可行之言(13.3),不茍之言(13.3),讱言(12.3),危言(14.3),怨言(14.9),不怍之言(14.20),無(意)義之言(15.17),躁言(16.6),圣人之言(16.8),戲言(17.3),中倫之言(18.8),厲言(19.9),等等。其中有些指言的形式,如巧言,有些涉及言的內容,如信言。為了知言,首先就必須聽到他人之言。而為了聽到他人之言,我就需要開口跟他說話。但孔子告誡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15.8)[4]試比較孟子之所言:“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孟子·盡心下》)這里的“可”不僅意味著“可以”或“能夠”,而且意味著“應該”。如果我可以跟某人說話,應該跟他說話,卻沒有去跟他說話,我就失去了這個我本應該加以珍惜的人;而如果我不應該跟某人說話,如果我認為他是一個不能讓我與之說話者,我卻去跟他說話,那么我就失去了我同樣應該加以珍惜的言語。知者應該是一個讓自己既不失去不該失去的可貴他人也不失去不該失去的可貴言語的人。然而,問題是我如何知道某人是我可以跟他說話的人,某人不是我可以跟他說話的人呢?換言之,按照孔子要求我們的,為了知人,為了知其是否“可與言者”,我就必須知言,不然即無以知人。但為了知言,我就必須先開口跟他說話。因為,如果我不首先以我之言接近他,如果我一定要等他先開口說話[1]這樣我就可以“察言而觀色”(12.20),從而在與他人的交往中掌握主動了。但如此察言觀色就是將他人作為對象而知,而不是將其作為他人而尊重。,那也許就永遠不會聽到他之言,因而也就永遠都不可能知其言。而不能知其言即不能知其人。這樣,我在還沒有得到他之前就已經失去了他。于是,為了不失去一個我可能不應失去的人,我必須知其言,而為了知其言,我就必須先開口向他說話,亦即,以我之言接近他,或以我之言來讓他接近我。而這也就是說,以我之言將自己在他面前毫無保留地敞開。[2]孔子認為自己就是這樣向他人敞開自己的。以孔子與弟子的關系為例:“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7.24)而當我如此向他開言之時,我可能還并不知道他是否“可與言者”。而不知其是否可與言而竟與之言,這在孔子看來當然是失言。但我如果不首先“失言”,主動“失言”,亦即,首先主動以自己之言在他人面前毫無保護地暴露自己[3]所謂暴露就是將自己“剝皮露肉”般敞開,讓自己在他人面前無處藏身,一覽無余。這一表述并非夸張,而是每一我在他人面前的必然處境。《禮記·大學》中說小人見到君子時才試圖掩蓋自己的不好之處,不過沒什么用,因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但必然會在他人面前像露出自己肺肝那樣暴露自己的全部內在隱秘的并非只有小人,君子亦如此。,我就必然可能“失人”。這一“必然可能”很容易理解:如果我應該等待他主動首先開口說話,以便知其是否“可與言者”,那么他就也應該等待我首先主動開口說話,以便知我是否“可與言者”。如此一來,二人就會面面相覷,陷入無限的等待之中。雖然已經面面相對,我與他卻各自堅如沒有開口或裂縫的硬殼。這樣的硬殼保護著各人的內在性,看守著自身的秘密。沒有一人首先主動以自己之言打開自己,因而也沒有一人會被對方之言打開。除非使用狡計,引誘對方走出掩蔽,以便置其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這樣,我與他人的關系之中就毫無真誠可言。
因此,為了不失人,不失去他人,為了不在我尚不知其是否“可與言者”時即失去他,我就必須失言,亦即首先主動開言。我必須冒“失言”之險,才有可能讓自己無“失人”之虞。我,作為君子,在與他人的關系之中乃是必須失言者,首先失言者,永遠的失言者。只有這樣,我才有可能不失去他人,也才有可能不讓他人失去我。因此,“不失人亦不失言”只是理想,但如果真想無限接近這一理想,那就只能從我自己之首先主動失言開始。因此,我們也許可以把孔子的話擴展為:“不失言無以知言,不知言無以知人。”而對于孔子的下述憂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16),最終也就應該這樣來理解:既然應該怕的首先不是他人不知我,而是我不知他人,而為了知他人我就必須知其言,那么我就必須甘為首先主動失言者。我由于我自己的必然的失言而知人,包括知其可能為一“不可與言”之人。而當我如此知人之時,我也就必然已經讓他人知我了,因為我已經以我之言——我之既主動而又被動、既被動而又主動的“失言”——向他人敞開了自己。所謂“既主動而又被動”是說,我的主動失言其實首先總是被動回應他人的結果。所以,不必擔心自己不為他人所知,而只須憂慮我對他人的無知。而此無知從根本上說僅意味著無知于他人之為他人,無知于他人之為我必然需要對之做出回應者。這才是我的最大的無知,因而也是我的最大的擔憂。而我之知,在成為任何可以加以利用的特定知識之前,也必然首先僅意味著知他人之為他人,亦即知他人之為我必然已經對之做出回應并即因此而已經對之做出應承——應諾與承擔,應諾即承擔——者。如果我們仍以“知”稱之的話,那么此知才是最基本的知,是先于判斷、先于評價、先于定性的知,是無知之知,是僅知他人之為他人這樣一種純粹的知,而這也就是說,是對他人的無條件的根本尊重。
當然,此知也必須落入判斷和評價之中,亦即成為具體的相對的知。不然,在超出二人關系的家與邦之中,不同個人之間的現實關系就無法實現,而人際秩序也就無法建立。例如,孔子相信,在他所熱愛的依據長幼尊卑等級維系的貴族社會中,君子應能影響小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2.19)而為了將君子拔擢到小人之上,成為小人的表率,從而讓特定政治倫理秩序得以維持,就需要知道如何才算君子,誰人可為君子,因此就必須有一定的標準。例如,根據孔子,行己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就是可以衡量一人是否君子的四個標準。[1]《論語·公冶長》:“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5.16)再如,在國之治理之中,為了能夠“舉直措諸枉”(2.19,12.22),亦即將正直的人提拔上來,就必須具體地知道誰為直者。但標準不同,則評價有異。例如,微生高有直名,孔子卻不以為然:“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鄰而與之。”(5.24)孔子以為微生高從鄰居借醋給向他借醋的人,是曲而不直,但若根據不同標準或從不同角度來看,此種行為也未嘗不是某種直的表現:微生高既不想讓他人空手而歸,從而感到失望,也不想讓他人感到尷尬,覺得因為借了點醋而竟欠情于兩人(微生高和鄰居),因此就自己向鄰居借來醋給他而并不說出自己借醋的實情。[2]當然,原文沒有明說微生高是否告訴了借醋者這醋是自己從鄰居借來的。如果微生高直來直去地告訴借醋者醋是借來的,那他的行為似乎就沒有可被批評為不直之處了。孔子和葉公對于哪種做法為直的判斷更是標準不同導致評價有異的好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13.18)在葉公看來,親人之間互不隱瞞對方過錯為直,在孔子看來則反之,親人之間互相隱瞞過錯為直。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直顯然不同于葉公的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的直。這里無法詳細討論這一聚訟紛紜的文本中哪一種直為直或哪一種直更直,而只想借此不隱之直與相隱之直的不同來表明,具體的知人離不開評判,而評判離不開標準,標準與價值觀念緊密相連,而價值觀念則必然是沖突之地。孔子與葉公價值觀念不同,二人對同一人物行為的評價也因而有異。
因此,孔子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可能有一仍待吾人深思的形而上或超越性意義。讓人知己,就必須讓己知人。但讓己知人首先并不是將他人作為“對象”而置于自己的察言觀色的目光之下。知人的根本方式是讓自己失言,亦即將自己向他人敞開。當我首先主動在他人面前失言即開口說話之時,我就已經讓人——他人——以根本的方式知我了。當然,在孔子的不怕不為人知而只怕己不知人的憂慮之中,還有另一層憂慮,一種更具體的憂慮,那就是擔心自己沒有可為人知的才能:“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15.19),“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4.14),“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14.30)。這樣的憂慮是從“形而上”的知人知己的層次下降到具體的個人修養的層次的憂慮。我可以不斷培養自己的能力,努力讓自己有可為人知者,即品德和才能,但可以看到和承認我是否在此意義上有知的最終也是他人。他人看不到或不承認,我就只好“懷才不遇”。這是傳統士人的標準感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孔子才雖然反復說不怕別人不知自己,只怕自己不知別人,或不怕別人不知自己,只怕自己沒有才能,卻也還是會不禁感嘆:“莫我知也夫!”沒有人看到他的才能,沒有人知道他,只有天:“知我者,其天乎!”(14.35)在《論語》中,這樣的感嘆我們雖只聽到一次,卻很明確地傳達了孔子的自信。這一自信應源于孔子通常的自知,而這一自知則包括知己之有知。被弟子稱為夫子自道的“知者不惑”,正是中國傳統讓我們熟悉的知者孔子的形象。[1]《論語·憲問》:“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14.28)
三、簡短的結語:“吾有知乎哉?”
然而,孔子始終確信自己有知嗎?我們可能一定會為孔子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在某一特定時刻,孔子卻竟然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有知。不僅是懷疑,而且是否定:“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怎樣一個時刻?是他人帶著問題到來之時!又是誰引起了這一有關自己是否有知的問題,這一自我質疑?是他人,某一他人——不是君子,不是雅人,而是一位鄙夫,一個鄉野之人,沒有什么學問和教養的人。但就是這樣一個卑微者的一個問題,就置孔子于感到需要自問自己是否有知的地位之上,并令其覺得自己“空空如也”。其實,我們自己也一定都程度不同地體驗過,正是他人的問題才逼出我的“空空如也”之感。當我與自己獨處之時,我可能以為自己有知,并感嘆無人知我有知,而當我暴露于他人之前時,我才會感到自己無知。但這是必然的。他人之問對我是一種喚醒,從而讓我開始警覺。他人之問將我召喚到我對自己之無知的意識之上,不然我就還會陶醉或沉睡在我的自以為有知的自滿自足之中,或沉湎和陷溺于“莫我知也”的感嘆之中。
當然,有解釋者認為,孔子稱己無知只是自謙。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問題之為問題就在于其總能讓被問者出乎意料。如果被問者對一切問題都有所準備,可以回答一切問題,那也就沒有真正的問題了。問題,即使是一個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就像孔子之問自己“吾有知乎”那樣,也預設了與我有別的另一者,預設了他人。而他人總是那會使我猝不及防者與那能讓我出乎意料者。孔子之會自問自己是否有知,就正是因為“有鄙夫問于我”,盡管在我們討論的這一文本中,這位鄙夫的問題應該不會是直接問孔子自己是否有知的問題。但他人的問題卻總會讓我回到自己,甚至是把我逼向自己。我從而才可能開始向自己提問,這也就是說,把自己放到自身之外,將自己與自身分開,把自己置于問題之中,羞愧于自己的自信,并開始承認自己的無知,自己的根本性的“空空如也”。而只有從這一承認開始,真正的探究,從他人之問而開始的探究,一種與他人的參與密不可分的探究,一種由于他人而又為了他人的探究,才有可能,才會開始。而所謂人類共同體的構建,也從根本上離不開這一本原的他人之問與我對他人原初的無條件的(回)應—承(擔)。
至于孔子的“叩其兩端而竭焉”的應承方式,則將是我們另一研究的主題。
2019年11月—2020年3月
撰寫與修改于北京—成都—悉尼—基督城
2020年3月27日定稿于新西蘭基督城
于時全球新冠病毒洶洶,新西蘭亦處于全國緊急狀態,居民必須在家自我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