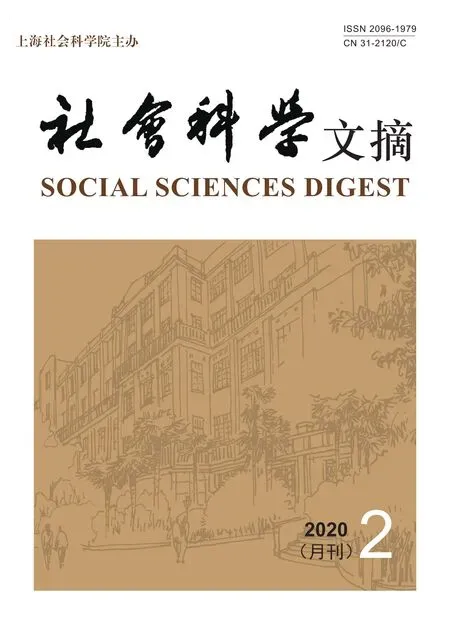西方文論關鍵詞:普通讀者
文/殷企平
在西方文學批評史上,“普通讀者”一詞得以登堂入室,這要歸功于大文豪約翰遜(Samuel Johnson)。他在名篇《葛雷傳》中這樣寫道:“我欲與普通讀者達成一致,并為此而歡欣鼓舞。凡欲飲譽詩壇者,其資格須由讀者的常識而定。飽學之士會對詩人評頭論足,并在條分縷析中盡顯風雅,或者引經據典,但是詩壇榮耀的決定權屬于那些不帶偏見的普通讀者。”這番話看似寥寥數語,卻飽含深刻思想,其中既有對文學/文學批評性質、文學對象的思考,又有對文學批評的倫理關懷,還有對文學評判標準的洞見。約翰遜是在論及葛雷的《墓畔哀歌》時發表上引觀點的。詩中,格雷面向窮苦大眾,謳歌那些無人憑吊的墓地安息者,指出他們中間“也許有緘口的彌爾頓,從沒有名聲”,只是因為“‘貧寒’壓制了他們高貴的襟懷,/凍結了他們從靈府涌出的流泉”,就像“世界上多少晶瑩皎潔的珠寶/埋在幽暗而深不可測的海底”。約翰遜贊揚這首為普通人譜寫的詩歌,并渴望就此“與普通讀者達成一致”,其用意不言自喻。在他之后,伍爾夫(Virginia Woolf)先后于1925年和1935年發表了兩部散文集,都冠名為《普通讀者》,并給出了理由:“如果他[筆者按:指普通讀者,包括伍爾夫自己]如約翰遜所說,在最終裁定詩壇榮耀方面有某種發言權,那么我們就值得寫下自己的思想和見解。盡管它們本身微不足道,卻能促成一種巨大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伍爾夫此處干脆視自己為普通讀者中的一員。
伍爾夫還寫道:“關于閱讀,一個人能給另一個人的唯一忠告就是跟直覺走,開動腦筋,得出自己的結論。如果我們之間能達成這一默契,那么我就會斗膽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議。因為有了這種默契,所以你們不會讓我的建議束縛你們的獨立判斷,而獨立判斷才是讀者應擁有的首要品質。”此處“獨立判斷”一語既體現了對普通讀者的引導,又體現了對后者的尊重。這種良性互動是文學批評活動所不可或缺的,因為它關乎文學/文學批評的性質,尤其是文學批評的倫理維度(批評家的責任與使命)。然而,在過去四五十年中,曾經備受尊重的普通讀者漸行漸遠了。文學教授/批評家們“常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宣揚自己的‘主體立場’”(美國學者奈特語),或者癡迷于挖掘文學作品背后的“意識形態”,甚至醉心于學術特技表演,而全然不顧跟普通讀者溝通的必要性。這一現象其實是一種文化癥候:普通讀者的消失,標志著文學批評的異化。
文學批評的異化
在過去幾十年中,輕視乃至敵視普通讀者的傾向已經釀成了國際潮流,學府和研究機構的高墻內外,西方文論曲高和寡。更可悲的是,當年瓦雷里(哀嘆的扭曲世態依然存在:“有些人對詩歌從無熱腸,他們不懂世人為何需要詩歌,而且從來就不愿讓詩歌誕生,然而不幸的是,其中一部分人竟然鬼使神差地竊據了評判詩歌的權位……據以傳播自身一竅不通的東西,用出全身解數,傾盡全部熱情,其后果可想而知,只能是更加讓人恐慌。”也就是說,文學批評本應有的宗旨是要為所有文學愛好者服務(既為專業讀者,也為普通讀者),但是它如今很少為普通讀者服務。就如英國學者雅爾丁(Lisa Anne Jardine)所說,“普通讀者不復存在了”。為什么會這樣呢?
問題就出在被無限拔高的“理論”。克莫德(Frank Kermode)曾經哀嘆:“能夠指望普通讀者聽懂理論教授們高談闊論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假如理論家們跟普通讀者扯上了關系,就會覺得自己的尊嚴被冒犯,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奇怪情狀。那些理論家自詡為專家,不再對普通讀者負有義務……許多書籍被劃入文學批評類別,其供應量日益增多,可是文學愛好者中很少有人能讀懂這些書,就連專業讀者也不都懂。”同樣,奈特(Christopher J.Knight)也曾感嘆道:“(文學批評家們)有一個壞習慣,即關心理論的程度超過了詩歌或戲劇,因此他們必然會冷落文學本身,盡管后者表面上是他們的研究對象。”奈特的如下批評更為尖銳:“文學研究明顯地游離了文學本身,偏向了文學的理論化,以致我們要問:如今的理論家……究竟是文學的朋友呢,還是敵人?我們這樣提問,似乎并沒有無禮。”奈特此處所說的,就是我們在上文中所說的“文學批評異化”,它也曾遭到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抨擊:“文學批評已經遠離公共領域,躲進了大學的象牙塔,在那里變成了另一種東西。它不喜歡原先意義上的評判工作,結果變成了現在的文學理論:作為文學的一種變體,它一味迎合各種時髦的意識形態,熱衷于拉山頭,占地盤,充斥著專業話語。”
若要追根溯源,上述現象可以在柏拉圖那里找到根子。就如美國學者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所說,“文學批評始于要文學消失的意愿,柏拉圖反對荷馬的主要理由就是荷馬本人的存在”。當然,柏拉圖當初的激進主張并未阻遏文學的生長。在隨后的千百年里,文學與文學批評相輔相成、共同繁榮的情形有目共睹,但是在過去的四五十年里,“柏拉圖的傳人們再次變得強勢了”(奈特語)。這種“強勢”的后果便是“理論繁榮”。用克莫德的話說,過去幾十年可以視作“文學理論全盛期”,可是“這文學理論全盛期似乎勢必意味著對‘文學’的冷漠乃至敵視”,或者說“理論正在淹沒文學”。那么,這對文學愛好者/讀者——尤其是普通讀者——又意味著什么呢?
理論淹沒了文學,也就淹沒了廣大讀者,至少拒后者以千里之外。奈特有一句名言:“理論不僅打敗了普通讀者,而且打敗了文學。”這句話也可以倒過來說:理論打敗了文學,從而打敗了普通讀者。更具體地說,“人們實際閱讀的文學并非評論家們所討論的文學”(克莫德語)。既然如此,普通讀者聽不懂理論教授的話,也就在所難免了。倘若理論教授們意識到其中的問題,那情形還不至于太糟糕,可是“評論家/小說與小說愛好者之間的溝壑已被接受,無人想去彌合”,而“至于普通讀者為何跟我們(筆者按:指專業讀者/批評家)格格不入,則無人想要弄明白”(克莫德語)。更令人擔憂的是,上述鴻溝甚至橫亙在許多大學的文學課堂上,橫亙在學生與教授之間,前者一心想讀懂文學原著,而后者則一味地沉迷于高深理論。對于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奈特有過一針見血的分析:“理論并非簡單地需要讀者,它需要的是弟子,而尋找后者的最佳場所就是專業院校。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羅·德曼,他把教室變成了培養弟子的皮氏培養皿……凡是弟子,都不必把千百個文本讀上千百遍,而只需要某種便攜式理論,它不管應用于哪個文本,都同樣靈驗,這正好跟德曼的解構主義理論相契合,后者聲稱每個文本都是同一個文本的變體。”也就是說,德曼式的教授們根本就沒擔負起培養文學讀者的使命,更遑論對普通讀者的責任。上述問題的根子在去經典化思潮。
去經典化:文學批評異化的根源
前文提到,文學批評家有義務就文學經典價值與普通讀者達成共識。一方面,批評家有責任用經典作品去引導普通讀者;另一方面,普通讀者是檢驗經典性的最高標準。然而,自20世紀中葉以降,打著各種“理論”旗號的諸多學術流派都加入了一場針對文學經典的“顛覆性狂歡”,其理由頗能蠱惑人心,正如湯普金斯(Tompkins)所言:“經典作家的聲譽并非來自他/她作品內在的優點,而是來自復雜的外部環境。在環境復合體的作用下,一些文本得以進入人們的視野,進而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順著這一邏輯,揭示經典背后的意識形態就成了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而普通讀者最關心的經典本身及其內在審美維度則淡出了文學批評家的視野。一個連帶的后果就是普通讀者的淡出。
更糟糕的是,熱衷于“理論”的教授/批評家們不但無視上述情形,而且為之辯護。例如,卡勒(Jonathan Culler)就曾大張旗鼓地宣揚“晦澀的長處”,同時還批評有些教師慫恿學生屈服于“奉清晰為圭臬的意識形態”。言下之意,晦澀是正道,而清晰則成了邪道。既然晦澀成了正道,那么普通讀者自然就被關在門外了。卡勒在《框定符號:批評及其機構》一書中歡呼“理論”的繁榮和文學批評的“質變”。所謂“質變”,即“超越傳統文學研究的邊界”。文學批評/理論帶有跨學科特色,這本來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但是卡勒所提倡的并非僅僅跨學科,而是一直要“跨”到文學批評變質。這又從何說起呢?
這還得從卡勒的基本觀點說起:他篤信文學批評因其“跨學科特性”而變成了“一種新型的、擴張了的修辭學”。他還引用了費德勒(Leslie Fiedler)的一句話:“文學批評總是在變成‘另一種東西’,其原因很簡單——文學永遠是‘另一種東西’。”這“另一種東西”究竟是什么東西呢?卡勒又借用羅蒂(Richard Rorty)的一段話來加以說明:“從歌德、麥考萊、卡萊爾和愛默生的時代起,一種文類開始形成;它既不是對文學作品的評價,也不是觀念史,既不是道德哲學,也不是社會預言,而是所有這些東西的混合,形成了一種新文類。”然后,他接過了“新文類”一詞,給出了自己的解說:“對于這一新文類,最方便的稱呼就是‘理論’。如今,‘理論’這綽號已被用來指稱那些挑戰并重新定位思想的著作,它們表面上屬于文學領域,但是由于它們在分析語言、思想、歷史或文化時提供了關于表意的新解釋,而且具有說服力,因此它們實際上大顯身手的地方是那些文學以外的領域。”至此,卡勒所青睞的“另一種東西”已經水落石出:它原來就在“文學以外”。
細心人會發現:卡勒使用了瞞天過海之術。他把羅蒂和費德勒所說的“新文類”和“另一種東西”又變成了另一種東西,可謂此“另”非彼“另”。事實上,羅蒂和費德勒都沒有排斥文學本身。費德勒所說的“另一種東西”其實永遠是以文學為前提的:既然文學永遠是“另一種東西”,那么這“另一種東西”就永遠離不開文學,二者互為表里,可謂二律背反。同樣,當羅蒂強調“新文類”時,他強調的是“所有這些東西的混合”,其中仍然包含著文學,尤其是包含“對文學作品的評價”。然而,到了卡勒那里,文學已不復文學,批評亦不復批評——文學失去了經典性,而文學批評則變成了“理論”;批評家們不再對文學作品作全方位的評價,更無須就作品的經典性達成共識,而只要一根筋地挖掘作品背后的意識形態即可。更透徹地說,卡勒看到的不是文學作品,而只是作品中的“表意邏輯”——“表意邏輯”“表意系統”和“表意機制”等詞語高頻率地出現于《框定符號》一書。挖掘“表意邏輯”,就是挖掘所謂的“意識形態”。卡勒及其追隨者發現,一旦逮住了“意識形態”,他們的“理論”就無往而不勝。用克莫德的話說,“理論”其實只有一個法寶,即“格外擅長發現暗藏的意識形態”,或者說“總能在任何經典里發現某種駭人的審美意識形態”;因此,只要預先認定經典竊據了“寶典”——“作為儲存已知真理和通行價值觀的寶典”——這一位置,“理論”就“總能有所斬獲”。可想而知,如此一味追蹤暗藏意識形態的“理論”及其批評活動是不會把普通讀者放在眼里的。
揭露去經典化潮流的謬誤:重塑普通讀者的必由之路
以上分析表明,普通讀者不受待見,是去經典化思潮作祟的緣故。因此,要重塑普通讀者,就要從分析去經典化思潮的要害做起。概括地說,去經典化思潮的要害可以形容為“簡化兩步法”:第一步把經典的形成過程簡化為“經典化”;第二步把“經典化”進一步簡化為權力運作的結果。這兩步簡化法都把普通讀者排除在了文學批評活動之外:第一步排斥經典性,排斥文學的審美維度,這對普通讀者來說,無異于釜底抽薪——普通讀者最敏感、最有發言權的地方正是審美維度;第二步則干脆剝奪了普通讀者對于經典化的參與權。有鑒于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為經典性辯護,并審視普通讀者在經典化過程中的作用。
要為經典性辯護,就要先考察那些否定經典性的人拿出了什么理由。否認經典性,否認文學具有獨特的內在本質,否認它的審美維度,把它等同于一般的“寫作形式”或任何非文學文獻,這一觀點有一個極具煽動性的理由,即“平等”和“民主”。用新歷史主義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的話說,“社會能量的循環”給了所有文本“平等的認知潛能”。基于這一觀點,格林布拉特在解讀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時,無視該劇的審美維度,一味地強調該劇的檔案功能或“記憶”功能,即幫助后世記住“在伊麗莎白一世時代和詹姆士一世時代的英國社會,處于經濟生活和意識形態中心的是……勞動者和統治者之間的區別”。針對這種閱讀策略,美國學者科爾巴斯(E.Dean Kolbas)曾尖銳地指出:“把《暴風雨》這類經典文藝作品的內容簡化為純粹的文本性,無異于把人類的痛苦也僅僅當作往昔的文本現象,好像這些作品除了檔案價值之外,對現今人類社會再無意義可言。這樣做不僅是違背良心的,而且危害了文學藝術描述愿景的功能——文學藝術能展望脫離了不公和殘酷現象的未來社會,而這樣的愿景非依靠想象力不可。”科爾巴斯此處強調的就是經典性。
當然,經典性的內涵十分豐富,而在這諸多內涵中,審美愉悅是先決條件。張隆溪就曾說過:“道理本來很簡單:如果你在文學中找不到愉悅,就不要假裝是文學評論家——但是在如今的特殊時期,對審美愉悅的強調顯得尤其重要,因為現在文學作品經常被當作社會、歷史或政治的文檔使用,借以批判某些話題,或達到某些目的。”我們還須補充一句:審美愉悅的試金石恰恰是普通讀者——如果一部作品能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普通讀者心中喚起審美愉悅,那么它就滿足了經典性的先決條件。
至于普通讀者在經典化過程中的作用,一個關于狄更斯的例子就頗能說明問題。在小說《老古玩店》臨近殺青時,狄更斯每天都會收到讀者的來信,不僅來自國內,而且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普通讀者們對小說女主人公耐兒的故事反響之熱烈,從狄更斯的一次演講中可見一斑:“這位早年夭折的小女孩兒在大西洋彼岸竟引起了如此濃厚的興趣……在英格蘭時,我曾經收到許多來自遠在地球西邊的美國的信件;寫信者都居住在沼澤地帶和密林深處的那些小木屋里。許多被斧頭和鐵鍬磨練得非常堅定的手,許多被夏日驕陽曬黑了的手,拿起了筆桿子,向我敘述一個個有關普通人家悲歡離合的小故事。……許多母親——我現在已不是成個成雙地數她們,而是成十成打地數她們——也同樣給我寫信……”透過這字里行間,我們看到的是小說家和普通讀者之間的一種健康關系,一種真誠的、雙向的心靈交流。與之相比,那些商業炒作,那些權威機構的“蓋棺論定”又能算什么呢?
結語
總之,作為審美愉悅的試金石,普通讀者在文學批評活動中的地位不可小覷。在文學批評異化日益嚴重的今天,還普通讀者以應有的地位,已成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