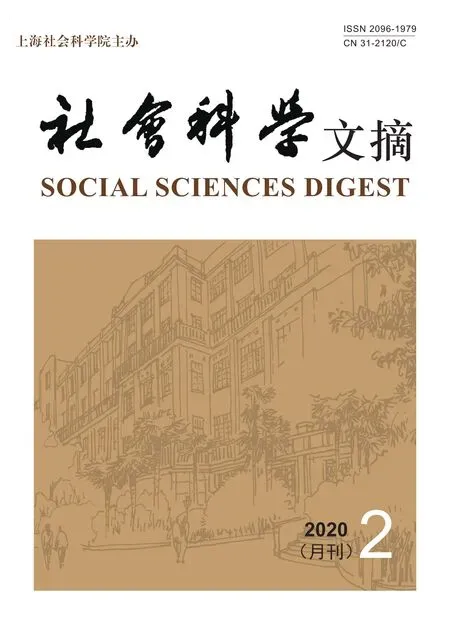“去耕種自己的園地”
——關于回歸文學本位和批評傳統的思考
文/張伯偉
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新編了一種出版物——《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在第一輯的卷首,刊登了一組總題為“‘十年前瞻’高峰論壇”的筆談,匯集了當今活躍在學術研究第一線的21位老中青學者的發言稿,在一定程度上,將其視作對當下古代文學反思的代表,也許是合適的。在目前的古代文學研究中,以文獻擠壓批評,以考據取代分析,以文學外圍的論述置換對作品的體悟解讀,已是屢見不鮮的現象,究竟應該如何進行“文學”研究,竟成為橫亙在古代文學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難題。以上反思代表了古代文學學界對當下研究現狀與存在問題的某種擔憂,但較真起來講,上述意見不應該是文學研究中的老生常談嗎?而當一個老生常談變成了研究界普遍糾結的問題時,事情恐怕就不那么簡單。有學者指出這種現象與某種“傳統偏見”相關,但傳統是多元的,有一種傳統偏見,往往就會有另一種針對此偏見的傳統。又如把文學的藝術性研究看成“軟學問”固大謬不然,但這是否也暴露了長期以來文學研究中的某些弊端。由于缺乏對文學本體研究的理論思考和方法探究,“純文本”研究往往流于印象式批評,即便是人們視為典范的聞一多的“唐詩雜論”,在被敏銳的感覺、精致的表述掩蓋下的,依然是“印象主義”的批評方法。而考據與辭章、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如何,孰重孰輕、孰高孰低,其爭論辯駁也由來已久。因此,對上述問題作出清理,以求在一新的起點上明確方向、抖擻精神、重新出發,不能說是沒有必要的。本文撰述的宗旨,一方面是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的針砭,一方面是對現代學術中某種傳統的接續,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中國批評傳統的再認識。
從一重公案說起:實證主義文學研究批判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針對長期存在的僵化和空疏,學術界開始追求學術性和多元化。但到90年代之后,中國的人文學界逐步形成了如李澤厚描繪的圖景且愈演愈烈:“九十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王國維、陳寅恪被抬上天,陳獨秀、胡適、魯迅則‘退居二線’。”與之密切相關的,就是文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的死灰復燃,并大有燎原之勢。近年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的課題指南中,類似“某某文獻集成與研究”的名目屢見不鮮,雖然名稱上還帶了“研究”的尾巴,但往往局限在文獻的整理和考據,并且多是一些陳舊的文獻匯編影印。這多少反映出學術界的若干現實,也多少代表了學術上的某種導向。
徐公持在總結20世紀最后20年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時,舉出當時老一代學者“再現學術雄風,其中錢鍾書、程千帆堪為代表”。如果說,21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仍然有對前人“照著講”“接著講”甚至“對著講”的必要,那么,我們最迫切、最需要接續的就是由錢鍾書、程千帆為代表的學術傳統,并且在理論和實踐上向前推進。
從批評實踐看文學、史學研究之別
在20世紀中葉,陳寅恪探索和實踐了“以詩證史”的研究方法。從文學理論的立場看文學和歷史的關系,一種人們熟悉的看法就是認為文學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反映,因此,理解作品就要將其置于歷史背景之中。但文學中展現的歷史,與實際發生的歷史并不一定吻合,為了研究歷史而利用文學材料,就會對文學描寫加以糾正,這便屬于歷史研究。而為了糾正文學描寫,就需要對史實(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作考據,轉而輕忽甚至放棄文學批評。即便無需糾正,但如果僅僅將作品看成文獻記載,也談不上是在進行文學研究。當陳寅恪用“以詩證史”的方法去研究歷史的時候,他心目中的意義就在于“可以補充和糾正歷史記載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糾正”,被他“糾正”的往往不是歷史記載,而是作品描寫。其為史學研究而非詩學研究,不待細辨即可知。但陳寅恪對文學極為精通,故其論著也時時發表對文學研究的卓見,且深受學者重視。
在文學研究上,錢鍾書對陳寅恪沒有什么吸收。程千帆則深受陳寅恪的影響,他對陳氏學術方法、宗旨、趣味以及文字表達的理解,遠勝一般。但程千帆的學習方式,不是形跡上的亦步亦趨,而是在把握其學術宗旨的前提下,根據自己的研究內容,在學術實踐中“有所法”又“有所變”,將重心由“史”轉移到“詩”。他們之間的區別,是一個很好的辨析史學研究和詩學研究之差異的個案。如上所說,中國古代詩歌往往包括時間、人事、地理,所謂“人事”,不僅有時事,也有故事,所以在研究工作中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對史實的考證。若是史學研究,就會判斷相關的某一記載(無論是歷史文獻還是文學作品)是出于“假想”或“虛構”,因而是“錯誤的”或“不實的”。但若是詩學研究,史實的考證就僅僅是提供理解詩意的背景,而非判斷詩人是否實事求是的律條。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程千帆與陳寅恪的差異。如果從作品出發,又回歸到作品,就會尊重詩的特性,學習并堅持對詩說話,說屬于詩的話。文學批評不排斥甚至有時也需要考證,但僅僅以此為滿足,并未能完成文學批評的任務。
關于文學研究中的考據與詞章,程千帆還說:“詞章者,作家之心跡,讀者要須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氏之言,實千古不易之論。”其所引孟子云云,見于《孟子·萬章上》,以“千古不易之論”為評,似可表明,現代學者的文學批評,也有自覺接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之某一傳統者在。由此重新思考我國兩千五百年文學批評之發展,也可以獲得一些新的理解和認識。
中國文學批評的另一傳統
對中國文學批評作出整體描述,是現代學術形成后的產物。當時人多以19世紀以來的歐美文學觀念作為參照系,由此導致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結論,即中國的批評傳統以實用的、道德的、倫理的、政治的為主要特征,雖然也含有審美批評,但在整個批評體系中似乎僅僅偏于一隅。在我看來,這是對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的簡化和僵化,尤其是因為缺乏與西方批評傳統的整體對應,因而遮蔽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另一傳統——審美批評(包括非常豐富的技術批評)的傳統。盡管已有學者對此作出了呼吁和闡發,但仍有進一步呼吁和闡發的必要。面對今日文學研究的困境,如果我們要從中國批評傳統中尋找資源,對于這一隱而未彰的傳統,有必要予以揭示。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孟子的貢獻可謂極大。“文學批評”是一個外來的名詞,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相應的則是由孟子提出的“說詩”的概念,文學批評家也就是“說詩者”。什么是“說”?我們不妨看看中國最古老而權威的解釋——許慎的《說文解字》曰:“說,說釋也。”段玉裁為我們作了進一步的闡明:“說釋即悅懌,說悅、釋懌皆古今字,許書無悅、懌二字也。說釋者,開解之意,故為喜悅。”因此,西方的“文學批評”形成一種理性判斷的傳統,而中國的“說詩”是一種由情感伴隨的活動。
孟子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貢獻,簡言之有二:一是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說詩方法;二是對“說詩”和“論史”作出了區分。這兩者也是有聯系的。孟子說詩方法的要義在于:首先,要尊重詩的表達法,為了發抒情志,語言上的夸張、修辭中的想象是必不可少的,這是文學的特性;其次,詩歌在語言上往往夸張、變形,詩人之志與文字意義也非一一相應,正確的讀詩方法,就是“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讀者的意去迎接詩人的志,即“以意逆志”。所以孟子之“說詩”,是以認識詩語的特征為出發點,最終也回到詩歌本身。說詩如此,論史則不然。《孟子·盡心下》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他認為武王伐紂,是“以至仁伐至不仁”,怎么可能殺人無數,以至于血流漂杵呢?從語言修辭的角度言之,“血流浮杵”只是一種夸張,以形容死者之多。但在孟子看來,作為記載歷史的《尚書》,不能也不應有此種修辭。他在實際批評中體現出的說詩和論史的區別,具有重要的意義。張載曾對此作了對比:“‘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一為詩,一為史,文字性格不同,所以讀法也不同。“說詩”與“論史”不同,這是孟子的千古卓見。
中國早期的審美批評至《文心雕龍》作一總結,這就是“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首先是一種感情活動,在獲得真知灼見之后,內心也必然充滿喜悅,甚得傳統“說詩”之髓腦。而經鍾嶸《詩品》揭橥的“詩之為技”的觀念,到了唐代,衍伸為一系列從詩歌技巧出發的詩學著作,涉及聲律、對偶、句法、結構和語義,為分析詩歌的主題、情感等提供了大量的分析工具和評價依據。但自宋代開始,這一情況發生了較大改變。
不識詩語特征,拘泥于史實從而導致對詩歌的誤判,在宋代以后屢見不鮮。比如杜牧《赤壁》詩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許顗《彥周詩話》譏刺道:“孫氏霸業,系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涂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胡仔也附和其說,認為“牧之于題詠,好異于人”,乃至“好異而叛于理”。他們都自以為熟諳史實、深識道理,便可以高屋建瓴、義正辭嚴地批評詩人,殊不知正如四庫館臣的反駁:“大喬,孫策婦;小喬,周瑜婦。二人入魏,即吳亡可知。此詩人不欲質言,變其詞耳。”“不識好惡”的“措大”正是批評家自己。其共性就是不以文學的眼光看文學,面對著詩卻說著非詩的話,尤其是這些議論有時還出于名人之口,這就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古代的說詩傳統。從審美(如情感、技巧)出發對詩歌作批評的傳統,也就被壓抑成一股雖未中斷但卻易受忽略的潛流。
現代學術傳統:理論意識與比較眼光
如果將錢鍾書、程千帆的學術傳統合觀并視,我想舉出兩點對今日文學批評尤其是古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的學術遺產。
第一,從作品出發上升到文學理論,以自覺的理論意識去研究作品。錢鍾書自述其“原始興趣所在是文學作品;具體作品引起了一些問題,導使我去探討文藝理論和文藝史”,其《通感》解決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程千帆則強調“兩條腿走路”的原則:“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二是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后者則是古人所著重從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來。”雖然兩種方法都是需要的,但后者在今天“似乎被忽略了”。為此他探討了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的問題,試圖“在古人已有的理論之外從古代作品中有新的發現”。在對具體作品的研究也就是文學批評中,中國學者往往不太在意理論問題。錢鍾書指出:“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幾乎是什么理論都不管的。他們或忙于尋章摘句的評點,或從事追究來歷、典故的箋注,再不然就去搜羅軼事掌故。”“尋章摘句的評點”最典型的做法就是鑒賞型的喝彩或譏諷,尋求出處或軼事掌故則多半是為“考據”服務的。程千帆對這樣的文學批評也有不滿:“那就是,沒有將考證和批評密切地結合起來。……這樣,就不免使考據陷入煩瑣,批評流為空洞。”而造成這兩種現象持久不衰的原因,就是對理論的敵視或輕視。程千帆很重視文學理論。20世紀40年代初,他在任教武漢大學和金陵大學的時候,講授古代文論,就編為《文學發凡》二卷,具有以中國文論資料建立文學理論系統的雄心。錢鍾書同樣非常重視文學理論,不僅在他的著作中廣泛征引西洋文學理論著作,而且直接翻譯過歐美古典和現代理論家的論著,其中較為容易看到的就多達35家。
第二,在文學范圍內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批評,使民族文學的特性通過比較而具備文學的共性。同時,揭示了共性也依然保持而不是泯滅了各自的特性。在這一方面,錢鍾書表現得更為突出。1945年錢鍾書用英語作了一個題為《談中國詩》的演講,在結束部分說:“中國詩并沒有特特別別‘中國’的地方。中國詩只是詩,它該是詩,比它是‘中國的’更重要。”一般人談中西文化,因為從外表上看差異大,于是就大談其差異,錢鍾書偏偏能看到其中的“同”。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詩”在文學的框架中發現了“同”,又在各自的文學中保持了“異”。眾多的古代文學研究者,在面對西方文學和文學理論的時候,總是強調中國文學的特殊性和差異性,所以只能在古代文學甚至不能在中國文學的范圍里討論問題。
作品層面以外,還有理論層面。1937年錢鍾書寫了《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里面就談到,“中國所固有的東西,不必就是中國所特有的或獨有的東西”;中西文學理論有差異,但“兩種不同的理論,可以根據著同一原則。……雖不相同,可以相當”;最后歸結到“這個特點在現象上雖是中國特有,而在應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們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廣到西洋文藝”。他通過中西文學理論的比較,拈出異同,彰顯特色。這是從中國出發看西洋,又從西洋回首望中國。他希望中國文學作品能夠走向世界,成為人類的精神財富和文化修養,抒發的是一個中國書生的夢想。我們需要走出的第一步,就是改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偏于一隅的狀況,這也需要研究者改變自我封閉的心態。
余論
文學家當然有其社會、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訴求,但這一切都要通過文學訴求來實現。所以,文學批評也只能以對其文學訴求的回應為出發點,否則,既證不了史,也談不了藝。誰能以“白發三千丈”和“飛流直下三千尺”的對比來證明李白的愁發比廬山的瀑布長十倍呢?在今日古代文學研究的再出發時,我們最應接續的是錢鍾書、程千帆為代表的學術傳統,這不僅因為他們都針對實證主義和印象式批評予以糾偏,堅持面對文學說屬于文學的話,而且因為他們的珍貴的學術遺產,也已經為我們在探索之路上的繼續前行樹立了典范。
文學批評是一門學問,是一門獨特的知識體系。拋棄了實證主義,超越了文獻考證,文學批評有其自身的知識系統,也需要不斷更新自身的知識儲蓄。讓我們再聽聽韋勒克的忠告吧:“我們并不是不再那樣需要學問和知識,而是需要更多的學問、更明智的學問,這種學問集中研究作為一種藝術和作為我們文明的一種表現的文學的探討中出現的主要問題。”這讓我想起了另外兩位中外先哲的遺訓,一位是中國的孟子,他說:“人病舍其田而蕓人之田。”放棄自家田地不種,偏偏去耕耘他人之田,在孟夫子看來已經成為某些人的“病”。另一位是法國的伏爾泰,他筆下的“老實人”在歷經人間生死榮辱之后,終于在最后幡然醒悟道:“我們還不如去耕種自己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