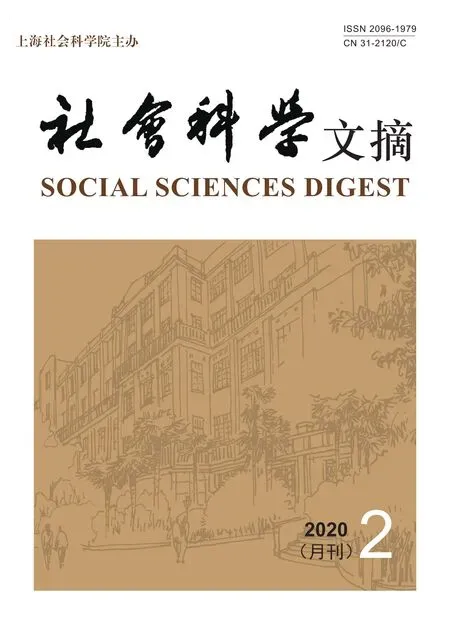理論研究與實證探討的基本區別
——以古史探索為例
文/易建平
近來湯惠生發表長文,將中國考古學近幾十年發展的推動力,總結為在以夏鼐為代表的“實證派”和以蘇秉琦為代表的“理論派”兩個不同研究取向之間的互動。湯惠生認為,夏鼐的實證派多采用歸納法,歸納在先,而后求理;蘇秉琦的理論派則倚重演繹法,先建立理論,然后據以對具體的研究對象進行分類概括。
關于這兩家研究方法總結的對錯不在此討論。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兩家分別以“實證”與“理論”名派,容易給人印象,一般意義而論,實證研究必須先進行事實歸納,而理論探討則可以先建立學說,然后給研究對象帶套子。湯惠生本人應該未必愿意讀者作這種解釋;他本意應該是專指夏鼐與蘇秉琦兩人不同的研究取向而已。遺憾的是,僅就文本而言,湯惠生的這種辨析確實又明確指向一般意義上實證研究與理論探討各自在基本方法上的區別。更為重要的是,湯文文本導致的這兩種理解,確實在中國學術界尤其廣義的史學界擁有相當程度范圍的共識。因而,我們下面就一般意義上這兩種研究在方法上的基本區別進行討論,看來不無意義。本文尤其針對的是,廣義史學界的這種共識。
歸納法的基礎作用問題
學術界通常所言實證研究,其實也就是指具體的個案研究,或者曰,微觀研究。相對而言,理論研究是一種宏觀研究。兩者在基本方法上本無本質區別,歸納法在其中的作用都同樣重要。甚至,可以認為,宏觀的理論研究之基礎首先就是歸納法。理論的創立,絕不可能僅僅依靠天馬行空式的想象,絕不可能僅僅使用所謂義理來進行演繹,尤其是,20世紀以來,科學在方法上的要求越來越嚴格之后。理論的創立過程一旦開始,也就是微觀材料或者湯惠生所言實證材料歸納的開始。同樣,理論創建工作的完成或終結,都難以離開微觀材料的檢驗。使用波普爾的語言來進行描述就是,宏觀的普適性理論隨時都有可能被任何一件實證材料或微觀材料所“證偽”;理論只有在未被證偽之前,方可并不“正確”地稱之為“正確”。故而,湯惠生所言兩者不同,用于區別夏鼐與蘇秉琦之兩種研究取向或許可行,用于劃分一般意義上的實證研究或微觀研究與理論探討之基本方法,則是一種巨大的學術誤解。
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或微觀研究的實質區別,與其說是在根本的方法上,還不如說首先是在所涉及研究對象的規模上。通常的微觀研究,比如,研究某一只天鵝羽毛的顏色,研究某一個特殊時空范圍內發生的事件,我們的學術界稱之為實證研究。給所有天鵝羽毛的顏色下一個抽象的定義,總結所有那類事件出現的共同規律,我們通常稱之為理論研究。但是我們往往忘記了,第二種宏觀的研究,只有在所有第一種個案研究的基礎之上,理論上才有可能實現。它絕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只要研究了一只或幾只天鵝羽毛的顏色,研究透了某個或某幾個相類似的事件,就可以進行所謂的義理演繹,下出所有天鵝羽毛都是白色的擁有百分之百肯定性的定義,總結出對所有尚未歸納的類似事件都適用的所謂普遍規律。或者,僅僅研究了一個或幾個對象之后,就做出結論認為,世界上,只有那一只或幾只天鵝羽毛的顏色是白色的,那個或那幾個事件的出現是獨一無二的。真正的理論研究,理論上必須認真對待所有天鵝羽毛的顏色,仔細探討世界上所有時空范圍內的相類似歷史事件,才有可能下出一個普適性的定義,總結出來一條普遍規律,或者,作出一個獨占而排他性的結論。
正因為有了研究對象規模的區別,微觀研究與宏觀的理論研究,隨之出現了另外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區別,那就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把握程度。微觀研究的對象數量十分有限,研究者相對容易掌握。宏觀的理論研究就不一樣了,它的研究對象規模通常很大,有的時候幾乎是無限的大,以至于研究者實際上根本無法完全把握。
這就往往導致了兩種研究更為重要的一個區別,結論確定性的不一樣。微觀研究者較為容易把握自己的研究對象,因而,研究結論相對更為容易確定。比如,研究一只或者幾只天鵝羽毛的顏色就是如此。理論研究工作就不一樣了,研究者很多時候都難以把握自己規模太大的研究對象,有的時候根本就是完全無法把握的,因而,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結論的確定性,只能隨著其對研究對象規模把握程度的減少而減少。比如,給所有天鵝羽毛的顏色下一個定義就是如此。
理論研究難也就難在這里。人的能力說到底是十分有限的,而研究對象的規模則常常過大,有的時候甚至可能是無限的大。這是一對根本的矛盾,有的時候甚至是無法解決的矛盾。人之有限的能力,無法把握過大甚至無限規模研究對象的時候,怎么可能獲得微觀研究那樣更具確定性的結論呢?這也許就是學者有時候將微觀研究等同于實證研究,而將宏觀的理論研究看作是非實證的義理演繹的原因。在歸納法無法窮盡所有研究對象的時候,研究者確實不得不經常在不完全歸納基礎之上使用“義理”進行演繹。不過,這絕不是說,理論研究可以不需要進行微觀材料的歸納,不需要建立在個案材料實證研究的基礎之上;更不是說,理論研究本身不是實證研究,而僅僅是“義理”演繹。
宏觀的理論研究不同于微觀研究的地方還在于,研究者應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因而,也應該清楚地知道自己研究結論的確定性,將會隨著自己所掌握對象比例的減少而減少,結論隨時可能會被自己未曾掌握的材料所推翻。這也應該就是為什么,在英語中,理論(theory)這個詞是與假設(hypothesis)同價的;它絕非真理的同義詞,就像在中國話語系統中經常被人所理解的那樣。其根源,我以為,大頭就在于此,就在于理論研究對象的規模很多時候都是研究者所難以完全把握所導致的研究結論難以獲得微觀研究結論那樣程度的確定性這一點上。
為簡單計,還是以天鵝羽毛顏色的研究舉例。如果是微觀研究,研究對象只是數量十分有限的天鵝,研究者很容易研究透徹它們或者它們羽毛的顏色,下出較為確定的結論。如果是宏觀的理論研究,對象就是古往今來地球上所有天鵝羽毛的顏色了,這幾乎就是無限的了,實際上也是研究者所無法全部掌握的了。今天,即便已經研究了所有可能見到的天文數字的天鵝,但你恐怕依舊難以確定,除了白色的之外,是否還會在什么時候,飛出來一只黑色的天鵝,甚至紅色的、藍色的或者其他什么顏色的天鵝。在這種把握基礎之上的研究結論,依舊無法達到微觀研究結論那種最高可能百分之百的確定性。你依舊無法肯定,何時會有一只甚至更多的其他顏色羽毛的天鵝出現,推翻你凡天鵝都是白色的結論。事實也是如此。很長時間以來,大家都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但是,澳大利亞黑天鵝的發現,推翻了人類這一延續很長時間的認識。既然如此,既然無人可以把握過去和現在所有天鵝羽毛的顏色,要對所有天鵝羽毛的顏色下出抽象的定義,其確定性當然就無法與關于數量有限天鵝羽毛顏色的微觀研究結論的相比肩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所謂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也就是微觀研究的基礎都是歸納法,它們在根本的方法上并無實質意義的不同。它們的區別更在于:一是研究對象的規模;二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規模的把握程度;三是由此導致的研究結論的確定性。其中,對于理論研究者,最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類能力的有限性,研究對象規模的過大甚至可能的無限性,這一矛盾所導致的研究結論確定性方面的缺陷。
他人研究成果的利用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區別,也是源于人類自身能力的有限性限制。我們進行微觀探討時候,對象更為容易研究透徹,這也是其結論更為可靠的原因之一。并且,研究者的結論可以完全或者主要建立在自己一個人的實證檢討基礎之上,這當然更可以保證結論的可靠性。而宏觀的理論研究就不同了。首先,一個人難以像做微觀研究那樣,對每一個案例都檢討得那么細致。其次,尤其是,他難以做到自己親手來檢驗所有的對象。在理論研究的實際過程當中,研究者所謂的處理或者歸納盡可能多的實證材料,其實,更多時候是處理或者歸納他人的微觀研究成果。這就難以保證,他人研究的可靠性與自己親自進行微觀檢驗的可靠性一樣,由此大大增加了自己所下宏觀結論犯錯的可能性。
在人文學科領域,這個風險更大。研究者檢驗一只天鵝羽毛顏色的能力,足以讓他檢驗所有天鵝羽毛的顏色。探討人類歷史演進的規律,就遠不是那么簡單了。一位研究者可以精通甲骨文或金文,并通過這類特殊的技能精通中國商或西周的歷史,但他絕無可能借助自己的這些專業能力,親自研究古代埃及、兩河流域、印度、希臘、羅馬與瑪雅等社會,以從中歸納概括出來它們演進的共同規律。要通過原始文獻親自做任何一個這一類地區社會的研究工作,首先都需要學習它的文字,需要掌握古代埃及象形文字、蘇美爾與阿卡德楔形文字、梵文、希臘文、拉丁文或者瑪雅象形文字,等等。一兩個地區甚至再多點地區,也許有天才可以掌握它們全部的古文字。但要掌握所有相關地區的古文字,就不是任何一位單獨個體的能力所可以達到的了。僅僅這一點,就足以阻礙研究者親自檢驗所有的相關研究對象。何況,其中許多地區都有浩如煙海的原始文獻,比如古代埃及,比如古代兩河流域,僅僅某一個時段某一個有限空間的歷史,文獻就多得足以耗盡一位研究者的一生。不得已,人文領域理論研究僅僅這方面的困難,就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利用他人風險系數較高的微觀研究成果,從而增加自己結論犯錯的可能性。
退一步,先不說這種風險。在人文學科領域,要想充分利用好他人的研究成果,實際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定有一位美國學者,研究酋邦與早期國家起源與演變的規律,熟悉了中國以外所有地區的案例之后,他還要面對中國的例子。理論上,他應該自新石器時代開始,至少研究到戰國群雄競起。最好的辦法是,他來親自研究凌家灘、牛河梁、良渚、石家河、石峁、陶寺、二里頭、成都平原諸古城、丹土、堯王城、兩城鎮、商、西周與東周諸國等考古材料,親自研究甲骨文與金文材料,親自研究《尚書》《左傳》《國語》《逸周書》《竹書記年》《史記》與諸子百家等傳世文獻材料,親自研究后來出土的簡帛材料。但是,他看不懂中文,不僅不能直接翻檢原始材料,而且不能直接閱讀中文的研究成果,而只能借助于張光直、許倬云、夏含夷、劉莉等人十分有限的英文著述來研究。這就大大限制了其閱讀范圍。且不說第一手原始材料,即便是他人研究成果,他也無法像能夠直接閱讀中文著述那樣,獲取那么廣泛的更多更為前沿的信息,尤其是新發現材料的信息。這就大大削弱了他自己理論研究的實證基礎。
其實,面對的困難還遠遠不止如此。比如,一位美國人,研究酋邦起源與演化的理論問題,理論上,中國例子,不僅首先需要熟悉史前與夏商周各自早期的歷史,而且需要熟悉后來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如匈奴、夫余、烏桓、鮮卑、吐蕃、契丹、蒙古、女真等興起的歷史,最好還要研究更多的當今仍舊活躍的少數民族如彝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瑤族、傣族、傈僳族、仡佬族、高山族、拉祜族、佤族、納西族、仫佬族、景頗族、毛南族、撒拉族、布朗族、鄂溫克族、怒族、基諾族、德昂族、獨龍族和珞巴族等社會演化的歷史。且不說這些方面是否都有英文著述,更不必說,是否都有充足的英文著述。即便他中文很好,真要都吃透那么多他人的研究成果,花費一生都不能說多。這還僅僅是中國個案。理論上,世界各個地區相關的他人研究著述都需要如此去熟悉。理論上,除了他人的中國研究成果之外,目前探討酋邦社會的演進規律,研究者至少還需要處理古代埃及、兩河流域、赫梯、印度、希臘、羅馬等傳統關注地區的相關研究著述,還要熟悉更為晚近討論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非洲、澳大利亞、東南亞與太平洋諸島嶼上早期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成果。說實話,即便他能力超常,要對那任何一個領域的研究著述都搜集全面,然后進行誰更具權威的判斷,需要做的工作都已經太多。何況,他面對的,理論上是所有那些地區所有的相關研究成果。這就可以想見,做這一類宏觀的理論研究,困難會有多大。
理論研究可能遇見的上述種種困難,的確不易克服。我們尤其清楚,只要沒有透徹檢討過所有的對象,就不能保證,理論研究結論獲得像微觀研究結論那樣的可靠性。但是,這并非是說,困難反正難以克服,研究者因此反而能夠偷懶,在僅僅掌握數量十分有限的實證材料(包括他人的研究成果材料)之后,便可以使用“義理”演繹出來無限確定性的結論。如果有人真那么做,那是在做文學,不是在做科學;即便偶爾蒙對了,那也與嚴格意義的科學研究相距甚遠。科學雖然知道研究者的能力有限,但也要求他盡可能多地掌握微觀材料。對于理論研究來說,一百個研究對象,五十個研究對象,建立在這兩者歸納基礎之上結論的可靠性,絕非等同。可以肯定地說,一個理論,歸納的微觀材料(即便都是他人的研究成果材料)越多,可靠性就越大。這激勵著研究者互相競爭,在進行理論探討時候,為了提高自己結論的可靠性,盡可能多地把握研究對象。在理論研究領域,一百步是肯定可以嘲笑五十步的。
這也就是為什么,許多理論研究的大家,窮盡一生,都只在很少幾個問題上打轉,而其傳世者,往往也只有不多的成果。尤其是進入了20世紀以后。為了盡可能扎實地確立自己的理論,他們需要涉及的領域,實在太多;需要檢驗的材料(包括他人的研究成果材料),實在太多。而且,即便像他們那樣工作,人之有限能力與研究對象過大之間的矛盾,還是會充分表現出來,使得其辛苦建立理論的可靠性,難以與微觀研究結論的相比肩。
在實際的工作當中,許多學者不像那些大家一樣,按照理論研究本身需要的那樣廣泛地進行閱讀。許多時候,許多學者都只是碰見哪種材料利用哪種,根本就不在意其可靠性如何。其實,不少人本來也未下功夫去了解自己的所謂研究應該擁有哪些基礎,需要哪些材料。就是這樣的態度與基礎,有些人往往還急于同前人劃清界限,建立自己的所謂“理論”。這種情況,在中國學術界尤其嚴重。尤其是在涉及到國外理論或者材料的時候,有些人所謂發現的材料,經常只是在某位外文系老師帶著學生偶爾在錯誤百出翻譯過來的著作中碰巧遇到的。他們在做宏大理論研究的過程當中,絕未就其應有的理論與微觀基礎系統摸過底。就是這樣,他們還急于同碰巧遇見的外國人撇清關系,急于建立解釋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所謂“自己的”“理論”。可想而知,這種所謂的“特色”理論研究,有多少可靠性。
理論研究與實證探討互動等問題
這就遇到一個問題。既然理論研究的微觀材料基礎是如此薄弱,因而,導致結論犯錯的風險如此之大,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學者耗盡一生前仆后繼地進行普適性的理論探索呢?
原因當然首先在于,普適性規律的認識在人類實際活動中的無比重要性。自古以來,人類就有意無意地在探索事務(事物)運行的普適性規律。離開對可以預見事務(事物)運作的普適性規律的認識,人類都無法進行基本的生存活動安排。比如,假設不能肯定太陽每天都升起,人類就難以準備下一個白天行動的計劃。假定不知道某些動物的活動規律,就不知道在什么時候哪個地方去捕獵它們。假定不知道季風運行的規律,蒸汽機驅動船舶之前的人類就無法計劃某個方向的遠航。假定不知道尼羅河漲落的規律,古代埃及人怎么可能進行耕作安排。假定人類本身的行為沒有規律可言,人與人互相之間就無法判斷敵友,人類就不可能形成穩定的社會。總而言之,人類的活動都是建立在各種普適性規律的認識基礎之上的。認識的普適性規律越多,人類掌握世界的能力也就越大。或許正是這種普適性規律的重要性,引起了人類對其進行理論探索的好奇心。
就研究本身而言,理論探討雖然是從微觀研究的歸納開始的,但是,進行微觀研究離開普適性理論其實也同樣寸步難行。普適性的理論是我們進行思考和研究最為重要的工具,它們越多越清晰,我們對微觀對象進行探求就越容易。其實,進行微觀研究時候,我們的工作之所以能夠展開,都是有意無意使用了許許多多普適性概念與系統理論工具的原因。比如,研究商人王權的起源與發展,其中,至少“人”、“王權”、“起源”與“發展”,都是這樣一種普適性的概念工具。此外,“商”也是一種有限范圍的集合概念,因此也是具有一定范圍的抽象性或普適性的概念。本質上,語言本身就主要是由抽象的概念組成的,離開抽象也就是普適性的概念,人類難以進行思考與交流。同樣重要的是,研究商人王權的起源與發展問題,首先必須采納一些較為系統的普適性的理論,來假定什么樣的社會具有什么樣的權力結構,以及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個人或者一群人的行為偏好。離開這種概念與系統理論的工具,我們在面對研究對象時將會一籌莫展。
還有,也在于這種探索也存在著成功或者愈益接近成功的可能性。對于個人來說,力量的確有限。但是,無數研究者的力量前仆后繼地投入,卻有可能使得普適性理論探索的成果得到不斷的修正(推翻也是一種修正),因而使得后來者具有愈益增大的解釋效力。理論研究的這種時間模式,在實際的過程當中,常常展現出來一部漫長的歷史畫卷。比如,對人類社會不同權力結構形成與發展演變的根本的普適性原因的探討,亞里士多德解釋為希臘人天生愛好自由、東方人天生懦弱習慣于奴役,孟德斯鳩認為是地理環境所致,魏特夫概括為雨水農業與灌溉農業引發,近來謝維揚又總結為部落聯盟模式與酋邦模式的影響,我本人的解釋是社會規模的不同,等等。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學者,不斷地利用新的實證材料修改補充甚至推翻他人的結論,努力建立自己的理論。大體上,隨著時間推移,越晚的學者,在同一個問題的不同答案展現出來愈益堅實的微觀或者實證研究基礎,因而往往更具可靠性、更具解釋效力。
此外,理論研究旨在解決涉及到的所有相關微觀研究者都可能會感興趣的共同問題,故此,它可能會吸引許多人在其專業范圍領域對其進行檢驗,尋找其在某個方面的缺陷,或者進行補充,進而可能進行修正,進而可能使得它(在肯定的情況下)或者其他理論(在否定的情況下)解釋的效力更大。微觀研究者的參與討論,無論結果是肯定還是否定,從長時段看,最終都有可能增強理論研究解釋某一問題的可靠性。
不過,理論研究工作吸引著不同專業范圍微觀研究者對其進行討論,這種現象也導致了相應問題的產生。來自某個領域的挑戰者熟悉的往往只是自己狹窄的專業,而他討論的理論又必然會涉及到許多他并不了解的其他專業,故而,他的意見,無論贊同還是反對,效力往往都會受到自己專業范圍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之下,微觀研究領域的專家們對普適性理論發表的意見,很多時候都像盲人摸象,誰也不容易說服誰。因此,凡是理論問題,學術界經常是爭論不止,歷經百千年而難以獲得共識。當然,這主要是就人文學科領域內的理論討論而言的,正是在這個領域,不同專業的微觀研究者之間互相才那么隔膜。在自然科學領域,普遍性規律建立的不同專業基礎,相對容易可以抽象成為不同專業的研究者都可以讀懂的數學語言或者實驗語言。
結束語
綜上所述,本文核心結論是,在基本方法上,理論研究與實證探討并無根本區別。離開歸納法,理論探討同樣寸步難行。
當然,我們所說理論研究,是指那種開創性質的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很多時候所謂理論研究,其實就是套套,就是將十分有限的微觀材料套進流行的理論之套當中。尤其是,套進某些經典作家某一部分分割出來的其實是在當時特殊場景之下的特殊論述甚至片言只語當中,這一直是幾十年來流行的做法。很多時候,某些人甚至不管其適用的所謂理論甚至片言只語是否過時;不管新發現的許多實證材料,是否已經否定了它(們)。這種所謂的宏觀研究當然就與微觀研究或者實證研究在方法上擁有巨大的區別。這當然就可以不需要使用歸納法,不需要使用數量巨大的微觀或者實證材料來進行嚴格檢驗。這種理論研究當然就與實證探討在方法上有著根本性質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