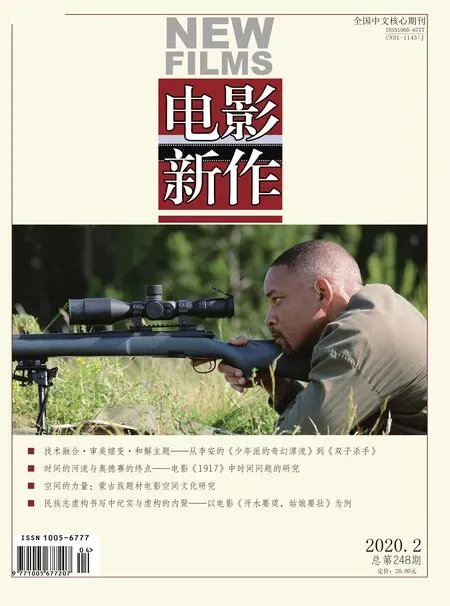私紀錄片的概念梳理與公共性芻議
趙鹿鳴
一、問題的提出
長期以來,中國的紀錄片都不是一個固定、簡易的藝術形態,而是動態的且蘊含了群體與個人、主流與邊緣關系的話語體系。在有限的供個體書寫的時空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漸出現的中國紀錄片轉向是唯一且珍貴的聲音,中國學者呂新雨將這一轉向稱為“新紀錄運動”。在這一語境中,中國的影像知識分子試圖將紀錄片的拍攝原則聚焦在真實、客觀、獨立等特征上,并旗幟鮮明地將電視臺所制播的紀錄片重新命名為“專題片”,由此與他們所生產的紀錄片相獨立(如,吳文光的《流浪北京》、段錦川的《八廓南街16號》),“平民”“底層”“社區”等影像文本成為后者最常出現的人文景觀。時至今日,新紀錄運動見證、指導下的紀錄片(且由于脫離體制、獨立制片的屬性,多被敘述為“獨立紀錄片”)盡管未能成為中國文化生態中的主流,也尚不具備走向商業市場的穩定能力,但它們的存在無疑昭示著一個更為多元的紀錄片業的光臨。本文接下來再次提到的“紀錄片”,將沿用新紀錄運動中的觀點,將之與“專題片”所區分。
在當代影像作品的序列中,從屬于獨立紀錄片的私紀錄片是世紀之交才在中國出現的一員。日本學者那田尚史(Nada Hisashi)認為它(他命名為Selfdocumentary)受到日本私小說的影響,傾向于拍攝自己或記錄私人環境。其觀點強調:如果說多數獨立紀錄片表現的是一種向上的姿態,是從底層的視角發出的革命性的呼喊,那么私紀錄片更像是來源于底層,并駐足在底層,傾向的是對自我倫理的解剖、聲討和放棄,堅持的是一直向下,直到抵達內部精神世界的方向。
在中國學者樊啟鵬的研究中,被視作私紀錄片且得到了少量曝光的中國作品有:王芳的《不快樂的不止一個》(2000)、唐丹鴻的《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2000)、楊荔鈉的《家庭錄像帶》(2001)、章明的《巫山之春》(2003)、胡新宇的《男人》(2004)、魏曉波的《生活而已系列》(2011-2017)等。近年來,另有《日常對話》(2016)、《四個春天》(2019)等作品被學者納入私影像/私紀錄片的概念中討論。方興未艾的私紀錄片,以“私”字為立足點,與傳統意義上的“公”形成對照,吸引人們關注。
但是,私紀錄片的出現伴隨爭論。美國學者凱文·謝爾曼(Kevin Sherman)相信這類創作方式重視自我對真實的介入,代表著“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的極致,亦有學者認為它比其他紀錄片產生了更多的倫理問題,甚至從“偏激”的角度來講,不應該算作“紀錄片”。在此之上,一個更為顯著的現實是,圍繞私紀錄片的定義和討論依舊模糊,盡管有學者對它目前的特征進行了總結(如,多聚焦自己與家人、非職業化拍攝、自我治療功能、充滿倫理爭議),但這種特征是所有紀錄片都可能具有的,這并非區分私紀錄片與其他紀錄片的充分要素——因此,它與其他紀錄片亞類型的邊界是什么?它與自我治療紀錄片(Self-therapy Documentary)、第一人稱紀錄片(First-Person Documentary)、自畫像電影(Self-portrait film)等概念是等同還是有別?在此基礎上,它的公共性意義是什么?這都需要我們更進一步地回答。
因此,本文將以已有文獻和影像資料為參考,著力解決兩個問題:嘗試對私紀錄片以及近似概念進行辨析和確定;同時,在此基礎上,探討私紀錄片的私人性與公共性關系,由此完成對私紀錄片意義的再思考。
二、私紀錄片:一個亟待厘清的概念
8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在中國的擴散,給予了中西各類文化的生長土壤。一定程度上,私紀錄片在中國作為一種創作取向的出現也與后現代主義在影像知識分子中的傳播相伴而行。私紀錄片的特點可以是私人的、反權威的、模糊性的,但這種模糊性也讓它時至今日都界定不清。本文認為,如果在學理上都未能對“私紀錄片”這一概念進行梳理,那么我們圍繞它進行的討論自然缺乏立足點。綜合來看,私紀錄片的邊界問題可以初步劃分為三個不同卻互相聯系的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需要將私紀錄片與其他紀錄片進行界分。當我們視私紀錄片為主體,用它來對照其他紀錄片之前,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私紀錄片是否真的與其工整對應的“公紀錄片”有清晰界限?換言之,我們憑什么說某部作品帶有“私”的烙印,這里面的判斷標準是什么?這涉及私紀錄片的界定問題。當它從早期電影的實驗中脫胎(如,早期的私人戲曲紀錄片),得到溫斯頓(Brian Winston)等后現代主義紀錄片理論家的合法性認定,成為一種不約而同的創作取向時,李瑞華、岳筱寧等中國學者試圖從私紀錄片的特征入手完成對它的界定,綜合起來有如下幾個部分:
1.私紀錄片多強調真實、私人、主觀化的內容展現;2.私紀錄片多將拍攝主體聚焦在自己、家庭和親友上;3.私紀錄片的拍攝者多為非職業出身;4.私紀錄片多存在倫理爭議;5.私紀錄片多帶有宣泄、治療的功能。
這些特點使私紀錄片與整個紀錄片體系構成了包含關系。但令人困惑的是,基于已有影像作品總結的這些特征無非是填充了包含關系的“里”,而非“邊”。在面對大量新涌現的、含混/模糊的、專業/非專業的紀錄片時,我們依然很難將它們準確貼上或“私”或“公”的標簽,因為非職業化、倫理爭議、以自己或親友為拍攝主體也可以是很多紀錄片的特征,而大量帶有實驗色彩的先鋒紀錄片或影像裝置藝術同樣會加入私人、主觀化的內容,這些都并不一定是私紀錄片獨有的。因此,找到它們與其他紀錄片更準確的界分方法才是更值得完成的要務所在。
第二個層面,是需要將私紀錄片與其他相近概念合并或界分。“私紀錄片”(Self-documentary)是本文援引的說法,與它相近的概念還有私影像/電影、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私人紀錄片(Personal Documentary)、自畫像電影(Selfportrait film)、自我治療紀錄片(Self-therapy Documentary)、第一人稱紀錄片(First-Person Documentary)。這些詞匯或單獨或共同地出現在不同學者的研究中,且表述不一。結合已有的影像資料,我們基本可以認可“私紀錄片”與“私人紀錄片”“私影像/電影”這兩個說法為相同表述,僅存在翻譯或傳播上的不同。但困惑存在于第一人稱紀錄片、自我治療紀錄片、自畫像電影等說法是否也等同于“私紀錄片”這一問題中——如,美國學者愛麗莎·勒寶(Alisa Lebow)等人編寫的《關于我的電影:第一人稱紀錄片中的自我與主體性》(THE CINEMA OF ME:The Self and Subjectivity in First Person Documentary)詳細討論了第一人稱紀錄片在多元文化、地理和政治背景下所帶來的理論、意識形態和美學挑戰,但書中也多次以“私人紀錄片”(Personal Documentary)展開論述,且未做區分。相同的情況出現在美國學者斯科特·麥克唐納德的專著《美國的民族志電影與私人紀錄片:劍橋轉向》(American Ethnographic Film and Personal Documentary:The Cambridge Turn)里,他也大而化之的將第一人稱紀錄片、私人紀錄片、自畫像電影統稱為私人移動影像(Personal Moving Images)。相似的是,也有中國學者選擇直接將第一人稱紀錄片等同于私紀錄片而討論。由此,矛盾產生了——《尋找薇薇安邁爾》《華氏911》等歐美知名紀錄片無疑也將第一人稱攝制作為自己的創作手段,但它們與我們所討論的《日落印象》(日本,1975)、《不快樂的不止一個》(中國,2000)等片從選材、手法和商業操作上都有明顯不同,把它們歸為一類顯然有待商榷。因此,本文認為,歐美所稱的第一人稱紀錄片、自畫像電影等名稱,與中日兩國的私紀錄片雖存在含義上的重合,但更多的是翻譯上的相似,不便大而化之。而自我治療紀錄片盡管與私紀錄片在作品指認上更為接近,但由于這兩者在術語命名上的維度并不相同,亦不做等同處理。
第三個層面,是從私紀錄片的私字本身入手,對它們的“私”(Private)與“公”(Public)進行界分。與私小說、私攝影等其他領域術語相似的是,“私”字作為一種創作指導的出現意味著創作者堅持自我的體驗和立場,即達到相對條件下的私密領域。其次,“私”是相對于“公”而言的,它指涉著公共領域、個人領域和私密領域間的共融與僭越關系,意味著主流價值觀、文化象征等共有秩序和規范在這一時刻被暫時遮蔽。從這個角度來看,私紀錄片的內容似乎可以是完全不受限的,因為它們不必對觀看者承擔責任,任何焦慮、不安,或毫無意義的影像內容在這里都可以取得合法性。學者呂新雨的研究便指出:這種自我踐行的紀錄片倫理,把自己的底層生活看成最本真的存在,唯一的卻是屬于他們的存在,在此,自我肉體的倫理成為信仰。“私”字本身,便成了最高法則。
需要強調的是,私紀錄片雖包含“個人化”,但它所強調的,顯然更多的是“私人化”。因為紀錄片的拍攝和完成本就是創作者基于自身認知的主觀體驗,這是無法回避的必經流程。以個人視角完成的紀錄片很難就可稱之為私紀錄片,對現實做出個性讀解并不一定涉及私人體驗——如,紀錄片《超碼的我》的導演摩根·史柏路克主動進入鏡頭,以身體作為實驗品,自述自己連續只吃三十天麥當勞而出現的變化,借此探討健康話題。從描述上看,這很像一個私紀錄片,但是很明顯,導演的介入扮演的不過是迎合觀看者的表演性、甚至可以說商業性的角色,而作品所討論的話題也帶有豐厚的公共意義。而在我們更多承認的私紀錄片中(如,魏曉波的《生活而已》、章明《巫山之春》),涉及隱私元素的內容變得無處不在,去除圍繞它們展開的倫理批評,這些鏡頭的出現才是我們所強調的“私”字的意義所在。
由此,結合這三個層面的邊界問題,同時參考已有的影像資料,筆者嘗試整理出兩條判斷紀錄片是否帶有私屬性的路徑,這兩條路徑幫助我們判斷作品是否具有“私”的屬性。
第一,是從創作者的意志入手判斷。創作者意志在這里被具體闡釋為——作為整部紀錄片的導演,他是否有意限制,或是矛盾于作品的公開放映。事實上,大部分私紀錄片之所以乏人知曉,是因為這些作品的創作者并不熱衷于將它們展出、參評,或者出于尊重被攝者的意愿(多數是他們的戀人、親朋),只會謹慎地選擇小范圍放映,甚至只展示給自己最信任的好友觀看——拍攝,但減少分享。導演李有杰曾在草場地工作坊等場合公開放映了自己的紀錄片《衣胞之地》,但他在此后感到猶豫甚至困苦,他覺得“沒有人有資格跟我分享我與奶奶的影像”。一個更為顯著的案例是《生活而已》系列的導演魏曉波,他在豆瓣等社交媒體上頻繁發表諸多有關私紀錄片的觀點,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這類創作者的矛盾內心:
我希望能夠記錄下看似正常發展的社會下的個體的矛盾……僅僅是記錄下來,別人能看懂就看,看不明白算了,反正也沒多少人能看得到。所以在拍攝、剪輯的時候我盡量地以一種完全主觀的視角,不去考慮什么客觀、真實、流派、紀錄片的定義,真正的紀錄片問題只有一個,人的問題……如果說常規的涉及公共話題的紀錄片像是公開的演講,而私人影像更像是人與人之間私下的言語,它希望能夠和觀眾達到某種溝通。
在面對網友希望索要資源或增加放映場次的請求時,他也這樣回答:
不能來我這看,你可以去買其他的片子……有些片子看不到比看到好。
這些觀點或許并不是出于對著作權的考慮,而僅僅是因為他們面對自己私人化的作品進入公共領域的猶豫(既想與大家進行有限的公開討論,又想避免倫理、價值觀爭議)。因此我們首先將這一特征作為判斷作品是否帶有私屬性的第一路徑,即導演對于作品公開的有意控制(控制參與評選、控制公共放映、控制討論),這是一種矛盾心理,是作品傳播上的“私”。
第二,是從作品本身的內容和意義入手判斷。這其中又分為兩部分,首先是對公共價值的有意消解,《未完成的生活史》《生活而已》等作品,其立足點都是基于創作者自身非常小的生活側面,比如僅僅是記錄自己或者父母、朋友的某種生活狀態,而不去考量被攝者是否具有階層或者職業的代表性。在多數獨立紀錄片的拍攝需要經過提案才有可能獲得資金支持、需要經過周密設計才可能獲得獎項的當下,帶有私屬性的紀錄片無疑是一種更為平民、坦白、簡單的拍攝選擇,創作者自發地拍攝、剪輯他們感興趣的素材而不用回答“拍這個場景、人物到底有什么意義”的質疑。其次,是對公共價值的有意違叛。部分紀錄片的拍攝記錄了大量含有裸露、性愛、暴力的鏡頭,而這本就是對世風良俗的一種挑釁,也決定了它們不能走上大范圍的“公”的舞臺——拍攝,但不能分享。學者呂新雨在評價《男人》《巫山之春》時認為:“這類片子的暴露、深刻以及道德的冷漠感讓人觸目驚心,它所引發的不安甚至恐懼,來源于它侵犯了直接的現實本身……DV機器的出現,它對私領域介入的方便,使得攝影機倫理以及由此帶來的問題再一次沖擊我們。”我們將這一特征作為判斷紀錄片是否帶有私屬性的第二路徑,即作品內容上的“私”。
由此來看,此前研究所認為的家庭式、非職業化、倫理爭議、以自我或親朋為拍攝主體等特征已經可以被歸置到傳播或內容上的私有性當中去。而將私紀錄片與其他紀錄片的界限劃分為這兩個路徑或許也將幫助我們更好地整合和探討私紀錄片作品,尤其是為討論它們的公共性意義提供保障。
三、中國語境:私紀錄片的公共性
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經典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到:公共領域一直是私人領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別于私人領域,且只限于與公共權力機關(如,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有關的事務,而政治公共領域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加以調節。即,公共領域是以公民為主體,供國家機關與私人領域進行交互、溝通的開放空間,文化產品(如,電影、書籍、電視節目)可以在其中發揮輔佐公共領域構建的作用。時至今日,盡管有諸多學者認為,中國尚不存在哈貝馬斯所指認的規范化的公共領域。但隨著網絡空間的孕育、影像工具的普及,我們嘗試去論證:在廣泛意義的公共領域中,私紀錄片能否與民間社會發生互動,由此產生共識。
在論證私紀錄片的公共性之前,我們依然要將專題片(在這里視作“新紀錄運動”之前的主流紀錄片)和紀錄片納入我們的對照范圍,這其中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不同時期中國的紀錄片在公共領域的構建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更直接一點,中國紀錄片是否真的發揮過公共領域的構建作用?這是我們討論私紀錄片公共性的前提。
在中國電視得到真正發展乃至普及的20世紀80年代初,專題片是權力機關在電視上除電視劇、新聞之外的第三種宣傳工具。以《話說長江》為代表的電視專題片以人文科普作為辦法,以強調群體記憶的方式,完成對公眾在大眾傳媒視野下的教化,同時得到公眾的積極反饋(如,《話說長江》后《再說長江》的推出)。在全能主義轉向權能主義之前,專題片的議題聚焦宏大敘事,較少制造“對話”機會,民間社會發育缺乏媒介表征。
而在其后的90年代,“新紀錄運動”中涌現出的大量獨立作品極大豐富了中國紀錄片的講述方式。這種運動的出現絕非偶然,改革開放帶來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巨大變遷促使影像創作者開始思考,如何逃脫體制內的專題片的創作束縛,將目光轉向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和利益訴求,用去官方化的語言去描繪中國的社會現實。按照學者呂新雨的觀點來看,這些紀錄片“建立了一種自下而上的透視管道,在當今中國化的政治經濟格局下,透視出不同階層人們的生存訴求及其情感方式。”而這一過程也自然而然地對公共領域的建立施與了養分。如,澳大利亞學者瑪格麗塔(Margherita Viviani)認為,20世紀末以來,中國的獨立紀錄片與各國作品一樣,常以根莖(rhizome)的形式與社會發生互動,知識分子指導下的這些紀錄片即使永遠不會實現廣泛分布,也不會進入社會主流話語,但他們關注弱勢群體的行為依然有助于公眾的權利聲張和社會改革。這是我們注意到的,中國的紀錄片與公共領域產生關系的第二個階段。
而到了私紀錄片的視閾之下,我們又如何考量它的公共性?其他獨立制作的紀錄片是因為積極涉足社會事務所以才在公共領域的構建中發揮了作用,但私紀錄片的特征就是“私”,它與公共領域的“公”似乎是兩個截然對立的觀念。那么,二者的互動關系究竟是怎樣的?這大致需要分為三個層面去討論。
第一個層面,是基于最顯性的視角來看,私紀錄片不與公共領域發生任何關系,這與多數該領域創作者的意志相伴而行。比如以《流浪北京》而聞名的導演吳文光在接受采訪時認為:“私紀錄片(他的說法是私影像)只和我自己有關。任何東西,我拍的,都只和我自己有關。”態度鮮明地表達自己不在乎公共性的立場。相似的表述還存在于導演魏曉波的社交網絡中,他談道:
現場經常有觀眾問我想表達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上學的時候經常總結文章的“中心思想”上癮了……我們能不能也試圖從文本中發現真理不是真理呢?這應該也是對作品的理解方式……我當然可以一本正經地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去闡釋、分析、讀解自己的作品的意義,但作品存在的意義是什么?它比“意義”重要。
只將作品關注于自身而不考慮社會意義,這作為一種創作選擇看似沒有問題。但也招來了電影人士的批評之聲——關注克拉瑪依大火事件并將其拍攝為紀錄片的導演徐辛的觀點是:“作為獨立紀錄片導演,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去拍什么私影像,起碼是沒有良知。”言下之意是,他認為,但凡是獨立的紀錄片作品,都應該承擔一定的公共責任。中國獨立影像展選片人、學者王池也在博文中委婉表達對私紀錄片整體意義缺乏的擔憂:“在我們看來,導演或許還可以將個人的遭際與更大的社會現實或歷史演進聯系起來,將個體的自我轉化為某個階級、階層成員的自我……此時紀錄片便從純粹的私影像跨越到了更具社會歷史含義的民族志影像。”在很多人眼中,創作者放棄公共話題轉而投身私紀錄片,是一種背離獨立紀錄片精神的“逃避”表現。而這,也將是私紀錄片持續受到批評的原因之一。
第二個層面,是從隱私視角來看,私紀錄片對公共領域造成侵犯。盡管私紀錄片走入主流傳媒通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哪怕它們選擇在一些小范圍的場合(如,影展、民間沙龍、學術交流)出現,對諸多觀看者而言都是一種挑戰。日本導演原一男在1974年的私紀錄片(盡管在當時尚未形成這一說法)《絕對隱私的性愛戀歌》真實無保留地展現了他的妻子、情人的私人生活,這一作品在當時并未得到多數世俗公眾的認可,甚至招來了日本當局的封禁。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據訪談資料介紹,胡新宇的《男人》在云之南紀錄影像展放映時,片中充斥的粗口和對女性的性別侮辱讓大量女觀眾批評不斷,“曾經放到四分之一的時候,已經有四分之三的女人走掉了。”這都是私紀錄片被部分人視作“侵犯”的問題所在。
此外,私紀錄片的創作者盡管基本會在作品的傳播層面予以限制,比如盡可能控制放映場次。但隨著攝制、網絡技術的流行,這種保護顯得更加力不從心。私紀錄片在網絡渠道的出現讓其肆意地在公共領域流竄,這違背了“私”的本質,也加重了對被攝者的侵犯,放大了倫理問題。受此影響,《不快樂的不止一個》《我的父親母親和我的兄弟姐妹》等作品為了保護親友隱私,在近年來都選擇了停止了對外放映,轉而自我收藏。
需要注意的是,私紀錄片的這種隱私問題并不同于“網絡直播間”等新媒體平臺生產的影像,后者同樣來自底層、聚焦自我,但這種聚焦的實質是以“分享”為中介達成的“交易”——他們販賣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間和作為欲望的身體,其目的是吸引觀看者用“購買”、“打賞”等行為完成自我隱私的商業販賣。這與私紀錄片傾向凝視自我、非商業的屬性無法達成一致。同理,還需要關注“Vlog”(視頻日志)的興起。但研判它的公私屬性的前提是學界是否視Vlog為一種紀錄片,這需要更多的研究介入。
第三個層面,是從想象的視角出發,思考私紀錄片對公共領域的協調作用。我們目前所列舉的私紀錄片作品,基本屬于職業化的導演進行的創作。而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些作品,是因為它們起碼經過少量的曝光。但需知道,基于“私”的屬性,絕大多數的私紀錄片并不會被人所知曉,而僅僅作為一種家庭錄像或者自拍式的影像日記存在。那么,它們將對公共領域的構建產生怎樣的作用?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可以更充分回答私紀錄片能否還算作“紀錄片”的質疑。
首先,私紀錄片的存在強化了私人化的經驗表達的合法性。當消費文化和大眾媒體不斷通過刻板化的敘事來框定不同人群的形象規范,這種敘事在塑造整個社會的運轉程式的同時,也干預甚至壓制了私人本應具有的表達權利與觀照真實自我的能力。但通過攝像機的在場,私紀錄片給了創作者與自己和家庭親友私密對話的可能,它如同發揮了社會安全閥(Social Safety Valve)的功能,將創作者平時的困苦、蓄積的敵對情緒及個人間的怨恨予以解答或宣泄,從而對社會焦慮起到了緩和作用。從這個視角來看,私紀錄片絕非只有“私”字而已。正如《膠帶》導演李凝的觀點:“我認為的私不是一種徹底封閉的私,而是公共空間的縮影,烙印著公共空間的痕跡……當私成為極致后反倒會呈現很公共、很社會的東西。”
同時,私藏的,或是極少被公開的私紀錄片,也不斷造就著具備公共性的個體。當攝像頭/移動設備成為人類在數字時代的器官,一個新的記憶工具,人們得以在感知外部世界的同時,建立起更豐滿的自我意識。4私紀錄片由于其獨特的拍攝取向,在缺乏拍攝資金、腳本甚至經驗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獲得定義上的成立,它成為人們最容易上手并書寫的美學文本。因此,從影像(媒介)行動主義(Media Activism)的視角來看,私紀錄片不僅僅可成為一種創作選擇,它還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更經得起反思、更積極的生活方式。”它有機會作為社會啟蒙中的新方向,提醒更多的人拾起影像工具,利用工具的在場來完成自律和反思,帶來超越影像文本的社會影響。
從這個視角來看,私紀錄片并非“不需要社會意義”,而是基于動作/行為本身進行意義再造,嘗試取得成為公共媒介的合法性。這是我們基于某種未來立場提出的第三個層面,是對私紀錄片公共性意義的想象和展望。
結語
今天,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成長與整個中國社會的多元發展并轡而行。私紀錄片作為整個紀錄片譜系中方興未艾的一員,值得業界與學界關注。但就目前的研究來看,針對私紀錄片的討論更多的是從某種約定俗成的“片單”里找尋證據,如同一種契約一樣把這些過去的作品劃分在私紀錄片的行列,卻缺乏對劃分依據的詳細解讀。就比如我們判斷是否給予一個作品是“獨立紀錄片”的稱呼時,側重的是它是否有獨立制片、獨立精神的屬性。那么,私紀錄片的邊界在哪?這需要我們從“私”字入手進行更明晰的考察。
因此,本文嘗試性歸納出兩條判斷紀錄片是否帶有私屬性的路徑,但這并不是憑空創造,而是基于已有研究和影像資料的再整理。第一個路徑是從創作者的個人意志出發,如果他出于個人意愿或尊重被攝者意愿的情況,對作品的公開放映感到猶豫、矛盾,那么我們便判斷具有傳播上的“私”屬性。第二個路徑是從作品的內容意義入手,如果是對公共價值的有意消解乃至違叛,那么便認為它具有內容上的“私”屬性。當一個作品帶有這兩種私屬性的傾向,那么它也許就屬于我們目前所探討的私紀錄片。這種整理方法為我們考察作品的公共性意義提供基礎。
那么,私紀錄片與公共領域的關系到底是什么?這需要從三個層面去討論。
第一個層面,是從尊重導演創作本能的視角出發,使私紀錄片盡量不與公共領域發生任何關系。因為他們作為創作者,只愿讓紀錄成為生活的有機組成,將攝影機視為僅供自我歡愉的器官,從而完成存在感的再確定。第二個層面是以批判的視角來看,私紀錄片哪怕只是少量的曝光,也或許會給公共領域帶去人情倫理上的隱患。至少會在較長一段時間里,蒙受“放棄揭露任何社會問題”的洶涌質疑。而在最重要的第三個層面,我們嘗試去想象,當社會矛盾難免成為當下中國的一種“常態”,私紀錄片是否在發揮一種社會安全閥的功能,去緩解、宣泄個體困惑、壓力和矛盾,因為它的拍攝理念可以讓每個人都通過一個簡易的美學文本去完成表達,并通過影像工具的在場完成自律和反思。這是我們期待的,私紀錄片能夠被完善、承認,并最終抵達的公共價值。
【注釋】
1 Qian Y. Power in the frame: China's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movement[M].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3.
2 呂新雨. 紀錄中國: 當代中國新紀錄運動[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3.
3 [日]Hisashi N. Self-documentary: Its origins and present state[J]. Documentary Box, 2005, 26: 15-23.
4 樊啟鵬. 中國私紀錄片帶來的變化與挑戰[J]. 電影藝術, 2007 (6): 136-139.
5 張斌,潘婷婷.私紀錄與生命影像——紀錄電影《四個春天》讀解[J].電影新作,2019(2).
6 黃鐘軍. 臺灣私紀錄片的個體認同和公共表達[J].當代電影,276(03):80-83.
7 [美]Sherman K. Book Review: American Ethnographic Film and Personal Documentary: The Cambridge Turn[J]. 2013.
8 李瑞華.“放逐”隱私與“表演”生活——私電影的倫理爭議[J].電影文學,2011(24):9-10.
9 來自華東師范大學學者聶欣如對筆者的郵件回復。
10 汪暉.九十年代中國內地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J].電影藝術,1995(1):12-16.
11 [美]布萊恩·溫斯頓,王遲譯.當代英語世界的紀錄片實踐——一段歷史考察(下)[J].世界電影, 2013(4):174-178.
12 樊啟鵬.中國私紀錄片帶來的變化與挑戰[J].電影藝術,2007(6):136-139.
13 [日]Hisashi N.日本私紀錄片的起源與現狀[J].電影藝術,2007(3).
14 岳筱寧,雷蒙.私紀錄片的倫理困境與道德救贖[J].當代電視,2014(5):17-18.
15 李姝.私紀錄片的影像療愈功能探究[J].電影文學,2017(18):21-23.
16 劉尋.像一把刀子——中國“私影像”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1.
17 徐亞萍.通往真實的自我—中國私紀錄片研究[D].北京. 中國傳媒大學,2009.
18 [美]The Cinema of Me: The Self and Subjectivity in First Person Documentary[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 [美]MacDonald S. American Ethnographic Film and Personal Documentary: The Cambridge Turn[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20 孫紅云.公開的隱私:第一人稱紀錄片[J].電影藝術,2010(06):92-97.
21 [美]Arthur P. The moving picture cure: Selftherapy documentaries[J].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2007, 94(6): 865-885.
22 呂新雨.“底層”的政治、倫理與美學——2011南京獨立紀錄片論壇上的發言與補充[J].電影藝術,2012(5):81-86.
23 聶欣如. 紀錄片“客觀性”之爭論[J].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6(03):1-40.
24 小帆.亮出你的底牌[J].大眾·DV,2010,(6).
25 參見魏曉波在豆瓣網上撰寫的文字資料: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7846847/.
26 參見魏曉波在豆瓣網上撰寫的文字資料: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11226123/discussion/51123655/、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11226123/discussion/615625505/.
27 呂新雨.新紀錄運動的力與痛[J].讀書,2006(5):12-22.
28 [德]哈伯馬斯,衛東,曉玨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 學林出版社,1999.
29 [德]Habermas J, 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M]. MIT press, 1991.
30 Davies G,Habermas in China: theory as catalyst[J]. The China Journal, 2007 (57): 61-85.
31 Huang P C C. "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J].Modern China, 1993, 19(2): 216-240.
32 [美]Madsen R.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J]. Modern China, 1993,19(2): 183-198.
34 郭堅剛, 席曉勤. 全能主義政治在中國的興起, 高潮及其未來[J]. 浙江學刊, 2003, 5: 157-159.
35 呂新雨. 紀錄中國: 當代中國新紀錄運動[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3. 導言P23.
36 [澳]Viviani M.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films: Alternative media, public spher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itizen activist[J]. Asian Studies Review, 2014, 38(1): 107-123.
37 參見吳文光接受網易專訪的文字資料:http://v.163.com/special/008563C1/wuwenguang2nd.html.
38 參見魏曉波在豆瓣網上撰寫的文字資料:https://www.douban.com/note/545489527/.
39 參見徐辛在現象網上撰寫的文字資料:http://fanhall.com/group/thread/17052.html.
40 參見王池在新浪博客上撰寫的文字資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1d39a0101a7dp.html.
41 參見中新網對吳文光的報道: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0/08-04/2446374.shtml.
42 參見John Berra對原一男的專訪:http://www.electricsheepmagazine.co.uk/features/2010/01/10/extreme-private-eros-interview-with-kazuo-hara/.
43 參見胡新宇接受Artworld專訪的文字資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fa747010009lr.html.
44 呂新雨.購買“民主”:新媒體時代的勞動價值論[J].新聞與傳播評論,2018 (1):6.
45 參見李凝接受現象網專訪的視頻訪談資料: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MTgxMDUy.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
46 黃文達.后電影:數碼時代的電影語言[J].當代電影,2004(4):119-122.
47 孫瑋.賽博人:后人類時代的媒介融合[J].新聞記者,2018,No.424(06):6-13.
47 [美]Carroll W K, Hackett R A. Democratic media activism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J].Media,culture & society,2006,28(1):83-104.
48 劉尋. 像一把刀子——中國“私影像”研究[D].福州. 福建師范大學. 2011.
49 聶欣如.關于“先鋒紀錄片”的四個問題[J].未來傳播,2019,26(05):89-95+126.
50 李瑞昌.經濟新常態下的公共治理創新[J].探索與爭鳴(7):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