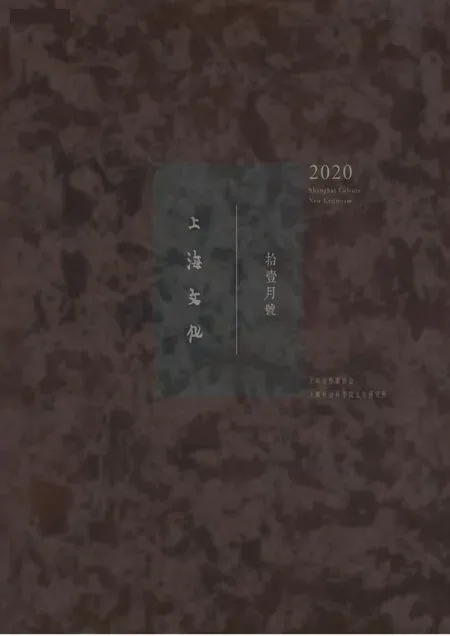在詞和詞之間
關于托卡爾丘克的《云游》
許志強
一
《云游》(于是譯)引起議論的首先應該是它的碎片化寫作。由一百十六個片段組成的敘述初看好像不成其為敘述,難怪出版社以為是作者誤將文件夾里的素材交上來了。托卡爾丘克在書中交代說,她師法麥爾維爾。將故事、哲學和歷史熔于一爐,那種百科全書式的敘事意圖是有點相似。但是,《白鯨》的“離題話”都是圍繞著主干故事,所以毛姆認為不妨將它們從故事的本體上摘除。那么《云游》呢?它有好些個互不相干的故事,沒有所謂的故事本體,即便想摘除好像也無從下手。這是《云游》的顯著特征:沒有“恰當的”結構,沒有“恰當的”文體;它是從云端俯瞰或許才能夠看見“整體”的一個大雜燴。
題為《庫尼茨基:水》的故事,講去一個島上旅游的三口之家,妻子和兒子楞是在這個芝麻大的島上失蹤了,丈夫和警察當局苦苦尋找而未得。讀者不知道這個故事想要講什么,它的謎一般的氣氛以緩慢的節奏在字里行間彌漫開來。敘述人聲稱:“……我始終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作家。生活總能與我保持一臂之遙。我頂多只能找到它的尾跡,發現它拋棄的舊皮囊。等到我可以確定它的方位了,它早已逃之夭夭。我能找到的,只是它曾經逗留此處的標記,儼如公園樹干上某些人留下的‘到此一游’的涂鴉。在我寫下的故事里,生活會演變為不完整的故事,夢一般的情節,會從不知其所在的遙遠場景,或一看就知道的典型場景里浮現出來——因而,幾乎不可能從中得出所謂的普世定論。”
一邊敘事一邊對敘事行為發表評論,甚或兜售某種寫作的形而上學,這在后現代小說中是常見的。認為生活的本質總是在被辨認之前就逃逸了,它留下的痕跡只是提供本質不在場的證明,這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的觀點,因此上面引用的那些話不妨看作是小說版的德里達。它是想給那個有頭無尾的故事做出辯解或說明嗎?如果是,則未免有點乏味。雖然敘事人并不等于作者(按照韋恩·布斯的說法),但我們會把那些雜七雜八的議論當作是托卡爾丘克的發言。敘事人說“我觀察不到界線……”“我不相信恒定的假設……”口氣頗似迷宮中徘徊的作者,——她可能是一位聰明而躍躍欲試的女博士,把德里達的理論翻譯成心情日記,也可能是一位深刻的“盲視者”,像博爾赫斯那樣凝視一朵玫瑰。《云游》的前六十頁(或前一百頁)讓人覺得,作者更像是前一種人。
這樣下結論當然是草率的,而且失之于夸張。《云游》前一百頁并非德里達的理論的翻版,更非新手的尚顯稚嫩的探索。它是遠航的起點。我們有理由在啟程階段感到不適,而真正的航行總是這樣開始。前一百頁中嵌入的第二個故事《圣灰禮拜三的盛宴》,講一名退役水手在一座小島上開輪渡,為觀光客和上下班的職員服務。不妨將這個故事視為此書寫作的一種象征。有一天,輪渡駕駛員冷靜而堅定地(或許更是狂熱而幽默地)偏離航向,將渡輪駛向公海,置全體乘客的呼聲于不顧。這個有麥爾維爾氣息的故事,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托卡爾丘克的作風:機敏,大膽,壯實而有爆發力。
還應該加一個詞:時尚。選擇碎片化的形式寫作也是一種時尚行為,作者說:“……這就是我發揮想象的方式,而且我認為讀者在這些碎片化的文本中暢游也會很輕松。……我們和電腦的關系已經改變了我們自身的感知——我們接受了大量迥異的、碎片化的信息,不得不在頭腦中將它們整合起來。”這是對《云游》的創作形式的一個較通俗的解釋。電子時代的技術文明及其衍生的生存狀態,是這部小說著力表達的主題,富于濃烈的時尚氣息,這一點稍后會有論述。
回到碎片化寫作。在使用電腦之前這種創作形式就早已存在。例如,福克納的《野棕櫚》、克洛德·西蒙的《三折畫》等,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相關的故事拼接起來,形成虛構作品的一種變態形式,作用于讀者的感知。廣義上講,不是按照線性的體系化框架架構的文本都屬于碎片化寫作,例如尼采、齊奧朗的作品。此種文體的歷史淵源可追溯至18、19世紀的德國浪漫主義,耶拿浪漫派和施萊格爾兄弟,所謂“漸進的萬象文學”和作為“斷片”(fragment)的理論表述形式或“語錄體散論”,等等。經過現代主義洗禮,這種形式可以變得非常隨意又包含創意,例如胡里奧·科塔薩爾《跳房子》第三部《在別處》,其大雜燴的拼貼帶有玩笑性質,諸如報章或書籍的摘錄、故事里套故事、美學思考或軼事報道,等等;總之,都是一些不加論證的陳述和取消矛盾律的反諷;精神還是耶拿派的精神,怪論和叛逆的色彩更辛辣了。托卡爾丘克的同胞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在其《費爾迪杜凱》(易麗君、袁漢镕譯)第四章《孩子氣十足的菲利陀爾的前言》中宣稱道:“因而正是這些原則的、基本的和哲學的道理促使我們在各個部分的基礎上構筑作品——將作品作為作品的細小部分對待——也將人作為部分的組合物對待——在我將整個人類作為部分和一大堆部分的混合體對待的時候。但是假若有人這樣指責我,說這種細小部分的概念,老實講,根本就不是任何概念,只是胡謅、挖苦、拿人開涮;說我不是遵循藝術的嚴格規則和標準行事,而是試圖用那種挖苦話來挖苦他們,我就會回答說,是的,正是如此,我的意圖正是這樣,而不是別的。而且,上帝保佑,我會毫不遲疑地承認:‘先生們,我渴望在多大的程度上偏離你們自己,就在多大的程度上偏離你們的藝術……我無法忍受你們的藝術,因為我也不能忍受你們——連同你們的觀念,連同你們的藝術觀點,連同你們整個的藝術世界。’”
這段話的前半段適用于《云游》。“將作品作為作品的細小部分對待”,說明是有一個整體的概念,否則就無所謂“構筑作品”了。貢布羅維奇在哲學和人類學的意義上強調他是一個部分論者或部分主義者,則是在表達諷刺和藐視。托卡爾丘克不是這樣。她要溫和得多。她雖然投身于技術文明,卻連溫和版的馬里內蒂都不是。她既不可能有科塔薩爾的先鋒姿態(就碎片化寫作的形式而言,能玩的科塔薩爾都玩了),也不具有貢布羅維奇的極端文雅和極端道德所催生的傲世之情。她談論“復發型脫癮癥候群”,談論“人體標本”,表示對“畸形學、非常態”感興趣。她那個敘事的聲音,如布克獎的評委所言,“從機智和快樂的惡作劇漸漸轉向真正的情感波瀾”,還是相當討人喜歡的。對她來說,“將作品作為作品的細小部分對待”符合碎片化寫作的一般定義;而“將人作為部分的組合物對待”則碰巧像是一個隱喻的說法,暗示了她對人體解剖學的興趣。在《云游》中,“人體解剖學”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托卡爾丘克相信,只要堅忍不拔地在一種非常規的形式中冒險,就會鉆探到事物的要義;但是要付出代價。所謂“站到詞與詞之間,立于想法與想法之間深不可測的深淵”,這難道不是對碎片拼接的詩學意義的闡釋嗎?或許是一種最佳的闡釋了。和貢布羅維奇、科塔薩爾一樣,托卡爾丘克站在象征主義的立場看待語言和精神哲學的關系。“隱蔽的關聯比明顯的關聯”更值得嘗試。尋找理論的合法性不如投入冒險。換言之,為了“無法以詞語轉述”的事物,你必須跨越深淵。
二

該篇廣博的文化視野和流動的時代氣息,使它注定不會凍結在小語種小受眾群里。與其說它是一部波蘭小說,不如說是一部數碼時代的歐洲小說。從視野、身份、選材性質及范圍看,出生于1962年的托卡爾丘克屬于新一代東歐作家;她的視野和身份就是全球化時代的無國界流動的身份。《云游》寫歐洲公民,民族國家的色彩不濃厚,母國波蘭也不占據特殊地位。一種新的技術文明景觀及其積極的潛能吸引作者的興趣;主要是由現代交通和通訊所構成的景觀,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變異,因為在純文學領域還未如此集中地描寫過(帕維奇、波拉尼奧的作品或多或少是寫到了),《云游》便成了這些新生事物的代言。




《云游》包含的那些解剖學故事有虛有實,其中紀實的部分已加入杜撰,而虛構的部分也肯定是深入利用了文獻檔案;這種虛實相生、虛實轉換的敘述,帶有顛覆性和奇幻性,像是在開玩笑,又像是在譜寫知識神話,讓人想起博爾赫斯以及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和丹尼洛·契斯的創作。也就是說,她的精神和方法主要是從當代諷喻敘事的頂尖作家那里學來的。書中有關解剖學的章節是精心編織的諷喻敘事,在玄秘的意義和世俗的意義之間移步換形,——確切地說,是在詞與詞之間注入諷喻和冥思的意味;而當這種敘事達到一定的長度時,貌似玩笑的東西也就具備了不可阻擋的啟迪力量。
17世紀弗拉芒解剖學家和醫生菲利普·菲爾海恩,史上實有其人,《云游》寫他一條腿截肢,卻長年感到膝蓋以下皮膚癢,腳趾痛,這種虛空部位的痛癢令他輾轉難眠,思考肉體和靈魂的關系,并且以其友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哲學推斷和發問——“我的疼痛是上帝嗎?”書中有一章題為“寫給截肢的信”,把醫生的形而上的痛癢寫得妙不可言。
題為“肖邦的心臟”的章節,寫肖邦死后心臟被挖出(又是和解剖學主題相關的細節),鼓鼓囊囊塞進玻璃罐,玻璃罐藏在裙子底下,確切地說,是頂在了女人的陰部前,躲過邊境崗哨的盤查,得以回歸祖國波蘭;這一章寫得莊諧并作,技法精湛,昆德拉想必會擊節稱賞,其諷喻的力度直追羅貝托·波拉尼奧《荒野偵探》中描寫墨西哥詩人奧塔維奧·帕斯的章節。托卡爾丘克寫解剖學,就像普里莫·萊維寫化學,并不是要把作品寫成科學。她揮灑筆墨,氣度不凡,展示想象力和文化知解力的一個高水準。
這部用一百十六個片段拼接而成的小說,反映一個不斷形成不斷崩潰的世界。有趣的是,它在瞬間(活在碎片化的瞬間)和永生(讓尸體長存的古老執念)之間維持著某種張力。因此,也不能說作品的兩條主線之間是缺乏關聯的。
從詩學原創性的角度講,可以說當代已無先鋒派;從文化形態學來看,科技文明主導下的當代生活景觀卻還未必真正進入純文學的視野,而《云游》提供了這方面的關注、思考和描繪。它以謎一般的片段拼貼告訴我們,不僅美學和感知方式在分化,文化的概念也在分化,價值、信念、生活方式、社群歸屬感等無不如此。該篇的關注和思考是多方面的。面對數碼時代的科技文明所形成的景觀,它以權利價值論為導向,突出個體的選擇的一面,卻未在發生學的意義上談及承受的一面,后者同樣能夠(當然不一定全都)體現權利價值論,對命運和存在的探究卻更深刻、感人,像卡夫卡、李斯佩克朵等人的創作所體現的那樣。《云游》的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比卡夫卡、李斯佩克朵更具現實針對性,不像后者那樣更多是在寓言和存在論意義上展開。另一方面,主張個體價值優先的現代個體權利論(權利論優先于真理論),傾向于虛無主義的肉身輕逸的狂歡,使得《云游》無論是精神還是形式都跟卡爾維諾《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倡導的“輕逸”美學頗為一致。可以說,基于肉身輕逸的狂歡,似乎難以延續卡夫卡式的對絕境和悖論的追問,因此從文學表現的角度講,僅僅強調新文化景觀中的個體自由的一面,視界和深度似還有待于拓展。再說,新文化景觀中的個體自由本身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就此而言,《云游》的文化意識形態表達有著可供進一步討論和辨析的空間。



定義《云游》的作者是一個什么性質的作家,必須考慮的是這兩個因素,即“世界史的尺度”和“超越故鄉的普遍性精神”。它們指向托卡爾丘克作品的精神及智性的活力。可以說,這份活力是屬于邊界不甚明確的跨國多元文化的生成,屬于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描述的“世界文學空間”。
?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云游》,于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9-70頁。
? 薩默塞特·毛姆:《巨匠與杰作》,李鋒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02頁。
?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云游》,于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頁。
?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云游》,于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頁。
? 宮子:《對話托卡爾丘克:夢境比現實更加龐大》,《新京報》2018年3月3日B03版。
? 《歐美古典作家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一、二),外國文學資料叢刊編委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第385-386頁。
? 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費爾迪杜凱》,易麗君、袁漢镕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第118-119頁。
?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云游》,于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頁。
? https://thebookerprizes.com/international/backlist/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