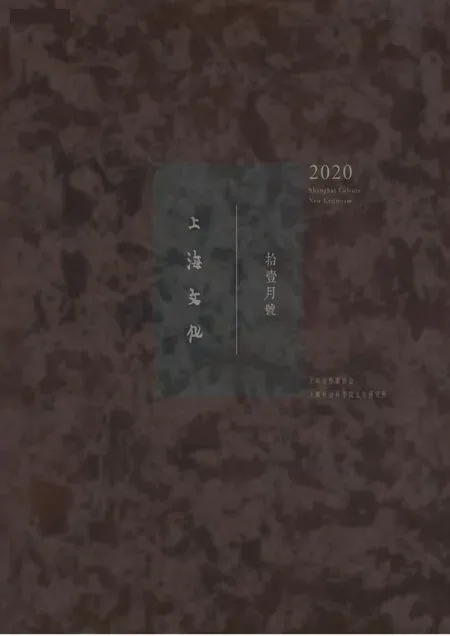在藍色與空無中:伊夫·克萊因的多重身份建構
張 浩
1.引 言
1962年6月的一天,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因突發心臟病死于巴黎的一處寓所。一個月前,他剛剛過完自己三十四歲的生日。雖然其藝術生涯僅延續了八年,但這足以讓他席卷整個歐洲藝術界。關于他的離世,迥異的評價出現在當時大西洋兩岸的媒體上。一邊是法國藝評人皮埃爾·雷斯塔尼(Pierre Restany)(克萊因堅定的支持者)斷言“他的傳奇只會不斷生長”,法國《世界報》的訃告稱他為“當代巴黎前衛畫家中最洶涌不安,最具代表性的畫家”。另一邊的美國極簡主義藝術家和評論家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則指出“他不如幾位最頂尖的美國年輕藝術家出色,但他仍是優秀的二流藝術家”。
半個多世紀以來,克萊因數次回到人們的視野中,贊美與懷疑的聲音也一直伴其左右。正如學者伊夫-阿蘭·博瓦(Yve-Alain Bois)2007年的文章《克萊因的現實性》中所提醒的,“今天的克萊因與1960年代的克萊因并不相同”。時隔多年,現在的情況不但沒有變得簡單,反而更加復雜。除了人們熟知的藝術作品,克萊因還留下了數量可觀的私人日記和書信,相冊和影片,以及大量的發言稿、展覽聲明和文章,特別是考慮到他的全部作品創作于1954年至1962年之間,即藝術家二十六歲至三十四歲之間。如果遵循克萊因1959年在索邦大學(Sorbonne)的著名宣言,他的繪畫只是他的藝術的“灰燼”,那么他的其他藝術創作是什么?能夠凝聚為灰燼的藝術又是什么?是否可以作為擴展領域的藝術從而將他更大范圍的實踐(文字、展覽、表演甚至體育運動)都納入在內?克萊因處理藝術與生活的方式也導致諸多的解釋問題,使得很難用簡化的前后一致邏輯去理解其多元策略。如何處理克萊因刻意修訂的過往言辭,特別是涉及個人傳記的成分?如何看待克萊因管理和傳播個人形象時的姿態表現?此類問題不勝枚舉。筆者認為,面對把身份作為美學項目加以塑造的克萊因,拆解構成其藝術與生活的悖論性元素,也許可以為重建其在當下的意義提供一定的清晰度。
2.成為畫家
伊夫·克萊因1928年4月28日出生于法國尼斯,父母均為畫家。父親的繪畫風格(海濱景色或風景中的馬)比較具象,母親的繪畫(形式和色彩構成)則更接近抽象。年輕時的克萊因對學校課程沒多少興趣,他在期末考試中未能通過大學申請。從那時起,他便決定不接受任何學校教育。對他來說,這將會是一次解放。此時柔道成為他的新興趣,1952年在姑姑資助下,他遠赴東京學習柔道。也許應該更清楚地強調,根據藝術家自述,克萊因1946年在父母的影響下開始繪畫,即便這一開端充滿了憤怒(對父母因職業而忽視他而深感不滿)。直到大約一年后的一天,克萊因對自己說:“為什么不(這樣做)?”他的解釋是“生活中‘為什么不’是主宰一切的決定,這是命運”。他遵循這一靈光乍現的啟示,希望成為一個具有完全不同想法的畫家,他首先將質疑的矛頭指向父輩們最為倚重的繪畫元素——線條與色彩。“普通繪畫是眾所周知的監獄窗口,其線條、輪廓、形式和組成均由欄桿確定。這些線條具體化了我們的注定死亡,我們的情感生活,我們的理性甚至我們的靈性。它們是我們的心理界限,我們歷史的過去,我們的骨骼框架;它是我們的弱點,我們的愿望,我們的才能和我們的創造物。”在克萊因看來,繪畫中的線條被具象化為監獄窗口欄桿,體現了世俗的秩序,將一切創造力和生命力都禁錮起來。克萊因希望扮演挑釁性的角色,越過邊界,與這些弱點做抗爭。而色彩就像一個“感性的純粹空間”,讓他擁有“完全自由”的感覺,這些吸引他創作出單色表面去觀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絕對中可見的東西”。
另外克萊因還討論到如何識別“畫家”這一身份。他自稱,“我將成為‘畫家’。人們會說我:那是‘畫家’。我會覺得自己是‘畫家’,一個真正的畫家,正是因為我不畫畫,或者至少表面上沒有畫。我作為畫家‘存在’的事實將是當今最‘令人敬畏的’繪畫作品”。克萊因在此引入了一個全新的作品概念,即作為畫家存在本身就可以作為最有力的證據。更準確地說,這種存在的事實不是通過具體實在的、可以看到并觸摸到的作品來確定,而是通過一個宣言或一個口號,首先自我“封立”而成的。畫家,在克萊因這里,作為一種身份,主要是被自我賦予的,在創作經歷中得以顯現。按照這種被大幅擴展了的作品標準,便不難理解他將藝術融入生活的嘗試。作品似乎只是導向更大目標的方法,某些超越藝術的東西才是他所念茲在茲的,比如自由。“藝術是完全的自由,它是生命;一旦有任何形式的禁錮,對自由的冒犯,生命就會隨著禁錮程度而成比例地減少。”克萊因將自由視為藝術自身生命力的重要指標,而他對“作品”的定義恰恰也與藝術的自由本質構成呼應。
3.為何選擇單色畫和藍色
克萊因短暫的人生也許是他基本上專注于藍色的根本原因,因為并沒有足夠的時間供其發展自己的藝術。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出發點僅僅是藍色。即使在色彩上,克萊因仍然具有多樣性。應該強調的是,他的第一個單色畫實際上是彩色的。藍色,金色和粉紅色成為克萊因的三種基本色。在他腦海中,單色繪畫中的這三種基本顏色“是世界的普遍解釋原則”。在索邦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指出這三種顏色的等效性,“藍色,金色和粉紅色具有相同的性質。在這三種狀態層面的任何互換都是可靠的。”另一方面,色彩沉浸在巨大的感性當中,而純粹的感性對于克萊因而言是相當高頻的術語。歡快的色彩,雄偉、低俗或甜美的色彩,暴力和悲傷的色彩。將不同的色彩與種種情感聯系起來,這并不是什么嶄新的想法。“對我來說,色彩的每一個細微差別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個個體,這一存在不僅與基本色來自同一種族,而且絕對擁有個性和不同的靈魂。”




4.空間的藝術家


5.講故事的人


不可否認的是,這堪稱一篇精彩的回憶文章,充滿戲劇性元素。一切似乎都是合理的。把這一版本與本文第三章提到的版本進行比較,故事(不一定是真相)也許會呈現得更為完整。第一個版本通過巴什拉的作品,注重色彩與情感,空間與靈魂的聯系。第二個版本則是對選擇過程的補充,主要考慮觀眾的沉思,服務于更高層次的藝術家的目的,即純粹的感性。對于這兩種敘述,筆者無法斷定哪一個是真,哪一個是假,也許兩者都是事實。問題的關鍵在于克萊因反復使用的策略,符合他自相矛盾且富含表演力的人物形象設定。同樣的策略在日常生活層面也不乏表現,比如克萊因在法國獲得的柔道頭銜,其實歸功于姨媽的來信與適當的幕后操作。

需要注意到,根據學者伊夫-阿蘭·布瓦的考察,將整個畫布涂成藍色,克萊因并非持有這種想法的第一人。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曾深入考慮藍色的問題,可以說克萊因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這位前輩的夢想。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巴內特·紐曼(Barnett Newman)通過延展畫布直至占據整個墻體,也達到類似的效果。然而目前并沒有證據顯示克萊因在畫出藍色單色畫之前曾看到過紐曼的作品。
6.歷史前衛與新前衛之爭中的克萊因
涉及到單色畫的發明權,克萊因曾濃墨重彩地宣傳自己的獨創性。在化學家的幫助下,國際克萊因藍(International Klein Blue,簡寫為IKB)也順利成為克萊因名下的專利。對于來自1920年代俄羅斯至上主義藝術家卡西米爾·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ch)的影響,克萊因堅稱從未意識到。選擇性的視而不見,配合對發明權的獨占,除了意欲完全隔斷與現代主義繪畫傳統之間的關聯,更意味著對自我神話的強烈欲求。誠然,好名聲不容錯過,即便需要一些夸張,需要施加表演的魅力,這些都發生在克萊因身上。克萊因早熟的復雜性,也使得他作為二戰后藝術界的關鍵人物,被卷入了關于歷史前衛和新前衛關系的長期爭論中。




7.結 語


Nuit
Banai
,Yves
Klein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 2014,pp
. 171-172.?Yve
-Alain
Bois
, “Klein
's
Relevance
for
Today
”,October
,Vol
. 119 (Winter
, 2007),p
. 76.?Yves
Klein
,Overcoming
the
Problems
of
Art
:The
Writings
of
Yves
Klein
,ed
.Klaus
Ottmann
,New
York
:Spring
Publications
, 2007,p
.X
.?Ibid
.,pp
. 82-83.?Ibid
.,p
.X
.?Ibid
.,p
. 45.?Ibid
.,p
.XV
.?Olivier
Berggruen
,Max
Hollein
and
Ingrid
Pfeiffer
,Yves
Klein
,Ostfildern
:Hatje
Cantz
, 2004,p
. 48.?Ibid
.,p
.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