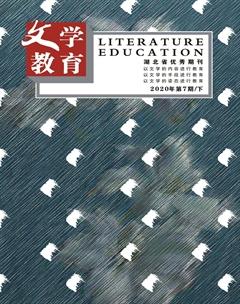金曾豪散文與“江南現象”研究
陶開顏 查能
內容摘要:金曾豪是常熟籍重要散文作家。其作品不僅為我們展示了個體生活的現實,也展現了江南地域、江南文化對作家的深刻影響。本文將從地理、個人、生活的多元維度,發掘金曾豪首部散文集《藍調江南》與區域文化“江南現象”之間的必然關聯與文化價值。
關鍵詞:金曾豪 《藍調江南》 江南現象
金曾豪誕生于常熟練塘的一個中醫世家,溫雅的家風和秀美的風物,使金曾豪養成了沉默敦厚、勤學善思的性情,而曲折的人生造就了他堅韌不屈的情操。他的生平和為人,潛移默化的牽引著他的行文風向。作為著名常熟籍作家,金曾豪以其純澈靈性的兒童小說和清俊秀麗的散文作品在文學界享有盛譽。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兒童文學的傾心創作,同時以散文為載體,對江南風土人文全力弘揚,總計出版了40多部專著。
然而,關于區域文化和相關作家的研究,理論雛形提出雖早,但是成體系的建樹很少。大多研究者都埋頭于主流文化的熱門作家群體,對其反復咀嚼,卻對相對冷門的區域及作家缺乏關注。金曾豪的散文也有著相似的處境——由于過于耀眼的兒童文學光環,其散文被迫處于邊緣地位,與之相關的研究甚少。實則,其散文風格鮮明且獨樹一幟,氣質清新秀美,真實生動地重演生活,富有童真、童趣,極具知識、文學色彩,詩性審美價值也極高。因而本文將從研究金曾豪散文的薄弱點入手,以區域文化為大視域,從地理、個人、生活的多元維度,發掘 “江南現象”對金曾豪首部散文集《藍調江南》的生成意義,并以此補全金曾豪作品研究的譜系。
一.地理的江南
特定的環境匹配著特定的創作建構,這是一種無從造假的標識。作家身處的環境極大概率呈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形成難以磨滅的地理印記。
(一)小鎮輕波——金曾豪散文的“水現場”
車前子曾在《江南話本》中這樣描述:“清水淡墨,它被描在暗黃的毛邊紙上,一塊云、一團煙,云而已、煙而已。”[1]金曾豪自小生活在陽澄湖畔的常熟練塘,作為典型的江南小鎮,練塘無疑具有這些清淺幽遠的江南意味。金曾豪也通過截取美景,渲染出江南風貌,用這些靈動別致的開幕和轉場,使行文流暢毫無斧鑿痕跡。
金曾豪極愛也極善寫水,“練塘是一條白練般飄逸的河。河穿過鎮子,鎮子便隨了河的名。水鄉小鎮常常是這樣得名的”[4];(《呼鴨》)“水鄉,河浜如網,淌淌船很忙,很快活”[4];“少女捉住一朵菱頭,提起來,一把紅菱燦然出水。若有斜陽晚霞映照,紅瑪瑙似的更好看。淋漓的水也成胭脂色了”[4];“就有一兩只紅蜻蜓飛起來,在水面上盤旋”[4];“江南的城鎮除了街巷,總還有一個水系網絡著。常熟城里有好幾處‘三步兩條橋,走三步路就能踩到兩條橋,可見河之多”[4](《網船》)濕潤的氣候,豐沛的雨水,造就了密布的河網,水與江南密不可分。依水而建的住宅店鋪,略帶腥味的網船,繁忙的商船,藻荇間的土婆魚,采紅菱的少女,盤旋的蜻蜓……氤氳的水汽,夾雜著人聲鴨鳴撲面而來。這零星的幾點水色卻暈出了生活人氣,暈出了澄澈風情。
江南的物與人都被水的現場裹挾,諸如那些刺透歷史迷障,具有不竭源流的經典江南意象——《采蓮曲》中荷葉羅裙、芙蓉如面的采蓮少女,《望海潮》里“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鄉邦風土,《菩薩蠻》中“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的悠然姿態。水給予江南一種仿佛蘆花深處飄渺而來,揉和神話想象、詩性智慧和審美思維的終極氣質。
(二)筆尖微瀾——金曾豪散文的“水化”情結
在金曾豪的散文中,水作為一種意象產物,卻又從具象的形體中逸散開來,以情感、氣質之姿浸潤筆端,使行文風格也似潺潺流水,細膩平和,撫慰人心。
《八音刀》洗頭的疲倦感、理發時“洗心革面”的愉悅感、洗發皂“五洲固本”的氣味,一切都是平凡生活的安逸與靜謐,老派的親切,樸素和庸常的詩意。《一頭有名字的羊》放羊、割草是享受大自然的氣息,聞著清香給人踏實之感。《家里的灶頭》一家人在灶頭邊忙活感受人世間的秩序……一派祥和與安逸,娓娓道來,作者也罷,散文中的人也罷,已是流水入海。水深無聲,人情也如此。
誠然,水“溫柔時可以像女人的淚,剛強時可以沖破堅固的堤”[2],金曾豪散文平靜之中,卻有著流向心靈的力量。或于《八音刀》永生為去世的父親剃最后一個頭中感慨歲月流逝,或于《一頭有名字的羊》榮小弟不慎落水、白雪生離死別中見證“我”的成長,或于《家里的灶頭》想起過世母親往昔叫喚吃飯聲音時的唏噓不已……淡淡的敘述中透露出藕絲連連的情誼,江南的人情雜糅在瑣碎的生活片段中,似恬靜的水面上仍有波瀾動蕩,不是直涌向心頭,而是圈圈泛起,輕柔,卻足以壓迫一時半刻。
二.個人的江南
莫言在《每一個寫作者都離不開鄉土》中說到“作家創作的故鄉情結是難以磨滅的,很多作家都是自覺地運用鄉土文學,全世界的作家幾乎無一例外。作家創作到一定層次以后,必然會開發利用他的故鄉,他的童年,即便寫著與故鄉無關的作品也會在其中發現故鄉的影子。”[3]童年作為最初的生命體驗,金曾豪對其充分挖掘,使記憶擁有了深發和外化的多重可能。
(一)故園樂土——金曾豪散文的兒童視角
金曾豪童年與江南小鎮的零距離接觸,是他散文創作的靈感源泉。真實的場景、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故事,所有的真實都在真誠的筆下展現出來,理所當然地會給人一種真摯的親切感,卸下防備,欣然接納。用孩童的視角,親身經歷在江南小鎮發生的故事,于日常生活中感受人來人往的善意,享受柔軟又寧靜的氛圍,不追不趕地閱讀完整本書。
以自身為線索展開的長幼、同輩之間的人情網絡最是真摯動情。父親對于少年金曾豪有著深刻的影響。正如《樹德堂》里所寫的,他同病人侃侃而談,通察病理又善解人意。他的儒雅風度“和中藥店的情調是相一致的。”[4]父親常帶“我”來小坐片刻,陶冶情操、熟悉草藥,耐心告誡“我”好好練字,傳承家族的文氣和醫術。
母親善于講故事也勤于家務,是一個樸實善良的勞動婦女。她和“我”的互動都極為溫馨,具有濃郁的煙火氣。一家人在母親地帶動下圍繞著“家里的灶頭”熱火朝天的忙活起來,巧手的母親用簡易的食材烹制出味美的菜肴。而在《螢火蟲,夜夜紅》中,母親用夸張的想象將豐富的人生經歷編織成趣味紛呈的故事,給予了“我”最初的文學啟蒙。
孩提王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度,兒童游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金曾豪筆下的同輩友誼是這樣的純粹。《呼鴨》中男孩子與鴨子上天入、地槍林彈、怪叫連天、水花四濺的激烈戰爭,《螢火蟲,夜夜紅》摸著黑的“轉轉”經歷,《電影船》斗智斗勇、“忍辱負重”的潛伏……這些游戲活動并非出于什么功利的目的,而是任憑天性,有感而為,飽含著旺盛的生命活力和無限的好奇與創造。
這些文章通過孩童的視角重新梳理了往昔細碎的日常,折射出一種純粹且真實的老派的歲月靜好,讓人不禁被這個柔軟清麗、人情溫婉的江南小鎮俘獲。
(二)得失長歌——兒童視角下的成人思考
江南文化是感性的,它能發掘苦難掩埋的詩意。金曾豪是敏感的,他能洞察主流裹挾下的私語。文化和作家一拍即合,淡淡的憂愁成了文學最蘊藉的底色。
社會的動蕩,人性的破敗并沒有粉碎金曾豪純凈的童心和對生活的摯愛,他將對逝去故鄉的無限眷戀與憐惜付諸筆端,以童年時代的自己為錨點,用孩童的視角勾連起那個江南小鎮的風貌況味,行云流水的文字背后是一種穿透時空的在場感。他的作品洋溢著內在的愉悅和感恩,一絲不茍地清點著故鄉給予自己的每一份饋贈,每一絲感動。如茶館中“可以清心也”漢字獨特妙處的饋贈;評彈給予的文學藝術方面的教益;中藥材具備的文化魅力;灶頭帶來的美食與家人互動的溫馨;月亮下的故事會……
“童年推到了一堵堵文字的高墻出來,那些漸漸消逝的事物被張開的手臂攔住。”[1]悠遠的回憶能讓快樂褪色成憂傷,熱鬧的老茶館,清澈的河流,八音刀的絕技,灶火,老樹,白雪,沈興,父親,母親都成了淡淡的影子,再見不到。
貫徹在金曾豪行文之中的歡喜和憂傷,緊緊的貼合著“得到”和“失去”,就好比那理發店里的那一幅西洋風景畫,“得到”它的時候,年少的金曾豪是何其地感動。可終究是“失去”了,“那幅風景畫已經不在了,鏡框里換了偉人的照片。”[4]在特定的歲月里,生活和人性失去了聲音,逝去注定無法挽回,但它已經以更美好的形式被永久銘記,“找不到這幅畫可能不是壞事,真找到了,說不定反而會破壞了珍藏在我記憶中的美麗。畢竟,用現在的眼光看,那也許只是一幅印刷粗糙的風景畫而已。”[4]金曾豪也許就是懷著這樣憂郁而慶幸的復雜心情,去書寫那個失落的江南吧。
三.生活的江南
溫養在江南自由溫潤的文化風氣里,無論是販夫走卒還是知識分子,都擁有健全的人格精神和樂觀的生活態度,他們所參與創造的風俗無疑是汪曾祺口中“生活的抒情詩”。而金曾豪也致力于去描繪這些可親可敬的小鎮居民,這種淳樸健康的民俗風情。
(一)活色生香——金曾豪散文中的風俗現場
茶館開的最早也總是最熱鬧,茶客大多是熟客,老年人居多,常攜鳥帶狗,談天說地—— “上至國際風云軍國大事,下至家長里短雞毛蒜皮”,“若是發生家庭矛盾、鄰里糾紛,當事人往往會約定到某茶館‘吃講茶。”[4]茶客們多厚道熱忱,正義感十足地主持公道,又能侃能說,就像幾個老人議論瞎子阿炳,離奇靈活的開頭創作也為生活潤色不少。又比如說書的男女先生。“遠遠不只在講故事,他們把難敘之事娓娓道來,把難狀之物呈之目前,把難言之情訴出微妙,看似隨口而出,其實句句都是有心。”[4](《茶館》)傳神生動的說書,溫文爾雅的先生,聚精會神的聽眾,偷聽的孩子還在和蚊子戰斗。事后還會有懂行的聽眾和評彈藝人交流切磋,共同傳作。這小小的一個剖面就把小鎮人們日常時光的怡然自得,鄉間鄰里的親切熱絡,生活觀念的樂觀積極寫得極真極醇。
畢竟民以食為天,小鎮的吃食自然是極豐富又極考究的。金曾豪打小又是極熟絡,對小鎮的美食地圖了如指掌。鋪開來講,茶館里的排骨面;書場上西瓜子、南瓜子、花生米之類的消閑小吃;曾舅母的鴨蛋;巷口的臭豆腐干、爆米花、麥芽糖、螄螺;自家灶上的飯粢糕,大鍋上的一品鍋、螃蜞豆腐……江南人既勤快又手巧,也樂于琢磨吃的花色,外面的零食能點嘴,家里的菜色又穩夠自足,自然便宜貪嘴的大人孩子。金曾豪是極懂行的:“‘喊面要講清楚加什么面澆,還有是否免青,是否緊湯什么的。‘免青就是免放蔥花。那時我常想,‘免青的人真憨,那灑了蔥花的湯面有多香啊!”[4](《茶館》)即使只是小生意,茶館也很是上心厚道。面怕冷,故放在籃子由小伙計提著跑,即使是清湯寡水被蔥花吊了味以后也是香極,更別說讓狗饞的不能自已的排骨面。而極香又極臭的臭豆腐干,“賣家就把炸成金黃色的臭豆腐干放在一片綠色的通心葉上遞給你。鍋邊小幾上備有紅色的辣醬,任你去抹。翠綠、金黃、鮮紅組合在一起,悅目得很。花幾分錢可獲得味覺、嗅覺、視覺三方面的愉悅。”[4](《巷口小吃》)這寫法,儼然是在刻畫一件不得了的藝術品,而吞吞吐吐、神神秘秘的店家也儼然一副高人做派,讓人愈發好奇。這些立體式的吃喝玩賞倒也將江南人滿地雞毛里娛樂精神發揮到了極致。
金曾豪所描繪的這個粗看有些土氣,實際卻滿是親昵人情的“土熟”風俗現場,將老派江南骨子里的溫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生活歌者——金曾豪散文中的可愛小人物
創造并享受著這種美好風俗的人們,是金曾豪散文著力更深的生活主人公。他們在并不富裕的物質條件下,仍秉持熱愛之心,是羅曼羅蘭筆下當之無愧的英雄。
比如說《八音刀》里三位各具特色的理發師:“刀功了得,傳說年輕時能用剃刀劈死飛過的蒼蠅”[4]的沈興;擅長“緊拉慢唱”剪子功夫的雄生,被喜歡掏耳朵的顧客青睞的永生。除了本職理發,理發師可以說是身兼數職、多才多藝,有什么困難求助,一支煙的事兒。此外沈興的心寬體胖,愛開玩笑,雄生的聽書黃酒,他們恪守職業道德,他們也享受生活,這群匠人的形象栩栩如生。推銷梨膏糖的小販“小熱昏”總唱著那首即興的開場曲《吃不吃歌》,總能通過一些有趣幽默或刺激或通俗的故事吸引人們,善于演繹神話傳說的年輕理發師前前老可以把孩子唬得一愣一愣的。金生老漢是個養牛老手,最神的是他能從牛胃里取出異物。老漢養的獨角牛忍受痛苦保護小主人,而老漢則保護刺傷他眼睛的獨角牛。牛與人結下深深羈絆,老漢牽獨角牛,兩個老伙計晃晃悠悠的走過橋。這些人們構成了小鎮最主要的故事,以他們堅韌樂觀的性格謳歌著生活。
生活的歌唱者不僅僅是他們,書里的歌者是這些可愛可親可敬的小人物,而書外的歌者則是金曾豪。他極大的削弱了現實的矛盾,絲毫沒有舊時代的陳舊氣息,他深知他的文字并非對于生活的嚴刑拷打,致力于發掘一些瑣碎的日常,去寫茶客閑談,先生說書,少年少女的呼鴨,船上的電影,巷口小吃的制作銷售……從這些熱氣撲騰、有滋有味的民俗現場,追尋其背后的美好人性,文化不滅的“童心”。
結語:但如今江南文學卻深陷失語的四重窘境:基于近代文化格局西方哲學理論的大框架,中華文化的生態空間遭到了極大的擠壓,身為非主流文化且拒絕政治發聲的江南文化更是受到了孤立。同時狹隘化的自身創作,較低的文化產能,以及最為關鍵的被迫同質化的現實土壤,都使江南文化處于近乎絕境的話語邊緣。
而金曾豪試圖用一種語言,一種文字去復活江南,使具有地域美,個人情,生活真的唯美江南從失語的泥濘中掙脫。他通過對江南地域最為真摯純凈的描摹,用清醒而又清晰,精致而又謹慎的筆調,以無以匹敵的生命意識,將江南的物與人緊密的羈系起來,使得慣常的私人庭院式的物質江南躍遷到精神故里式的靈魂江南。
遠離政治云煙,摒棄現實喧囂,以瑣碎描繪真人間,用日常謳歌真性情。金曾豪筆下的老派江南,有草間的螢火,有船上的電影,有巷口的小吃,有遠去的呼聲,有棚下的白羊……蒙著薄薄微雨,并不明媚,但已足夠溫馨。在鋼筋混凝土的寂寞現實蹣跚遷徙滿身塵埃,驀地看見這樣一個熟悉的江南,怎能不悵然而涕下?
參考文獻
[1]車前子.江南話本[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2.12
[2]錢歌川.巴山夜雨[A].//俞元桂,姚春樹,汪文頂,等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卷二.1990:215
[3]莫言.每一個寫作者都離不開鄉土[N].檢察日報.2007-4-27(BI)
[4]金曾豪.藍調江南[M].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3.
[5]樊均武.水性江南:近現代江南散文的觀照視角與審美特質[D].浙江師范大學,2011.
[6]周紅莉.江南意象的記憶與闡釋——論90年代后江南散文[J].文藝爭鳴,2006(6).
常熟理工學院大學生創新項目課題論文。項目名稱:《金曾豪散文與“江南現象”研究》;編號:XJDC2019183;參與人:陶開顏,查能;導師:周紅莉,常熟理工學院,教授。
(作者介紹:陶開顏,常熟理工學院漢語言師范專業學生;查能,常熟理工學院漢語言師范專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