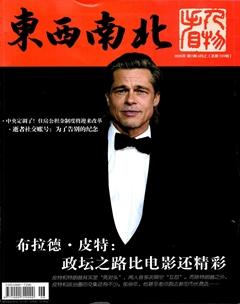王文博:雷神山醫院唯一的志愿者
陳莉莉

其實,剛開始他什么都不懂。
2020年1月25日,武漢宣布封城的第三天,甘肅人王文博從蘭州趕往武漢,給武漢的醫院運送物資,主要是甘肅的土豆和蘋果。
2020年2月16日,王文博成為雷神山醫院的志愿者,工號ZY0001。
在此之前,他經常打交道的是農產品,那天以后,則是傳染、疾病與生死。“正壓、負壓、液氧、醫廢”代替“土豆、蘋果、黃芪、寬粉”,密集地出現在從那天以后的時間里。
回到蘭州,翻看雷神山醫院的照片與視頻,他希望可以快點忘記。似乎只有忘記,才可以開始接下來的日常。
2020年冬末春始,他與人類新發現的一種傳染疾病短兵相接的經歷,足夠讓他更加飽滿地行走在人生路上。這場疫情中有太多個“王文博”,他們再普通不過,卻讓人們在慘烈的悲痛中看到了溫暖與希望。
瘟神
1月23日的早晨,剛起床的王文博看到了武漢封城的信息。
1月25日,封城第三天,生于1990年的王文博從蘭州啟程進武漢。蘭州鐵路系統給武漢捐贈一批物資,王博文申請隨車。
回到蘭州以后,一個朋友要捐贈蘋果。王文博找了很多人幫忙運輸,“沒有人愿意來”,最后找到了甘肅方舟救援隊。過去王文博就在方舟救援隊當志愿者,“有災難發生時,第一時間去現場”。
1月25日到2月13日,他和救援隊一起運送物資。王文博多是用自己的車,蘭州到武漢往返3000多公里,那段時間,他的車跑了4萬多公里。
路上總有些難忘的事情。有一次,從武漢回蘭州的高速上,在陜西藍田服務區,王文博和他的運輸團隊被陜西省藍田交警扣了下來。
“我是在捐贈物資返回蘭州的路上,不是逃離武漢。”王文博給湖北打電話,對方說你已經出了湖北,不在湖北的管理范圍;給陜西打電話,對方說你聯系我們防疫總指揮部,聯系以后,對方說不知道這回事。
那沒辦法。前、后各一輛警車,把王文博和他的運輸團隊帶到一個醫院做檢查,量體溫。當地工作人員說他們收到消息,得知王文博團隊里有確診的。
他們把王文博從醫院拉到了一個隔離點,每個人相距恨不得10米遠,王文博想跟他們說話,他們立刻伸出胳膊說,“你不要過來。”
王文博有甘肅省的捐贈文件,也有湖北省的接收文件,也有通行證,所有證件齊全。到了隔離點,工作人員也很懵。
王文博給當地紀委打電話,“很離奇”,當天下午6點多,王文博他們就可以走了。還是把他們扣下來的那批人,把他們送了回去。前、后警車,從陜西省藍田縣送到了甘肅省寶雞市境內,200多公里的路程。
唯一
有一次,王文博給雷神山醫院送物資,但是東西到了庫房,沒人卸,對方說現在找不到人。
王文博說:“那我能來么?”對方說,那肯定不可能。后來王文博知道他是雷神山醫院庫房組組長。
2月9日,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全面接管雷神山醫院,需要成立“黨員突擊隊”。王文博看到組長發了一個朋友圈:雷神山醫院招募志愿者,必須是武漢本地人。他不是本地人,但帶著黨員證過去了。
雷神山醫院黨建人事處的處長說,“醫院不管你防護、不管你住宿,只管你吃,其他全靠你自己,沒有報酬,萬一被感染了,不負責。”王文博說,“行。”對方說,“那你明天來吧。”
真正過來了以后,就不一樣了。醫院每天發口罩,經常發一些小零食。在雷神山醫院里住了4天,因為是活動板房,不隔音,睡得不好,他就被安排到了外面住。王文博就說他們在騙他,剛開始說的條件那么差,后來對他又那么好。“他們就想看看我的決心程度。”
在武漢,王文博認識很多志愿者,本地的、非本地的,沒有人會選擇去醫院。
最缺人的時候,有的醫院找保安要付1000元一天的報酬。在王文博看來,“那時候每一個愿意出來工作的人,都很偉大”。
王文博的同事全部是來自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和武漢第三醫院的工作人員,他是唯一一個志愿者。拿到工牌(ZY0001)的時候,王文博特別開心。他就問,這個號怎么這么好啊?工作人員說,“只有你一個。”
王文博就說,“那如果以后再招志愿者,我是不是可以當組長?”對方說,“沒問題。”直到離開,他是他自己一個人的組長。“以為是第一個,結果是唯一一個。”
那時候他不知道ICU是什么,也不知道正壓、負壓、液氧、醫廢、污水處理池是什么。
他是一個完全沒跟醫院工作打過交道的人,但是進到醫院后,有工作任務時,他收到的指令是把這個做了,把那個做了,“全是專業術語”。

他們告訴王文博什么,他第一件事情是先去百度,大概了解一番,再下手去做。他“喜歡多管閑事”。平衡車壞了,他會修,無人機來了,他會操作,需要寫資料了,他會寫,庫房亂了,他會整理。
在同事肖琳琪的眼里,王文博“神通廣大”,會很多技能。
陽性
是醫院就有風險。
2月16日,王文博到雷神山醫院報到的第一天。
剛進辦公室,工牌還沒拿到,一個人過來對他們說:“趕緊全部都出去。”有點懵,他隨著緊張的人群跑出了辦公室。出來還聽得到里面的人在打電話:我們的命不是命嗎……
后來了解到,前一天辦公室里的一批人中有3個人核酸檢測陽性,要先對辦公室全面消殺,“把桌子上那些喝的、吃的、用的,全部拿出去扔掉了。”
好多人都說王文博像中彩票一樣:“剛來第一天,辦公室里就有人確診。”
一個多月的時間里,王文博辦公室里的工作人員經歷了好幾起“測出來有問題”。包括王文博自己。
身邊有人感染了,王文博和他辦公室里的同事們就需要做檢查。王文博前后做了5次檢測。剛開始他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來才知道。3月8日,王文博血清抗體檢測雙陽,他被要求回住處隔離。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感染的。后來又查CT、測核酸,回蘭州前,他又去測了血清抗體,一個陽性一個陰性。醫生說他這是自愈了,有抗體了。“這么重大的一個病,沒有感覺到就已經結束了。”
來武漢之前,他問了在醫院工作的朋友,朋友說,只要防護得當,應該沒什么。退一萬步講,真的被感染了。“只要休息得好、吃得好、抵抗力強,這個病就不怕。”
他說他看到血清抗體檢測結果是雙陽時,他想的就是:“我的體質還行,能扛過去。”“其實,如果有萬一,我還有一個哥哥。”
造業
因為前期捐物資,王文博跑遍了武漢所有的醫院。
王文博曾想去金銀潭醫院做志愿者,但是金銀潭醫院表示堅決不招志愿者。“他們說極度危險。”
他需要去金銀潭醫院送物資。其實直到現在,他也想不起從哪個門進去的,他好像是穿行了整個醫院。剛開始保安跟著他,后來保安不走了,說“你自己往前走吧”。
深夜,一個人,醫院里的樹很低。一個穿著“特別嚴密的防護服”的人看到了他,問他來做什么,王文博說來捐贈物資,她驚呼幾句本地話,后來王文博問了當地人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說造業啊,造業啊。她說你知道這是啥地方嗎?這是毒窩,你知道嗎?”在王文博看來,她特別恐慌。她對王文博說:“你們捐的東西值多少錢?比命重要?”
她聲音很大,一面大聲喊,一面給他全身消殺,她說:“對面的方艙醫院(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有2000多病人,我們這里有800人。你送完物資趕緊回去,別在武漢待了。”
她的聲音和動作,讓王文博感覺有點兇,但他知道她是善意的。她說王文博戴的口罩是假的KN95,“沒有用”,她給了王文博一些處方藥,一副護目鏡,一套防護服。那套防護服,王文博后來送給了另一家醫院的醫護人員。
到了雷神山醫院當志愿者以后,有一天突然想起來這件事,王文博問同事:“你們這里‘造業是啥意思?”他們說:“遭罪,可憐。”
在中南醫院的經歷,王文博覺得他們很嚴格。與王文博對接的工作人員對王文博說,“你離我遠遠的,不要過來。”他們正好就在發熱門診的樓上,他們把接收單給王文博時,用酒精噴了好幾遍,噴完以后放在那里,讓王文博自己取。
辛苦、夢想、勤奮
從3月15日開始,辦公室里每天都問王文博什么時候走。每次問到這個話題,就一片沉默。
有一個處長問王文博,“如果雷神山醫院給你們單位發函,能把你留在這里嗎?”王文博心里想,主要是我自己覺得可能沒有太大價值。
有一天,王文博照舊被隔壁辦公室借過去。他聽到了肖琳琪的聲音:“我們怎么把他留下來,他真的幫了我們好多忙。”他們希望王文博跟他們一起等到雷神山徹底關門再走。討論了很長時間,他們不知道隔壁的王文博在流眼淚。

王文博說他覺得自己其實什么都沒做。“可能就是因為特殊情況下相處的感情,就特別珍貴。”
有一次需要王文博處理的工作,他覺得有點不對勁,因為他認為有很多是涉密的信息。他專門去問涉不涉密。對方說:涉密。他不知道他怎么得到這么高的信任。他特別感動。
臨近離開,很多事情又找到了他,甚至捐贈庫房的鑰匙也交給了他。但是他發現,工作量很大,沒有十天半個月干不完,而他可能過幾天就要走了。“他們就說你想想辦法,你肯定有辦法。”
“你們是想用工作留住我嗎?”對方說:“我們都是這個想法。”
王文博說他不知道該怎么拒絕。“都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如果我走了,這些工作怎么干?”
20多天沒整理的庫房交到王文博手里,他用了兩天整理得差不多了。那天晚上王文博吃了三碗米飯、兩份盒飯。“又被夸了一遍。每天都在夸贊中度過。”
告別在即,同事程勵用無人機做了一段視頻送給王文博作為分別禮物。視頻里,王文博穿著紅色的衣服,站在“武漢雷神山醫院”前,對著鏡頭揮手。
來的時候沒想到會在武漢待那么長時間,帶的衣服不多。到了這里以后,這個(醫療隊)給一件,那個(醫院)給一件,現在他有十幾件顏色不一的沖鋒衣,他把它們帶回了蘭州,留作紀念。
雷神山醫院給他做了一套衣服,寫他的名字:“武漢雷神山醫院王文博”,也會有一雙寫有他名字的鞋,他覺得這段時間“全套蹭吃、蹭穿”。
王文博的網名叫“辛懵溱”,解釋起來就是:辛苦、夢想、勤奮。他說他的想法再樸素不過:勤奮以及不怕辛苦,就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就是覺得“夢”與“勤”太簡單了,“不夠感覺,就找了兩個不太常見的字”。(文中程勵為化名)
(張麗薦自參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