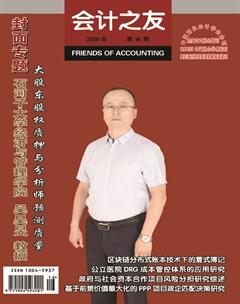黨組織治理與國有企業創新績效
王中超 周紹妮



【摘 要】 堅持黨的領導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如何在國有企業中探究黨組織治理的作用及其途徑是理論和實務領域討論的重要問題。以2012—2017年國有上市公司為樣本,考察黨組織參與治理對國有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表明: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國有企業創新績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相對于發明專利,非發明專利對創新績效的提升貢獻更明顯。進一步研究發現,公司黨委主要通過參與董事會以及管理層治理來發揮對創新績效的積極作用。研究結論為完善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培育世界一流企業提供了參考。
【關鍵詞】 黨組織; 治理參與; 企業創新; 國有企業
【中圖分類號】 F27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0)16-0126-07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雖然目前關于“世界一流企業”的評判標準尚存爭議,但毫無疑問對企業創新能力的衡量必然包含其中。作為國民經濟的“壓艙石”,國有企業更是國家經濟創新體系的重要主體,其創新能力與活力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國家經濟發展與運行的狀態,事關“新常態”下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目前,在黨中央強化對國民經濟和國有企業領導的背景下,公司黨委成員通過“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制度安排參與治理是我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的一大特色。由于黨組織對國有企業領導人直接的人事任免權及控制權[1],公司黨委成員兼具動機和能力將黨的意志內化到公司治理行為中并產生相應的經濟后果。
已有研究發現,公司治理的相關特征對企業創新有著重要影響[2-3],甚至是制度基礎[4]。隨著創新理論的不斷發展,學者們基于傳統的公司治理視角從內部的代理沖突[5]、管理層激勵[6]、股權結構[7]擴展到企業外部的產業政策[8]、經濟聚集[9]、甚至國家文化[10]等方面展開了積極探索。黨組織通過“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制度安排參與董事會、監事會以及管理層對企業經營管理以及決策施加影響,發揮治理作用[11]。那么,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是否會影響企業創新活動呢?如果存在影響,影響的路徑是什么?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以2012—2017年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考察了黨組織參與治理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黨組織參與治理對創新績效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通過研究影響路徑發現,黨委主要通過參與董事會與管理層發揮對創新的積極作用。
與以往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貢獻有:第一,基于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視角,考察了其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為企業創新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豐富了企業創新動因研究的相關文獻,也從理論上提供相關經驗證據加以指導實踐。第二,在當前黨中央強化對國有企業領導的背景下,豐富了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經濟后果相關研究,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作用提供了新的證據。第三,研究發現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國有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更多體現在追求“數量”的非發明專利上。這為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維護良好的治理環境以及有關部門制定完善對國企及其領導人的考核要求,合理引導國企創新行為,提升創新質量提供了有益的實踐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早期學者們通過理論分析探討了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相關問題,主要集中于黨組織如何參與治理以及如何與現代企業制度融合等問題的探討[11],缺乏大樣本實證數據的檢驗。近年來,學者們通過實證研究豐富了黨組織參與對公司經濟后果影響的相關文獻。馬連福等[12]研究發現,黨組織參與有利于提高董事會效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陳仕華等[13]在考察黨組織參與國有企業并購活動中發現,黨組織參與對并購溢價有顯著作用,能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現象,該作用在黨組織參與董事會、監事會中更加顯著。于連超等[14]也發現黨組織參與董事會和監事會時作用顯著,會顯著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水平。此外,部分研究發現,黨的組織部門或者紀檢部門參與還有降低代理成本[15]、抑制高管薪酬[16-17]、減少非貨幣性私有收益的作用[18],對企業績效有積極作用[19]。還有學者從審計研究角度出發,發現黨組織參與增加了國企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具有信號傳遞效應[20],顯著降低了被出具非標意見的概率[21]。
具體到國有企業創新活動的研究背景中,雖然目前學術界對國企的創新效率尚存爭論,有觀點認為相較于民營企業,國企創新存在雙重效率損失,國企創新效率較低[22],也有人認為由于面臨更有利的外部環境,國企的創新效率高于民企[23]。但毫無疑問,既然創新活動是企業的重大經營管理決策,在深化黨組織領導的國有企業中,黨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必然會對該項活動產生重要影響。誠然,從研發投入到最終實際的創新產出之間有較長的作用鏈條,企業同時也面臨高投入是否就能帶來高產出等問題。一方面,在當前“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制度安排下,黨委成員同時任職公司董事、監事、管理層,使得黨委成員有能力在企業創新的全過程參與其中,發揮治理、監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提升創新水平,推動高質量發展,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的戰略目標下,作為國民經濟的排頭兵,國有企業也有義務在創新發展方面承擔相應的責任。國企黨委為發揮政治領導的作用,通過參與董事會、監事會以及管理層對創新活動產生影響。基于此,提出假設1。
H1:黨組織參與治理能夠提升國有企業創新水平。
此外,在國資部門對國有企業及國企領導人年度及任期雙重考核的背景下,國企領導人往往對更能顯示其政績的項目有明顯傾向[24]。一方面國企承擔了國有經濟創新主體的責任,另一方面在黨管干部的制度安排下,黨委成員本身作為企業領導人之一若還同時擔任公司董事、監事或者管理層職務,那么黨委成員應當會通過其兼任職務來實現上級部門對企業創新方面的考核目標。例如,黨委成員同時也是董事會成員時,“討論前置”程序能夠節約溝通時間,使得黨委把關的“三重一大”決策充分傳達給董事會成員,有利于保證黨的路線、方針與企業經營決策相結合。而監事會的本質是對公司經營業務及財務等方面的監督,是現代公司治理內部的重要制衡機制,它通過“健全機能”與“激勵機能”來對企業經營管理活動進行監督。相對于董事會對創新過程的直接作用,監事會成員更可能是通過“間接”渠道,來發揮對企業創新產出流程的監督作用。因此,相較于監事會的“事后監督”,董事會由于在“事前決策”上發揮作用,對創新活動的激勵效果應當更強。管理層由于在創新活動中處于“第一線”的位置,公司黨委成員兼任管理層有利于落實黨對創新型企業的號召,更有效地分配公司資源、加強對創新過程的管理。此外,根據資源依賴理論,存在“交叉任職”的公司有利于加強與外部的政治關聯,以謀求更多的企業資源,從而作用于企業創新活動。但是,有研究發現黨委書記的多重任職有損于公司運營效率。因此,可能由于上述兩種效應同時存在而導致“交叉任職”的觀測效應不明顯。綜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設2。
H2:從黨組織參與對創新活動的作用路徑來看,相對于參與監事會和交叉任職,參與董事會與管理層的治理效果應當更為明顯。
三、樣本選擇與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為檢驗黨組織治理與國有企業創新活動之間的關系,本文以2012—2017年我國A股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黨組織參與數據的具體獲取過程如下:首先通過手工翻閱公司年報“高管個人信息”部分,查找黨委成員是否兼任公司的董監高;其次,在認定黨委是否參與公司董監高治理時,不僅考慮本公司黨委參與情況,還將在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單位擔任黨委職務同時又擔任本公司董監高職務的成員也考慮進來。理由是國有控股股東單位黨委委派的董監高必然會推動落實上級的政策和方針,從而可能對企業創新活動產生影響。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國有企業幾乎都建立了公司黨委,但是由于公司黨委相關信息為非強制披露的信息,有些公司并未通過企業年報、公司官網等途徑反映,這部分國有企業的樣本無法獲取,因此不在本文觀測值之中。專利申請及公司財務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并剔除以下樣本:(1)金融保險類公司;(2)ST、PT等特殊類公司;(3)關鍵數據缺失的樣本。經整理,得到有效樣本1 764個。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定義
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來考察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
INNOVATION=β0+β1PAR+β2MARKET+β3CFO+
β4PPE+β5SIZE+β6ROA+β7GROWTH+β8LEV+β9AGE+
β10TQ+β11AF+β12MHOLD+∑INDUSTRY+∑YEAR+ε
(1)
INNOVATION是創新績效的代理變量,以企業年度申請專利(PAT)數量衡量,并借鑒黎文靖等[8]的思路,將年度申請專利進一步區分發明專利(PATFM)和非發明專利(PATOT)。
PAR為黨組織參與治理的代理變量,分別用黨委成員擔任董事會成員比例(PARD)、黨委成員擔任監事會成員比例(PARS)、黨委成員擔任管理層比例(PARM)(“雙向進入”)以及黨委(副)書記任董事長、監事長或總經理(CROSS)(“交叉任職”)4個指標來衡量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本文關心的是變量PAR的系數β1。根據上文假設,預計β1的系數顯著為正。
控制變量方面,本文參考了Hirshleifer et al.的做法[25],選取了市場化程度(MARKET)、現金流量比例(CFO)、固定資產比例(PPE)、管理層持股比例(MHOLD)、公司規模(SIZE)、盈利能力(ROA)、分析師關注度(AF)、成長性(GROWTH)、資產負債率(LEV)、上市年齡(AGE)、市場價值(TQ)。此外,還控制了行業(INDUSTRY)和年度(YEAR)的虛擬變量。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為減緩內生性對研究的影響,將所有控制變量采取滯后一期的方法處理,并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水平上進行Winsorize處理。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創新績效來看,發明專利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6.465,標準差為1.493,可見樣本公司的創新水平差異較大。此外,公司平均擁有的實用新型專利與外觀新型專利之和多于發明專利。從“雙向進入、交叉任職”來看,公司黨委成員任公司董事會成員的比例是19.3%,黨委成員任監事會的比例是17.8%,黨委成員任管理層的比例是10.8%,約73.6%的國有企業存在“交叉任職”的情況。
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分年度統計數據顯示,近三年(2015—2017年),黨組織參與治理的程度呈上升趨勢,具體表現為黨組織參與董事會比例由2015年的18.3%提升至2017年的20.5%,參與監事會比例由2015年的13.8%提升至2017年的17.7%,參與管理層比例由2015年的10.1%提升至2017年的14.2%,交叉任職比例也由2015年的79.6%提升至2017年的82.3%。這體現了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以及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不動搖方針,突出了本研究的現實意義。
(二)回歸分析結果
表3列示了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國有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變量PARD、PARM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且達到了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黨委成員參與董事會、管理層比例越高,對企業創新績效水平的促進越明顯,H1得到支持。如前所述,國資委對國有及國企負責人考核辦法既涉及業績考核、基礎管理等方面,更涉及企業的長期發展方面,例如企業創新能力。因此,對于任董監高的國有企業黨委班子成員來說,在貫徹執行黨的大政方針時,其更有動力響應“創新型國家”“世界一流企業”等號召,從而加強創新活動過程中的管理和執行,提高了創新活動的效率,使得創新績效水平提升。此外,監事會參與對創新績效水平雖然表現為正,但未達到顯著性水平,可能原因在于董事會和管理層相對于主要起監督作用的監事會更有利于發揮在企業創新活動中的決策與管理作用。而“交叉任職”的代理變量CROSS可能由于同時具有激勵和弱化效應使得其在創新績效水平上并不顯著,H2得到支持。
進一步的,將創新績效分為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三類。一般認為發明專利屬于“高質量”創新,而后兩者創新難度及水平相對較低。根據上文,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會提升創新績效,那么創新產出更多是發明專利還是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呢?這關乎到創新質量的高低,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將黨委參與程度與創新的類型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1)至(4)列為黨委參與程度對發明專利的回歸結果,(5)至(8)列為黨委參與程度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的回歸結果。對于創新質量較高的發明專利而言,僅僅在黨委參與管理層中發現了對發明專利較弱的促進作用,表現在(3)列中,變量PARM的回歸系數為正,達到10%顯著性水平。由(5)至(8)列可以發現,黨組織參與程度對國有企業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有更明顯的促進作用,表現為變量PARD、變量PARM分別在1%、5%的水平上顯著。
值得關注的是,相對于發明專利,黨委參與對實用新型、外觀設計的發明提升作用更加明顯。這與黎文靖等[8]研究得出企業可能存在策略性創新的結論有相似之處,即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國有企業創新也可能存在“策略性”。針對這種情況,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現有國企領導人考核制度、黨管干部的背景下,相對于創新的“質量”,擔任董事會和管理層的黨委成員更加關注創新的“數量”,為達到業績考核要求,從而分別在決策和執行層面以響應黨中央提出的相關號召。此外,從作用路徑來看,依然是黨委成員參與董事會與管理層時促進作用顯著,再次驗證了H2。
(三)穩健性檢驗
1.Heckman兩階段回歸。本文黨組織治理數據通過手工收集公司年報中“高管個人信息”部分,查找黨委成員是否任職公司董監高獲得。為了緩解只選擇披露黨組織成員任職情況的樣本所帶來樣本選擇偏誤問題,使用Heckman兩階段回歸法增加結論穩健性。第一階段以是否披露黨組織成員任職董監高為被解釋變量,以企業最終控制人是政府部門還是國資部門(用CONT表示,政府部門控制取1,國資部門控制取0)以及是否處于東部地區(用EAST表示,東部取1,否則為0)為解釋變量,控制變量選取與模型1中控制變量相同,進行Probit回歸得出逆米爾斯比率(IMR),在第二階段回歸中將變量IMR作為新的控制變量用模型1對創新績效(PAT)進行回歸以檢驗樣本選擇偏誤問題。選取變量CONT的理由是最終控制人關系到國有上市公司的管理體系,當屬于國資監管部門管理時為垂直管理,此時有利于“上傳下達”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當屬于地方政府部門管理時為屬地管理,此時管理形式更加靈活多樣,便于執行地方政令。因此,二者管理體系的差異可能影響國有上市公司的黨組織信息披露情況。此外,選取變量EAST的理由是,有研究表明,在市場化程度不同的地區,政府對國有企業干預程度不同,導致其信息披露行為有所不同[27]。當國有企業處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企業受政府影響程度相對較高,此時披露黨組織相關信息可能性更高。
表5報告了Heckman兩階段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最終控制人是國資部門、處于非東部地區的公司年報中披露黨委成員的可能性更大,這與馬連福等[16]的研究相符。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發現,逆米爾斯比率IMR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的確存在樣本選擇偏誤的問題,但核心解釋變量依然顯著為正,表明在考慮了樣本選擇偏誤后黨組織參與對創新產出依然是正向的促進作用。
2.傾向得分匹配。盡管主回歸分析中使用了控制變量的一期滯后項以緩解內生性,得出黨組織參與治理能提升國有企業的創新績效,但此結論可能仍面臨內生性問題,即在創新績效更高的國有企業中是否黨組織參與治理的可能性更高呢?為緩解此問題,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控制樣本選擇偏誤。借鑒陳仕華等[13]對黨組織參與變量二元劃分的做法,當公司黨委成員任職董事、監事或高管時取1,否則為0,將原主檢驗中核心解釋變量的連續變量替換為二元制指標以進行傾向得分匹配。配對時,為保證盡可能減少主觀影響,將全部的控制變量選取為匹配變量,同時,使用較為穩健的核匹配方法進行檢驗。匹配后除個別變量外(變量LEV和變量MOLD),其余匹配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均小于10%,T檢驗顯示匹配后實驗組和對照組無顯著差異,表示匹配效果較好(限于篇幅該結果未匯報)。
表6報告了采用PSM法后,處理效應的檢驗結果。變量PAT和PATOT的ATT估計值分別為3.781和2.892,均大于臨界值1.96,達到顯著性水平,而變量PATFM的ATT估計值雖然為正,但未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黨組織參與對創新績效有顯著提升,對非發明專利的產出提升明顯。因此,在經過傾向得分匹配法進一步控制內生性之后,回歸結果仍然支持了上文的結論。
3.其他穩健性檢驗。將縮尾程度擴大至5%,進一步降低極端值影響;減少樣本量,以2013—2016年間的樣本進行檢驗。總的來看,結果未發生根本改變。
五、結論與啟示
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的背景下,發揮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的領導作用,使國企成為國民經濟向好向上發展的“壓艙石”,關鍵要找到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作用的證據,從而為落實兩個“一以貫之”與相關的國資國企改革措施提供方向。基于此,本文以2012—2017年國有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手工收集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相關數據,驗證了黨組織參與對國有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的相關證據。研究發現:(1)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創新績效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2)相對于發明專利,非發明專利對創新績效的提升作用更大,說明現階段公司黨委對創新績效更多關注“數量”。(3)從作用路徑來看,公司黨委主要通過參與董事會以及管理層來發揮對創新的積極作用。
本文的政策啟示在于:(1)在當前深化國企改革階段,要充分認識并發揮黨組織的積極作用,進一步出臺相關文件對黨組織的權力邊界及范圍進行合理指引,發揮這一制度安排的優越性。(2)盡力為企業黨組織配置政治素養與專業水平過硬的“又紅又專”人員,構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與環境,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以充分發揮黨組織對企業創新的積極作用。(3)考慮到目前黨組織治理對企業創新的促進相對集中在非發明專利上,政府有關部門在對國企及其領導人考核時應當區分創新行為的難度與創新產出的價值,合理引導國企創新行為,提升創新質量,以創新推動發展,早日實現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的發展目標。
【參考文獻】
[1] JOSEPH P H,FAN T J.WONG,TIANYU ZHANG.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corporate governance,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
84(2):330-357.
[2] BELLOC F.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a survey[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2,26(5):835-864.
[3] 魯桐,黨印.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分行業比較[J].經濟研究,2014,49(6):115-128.
[4] O'SULLIVAN M.The 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24(4):393-416.
[5] LA PORTA R L,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9,54(2):471-517.
[6] HOLMSTROM B.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1):74-91.
[7] 李文貴,余明桂.民營化企業的股權結構與企業創新[J].管理世界,2015(4):112-125.
[8] 黎文靖,鄭曼妮.實質性創新還是策略性創新?——宏觀產業政策對微觀企業創新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6,51(4):60-73.
[9] 董曉芳,袁燕.企業創新、生命周期與聚集經濟[J].經濟學(季刊),2014,13(2):767-792.
[10] CHEN Y ,PODOLSKI E ,RHEE S G ,et al.Local gambling preferences and corporate innovative success[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4,49(1):77-106.
[11] 吳敬璉.現代公司制度與企業改革[J].中國經濟問題,1995(4):1-10.
[12] 馬連福,王元芳,沈小秀.中國國有企業黨組織治理效應研究——基于“內部人控制”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12(8):82-95.
[13] 陳仕華,盧昌崇.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治理參與能夠有效抑制并購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嗎?[J].管理世界,2014(5):106-120.
[14] 于連超,張衛國,畢茜.黨組織嵌入與企業社會責任[J].財經論叢,2019(4):61-70.
[15] 余怒濤,尹必超.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了嗎?——來自中央企業監事會黨組織治理的證據[J].中國會計評論,2017,15(1):67-88.
[16] 馬連福,王元芳,沈小秀.國有企業黨組織治理、冗余雇員與高管薪酬契約[J].管理世界,2013(5):100-115,130.
[17] 陳紅,胡耀丹,納超洪.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管理者權力與薪酬差距[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8,40(2):84-97.
[18] 陳仕華,姜廣省,李維安,等.國有企業紀委的治理參與能否抑制高管私有收益?[J].經濟研究,2014,49(10):139-151.
[19] 郝云宏,馬帥.分類改革背景下國有企業黨組織治理效果研究——兼論國有企業黨組織嵌入公司治理模式選擇[J].當代財經,2018(6):72-80.
[20] 程博,宣揚,潘飛.國有企業黨組織治理的信號傳遞效應——基于審計師選擇的分析[J].財經研究,2017,43(3):69-80.
[21] 李世剛,章衛東.民營企業黨組織參與董事會治理的作用探討[J].審計研究,2018(4):120-128.
[22] 吳延兵.國有企業雙重效率損失研究[J].經濟研究,2012,47(3):15-27.
[23] 劉和旺,鄭世林,王宇鋒.所有制類型、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J].中國軟科學,2015(3):28-40.
[24] 周黎安,羅凱.企業規模與創新:來自中國省級水平的經驗證據[J].經濟學(季刊),2005(2):623-638.
[25] HIRSHLEIFER D A,TEOH S H,LOW A.Are overconfident CEOs better innovators?[J].Journal of Finance,2012,67(4):1457-1498.
[26] 王小魯,樊綱,余靜文.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6)[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27] 李慧云,劉鏑.市場化進程、自愿性信息披露和權益資本成本[J].會計研究,2016(1):71-7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