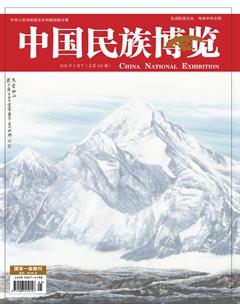空間的言說:中國國家博物館與石魯經典性的建構
【摘要】博物館是藝術社會學中賦予藝術品資格和認定藝術作品價值的重要環節。本文通過考察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建筑形制、藝術氛圍和梳理有關石魯的藝術展覽,探討了博物館建構石魯及其作品經典性的途徑和意義。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收藏、研究與展覽等行為是不斷賦魅石魯的過程,石魯作品價值也因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顯。藝術品的歷時性與共時性在博物館中相遇,中國國家博物館空間成為石魯經典性的重要建構之手。
【關鍵詞】中國國家博物館;神圣空間;藝術展覽;石魯;《轉戰陜北》;經典性;建構
【中圖分類號】TU236 【文獻標識碼】A
1917年,杜尚簽名“R. Mutt 1917”的《泉》因對傳統藝術標準的“褻瀆”而震動了當時的藝術界,這位反藝術的藝術家最終經由阿倫斯伯格夫婦將作品送入了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成就了藝術史的一個經典。博物館這類具有特殊意義的公共空間是承載人類歷史記憶和共同情感的容器,博物館所代表的藝術界的認可是藝術作品獲得資格和價值的重要途徑,由此,博物館締造著一個個藝術經典。
一、中國國家博物館類神圣空間的形成
從最初的巖洞和巢穴到后來的宮殿與房屋,空間的實用性追求不斷讓位于對情感、審美理念或某種社會話語的表達。因建造目的不同,有的空間成為意大利藝術史學者李格爾所說的“意圖性紀念空間”,而另一些則成為“非意圖性紀念空間”。意圖性紀念空間在修建時常以紀念碑、紀念館、博物館等作為主要表征,它不僅是物理空間,更營造了與紀念、追思、緬懷、懺悔和信仰有關的精神空間。意圖性紀念空間一般都具有類神圣空間的性質。
“神圣空間”本是一個與西方宗教信仰和宗教學研究相關的語匯,西方有學者從20世紀60年代已開始著重關注神圣空間(sacred space)的研究,我國學者目前對“神圣空間”的使用和研究雖多與教堂、神廟和祠堂等意圖性紀念空間相關,但也在不斷地將其本土化。神圣空間是國家和民族集體精神和共同信仰的儲存空間,是服務大眾的,是群體情緒的宣泄地。神圣空間是被構建出來的,它通過崇拜物和神圣氛圍的營造來使進入空間者心靈滌蕩,達到精神皈依的目的。進入近代社會以來,神圣空間在不斷世俗化的過程中逐漸與國家權力的干預密不可分。柯律格將1958-1959年北京興建的“十大建筑”(包括中國國家博物館)視為“黨對藝術的控制和贊助”。從興建初衷、博物館的形制與規模、空間氛圍的營造和所擔負的社會使命來看,中國國家博物館具有類神圣空間的性質,成為國家意志在藝術空間中的重要顯現。
中國國家博物館簡稱“國博”,前身為中央革命博物館和北京歷史博物館,最初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十周年而建,興建初衷已頗具政治意涵。國博地處天安門廣場東側,與人民大會堂相對,最初的設計就被納入了天安門廣場整體環境的考慮之中,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特殊。2003年,隨著中國的國際形象發生改變,國博啟動了改建工程,全世界90多位著名建筑界人士參與了設計方案的評審,方案后報國務院備案。1959年國博建成時已是中國十大建筑之一,“也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幾大博物館之一”,改建后的新國博則“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單體博物館”。國博通過廊柱、門、墻、屋頂、雕刻、建筑材質、裝飾物和色彩等營造了一種紀念性氛圍,建構著對國家和民族集體記憶。改建后,國博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央大廳四周的磚廳、木廳、銅廳和石廳以不同材質裝飾,均由大師親自完成,和國博劇場都以紅色墻幔進行裝飾。磚、木、銅、石都具有經久不變的物理特性,紅色是隆重、莊嚴的象征,體現了國人對革命歷史的追憶。國博展廳色彩基調為灰色,地面與墻面形成同一色系的呼應,展柜多是金絲楠木,這“是國家博物館特有的標志性展陳設備”。展品被置于展柜中或以欄索圍擋,這一社會生活的規范和禁止使國博的神圣性得到強化。“景園設計方面,國家博物館由于地處天安門廣場,為了傳達出莊嚴和雄偉的氣魄,在主入口兩側和兩個庭院都種植了松柏類植物,這也與天安門廣場的植物配置相統一。”因此,無論是整體還是細部,中國國家博物館都具有類神圣空間的性質。
改建后的國博空間追求實用性和深刻美學理念的統一,既必須成為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代表,又要成為當今中國形象的象征。一言以蔽之,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中國大國形象的重要言說者。國博前館長呂章申曾多次以“中華文化的祠堂和祖廟”和“國家文化的客廳”來贊譽國博;國博原副館長陳履生在采訪時也將博物館比作“城市文化的祠堂”。
藝術品收藏是博物館的基本職能,國博的類神圣空間性質決定了它的收藏必須遵循一系列的嚴格標準,是出于塑造國家形象的目的。石魯的經典性首先源于國博空間的類神圣性。
二、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收藏與石魯經典性的建構
石魯的經典之作《轉戰陜北》(1959年)現懸掛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中央大廳,與董希文的油畫《開國大典》并列,被譽為國博的鎮館之寶。《轉戰陜北》的誕生與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創建有莫大關系。1958年9月,中央革命博物館建館的申請報批中央,得到了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全力支持,當時成立了中國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籌備組,組長是毛澤東秘書田家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共同研究革命美術的創作活動。從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中國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開始組織革命歷史題材美術作品的創作、修改和展覽,當時,博物館對每件作品的題目和尺寸都作了規定。1958年底,中央革命博物館因組織第二次革命美術題材作品創作活動,借調了當時陜西美術家協會的石魯。因對新中國的政治熱情和王朝聞的推薦,石魯接受了毛主席轉戰陜北的創作題材。
根據195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的作品修改意見來看,《轉戰陜北》等革命題材的美術作品是為了表現國家革命建設的偉大歷史和新中國的政治理想,因此,政治性和革命歷史的紀實性是首要考慮。在1960年修訂的美術作品目錄中,石魯的《轉戰陜北》赫然在列。和同期借調為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進行創作的董希文、李可染等藝術家不同,石魯的《轉戰陜北》以寫意的手法將轉戰陜北的宏大歷史場景濃縮在千丘萬壑中的毛澤東和兩人一馬上,作品以少勝多,以小見大,構思非常之巧妙。之后,中央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多次指導修改這批作品,《轉戰陜北》最終歷經選拔而成為特級美術作品。根據李冠燕的記述,“特級美術作品”的鑒定標準是世界名畫,這個級別的劃定認定了石魯《轉戰陜北》在中國美術史上的重要地位。與石魯《轉戰陜北》一起最終在1961年7月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的149件美術作品“很多都成為在新中國美術史上具有深遠影響力和重要地位的作品,是記錄時代的經典。”當然,國家級博物館的官方認定是一方面,石魯《轉戰陜北》卓越的藝術性是其經典性形成的主要原因。
文藝復興至19世紀初期的歐洲博物館基本只為少數群體開放,因此具有“別異”和階層區隔的作用,博物館的大眾化實質是傳達文化權威和為藝術品賦魅的過程。現代博物館以收藏藝術史中坐標式或具有重大美學和歷史意義的一流作品為核心任務,從而實現對藝術史的書寫,藝術家也以作品能否進入博物館為創作的終極目的。有人指責博物館成為對藝術作品野蠻評價、占有和剝離作品原初語境的罪魁禍首,認為博物館的藝術作品不是自在地呈現,而是服從于博物館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屈從于某種權力話語,藝術的審美性和自主性相對被忽視。本文認為,博物館并不必然剝奪藝術品表達的自由和審美性,作品放在博物館的展廳內,燈光照射,觀眾凝神觀照,其審美意味反而更加突出。博物館影響著人們的審美判斷,形塑著一個民族的審美趣味,它似乎有一種塑造和改寫藝術史的魔力:一旦物品被置于博物館中,即使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它也就獲得了“藝術”這一合法身份。古德曼認為是博物館使藝術成為藝術,實際是肯定了博物館賦予藝術身份的權力。
在國博館藏空間內,懸掛、阻隔、凝視、肅穆的儀式感使石魯作品成為被凝神觀照的對象,作品的崇高性和無功利的藝術價值被凸顯。人們不會在國家博物館中去追問《轉戰陜北》的價格,而會被它所震撼、所折服、所吞沒,他們可以從日常繁瑣的生活中短暫逃離中獲得精神休憩,審美經驗進而生成。
三、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藝術展覽對石魯經典性的建構
據采訪石迦所知,石魯家屬從2012年9月到2017年2月曾3次向中國國家博物館捐贈了705件石魯作品。2012年9月21日捐贈的151件作品主要圍繞《轉戰陜北》形成作品系列。作為回應,國博在2012年成立了“石魯藝術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中心發揮了推動20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和引領石魯研究風向的重要作用。2014年8月25日的第二次捐贈包括書畫84件、寫生稿3套(58張)。2017年2月27日,石魯家屬第三次捐贈了412件作品,這兩次捐贈覆蓋了石魯各時期的寫生創作稿及代表作品,包括國畫、油畫、版畫等。石魯家屬的三次捐贈使國博成為石魯作品全球最權威的收藏機構。
收藏之外,對石魯作品的研究與傳播也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重要工作。藝術展覽可為藝術現象、流派和作品正名,入藏以來,國博舉辦了幾次重要展覽,對石魯經典性的形成和價值的傳播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1979年12月8日,中國美術館將《轉戰陜北》從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借出,中國美術家協會及西安分會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石魯書畫展。這是石魯生前唯一一次個人畫展。圍繞這個展覽,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石魯作品選集》,里面選取的一百多幅作品涵蓋了石魯1946年到1979年的創作。這部石魯作品選集其實是1964年因《轉戰陜北》受到影響而本該早已出版發行的畫冊。當時,《轉戰陜北》遭受非議,石魯憤然退回稿費并拒絕修改,這幅作品因此沉寂多年。1979年的石魯個人畫展,不僅使《轉戰陜北》得以正名,也使遲遲未露面的石魯畫冊最終與公眾見面,這次展覽反映了人類對藝術美的尊重,因此,這部《石魯作品選集》的歷史意義非常重大。這次展覽后來在武漢、南京、長沙、廣州、西安等地展出,石魯和《轉戰陜北》的傳奇色彩使畫展在公眾中引起了巨大反響。本次展覽與1961年10月中國美術館長安畫派進京展一起,基本奠定了美術界對石魯的認知。1979年正是國內解放思想的歷史時刻,王朝聞發表的《再再探索》對與石魯的交往、石魯的藝術理念和他在新中國美術史的地位及作用進行了闡發,推動了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石魯研究。
2014年3月22日,中國國家博物館在多方協商后,精心挑選了石魯105幅作品在新西蘭惠靈頓的Te Papa國家博物館舉辦了石魯畫展。本次畫展由國博和新西蘭國家博物館共同策劃,名為“革命的藝術,藝術的革命——石魯藝術展”,展覽按年代進行編排,作品基本涵蓋了石魯整個創作生涯中幾乎所有的藝術種類,還展出了石魯常用的寫生工具、創作過程資料及石魯生前照片,立體地還原了這位藝術大師的風貌。本次展覽持續三個月,新西蘭許多觀眾數次觀展,留言表示內心極為震動。“革命的藝術,藝術的革命——石魯藝術展”將中國傳統藝術推介到海外,石魯傳奇色彩的一生和極具個性的作品引發了世界其他地區對中國畫的極大興趣。隨著石魯及其作品的國際化,石魯研究將逐步深入,石魯藝術品市場也將得到不斷規范。
2016年7月20日,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武漢美術館舉辦了“蒼山為岳——石魯作品展”,策展人為武漢美術館館長樊楓和時任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的陳履生。這次展覽包括石魯各創作時期120余件作品和相關的文獻資料,特別是《轉戰陜北》《山區修梯田》《延河飲馬》《東方欲曉》和《南泥灣途中》等代表作更是吸引了大量觀眾。在“石魯的藝術精神和當代水墨畫創作”研討會上,張渝認為“蒼山為岳”這個展題已經表明了石魯之于中國美術史的意義,并對石魯的抗爭精神進行了文化根源上的追問;陜西美術博物館館長羅寧將石魯和凡·高進行了對比;湖北美術館副館長冀少峰從“熱情和希望”“個體和國家”及“平凡和英雄”三個角度對石魯及其創作進行了解讀。2017年10月,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了樊楓主編的《蒼山為岳:石魯作品與當代水墨創作研究集》,研究集分為“高山仰止”“藝術風神”和“畫為心聲”三部分,包括作品圖版、研究文章、學術研討會紀要、作品圖錄和石魯藝術年表。石魯家屬高度贊揚了國博和武漢美術館合作的這次展覽,認為展覽學術成果質量高,社會影響大,是傳播石魯一次非常好的嘗試。
2019年8月9日,國博舉辦了“屹立東方——館藏經典美術作品展”,在精心挑選的13幅作品中,石魯的《轉戰陜北》赫然在列。本次展覽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作品主題的時間跨度從井岡山斗爭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直至新中國成立,力圖全景式地向觀眾展示中國革命從‘星火燎原到‘開國大典的艱難曲折和苦難輝煌,引導觀眾緬懷革命先輩浴血奮戰的崢嶸歲月,牢記紅色政權是從哪里來的、新中國是如何建立起來的。”12月,中國國家博物館將舉行“紀念石魯先生百年誕辰展”,目前本展覽各項工作已經在積極進行中,這次展覽將從2019年12月10日持續到2020年2月9日,屆時將出版石魯畫冊和畫集《百年石魯》(上下卷),召開研討會、出版論文集,相信這是進一步傳播石魯藝術價值的重要藝術活動。
藝術展覽對藝術家和作品的傳播效應往往呈幾何倍數增長,國博舉辦的藝術展覽將進一步鞏固石魯在中國美術史中的地位,對他作品的價值傳播發揮積極作用。
四、結語
1964年,《轉戰陜北》因遭遇非議而被從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墻上取下,之后15年不見天日。因《轉戰陜北》及之后的文化運動,石魯遭遇了巨大的磨難,他被認為患有精神疾病,流浪于深山野林,食不果腹,形容癲狂。即便如此,石魯仍矢志不改,用純潔的心去擁抱美和理想。回顧石魯的一生,我們發現,石魯的真正價值在于他對藝術忠貞不渝的情操和對美與人類至純、至真的情感的追求。博物館是一個民族自性(identity)的標志,中國國家博物館對中華民族自性的表現與石魯對民族自性的追求是相通的,石魯因國博的認定和傳播而成為國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創作者與傳遞者。
注釋:
①[英]柯律格著,劉穎譯.中國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19.
②鄧璐.建筑空間與展陳空間形態的塑造——以“中國國家博物館建筑設計展”為例,載《中國博物館》,2017(2):1.
③鄧璐.建筑空間與展陳空間形態的塑造——以“中國國家博物館建筑設計展”為例,載《中國博物館》,2017(2):3.
④陳成軍,郝寅祥.國家博物館展柜設計和使用中的幾點思考,載《中國博物館》,2013(1):97.
⑤何卓書、文思揚.淺談中國國家博物館與首都博物館的設計特點,載《廣西城鎮建設》,2012(5):75.
⑥堅持“學術立館”為全面建設世界一流大博物館而奮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學術工作大會”上的講話,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6):10.
⑦載《長江日報》,2014,5(27):20.
⑧李冠燕.光照史冊的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以籌備建立中國革命博物館為契機,載《榮寶齋》,2018(7):159.
⑨李冠燕.光照史冊的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以籌備建立中國革命博物館為契機,載《榮寶齋》,2018(7):156.
⑩石迦,男,石魯之孫,中國國家博物館特聘研究員,陜西國畫院青年畫院副院長,陜西長安畫派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原西安美術館副館長。
11 這是國家博物館設立的第一個專門研究20世紀著名美術家的研究機構。
1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官方網站:http://www.chnmuseum.cn/ zx/mtgz/201408/t20140826_3260.shtml.
13古籍.國家博物館即將舉辦“屹立東方——館藏經典美術作品展”https://mp.weixin.qq.com/s/_wZegEkLtLDBsg-h_kRQXg.
參考文獻
[1]馬繼賢. 博物館學通論[M].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
[2]丁寧.圖像繽紛:視覺藝術的文化維度[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3][英]柯律格著,劉穎譯.中國藝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薛軍偉.藝術與博物館——英美藝術博物館學研究[D].中國美術學院,2010.
[5]陶少藝.博物館與記憶以及社會責任[C].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會議論文集,2011-12-28.
[6]謝海濤.消費語境下博物館藝術的價值重構及其文化表征[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28(4):124-127.
[7]丁寧.藝術博物館:文化表征的特殊空間[J].浙江社會科學,2000(1):143-150.
[8]田軍.藝術類博物館所面臨的當代藝術之收藏問題[J].中國博物館,2014(4):27-31.
[9]蘇東海.博物館論[J].中國博物館,2005(1):3-11.
[10]蘭維.文化認同:博物館核心價值研究[J].中國博物館,2013(1):20-25.
[11]李冠燕.光照史冊的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以籌備建立中國革命博物館為契機[J].榮寶齋,2018(7):144-161.
[12]陳成軍,郝寅祥.國家博物館展柜設計和使用中的幾點思考[J].中國博物館,2013(1):97-103.
[13]陳蘊茜.紀念空間與社會記憶[J].學術月刊,2012(7):134-137.
[14]楊林,張繼焦.政治空間的神圣性建構——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為例的考察[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6):50-53.
[15]“蒼山為岳:石魯作品展”學術研討會[J].美術文獻,2016(5):42-49.
作者簡介:王曼利(1978-),女,漢族,陜西西安人,西北大學藝術學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藝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