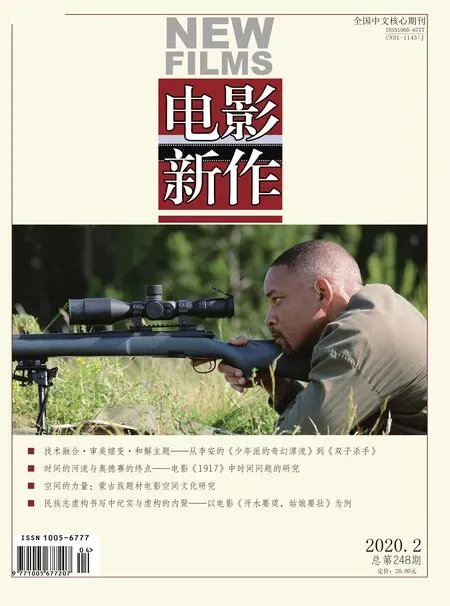中國無聲電影時期的“聲音景觀”與現代性觀念的形成
李 雋
從1896年上海徐園“又一村”首度放映電影,到1929年上海夏令配克戲院第一次正式放映完整的有聲電影《飛行將軍》,電影在中國至少有超過30年的時間是“無聲”的。但是如果從寬泛的角度而言,電影從來就沒有真正“無聲”過,因為即使在無聲電影的時代,公開放映影片時也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某些聲音。根據一些無聲電影時期的觀眾記錄,當時中國播放電影時,“其先必西樂競鳴,并有華人從旁解說”,演出過程中,“樂聲鳴鳴然,機聲蘇蘇然”,觀眾看到興起之,會“皆拍掌狂笑”,演出散場后意猶未盡者,還會“口講指畫以為妙絕也”。即在中國的無聲電影時期,電影觀眾們可能聽到的聲音包括觀眾的議論聲、解說員的講解聲、樂隊的配樂聲、放映機發出的嗡嗡聲等等。這些來自影院的不同聲音,共同引導、控制和影響著觀眾們對電影的感知。如何“抑制”某些聲音,將它們掩蓋、替代甚至排除?如何創造某些聲音,讓它們豐富和拓展觀眾們的觀影體驗?圍繞上述問題,無聲時代的電影人做出過諸多嘗試,形成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有聲電影”的“史前史”。
聲音的“構建”是一個與社會語境充分互動的動態過程,通過聲音的“構建史”,我們可以管窺社會的“發展史”。在電影聲音技術尚在醞釀階段的無聲電影時期,人為“構建”聲音的渴望和嘗試更為顯著。而在中國,這種嘗試立足于中國由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時期,不可避免地纏繞著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等現代文化議題,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展現出世紀之交現代性觀念在中國生成和發展過程,彰顯出更加豐富而多元的文化意味。這也構成了本文選取中國無聲電影時期來探討電影中的聲音的意義。
一、秩序與規訓:噪音問題
我們首先要討論的是電影院內的“噪音”。它雖然不是“應該存在”的聲音,但卻不容忽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噪音”并沒有被認為是一種應該“驅逐”出電影院的聲音,甚至被視為觀眾審美體驗的一部分。直到“現代化”的電影院建立,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秩序形成,“噪音”才成了一種應該被“規訓”的聲音。

圖1.電影《寶蓮歷險記》劇照
無聲時期的電影院內“噪音”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電影院中的談話聲、哭鬧聲、吆喝買賣聲等妨礙他人觀影的聲音,另一種是電影放映機帶來的噪音。1909年的《圖畫日報》上的一篇《四馬路影戲之喧嘩》記載了某次電影放映的場景。盡管放映是的“固絕無聲息之美劇”,但因雇傭了洋鼓洋號和中國鑼鼓,以至于“喧嘩之聲不絕于耳”。作者據此繪制了“影戲喧嘩圖”,并作“五更調”形容之。在五更調中,作者多次強調“不絕于耳”的鼓號聲帶來的頭脹耳聾:“號筒響,洋喇叭呀, 聲氣真長,呀呀得而噌,吹得頭脹”“打鼓蓬蓬,呀呀得而噌,耳朵震聾”“鑼鼓亂敲,呀呀得而噌”,但電影觀眾對這些噪音并不反感,反而心滿意足:“真擁擠,好熱鬧呀,吵得稀奇,呀呀得而噌,阿要神奇”。從配圖可知,這次影戲的放映地點是四馬路的一處“影戲園”。這個“影戲園”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專門電影院,通常是租賃傳統的茶樓、戲院等作為放映場所。二十世紀之初,西班牙商人加侖·白克就曾在四馬路的升平茶樓、虹口乍浦路跑冰場等地放映影戲。后來,他將設備轉賣給其同鄉安·雷瑪斯,安·雷瑪斯也曾在四馬路的同安茶居和青蓮閣茶樓等地放映電影。同年,《圖畫日報》上另一篇題為《作影戲》的圖文記錄了另一場影戲放映的場景。從圖上的說明“借間屋子作影戲”可以推測,放映商可能是租賃了一處傳統茶樓放映電影,觀眾們在左側觀影,右側是一支樂隊正在賣力表演。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專門的電影院在中國并不多見。根據記載,1896-1915年之間,在《申報》刊登影廣告的放映場所有90余家,其中以“影戲園”命名僅10余家。影戲多作為一種“余興” 穿插在戲曲、戲法、魔術甚至煙花爆竹等諸多項目之中,在茶樓、戲院、花園等處放映。或許是由于觀眾最初是在戲園、茶園等傳統農耕文化時代的娛樂場所接觸到電影的,他們在這些場所的欣賞習慣也就自然而然地移植到看電影的過程中來:戲臺幕布上放映影片,臺下觀眾可以自由走動,既能與旁邊的看客談笑風生,又可以邊品茶吃點心邊看電影。這些場所往往喧囂嘈雜,不過這樣喧鬧的環境并不被視為一種弊端,反而是觀眾觀影體驗的重要一部分。對于當時的觀眾而言,觀影的樂趣并不限于影戲本身,還來自觀影場所的諸多活動,電影內外混雜的聲音給觀眾帶來了一種交錯滲透的審美體驗。
隨著電影事業的演進,尤其是自1908年虹口活動影戲園拉開新式電影院的序幕以來,電影逐漸發展為一種具有新的觀看習慣和審美趣味的現代娛樂活動。20世紀20年代以后,新式電影院逐漸取代了過去那些充滿農耕文化印記的放映場所。新式電影院在硬件方面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點:1.相對封閉的觀影空間;2.黑暗的觀影氛圍;3.編號的觀眾坐席;4.“鏡框式舞臺”。“現代化”的觀影空間使電影從諸多農耕文化時代的娛樂活動中脫穎而出。伴隨著觀影空間在形式上的變化,建立一套與之匹配的“現代”行為準則的呼吁隨之而來,其中自然也包括對妨礙他人觀影的噪音的“規訓”。1920年《影戲雜志》第一卷第3期刊登了一份“觀影十誡”,其中第二條“勿高聲擾亂他人,影戲以安靜為快樂”、第四條“勿與爾之朋多言語,使彼不能專心于影戲”、第九條“映演時,影片偶或中斷,切勿狂叫,須知影片決不能以爾之狂叫而自續,故續靜待勿躁”都直接與遏制妨礙他人觀影的噪音有關。1923年8月《申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了吾國吾民看影戲時五點不文明的舉動,其中第一點“忽坐忽立口內時作怪聲”、第三點“見接吻則拍手狂喊”和第五點“帽子不脫(指西式)并高聲談論”都涉及了“噪音”,這篇文章同時給出了六點觀影守則,有四點直接涉及了噪音的“規訓”,分別是:“一、寂靜無聲”“四、勿喁喁細語”“五、見國旗則拍手表示歡迎”和“六、靜坐勿動”。
安靜觀影的意義絕非限于不打擾他人。1926年9月《申報》上一篇題為《電影場中之注意》的文章開宗明義地談到:“影戲乃社會教育高尚之娛樂也,茍劇本精良,風化因之亦可轉移,凡觀劇者對于公眾之道德亦須注意,一則可以表示自己之人格,二則勿被外人輕視,謂吾國國民無程度也”。維持電影院之秩序關系著“公眾之道德”,而“公眾之道德”作為現代社會文明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又與強國強族的民族國家宏大愿景相聯系。20世紀伊始,梁啟超等人就已經論述過“公眾之道德”與強國強族之間的聯系。1902年,在《新民說》第五章,梁啟超指出“公眾之道德”是國群形成的基礎:“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1907年《東方雜志》刊出的一篇《論救中國必先培養國民之公德》延續了梁啟超的“公德觀”,論述了“公眾之道德”與國家興亡之間的關系:“使人人皆知有公德,則相組織相維持,各盡其義務而國可保。使人人皆不知有公德,則相傾軋相趨避,各放棄義務則國立亡”。培養公德需要載體,電影院就是這樣一個實踐現代市民規范的空間之一。
觀眾發出的“噪音”可以通過制定公共秩序“規訓”,但放映機發出的“噪音”則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在電影技術尚未發達到能夠克服機器“噪音”之前,電影人主要是通過制造其他的“聲音”進行掩蓋。根據音樂家王云階的回憶,在無聲電影時期,“影片放映時,對話由影院雇人代說。音樂的部分,大城市的影院,聘請技術較好的樂師臨場按照劇情配奏;小的城市和鄉村里,則只用兩三人的小樂隊或者留聲機唱片配音”。這些對話和音樂一方面實現了對“噪音”的掩蓋,另一方面也創造出新的文化意蘊,并參與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圖2.導演孫瑜
二、啟蒙與教化:電影解說
在近代,電影不僅是一種娛樂的手段,還被賦予了拓寬眼界、啟迪民智的啟蒙理想。自晚清嚴復提出“開民智”,并將其與國家“富強之源”聯系起來,“開民智”就成為晚清和民國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開民智”的啟蒙理想并不只停留在思想層面。世紀之交傳入中國的電影就成了實現這一理想的載體之一,與民眾教育和社會啟蒙聯系在了一起。1897年,同慶茶園的電影廣告上就宣稱電影能夠“令人觀之別開眼界”。1898年,張園發布的電影廣告中也稱看電影能夠使“民智日開,富強可久”。1919年《東方雜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認為,電影能夠面向普羅大眾,讓愚蒙民眾開眼界、長見識,這是書籍報刊等以文字為載體的媒介所不能達到的:“當知此數百萬之看客,無智識者實占其大多數。此種人民不能閱讀高等之書籍,見聞不出戶庭之外,惟活動影戲乃能授此輩高尚之藝術思想,且使安處鄉里而得目擎世界之大觀”。1927年,《長城特刊》上刊載的一篇文章甚至認為,電影是比學校更有力的啟蒙和教育手段,因為“教育的力量所能及到的只是在校的一部分國民;而影戲的力量之所及,則是社會上大多數的國民”。
不過,要“看”懂電影進而“開民智”,對于當時許多人來說并非易事。1927年,《中國影戲雜志》上一篇題為《看影戲與聽影戲》的文章,記錄了幾樁因為“看”不懂無聲電影轉而“聽”的趣事:一次,作者問一位同看影戲的親戚,影戲是否好看。這位親戚先表示好看,繼而改口為“好聽,一架鋼琴發生出來的調子好聽”。另一次,作者發現一位和他同在一個影院看外國電影的老者總是在他發笑時跟著發笑,與老者同來的青年問老者為何發笑,老者答道:“我只假作笑,不然,那一般看的人們便會鄙我不曉得英文了”。看不懂電影的觀眾在當時并不是個案。作為一種采用新媒介的娛樂項目,電影有著新的表達方式,觀眾理解它需要時間和經驗。尤其是外國影片,許多觀眾不懂外文字幕,加之“無聲”,理解就更為困難了。
看不懂電影,觀影活動也就索然無味。為了幫助觀眾“理解”電影,一些電影院設置了電影解說員這一職位。電影解說員究竟何時誕生,目前并沒有確切說法。不過,從現有的材料來看,這一職業的出現幾乎和電影傳入中國同步。早在1897年,《游戲報》上的一篇《天華茶園觀外洋戲法歸述所見》就提及放電影時“有華人從旁解說”。1900年,臺灣淡水館九號房間放映了十幾部電影,放映技師松浦章三兼任解說。1904年,香港青年會免費放映電影,一位叫做楊文登的牧師進行解說。據稱,這是香港最早的電影解說員,并且“此后多次放映,都有牧師或醫生等解說”。
20世紀20年代以后,隨著專業電影院的出現和普及,電影解說員的重要性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1920年《影戲雜志》上刊登的一篇《影戲院應當注意的兩件事》中,提醒影戲院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應當設置電影解說員。這篇文章認為,解說員的作用至少有二:一是有助于觀眾理解劇情,尤其是外國影片,“要知道我們中國人懂英文的畢竟要比不懂的少”,即使懂英文的人也不會反對,“因為說明的人,他至少要看過一次,那是一定比別人來得熟悉了”;二是增加趣味,該文提及日本電影院均設有解說員,他們“很有學問且善于滑稽”,即使是不好看的片子經他們的解說潤色后,觀眾也能盡興而歸。進入20世紀20年代以后,電影解說員日益增多,并成了一個工種,甚至成為許多電影院的“標配”。電影講解員的收入頗為可觀。根據北京真光電影院刊登在《晨報》上的一則招聘電影解說員的啟事,真光電影院每天開演時間為下午三點到五點半,講解員需在這兩個半小時內講解一到一個半小時,此外概無責任,每月薪水可達35元——在當時,這是頗為不錯的收入。由于工作時間固定、內容輕松且報酬可觀,電影解說員成了炙手可熱的職業。
擔任電影解說員需有較高門檻,關于這一點。不妨參考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新愛倫影戲院刊登的一則解說員招聘啟事:
今欲延請演講員一位,專在臺上講述劇情,須喉音洪亮,深諳英文,能操滬、粵語者為合格。請每晚八時半至本院接洽可也。
由上可知,電影解說員首先需要聲音洪亮,足以能蓋住電影院內觀眾和機器發出的噪音;其次必須通曉多種語言,既能深諳英語,又能掌握當地方言;最后必須有較強的表達能力,幫助觀眾理解劇情,并讓他們感覺詼諧有趣,從而達到為無聲影像“增值(added value)”的目的。一般來說,解說員的任務有兩項:一項是為觀眾誦讀字幕,這項工作一方面是為了照顧一些不認識字的觀眾,另一方面,即使對于那些識字的觀眾而言,由于對聲音的感知要快于對字幕的感知,因此誦讀字幕依然是項有意義的工作。第二項任務是講解演員的行為動作。舒湮先生在他的《微生斷夢》中回憶過他幼時在鎮江一家由倉庫改建的電影院觀看電影的場景。根據他的回憶,無聲電影《寶蓮歷險記》在此連映兩三個月,有解說員用漢語對演員的動作進行詳細講解,如:“且看他二人一見鐘情。現在正在相互眉目傳情,不知下一步又將如何?”肉麻而有趣的解說贏得了在場觀眾的掌聲和笑聲。這些解說詞用今天的標準來看,有點廢話連篇。但在當時,電影解說員的陳述幫助“看不懂”觀眾“聽懂”,從而構建起一種“幻覺”,讓觀眾們似乎可以在銀屏上“自然地”看到了這些“幻覺”,從而幫助觀眾更好地理解和適應電影這一新媒介。
在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電影講解員事業并不算很發達。1927年刊登在《大公報(天津)》上的一篇文章中說:“從前在北京有兩三個影院也這樣做過,不過不久就取消了”。不過,在內地一些相對欠發達的地區,電影講解員的職業甚至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末有聲電影普及的時期。直到1939年,“昆明多數電影院仍繼續供給華文講解”,而一些因為戰事從上海遷居昆明的人則“感覺講解員的聲音妨礙片中的對白”,這些人經常光顧的電影院便因此取消了講解員。這或許是因為北京等大城市的市民因為接觸電影的時間長,更早具備了“看懂”電影的能力,電影講解員在完成了電影“啟蒙”的任務后,也就隨之退出了歷史舞臺。
三、聲與畫:電影音樂的探索
幾乎從電影進入我國的時刻開始,音樂伴奏就存在其中,上文提及的刊載于1909年的《作影戲》就是一個例子。最初,伴奏的目的或為招徠顧客,或為遮蓋噪音,音樂往往和劇情沒有必然關系。
音樂與劇情的“斷裂”是當時剛剛問世,尚在蹣跚學步的電影的特征所決定的。最早的電影的重心不在于講述好一個故事,而在于忠實地記錄下鏡頭前的空間。它們幾乎都是以一個固定機位、固定鏡頭拍攝,片長也較短,甚至不足一分鐘。當然,最早的中國電影觀眾也并沒有讓電影講故事的訴求,他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被機器“復制”的事物的本身。在他們眼中,電影只是一個來自西方的,令人驚奇的小玩意,只是以一種欣賞雜耍或領略科學儀器的心態對待它。1897年《新聞報》上的連載的《味莼園觀影戲記》曾詳盡記載了味莼園(即張園)的一次電影放映活動。根據記載,當晚共放映影片20回,內容為繁華的街景、火車到站、海岸邊驚濤拍岸、騎腳踏車的人、渡船從橋下駛過等。這些小片段式的電影當然不可能展示復雜的時間關系和因果關系,更不可能有足夠生動的故事性。在這種語境下,音樂只是為了避免“靜默”的畫面太過無聊,或者掩飾機器噪音的缺陷,演奏什么樣的音樂因此也就無關緊要了。
隨著影視藝術的發展,電影制作者已經掌握如何用多鏡頭和剪輯去構建復雜的敘事關系和因果關系從而講好故事。尤其是20世紀10年代后故事片(feature-length film)的出現,電影的“敘事性”更加受到了重視,觀眾們隨之對音樂和劇情的關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年代以后,陸續有觀眾發表電影配樂應該“音畫和諧”的看法。例如,1925年一位署名俊超的電影觀眾在《申報》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影戲院中之音樂、其旨在乎輔助觀眾感情之興起、而補足影片之意義”,因此影片中的音樂必須配合電影的情節引起觀眾們的“共情”“視影片與樂聲之悲喜哀樂、為自身之境遇”,而假若音樂與電影無關,甚至違背影片中的情節,“則會另觀者心煩意亂,討厭非常,故無異乎聚蚊雷于耳矣”。
在實踐領域,電影配樂也已從單純地“制造”聲音,變為講究“音畫和諧”。大城市較為高檔的電影院中幾乎都有樂隊現場演奏,這些樂隊甚至演進出一套專門適應影片伴奏的程式。《時報》上一篇題為《音樂與影戲》的文章記錄了這種變化:
目下音樂與影戲殆成不可分離之局勢。影戲園之業者茍不招致完美之音樂班,鮮能引起觀客之興趣而使其蒸蒸日上者。
在影戲發軔之初,戲院中之音樂僅為一種娛耳之消遣品,與影片內容原不發生任何關系,所奏之曲所用之樂器亦與尋常毫無區別。今則不然,影戲院之樂隊有特別之組織,樂器有特別之構造,曲譜有特別之編制。總之,影戲之音樂已跳出尋常音樂之范圍而自開一發展之新途矣。
《影戲院中之音樂》《上海之影戲院》等文介紹了20世紀20年代上海各大電影院及音樂伴奏的情況,再佐以各大電影院當時發布的廣告,我們可以推斷出以下幾點:第一,20年代以后影院配樂已經非常普遍。檔次較高的電影院,如大光明、夏令配克等,幾乎都請了樂隊駐場。電影音樂伴奏通常由鋼琴擔當,更為高檔的電影院還會增設梵啞鈴隊,甚至“鸞笙鳳瑟,鐵板銅琶,應有盡有,無不具備”。電影院聘請的樂隊也不僅限于中國,還有的會雇請西人樂隊,聘用歐美樂師;第二,觀眾對各個電影院的配樂水準評價不一,評判標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能否達到“聲畫和諧”。卡爾登、愛普廬等電影院的配樂因為“能吻合劇中之狀態,且悠揚得體”,能夠成為電影與觀眾之間的樞紐,因此受到了觀眾的好評,但也有的電影院,譬如中央,配樂“犯牛頭不對馬嘴之病,如幕中方悲哀,樂則為喜樂,幕中方喜樂,而樂則為悲哀,二者恰得其反”,不僅讓影片減色,還讓觀眾的神經受擾。
除配樂以外,中國的電影人對電影的音畫關系做出了更多新的探索。1926,明星公司出品的,由卜萬蒼導演、包天笑編劇,根據托爾斯泰名著《復活》改編的電影《良心的復活》在中央大戲院上映,電影明星楊耐梅親自登臺獻唱劇中的插曲《乳娘曲》。當影片放映至楊耐梅飾演的綠娃看到孩子病夭,劇中人楊耐梅突然“于慘綠電光中,荊釵裙布衣,鄉間女子裝,伏于一搖籃之側,發凄之音調,歌聲悲越,聞者咸肅然致敬,未幾起立,站于十余花籃之后,且歌且泣,慘動心脾……歌畢燈明,楊耐梅一鞠躬后退,而全劇告終”。不過,根據其他一些媒體的報道,楊耐梅在中央大戲院的登臺“首秀”可能不大成功。《上海花》上刊載的一篇新聞稱,楊耐梅演唱時因為節拍不合,“一時觀眾大喝倒好,并以銅圓向臺上亂擲”。另一家媒體《羅賓漢》也報道稱:“有人以銅板角子向臺上丟去,幸未中梅”。不過,不管怎樣,這種充滿“噱頭”的形式還是引起了熱情的圍觀。首演的第二天竟有600人因無票無法入場,中央大戲院登報致歉,并宣布再加映一場。
作為“無聲時代”一種對“聲音”的大膽探索,楊耐梅的登臺獻唱自然不可能盡善盡美,但這一形式至少在兩個方面實現了突破:首先是現場演出與影片內容相結合。在放映電影時引入現場演出的方式并不新穎。例如,卡爾登大劇院經常會在放映電影之前,邀請包括卡爾登飯店音樂班在內的,多達六十人的樂隊,為觀眾演奏助興。不過,這些演出和電影內容沒有任何關聯。而楊耐梅的獻唱卻是對影片內容的“還原”,她的“聲”與“色”和電影的“畫面”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一種另類而充滿想象力的形式實現了“聲畫和諧”。其次是開創了為電影原創音樂的先河。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提及的那樣,幾乎從電影誕生伊始,電影配樂就出現了,但這些配樂都不是根據電影內容原創的,而是根據一套程式從既有的樂曲中選取,例如深情時用《月光曲》《圣母頌》,歡樂時用《春之歌》,追逐時用《塔蘭臺拉》。楊耐梅在影片中現場的《乳娘曲》則不同,這首歌曲是包天笑作詞、名伶馮春航作曲,專門為電影創作的。它的出現為日后電影歌曲的興起和繁榮奠定了基礎。
除《良心的復活》以外,另一次值得一提的聲音探索是剛從美國學習電影歸來的孫瑜執導的他的第一部電影《瀟湘淚》(1928年,后改名為《漁叉怪俠》)。在這部影片中,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使觀眾依助視覺與想象,“聽”到了電影中的歌聲。該片中有一處這樣的情節:湖南漁民老吳坐在吳淞漁民李華的船頭,用他從湖南帶來的斑竹簫吹了一曲娥皇女英哀悼舜帝的曲子。為了展現好這一情節,孫瑜用古詩字幕疊印于畫面之上,又請配樂師專門播放了一段優美的洞簫獨奏。觀眾們雖然聽不到演唱,但在洞簫樂曲聲中看著字幕,也有了一種想象中的聲音。孫瑜在自傳中認為《瀟湘淚》在各方面都很差,但對他在“電影歌曲”方面“幼稚而大膽”的探索頗為滿意,他認為這次嘗試奏響了“電影歌曲”的序曲,為他后來拍攝出含有第一首電影歌曲《尋兄詞》的電影《野草閑花》奠定了基礎。
結語
噪音、解說員的聲音和電影音樂,是三種在中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語境中發出的聲音,它們關聯著現代社會秩序的形成、啟蒙現代性意識的興起和對電影這一現代新興藝術的探索,既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和形塑的伴生物,也是中國發展和變遷的表征。
【注釋】
1天華茶園觀外洋戲法歸述所見[N].游戲報,1987-08-16(1).
2 味莼園觀影戲記上.新聞報[N].1897-06-11(1).
3 同1.
4 同2.
5 四馬路影戲之喧鬧[J]. 圖畫日報,1909(36):7.
6 同5。
7 陳一愚. 中國早期電影觀眾史(1896-1949)[D].中國藝術研究院,2013:49.
8 影戲觀眾之十誡[J]. 影戲雜志,1920,1(3).
9 姚昆元.看影戲時我人應守的規則[N].申報,1923-08-22(19).
10 電影場中之注意(道德)[N]. 申報,1926-09-15(19).
11 梁啟超.論公德[A]. 梁啟超全集[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0.
12 社論. 論救中國必先培養公民之公德[J]. 東方雜志,1907(07).
13 王云階. 論電影音樂[M]. 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4:7.
14 請看美國新到機器電光影戲[N]. 申報, 1897-10-05(6).
15 新到機器大影戲[N]. 游戲報,1898-04-14(1).
16 羅羅.活動影戲發達之將來[J].東方雜志, 1919, 16(4) :113.
17 阮毅成. 影戲與社會道德[J]. 長城特刊,1927(09):37.
18 佩茜.看影戲與聽影戲[J]. 中國電影雜志,1928,1(10):14-15.
19 天華茶園觀外洋戲法歸述所見[N]. 游戲報,1897-08-16 (1).
20 黃仁,王唯. 臺灣電影百年史[M]. 臺北:中華影評人協會出版社,2004:10.
21 余慕云. 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M].香港:香港次生文化有限公司,1996:26-28.
22 君健. 影戲院應當注意的兩件事[J]. 影戲雜志,1921,1(02):46,90.
23 無標題[N]. 北京晨報,1921-10-30.
24 新愛倫戲院廣告[N]. 申報. 1920-02-23 (5).
25 舒湮.微生斷夢[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0:92.
26 渺渺. 關于電影說明書的幾句話[N]. 大公報(天津版). 1927-10-16(5).
27 電影院內之講解員(中英文對照)[J].實用英文,1939,5(05):4.
28 味莼園觀影戲記上.新聞報[N]. 1897-06-11(1).味莼園觀影戲記續前稿.新聞報[N]. 1897-06-13(1).
29 俊超. 影戲院中之音樂[N]. 申報. 1925-09-16(18).
30 左匋,現乙. 音樂與影戲[N].時報,1924-09-17(8).
31 同29.
32 不才. 上海之影戲院[N]. 上海常識,1928-08-11(2).
33 卡爾登廣告[N]. 銀星,1927-10-01(13).
34 同29.
35 瑤瑟.《良心復活》中之乳娘曲[N]. 新聞報本埠副刊,1926-12-28(2).
36 七十二小時報告[N]. 上海花. 1926-12-26(2).
37 享丁丹.無標題[N]. 羅賓漢,1926-12-26(2).
38 孫瑜. 銀海泛舟:回憶我的一生[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