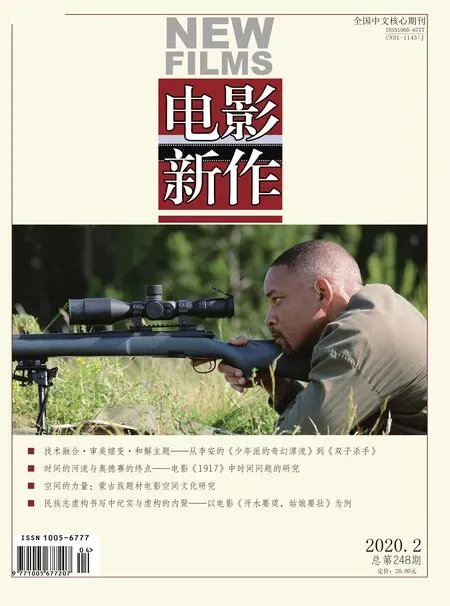民族志虛構書寫中紀實與虛構的內聚
——以電影《開水要燙,姑娘要壯》為例
劉思成
一、民族志虛構(ethno-fiction)的理論化
自讓·魯什于1955年拍攝了第一部被研究者視為運用“民族志虛構”的紀錄片《瘋狂先師》(Les Ma?tres Fous)伊始,越來越多的紀錄片作者將此法奉為圭臬,民族志虛構也逐漸稱為獨特且有效的民族志電影創作準則。拍攝時除了保留傳統的民族志書寫準則外,創作者需要通過設置“臨時劇本”的方式,引導被攝對象作為“臨時演員”,對反映的民族志問題(ethnographic issues)進行“反身式表演”,最終使電影作品兼備文獻記錄和景觀展演價值。但是,為了不使真實原則于展演之間喪失合理性,此法需遵守民族志電影拍攝原則的參與式觀察法和聚焦個案或小群體的慣例,因此無可避免地余留有“他者”角度凝視的痕跡和偏見。
彭兆榮認為,民族志文本中的文化本真性是流動的,不可以輕信的心態去接受任何一種演繹下的真相(truth)。除了需要質疑經由技術手段(即攝像機和演繹)處置過的真相的樣態之外,筆者認為還存在第二層含義,即拍攝過程本身對真實的破壞性,且難以規避。破壞性意味著記錄人對自身主觀經驗服從和對原本就不全面事物的忽視或進一步遮蔽。創作者以個人經驗賦予所見物“普遍化原則”,同時無意識地把被遮擋/未察覺之物視為視之無物。此外,而實踐中除了需要依仗創作者的自我掌控,也要應變各種偶然因素。因此,各式民族志書寫下“真實”的爭論孰是孰非,難以下最終的定義。本文無意深入探討民族志創作者的姿態差異,也就是作為觀察者的第二重身份的矛盾,而是從功能論角度證明民族志虛構手段能夠為“真實與虛構之辯”騰挪出可協商空間。
關于民族志虛構手段的判斷基準,索伯格(J.Sjoberg,2006)提出了四個創作/美學原則。首先,創作者需要審慎選擇攝影機的關照范圍,通常為小規模群體或個體。創作者需要依托田野經驗在拍攝者、被記錄者與周遭環境之間建構緊密聯系。其二,肯定了分享人類學(shared anthropology)的批評作用。索伯格認為,由拍攝到放映的過程均要接受反饋,重視價值觀的傳遞與互動。民族志影片的創作準則提倡以合作、對話和思考等互動式干預過程,這與影片本身的存在價值也是對等的。第三為即興拍攝(improvising filmmaking)手法。在拍攝時,拍攝者的注意力需要保持機警,攝影機維持流動狀態,拍攝到內容需要直截了當,切入主題,捕捉有價值的瞬間。必要時可令攝像機展現出輕度“挑釁”(cine-provocation)姿態,以適度干預或指揮拍攝的方式達到理想效果。最后,需要有限度地刺激被攝對象進行即時表演(improvising action)。此處并非指演員的臨場應變能力,亦非演員能夠迅速進入某個情境,進而達成戲劇效果的表演天賦,而是被攝對象在面對第二方(攝影機和人等“非自者”)在場的狀態時,能夠不受干擾,其言語和行動方式維持與平日無二,將受傳統塑造的知識狀態和個體經驗還原并表演出來(act out)能力。
理畢創作原則,筆者借此辨析民族志虛構的兩種中文譯法。此概念英文為ethnic-fiction,目前可檢索到的中文譯法有兩種。其一為“民族志虛構”,第二種由朱靖江(2015)參照視覺人類學的相關著作翻譯而來,譯為“虛構式影像民族志”。“民族志虛構”在語義層面強調寫作文本的虛構與真實之間的“中間樣態”。“真實”的依據為經驗的抽象提煉、典型化(incarnation)和拼貼,意味著實際經驗是文本材料呈現的可靠來源。“虛構式影像民族志”的語義則稍顯狹隘,將范圍限制于以影像資料層面,因此筆者認為“民族志虛構”的譯法從寓意和背景上更符合原意。讓·魯什在創造此概念時,旨在合法化民族志電影創作過程中,對文化展演的“描繪(depiction)”不可避免會滑向展演,進而進入的一種“后真實狀態”。當懸置的表演性介入表達以后,在虛構表達和真實性間產生雙向流動,二者在對沖中達到平衡。其二,“民族志虛構”手段已經被諸多學者拓展至心理學、歷史學和殖民文化研究等跨學科研究和書寫之中。例如人類學家馬克·奧格(Marc Auge)在著作 No Fixed Abode: Ethnofiction中,將民族志虛構概念引入對冷戰中期至末期的全球化趨勢同技術和人類間聯系的研究。其三,“民族志虛構”不會受到媒介類型的束縛。文字,藝術品,影像和聲音等均為可行可信的材料,而且易于滿足接受者多樣化的偏好。
民族志個體樣本的文化展演是矛盾的,本能的,由身體主導的。人的身體與經驗在浸淫加速主義的變化中,陷入了深遠持久的異化過程。同時,我國豐富的人文地理資源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而人作為文化承載物也具備復雜性,因而吸引了人類學家的目光。聚焦于個體經驗和農村性(rurality)/城市性(urbanity)的研究和書寫成為民族志研究洞悉文化存在狀態與當下流變的途徑,以人為本的多元批評視角也將個體的存在意義置于地域經驗書寫下,“以人敘事, 以事襯人”。凝結于身體表演的文化原貌受到被觀察樣本范圍的限制,并將其問題化。任何虛構表述很難對樣本的元真實出現僭越。
記錄者自身是事件的觀察者和分析員。與自我人類學視角一般,創作者的感受被延伸至“攝影筆”上,被表述對象與表述者的經驗和訴求得以相互對照。同時,電影作品對實在界的加工復現并不適合以絕對真實硬性要求。民族志虛構進一步調解了爭議,賦予電影等量于真實性價值的靈韻(aura)和更深刻的美學體驗。 本雅明理論下“光暈”本身便具備模糊性與神秘性,是文本審美價值的來源,能夠解蔽并將觀者推入被記錄對象的情境之下。同時,民族志電影依賴創作者直接經驗與呈現方式,正是靈韻的獨異性,“與創作者本人的藝術思維緊密相連,因此他獨一無二。”。因此,民族志虛構作品雖然與以描繪真實圖景為先,但仍具備作者屬性與藝術性。
二、民族志虛構作為批判視角的中間狀態(inbetweenenss)
第一處“中間態”指的是民族志虛構手段作為連接影像民族志和少數民族研究視角的紐帶。人類學影像志審視少數民族的角度由客位(Emit)逐漸過渡為以少數民族成員自我敘述為基準的主位(Emic),這標志著舊視角的偏離和新視角的介入。電影主題表達不再游離于文化表征和膚淺認知,轉而以反映少數民族文化的存在狀態與精神內核為目的。故事講述者回歸于少數民族文化群體內部,塑造方式也由單一化的身份或民族認同感塑造,或異域風情搬演,拓展到對生活狀態,心理立場,及文化存在等由人塑造的場域之中,并作出反身性回應。抑或觸及少數民族群體當下的隱性變化,以記錄景觀消失,現代性對原始生活的浸染,重新闡釋民族性等嚴肅主題。朱靖江指出,影像民族志與少數民族題材有著“天然的聯系”。此“天然的聯系”不僅是電影人對民間文化與生態的自覺記錄,更意味著一定的歷史淵源。自上世紀初影像民族志研究視角被介紹到中國來之時,就與眾多本土學者關注少數民族文化變化和生活方式演進的文獻性研究理念不謀而合。早先在費孝通的主導下,與1957至1966年間接連出現了以“民族識別”為目的的紀錄片拍攝活動,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較早與少數民族相關的,具備影視人類學價值的活動(Chu,2007和Gillette,2014)。早先的影像民族志記錄行為將少數民族社會景觀的變化文獻化,憑借窘迫的物力資源最終完成了“16部,22個民族123本(膠片)”的可觀工作量,因此劉達成將這些價值連城的影像資料資料喻為 “舊面貌”的“凝固的歷史”。
將影像民族志與少數民族研究結合是合理的。首先,少數民族題材在文化表述的特殊性與多元性賦予該母題以民族志研究的價值。由于多數少數民族世居區域地處偏僻,“邊陲”和“偏遠神秘”等標簽成了這些區域的代稱,邊緣化的、異域風情濃郁的文化生態明顯異于主流文明形態。少數民族群體是“鄉土中國”敘事的主要傳達者。長期的農業生產模式和滯后的城鎮化過程明確定義了世居區域的鄉村屬性(rurality)。時至今日,“未開化”“原始主義”“貧窮”等依然是對這些區域常見的形容方式。民族志電影可以起到一系列解蔽、去魅和幫扶作用,記錄社會/時代變遷,協助弱勢集體得到關注的正向推動作用。例如由吳文光發起的“村民影像自治計劃”給予了村民操作拍攝工具的技能和為底層境況去蔽的契機,也是平民自者書寫歷史的機會,更是社會性的,實驗性的民族影像志實操。

圖1.導演羅伯特·弗拉哈迪
民族志寫作注重小社群經驗的傳統得以明晰微觀的區域差異。許多研究中,許多學者和創作者常以“大西北”“西南地區”等地理界線作為限定研究范圍的標準,但大區域內部的無數小型聚居地卻是“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文化形態迥異,具備多樣性和典型性。首先,民族志寫作對小社群的雕刻(sculpt)不僅具備景觀展示的效能,這些“活樣本”更是對少數民族文化肌理展演的重要參照。被展演的少數民族文化符號常見為村寨、小鎮,或聚焦與民族節日慶典,傳承物(如手工藝,風俗信仰,民歌等)。其次,民族志視角的介入也能夠細致地關照并記錄變化。在城鎮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收獲和失去是等量存在的:聚落景觀加速更新,區域經濟發展愈加迅速時,人們面臨著生活方式變遷、風俗轉變和傳統價值觀出走等狀態,少數民族文化圈層內部經歷著巨大的角力。如果僅以非本民族視角(客位)審視變化時,不免誤讀甚至曲解。民族志視角的介入使相似的問題暴露在日常生活和對當下性的揭露之中。以少數民族成員為主體的主位視角,從具體的現象學角度切進,記錄其消失或異化的過程。從微觀文化簇的質變過程中以小見大,利用多重“文化樣本”對時代精神和時下困惑做出回應。如張金華所言,民族志對與少數民族文化研究的勾連是保護文化“活化石”的“文化救險”行動。
第二個“中間態”是指民族志虛構手段在為“真與偽”的悖論提供了解法。由田光,王紅翻譯卡爾·海德(Karl Heider) 的著作 Ethnographic Film的中譯本書名為《影視民族學》,雖然該意譯法有待商榷,但卻表明了海德的民族志電影理論對中國少數民族題材影視作品的創作和研究具有深遠影響。海德在著作肯定了視覺人類中虛構和真實敘述可以形成的平衡。他認為,人物身處拍攝現場的條件制約中,創作者要求被攝對象有限度地按照創作好的劇本進行搬演是合理的,并直白地命名這種做法為“好萊塢式人類學”(Hollywoodstyle authropology)。盡管海德認為此舉屬于“商業冒險”(commercial venture),但并未與民族志電影手段的創作初衷相背離,即展現深層次人際關系的互動和傳達潛在的“情感動態” (dynamics of emotion)。弗拉哈迪的作品也由于存在一定數量的擺拍,被批評家調侃道:“弗拉哈迪無邊的想象力和講故事的天賦,使他能夠在他癡迷于對‘絕對真實(vary realities)’的記錄同時,顧及到應對資助他的好萊塢制片廠時要提防的雷區(即對影片“故事性”的“執著”),中和于項目中(尋求解法)”。但適當的擺拍或搬演并未對他作品所傳遞的可信度和受歡迎程度造成局限。隨著“好萊塢模式”同其他舊時與之分庭抗禮的理論與實踐方式之間的界限日益交融,這種“中間態”的合理性被進一步證明。民族志虛構手法與民族志電影的外部爭議無關(例如如何劃定民族志電影的范圍),而是位于內部的,概念化的協商。
然而,容觀藑警惕地指出人類學影片與少數民族題材交匯之后,電影的創作形成了“兩張皮”的勢頭。一面是學者越發注重的專業性,一面是藝術工作者對“表層的生動”的追求。容認為電影人未經過人類學學者的專業訓練和深入了解,因此這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事實上,藝術性與專業性的邊界在民族志書寫實踐中已出現交融。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陸續出現的一系列“文化人類學小說”與當下具備民族志價值的少數民族紀錄片都出現了所謂的“文學轉向”。換句話講,非紀實性書寫在民族志材料中已經具備合理性和合法性,構建當代田園烏托邦和“鄉村酒神精神”與切真的文化/生活描寫并不抵觸。此類文本價值則在于以微觀視角對整體境況的見微知著,創造開放式的批評,摒棄印象為先的思考,用小說家的方式重新理解人類學的材料,破除舊的學科壁壘與風格流派的局限。而對于非紀錄片性質電影的人類學研究價值,威克蘭德(Weakland)指出,電影拍攝首要的價值是生成生活圖景,因為有選擇的生活場景是日常經驗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組合(organization)。當電影的虛構與真實被文化標準化后(culturally standardized),會自覺地形成有利于表達的電影范式。以民族志虛構概念挖掘少數民族題材故事片的文獻價值,得以顯示出此類題材電影的是雙重美學觀念:藝術表達價值與關照真實少數民族文化與倫理建構的價值。民族志虛構的詩意絕非僅來源于對少數民族聚居地生態的浪漫化或奇觀化,也絕非刻板的記錄與鏡像化的復現,而來源于虛構與真實雙方在影像實踐中達成的非對抗性的,可共存的微妙平衡。
民族志虛構電影的作者性創想與非虛構記敘之間并不存才不可逾越的邊界。拉波特和奧弗林認為:“要道德上的困境和肆溢的復雜性的糾葛,就必須承認人類學命定的是在表述(作者的)多種生活中的一種……”劉大先亦于文章中有言,創作者無法在復雜且具備多重偶然因素的世界中忠實于任何一種“歷史的真實”。但民族志作者可以多維度地,重復地解讀微觀現象,創作者活動以注入超驗性和主觀預判對“真實”構成潛在干預,作為對“大歷史”視角的補充。索伯格也認為文化展演的戲劇化處理在后現代人類學的研究中變得愈發常見。索伯格所謂的“戲劇化”處理是憑借具備現實意義的意象拼湊出“事件”,以展演民俗和特殊的價值基準為媒介,反映時下某一群體的思潮、困境、變革的局限性、流動的現實和個體/集體心理狀況,將少數民族的獨一性和存在憑據傳達給觀者,進而激發觀看方的共鳴和他們同理性的真實經驗反射,這是民族志虛構手段需要達成的又一目的。
但是,此類電影的類型化“外部邊界”卻十分明晰。在類型化討論的語境中,依照文本的風格,民族志虛構電影應被歸類為 “紀實型虛構電影”(docufiction)。在中文語境中,這個概念與文獻紀錄片(docudrama)極易混淆。二者均以真實標榜,但唯一區別在于處理虛構性(fictionality)的方式。前者在拍攝方式參考直接電影,在電影語言與風格則非常接近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偏愛使用無技巧的寫實主義手法制作,用以審問(integrate)現實而非粉飾(mask),展現焦慮與危機,檢討情態和倫理,并生成隱喻。同時,反情節敘事是對現實經驗的凝練,不針對任何事實。后者則是對歷史事件的戲劇化重演,在力圖重現歷史事實或某個轉折時刻,電影情節與真實的歷史走向一致的同時,其次要元素,例如配角,情節,對白,劇情線索等允許進行合理虛構,以增強藝術效果。
第三個“中間態”在于電影的真實與虛構皆是圍繞“人”來討論的,回歸于個體的價值。科茨(Jennifer Coates)在文章引用了今村昌平對電影想象和現實的回應:無論在紀錄片還是劇情片中,今村昌平都是以“人”為電影的表現核心(主題,表現等),也是催生困擾和矛盾“旋渦”的“始作俑者”。他的作品始終將人物塑造視為第一要務,不斷揣測人物多變的心理狀態(mentality)。通過將人物放置在各式情境之中(家庭,工作區域,社區,少數族裔聚居地等),對人物欲望和動機進行推演和假設,賦予枯燥的真實以情動體驗(emotionalize),而進階為“真實感(sense of reality)”。同時,今村昌平拒絕自己的作品走向任何一個極端,貫徹了他只書寫“實際上的日本”的信念。據此,科茨認定民族志虛構電影夠打破了故事敘事和紀實的邊界,并尋到支點,為創作提供平衡力。人種志學家施密特(Schmidt) 也認定以虛構的方式撰寫民族志(fictionalizing ethnography)的實質是將文本書寫的視角集中于“人物”的雕琢,她將民族志的人性化(humanize ethnography)視為固有創作原則,主張以人本主義思想對創作的主導。塑造血肉豐滿的人物,有據可依事件沖突,是維系文本人類學價值的必要因素之一。同樣,人的狀態展演促成了戲劇性,電影每一幕的“動機”都是圍繞固定的對象和中心思想被鋪陳,被激發,且與現實世界中的環境與個體/小群體連通,進而先產生互動(interaction),其次生成沖突,后解決問題。借助虛構敘事想象,將映射現實世界境況的任務同作者化表述結合起來,虛構性和現實映射也在電影對人物的刻畫上也達成共識。
三、《開水要燙,姑娘要壯》:即興與真實
苗族題材電影《開水要燙,姑娘要壯》(后文簡稱《開水》)拍攝于2007年,導演胡庶認為這部作品具有一股“羞澀的力量”,這是他在創作期間在長期在當地工作生活,同村民朝夕相處帶來的最直觀的感受,胡庶以“苗族性”概括寨民的性格特征和區域性的文化風情。在這部電影中,胡庶的書寫同樣以展演苗族性為核心。在他看來,利用苗寨的原生態景觀和寨民的本色表演就意味著呈現了真實的存在狀態。他說:“我理解的原生態,就是能給觀眾這樣一個印象——相信這些人,這件事是真的。我想呈現出一種感覺,讓人覺得這種生活狀態的確真的是這樣,不是哪里挪過來的,不是擺在舞臺上演的,而且這個場景也不是搭建的。”胡庶將文化本真性理解為觀眾在欣賞后的信服感和直觀的感情共鳴。在他看來,真實與虛構寫作的平衡不僅是電影的民族志價值之于文化展演或真實景觀素描所展露出的意義,最終決定權同樣在于觀眾的評價。《開水》成功地實現了民族志虛構手法的“中間狀態”,即有對客觀可靠的經驗的復現,也有對故事情節的有保留的干預和戲劇化。
影片的“真實”體現為電影拍攝對真實條件得當的利用和處理方式。胡庶在選擇電影內部空間和營造情景時,將現實的可感知存在物(景觀,人物,話語,場所等)不加改動地記錄于文本內,用自然主義的手法,借助真實景觀雕刻了苗寨的生活圖景,即作為電影的詩意和藝術感形成的土壤。現實中的苗寨位于貴州和廣西兩省交界處榕江縣的月亮山區深處。劇組于計懷寨和計劃寨兩個苗族村落取實景拍攝。開拍之前,劇組用一個月的時間居住在寨子周圍,同寨民一同勞作生活,深入交流。劇組在搭建營地,協調前期工作同時熟悉周邊環境。但令人惋惜的是,電影拍攝完后,兩座寨子均被拆除,《開水》記錄下的影像竟成了兩座百年苗寨的銀幕絕響。
《開水》中的演員均為當地村民,用苗人演繹苗人的生活。每一位非專業演員分配到的角色均與其實際的身份背景相近或相關。例如,導演在面試了寨子中所有少女之后遂決定選朱小片擔任主演,并且隱去她原本的姓氏為女主角命名。在胡庶看來,除了微胖的體態,朱小片我行我素的性格才“苗”的可愛。同時,電影中的鄉長由政府官員扮演,小學班主任王老師由一名駐村教師飾演,小片的母親則由一名學校的女教師扮演,其余的村民演員也“各司其職”。所有的演員均與小片熟識,是現實中苗寨局限的人際關系網絡的搬演,電影主人公的生活圖景建立在演員熟悉的環境下,為進一步的表演預設了非陌生的情境。
本片的寫實性同樣體現在對苗族村落中“苗族人的生活方式”進行了在地的,細致的刻畫。廖海波依照電影文本對少數民族原生生活圖志演繹的不同水準,將電影分為三個檔次:景觀電影,民俗電影和文化電影。《開水》稱得上是一部文化電影,它的成功在于電影文本包含但并未局限在對少數民族風俗,儀式等展演之功能之上,導演憑借田野經驗和獨到思考,描繪村民的日常生產勞動,從日常化的瑣碎細節和情境中側面刻畫苗民的性格特質與獨有的文化表征。例如小片和朋友聚在院落中一邊繡花一遍閑聊,苗族古樸的織布機和身著傳統服飾工作的苗族少女共同傳達出別樣的詩意。此外,電影還包含對打糍粑,堆稻草等農業活動,王老師在毛坯房中為寨子中的學童授課,舞蹈比賽排練,寨民圍坐在灶臺周圍飲宴,村鎮集市等生活情境的展演。電影對角色在生活空間內部狀態的雕刻性記錄和生活化行為的白描式性記錄豐富了《開水》的民族志價值, 同時也克服了單純的符號化堆砌,達成了對文化樣態的解蔽式呈現。

圖2.導演讓·魯什
《開水》中同樣以隱喻的方式映射現實。在現實中。村長一職作為基層與上級政府之間的樞紐,除了要進行自家的農業生產,還要負責上級政令的接受,傳遞和執行,協調村寨內部事物,做出決策等。本片中舉辦苗舞比賽是鄉政府的決議,村長負責挑選寨子里合適的女孩參賽,組織排練,安排伴奏用的蘆笙手,兼顧要接待領導視察,維護村寨的秩序等工作。《開水》隱晦地展示了基層政治生態下村長與村民之間的關系紐帶。平時雙方生產互相幫助,但逢節日則共同飲宴娛樂,村長與普通村民往來的姿態平等,方式直接。當雙方即涉及利益交換時,村長則會以集體利益為先,兼顧人情。例如,村長與化肥廠老板飲酒至微醺,接受了他對寨子舞蹈隊的贊助,并答應幫化肥廠打廣告。而在挑選舞蹈隊成員時,除了參考“選用苗條女孩”標準之外,也會優先考慮與自己關系較密切的家庭。
關于虛構書寫,《開水》通過在反情節,平鋪直敘的“鄉村日常圖像志”中設立矛盾與巧合,以幽默的筆調貫通寫實敘事與戲劇化手法的邊界。與此同時,傳遞了村民不同代際,不同身份間的心理差異,個體的異化和逐漸不合時宜的傳統觀念與當下思維方式的對立。
第一個主要矛盾是小片的“減肥問題”。小片因為體態豐滿而被村長排除在參加舞蹈訓練的人員之外,母親也曾三番五次地向村長求情,但得到的答復皆是模棱兩可。直到小片親自找到村長家,村長才口頭許諾,只要她能在一個月內瘦下來,就可以加入舞蹈隊,同時讓兩個村民用稱量過糧食的秤測量小片的體重,使得小片心花怒放。待她離開后,村長卻扭頭對妻子表示,一個月后小片若是再來詢問,他便隨便找一個人抱一下小片,說她的體重依然不達標準。這樣做即能暫時讓小片滿意,又能不違背鄉里領導的意愿。反觀小片,為了能在短時間瘦下來,便以不餓為由拒絕吃飯。她開始嘗試各種減肥的方式,跑步,轉呼啦圈,甚至倒立念課文。當幾位要好的女孩聚在一起閱讀從城里帶回來的時尚雜志時,小片被其中的插圖吸引。小片到鎮上賣雞,卻在售賣香港女明星海報的小攤前流連忘返。而小片的母親卻極力反對她的“減肥大計”,當從姐姐口中得知小片絕食的消息以后,母親怒不可遏地訓斥小片,并對她說:女孩像棵菜,長得胖嫁得快。
第二處戲劇性矛盾集中于小片的“上學問題”。出于經濟狀況,母親不愿讓小片繼續上學(母親甚至找王老師索要先前上繳的8元試卷費),小片對此的態度也猶豫不決。而王老師執意讓成績較好的小片留在學校,并四處尋求幫助。找村長協商無果后,王老師便借牯藏節為契機向寨佬尋求幫助。當寨子中的男人們相聚飲宴,圍坐在在陰暗的房間中,點起篝火煮食火鍋,推杯換盞的間隙,王老師向寨佬反映小片的情況,而寨佬卻用“女孩子讀書多了禍害男人”的理由拒絕提供幫助。隨后,王老師于舞蹈比賽前夕騎自行車到鎮上辦事,在山路上偶遇鄉長的車隊,他當即攔下車隊向鄉長尋求幫助,卻被鄉長嚴詞苛責,尷尬碰壁。《開水》的巧妙之處在于以諧謔的方式展現諸多的差異,卻不施加評論和干預,言有盡而意無窮。
《開水》所有的分叉路徑敘述與矛盾的想象性和解全部匯聚成一處巧合,即影片最后的苗舞比賽。所有的鄉鎮領導都坐在主席臺上充當評委,期間王老師遞了一張寫明小片失學困境的紙條到評委席上,眾人傳看之際恰巧被化肥廠老板得知,他當即決定資助小片繼續上學。同時,在上場比賽的前一刻,計懷寨隊伍中的一名女孩趁亂溜出了村子,慌忙間小片臨陣掛帥,她身著苗族盛裝,挽著繡有自己發明的花紋的頭帶,陰差陽錯間實現了自己登臺跳舞的愿望。最后,計懷寨代表隊因展示印有化肥廠廣告語的橫幅而獲頒“最佳創意獎”,沒有因為令人尷尬的舞蹈表演而名落孫山。導演將令人會心一笑的巧合匯集于電影最后的高潮中,升華了之前無技巧的,緩慢的敘述風格。
民族志虛構手段將少數民族的文化真實性吸附于對現實景觀的復刻與生活經驗的模擬中。此處“景觀”并不僅指代真實的自然美景與具有原始苗族特色的村寨建筑群,“經驗”也不局限于敘事的虛構和真實的動態平衡,更是人與環境反復磨合后催生的情境感,以及引發的文化層面復數意義。譬如全片出現若干處鏡頭描繪小片獨自坐在自家吊腳樓的露臺上,或怔然遠眺,或做女紅,而畫面下部可見到其他人家的窗戶與數條小徑的交叉路口,寨民們來來往往,自顧忙碌。畫面的最遠處是掛滿梯田的山沿,云霧隱約可見。這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意境:人,傳統民居,與遠山相映成趣。再如電影結尾處,跳完舞的小片依舊身穿盛裝,立于河邊,任憑河水浸濕褲腳,她無喜無悲,似乎在嘗試感知環境的流變。而在舞蹈比賽中,苗族少女隨著蘆笙的伴奏笨拙地起舞,機械式的表演讓人無法感知舞蹈背后的深層意義。淪為民俗搬演的舞蹈比賽隱喻著苗族文化主體性(subjecthood)對和本族人的感召力/信仰力正在衰退,小片作為族群成員正親歷著遲緩的文化異變。
民族影像志能夠從外部記錄某個族群正在消亡的暫態,跳脫他者思維,正如兼具“神性”和“苗族性”的小片肖像一樣,從少數民族文化簇(cultural cluster)的內部體驗,凝視,解蔽,感知和反映現實,實現真正的“文化化”(culturalized)書寫。而民族志虛構手段的目的則更加明確:將觀察和批評的視角指引向了詩意的,藝術化的方向。
【注釋】
1 彭兆榮.民族志視野中“真實性”的多種樣態[EB/OL]. http://www.sohu.com/a/217950462_136745.
2 對于電影拍攝者的觀察者(observer)身份的解讀,詳可參考云南大學徐函的論文《人類學“觀察電影”的發展及其理論建構》,刊于《世界民族》2016年第2期,第35-43頁。作者徐函借對比觀察電影(observational cinema)與傳統民族志電影的現象學的異同,以細致辨析觀察者身份對敘述真相的影響與引導。
3 Sjoberg.J.The Ethnofi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art 1 and Part 2)[EB/OL].http://www.faktafiktion.se/pdf/The%20Ethnofiction%20in%20 Theory%20and%20Practice%20Part%201.pdf.
4 朱靖江. 虛構式影像民族志:內在世界的視覺化[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43-47.
5 Joni L. Jones.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The role of embodiment in cultural authenticity[J]. Theatre Topics, 2002,(1):1-15.
6 王麗君.影視人類學視閾下紀錄片的故事性分析——以影片《神性消弭的爾瑪》為例[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18.
7 徐建新.自我民族志:整體人類學的路徑反思 [EB/OL]. http://www.cssn.cn/mzx/201904/t20190426_4870358_2.shtml?COLLCC=3995562769&.
8 羅如春. 論本雅明的靈韻觀[EB/OL].https://www.xzbu.com/7/view-7140497.html.
9 同3.
10 朱靖江. 在野的守望:影視人類學行思錄[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22.
11 Y.Chu. Chinese Documen tary: Fromdog matopoly phony [M].Lond on: Lond on Routledge,2007.148-182.
12 Gillette, M.B. New Anthropology Film in the New China [J].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30 (1): 1-13.
13 劉達成.獨具魅力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J].民族藝術研究,1996(6): 71-76.
14 張金華.視覺與抽象的悖論——原生態人類學電影的多維解讀[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4,(5): 2-8.
15 王海飛.近三十年來中國影視人類學的發展與研究[J].民族研究,2008(2):95-110.
16 原著雖然大量以少數族裔紀錄片為例證,以探討“民族志”電影的理論化和拍攝經驗為主要目的,但并未指明“少數族裔”題材的電影為研究主體。因為筆者認為“影視民族學”這種譯法并不能清晰傳遞研究主體的屬性。
17 Karl,H.Ethnographic Film[M].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26-28.
18 Martha B. A Boatload of Wild Irishmen by Mac Dara Curraidbin and Brian [J]. Leonerdo. 2013 (3):293-294.
19 容觀藑.關于加強人類學影片研制工作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13-16.
20 森茂芳.“民族紀錄片”的歷史演進、國家傳統和美學創新[J].民族藝術研究,2018 (03): 130-138.
21 [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鮑文研、張亞輝等譯.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202-211.
22 Weakland,John H.Feature Film as Cultural Documents[A].Paul Hockings.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C].De Gruyter.1995:45-68.
23 同21.
24 劉大先.當代經驗、民族志轉向與非虛構寫[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919/c404030-30302979.html.
25 Sjoberg, J.Ethnofiction: genre hybridi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based research[D].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2009.
26 因目前尚無準確翻譯,因此文中將docufiction直譯做“紀實性虛構電影”,參考英文解釋cinematographic combination of documentary and fiction film。同樣,docudrama解釋為dramatized film based on real event。中文翻譯為“文獻紀錄片”并不能準確表達這類文本的演繹/搬演的屬性,因此筆者認為該譯法也值得商榷。
27 Pault.M.H. Real with fiction[J].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2007, 23(1): 16-25.
28 Coate.J.Blurred Boundaries: Ethnofiction and Its Impact on Postwar Japanese Cinema[J].Art,2019(2):1-12.
29 Schmidt,NJ.Ethnographic Fiction: Anthropology's Hidden Literary Style[J].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1994(4):11-14.
30 胡庶.“苗”與劇情化記錄[EB/OL]. http://bbs.tianya.cn/post-384-4419-1.shtml.
31 劉潔.紀錄片的虛構:一種想象的表意[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280-299.
32 同30.
33 同31.
34 廖海波.影視民俗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49-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