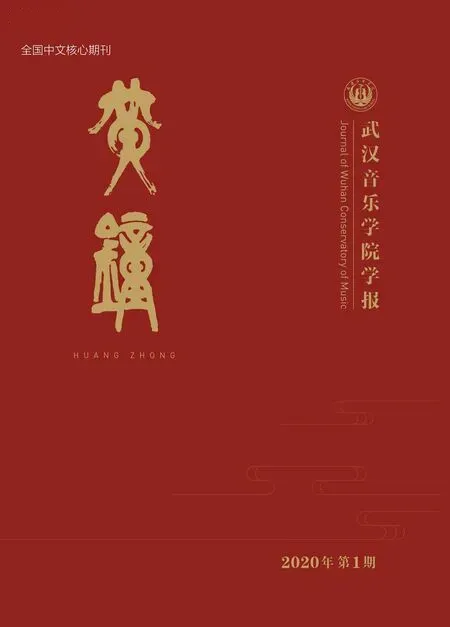是革新,還是復興?
——勛伯格“無調性”音樂中的復調-音程式創(chuàng)作思維探究
袁利軍
與前些年相比,近幾年國內學界有關阿諾德·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無調性”音樂創(chuàng)作的研究,已不再專注于“無調性”音樂作品中是否有調性因素的出現(xiàn),而是越來越注重去挖掘“無調性”音樂作品本身的形式建構原則,或與調性音樂的組織邏輯進行比較。①如楊玉嬋:《勛伯格<鋼琴組曲>Op.25的藝術特征和技法研究》(山東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趙倩:《勛伯格鋼琴作品23中第五首的創(chuàng)作技法及演奏分析》(《音樂創(chuàng)作》2018年第1期,第149-151頁);孫宇:《勛伯格<五首管弦樂小品>(Op.16 No.2)結構思維研究》(《音樂探索》2018年第2期,第101-107頁);師占成:《勛伯格音樂的音高組織與結構思維——以<勛伯格三首鋼琴小品>(Op.11)第一首為例》(《內蒙古藝術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第101-112頁)等。在這一悄然轉變的背后,有一個觀點實際上已得到越來越多的默認,那就是“無調性”音樂其實并非調性音樂的完全對立面,而是與調性音樂創(chuàng)作思維并列存在的另一種創(chuàng)作邏輯和思維方式。在這一基礎之上,本文則進一步認為,勛伯格“無調性”音樂中的創(chuàng)作思維方式實際上也并非完全革新的產(chǎn)物,其中主要依賴核心音程動機進行復調立體化貫穿的組織手段,與調性產(chǎn)生之前早期音樂的構建方式存在著一定的共通之處。
一、音樂歷史中的復調-音程思維與主調-和弦思維
依據(jù)不同的音高組織邏輯原則,學界有將西方音樂歷史劃分為前調性時期(大約17世紀之前)、調性時期(大約18、19世紀)和后調性時期(20世紀以來)三大階段之說。②可參見[美]Joseph N.Straus:Introduction to Post-Tonal Theory(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1990);陶辛:《西方音樂前調性時期音高組織思維研究——序論》(《音樂藝術》2003年第3期,第50-54頁)。前調性時期的音高組織主要依靠音與音之間的對位化關聯(lián)來完成,調性時期則依靠和弦與和弦之間的等級化關聯(lián)體系進行建構,而后調性時期(包括“無調性”創(chuàng)作)則表現(xiàn)為將調性時期的等級化體系放棄之后所進行的一系列個性化探索。
事實上,在調性產(chǎn)生之前,西方音樂在組織邏輯上便存在著類似“無調性”音樂中運用音程動機貫穿進行組織的例證。譜1是奧地利音樂理論家魯?shù)婪颉だ椎伲≧udolph Réti,1885-1957)在其名著《調性·無調性·泛調性》中所例舉的一首對中世紀格里高利圣詠有重要影響的猶太圣詠旋律。
譜1 雷蒂著作中例舉的猶太圣詠旋律③ 譜例引自[奧]魯?shù)婪颉だ椎伲骸墩{性·無調性·泛調性》,鄭英烈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頁。

他認為,在這首圣詠中,“所有的音都被一種十分類似調性的力量吸引在一起。E音代表中心旋律點,即一種主音,而整條旋律線可以看成是一個主要通過與這個基礎音的關系而建立起來的音樂單位。”④[奧]魯?shù)婪颉だ椎伲骸墩{性·無調性·泛調性》,鄭英烈譯,第16-17頁。他將這種現(xiàn)象稱為“旋律調性”。他認為,這種在古老的圣詠和一些民間音樂中常見的現(xiàn)象,顯然與西方古典音樂中所謂“和聲調性”的概念是不盡相同的。不僅如此,在整個西方音樂的歷史進程中,這兩種調性類型還呈現(xiàn)出了一種此起彼伏的發(fā)展態(tài)勢:當“和聲調性”成為音樂中的統(tǒng)治概念時,正是“旋律調性”從這種局面中弱化甚至消失的時候,而在20世紀現(xiàn)代音樂中,“和聲調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摒棄,而“旋律調性”則有可能得到合情合理的復興。⑤[奧]魯?shù)婪颉だ椎伲骸墩{性·無調性·泛調性》,鄭英烈譯,第19頁。在這一觀察視角之下,西方音樂歷史實際上也被大體分成了三個階段,并且這三個階段大致與之前提出的前調性、調性和后調性時期的劃分基本一致。只不過,這樣的劃分方式似乎能夠更好地將每個時期的創(chuàng)作思維本質揭示出來,尤其在第三個階段,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對第一個階段創(chuàng)作思維進行復興的做法。
實際上,在雷蒂的這一“旋律調性”概念中,主音的調性中心地位是依賴其他各音與其之間所構成的音程關系而得以確立的。并且,前調性時期復調音樂的組織建構也都是以音程的對位化建構為主的。鑒于此,我們不妨將這種組織思維稱為復調-音程思維,以此與調性時期具有嚴格等級化的主調-和弦思維形成對照。在復調-音程思維模式下,各音、各音程之間不存在等級上的差別,彼此平等、獨立,并通過一種音對音的組織思維進行音樂的建構;而在主調-和弦思維模式下,各音則與其較近的泛音組成縱向排列的和弦,并依據(jù)共同音的多少判別諸和弦之間的遠近關系,還根據(jù)各和弦構成之間的等級差別來建構具備強大向心力的調性組織體系。也就是說,在調性和聲體系出現(xiàn)之前,西方音樂主要靠的是音程以及結合體的組合形式進行復調化構建,而當和弦連接的形式出現(xiàn)之后,其從不協(xié)和向協(xié)和的“解決”進行更加能夠產(chǎn)生出某種從不穩(wěn)定到穩(wěn)定的滿足感。但凡事均有極致,當調性體系及其中的主調-和弦連接原則在19世紀末的一代作曲家那里行將就木時,以音程以及結合體為核心的復調組織形態(tài)便有可能再次浮出水面,成為西方音樂建構的根本基礎。
實際上,掀起“無調性革命”的作曲家阿諾德·勛伯格本人也曾明確地闡述過這兩種創(chuàng)作思維之間的差異:“雖然古典音樂文獻中的許多樂章都是把主調音樂的和對位的技巧兼收并蓄,但它們之間卻有著根本的區(qū)別。主調音樂式旋律的處理基本上決定于用變奏手法的動機發(fā)展。對位的處理則相反,它不是把動機加以變化,而是展示基本主題(一個或幾個)所固有的各種可能的結合。”⑥[奧]阿諾德·勛伯格:《作曲基本原理》,吳佩華譯,顧連理校,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頁。也許,勛伯格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才敢于大膽拋棄調性,邁向“無調性”的不歸路,因為他在潛意識中明白,就算音樂中沒有了功能調性體系的組織,卻仍有另一種用來組織音樂作品的手段,那就是早在調性體系產(chǎn)生之前就已在歷史中出現(xiàn)的復調-音程結合貫穿的形式構建手法。
這樣的觀察視角,有利于我們更加清醒地看待“調性”這一西方音樂歷史中最為重要和核心的組織手段。盡管西方音樂在幾百年的發(fā)展中逐步孕育出了“調性”這一典型的充滿西方文化精神的高級音樂語言體系,并依照自身的發(fā)展邏輯推動了數(shù)代音樂家的創(chuàng)作,但理論研究者卻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音樂語言并非西方音樂的唯一建構方式,也并非從一開始就存在。就其本身作為一種語言體系而言,它注定會在歷史中走向衰竭和自我否定的境地。
二、“無調性”音樂創(chuàng)作與復調-音程思維
為了論證“無調性”音樂與復調-音程思維之間的關聯(lián),我們來看一下勛伯格“無調性”作品組織邏輯的實質。籠統(tǒng)地說,這類作品中包含著一種“音程動機縱橫立體貫穿”的核心組織手段:每部作品都建立在所謂“核心音程細胞動機”的基礎之上。這個“核心音程細胞動機”由3至12個音級按照特定的意圖自由排列而構成,在音樂的發(fā)展與構建過程中,其可以橫向、縱向或橫縱結合等多種陳述方式出現(xiàn),也可以用它的倒影、逆行和倒影逆行以及各種轉位和移位的形式出現(xiàn),從而在樂曲中起到對比與統(tǒng)一的邏輯作用。
以勛伯格《空中花園篇》(Op.15)中的第7首(1908)為例(見譜2)。這首歌曲共19小節(jié),是勛伯格較早顯露出“無調性”創(chuàng)作思維的系列作品之一。盡管這是一首聲樂作品,但其中卻充滿著器樂化的創(chuàng)作思維。如譜2所示,在第1小節(jié)中出現(xiàn)的兩個不協(xié)和和弦顯然并不構成某種傳統(tǒng)功能性的和聲進行,而是充當了全曲的核心音程動機。第一個和弦由兩個大三度音程疊加而成,第二個和弦則由增四度和純四度疊加而成。其中所包含的大三度、純四度和增四度音程在樂曲后面的主要骨干處進行了變化性貫穿。如第3、4小節(jié)強拍上的變化形式:第一個和弦向上大二度移位加轉位,第二個和弦將其中的增四度和純四度音程上下倒置并向下小六度移位,同時兩個和弦的時值縮減1/2。再比如第7、8小節(jié)的擴展性變化:第一個和弦向上大六度移位加轉位,并擴展出過渡音;第二個和弦將其中的增四度和純四度音程上下倒置并移位(其中的以等音形式出現(xiàn)),并擴展出過渡音;第三個和弦與第一個和弦一樣,經(jīng)由過渡音后,第四個和弦則擴展成了由大三度和純五度疊加的形態(tài)。第9-11小節(jié),對核心音程動機中的第二個和弦進行了展開:其中主要的縱向和弦是由純四度和增四度疊置而成的,而中間的“分解和弦”也以純四度和增四度音程為主。終于,在第13-17小節(jié),核心音程動機的終極擴展變化形式出現(xiàn),半音階中的十二個音級出全,意味著發(fā)展過程的終結。最后兩小節(jié),核心音程動機以增值的形式“原樣”再現(xiàn),增加了結束時的穩(wěn)定感。除了以上提到的這些地方之外,其他小節(jié)處則大都以過渡句的樣貌出現(xiàn)。要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不管核心音程動機在這些地方的外形作出如何變化,其中的“音程內容”是保持不變的。
譜2 《空中花園篇》(Op.15,no.7)⑦ Arnold Schoenberg:Das Buch der h?ngenden G?rten,Op.15,Vienna:Universal Edition,1914.


1909年,《空中花園篇》(Op.15)還未完成,勛伯格便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鋼琴曲三首》(Op.11),其中的三首樂曲所采用的主要創(chuàng)作手段仍然是核心音程動機的貫穿。但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是,這部作品中所有的不協(xié)和音得以全面解放,音高之間沒有任何的等級性差別,所以這一核心音程動機在進行貫穿時,已經(jīng)完全實現(xiàn)了縱、橫貫通的立體化組織關系。如其中的第1首(見譜3),由b、g組成的三音核心音程動機(包含小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在前幾小節(jié)中以縱、橫的形態(tài)貫穿出現(xiàn)。尤其是第4-5小節(jié),這一動機以四聲部對位的方式出現(xiàn),其中包括高聲部出現(xiàn)的小三度音程、中聲部出現(xiàn)的加了經(jīng)過音的小二度音程,以及次中音聲部出現(xiàn)的對核心音程動機的橫向變形展開。在這期間,低音聲部的、中音聲部的b以及高音聲部的g又以縱向排列的形式構成了對核心音程動機的變化形態(tài)。
在5:00~15:00之間,站內出現(xiàn)由負荷和光伏發(fā)電引起的不平衡功率,電動汽車輔助儲能電池進行充放電,SOC在充電時上升,在放電時下降,電動汽車的調制功率在-1 500~1 500 kW之間。
譜3 《鋼琴曲三首》(Op.11,no.1)第1-5小節(jié)⑧ 譜3、譜4的版本均為Arnold Schoenberg:3 Pieces,Op.11,Vienna:Universal Edition,1910(1925).

再比如其中的第2首(見譜4),第2小節(jié)出現(xiàn)的核心音程動機Ⅰ(由三音構成的增五度、增四度和大二度音程)在第3小節(jié)通過“發(fā)展性變奏”⑨這一概念為勛伯格在分析勃拉姆斯的作品時提出,其主旨在于對音程動機進行的各種“在變奏中展開”的技術手段,如改變順序、裁減、增值、移位等。一個動機經(jīng)過發(fā)展性變奏之后,其形態(tài)可有較大改變,但其實質卻與原動機保持一致。的手段擴展為了音程動機Ⅱ(即在原有的音程之外,又增加了大、小三度和小二度音程)。在該樂曲的第1-13小節(jié)(第一部分)中,這兩個音程動機在主要的骨干處得到了各種變形、擴展和模進的再現(xiàn)。如第4小節(jié)的高聲部c實際上是音程動機ⅠⅠ的逆行變化形態(tài)(核心音程為大二度、小三度和小二度);中聲部的所包含的核心音程則為小三度、小二度和增五度,低聲部的兩個縱向音程分別是和(大三度的轉位形式),均為核心音程動機所包含的音程。第4-5小節(jié)低聲部出現(xiàn)的三音雖然似乎是作為過渡音出現(xiàn)的,但其中所包含的音程也在核心音程動機當中(增四度的轉位形式和大三度)。從第5小節(jié)到第9小節(jié),高聲部的音型似乎形成了一個推進高潮的段落——在第9小節(jié)的強拍和弦上到達高潮,其中所構建的音型也為兩個音程動機采用相同的方法所進行的綜合變形形態(tài)。之后,在第9-11小節(jié)出現(xiàn)的兩次推進,也是音程動機Ⅰ、ⅠⅠ的變形模進再現(xiàn)(核心音程為小三度和大、小二度),低聲部則為動機ⅠⅠ的縱向排列形式(核心音程為增四度、大二度和大三度)。終于,在第11-12小節(jié)處將十二個音級全部出齊,代表著音程動機發(fā)展的終極形式。而后,在第13小節(jié)以縱向和弦的形式回顧了核心音程動機中的音程內容,其中所包含的音程除了核心音程減四度(增五度的轉位)、大二度之外,還出現(xiàn)了相對協(xié)和的純五度音程,由此產(chǎn)生出相對終止的效果。另外,為了保證作品的統(tǒng)一感,作曲家在低聲部設計了持續(xù)不斷的三度音程背景,為高聲部對核心音程動機的各種擴展和變化提供了空間。
譜4 《鋼琴曲三首》(Op.11,no.2)第1-13小節(jié)

不僅如此,時隔十幾年后,當勛伯格于1923年宣稱自己創(chuàng)立了“十二音作曲法”時,其作品中也是類似的做法。只不過,這一時期的作品在對音程動機進行貫穿發(fā)展時,又兼顧到了其中的有序化排列,以及十二個音級的不可重復性——這也正是“十二音作曲法”的本質。以他完成于那一年的作品《五首鋼琴小品》(Op.23)中的第1首為例(見譜5)。
譜5 《五首鋼琴小品》(Op.23,no.1)第1-4小節(jié)⑩ Arnold Schoenberg:5 Pieces,Op.23,Copenhagen:Wilhelm Hansen,No.2326,1923.
首先,在前三小節(jié)中,十二個音級就全部出齊了(見譜例中標注的數(shù)字0-11);其次,通過對這幾小節(jié)音高組織邏輯的分析,可看出這類作品的組織依然是依靠核心音程動機的多樣化貫穿來完成的:高音聲部的三音動機所包含的音程是增二度和小二度,中音聲部的三音動機和低音聲部的(a-c-b)則主要包含小二度和小三度。由于增二度和小三度的音響效果是一樣的,在“無調性”音樂中,也可以將這幾個三音動機看作是同一動機的變化形式。如譜5所示,在短短幾小節(jié)中,對這一核心音程動機通過倒影、逆行倒影和移位的變化形式就多達十個。這些形式以縱橫交錯的方式排列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這類音樂中的音高組織建構邏輯。
而在勛伯格之后創(chuàng)作的完全十二音作品中,“核心音程動機”由之前的三音或五音動機徹底轉變成了由全部的十二個音級所構成的有序化“序列”。并且,由于十二音序列內部的音程內容是“恒等”的,因此這類作品的創(chuàng)作重心便轉向了對序列進行多樣化處理的方式上去了。比如美國作曲家喬治·佩爾(George Perle,1915-2009)對勛伯格1944年完成的十二音作品《鋼琴和樂隊協(xié)奏曲》(Op.42)前幾小節(jié)的分析(見譜6)。
可看出,高聲部是對十二音序列的原型展現(xiàn),其中每個音都沒有重復(持續(xù)音除外)——第5-6小節(jié)中對編號8、9、10三音的音型反復在作曲家看來并不算是重復,而低聲部則以片段化的自由組合形式填充在高聲部的長音空隙當中,由此形成連綿不斷的音響效果(見譜6中的數(shù)字標注)。

通過以上對勛伯格在不同階段創(chuàng)作的“無調性”音樂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核心音程動機的多樣化貫穿是其中的根本性思維方式。這些音程動機通過轉位、移位、縱橫變化、逆行、倒影、倒影逆行等方式進行的外在性變化,使音樂的音響不斷地得到更新,但并不會影響其中的本質性“音程內容”——這才是我們對這類作品進行考量時的主要“憑據(jù)”。而這種做法,正是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復調-音程創(chuàng)作思維的體現(xiàn),或者說是對這種思維方式的延續(xù)與發(fā)展。
在勛伯格的作曲觀念中,“無調性”音樂中的核心音程動機被稱為“基本型”(Grundgestalt)。為了更清晰地表達這類作品中的組織思維,他也曾在自己的著述中明確表示,“基本型”這個概念的內涵在英語中應該被稱為“基本集合”(basingset),或“十二音集合”(12-tones set),或者簡單地稱為“集合”(set)。?[奧]Arnold Schoenberg:“Problems of Harmony”(1934),The Musical Idea and the Logic,Technique,and Art of Its Prese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279.美國音樂理論家阿倫·福特(Allen Forte,1926-2014)將“無調性”音樂中不能稱為和弦的這些音程動機也稱為“集合”,并總結出一套音級集合的分析理論,無疑是音樂分析學一次革命性的發(fā)展。可見,運用“集合”這一數(shù)學概念來指稱“無調性”音樂中的組織邏輯似乎是比較合適的,它能將“無調性”音樂依靠音程組合的復調式構建來組織樂曲的邏輯加以暗示出來。正如喬治·佩爾所言:“在無調性音樂中,音樂的線條方面不再受標志調性音樂的和聲和旋律的嚴格標準所支配,這已大致暗示出把對位化寫作的方法用來作為組織整個音樂總體的方法。”?[美]喬治·佩爾:《序列音樂寫作與無調性——勛伯格、貝爾格與韋伯恩音樂介紹》,羅忠镕譯,第25頁。
武漢音樂學院鄭英烈先生早在1989年的論文《從調性到無調性——兼論勛伯格的集合意識與集合思維》中就提到,勛伯格在1905年的作品《歌曲八首》(Op.6)中已用到了自己的“署名集合”(EsCHBEG,即由六音構成的集合形式),從而展現(xiàn)出基于“集合思維”之上的作曲法。比如,其中第二首歌曲的歌唱聲部第一樂句采用了“署名集合”,并且這個集合所采用的是“無序”和“移位”的形式;而其中第六首歌曲的鋼琴引子右手聲部采用的是“署名集合”補集的逆行移位形式。不僅如此,1909年,由這一集合作成的旋律又被勛伯格用在了“無調性”作品《期待》(Op.17)當中。鄭先生認為,“這就從本質上有別于以往一些應用某大師的名字作為動機的做法,它意味著勛伯格基于集合思維的新的作曲法的潛意識已反映到他的作品中來了”。?鄭英烈:《從調性到無調性——兼論勛伯格的集合意識與集合思維》,《音樂研究》1989年第3期,第86頁。
筆者認為,在這種以音程內容為主要考量標準的“集合思維”模式之下,所有的和弦都失去了以往在功能調性體系中的“功能性”,而僅以其中所包含音程內容的異同和相似度來判斷彼此的關系。比如大三度和減四度并沒有功能上的區(qū)別,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所包含的音程內容也是相同的,而屬七和弦和半減七和弦也是相同的。通過這一角度的思考可推出,勛伯格的“無調性”和十二音作品中所展現(xiàn)出的,已并非是傳統(tǒng)調性思維所引致的中心感和動力向前的組織體系,而是以音程的“并置”化為邏輯,采用許多靈活的方式造成音樂構造上變化的另外一種結構方式。如此,既保證了作品的有機統(tǒng)一,同時又與傳統(tǒng)的調性結構方式完全不同。
另外,“集合思維”的概念中其實也暗含了音高組織在縱橫層面貫通的立體化創(chuàng)作思路,?這是勛伯格提出的“音樂空間”(musical space)概念的實質。而這是一種復調化的思維方式。美國學者默里·迪寧(P.Murray Dineen)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個勛伯格在教學中的故事:“勛伯格撿起一頂帽子,拿到他的學生面前,解釋道:‘你們看,這是一頂帽子,不管我從上、從下、從前、從后、從左、從右去看它,它一直都是帽子,盡管從上和從下看到的不一樣。’”?引自[美]P.Murray Dineen:“The Contrapuntal Combination:Schoenberg’s Old Hat”,Music Theo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st,edited by Christopher Hatch and David W.Bernstei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435.他認為,對勛伯格而言,“無調性”創(chuàng)作中的集合思維就是這頂“帽子”,它是一個多面的“音樂空間”。對于復調對位式作品而言,一個基本結合就是中心,每一個新的對位結合就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中心,雖然表面形狀不同,但聽上去依然可辨。而在“無調性”音樂的“集合思維”下,各音高之間的組合以及變化形式似乎也是這樣得以完成的。因此,默里·迪寧在文章中生動地將此方法稱為勛伯格的“舊帽子”。?參見[美]P.Murray Dineen:“The Contrapuntal Combination:Schoenberg’s Old Hat”,Music Theo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st,edited by Christopher Hatch and David W.Bernstein,p.435.與之對應的是勛伯格的“新帽子”——發(fā)展性變奏的技術。而勛伯格本人則也曾在1950年的文章《巴赫》中寫道:“巴赫是第一位十二音作曲家”?[奧]Arnold Schoenberg:“Bach”(1950).Style and Idea:Selected writings of Arnold Schoenberg,edited by Leonard Stein,with translated by Leo Black,London:Faber&Faber,1975,p.393.。
這種依據(jù)復調式對位結合進行建構的方式,實際上有利于在音樂作品中構建出更加立體的、多維空間式的音樂樣貌。而勛伯格本人的確十分重視復調對位技術在創(chuàng)作訓練中的地位,正如他在《對位法初步訓練》一書中所言:“須以一種十分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對位理論。它不只是純粹的理論,而更是一種訓練方法。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意在教會學生在日后作曲時學會如何運用知識和思想。因此,不但要發(fā)展學生在聲部寫作方面的能力,而且還要向他們介紹非常藝術化的作曲原理,從而引導他們認識到這些原則能在多大程度上作為藝術中的通用原則”?[奧]阿諾德·勛伯格:《勛伯格對位法:對位藝術的探秘之鑰》,[美]倫納德·施泰因編,周強譯,孫紅杰校,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57頁。。可見,對于勛伯格而言,學習復調對位法不僅僅是為了效仿前調性時期作曲家的寫作手法,而是將其作為一種更為通用的音樂創(chuàng)作思維,運用在具體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去。很顯然,我們在他的作品中也的確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
可見,“無調性”音樂中的組織邏輯確非憑空出世的全新手法,而是來自勛伯格對歷史中兩種音高組織思維(尤其是前調性時期)的深入理解。
三、“無調性”音樂復興復調-音程思維的多重緣由
上文已證實“無調性”音樂與復調-音程思維之間的關聯(lián),而如果從歷史、美學與哲學的視角去反思這一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緣由,則也有一番意味。
從音樂創(chuàng)作的原初層面來看,作曲家在面臨音樂創(chuàng)作時,他首先面對的是每個獨立的音高本身,而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任務就是將這些音高進行彼此之間特定的組織和構建。當兩個音出現(xiàn)之后,音程的意義便顯露出來。而就音程概念中的兩個音高本身而言,它們之間本來并不存在著優(yōu)劣高低的等級差別。反倒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出現(xiàn)的功能調性和弦體系,賦予了這些音高以特定的等級功能性。從“和弦”本身的構成上來看,它在縱向構成上的幾個音之間便已達成某種等級性的關系,比如根音實際上產(chǎn)生出了將其他各音聚合起來的一種中心力量,其他幾個音都因為與根音之間的某種功能性關系而產(chǎn)生出特定的功能屬性。同時,這幾個音又以縱向的形式融為一體。由此,“音程”與“和弦”之間的屬性區(qū)別便一覽無余:“音程”一詞不包含某種功能性,而“和弦”一詞則為其中的音高添加上了更多的功能性內涵。由此可見,“調性”才是西方音樂特定歷史下出現(xiàn)的一個特殊文化產(chǎn)物,而前調性時期和后調性時期無非是沒有采用這一對象進行創(chuàng)作而已,同時其更多地依賴于無等級差別的單個音和音程作為基本單位,似乎反倒能夠顯示出更具原初意味的作曲內涵。
正是由于音程思維下對單個音高所附屬的功能性進行的撇除,便讓“無調性”音樂和十二音序列音樂在音高組織和建構方面與之達成了某種共通。也正是基于音程和和弦之間原本就存在的這一差異,復調-音程思維和主調-和弦思維所構成的音樂樣貌也形成了差別。在主調-和弦思維下,和弦是音樂建構的最小單位,因此作曲家的音樂創(chuàng)作所關注的主要是其中和聲銜接的橫向功能邏輯,由此形成了具有明確方向感和動力性的音樂;而在復調-音程思維模式下,由于音程或單個音成為音樂建構的最小單位,因此作曲家在創(chuàng)作中則不僅要關注橫向上的音高序進,同時也需要兼顧各音高在縱向上的結合方式,由此形成了更具空間化和立體化的音樂形態(tài)。
從另一角度來看,歷史之所以形成這樣的音樂發(fā)展樣貌,實際上與每個階段主導性的美學思潮也有著神秘性的關聯(lián)。前調性時期,西方世界受到基督教文明的壟斷性統(tǒng)治,其在美學觀念上追求的是同一性和相似性,而對對立、差異和變化則持排斥態(tài)度,因此那一時期的音樂中在音高組織上也體現(xiàn)出平等、無等級差別的狀態(tài)。而在調性時期,啟蒙理性哲學占領著觀念上的主導地位,其講求理性以及對立統(tǒng)一的規(guī)則和規(guī)范,因而音樂中的各要素便也相應地具有了嚴格意義上的等級劃分,并形成了一套嚴格的規(guī)范體系。在后調性時期,隨著非理性主義哲學的崛起,對理性、中心和規(guī)范的打破,以及對規(guī)則和權威的排斥成為主導理念,在音樂創(chuàng)作中尋求去除中心性和等級性等美學觀念,都恰恰成為復調思維與音程思維得以復興的樂土。
從哲學角度而言,前調性時期流行的經(jīng)院哲學強調對基督教教義的專權維護,因此其音樂中追求相對平穩(wěn)、協(xié)和和無差異性的音高組織傾向,而調性時期以哲學家黑格爾(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肯定辯證法”為主導的德國古典哲學強調矛盾對立雙方在更高層面上的和解,推崇所謂“同一性原則”,因此那一時期的音樂中遵循著唯一的調性體系原則,幾乎所有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都是在這一體系原則之下進行發(fā)揮。在后調性時期,以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Adorno,1903-1969)的“否定辯證法”為代表的現(xiàn)代哲學的核心則是對“同一性原則”的批判,強調對個體性和差異性的正視和保留。因此這一時期的音樂中充滿著對立的各方,它們不尋求解決和化解,而是赤裸裸地以對立的姿態(tài)展現(xiàn)在作品當中,呈現(xiàn)出平行化和并置化的特征。比如在勛伯格的十二音序列作品中,不僅十二個半音的地位均等,包含十二個半音的序列之間也構成平等、無等級性的伙伴關系,而非依附和主次的關系。事實上,阿多諾也認為,勛伯格的十二音音樂本質上就是一種對位法性質的技法,復調風格和對位法在這里實現(xiàn)了真正的復興和再生:“對位法毫無疑問地是十二音技法的實際受益者,它在作曲中獲得了首要地位。在十二音音樂中對位法的邏輯優(yōu)越于和聲-主音音樂的邏輯,這是因為這種邏輯將縱向結構從和聲的約定俗成的力量中解放了出來。……依靠序列關系的力量的普遍性,十二音技法從本源上講就是對位性質的技法,因為所有共時的聲音都是獨立的,一切都是序列的整體組成部分……”?轉引自于潤洋:《現(xiàn)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頁。
綜上所述,勛伯格“無調性”作品中以單個音為個體彼此組合而成的縱橫貫通式的空間化音樂,是由復調-音程式創(chuàng)作思維所構建出來的結果,是在某種程度上對前調性時期音高組織思維的復興和拓展。而無論從音樂創(chuàng)作的原初層面,還是從歷史、美學和哲學的視角來看,這樣的結果都有一定的必然性。
——評《勛伯格與救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