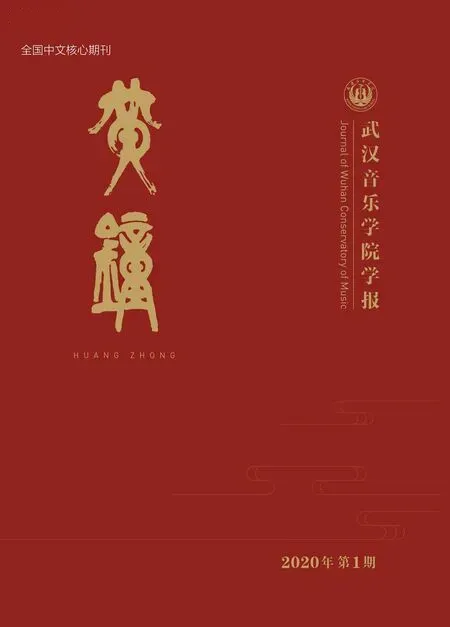近代中國音樂史加強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學術意義
夏滟洲
歷史學層面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內容包羅萬象,領域十分寬泛。日常生活史既是具體的歷史存在,又是綜合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理論范疇。從理論上,日常生活史研究具體的人與社會生活方式、人的實踐行為及其觀念的歷史。內容涉及日常生活中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兩個方面。前者是與日常物質文化相關的各種日常實踐行為;后者是與大眾日常實踐形為相關的觀念活動,這種觀念活動既受大眾內在的精神文化需求驅動,又與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活動有關,作用并反作用于外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可見,由具體的人在具體的生活實踐中繪就的日常生活,完全可以成為我們了解近代中國音樂文化發生、發展的接觸點。事實上,歷史是具體的人在具體的生活實踐中繪就的,人的求知欲促使我們想了解中國近代音樂文化的發生、發展過程及與之相關的情境,日常生活史研究無疑可以完美建構起豐滿、均衡的中國近代音樂解釋體系。
從發展眼光來看,將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作為中國近代音樂史的理論探討對象之一面,一是學科自身建設的需要,二是可以引領中國近代音樂史學研究注重以問題意識整合不同類型的史料,進而加強對史料與音樂本體之外的歷史語境的想象與理解。下文擬在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討論開展日常生活史研究之對中國近代音樂史學研究拓展的積極意義。
一、近代中國日常生活中的音樂與研究
作為人類發明的一種智性形式,音樂史是一門在歷史的框架內研究和理解人類所創造的音樂作品,以幫助我們發展和理解當下的音樂藝術。它既包括揭示隱含在音樂作品本身之中的歷史,又包括從音樂作品的內在建構中讀解到作品的歷史性質,還包括依據那些傳世的音樂作品的作者、創造過程及與之相關的情境的探索。事實上,檢索中國近代音樂史學界的研究,不難發現學界聚焦于中國社會音樂文化思潮的變動,及大量的音樂本體研究等方面,甚或在概念框架中獲得解釋的理論方法總結性研究,都取得了豐富、富有創建的成果。現如今,筆者提出把日常生活史當做一個理論探討的視角和領域,原因在于音樂史一方面與其他學科的交融趨勢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以音樂為出發點而研究人類歷史的學科要求使然。當音樂的形式結構和風格、材料運用與音樂欣賞自洽,音樂文化的時代精神得以完成建構。然而,音樂史作為我們理解人類歷史的一種必要形式,我們要盡可能寬闊地從人類活動背景中去探索和理解音樂家的創造。可見,基于日常生活的音樂史研究,在深化中國社會音樂文化思潮的變動,和大量音樂本體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解釋音樂作品與世界和社會的關系,從而更為全面地展現音樂之為人類精神持續進化的歷史面貌。
音樂的客觀存在,始終與其賴以生存的整個社會環境融為一體。常態下的音樂文化即我們所稱謂的傳統音樂,特別是與特定民俗、禮儀和之間聯系密切的傳統音樂,長久生存于小農經濟社會秩序之中,在漫長的發展中凝結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穩態屬性,在近代音樂發展中,發揮了音樂基本結構的均衡性,豐富了大眾日常生活,反映了社會與時代共同的文化特征和習慣作用。針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研究,學者們深入田野,進行社會調查,采用民族音樂學通常的研究方法,從本體分析到樂種形態描述,再到民族志、風俗志描述,一批批成果如陜北民俗音樂研究、河北固安屈家營音樂會研究、少數民族民間音樂等,將中國傳統音樂的文化屬性、音樂的社會功能及其在特定社會風俗或特定意識中的功用做出具體研究。
更多歷史學視野下的研究,揭示出任何社會的音樂都是奏鳴于時代之弦上的。面對近代中國日常生活,音樂史學研究者緊緊抓住歷時演化的基本現實,從歷時的角度將紛繁的史實梳理出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見解和問題。同時,諸學者務盡其力遍訪史料,考證錯舛,于瑣碎難尋的第一手資料中輯錄出版了大量的音樂家全集、作品集、音樂文論、文集等,既為研究近現代音樂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又深化拓展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的研究維度。基于歷史學層面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成果不勝枚舉,這些成果標識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研究中音樂史學本體意識的確立,以及在具體研究路徑、觀察視角上反映出研究者的主體意識與差異等研究特征,影響要大于所收獲的研究成果。造成這一局面的出現,原因在于一定社會意識形態對研究者的束縛。換言之,面對我們身邊的音樂生活,究竟應該抱持一種什么樣的立場重構“讓史料說話”的客觀主義治史傳統?
將音樂納入意識形態領域,也是近代中國日常生活研究中的一部分。音樂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其存在和發展不僅深受社會物質生產的現實影響,還要受到政治、法律以及宗教等常態活動的影響。近代中國在歷時上經歷著傳統向現代的逐漸轉化,共時上經歷著中西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中國人民的反侵略和反壓迫、國內多種政治勢力之間的文化斗爭,刺激新興音樂文化發展,涌現出各種思潮。繼20世紀上半葉發生諸種論爭和多元思考以來,學界收獲了相當成果,如張靜蔚①張靜蔚:《近代中國音樂思潮》,《音樂研究》1985年第4期,第77-92頁。、馮長春②馮長春:《中國近代音樂思潮研究》,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年版。、余峰③余峰:《近代中國音樂思想史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等的研究,將中國近代有關音樂思潮史實加以梳理,分析了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互動關系,闡述了音樂文化的時代精神,平衡了音樂研究中的哲學維度,筑起了音樂研究的理論之基。
以往中國近代音樂史研究,除了上述三個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研究把日常音樂生活視為一個觀察點,認為日常生活是人們為維系自身存續和再生產,在一定的社會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中一切常態活動的總和,從而在研究中以一幅幅特寫式的畫面展現豐富的近代中國音樂生活,既是特定歷史條件下音樂家的創造和人們精神生活的表現形式之一,又是人們娛樂交往和影響自身精神世界的介質。學界部分地采用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路徑,或以人物為主線,以點帶面描述人與社會、人與時代的互動關系,如孫繼南的黎錦暉研究④孫繼南:《黎錦暉評傳》,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年版;《黎錦暉與黎派音樂》,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年版。;或站在當時日常音樂活動的角度論述了中國近代社會文化生活的關系,指出諸如早期西方音樂傳入中國時,雖然是西人娛己的日常行為,但也潛在地對中國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如宮宏宇的系列研究⑤宮宏宇的系列研究文論:《“貝多芬”在上海(1861-1880)》,《中國音樂學》2016年第1期,第36-43頁;《晚清上海租界外僑音樂活動述略(1843-1911)》(之一、之二),連載于《音樂藝術》2015年第2期,第19-29頁與2016年第1期,第87-101頁;《晚清海關洋員與國際博覽會上的中國音樂——以1884年倫敦國際衛生博覽會為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第3-19頁,等等。;或針對一些留學國外音樂家、在華外籍音樂家的活動展開研究,有社會歷史背景,也有音樂家的工作行為、人際交往等日常生活,如韓國鐄的研究⑥韓國鐄:《留美三樂人》,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實業有限公司1984年版;《韓國鐄音樂文集》(一~四),臺北:臺灣樂韻出版社1990年版(一)、1995年版(二)、1992年版(三—四);《自西徂東》(二輯),臺北:臺灣時報文化實業有限公司1981年版(一)、1984年版(二),等等。,“使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研究的步伐得到提高。同時也糾正了一些因為粗略研究而形成的錯誤結論”⑦劉湜湜:《從<留美三樂人>看韓國鐄的史學研究》,《交響》2010年第3期,第107-112頁。。特別是洛秦⑧洛秦的有關研究文論:《音樂1927年敘事——國立音樂院(今上海音樂學院前身)誕生中的中國歷史、社會及其人》,《音樂藝術》2013年第1期,第6-28頁;《論上海“飛地”音樂社會的政治與文化空間》(上、下),連載于《音樂藝術》2016年第1期,第68-86頁和2016年第2期,第44-61頁,等等。的有關研究及其基于“地方性知識”的區域音樂文化論域——“音樂上海學”,與熊月之主持的“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⑨如葛濤:《唱片與近代上海社會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馬軍:《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系列研究殊途同歸,以人類學所強調的研究中“他者”的立場,關注上海城市社會音樂生活的方方面面,拓展了近代中國音樂生活的解釋空間,更新了中國近代音樂史的研究旨趣。
二、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三個關聯層次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音樂學家郭乃安就發出呼吁“音樂學研究應該關注人”。郭先生在其《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一文中指出,“音樂,作為一種人文現象,創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樂的意義、價值皆取決于人。”還說,“在音樂本身與外部諸條件的交互關系中有一個中心的接觸點,那就是人。人是音樂的出發點和歸宿。”⑩郭乃安:《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中國音樂學》1991年第2期,第16頁。個中道理,世間日常音樂生活是人的創造、人的需求,無論哪一方面都離不開人的因素和人的推動;而對日常音樂生活的研究,亦是在通過關注平凡之人重復的日常音樂生活的研究,來尋找歷史的動力和意義,開拓新的內涵和研究空間。到2012年,史學界始見這一看法,如常建華認為,“社會生活史就是以人的生活為核心聯接社會各部分的歷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價值,應該是建立以人為中心的歷史學。生活史立足于民眾的日常活動,從生活方式上把握民眾,民眾生活鑲嵌于社會組織、物質生活、歲時節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態中才能體現出來,并揭示民眾生活與政權的關系以及歷史變動帶來的影響。”?常建華:《中國社會生活史上生活的意義》,《歷史教學(高校版)》2012年第1期,第7頁。
藝術基本原理告訴我們,音樂生活的構成包括社會、音樂家、作品和受眾幾個環節,活動隨人類日常娛樂、儀式、禮俗等實踐活動過程中的需要存在和發展,其發生經歷著流動與互聯反饋的動態性活動過程。對日常音樂生活的研究如前所述,我們可采取歷史學、或社會學、或人類學、或民族志風俗志的描述以及跨界學科等方法,針對不同研究對象分析其具體的、日常的現象,通過這種分析找尋日常生活與歷史特征的契合點。聯結各個條件的中心接觸點即“人”。因為,音樂生活的主體(音樂家和受眾環節)是人,音樂的物化載體(作品環節)也是人的創造,社會更是主體賴以生存的基本生態環境,正是在那里,人們日復一日重復著聽賞音樂、使用音樂的各種活動,于是,在一個歷史的框架里,基于主體的活動我們有了考察音樂日常生活的觸角,憑借日常生活史我們有了理解人類歷史的必要形式。畢竟,一部音樂作品的存在,并非意味著音樂史的存在,對其的研究,亦不能完全立足于音樂本身。
從理論上說,以“人”為中心,運用日常生活史的視角和領域可以在三個關聯層次中得到確立:
其一,加強日常生活史研究與歷史變動的關聯。歷史研究,就是探索、理解人類過去所發生的,或想象中發生過的特殊事情的因果關系。歷史存在的形態有兩種,一種是常態的、在一定時間內歷史事情基本處于不變的狀態,一種是動態的、在相對時間內歷史事情發生變化的狀態,即非常態的。非常態的歷史事情就是歷史變動。歷史變動還表現在,受政權分治、更替的影響而發生的變動,在不同時空中的發展有差異,影響文化、民族、語言、風俗、思想、宗教等方面雖然會有實質上的不同,但卻有著恒常的內在聯系。日常生活史恰好注重把握歷史事情的內在聯系,通過研究社會生活與其內在的觀念形態之間的互動關系,從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上去理解、把握各種特殊事情的意義,將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歷史融為一體。其現實意義則是通過日常音樂生活史的研究認識過去時代的物質文化變遷,通過對前人音樂生活的觀照來認識當下。
其二,加強日常生活史研究與音樂學研究中敘事與分析的關聯。敘事與分析是歷史撰述的基本方法和要求。歷史是被記錄下來的過去發生的事情,但歷史本身并不會敘事,我們對過去所發生的,或想象中發生過的特殊事情的因果關系的探索、理解,就是歷史敘事。敘事強調掌握大量的歷史文獻,并在梳理和提煉文獻的基礎上敘述歷史、還原歷史。日常生活史強調自下而上地觀察歷史,理解的歷史生活實景,僅靠單一的材料遠遠不夠。除文獻載籍、圖像遺物外,還需搜羅區域社會調查資料、民間文獻、地方志及分志(風俗志)、民間日記、藝人抄本、口述史、樂器實物、樂譜類、音像類、報刊、宣傳海報、節目單等與人類音樂活動有關的各種資料,通過對這些材料的綜合運用和綜合性分析與敘事,以走進歷史主體,揭示社會生活的表象及其與主體經驗的內在聯系,還原音樂生活世界的特征。從這一關聯層次上,日常生活史研究可謂拓展了史料的范圍。
其三,加強日常音樂生活史研究與跨學科的關聯。音樂作為一個獨立自在的世界,依據其自身的邏輯與存在方式呈現特點,同時作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音樂還要受到其賴以生存的整體文化環境的限制。音樂史研究既是對具體的音樂作品所作學術研究,如具體作品形式與風格分析和材料研究,又是以音樂為出發點,運用相關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文化史理論研究人類歷史的學科。前者為所謂“內部音樂史”,即關注音樂理論自身合理性發展與自洽性建構的歷史,一般指欣賞、形式風格分析和材料研究,它對音樂的內部理路發展起著決定作用;后者為“外部音樂史”,也就是把音樂放在社會政治、文化歷史和心理因素層面加以考察的歷史,它對音樂的發展起著影響作用,好似音樂藝術的外部土壤一樣。?提出歷史研究“內部史”(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與“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解釋模式的,來自英國哲學家T.S.Kuhn為《國際科學史百科全書》撰寫“科學史”(History of Science)詞條時所區分的概念(T.S.Kuh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D.L.Sills(ed.),New York: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1968,2nd.1979,Vol.14,pp.75-83)。我國歷史學家葛兆光提出中國思想史的理論解釋范式即內部理路與外部土壤的關系問題,大意與之相同(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頁)。一段時間以來,這一范式為史學界所采用。事實上,在音樂史研究中,這種區分是十分機械的,它無助于對個體音樂家的理解。而日常音樂生活史研究并非完全以日常音樂生活為背景的研究,其研究范圍相當寬闊,并不局限于風俗史、民族志的路數。日常生活史研究有細膩的視角,但材料卻又十分重要,不僅有明確的史學學科邊界,還有相對集中的研究主旨。因此,我們倡導實踐日常音樂生活跨學科研究,不僅可以從外部促進音樂學研究中的社會學、符號學、經濟學、心理學的誕生,而且可以從學科內部深化且加強哲學、歷史學的研究。?夏滟洲:《音樂學研究中的“跨界”認識》,《音樂研究》2014年第2期,第17-21、81頁。還有助于揭示音樂作品與社會的關系,可以打破機械的“內部音樂史”和“外部音樂史”的闡釋立場。
三、以“人”為中心走進近代中國日常音樂生活
舉二例說明以“人”為中心走進近代中國日常音樂生活的學術意義。
(一)有關近代中國學校音樂教育生活日常
中國社會在近代的轉變,源自歐洲的音樂文化表現形式逐漸成為近代中國新音樂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中,給中國民眾帶來了深遠影響。受變法維新思潮影響,國內開始設立新式學堂,學校音樂教育逐步興起。一時間,辦新學,唱樂歌,國內主要城市特別是通商口岸城市中小學音樂教育有了明顯的發展和進步,成為20世紀初中國音樂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反觀既往近代中國學校音樂教育的研究,論域廣、成果豐,從多個層面將近代中國音樂教育因襲過程中出現的諸問題給予了充分關注,這些研究著眼于大視野、大結構、大過程和大比較,偏重于上層研究力圖從整體上說明近代音樂教育的客觀存在,解釋其發展規律,具有“社會科學化”特征。
學科的分化使我們的研究更富意義。源頭上,無論歷史學家的任務還是教育的功能,本來目的都是解釋歷史上發生的事情的意義,提高人們認識水平,以史育人。因此,從民族志到音樂人類學,其學術理路旨在開啟音樂史運用“平視”歷史的視角來敘事,于是,歷史人物、歷史事情取代了人類學的“初民”與“文化事象”“社會行為”,解釋空間驟然擴大。而音樂社會學的引入,以音樂為媒介,運用相互性視角綜合觀察人和社會的關系,既要注意到人和社會的顯性關系,又要發掘二者的隱形關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那種堅持系統整體論、合力論以求大求全的追求傾向。?夏滟洲:《音樂社會學學科規訓及操作機制新論》,《音樂藝術》2005年第3期,第120-128頁。在具體的歷史及情境中,人們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首先是源于生活的需要,繼而在特定的時代和地域中不斷發展并服務于人們的生活。從人類學到社會學,對這一歷史現象的研究,無疑是對傳統史學研究方法及研究進度的更新。
從日常音樂生活史與音樂教育研究的關聯中,我們可以看到研究理路上的更新。在近代中國音樂教育事業研究領域,諸多文獻為之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支撐,除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等之外,像俞玉滋、張援的《中國近現代學校音樂教育文選(1840-1949)》?俞玉滋、張援編選:《中國近現代學校音樂教育文選(1840-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孫繼南的《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史紀年(1840-2000)》?孫繼南編著:《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史紀年(1840-2000)》,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和張援、章咸的《中國近現代藝術教育法規匯編(1840-1949)》?張援、章咸編:《中國近現代藝術教育法規匯編(1840-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是關涉音樂教育的參考文獻。這幾種文獻不僅提供了大量反映中國學校音樂教育發展及先輩們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教訓,還為我們勾勒出了20世紀中國音樂教育事業的基本面貌,也是當今音樂教育工作者了解自身所從事專業的歷史及近代中國音樂教育生活的主要來源。其實用價值毋庸置疑,已然是眾多研究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史論題的必備讀物。大量相關研究,據之以長時段、大跨度的宏觀視野,傳統史學研究方法,觀察近代中國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規律,并無不妥。但是,存在于那種大結構、大過程之中的歷史研究,缺少對“人”的關注,以及發生在具體的“人”身邊的一些鮮活的材料,即便有具體個案研究,仍是理論總結居多,生動不夠。
對于近代中國學校音樂教育活動的研究,理應有多樣鮮活生動的敘事。近代中國繼新學堂的音樂教育之后,各地開辦的學校音樂教育,具體情況有深有淺,執行國民政府頒行的“壬戌學制”也有差異,且在加強音樂知識傳輸,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幫助學生輕松地掌握知識、創造愉快教學環境諸方面,有著一致觀念。各地注重音樂(美育)教育既是生活的日常,也是日常生活的必須,但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不同。基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既可以看到各地學校音樂教育的發展水平,又能通過總結當時日常教育的經驗以給今天以啟發。如1923年夏天老舍應邀在京師第一中學任教時,“舒老師不僅在音樂課中把昆曲當作教材,而且在國文課上也唱過戲,這使學生們大為驚訝。有一次他講解諸葛亮的《出師表》,大講《失街亭》里的諸葛亮,……便學著當時紅極一時的名演員譚鑫培的念白‘悔不聽先帝之言,錯用馬謖,乃亮之罪也’。他告誡學生們說:‘以后聽戲,不要只聽那些味兒,要看有益身心的感人之處,諸葛亮就知錯認過嘛。’……還有一次,講解駱賓王的文章,突然唱起了昆曲《彈詞》,只見他一板一眼打著拍子,一本正經地唱下去”?王晉堂主編:《古校邁向21世紀——北京一中校史稿》,北京:華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頁。,老舍在講授國文、音樂與修身課程時,運用京劇、昆曲等傳統音樂豐富課堂教學的記載,還原了民國中學學習生活和音樂教育生活的圖景。再看滬江大學附中的學生生活,“什么我最近學會了一種舞呀;啊,興奮極了,大家表演起來。‘喳……喳……,美麗的摩登舞!’‘ⅠfⅠhad a talking picture of you’,‘Ⅰlove you!’呀,震人心弦的洋歌!‘借燈光,暗里里……’呀,蒼涼圓滑的京調!”?周怒安:《一學期》,載《中學生文藝》(年刊)1931年第1期,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類似學生們課余的娛樂生活記載,反映了20世紀上半葉上海社會流行的摩登歌曲與傳統音樂形式及民眾的音樂欣賞觀念。同時期音樂社團的蓬勃發展也深深地影響到了音樂教育的發展方向。為追求身心平衡、和諧發展,民國中學生主動選擇文化發展道路,砥礪學識,紛紛組建社團、成立樂隊,培育才能,一時成為風氣,強化了音樂教育的實踐能力培養,延伸擴展了課堂知識學習,間接地為社會培養后備音樂人才起到了積極作用。在1920年后的廣東,“廣東華僑……還捐錢購買了許多管樂器,送回廣東的學校,建立管樂團。象臺山、中山、梅縣、新會這些華僑較多的縣份,中學、師范都建立了樂隊。……這些樂隊多則八、九十人,少則三、二十人。”?李凌:《二十年代后期廣東大、中學生的音樂生活》,載于李凌:《音樂雜談》第三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182頁。根據《冼星海全集》所載圖像資料,我們可知1924年冼星海就在其就讀的嶺南中學參加樂隊,擔任單簧管演奏。?《冼星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冼星海全集》第七卷,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前置插頁第4頁。1933年南京金陵中學存在的23個業余學生社團中,即有“國樂研究會、西樂研究會、話劇社、平劇社、國術研究會”?南京市金陵中學編:《南京市金陵中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頁。;北師大附中的國劇社成員還集資購買樂器,“每星期六下午一大堆響器如單皮、鐃鈸、小鑼、大鑼、堂鼓、胡琴、二胡、月琴都帶到學校里來。為了使國劇社正規化,聘請了羅小寶的堂弟擔任教師。……使我們很快達到彩唱的程度。像《法門寺》、《二進宮》、《武家坡》、《坐宮》等羅先生也一一給予排練,使大家對京劇增加了興趣。”?北師大附中編:《北師大附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頁。這些中小學課余音樂社團的學習及演藝(劇)活動,是校園文化的有機構成,也是對學校音樂課程的有益補充。
這里略舉幾則材料,試圖說明音樂史研究中采用日常生活史方法來敘述民國中學生的音樂生活,抑或說明課堂教學之外文娛活動的開展。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社會音樂文化的傳播度、學生對音樂的接受度,和學校對學生業余文娛生活的重視度,還有當時學生在傳播音樂、推動中西音樂文化發展形成過程的潛在作用。正是在這一層面,它十分恰當地定位了近代中國學校音樂教育“尚樂之風”的歷史存在,深化了中國近代學校音樂教育活態研究。
上例不成系統的研究還告訴我們,社會教育是個人生活社會化及人格形成的過程。在傳統和近代兩個不同社會中,社會教育與各種社會關系的互動,有著本質的不同。但在社會秩序的規范、人格的養成、修養的提升上則是一致的,這些教育的功能旨在培養人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塑造人性,調節人與社會的各種關系協調發展。然其同與不同,似乎只有“以小見大”的研究才能消弭之。日常生活史研究力圖解決的正在于茲。
(二)交集:任光與聶耳的生活日常
對近代中國音樂家的研究,絕大多數都集中于生平事跡的考訂、作品分析和歷史地位認識方面,鮮見對作曲家生活、作品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的分析,實難見其在當時社會生活的影響。一個客觀的事實,就任光與聶耳這兩位在近代中國音樂史上尤其在中國新音樂運動發展中做出重要貢獻的音樂家而言,學界對前者的關注稍遜于后者,原因眾所周知。倘若將二人有關日常生活、社會活動及其音樂創作加以綜合觀察,我們或許會得出些許與既往研究不同的看法。
任光和聶耳相差12歲,有著不同的出生、學習和成長軌跡。他們于1932年7月23日在上海相遇,開始了二人從事革命音樂活動的歷程,開始二人的交集。作為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因素——時間,在任、聶二人的交集中,雖然只有短暫的2年9個月不到的時間(其間還包括聶耳1932年8月7日離滬赴京到11月8日乘火車回到上海的3個月在內),但卻是聶耳完成全部音樂創作的階段、任光畢生音樂活動最為活躍的階段。此間他們二人的生活狀態反映了持主流價值觀的國人對社會關系與社會生活的思想和認識。下文先從大的時間點出發:
1931年4月22日,到上海才不到一年但過著窘迫生活的聶耳,以“聶紫藝”的名字考入黎錦暉組建的明月歌舞劇社,任小提琴演奏員。1932年7月23日,任光代表百代唱片公司音樂部去明月歌舞劇社審聽民樂合奏節目,初識聶耳,二人當場進行了鋼琴與小提琴的合奏;不久聶耳離開上海打算攻讀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然而考試不第,生活難覓,不得已返回上海;11月26日,在田漢等的幫助下,進入上海聯華影業公司一廠工作。任、聶二人再一次晤面,是在1933年1月,他們一起在上海成立了“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2月9日,包括任光、聶耳在內的31人當選“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此后他們頻繁相聚,切磋音樂創作。1934年1月24日,聶耳被聯華影業一廠辭退;4月1日,進入百代公司,主要工作是“幫助(音樂部主任)任光的一切收音工作,經常地教授歌者,抄譜,作曲”?李輝主編:《聶耳日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頁。文中括弧里的內容均為筆者所注,后同。;5月,二人組建起百代國樂隊(對外稱“森森國樂隊”);7月,任光受公司委托去香港錄音,“上海的事務,全由他(聶耳)負責”?徐家瑞:《聶耳的一生》,《中原》1945年2卷第2期,第62-71頁,上海:群益出版社。;11月下旬,聶耳從百代公司辭職。1935年1月,聶耳擔任聯華影業公司二廠音樂部主任,4月15日,在黨的保護下,聶耳離開上海,擬途經日本赴歐洲和蘇聯考察、學習;此間,任光在上海百代公司將聶耳的《鐵蹄下的歌女》(4月25日)和《義勇軍進行曲》(5月9日)灌制唱片,聶耳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留日學生藝術聚餐會做報告時熱情推薦任光的《漁光曲》(6月2日);7月17日下午,聶耳在日本東京西南方向55公里鵠沼海濱游泳溺亡,終年23歲。
根據日常生活史視角,任、聶二人的生活工作空間(以上海為中心)和工作內容(以音樂為中心)十分具體。在時間上,他們與普通人一樣過著平凡和重復的生活,但在生活的日常性與綜合性方面,有著普通人所沒有的日常行為,呈現出不同的特征。我們從中觀察這種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歷史問題,而發現了歷史的動力和意義,僅從三點加以分析說明。
其一是黎錦暉城市知識分子身份的確立。任、聶二人的交集其實也與黎、聶二人的交集重疊。倘若沒有黎錦暉的中介,任、聶二人的交集也許會推后甚或不可能發生。客觀上,灌制唱片是任光所工作的百代公司主要內容及黎錦暉憑借唱片推廣其歌舞音樂的需要,黎錦暉與作為音樂制作人的任光因為灌制唱片而建立聯系。20世紀20年代唱片逐漸走入百姓日常生活。繼1927年黎錦暉在法商百代公司推出第一首中國近代流行歌曲《毛毛雨》后,上海社會流行歌曲熱潮升騰;1934-1935年,電臺作為一種新興文化媒介而迅速發展,以唱片為媒介,歌星與流行歌曲逐漸融入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以黎錦暉為代表的都市音樂歌舞創作的盛行,是市民娛樂之需,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近代上海自1843年開口通商,隨著經貿發展,人們的生活環境已與世世代代沿襲下來的傳統生活有了很大變化。商業化的生活方式下,產生了新的生活需要。從1927年到1929年,黎錦暉通過舉辦中華歌舞專修學校、中華歌舞團、明月歌劇社,致力于都市音樂歌舞發展,順應了上海城市日常生活發展之需,迎合了市場,也解決了日常生活之需。從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來看,如果沒有良好的商業化運作收獲,黎錦暉定然難以接納徘徊街頭的聶耳,為之提供生存機會。然而日漸流行的社會新風尚,與世代相傳的傳統禮俗及人們歷來尊崇的倫理多有違背,加之隨后的社會現實和革命運動的發展在基本價值取向上與城市所需新生活大相沖突,都十分容易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這也是造成聶、黎沖突的社會根源。
1932年,聶耳先是通過《黎錦暉的<芭蕉葉上詩>》?聶耳:《黎錦暉的<芭蕉葉上詩>》,《時報》1932年7月13日,載《聶耳全集》編輯委員會《聶耳全集》下卷,北京: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5頁。一文表示了對黎錦暉的不滿,接著在7月22日發表《中國歌舞短論》?黑天使:《中國歌舞短論》,《電影藝術》1932年第1卷第3期,載《聶耳全集》下卷,第48頁。,狠狠地對年長自己21歲的黎錦暉進行了批判。批評持續到了1935年,“作曲家黎錦暉先生本年度印刷的歌曲集也頗為不少……,這可謂一大盛事。這些歌曲都有一個甜蜜的或壯偉的名字,……充分表示了那種玩意兒不過是供人享樂、沒有多少價值的東西。”?聶耳:《一年來之中國音樂》,《申報》1935年1月6日,載《聶耳全集》下卷,第86-87頁。在《中國歌舞短論》見報后,黎錦暉并無怨恨地語于聶耳,“你既然吃我的飯,就不應該罵我!”?鄭易里:《黑天使時代的聶耳》,《新音樂月刊》1949年8卷2期,第9頁,重慶:新音樂社出版。1935年,黎錦暉在給聶耳的祭文中,只字未提二人的分歧,反倒對聶耳稱贊有加,十分寬容:“目不離譜,手不離琴,口不離低唱淺吟”,“耳音”正確,恰巧姓“聶”,“真的比常人多了一雙耳朵”?黎錦暉:《悼聶耳記》,《人生旬刊》1935年1卷5期,第5頁,上海:聲美出版社。。縱觀黎錦暉1936年之前的音樂活動,及聶、黎二人在音樂創作上因趣味不同而存在分歧,但人生之艱辛與無奈恐怕唯有他自己最清楚,在當時,黎錦暉以一種經過世事變遷之后的包容與平靜,彰顯出一位知識分子的品格,具有鮮明的城市知識分子的特征,“城市知識分子是流動的,經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間自由行走,歷史感淡薄,空間感敏銳。”?許紀霖主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頁。
其二是任光兼作曲家、音樂制作人與社會活動家的多重身份認識。?參閱任靜:《任光研究》,西安音樂學院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文中采用音樂社會學理論對這一問題的深入分析。所見諸材料繪就任光一個單純、清晰的畫像。1919年,任光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中國一大批革命志士赴法勤工儉學的經歷一樣,抵達法國后參加左翼人士組織的文化協會,?俞玉滋:《革命音樂家任光及其創作——為紀念任光犧牲四十年而作》,《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1年第1期,第54-57頁。積聚了奔向革命的動力。當他回到祖國后,就充分地利用在外企工作不受國民黨政府檢查的便利條件,為中國革命新興音樂運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作曲家,積極從事革命音樂創作;并以自己所學加強革命音樂創作力量的輔導。?如1933年2月12日聶耳日記所記,“從今天開始,他(任光)改正我很多在‘樂句’與‘味兒’上的錯誤。”李輝主編:《聶耳日記》,第405頁。作為音樂制作人,通過百代制作大量革命歌曲唱片發行,發揮了新興傳媒的載體作用,為革命音樂傳播打開了積極的局面;他灌制大量民族民間音樂唱片,保存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作為社會活動家,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音樂文化組織,爭取和開拓了左翼電影音樂陣地;接濟被捕的“左聯”文藝家家屬,或將私人住宅用來接待聶耳、呂驥、張曙等“常客”,?田漢:《聶耳及<聶耳>影片》,載于田漢:《田漢文集》第11卷,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版,第528頁。保證革命文藝工作者有安全的活動場所,或駕駛私人汽車將同志們轉移至郊外等,掩護同志們不受反對派的迫害;?任光在百代公司的工作也有不順的時候,他所灌制反帝抗日內容的歌曲,一度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干涉,以至于公司不得不將已灌制好的唱片原版毀掉,為此任光被停職2個月。以上材料均見于徐士家:《關于任光生平的一些史料》,《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第55-56頁。等等。
在近代特殊的社會環境里,任光以其專業技能、職業身份和尚處優渥的生活資源,團結幫助了致力于左翼音樂運動的幾位重要人士,在促進進步音樂家的交流、學習和合作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28年,任光成為法商東方百代的高級職員,期間租住在徐家匯華安坊8號的一處花園式洋房里?《民族的號手——任光》,中央電視臺“探索發現”欄目20110111期。任光在哈岡路民厚南里有一套房子的事件,田漢也有回憶。田漢:《聶耳及<聶耳>影片》,載于田漢:《田漢文集》第11卷,第527頁。,有一架很好的鋼琴,還備有一輛奧斯丁牌的小汽車。?楊靜:《嵊州:被“遺忘”的任光》,《安徽商報》2009年12月25日,第B09版。在百代公司,任光的薪資不一定算高,但在當時上海普通人的工資待遇中是比較高的,“中國當時唯一的最高音樂學府‘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校長蕭友梅的月薪是400塊大洋,而任光在百代公司時月薪高達800塊大洋。”?向延生:《“民族號手”任光和他的絕筆之作<別了皖南>》,《音樂周報》2001年1月19日,第03版。冼星海也曾說過,他在百代公司里有月薪100塊大洋,“百代公司待遇的不平(有些技術很差的人薪水比我多八倍)”。據冼星海:《我學習音樂的經過》,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版,第9頁。這里不含其它經濟來源。再看聶耳的經濟狀況,總體上在百代公司要好于明月歌舞劇社。每月除基本薪資外,還可通過寫劇本、文章、演員、教提琴增加財源。如1931年9月5日,聶耳頂王人藝離開明月歌舞劇社的空缺,擔任樂隊第一小提琴,月薪25塊,生活暫時得到保障。到1933年,5-7月份每月收入28塊,寫文字獲得稿費10元;9月份未領工資;10月份是30塊。支出中,如10月份,房租11塊,飯10塊,娘姨2塊,洗衣2塊,車資、零用10塊,總計35塊?1933年10月19日日記。載李輝主編:《聶耳日記》,第427頁;《聶耳全集》下卷,第513頁。;常常出現“已借到下月的錢了”?1933年5月15日日記。載李輝主編:《聶耳日記》,第421頁;《聶耳全集》下卷,第508頁。的情形。由于有了任光的幫助,1934年4月聶耳到百代公司后,“最近收入較豐”?1934年2月24日日記。載李輝主編:《聶耳日記》,第432頁;《聶耳全集》下卷,第508頁。,所以這一年成了他的音樂年。?1934年1月29日日記。載李輝主編:《聶耳日記》,第431頁;《聶耳全集》下卷,第516頁。就在1934-1935年間,聶耳完成了他全部8部電影的配樂創作,為早期中國電影音樂做出了貢獻,創造出了獨具鮮明特色的中國革命新興音樂。
其三是聶耳作為中國革命新興音樂開創者的定位。聶耳到上海2年后,積極與“左聯”文化工作者的接觸,于1933年初在田漢介紹、夏衍監誓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繼1月參加“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后,2月12日與任光、呂驥、張曙、安娥等在滬發起成立“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1934年春,任、聶二人參加田漢發起成立的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隨著左翼音樂運動興起,聶耳的創作熱情高漲,同時不忘加強音樂技能的學習。站在日常生活史中立的研究立場,我們尚能發現,來自黎錦暉及明月歌舞劇社、任光的幫助、影響,特別聶、任二人相識后,從1933年2月分別作出其第一首歌曲,標志著二人同步開始新興音樂的創作實踐,到1934年初步找到創作的形式和風格,是聶耳自身努力學習的結果,也是聶、任二人共同進步、互相影響的結果。從《開礦歌》到去世,聶耳留下了35首歌曲,聶耳在學習的過程中豐富音樂基礎、提升音樂創作水平,?參閱陳聆群:《王人藝先生談聶耳和黎錦暉》,《音樂藝術》1985年第4期,第14-17、25頁;陳聆群:《八十回望——我的音樂歷程》,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梁茂春:《黎錦光采訪記錄及相關說明》,《天津音樂學院學報(天籟)》2013年第1期,第55-71頁;李輝主編:《聶耳日記》;等等。成就了自己的音樂理想,如他進入百代之后創立百代國樂隊而留下的4首民樂合奏作品,顯示了已然掌握多方面作曲技巧。在聶耳僅有的三年不到的創作時間,其所具有的開創性意義,堪稱他自己對中國新興音樂光明前途展望的體現與定位,確證了他在《一年來之中國音樂》一文中袒露的心跡,“新音樂的新芽將不斷生長,而流行的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了。”?聶耳:《一年來之中國音樂》,《申報》1935年1月6日,載《聶耳全集》下卷,第87頁。
結 語
以具象的“人”為核心,在各具個性的日常生活細節中發現歷史。然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圍之大,但再大也繞不開每個具象的“人”及其的生活。所以,以“人”為核心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想從復雜豐富的歷史圖景中敘述社會樣態和具象的“人”的面貌,從追尋歷史事情的發生與發展中,達到實事求是。如同李長莉研究晚清上海社會變遷后所得,“我們需要回到民間社會,回到歷史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去探尋中國社會生活近代化的實態,從中追尋中國社會近代化變革的內在源流”?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引言”第4-5頁。。因此,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緊扣普通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揭示出時代是如何影響固有的生活節奏與社會秩序的歷史。以此檢視近代中國音樂史加強日常生活史研究,貼近社會底層看歷史,深入“人”的日常生活,對于推演出任何時期歷史事情的基本結論都會發現一些之前不被注意的信息,甚至會得出一些不同于既往研究的認識。這樣的研究還不流于瑣碎的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