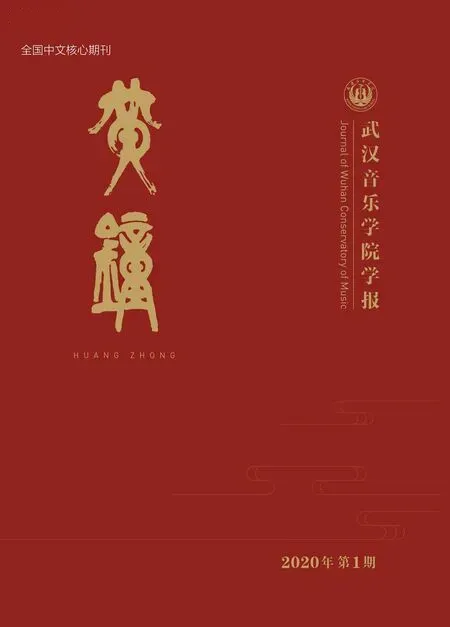杜蒂耶晚期創作中的音高結構探究
——以三部與“時間”相關的樂隊作品為例
劉 鵬
亨利·杜蒂耶(Henri Dutilleux,1916—2013)是20世紀后半葉法國當代音樂的標志性人物。他在創作中忠于自我,追求完美,留下的作品雖不多,但每一部都是精雕細琢的杰作。他的音樂被認為現代而抒情,精致細膩,然而對這種折衷的個人音樂語言風格的堅守,多少使他在激進的20世紀音樂浪潮中顯得有些保守。可當我們對其音樂本質進行深入探索,特別是認真思考其漸進化曲體形式中音高結構的設計及其積極作用后,杜蒂耶的音樂形象便立顯豐滿。
本文擬從其《神秘的瞬間》(1986—1989,為弦樂隊、匈牙利大揚琴與打擊樂而作)、《時間的陰影》(1995—1997,為管弦樂而作)、《時間與鐘》(2007—2009,為女高音與管弦樂隊而作)三部作品入手,對杜蒂耶晚期創作中的音高結構進行細致剖析。
經過對作曲家各個創作階段的比較,筆者認為,以將若干形態各異的音樂片段聯綴成曲的《神秘的瞬間》為分界線,標志了其晚期創作的新的風格突破,即“偏離”了在前期創作中以代表性技法“漸進生長”(progressive growth)為體現的時間綿延特性,而形成具備“瞬間”感的非連續性結構。①關于更詳盡的創作分期研究及其晚期創作中偏離特性的分析,可參見筆者另一篇論文:《突破與重塑:杜蒂耶晚期作品〈神秘的瞬間〉音樂分析——兼論該作在其創作軌跡中的偏離性》(待發表)。換言之,隨曲體結構特征的轉變,晚期創作中音高材料橫向發展的因果關系也相對被弱化,并顯露出在該階段才有的獨特的音高組織關系。從創作時間上看,上述三部作品雖跨度較大,但均屬作曲家的晚期創作。此外,由于杜蒂耶對待創作總是精益求精,因此每部作品的創作周期明顯較長,進而問世的晚期作品也為數不多,而選擇這三部在主題表達(對“時間”意象的關注)和體裁形式(較大規模的樂隊編制)方面都擁有共同特征的作品,對于闡明作曲家晚期創作中音高結構的組織關系具有典型意義。
20世紀90年初,作曲家在通過協商后同意將所有樂譜與資料捐贈于瑞士的保羅·薩赫檔案館(Paul Sacher Stiftung),而隨著文獻的積累,日前杜蒂耶的館藏共劃分為出版物、手稿、信件與研究文獻四個版塊。②保羅·薩赫檔案館檢索系統,https://www.paul-sacher-stiftung.ch/en/library.html。經過檢索(包括國內數據庫)可見,就總體研究趨勢而言,國內外研究動向仍大多關注于杜蒂耶的“漸進生長”技法以及成熟期創作的系列作品,而部分研究雖一定程度上關涉到其晚期創作,③國外代表文獻有——Jeremy Thrulow:“Métaboles as a Fork in the Road:Two Paths in Dutilleux’s Later Music”,Contemporary Music Review,Vol.29,2010,pp.485-496.該文指出作品《蛻變》為后期創作(原作者在文中并未有創作分期之設想,單純指后來之創作)并指出其有機化動機發展下存在“非有機”(inorganic)現象;國內代表文獻有——王穎:《始于理、止于情——迪蒂耶〈同一個和弦〉中的技法特征與平衡美學》,《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第99-113頁。該文對同屬晚期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Sur le même accord》(2002)從音高素材、作品結構及對稱手法等三方面進行分析,并試圖以平衡美學的觀點來解讀作曲家作品中的鏡像對稱特征。但未結合多部作品實例來揭示作曲家晚期創作中音高結構關系的專題性研究。因此,本文擬從代表性音高材料、音高結構的對稱性特點、音高材料的橫向處理手法以及基于中心音或中心和弦的調性布局與擴張等四個方面,來概括其晚期創作的主要和聲特征,一方面是為了便于充分理解作曲家的音樂語言而提供全面視角,另一方面也希望聚焦于音高結構的運用特征,或許能對20世紀現代派和聲語言與創作觀念的流變起到某種綜合性的參照作用。
一、晚期作品中的代表性音高材料
在杜蒂耶晚期作品中,由音程或短音列及其衍生的人工音階是他最常使用的音高素材。在一般情況下,個性化音列的頻繁使用對旋法風格以及塑造樂境具有決定性意義,而隨之不斷疊加則會形成若干人工音階。但作曲家在實踐中并不囿于機械化的運用,反而靈活地將多種音階相互組合、銜接,這意味著核心集合的不同形態特征(即源于同一材料的不同動機音型)在其晚期創作中具有統攝全曲的重要意義。
(一)集合(0,1,4)與增音階
三音集合(0,1,4)是杜蒂耶創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音高材料,其基本型由一個小二度與小三度(或增二度)構成,半音數為1-3,而通過將其循環疊加則將形成“增音階”(augmented scale)。④有學者也稱其為“六聲音階”([美]約瑟夫·內森·施特勞斯:《后調性理論導論》,齊研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161頁)。雖然相關學者的用法為特指,但術語“六聲音階”本身具有泛指意義,故筆者更傾向以“增音階”來指代說明。譜1是對增音階加以細化分類,根據循環核的不同如以音數1-3或者3-1連續疊加,則可得出兩種調式主音不同的增音階(縮寫為Aug-A和Aug-B)。正如前述,杜蒂耶在實際運用中常常會規避調式主音,即每一個音都可因得到強調而占據中心位置,也就意味著兩種增音階之間的界限有一定的模糊性。
譜1 集合(0,1,4)及其衍生音階

晚期作品中增音階的運用,屬作品《時間的陰影》最為顯著。其中,作曲家較多以集合(0,1,4)為核心動機來構建主題。見譜2中下行譜表所示的第三樂章F27⑤由于本文研究對象其部分的出版樂譜未設小節數,在例證時,為便于說明和查證,均采用排練記號、并前后作加減小節數進行標示,如F7+1意指排練記號7后一個小節。處童聲旋律截段,可以看出前5個音屬于音階Aug-A,而到中間部分則平順自然地過渡到音階Aug-B,而隨下一小節音的出現則又回到了之前的Aug-A。顯然,此處是將兩個不同循環核的增音階進行混用,集合(0,1,4)在此處發揮了材料統攝的作用。
譜2 《時間的陰影》F27處童聲旋律
(二)集合(0,1,3)/(0,1,2,4)與八聲音階/九聲音階
三音集合(0,1,3)與四音集合(0,1,2,4)也是作曲家晚期創作中較常使用的素材之一,而根據這兩種集合疊加而成的八聲音階和九聲音階與前述增音階也存在著密切的派生關系。從譜3可見,集合(0,1,3)可視為集合(0,1,4)音程緊縮的結果,而集合(0,1,2,4)則是將集合(0,1,4)中的小三度音程分裂成半音與全音的關系。此外,集合(0,1,3)基本型的半音數為1-2,其循環后將得到八聲音階。⑥此音階也被稱為“減音階”(Diminished Scale),這是因為本質上它是由兩個減七和弦疊加而成,但由于八聲音階的稱謂在學界已有共識,并具備特指涵義,故本文繼續沿用。而將半音數為1-1-2的四音集合(0,1,2,4)加以循環會構成九聲音階。上述兩類音階由于其循環對稱性的特征,移位后自映的可能性較高,因此也被梅西安納入有限移位調式中的調式2與調式3。
譜3 三種音階的派生關系

在杜蒂耶的最后一部作品《時間與鐘》中,第三樂章“最后的詩”第6-9小節,當女高音動情地唱到“我怎么可能離開你”(Qu’il ne me reste plus rien de toi)時,木管組依附著人聲的線條,讓每件樂器從低至高逐層迭入以形成“音色旋律”(見譜4)。這段旋律分別是由兩個八聲音階構成,彼此為上移減五度的移位關系,而木管聲部則通過線條的保持,最終形成了一個稠密的音簇式和聲。
譜4“最后的詩”第6-9小節縮譜

九聲音階則在《時間的陰影》第二樂章“罪惡天使”中有所使用。在作品F11處,弦樂聲部分別圍繞著三個音作上下半音的音簇,而隨之累積,和聲也逐漸順暢地轉換到兩個九音和弦(見譜5中的和弦A/B)。從譜5所展示的音高材料關系中可見,每個三音音簇所圍繞的中心為增三和弦,若將這些音簇依序排列將構成一個以半音數1-1-2為循環的九聲音階。當這個累積而成的音塊運動到和弦A/B時,杜蒂耶開始往其中注入全音階的因素,和弦A上方四個音為增音階、下方五個音為全音階,而和弦B上方六個音為增音階、下方三個音為全音階,這體現出了增音階在縱向和聲上與其它材料靈活混用的處理方式。
譜5“罪惡天使”F11-F12音高材料簡化譜

(三)集合(0,2,7)/(0,1,2)與自然調式音階/半音階
縱觀杜蒂耶整體創作,三音集合(0,2,7)與(0,1,2)具有相當代表性,而作曲家在晚期創作中也經常以其來進行旋律或和聲上的設計。如譜6所示,集合(0,2,7)在八度范圍內共有四種排列形式,其中打上星號標記的四五度疊置關系與集合(0,1,2)的音簇式排列一樣具有以中間音高為軸的對稱形態特征。此外不難發現,當任意音高連續7次的四五度疊置后,必然構成自然調式音階,而集合(0,1,2)也相似,若進行連續12次的疊置,十二個半音將完全呈現。
譜6集合(0,2,7)/(0,1,2)及其衍生音階

自然調式音階的實際使用以《時間的陰影》第一樂章“時光”為代表。整個樂章不僅都建立在一個以A自然大調音階縱向疊置的中心和弦之上,同時在中段,管樂聲部的旋律還會展現出從自然調式逐漸衍展至全音階或其他調式音階的態勢(見譜7)。譜7中下行譜表是此處和聲的簡化形式,注意這里的和弦往往是以純四度關系進行疊置,如中提琴演奏A3-D4;小提琴ⅠⅠ為B4;小提琴 Ⅰ為,即集合(0,2,7)核心音程關系的體現。該和弦長時間持續,并出現多次,其它和弦均作平移運動,可見杜蒂耶的和弦序進策略相當樸素且極富效果。
譜7“時光”里的和弦進行


至于半音階在縱向關系上的使用,在其晚期作品大致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作為十二音和弦。為了獲得較好的音響共鳴,其排列形式常常是在下方使用距離較遠的四五度疊置關系而上方為半音或全音的疊置關系(這似乎與泛音列的分音分布情況有互通之處)。二是形成半音音簇。就本文研究所涉及到的三部杜蒂耶晚期作品而言,由于完整的十二音音簇密集而尖銳的音響效果不太符合作曲家本人的和聲意趣,因此鮮少出現,但是其部分截段在特定的情境中也有著極其出色的發揮。
(四)三全音、全音階以及材料的綜合使用
由于全音階缺少傳統調性功能意義上的導音解決特征,所以其朦朧、晦澀且兼具色彩性的音響屬性讓它備受法國作曲家們的青睞,杜蒂耶也不例外。假如我們對全音階任意相隔兩個音級的音高進行提取,則必然會得到三全音的音程關系,而對于三全音的運用甚至可以說貫穿了杜蒂耶的整個創作生涯。
譜8 三全音在杜蒂耶部分作品中的運用

譜8是將三全音在杜蒂耶各個創作時期的運用情況予以展示:a)在《鋼琴奏鳴曲》一開始,主題穩固于兩個低音的交替運動中,而當主題第二次移位陳述時,低音進行則轉換到三全音B-F上,其目的是為了在情緒與和聲方面形成鮮明對比;b)在《第一交響曲》第二樂章“諧謔曲”,三全音則是起到了勾勒主題輪廓的作用,樂章一開始由低音弦樂撥奏出三全音,然后中提琴接著從C跑向至的旋律進行在音樂中相繼重復多次;c)所屬作品《蛻變》更為甚之,其三全音無論是在和聲序進還是旋律發展中都占據了核心地位;d)屬于《時間的陰影》,一開始主題圍繞音為中心予以陳述的同時,定音鼓與倍大提琴始終在低音區奏響的三全音輔以支撐,并且同樣的三全音進行還將作為“記憶信號”間或穿插于其他段落,如第二樂章末與整個第三樂章。
有些時候杜蒂耶還會將前述代表性音高材料進行綜合處理,或并置或結合,以生成出新的材料關系。譜9來自《時間的陰影》末樂章“藍色屬性?”,作曲家將第二樂章F11處三音音簇所疊置成的九音音階與第三樂章童聲旋律的增音階重構成一個新的半音數為1-2-1-3-2的人工音階,并且經過移位攀升,最終形成了類似于童聲主題旋律輪廓的、并同樣以E音作為起始或結束的音高材料。而除了將多種材料進行兼容外,作曲家也時常在某個音階或音列上或剔除某音、或附加上異質音,比如所謂“全音階+1”和聲的構成,即在全音階基礎上額外添加一個小二度音程以進行不協和的、半音性的干預。
譜9“藍色屬性?”F69處音高材料

上述所列舉這些代表性材料僅能說明杜蒂耶對某些音高結構的偏愛,而至于其所使用的原因、審美意識以及材料在時間進程的個性化展衍方式將留待下文繼續探討。
二、音高結構的對稱性特點
對稱是構成宇宙萬物的自然規律。在音樂史發展的各個階段,音樂對稱的現象不勝枚舉,尤其是在20世紀音樂中,隨著調性的瓦解乃至消失,對稱思維對于構筑音高結構和其他音樂要素的重要性也就逐漸凸顯出來。其實,當我們在探究杜蒂耶的代表性音高材料時,也就一定程度地展示出作曲家對對稱關系的喜愛。如圖1所示,在音級時鐘的幫助下,可見杜蒂耶所常用的各音高材料都以極為形象的方式展現出對稱的特點。
談到對稱,杜蒂耶本人總是提到“鏡像”(Mirror)的概念,他通常以此來解釋逆行或倒影的現象:“‘鏡像’的概念或者稱之為逆行的運用,即是將整個樂句倒轉過來,似乎也倒轉了時間”。⑦Henri Dutilluex:Music-Mystery and Memory,conversations with Claude Glayman,Translated by Roger Nichols,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2003,p.71.從其言論可見,作曲家對鏡像對稱的使用始終與記憶、時間相關聯。而筆者則根據作品所涉及的具體情況不同,將對稱方式從小到大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音級關系或音樂材料上的對稱。如集合(0,2,7)與(0,1,2)可被排列成以中心音為軸兩端呈四五度或小二度的對稱關系。另外如集合(0,1,3)與(0,1,4),其本身雖不具對稱性,但由它們所組成的八聲音階和增音階都兼具對稱性特點,這是微觀上的對稱關系。
2.橫向時間的對稱。與梅西安不可逆行節奏不同,杜蒂耶在晚期創作中常常不會進行嚴格的橫向對稱處理,而總是施加前后變化以形成不規則的對稱關系。如譜10《時間與鐘》的間奏曲,一開始大提琴聲部奏出固定的七音列(隸屬于八聲音階),其后在第3小節音列為之逆行,節奏相同,但同時附以靠琴碼演奏震音、撥奏等演奏技法來形成變化。第5小節的旋律是將音列原型中的兩個重要音程進行重組,與原型七音列存在著音高互映的關系,而第7-8小節與第一行的音色對比策略相同,但音高與節奏卻是前兩小節的嚴格倒影。總之,此段音樂材料精煉,但并不會感覺枯燥。
3.縱向音高的對稱。縱向對稱時聲部間的距離關系,經常與音樂線條的運動方向及其音響張力聯系在一起。譜11來自《神秘的瞬間》中位于樂章“遙遠空間”與“禱文”之間的片段,作曲家以縱向對稱的方式形成了從較寬廣到向內緊縮的扇形動態(fan-shape),同時速度漸快,力度則從p增至ff,其所蘊含的運動張力得以讓這兩個樂章平順銜接。

圖1 音高材料的對稱關系圖
譜10“間奏曲”第1-8小節

譜11“遙遠空間”F21+1縮譜

4.縱橫關系上的對稱。在《時間的陰影》第四樂章開始處,作曲家以的間隙音為軸使用對稱技法,隨和弦的橫向運動,音響空間也在相繼在緊縮與開放之間變換,同時局部旋律也出現節奏上的橫向對稱;
5.拱形結構的對稱:《時間的陰影》第一樂章根據其音高材料和織體寫法的不同,共劃分了為(ABCBA)五個段落,展現出拱形對稱的結構特點;
6.音色布局的對稱,如后文圖2所示,《時間的陰影》的音色布局具有以第三樂章為中心呈兩端對稱分布的特點。
已知杜蒂耶作品中存在如此多的對稱現象,或可進一步想象,如以作品《時間的陰影》為例,從其最微觀的音高材料上的對稱,到局部的形態對稱、拱形結構對稱,最后放大至作品總體音色布局的對稱,也就是說對稱關系讓杜蒂耶的作品如同俄羅斯套娃一般,層層相套,而對稱性作為聯系全曲的邏輯內核讓之呈現出類似幾何學上的“分形”特征。
三、音高材料的橫向處理手法
(一)在和聲基底上的旋律鋪展
譜12所示,是《時間的陰影》第一樂章“時光”中,整個中段小號聲部隨和聲轉換呈旋律鋪展(Stretched)的演變過程。F2+1處的背景和弦為A自然調式七音和弦,這時小號ⅠⅠ先大致以四度加二度的步態將中心和弦進行鋪展,接著小號Ⅰ以連續三度下行的線條完成了旋律最初的完整起伏。然后在F3處,當和弦平移至F大調七音和弦,小號旋律則隨之變換成級進,下行時則將前樂句材料下移二度并作重復。在第三階段F3+2,小號旋律在F大調七音和弦與A大調七音和弦交替的基礎上陸續增添上與音,而下行時不單將節奏拉長,且連續三度的運動愈演愈烈。最后在F4處,旋律延展為大調音階。我們可以注意到,樂曲中幾乎每個樂句都以全音階片段作為結束,從而有效地將不同的音階式音型給統一起來。最后,鋪底的和聲從自然大調七音和弦轉換至增音階六音和弦。
譜12“時光”中段小號旋律變形過程
(二)利用音程擴張緊縮來進行展衍
杜蒂耶時常會在創作中運用音程擴張(或緊縮)的方式來構筑局部的音響或主題。音程擴張,字面含義是指以音程距離從同度到小二度、大二度……直至延展到八度或復音程的方式來設計主題,反之亦然,如此呈現出從一個焦點向兩端擴散的形狀,杜蒂耶本人把這種形態稱之為“扇形”。而在晚期作品中,扇形形態被冠以音程擴張的方式來表現。如譜13《時間的陰影》的主題設計,其本質是一個呈“音程擴張”的自由十二音音列。旋律從三個音開始,不僅運用了前述童聲主題中的三音集合(0,1,4),并與其輪廓呈倒影關系,而作曲家在設計漸快節奏的同時搭配上從純一度不斷擴張到小七度的音程走向,半音數從1到10遞增變化。從第5小節起,改換為縱向音程擴張的方式,最后在尾部由定音鼓、大管與低音弦樂奏出的連續四度音程,最終停留在持續的中心音之上。
譜13 主題音高輪廓及其音程擴張
(三)通過序列及其變形進行展衍
十二音音列在杜蒂耶成熟期作品如《遙遠的世界》《夢之樹》等作中均有大量出現。但在晚期作品中,這樣的例子雖較少見,但也有存在,如《時間的陰影》第二樂章“罪惡天使”F14處,在小單簧管簡短的華彩中,一個十二音主題得到初次陳述,隨后整個樂隊將其承繼并利用移位、逆行等手段形成了多線條的對位織體。如譜14所示,F16處的長笛與單簧管所演奏的是該十二音序列的原型,而下方的大管與大提琴則是音列進行T2移位后的倒影;在下一小節,有三個聲部層次作堆疊,原型音列的T2移位出現在低音單簧管與中提琴聲部,中音區是演奏震音的小提琴ⅠⅠ和英國管,仍為其倒影,而在高音區的木管則又換為T3移位的逆行倒影。緊接著,木管與小提琴Ⅰ又出現音列原型的倒影,同時大管與大提琴則變成T2移位的逆行,最后由雙簧管、單簧管以及部分弦樂所演奏的原型音列逆行導向了下一個段落。從這僅四個小節的音樂中可以發現,作曲家對序列技術掌握的嫻熟程度以及他在變形過程所賦予不同樂器或組合、或對立的音色層次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其他數值關系的音列也在其晚期作品中有所使用,如譜10中的七音列。
(四)利用局部的對稱關系進行展衍
前文已提到音高材料內部的對稱性特征,此外杜蒂耶還會運用局部的聲部對稱關系來進行發展。譜15即《神秘的瞬間》“回聲”樂章F8處,可見大提琴與中提琴聲部為WT0音階小提琴聲部WT1音階此時音樂始終以鏡像對稱的方式來推動發展,一開始的九音和弦在一小節后很快地進行到由兩個完整全音階構成的、中間相隔純四度(E-A)的全音音簇,隨后力度突然漸強,原本兩個八度的音響空間被拓展至四個八度,之后又通過漸弱的滑奏收縮回來,而兩個全音階也相應上下替換了音區位置(見譜15)。
譜14“罪惡天使”F16處十二音音列原型及其變形

譜15“回聲”F8處縮譜

(五)通過主題疊置加以展衍
熟悉的主題面貌在杜蒂耶筆下并不會刻板地重復,而是在不同語境中被賦予新的特質,并時而通過將同一主題的若干變體或不同主題進行疊置來進行發展。譜16出自《時間的陰影》末樂章,在F62前后,由小號獨奏與大提琴的應答樂句牽引出了各樂章主題疊置的段落:在上方裝上弱音器的銅管延續了之前弦樂上演奏的第四樂章“光之波”的主題,而古鈸隨即進入,其前4號以時值擴大的方式間插地對“光之波”主題進行重復,而后7號音則混入樂隊,與高聲部旋律進行重疊。小提琴Ⅰ在高音區被要求以盡量抒情地拉奏出了近似于第三樂章童聲旋律的主題樂句,至此多個主題被有機地疊置在了一起。
譜16“藍色屬性?”F62處各主題疊置

(六)不同展衍手法的綜合處理
譜17是根據《時間與鐘》第一樂章的和聲進程所做的材料簡化譜。可以發現作曲家在此章中所使用的音高材料極其精簡,其本質上僅使用了兩種材料元素:一是調式音階(即a旋律小調音階,命名為材料x),從該調式音階中所截取并進行T11移位的五聲性材料x-1,將構成從第26小節開始的模擬鐘聲的和聲效果,同時其五度關系疊置的較空泛的音響也區別于前后密集排列的和聲進行;二是三音集合(0,1,4),筆者將它以及由它自由派生的“母音階”命名為y,其半音含量為1-2-1-2-1-1-3,而這個“母音階”包括了三種不同組合關系的“子音階”,如y-1是根據軸心音A向兩端拓展(0,1,4)集合而成,y-2仍是兩種循環核的局部堆聚,y-3則為完整的增音階。由這些音高材料縱向排列而成的和聲分布于作品的各個角落(和弦下方標志為其材料歸屬),它們或通過移位、截斷、重組、并置以及變化重復等手法,無論是密集還是離散,但源出關系始終一致。
綜上,杜蒂耶在對于音高材料的選擇可以說是極度精煉,但實際上呈現出的形態面貌以及音響效果卻又豐富多樣,想必這與作曲家在對待代表性音高材料時所賦予其對稱性特征以及靈活多變的展衍處理有關。總之,有限的材料鑄就出了杜蒂耶獨特而無限的音響世界。
譜17“時間與鐘”的和弦序進


四、基于中心音或中心和弦的調性布局與擴張
中心音,一如魯道夫·雷蒂所言的“流動的主音”,⑧[奧]魯道夫·雷蒂:《調性、無調性、泛調性——對二十世紀音樂中某些趨向的研究》,鄭英烈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頁。確實具備流動性,作曲家可以在喪失功能和聲和傳統聲部進行的音樂創作中,通過中心音的強調以展現上下段落的關聯性。而中心和弦則要么是建立在中心音上,要么是以相同(相近)的縱向音高材料與和弦排列所組成。中心性的獲得,從廣泛的意義上講,只要頻繁陳述、或保持一定長度、或出現在極端音區、或增大音量以及在特定節奏節拍位置強調某音,就會優勝于其他音。而在杜蒂耶的實際操作中,根據其形態特征可大致歸納為以下幾種方式:長時間徘徊在極低音區和極高音區的“錨音”(anchor note)和“云音”(cloud note),前者如《時間的陰影》第一樂章開頭,后者如譜18《時間與鐘》中飄在高音區的小提琴泛音;旋律主題的起始、結束音或作為核心并上下環繞的“支點音”(pivot note);或在旋律中不斷企圖毗鄰的“目標音”(target note)等等。關于中心音的表現方式實則已是不言而喻的事體,因此筆者將視野更多關注于杜蒂耶對某些中心音的使用頻率及其在結構布局所發揮出的作用。

圖2 《時間的陰影》中心音及音色布局
圖2部分展示出該作的主要音色布局,呈現出以第三樂章人聲、木管為中心,兩端對稱的設計。而其中心音的分布情況大致如下:在第一樂章“時光”中,除個別的極少段落外,中心音始終貫穿,并在第二樂章后半部分閃現于背景層面,最后在第五樂章中回歸,進而逐漸蔓延至所有樂器,可以說它孤獨地主導了整部作品。而在第三樂章之后的間奏曲中,杜蒂耶采取了所謂的單音音樂寫法,將同一個音散布于各個樂器之間串聯著,形成了色彩一趨一變的音色旋律。與意大利作曲家謝爾西(Giacinto Scelsi)的單音音樂不同,在筆者看來,謝爾西強調的是單音尤其是與各微分音之間的音響微差及其封閉自設的冥想意味,而杜蒂耶在整個間奏曲中的做法(他幾乎是第一次大范圍地運用單音寫法)無疑有著調性布局上的安排,由此形成了宏觀上的類似于主屬關系的調性結構。
再看看《時間與鐘》的情況。譜18是第二樂章“面具”的和聲序進分析,第1小節低音弦樂以三全音關系進行,而和弦則是由集合(0,2,7)疊置而成,而在最后的第40小節,雖然和弦變得更加復雜,但其三全音關系的走向與一開始遙相呼應;而第6小節當女高音唱到“升起”(s’élève),旋律便進行小九度跳進(E4-F5),此時出現的四音和弦有著固定排列形式(即純四度與增四度疊置,并附加一個二度音程)。第7小節的跳進亦是對人聲旋律的模仿,可以說杜蒂耶的和聲用法在這里通常是依附于主題,進行平移,因此具有色彩性和聲的特點。而在第9至11小節,弦樂開始逐層迭入以構成六音和弦(0,1,3,5,7,9)——由集合(0,2,7)與第6小節中的集合(0,2,6)并構而成——緊接著管樂以六音和弦為基底出現了一個短促的十二音和弦,這仿佛是唱詞文本中所描述的觀看者在面對面具時心里所激蕩出的回聲。
此外,在這首僅46小節的歌曲中,起碼有一多半的段落都埋伏著中心音,如該樂章一開始的強拍往往出現的是由豎琴和長笛持續演奏的音,以及若干段落中人聲旋律的起始音也如是。甚至在第22小節,如譜19所示,這個中心音的強調愈發明顯:小提琴Ⅰ演奏的人工泛音飄在最高音區,而小提琴ⅠⅠ重復演奏的八分音符節奏型讓其更具運動感。而在第37小節,就在女高音開始改以唱念的方式式,定音鼓、豎琴以及大號出現了持續的A音(為等音),似乎起到了某種屬音的意味。最后,弦樂聲部演奏的以A為低音的五音和弦短暫進行到三全音關系的D音上(見譜18第40小節),然后又回到為低音的和弦,最后這個和弦又以屬主關系最終解決到F的調域之中。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杜蒂耶晚期作品中和聲表征雖具復雜性,但核心材料卻相當精煉而統一。這些作品盡管從譜面上看具有一定的無調性音樂的技術特點,但由于中心音的貫穿,就好比風箏一般始終被“線”所牽引著,調性感也由此突出。借用高為杰先生的話來講,杜蒂耶的音樂“聽起來似乎是有調性的,但從技術層面上分析卻大多又是無調性的(尤其在稍后期的作品中)。這就形成了他獨特的泛調性風格,非常新穎別致”。⑨高為杰:《法國作曲家迪蒂耶的兩部交響曲》,《音樂愛好者》2004年第9期,第22頁。Henri Dutilleux的中譯名包括杜蒂耶、迪蒂耶、杜迪耶、丟蒂耶、杜悌尤等。本文采用第一種譯名。
譜18“面具”和弦序進分析

譜19“面具”第21-24小節縮譜

結 語
縱觀杜蒂耶三部管弦樂作品的音高結構設計及其組織特征,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無論是從橫向還是縱向的聲部關系來看,短音列及其派生的人工音階如增音階、八聲音階、九聲音階、自然調式音階以及半(全)音階等在其創作中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建構動機主題時發揮了重要的凝結作用;
其二,這些代表性音高材料內部都存在對稱性的結構特點,這體現出作曲家所追求的平衡的美學觀念;
其三,從作曲家對待音高材料并為之展衍的過程中可見,其手法豐富多樣。而且,晚期作品中的音高材料及其對稱技法等創作特征并非是孤立而割裂的,反而是與前期創作一脈相承。但無論是材料之間的關聯度與復雜度,還是織體、結構設計等方面都有簡化的傾向。⑩據美國音樂理論家倫納德·邁爾(Leonard B.Meyer)觀察,作曲家的晚期創作之所以會趨于簡約,一方面是因為作曲家已然到了不必彰顯自我與標新立異的年齡,一方面是因為生理機能的衰退的影響,而需要在作曲手段的強度與頻率的選擇上減少精力。其觀點原引自Leonard B.Meyer:Style and Music:Theory,History,and Ideolog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9,p.26.
其四,從調性關系的安排來看,不同結構的材料在交疊組合的同時勢必會導致調性的模糊,但作曲家對某個音進行強調,或者以某種排列形式的和弦為中心,甚至在隱伏的傳統主-屬關系的多重效應下,則呈現出一種既有傳統味道、但又極富現代感的音響效果。
有關杜蒂耶晚期作品的音高結構及其變化展衍的研究,本文僅是一個局部切片,尚有很多問題未能細表。但從筆者的根本立場來講,是希望通過這個局部的視角來透視出杜蒂耶晚期作品中部分的和聲技法與觀念問題。此外,事實上杜蒂耶的晚期作品在其整體創作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但如前所述,現有研究尚少,故在此拋磚引玉,進而亟待更多學者予以關注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