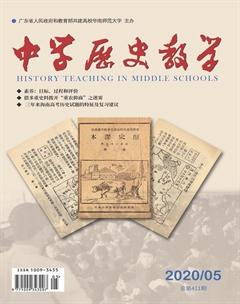歷史解釋中的“個性與通性”
胡斌
歷史由具體時空下的一系列事件和人物所構成,這些史事相互關聯形成歷史脈絡,成為某一特定史事發生發展的歷程。只有將歷史事件置于歷史進程中,才能顯示其存在的意義。德意志帝國經過數百年融合、戰爭終于走上統一的道路,建立了君主立憲體制。如教材所言,德意志民主政治是不徹底、不完善的民主,帶有一定的封建保守因素,但是細看其中的條款,其帝國議會由成年男子選舉產生,從選舉范圍看其民主化程度在當時的世界上是較為突出的。此外,德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國家福利政策、保護工人利益的國家,這與德國保守、專制的印象有一定的差異。從特殊史事出發,探尋歷史的矛盾與沖突,有助于澄清歷史發展的脈絡,從歷史的角度盡可能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看待和理解過去的事物。
一、“個性”的歷史:德意志用自由終結自由
我們先來基本回望一下德意志統一的過程,在鐵血之外,其實曾經有過議會協商、民主統一的嘗試,但時代的發展、德意志民族的狀況和民族主義的情緒使這樣的努力注定以失敗告終。德意志在羅馬帝國覆亡以后,曾經有過長時期的集權統一階段,從法蘭克王國到東法蘭克王國、再到神圣羅馬帝國,直至1356年,盧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在諸侯的壓力下,頒布“黃金詔書”,正式確認諸侯選舉皇帝的權利,承認諸侯在自己領地內的絕對君主權力,最終使帝國成了“眾多獨立邦國的松散結合體”。[1]組成聯邦議會來完成統一曾是德意志發展道路的一種選擇。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像霹靂一樣擊中這個叫德國的混亂世界。”[2]它用戰爭的方式喚醒了德國人的民族情感,也大大動搖了德意志地區的封建制度。法軍所到之處,舊的封建主義因素被廢除,宗教信仰自由、貿易自由等原則得到確立。以普魯士為代表的一些邦國也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走上政治改革之路,向資本主義轉變。1848年5月18日,全德國民議會在法蘭克福正式開幕。德意志議會的出現是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它代表著德意志民眾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議會協商,實現統一、實行君主立憲制度。但是,這也注定了該議會最終失敗的命運。那個時代的民族主義者倡導國家至上、威權政治,尤其在德意志四分五裂的情形下,民族問題一開始就成為議會的焦點,代表們無所休止的爭論讓人失望,人們普遍感受到議會的爭執不可能帶來國家的統一。1849年,當普魯士國王拒絕接受議會授予的德意志皇帝稱號以后,法蘭克福議會被迫解散,意味著要求“自上而下”地實現全民族統一、實行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德意志失敗。議會自上而下統一方式的失敗,標志民族主義的勝利。之后,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得出結論:“誰要統一德國,就必須征服德國。”在這一背景下,1862年出任普魯士宰相的俾斯麥不顧議會的阻力,強行推進改革,更在普魯士議會中喊出:“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人的決議能解決的,而是通過鐵和血。”在俾斯麥看來,只要政府滿足資產階級革命最迫切需要的國家統一,他們最終會改變態度,自由、民主這些空虛的觀念只要與現實需要相沖突,統統可以拋棄。
統一后的德國憲法卻包含了平等、直接選舉和秘密投票這些民主原則,這在當時是相當進步的,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直到1884—1885年選舉改革議會,才基本實現了男性普選權,又是為什么呢?這就要從制度的主要設計者俾斯麥說起,他不是自由主義者,但也不是民族主義者,他首先是一位普魯士人,他的政策致力于打造強大的普魯士,然后按普魯士的意志實現聯合,他以現實主義者而自傲,后來他被稱為現實政治的一流實踐家。在議會問題上,他雖然粗暴地跳脫了普魯士議會的限制,打擊了自由派。但在統一過程中,為了贏得對邦聯的控制,俾斯麥卻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民主人士。他知道如果要達到結成以普魯士為首的強有力聯盟的目標,需要把任何德意志政治家均為顧及的選民即民眾拉到自己一邊來。[3]工業革命后,無產階級興起,工人運動展示其強大的改造社會的能力,普通民眾已不再是中世紀莊園里任人擺布的農奴。俾斯麥為聯盟設計的憲法規定了兩個議院,上院代表各邦國、下院由男子普選產生。他想利用民眾的支持來加強中央政府以對抗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這使得自由派中產階級感到震驚和沮喪。俾斯麥的政策融合了專制家長制、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德意志帝國表面上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實際上卻是一個高壓極權的大國。在憲法中“沒有包含立憲制度的民意機構務必堅持的權力。它沒有基本權利,沒有稅收批準權,沒有部長負責制,沒有規定議員津貼,代替這些的卻是鐵的軍事預算和聯邦首相強有力的權力地位”[4]。這樣的議會制度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權上,而是建立在普魯士君主專制權力的基礎上,是為俾斯麥個人設計的。所以馬克思在總結德意志政治制度特點時指出,它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并以警察來保衛的、軍事專制的國家”。君主是實,立憲是虛,它的議會雖然具備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形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自由派所期待的自由主義精神在國家政權結構中并未體現出來,還不是真正意義的代議制。[5]
二、“通性”的歷史解釋,歷史教學的靈動和魅力
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都是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進行的,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是不可復制的,但其中有一些史事更具有獨特性。面對這些獨特性史事時,我們不能簡單地歸結于國情或歷史偶然性等空泛的概念化表述,要揭示特點,幫助學生理解其發展的脈絡。因為這些特殊之處,既能反映歷史事件的具體性,又能顯現出其所具有的特殊性。錢穆先生曾說過:“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6]
首先,理解獨特事件要在具體的時空下進行探討。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7]例如本文所述德意志民主政治的主要發展是于20世紀后半期,這一時期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為代表的“雙元革命”席卷歐陸,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思潮風起云涌;主導德國統一的普魯士雖經歷一定程度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但容克地主占據政治統治地位;德意志的廣大民眾在法國革命的刺激下,渴望消除分裂、走向統一,民族情緒與日俱增;此外,其中制度設計的關鍵人物俾斯麥抱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不斷調和不同階級、不同思想之間的沖突,既給予民眾較為充分的選舉權,又滿足無產階級的經濟要求,最終目的是實現德國統一和穩定。這樣的政治制度帶有時代、國情和俾斯麥個人等多重烙印,是歷史合力的產物。
其次,揭示史事的獨特性要著眼于歷史細節。歷史是復雜的、多變的,由眾多因素構成,要了解人物、事件除了在整體的時代發展潮流中理解,更要關注歷史的細節,人物的性格、成長的環境、獨特的社會心態等等都會對史事產生影響。俾斯麥曾利用埃姆斯密電以激起德、法人民的民族仇恨的外交事件,藉以令法國宣戰,發動普法戰爭。1870年普法兩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上產生了矛盾,法國駐普魯士大使貝內德狄帶著法國政府的新指令,來到普魯士國王的療養地——科布倫茨東郊的埃姆斯溫泉,希望求見威廉一世,轉達拿破侖三世的密函“希望陛下能保證,將來不要求這種已放棄了的候選人資格”。但這種無禮的態度,令威廉一世感到驚愕。之后威廉一世就把和法國大使交談的內容,從埃姆斯向柏林發出一份急電給俾斯麥。這時,俾斯麥正在舉行家宴,突然接到威廉一世的急電,在讀過電文后,俾斯麥非常開心,并問參謀總長毛奇是否對法國戰爭有全勝的把握,毛奇作了肯定的答復。于是,俾斯麥拿起筆來修改電文,他刪去電文中“還可在柏林從長計議”一句,在結尾部分加上了這樣的刺激法國的話:“國王陛下以后拒絕接見法國大使,并命令值日副官轉告法國大使,陛下再也沒有什么好談的了。”俾斯麥把這個電文在報紙上公布,并通告駐國外所有普魯士使團,埃姆斯急電的內容很快傳到巴黎,輿論一片嘩然,拿破侖三世被激怒了。1870年7月19日,法國向普魯士宣戰,普法戰爭爆發。俾斯麥成功的把發動戰爭的責任推給了法國人,使自己處于了政治主動的地位。可見,俾斯麥在統一過程中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并不是單一事件。他懂得如何煽動民族情緒,在對立、沖突中實現普魯士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對于獨特史事的理解要把握事件的本質。恩格斯說:“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8]這是指人們是在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歷史的,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的生活條件不是由人們自己選擇的,因而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歷史史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統一的產物。德意志民主政治也是如此,雖然它具有廣泛的選舉權、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但從其本質來看它維護的還是以普魯士容克貴族權力為主體的政治體制,它最終建立了一個威權政治體系,俾斯麥利用了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削弱了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力量,用形式上的民主扼住了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的咽喉,可以說俾斯麥是用民主的方式埋葬了自由。歷史學家西奧多·莫姆森說,通過這些政策,折斷了國家的脊梁。他解放了一個民族,卻未給他們自由。[9]
在歷史教學中,注重歷史框架結構的搭建,強調宏觀敘事,難免會忽視一些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獨特性,實際上,大至文化、族群,小至個人、細事,都有其獨立的“主體性”,他們有自己的生命力。歷史不見了細節、不見了人、不見了偶然性,就只能變成干巴巴的教條,變成了波瀾不驚、毫無懸念的必然結果。[10]只有珍視歷史的偶然、關注歷史的細節、探尋歷史的獨特面,將史事的“個性”與歷史的“通性”相關聯,才能正確地理解史事,做出合理的解釋。這要求教師在教學中一方面要關注歷史的規律、時代特征的構建,又要走進歷史人物的心靈、還原歷史的現場,體現歷史的生動和魅力,通過展現獨特的歷史史事造就更加鮮活、更為靈動的歷史教學。
【注釋】
[1]齊世榮等編:《15世紀以來世界九強興衰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頁。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35頁。
[3](美)菲利普·李·拉爾夫等著,趙豐等譯:《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64、368頁。
[4][5]楊菁:《從等級制到代議制——德國議會制度的演變》,《德國研究》2003年第1期。
[6]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香港:新民書局有限公司,1970年,第2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79頁。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頁。
[9] (美)邁克爾·貝蘭著,葉碩等譯:《帝國的鑄就》,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第447頁。
[10]鮑麗倩:《穿越”現實“與”現場“的歷史理解》,《歷史教學》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