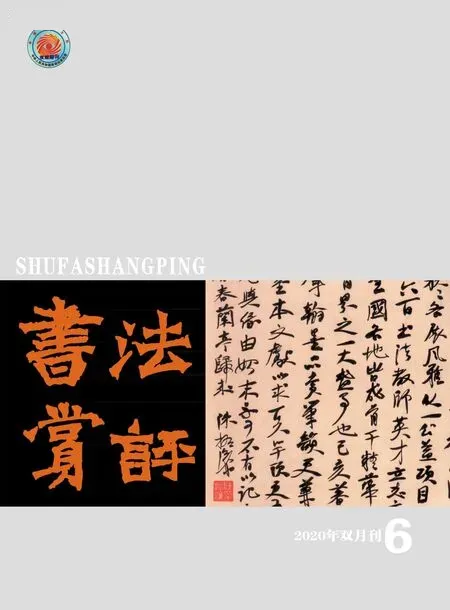從倪元璐、黃道周高堂大軸草書章法的異同看二者審美觀念的差異
鄭志超
章法著眼于全篇的布局,是欣賞一件書法作品最為直觀且重要的方面。章法雖不是字之本身,但章法之和諧妥帖卻取決于點(diǎn)畫與點(diǎn)畫、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起承轉(zhuǎn)合、俯仰照應(yīng)。明代解縉曾在其《春雨雜述》中言及章法:“上字之于下字,左行之于右行,橫斜疏密,各有攸當(dāng)。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斗亂而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破。”[1]可見,章法便是一種組合形式,是對(duì)字里行間疏密、虛實(shí)、大小、欹正等對(duì)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的把握。尤其是明代高堂立軸形式的興起帶來觀賞方式的改變,更需要書家著意章法作為全篇統(tǒng)領(lǐng)的作用,以表現(xiàn)流暢奔放、大氣磅礴的整體氣勢(shì)。故本文著重分析倪元璐與黃道周高堂立軸草書章法上具體處理方式的異同,并進(jìn)而探析章法處理背后二者審美觀念的差異。
一、字密行疏
字距緊密,行距寬疏是倪元璐、黃道周高堂大軸草書的顯著特點(diǎn),同時(shí)也是二人處理章法的相同點(diǎn)。當(dāng)然,這一章法規(guī)律并非倪、黃二人所獨(dú)有,晚明其他草書大家如王鐸、張瑞圖等皆以此種形式為之,這是晚明時(shí)代風(fēng)氣使然。但是也不能簡(jiǎn)單地認(rèn)為倪元璐與黃道周對(duì)字密行疏章法的選擇是盲從跟風(fēng),這其中必定包含著二人審美觀念以及點(diǎn)畫、結(jié)體特點(diǎn)的影響。
首先,字密行疏的章法形式形成強(qiáng)烈的黑白對(duì)比關(guān)系,字間的緊密凝重與行間的寬綽空靈更加突出視覺上的沖擊力,猶如“疏可走馬,密不透風(fēng)”之態(tài)。其次,倪元璐與黃道周的點(diǎn)畫與結(jié)字特點(diǎn)也決定著對(duì)字密行疏章法的選擇。孫過庭《書譜》嘗言:“一點(diǎn)成一字之規(guī),一字乃終篇之準(zhǔn)。”[2]點(diǎn)畫約定著結(jié)體的形成,結(jié)體又決定著章法的選擇。倪元璐的點(diǎn)畫或擦或揉,中側(cè)互用,方圓兼施,疾澀并至,給人一種剛勁暢達(dá)、蒼勁圓渾之感,同時(shí)伴隨著一些撇畫、豎畫有意識(shí)地凸顯夸張和顫筆帶來方向的細(xì)微變化,使得其點(diǎn)畫在酣暢流動(dòng)中又盡顯跌宕頓挫之態(tài),故倪元璐點(diǎn)畫的豐富性與耐看性較強(qiáng);黃道周的點(diǎn)畫方折勁峭,糾繞緊結(jié),常常增加更多的“絞轉(zhuǎn)”以表現(xiàn)生辣樸茂之感,雖不及倪元璐“變態(tài)”的更為強(qiáng)烈,但也表現(xiàn)出較多的變化與豐富。所以當(dāng)二人著意突顯點(diǎn)畫的審美特點(diǎn)時(shí),行距寬疏所形成的大面積“余白”便給了點(diǎn)畫足夠的展示空間,試想如將行距壓緊,點(diǎn)畫的表現(xiàn)便在整體的黑中消隱下去。同時(shí),二人的結(jié)體方式也決定著對(duì)字密行疏章法的選擇。以倪元璐《贈(zèng)毖軒題畫詩軸》(圖一)與黃道周《石城寺諸友過集》(圖二)為例,其一,二人字勢(shì)幾乎皆向右上傾斜,且多數(shù)行草雜糅,個(gè)字獨(dú)立性較強(qiáng),不似徐渭草書那樣打破字形相互穿插以求緊密蕭散,倪、黃二人的字勢(shì)決定其章法并不適用于壓緊行距。其二,劉熙載曾在其《書概》中將結(jié)體分為內(nèi)抱與外抱:“其有若弓之背向外,弦向內(nèi)者,內(nèi)抱也;背向內(nèi),弦向外者,外抱也。”[3]倪元璐的結(jié)體幾乎成內(nèi)抱趨勢(shì),視覺感受上仿佛有一股勢(shì)由內(nèi)向外發(fā)散,此時(shí)行距的大量余白給了這股勢(shì)以緩沖延伸的空間,使之避免碰撞而造成混亂;黃道周的結(jié)體雖中宮收緊大都趨于外抱,但其師法章草,結(jié)體大都取橫勢(shì),其許多字勢(shì)向左右伸展同樣需要行距的余白加以凸顯。所以說,正是字密與行疏對(duì)比下所形成的“一黑一白”以及筆勢(shì)與余白對(duì)比下所形成的“一動(dòng)一靜”將倪、黃二人章法上強(qiáng)烈的視覺對(duì)比效果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圖一

圖二
二、書勢(shì)表達(dá)上的區(qū)別
書勢(shì)即作者對(duì)點(diǎn)畫與點(diǎn)畫,字與字之間聯(lián)系與呼應(yīng)關(guān)系的表達(dá),倪元璐與黃道周高堂大軸草書章法中對(duì)書勢(shì)的表達(dá)具有顯著的差異。劉熙載《書概》中有言:“書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數(shù)字,大如一行及數(shù)行,一幅及數(shù)幅,皆須有相避相形、相呼相應(yīng)之妙。”[4]所以說章法的形成并不是字與字之間“摩肩而行,疊股而坐”的簡(jiǎn)單疊加,而是讓字與字之間在整體中“上下相承,左右顧盼”,使之產(chǎn)生對(duì)比、呼應(yīng)的關(guān)系從而呈現(xiàn)出時(shí)間性與節(jié)奏性。二人的區(qū)別便在于倪元璐主要依靠體勢(shì)來表達(dá),而黃道周主要依靠筆勢(shì)來體現(xiàn),即倪元璐側(cè)重于“意連”,黃道周側(cè)重于“實(shí)連”。
從圖一來看,倪元璐字與字之間真正“實(shí)連”的僅有“可有”“云氣”二字的連接,其余各字均各自獨(dú)立。為了表達(dá)草書連綿不斷的節(jié)奏性與時(shí)間性,倪元璐就不得不在字的體勢(shì)上下功夫。漢字本身的造型特點(diǎn)趨于方正,將字寫的橫平豎直,字內(nèi)空間勻稱,則其所表現(xiàn)的時(shí)間性是靜止不動(dòng)的。若稍加欹斜,在感官上便又有一種搖蕩欲墜之感,此時(shí)依靠上下字的挪讓、穿插使得本沒有筆畫連接的字間發(fā)生呼應(yīng)關(guān)系,加之對(duì)大小、虛實(shí)、粗細(xì)、長(zhǎng)短等對(duì)比關(guān)系的強(qiáng)調(diào),時(shí)間性與節(jié)奏性便由此生成。圖示中“上”“頭”二字以重墨為之,字距較大且各自獨(dú)立,與左側(cè)第二行“昨”“夜”二字壓緊字距形成的字組形成疏密、粗細(xì)的對(duì)比關(guān)系;其后“可”“有”二字實(shí)連,字形相對(duì)較小,又與左側(cè)“泰”“山”與上方“上”“頭”二字形成連斷、大小的對(duì)比;“錦”字單字獨(dú)立,字形再次展大;“崗”“無”二字形成字組,墨色由濃到枯,結(jié)體由密及疏,又與左側(cè)“氣”“美”二字的由枯到濃、由疏及密形成反差對(duì)比;“可”“畫”“圖”三字之間距離進(jìn)一步壓緊形成粘并效果,以及字形體積上的由大及小再放大的差異與左側(cè)“雨”“到”“西”三字的字距相對(duì)疏朗以及由小到大再到小形成反差。可見,倪元璐正是通過體勢(shì)上的變化與對(duì)比關(guān)系的強(qiáng)化以表現(xiàn)其章法的時(shí)間性和豐富性。
從圖二來看,黃道周對(duì)字與字之間聯(lián)系與呼應(yīng)的處理幾乎靠筆勢(shì)來完成,即字與字的“實(shí)連”。開篇“闌”字相對(duì)獨(dú)立,從“春”至“翔”連續(xù)五字一筆書寫完成沒有中斷,上下映帶,不絕如縷,其后雖有個(gè)別字相對(duì)獨(dú)立,但整體上字與字之間還是通過筆勢(shì)來連接。同時(shí),對(duì)大小、粗細(xì)、虛實(shí)、濃淡干枯等對(duì)比關(guān)系也同樣地突出強(qiáng)調(diào),如第二行首字“廓”,其長(zhǎng)度相當(dāng)于左右三字長(zhǎng)度之合,這樣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看得出是黃道周在章法處理上的有意為之,“錢”至“翁”四字連綿不斷,對(duì)粗細(xì)、大小、濃枯、開合的對(duì)比更是表現(xiàn)的痛快淋漓,點(diǎn)畫纏繞彎曲帶來字形的挪位更是給人一種跌宕起伏之感。所以說,倪元璐在章法處理上以“形不貫而氣貫”的方式表現(xiàn)其恣肆奇譎,黃道周則以“形氣俱貫”的方式來表現(xiàn)其姿媚勁峭。
三、款署上的區(qū)別
款署是對(duì)作品正文的補(bǔ)充與說明,雖屬于從屬地位,但卻是章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明代張紳在其《法書通釋》中嘗言:“行款中間所空素地,亦有法度。疏而不遠(yuǎn),密而不近。如織錦之法,花地相間要得宜耳。”[5]可見,款署的大小、位置、長(zhǎng)短要與正文做到和諧妥帖為要。
倪元璐與黃道周在落款形式上的差異如下:其一,文字?jǐn)?shù)量的不同。倪元璐喜落窮款,幾乎不作紀(jì)年,往往只落“元璐”二字,當(dāng)然也有兩行形式的出現(xiàn),但頻率較小;黃道周落款則喜落長(zhǎng)款,內(nèi)容較多,多數(shù)以兩行為之,偶有只落姓名時(shí)也僅僅是因?yàn)檎膬?nèi)容過多導(dǎo)致落款空間不足。其二,款署位置的不同。倪元璐落款位置靠上,加之常落窮款,所以左側(cè)底部往往留有大面積空白;黃道周落款往往靠下,當(dāng)然與其落款較倪元璐更多有關(guān),但具體來看,黃道周在落款處有意將左下余白填滿,甚至鈴印處已經(jīng)逼迫底部邊欄。其三,款署文字大小的不同。一般款署文字大小的規(guī)律是小于正文內(nèi)容,有時(shí)會(huì)出現(xiàn)均等的情況。倪元璐落款形式是符合這一規(guī)律的,往往多字或兩行形式時(shí)小于正文,僅落“元璐”二字時(shí)大致趨于均等;黃道周款署文字的大小卻反其道而行之,突出表現(xiàn)在對(duì)其姓名的放大,如其《洗心詩軸》(圖三)中,落款“洗心詩七夕作”小于正文,但書寫其姓名時(shí)卻沒有順勢(shì)以同樣的大小書寫,而是突然在左下角邊欄處為之,且大小甚至要超過正文,這種情況在黃道周高堂立軸草書作品中屢見不鮮。總體來說,倪元璐喜落窮款、位置偏上等款署特點(diǎn)是其著意突出作品左下方余白,以期表現(xiàn)其空靈奇譎的書法風(fēng)格;而黃道周的款署特點(diǎn)則是有意將左下余白盈滿,以期表現(xiàn)其雄厚樸茂的風(fēng)格特點(diǎn)。
四、章法處理背后二人審美觀念的差異
通過對(duì)倪元璐、黃道周高堂大軸草書章法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這其中的差異性背后隱含的是二人審美觀念的不同。黃道周在其《與倪鴻寶論書》一文中提到:“書字自以遒媚為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足是流矣。”[6]“遒”乃勁健、強(qiáng)勁之意,“媚”乃流麗、姿媚之意,可見,黃道周認(rèn)為書法要“遒”與“媚”相得益彰為高。然而在具體表現(xiàn)上又有所偏重,作為倪元璐長(zhǎng)子又是黃道周學(xué)生的倪會(huì)鼎在評(píng)價(jià)二人時(shí)甚為透徹:“先公遒過于媚,夫子媚過于遒,同能之中,各有獨(dú)勝。”[7]通過二人各自章法的具體處理方式足可印證,倪元璐高堂立軸草書明顯受到金石碑版文字的影響,其點(diǎn)畫的凝澀蒼勁、跌宕頓挫;結(jié)體內(nèi)抱所表現(xiàn)的雄強(qiáng)勁健;書勢(shì)表達(dá)上的以體勢(shì)變化為主,字字獨(dú)立,強(qiáng)調(diào)以上下、左右的空間關(guān)系變化來表現(xiàn)呼應(yīng)關(guān)系皆與碑學(xué)書法的審美觀念相契合,同時(shí)又與“遒”的意含相符。黃道周高堂立軸草書點(diǎn)畫凝練流麗,緊結(jié)勁峭;結(jié)體外抱盡顯崚嶒之態(tài);書勢(shì)表達(dá)上以筆勢(shì)為主,強(qiáng)調(diào)上下連延、氣勢(shì)流貫,清代宋犖曾評(píng)價(jià)其為“意氣流麗”,這正與“媚”的隱意暗合。并且在黃道周對(duì)董其昌的評(píng)價(jià)中也可看出對(duì)“媚”的側(cè)重,黃道周認(rèn)為董其昌雖“臨模之制,極于前賢”,但“率其姿力,亦時(shí)難佳”,此處的“姿”便的是“媚”。所以說,正是審美觀念上倪元璐以“遒”為主、以“媚”為輔,黃道周以“媚”為主、以“遒”為輔,造成了二者在章法表達(dá)上的差異。
注釋
[1]陳涵之.《中國歷代書論類編》[M].石家莊:河北美術(shù)出版社,2016.194 頁
[2]上海書畫出版社編.《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124 頁
[3]上海書畫出版社編.《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711 頁
[4]上海書畫出版社編.《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712 頁
[5]包備五.《中國歷代書法論文選讀》[M].濟(jì)南:齊魯書社,1993.249 頁
[6]李廷華.《中國書法家全集·黃道周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61 頁
[7]陳新長(zhǎng).《倪元璐書法研究》[M].蘭州:甘肅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7.25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