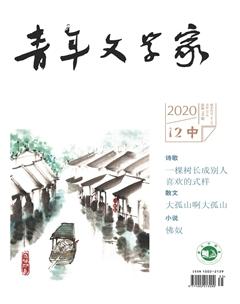“不負責任”作為一種批評
摘 ?要:作為美國當代著名的文學批評家,詹姆斯·伍德有著獨特的批評風格,在《不負責任的自我:論笑與小說》中,圍繞“不負責任”這一關鍵詞,詹姆斯·伍德展示了自己關于喜劇、小說藝術的美學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美學創見。本文擬就通過其批評對“不負責任”概念的論述,分析詹姆斯·伍德批評中“不負責任”的概念,認識其關于“不負責任”的批評思想,指出當中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不負責任的自我:論笑與小說》;不負責任;詹姆斯·伍德;文學批評
作者簡介:范圓圓(1998.2-),女,漢族,安徽安慶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中圖分類號]:I06.750.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5--03
一、批評視閾下的“不負責任”
在《不負責任的自我:論笑與小說》當中,不負責任作為唯一的形容詞,在“自我”、“喜劇”、“小說藝術”之間熠熠閃耀。詹姆斯·伍德無疑想要為這個詞重新定義,這也是他的美學信條之一。“那些人似乎太害怕自我意識,或者說太不相信言詞,尤其不相信闡釋的可能。”[1]1意識的表達依賴于言語,在言語規則修剪后的意識,是否能還原成意識本身,是一個大的問題。個人的意識能否被還原尚未可解,那位于文字之中的人物自我該如何表達?
詹姆斯伍德在他旁枝斜逸的敘述中,展開了關于自我以及不負責任的討論。
在《不負責任的自我:論笑與小說》的前言當中,詹姆斯·伍德將“不負責任”與“自我”相聯系,放置在喜劇的討論當中,“一種看待喜劇中‘不負責任的自我的方式,是審視小說中可靠的不可靠敘事和不可靠的不可靠敘事之間的差異。”[1]9讀者之所以能察覺不可靠敘事的不可靠,是因為有一個可靠的作者在提醒,那么“不負責任”涉及的就是敘事的可靠與不可靠問題,換言之,是讀者與作家在現代小說領域的對話與角力,作家的智識和讀者的智識在此交匯碰撞,豐富著現代小說的呈現形式。
在這里有必要先簡要回溯不可靠敘事的發展歷程。作為一個術語,它最早是由布思在1961年的《小說修辭學》中提出,“當敘述者的言行與作品的范式(即隱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時,敘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2]165在這里布思是就敘述距離的問題來討論敘述的可靠標準的。再之后詹姆斯·費倫、西摩·查特曼等學者進一步發展了不可靠敘事的研究。總結起來可以劃分為兩大研究方法,一是由布思開創,以詹姆斯·費倫為代表的修辭方法,主要從隱含作者的維度上研究,另一為主要從讀者維度進行研究的認知方法。那么再回到詹姆斯·伍德對這一問題的論述當中,在批評伊塔洛·斯韋沃的《芝諾的懺悔》一書時,詹姆斯·伍德用“不可靠喜劇”來形容伊塔洛·斯韋沃的創作。他首先將斯韋沃的“喜劇”劃歸在塞萬提斯與哈謝克的喜劇傳統中,接著用叔本華對喜劇的定義確定了斯韋沃式喜劇的概念,“喜劇產生于我們的觀念和客觀現實之間的不和諧。”[1]112因為認知的差異,喜劇效果出現在自我與真實世界之間的罅隙中,達到了反諷的效果。自私又世俗的中年男人芝諾借助心理醫生回憶并講述自己的過去,讀者順著第一人稱的敘事了解主人公的諸多事件,例如戒煙、娶馬爾芬迪家女兒等喜劇事件,但是由于主人公的性格,讀者又能夠從中推斷出芝諾的不可靠,這即是一種文本間不可靠性,“人物性格類型導致讀者對其可靠性的懷疑”[3],但詹姆斯·伍德認為“不負責任”遠非如此,他發現了斯韋沃敘述中不可靠的“不可靠”。
這種不可靠的“不可靠”來自于讀者認知參與人物自我矛盾的認知當中,伍德將其視為一種獨特的寫作策略。讀者的認知邏輯跳脫了人物自我的桎梏,因而看見芝諾的經驗自我(這里指被芝諾經驗統一的自我認知)與行動自我并不整齊劃一,他認為精神分析帶他回憶,他得以自愈,但悖論的是,他又“錯誤的斷定精神分析缺乏分析他的手段”[1]P15讀者的認知邏輯能夠判斷芝諾的錯誤,他以為自己的行動能夠解放自身,實際上他還是一個被束縛的人。人物沒有對讀者負責(人物本以為他能夠負責)。內向性的分析牽涉的是行動自我的問題,“這個自我進行思慮和去行動,這個自我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是有責任的或不負責任的,這個自我處于實踐世界的中心。”[4]245因而接下來我們有必要理解自我意識的問題,這也是詹姆斯·伍德“不負責任”的批評其二含義,在這里伍德進一步分析了自我與不負責任的關系,牽涉到了作家的“不負責任”。
二、自我對不負責任的演繹
詹姆斯·伍德對斯韋沃喜劇的分析除了揭示不可靠的不可靠敘事,還提及了自我如何上演喜劇的大戲:“人際間的誤解之所以好笑,都是因為它們不僅是表現交流困境的即時鬧劇,更能暗示出自我的虛妄。”[1]111對讀者而言,小說人物的自我在敘述和行動中得以一窺,同時作家的自我也潛藏在作品之中,甚至于作品見證了作家與自身的纏斗。
柯勒律治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他飽受疾病和毒癮折磨,也飽受著自我同一性的折磨。他一開始學習霍布斯、洛克等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的思想,之后又否定了這些思想,轉而接受了費希特、康德和謝林的思想。尤其是康德,為柯勒律治提供了關于自我的新理論。自我是一枚融合了被動與主動兩面的硬幣,柯勒律治據此提出了第一級想象力和第二級想象力,“第一位的想象是一切人類知覺的活力與原動力,是無限的‘我存在中的永恒的創造活動在有限的心靈中的重演。第二位的想象,是第一位想象的回聲。”[5]240在這里,柯勒律治認為想象具有二重性,即有意想象與無意想象,它們是理智與情感的統一,是對立的和諧,然而柯勒律治自己卻無法到達,只能始終向這種和諧靠近,他首先用比喻來超越自身,表達出他的“不負責任”,隨后他又找到了莎士比亞來拯救自我。
在《文學傳記》中他用比喻形容自己創作原則的易變,“就像是一只嬉戲的天鵝,一會兒在河岸上踩踏雜草,倏忽間,又恢復優雅姿態,在明靜祥和的河面上飛翔。”[5]369在《文學傳記》中還有很多這樣的比喻。柯勒律治作為早期浪漫派詩人,一方面順延著18世紀英國自然詩的傳統,將自然的神啟置于自我之上,另一方面,自我的情感、想象又不斷破土向上,這種矛盾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他的詩“是屬于自然的東西和完全屬于人的東西的結合,它是思想的形象化了的語言,而又不同于自然”[6]91。自然的化歸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安放自我的方式。因而他對比喻的使用,可以視為伍德所說的“迷戀一種不負責任的比喻”,他的焦慮和自責在比喻中被轉化展示,這也是他自由生命的體現。
無法實現和諧為柯勒律治帶來的是焦慮與不信任,他有意識的調和恰恰說明了他在憂慮能否對讀者負責,只做藝術作品中巧妙的領路人。他感興趣的莎士比亞成為了一個好的樣板,莎士比亞使人物做到了不負責任。讀者會驚訝于麥克白夫人慫恿麥克白殺人篡位的邪惡,又會惻隱于她每夜無眠的噩夢,這是她良心的燒灼。在莎士比亞筆下,小丑擁有閃光的智慧,瘋子看透了世間的真理。人物的跳脫的獨白不是離題,而是藝術的一部分,柯勒律治看到了這一點才會如此評價莎士比亞,“使用的每一個詞或每一個想法,都不是白費,不是多余……(這些戲劇形成了)最完美、整齊和連貫的整體。”[1]57
伍德以上的論斷來自于他對亨利·詹姆斯的推崇,亨利·詹姆斯認為,小說應該創造“不負責任”的人物,這種隨意變化的自由,是對人物的解放,也是對小說的解放。亨利·詹姆斯看重的是人物的真實,在他們“不負責任”的時候,“才能夠突然活起來,像真正生活里的人,像每一個自行其是、無力自知其無知、又執著于思索的普通人。”[7]文學在經過全面表現集體經驗逐漸轉向表現個體經驗之后,所勘探的是個體生存展示的可能性,這是文學的獨特性所在。這些人物與敘述的含混和復雜,包含了個體的審視,也是一種現代的存在與敘述。由此,伍德從莎士比亞筆下意識流般的漫思下溯,他找到了契訶夫,并提出了他獨特的美學標準——小說中的人物是否能夠擺脫作者的操控,發揮自己的自由意志。
三、小說人物的自由意志:一個美妙的悖論
按照詹姆斯·伍德的美學標準,契訶夫被劃歸為成功的小說家,在他心儀的譜系中徜徉,上承塞萬提斯、狄更斯等人,下接喬伊斯、貝婁等作家。伍德肯定契訶夫筆下人物的自由,“他們可以像真正自由的意識一樣行動,而不是作為文學人物被指使。”[8]123詹姆斯·伍德認為,契訶夫以自己人物的視角看故事里的世界,作家的敘述與人物的敘事合二為一,不僅如此,“人物經常會忘記他是契訶夫的人物,他某一瞬間的思緒似乎飄到了小說之外”[7]。最重要的是,他的人物是忘我的,人物忘了自己處于小說之中,與易卜生的人物相比,不再進行道德的戲劇表演,伍德舉了契訶夫的早期作品《吻》來論證。
《吻》講的是軍官里亞包維奇的故事,這位自卑的青年軍官被一位女士錯吻而獲得了新奇的人生經歷,他翻來覆去回憶這件事,思考錯吻他的女士是誰,最后忍不住告訴了同伴,他本以為他能講很長時間,甚至講到第二天,可惜他很快就講完了故事,還被同伴們懷疑在編造。在最后他對自己貧乏的生活感到巨大的失望——這是由他貧乏的故事引起的思考。伍德認為里亞包維奇不僅是對自己的故事失望,還是對契訶夫失望,由此人物沉醉在自己的情緒中擺脫了契訶夫的故事,實現了自由,這是人物的不負責任,他們拋棄了作為一個小說人物的責任。
但是小說人物真的可以擁有自由意志嗎?奧古斯丁就基督教的問題,對自由意志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在他之后,托馬斯·阿奎納、笛卡爾、大衛·休謨、康德等人都對自由意志有過討論,可以說自由意志向來是哲學中不斷討論的問題。總體來說,關于這一問題有三大論斷,決定論、非決定論與相容論,決定論服從于自然定律,認為人不自由,因而不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非決定論認為“并不是每個事件都有原因,有些事件是自由的,人的決定就可能如此”[9]303。相容論又被稱為弱決定論,它同意決定論的大方向,但是認為“如果我們愿意,我們也可以與別人有同樣的能力來塑造我們的性格”[10]113。當然文學不同于哲學,哲學上自由意志的爭論包含著一個未可知的前提,在各個階段或是由于對上帝問題未可知部分的爭辯(比如預定論、雙重預定論),或是由于對科學上的未可知(比如拉普拉斯預測宇宙的夸口),或是對人本身對了解不夠。當然就這一問題,我們在文學上的了解未必比哲學多,但是有一點很明了——人物是被作家創造出來的。明確了這一前提,可以發現,伍德的標準是一個美妙的悖論。
我們可以類比小說人物和現實人物。處于現代敘述之下的小說人物,他們的世界和現實世界一樣含混曖昧,不再單質干癟。在沒有完全做到現代敘述的作品中,讀者還是能夠看到過往道德諷喻的影子,以及作者操控人物那沒藏住的線。寫作時間的現代不意味著姿態的現代,這往往是不同步的。比如說勞倫斯筆下的查特萊夫人,就會在聽博爾頓太太的閑聊中表明什么才是好小說的標準,這顯然是作者的干預。從這個角度來說,伍德對契訶夫等不將小說人物的經濟功能過分放大的作家的首肯,無疑是有一定的意義的。在存在的視野中看這種寫作,它們撕開了故事對真實世界的遮蔽,把握了世界作為存在的千萬種可能性,展示了世界的復雜與含混,為小說的表現形式作出了貢獻。
可小說人物畢竟不是現實人物。他們真的擁有自由嗎?“人的自由,以及根據自己的意志而行動的自由,其基礎是他具有理性,理性能指導他理解支配他行動的法律,并讓他明白他應該在何種程度上聽從自己的自由意志”[11]195。小說人物的理性是作者給的,他無法按照自己的邏輯系統演繹出所有的故事,換言之,人物的理性是作家的理性,下一秒人物要做什么,也完全由作家來決定。最佳的現實主義小說即使做到讓讀者情緒共振到不能自已,也無法將小說人物化作一個活生生的人。藝術創作畢竟只是一種虛構,始終有個執筆人在凝視著紙中宇宙發生的一切。雖然說小說人物和整個作品的呈現,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讀者大眾、社會風氣、時代條例、作家靈感等等,都會產生影響,但直接決定人物命運的,還是作者。在這個維度上談小說人物的自由意志,無疑是個悖論,小說人物的自由都是作者給的,看起來自由、沉浸于自己故事中想要跳脫束縛的人物,也是作者想讓他們看起來似乎有自由意志而已。伍德所言的人物層面上的不負責任,最多只能對過往小說的寫作慣例不負責任。看起來像在對讀者、作者不負責任的那些人物,實際上還是負了責任,他們的跳脫、沉思、對故事的失望,本身也是故事的一部分。詹姆斯·伍德是認識到了這一點的,還是對契訶夫對批評中,他談到小說人物的自由是有限的,補充說明了一句,“至于這種自由畢竟來自作者的獎賞和操控當然是一個微小的悖論了:不然它從何而來呢?”[8]122伍德明白這是一個悖論,他無力解決,只能擱置它,讓它成為一個美妙的悖論。
總體而言,詹姆斯·伍德在批評中提出的“不負責任”的概念,是具有濃重的個人色彩的,他用一個貌似具有負面感情色彩的形容詞展現了自身的美學偏好,對某些作家分析的角度也不可不謂之老辣精絕。正如伍德自己所言,批評是關于說服的藝術。在驚嘆于他學識的淵博、文本細讀的功力時,也有必要辨明他的批評策略。至于是選擇被他說服,還是持保留意見,就要看讀者與批評家的對話效果了。在這個多元的時代,詹姆斯·伍德的批評貢獻了屬于他自己的美學。
參考文獻:
[1](英)詹姆斯·伍德著;李小均譯.《不負責任的自我 論笑與小說》[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
[2](美)布斯(Booth,W.C.)著;付禮軍譯.《小說修辭學》[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3]尚必武.《西方文論關鍵詞 不可靠敘述》[J].外國文學,2011(6):103—112.
[4](美)羅伯特·C.所羅門,凱瑟琳·M.希金斯著;梅嵐譯.《世界哲學簡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5](英)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著;王瑩譯.《文學傳記 柯勒律治的寫作生涯紀事》[M].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
[6]劉苦端編.《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論詩》[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7]張定浩.《文學能力:向詹姆斯·伍德致敬》[J].上海文化,2019(1):4—8.
[8](英)詹姆斯·伍德著.《破格 論文學與信仰》[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
[9]所羅門;希金斯;張卜天.《大問題 簡明哲學導論 第9版》[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10]黃偉合著.《英國近代自由主義研究 ?從洛克、邊沁到密爾》[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1]尼克洛·馬基雅維利;王偉.《君主論》[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