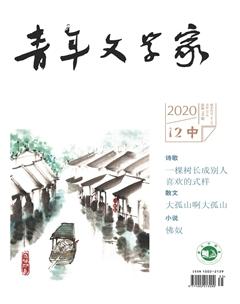余華的兒童敘事小說簡析
摘 ?要:人性問題是文學寫作中的重要命題,許多作家喜歡用兒童形象,作為整個成長過程中的初級階段來思考人性。在余華的創作中,常常讓兒童回到人之初的純潔心靈狀態,去體驗人世的惡,在這種對照中表現出探索的心態。
關鍵詞:兒童敘事;現實;溫情
作者簡介:王文玲(1977-),女,漢族,吉林省長春市人,博士,吉林大學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5-0-02
余華的創作中有眾多兒童敘事視角的創作,以人之初者展示人性異化的過程,與作家的人性和批判主題相契合。余華的兒童敘事作品也有早期和后期的區別,這與作家整體創作風格的變化相對應。兒童敘事很好地為作者的創作服務,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早期創作
余華的總體創作分為前后兩期,前期創作以痛擊現實真相為主。善良是人在兒童時期所呈現的天性之一,余華的作品利用兒童和成年對比的模式,讓兒童向成人世界行走,顯示原本沒有痕跡的心靈被現實的殘酷所涂寫的過程。這顯示了作家探索的心態,不滿足于就事論事,不滿足于描寫表面的虛偽,而是更進一步采取了更有力的對抗方式——“虛偽的形式”。[1]童年的經歷與余華的創作密切相關,但他的創作不以直接回顧童年生活為主,如莫言描寫童年的饑餓感受,蘇童描寫童年的難以忘懷的成長事件。余華的創作是對童年整體經驗的開發。《十八歲出門遠行》和《四月三日事件》都選擇童年期和成年期的臨界點——十八歲,開始切入作品,表現這兩個時期人性狀態的對照,意圖明顯。在這個臨界點上,少年第一次面對冷酷的現實生活,面對人性的殘忍,帶來心靈強烈的震撼。《現實一種》描寫了兒童的暴力心性的一面。《我膽小如鼠》中的男孩不是個性很強勢的人,而具有善良、天真、平和、友善的特點,帶有天真的初涉世事時的陌生和膽小。然而,他不和人打仗,不罵人,害怕暴力,這些特點都成為被嘲笑的理由。甚至他怕狗,怕鵝,不敢爬樹也被嘲笑。在現實中,向善的人性本能被弱肉強食、欺軟怕硬的價值觀念所取代。這展示了天性被異化的道路。“《我膽小如鼠》里的三篇作品,講述的都是少年茫然的經歷和內心的成長。那是恐懼,不安和想入非非的歷史,也是欲望和天性的道路。這時候,世界最初的圖像就像復印機一樣,迅速地印在了這些少年的心靈深處,他們的成長就是對這圖像的不斷修改。”[2]
人的本性具有善和惡兩個方面,具有野蠻和文明兩個方面,正確的價值觀就是要抑制惡的一面的發展。總體來看,余華通過兒童敘事表現了對現實的痛恨,渴望反抗和出擊。死亡、暴力和血腥可以說它們不是寫實的,是作者對世界的抽象概括,是通過敘述進行了轉化而來的。現實的虛偽表象是溫暖、關懷、友愛,真相是被冷酷與惡與充斥。認清現實的本質比單純的呼喊更為必要和迫切,也更加有力量。受難的呼喊要以冷漠敘述中的批判為基礎。兒童的天性之一是快樂和無憂無慮,人們在回想起童年時往往呈現出美好、溫馨的記憶。然而在余華的作品當中,兒童總是處于苦難之中。這是一種對兒童經歷的提取,提取了成長經歷中受難的一面。在現實生活中,即使是處于物質和心靈苦難中的童年,也總貫穿著快樂的時光和經歷。因為這是孩童追求快樂、熱愛游戲的天性的表現。余華筆下兒童的苦難化特點,體現著作家探索與批判的態度,受難的歷程正體現了對溫暖與安寧的渴望。
二、后期創作
余華的整體創作風格從1980年代側重于冷酷的書寫,到了1990年代發生了轉變,側重于溫情的書寫,1990年代的兒童敘事作品也呈現出這種轉變后的特點。1990年代,余華的創作觀念發生變化,更加重視人內心的感受,對人的不幸生活給以同情和關懷,表現出悲憫情懷,評論者也都注意到了這一變化。作者自述到:“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里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活著·前言》)。“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活著·前言》)后期的創作更加注重表現人在苦難面前的堅韌和承擔,這一時期的兒童敘事作品《呼喊與細雨》(1991年)是作家轉變期的產物,顯示了與前期寫作的不同。作品是苦難的“呼喊”,描寫少年在成長過程中被苦難充斥的生活,表現了對生命的憐憫和同情。作品中出現了寫實化的童年生活描寫,不再只是一味地概括化、抽象化敘述。在敘述風格上也改變了漠然和冷酷,出現了以前少有的溫馨和溫情,包括孩子“我”內心的痛苦、落寞、憂傷,這些從始至終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呼喊與細雨》被認為是以后出現的《活著》、《許三冠賣血記》等作品的先聲,是轉變期的重要作品。《活著》等小說關注人的具體生活經歷,展示人的承擔精神與樂觀。
其他作品也繼續著批判的主題,但兒童、童年描寫更多了心靈的刻畫。《祖先》(1993年)講述了人天性冷漠的一面,甚至是母子之情也表現出可怕的冷漠。嬰兒是無助的、最需要關愛的,卻遭到母親的漠視。所有的人對嬰兒“我”置之不理,包括父母,任嬰兒自己啼哭。哭聲引來了祖先來關懷“我”。這表現了從祖先到后代人的發展歷程中,人性的退化。《黃昏里的男孩》(1995年)中,男孩偷盜了水果攤主孫福的一個蘋果,攤主殘酷的懲罰了男孩,扭斷了他的手指。攤主認為自己行為是正當的,遵照了法律與道德意義上的合理原則。然而一個蘋果卻引來巨大的復仇,沒有看到孩子的罪惡是應該具有豁免權的,因為孩子在意識上還不成熟,偷盜也只是出于饑餓。小說展現了人極度自私的一面,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產生復仇的欲望,且具有極大的破壞性。《祖先》、《黃昏里的男孩》等作品雖然仍以工具化的方式運用兒童形象,但兒童形象是真實可感的,表現了心靈之痛。夏中義和富華認為余華的創作中存在著“受難”與“溫情”兩個母題,只是前期的創作傾向于受難,后期的創作則從童年經驗中開發出了溫情:“現在問題已經明了:到底是什么竟使余華母題于20世紀90年代發生如此變異?答曰:源自余華對其‘童年印象與成長經驗的二期開發”。[3]兩個母題都與童年書寫密切相關。
三、敘事意義
余華的兒童敘事作品具有獨特的敘事意義:第一,發揮了兒童敘事張揚童心的功能。作家的創作意圖是以文本中的人物為中介加以實現的。多數作家選擇的文本中介人物是成人,而當作家以兒童為中介來構成文本時,必然要利用兒童獨特思維、意識、行為的特點,或者用第一人稱自述,或者用第三人稱。正是這種制約體現出獨特的敘事功能。兒童敘事的獨特特點體現為兩個方面:首先,兒童看待世界是與成人的角度不同的。成人的眼光是經過社會的教化的,帶著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功利性、社會性。兒童的眼光則是接近人的自然天性的,純潔的、向善的、審美的,體現著人性的自由精神。當代的許多兒童敘事小說反應了童心的世界,反思了成人世界。比如汪曾祺、遲子健的小說,以兒童心性為真善美的象征,正面守護和歌頌真善美的情感,對兒童自然態的生命形象進行了贊揚。其次,兒童具有無知者的身份。兒童受制于自己的年齡和思維,能看到成人無法看到的事件,能去到成人無法去的場景,這使兒童往往成為某些隱秘真相的發現者,從而推動小說的情節發展。兒童對所見所經歷的事情又往往是不理解的,常常無法理解成人規則世界中的許多事情,這樣造成了陌生感,引發讀者的思考。在余華的創作中運用的是第一種張揚童心的功能代表了對純美人性的渴望和對精神家園的向往。
第二、展現了符號化、象征化的兒童敘事形式,不是直接描寫真實可感的童年生活。作品中兒童形象具有符號化的特點,起工具化的作用。從兒童主體性功能發揮的角度來說,兒童主體性體現得不明顯,而是為敘述服務。兒童形象呈現的是外在于心靈的、身份性等方面的特征。如在小說《現實一種》中,一連串的死亡復仇事件,起因于兒童的殺人,這里運用的是兒童身份無意識的特點,淡化故事的法律道德批判。《闌尾》中的犯罪行為來自于兒童單純的、無理性的好奇心,同時強調暴力、血腥、殘忍是人與生俱有的。小說描寫在父親闌尾發炎時,兩個兒子沒有送他去醫院,而是讓他自己做手術。原因是從一則故事中聽到可以這樣做。兒童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惡的,是生命本能狀態的同義詞,是人性真實性的表征。
第三,深刻批判了人性,體現了悲憫情懷和哲理的深度。關于“現實”共識的結論是人是受理性約束的,受親情、感性、良心、法律的約束的。而余華的作品揭露了人內心的真實是非理性的,被自私、個人主義、復仇所主宰。尤其在小說《現實一種》中,描寫了在家庭內部、親屬之間展示的人性的崩壞,給人以驚心動魄之感。仇殺的對象為道德“五倫”中的兄弟一倫。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誼是人性善的基本要求和規范,是牢不可破的人性底線。人們應當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姐妹、夫婦循禮、對朋友忠誠寬容、同道相謀、君仁臣忠。家庭、親情關系一直具有穩定性,因為這是出于對父母之愛和感恩的需要,是人們“愛”的情感的表達。五倫關系的破壞則反映了人性惡的程度。在《現實一種》中,種種人性真實被揭露出來,揭露了文明、理性在人心靈中遭遇的挑戰,這才是真實的現實。余華此時創作遵循的現實觀是顛覆經驗和常識,揭示人性的本質,用夸張和變形來放大暴力和死亡,在“冷靜”的敘述之后是巨大的憤怒。
注釋:
[1]余華:《虛偽的作品》,見《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2]吳炫:《穿越當代“經典”——文化尋根文學熱點作品局限評述》,《江蘇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3]夏中義、富華:《苦難中的溫情與溫情地受難——論余華小說的母題演化》,《南方文壇》,2001年第9期。